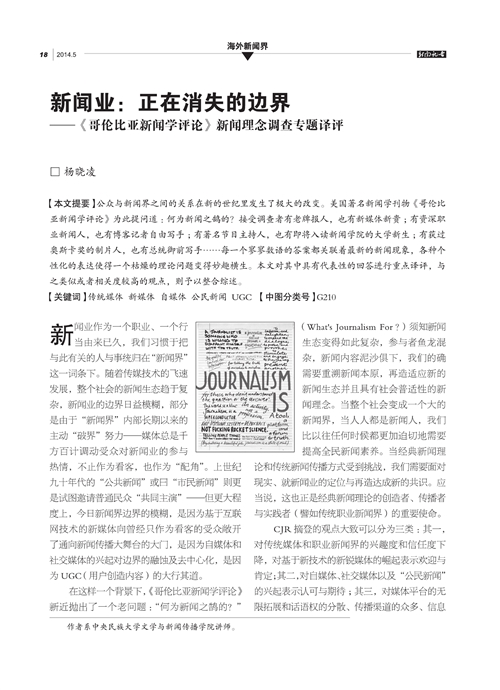新闻业:正在消失的边界
——《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新闻理念调查专题译评
□杨晓凌
【本文提要】 公众与新闻界之间的关系在新的世纪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美国著名新闻学刊物《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为此提问道:何为新闻之鹄的?接受调查者有老牌报人,也有新媒体新贵;有资深职业新闻人,也有博客记者自由写手;有著名节目主持人,也有即将入读新闻学院的大学新生;有获过奥斯卡奖的制片人,也有总统御前写手……每一个寥寥数语的答案都关联着最新的新闻现象,各种个性化的表达使得一个枯燥的理论问题变得妙趣横生。本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回答进行重点译评,与之类似或者相关度较高的观点,则予以整合综述。
【关键词】 传统媒体 新媒体 自媒体 公民新闻 UGC
【中图分类号】 G210
新闻业作为一个职业、一个行当由来已久,我们习惯于把与此有关的人与事统归在“新闻界”这一词条下。随着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的新闻生态趋于复杂,新闻业的边界日益模糊,部分是由于“新闻界”内部长期以来的主动“破界”努力——媒体总是千方百计调动受众对新闻业的参与热情,不止作为看客,也作为“配角”。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公共新闻”或曰“市民新闻”则更是试图邀请普通民众“共同主演”——但更大程度上,今日新闻界边界的模糊,是因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向曾经只作为看客的受众敞开了通向新闻传播大舞台的大门,是因为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对边界的融蚀及去中心化,是因为UGC (用户创造内容)的大行其道。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新近抛出了一个老问题:“何为新闻之鹄的?”(What's Journalism For?)须知新闻生态变得如此复杂,参与者鱼龙混杂,新闻内容泥沙俱下,我们的确需要重溯新闻本原,再造适应新的新闻生态并且具有社会普适性的新闻理念。当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的新闻界,当人人都是新闻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提高全民新闻素养。当经典新闻理论和传统新闻传播方式受到挑战,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就新闻业的定位与再造达成新的共识。应当说,这也正是经典新闻理论的创造者、传播者与实践者(譬如传统职业新闻界)的重要使命。
CJR摘登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对传统媒体和职业新闻界的兴趣度和信任度下降,对基于新技术的新锐媒体的崛起表示欢迎与肯定;其二,对自媒体、社交媒体以及“公民新闻”的兴起表示认可与期待;其三,对媒体平台的无限拓展和话语权的分散、传播渠道的众多、信息的泛滥以及权威性的丧失感到担忧,对传统经典新闻理念表达了追随与坚守的愿望。
杰·罗森:谁在场,谁报道
杰·罗森(Jay Rosen)是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公众与专业媒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以研究“市民新闻”运动并出版相关著作《记者的目标是什么》而闻名。
“何为新闻之鹄的?CJR提出的这一基础性问题比起‘谁是新闻人’这类更常见的问题好一百倍。”杰·罗森写道,“后者至多也就是引发一场课堂上的口水战,前者却值得深入思考。”罗森的意思不难理解——在一个人人皆可借助社交媒体传播新闻的时代,谁是新闻人、谁是传播新闻的主体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传播行为的目的与意义,只要人们就新闻传播的基本功能和目标达成共识,传播新闻的手段、渠道、媒介都只是技术问题而已。
罗森提出了一个“不在场”问题。随着社会生活场域的不断扩大,将有很多事情发生而人们不在场,但是又有知情的需要,这就产生了对信息传递中介的需要,新闻业由此产生。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了那些从前只有新闻记者才能拥有的工具、技能与手段,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谁在场,谁就有资格报道新闻?
“想象一下这样的世界:有‘新闻’,但没有‘新闻业’,也没有‘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新闻’本身比‘新闻业’可是更加古老,更加基本。人们一直都在交换新闻(‘里亚尔托有什么新闻?’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这样问道),但并非从一开始就需要被称作‘新闻人’的专门人士来搜集和告知新闻。只有当我们发现这种社会分工变得十分必要时,什么是新闻业的讨论才开始。”
“问题的关键在于规模。”罗森是指社区规模的变化。在新英格兰只有两百个居民的小渔村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新教堂启用、欧洲船只抵达,这些消息无需专业传播,村民们只要在外头随便转转就什么八卦都知道了。但是社区规模一旦扩大到一万人,情况就不同了。镇子西头发生的事情,镇子东头的人就未必有机会知道,除非有人专事消息搜集与通报。当人类的聚居与日常经济、政治活动发展到超出新闻自给自足的规模时,新闻业就出现了。
无妨沿着罗森的思路继续前行:终有一天,人类公共生活场域之大,会变得连庞大的新闻业也无法覆盖,再多的新闻记者,也无法满足人们对万千世界无数信息的即时发现与传播;而恰在这时,技术的发展又令几乎所有普通公民的手中都有了记录新闻的工具(如纸笔、摄录器材)和传递消息的平台与渠道(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所以,一个人人皆可是记者的时代轰轰烈烈地来临。罗森说:“我在场,你不在,所以让我来告诉你这里发生了什么。”换言之,谁在场,谁就有资格(或者责任)报道。社交网络的繁荣,实际上是给人际传播安上了大众传播的技术之翼,使得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纠缠交错,成为现代生活的奇观。
这对职业新闻界当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如本期CJR编者按所言,职业新闻界曾在九十年代末成功抵制“市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运动,但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更加汹涌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浪潮。“公民新闻”与“市民新闻”不是一回事,杰·罗森给“公民新闻”下的定义是:从前被称作“受众”的人们使用自有的新闻报道工具(手段与方法)向其他人传递新闻消息,那就是公民新闻。①与此不同,此前的“市民新闻”并不是独立存在于专业媒体之外的民间新闻报道活动,而是由专业媒体主导、有限度地邀请市民共同参与致力于解决具体社区的具体问题。换言之,时移世易,当年是专业媒体不愿意带“市民新闻”玩,而现在是“公民新闻”可以不带专业媒体玩儿了。
阿丽安娜·赫芬顿:新闻要带给人们对于世界的真实感知
“新闻要带给人们对于世界的真实感知,以便人们可以参与世界的构建并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无休止的赛马报道、对毫无意义的民意调查的炒作、讲究平衡甚于追求真相,以及仅仅聚焦于什么不可行,都无法带给公众关于世界的真实感知。新闻业也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可行的,这样人们才能在内在欲望的驱动下去帮助邻里,将他们所属的社区以及属于他们的世界建设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
赫芬顿邮报创办人阿丽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的说法包含了对传统媒体新闻内容的质疑与不满,也表达了改革的愿望。赫芬顿邮报是近年闯入新闻业的一匹黑马,2005年创办,2011年被美国在线以3.1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价值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它给自己取了一个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名字,但实际上不是传统纸质媒介,而是一个由私人博客发展起来的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新闻网站”内容特性有三:1.利用网络的聚合功能编辑、整合、链接其他网站的新闻;2.将UGC(用户创造内容)策略用到极致:一众名流在这里开设博客;网友评论被视作网站新闻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个内容平台呈开放、多元状态;力推“公民新闻”,发动用户免费为其提供内容;3.逐渐发展自己的优质原创队伍,向严肃高端新闻领域进军。赫芬顿邮报号称全美有1.2万“公民记者”每天为他们提供新鲜素材,如2008年“赫芬顿”发起Off the Bus项目,募集普通公民作为记者报道总统大选全程,一个采访任务可由数十乃至上百个“公民记者”共同参与,他们将自己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来,交给Off the Bus的编辑,最后由编辑整合成为完整的报道。试问传统媒体,谁家能够养得起这么多的记者呢?
贾科维兹:谁在讲述扣人心弦的真实故事,谁就是在从事新闻工作
“在如今这个数字年代,相当多的人以及各种组织及机构都有办法分享所知。只要有人在讲述扣人心弦的真实故事,就等于有人在做新闻工作。这种工作不限定非得是被称作‘新闻记者’的职业精英团队来做。当然尝试来做这种工作的人必须能讲精彩的故事,也有东西值得分享。一篇轻松戏谑插科打诨的文章,一个让复杂课题变得‘平易近人’的信息图表,或者一篇具有教化、鼓舞意义或者揭示真相的深度报道——所有这些都能让人变得更加敏锐明智,增强人们探索这个世界的能力。与此相应,会促进社会进步。”
SJR集团全权合伙人、CJR监察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贾科维兹(Alexander Jutkowitz)的答案触及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谁有资格报道新闻?真的是谁在场,谁就有资格吗?不,还该有一些限定条件:一是他要有精彩的故事,二是他要能把故事讲得精彩。我们甚至对他们有比对传统职业新闻人更高的期望:期望他们不像传统媒体那样高高在上,故作高深,而是能够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比起万金油式的记者,他们更加权威。而且,作为一个没有边际的群体,他们无处不在。
某种程度上,亚历山大·贾科维兹说的正是他们自己。SJR不是一个传媒集团,但却在生产内容、制造“新闻”,并且进行传播。SJR集团创建于2004年,是一个营销传播公司,核心业务是为著名品牌公司开发数字内容、讲述品牌故事、传播公司文化、培育忠实用户(同时也是这些传播内容的受众)。美国电影协会(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TED以及通用电器、施乐、戴尔等公司都是其客户。2013年6月,它被拥有80年历史的老牌战略顾问公司H+K看中并收购,成为其旗下公司。
新闻业的边界日益模糊。老牌的H+K战略顾问公司和它的主顾们从前或许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他们想要传播的内容,而SJR这类在数字时代应运而生的新锐公司本身就可以是一个媒体,正如亚历山大所说,在如今这个数字时代,相当多的个人或机构都有办法分享他们想要与人分享的东西。传统职业新闻界不再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而今条条道路通用户。
安德鲁·瑞弗金: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将更大程度来自公众的持续挖掘
“在一个为无数信息裹挟着飞速前行的复杂星球上,能够在新闻业中生存的是那些赢得新闻消费者特别信赖的新闻人,这种信赖和遇上雪崩的登山者对经验丰富的山地向导的那种信赖是一样的——他们不保证一定能找到路,但能保证诚实的努力。克朗凯特论断式的口头禅‘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已经过时,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将更大程度上来自公众的持续挖掘,而不是仰仗大媒体的大品牌。效果与影响有时也许仍会与抢先发布有关,但更多时候还是会来自各种洞见可以恣肆漫流的协作网络。”
CJR对安德鲁·瑞弗金(Andrew Revkin)身份的介绍颇有意思:“科学与环境问题记者,在纽约时报网站社论版撰写名为《圆点地球》(DOT EARTH)的博客。”说他是记者,但没说他服务于哪家媒体;说与《纽约时报》有关系,但这关系是在那里开博客。也许这一介绍本身已经反映了当前新闻业的某种状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只要有自己的博客并在上面发布自己的新闻类文章,你就可以被称作是一个记者。
安德鲁·瑞弗金曾经是个音乐人,后来热衷于为一些报刊杂志撰写环境问题文章,现在是纽约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的高级研究员,最具知名度的身份是纽约时报网站社论版博客《圆点地球》的博主。瑞弗金的博客是真正的个人博客,他是“一个人在战斗”。2013年8月,它被《时代》杂志评为2013年度最好的25个博客之一。
瑞弗金对CJR之问的回答与前面几位遥相呼应,普通公民在未来新闻图景中的身影在这种呼应中逐渐清晰。
克里斯·赫斯:任何人都可以做新闻,一如任何人都可以写小说或者搭露台
“与其说做新闻的记者是了不起的人物,不如说做新闻本身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新闻,就像任何人都可以写小说或者搭露台。同时跟写小说或者搭露台一样,做新闻也会因人而异,导致质量参差不齐。最好的新闻应该是诚实可信和引人入胜的,应该增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帮助公民捍卫自由意志,促使我们更加清晰缜密地思考那些影响社会认知的假设或臆断,并且发挥监督问责当权者的作用。”
克里斯·赫斯(Chris Hayes)是MSNBC日播黄金档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以34岁的年龄成为全美电视界最年轻的黄金时段节目主持人之前,他是MSNBC周末早间新闻节目“UP”的主持人。他也曾做过其他一些电视节目的客座主持人和评论员,此外还是美国著名周刊《国家》杂志(创办于1865年,号称美国最古老的周刊)的特约编辑。这位年轻有为的职业新闻人表达了“重业不重人”的观点,与罗森教授不谋而合。不过他同时强调做新闻会因人而异产生质量上的参差不齐,那么谁能提供最好的新闻?这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可以预见的是,“公民新闻”将使整个社会的新闻生态更加丰富多彩,并将促使职业新闻界或曰“主流媒体”追求更高的水准。
本·史密斯:社交网络的高度透明使我们和读者互视互动
“而今新闻的目标跟以往我们所谓‘好新闻’的目标仍旧是一样的:知会人们所未知的,回答人们所疑惑的,告诉人们你所知道的和你能发现的。网络媒体在‘搜索时代’走了一些弯路,但现在我们已经回归到传递信息、开启民智的正途上。社交网络的高度透明意味着我们可以看见读者在问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看见他们如何回应我们的回答。”
本·史密斯(Ben Smith)是一个典型的跨界新闻人,某种程度上也在为新闻业边界的模糊与消失作出自己的“贡献”。他曾是报社记者、周刊编辑和多家报纸的撰稿人;2004年至2006年,他先后开了三个颇有影响的政治博客;2011年12月起出任BuzzFeed网站的主编。他对传统主流媒体知之甚深,同时对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深为认同。
BuzzFeed是一个2006年创办于纽约曼哈顿的社交内容分类分享网站,它是一个可以探测“病毒式内容”(具有超强传播能力的内容)并借助编选程序生产“病毒式网页”快照、实时推送“病毒式内容”的网络技术平台。网站声称“拥有网上最热门、最社交化的内容”,最大内容特色就是“最新网闻以及你最想分享给朋友的各种事情”。它以颁发“徽章”的方式来对网帖进行分类排行与推送,用户可以用LOL(LAUGH OUT LOUDLY,大笑)、EWW(表示厌恶)、AWFUL(糟糕),WIN(获胜),FAIL(失败),WTF(WORSE THAN FAILURE糟糕透了),TRASHY(垃圾),GEEKY(讨厌),OMG(OH MY GOD,哦,天哪)等徽章对内容进行评价,如果某条网帖所获同类评价到达一定数量,相应“徽章”就会出现在网帖的边上,并且自动归类到首页的标签频道下。用户进入该网页的首页,便可以参照“前人”的评价来进行选择性阅读并继续贡献自己的评价值。
这就意味着,用户不仅可以直接评价新闻内容,并且其评价将直接影响新闻内容的下一步传播。由于技术特性的限制,传统媒体是无法真正赋权受众的,无论它多么努力地寻求传受之间的互动。而网媒与生俱来的最大特性就是互动,“受众”于是在这里变成了“用户”,网媒的“可用性”使得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到传播进程之中,这种体验是传统媒体无法给予的。所以,用户们会像玩游戏一样热衷于参与到新闻传播的过程之中,并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便捷分享机制呼朋引伴、成群结队。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这确实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它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从业者和受众纷纷越过主流媒体的边界,流向诸如此类的新媒体,大势所趋,无可避免。
麦克·麦森: 做新闻不需要从业经验
“做新闻不需要从业经验。42岁的李·罗伊·查普曼(Lee Roy Chapman)躬身去翻俄克拉荷马大学西部历史档案里‘90岁’的老文件,这就够了。在资料搜集和追索语境的基础上再加以技术技巧性的提升,更高品质的新闻就产生了。查普曼一篇3500字的文章迫使整个图尔萨面对种族隔离问题……”
麦克·麦森(Michael Mason)于2010年在图尔萨市创办了俄克拉荷马州第一家新媒体公司“大地报业”(This Land Press),这是一个融合性的媒体公司,既办杂志,也做广播与电视节目,还做网店及APP,几乎将所有新旧媒体形态“一网打尽”。该公司以创新性叙事新闻报道著称,内容主要聚焦于他们所在的市镇社区(图尔萨市位于俄克拉荷马东北部,系该州第二大城市,拥有人口近40万)。2011年《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一篇文章称其为“社区级别叙事新闻的罕见案例”,指其“具有将平面内容与网络特性完美结合的天赋”。②
麦克·麦森在回答CJR之问时骄傲地提到了自己公司的一个战绩:2011年9月1日,“大地报业”发表了一篇题为《梦想之都的梦魇:泰特·布拉迪与格林伍德之战》(The Nightmare of Dreamland: Tate Brady and the Battle for Greenwood)的文章,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泰特·布拉迪(1870~1925),曾经被看作图尔萨城的建城先驱、图尔萨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市民、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当地最受信赖的老牌主流媒体《图尔萨世界报》一直都在为他塑造着诸如此类的正面形象——尽管坊间传闻布拉迪与“三K党”③有牵连,但从未有人真正在意。直到2011年,一个从来没沾过新闻工作的边也没发表过任何文章的普通人,通过查阅尘封已久的档案发现,布拉迪竟是1917年图尔萨暴乱的参与者,是“三K党”的成员之一,还是1921年图尔萨种族骚乱的始作俑者。这个名叫李·罗伊·查普曼(Lee Roy Chapman)的“新闻外行”完全出于个人爱好发掘出的这个惊天秘密,令整个图尔萨市都陷入了尴尬,多处以泰特·布拉迪命名的地方被迫改名,而最尴尬的,大概莫过于老牌主流媒体《图尔萨世界报》。
“关于布拉迪的这一切就在那儿,都待了将近一百年了,但就只有一个叫查普曼的家伙会去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图尔萨世界报》成天讲布拉迪的故事,但它只是报道,从不质疑,从不调查。世界报可能认为他们才是新闻业的引领者,我不反对,但我只能给他们打个不及格的分数。这不,踢场子的来了:查普曼没发表过任何文章,他只是出于爱好去探索图尔萨的历史,我们可不可以说他是个新闻人?或者干脆说他才是新闻业的引领者?”
麦克·麦森的回答充满了新媒体去踢传统媒体场子的霸气。所谓正统新闻业,正在经历各种艰难各种批判。“新闻业总有麻烦。评论家接二连三、振振有词地说它处于危机之中,甚至正在失去民主社会的核心地位……这个一度让人自豪的职业之经脉正在被快速磨损,逐渐瓦解。” ④
上杉隆:公众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新闻界一直被当作是各种统治力量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调停者。理想中的新闻界被看作是监督掌权者的‘看门狗’。但是,现实中的新闻界并不总是能符合这种理想。譬如在对福岛事件的报道中,很难心平气和地宣称日本新闻界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伴随着社交媒体出现了众多新的表达平台。在任何一个组织或一波运动中都会有麦秕混杂的状况,谁能将麦子和秕糠分开来呢?恐怕公众已经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上杉隆(Uesugi Takashi)对传统主流媒体的不屑和对社交媒体的推崇显而易见。CJR对上杉隆的身份介绍是“新闻工作者、作家以及日本媒体公司No Border的CEO”。与上文提到的安德鲁·瑞弗金有点类似,上杉隆虽未受雇于媒体但也被称为“新闻人”。英文版维基百科称其为“自由新闻人”(freelance journalist),提及他曾自称得到过NHK提供的工作机会但NHK否认此事,并介绍他曾是日本自民党立法委员鸠山邦夫(Kunio Hatoyama)的助手并曾做过《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的研究助理,著有《新闻业的崩溃》等书。该资料同时指出他因曾发表虚假报道颇受争议:2012年3月他曾在《富士晚报》发表文章称福岛县的两个城市被认为不再适宜人类居住,而这个故事是根据一个冒牌记者(冒充《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的评论写出来的,报纸后来声明收回该报道并刊登更正启示,但上杉隆拒绝为此道歉。
维基百科的资料来源十分复杂,有时难断真假,但无需争议的是围绕这位自由新闻人确有争议存在。一个名叫“日本调查”(Japan Probe)的网站上亦有文章论及上杉隆的福岛事件报道,称其“拙劣、偏颇”,并对上杉隆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如果你关注日本的媒体事件,你可能听说过上杉隆,一个著名的自由记者,他特别喜欢批判这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外国媒体似乎真的特别喜欢采访他,可能是因为他总是拣他们想听的说吧:国际媒体做得比日本媒体好;日本民众是被洗过脑的绵羊,相信政府以及腐败的国内媒体说的一切;只有外国媒体才敢报道真相……诸如此类”,“上杉隆的说法经常被国际媒体不加任何核实和批判性分析就直接刊出,这很不像话,因为日本网民早就曝光他的说法纯属不实之辞。”这篇文章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事例说2012年4月上杉隆接受德国某媒体采访谈及日本的“新闻检查制度”时称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的一张骇人照片被禁止刊发,但实际上日本的两家大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都于2011年3月18日刊发了这张照片。
米歇尔·谢维兹:信息爆炸使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专业新闻人
“你问我是否记得靠报童扔在大门口的报纸卷来了解镇子里发生了什么新闻的日子?我可不记得。报童早就被移动设备取代了。人们现在都靠社交媒体来分享新闻,我们转发来自新闻机构的消息,也转发来自朋友的消息。新闻来源的单一渠道被全民参与的多元渠道代替了。有人认为既然人人都可提供‘新闻’,那么人人皆可担当记者的角色——但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事实上,信息的大爆炸也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职业新闻人。”
“互联网提供了获取新闻信息的快捷通道,但同时它也使不实消息和误导性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善于辨伪存真。这就是我们需要职业新闻人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新闻人这个名词不应被过于宽泛地滥用。”
作为即将入读马里兰大学新闻专业的新生,米歇尔·谢维兹(Michelle Chavez)对于CJR之问的回答与他的身份及状态当然是契合的,否则他有什么理由去选读新闻专业呢?如果人人都可以因为有个社交网络账号就毫不费力地成为“记者”的话。
米歇尔·谢维兹接着写道:“新闻机构被认为能够提供确定结果、确切消息和最新消息,这也就是说新闻消费者可以信赖职业新闻人的报道,尽管也有很多时候,新闻机构在抢发突发新闻时会为了时效性而牺牲准确性。至于报道中的错误,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有必要可以在随后的报道中加以纠正。但是,如果新闻业沉迷于这种速度/时效游戏,那么还有谁在那儿给我们提供可以确信的消息?如果新闻界想要保住公众对他们的尊重与信任,他们必须在两难中做出自己的抉择。”
这表明这个未来的职业新闻人对目前新闻界的状况并不盲目乐观,而是在进行清醒冷静的反思。从上个世纪同质媒体的恶性竞争到今天要在无数喇叭中吹出自己的最强音以留住观众的注意力,新闻界的确需要竭尽全力。但在一片嘈杂之中,冷静的态度和高贵的品格将更加可贵。当人们厌倦了太多的噪音,会重新寻求古典音乐的安慰的。
记住,当声音太多的时候,我们更加渴望一个值得信赖的声音。就像安德鲁·瑞弗金所说的那样:雪崩之时,登山者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山地向导,他不一定总能找到正确的路,但他至少在做这样的努力,而且,他的经验就是他的资本。
埃罗·莫里斯:新闻业比以往更加重要
2004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得主埃罗·莫里斯(Errol Morris)对CJR之问的回答表达了与米歇尔·谢维兹近似的理念:“世道”变了,信息多了,渠道多了,但新闻传播的经典传统更加重要了。
“人们说新闻业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电话和数码相机改变了新闻业。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数据与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包括既存数据以及我们持续不断地生产着的各种数据。遍地都是信息分享。但请不要弄混了——在信息的可得性、信息的分享与新闻传播之间是存在区别的。”
“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技术的发展使得阿布·格莱布丑闻的曝光成为可能。2003、2004年,小巧轻便的数码相机已经普及,人们能在CD上存储几百张照片并用互联网将它们传遍全球。将军上校们意识到事情不妙,企图将虐囚影像收起来烧掉,烧CD,烧数码相机,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压根儿不懂世道已经变了。”
“但是新闻传播辨别真伪的传统职能一点儿也没变。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里,那不表示我们不需要弄清楚那么多信息都意味着什么。因此之故,新闻业比以往更加重要。”
克雷格·纽斯马克:人民需要信得过的新闻
“我刚才脱口而出一句话:‘新闻界是民主制度的免疫系统。’也许是我对公民学课程的记忆太鲜活了,但它确实影响了我对新闻记者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与表述:监督问责掌权者。我们需要值得信赖的政府,我们需要值得信赖的好新闻来造就一个好政府。 ”
“一个行业必须要有自己的行为规范才能赢得信任。那意味着要用职业伦理来规范从业者的行为。我是一个外行,一个新闻消费者,我说不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知道人们需要信得过的新闻。作为新闻消费者我们也应当努力做到更好——只听从那些认可行业伦理并且认真遵从的新闻工作者。”
美国著名分类信息网站“克雷格目录”创始人克雷格·纽斯马克(Craig Newsmark)显然是专业新闻的捍卫者。他的观点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新闻消费者的行为提出了建议,他号召人们只消费值得信赖的新闻。做明智的消费者在如今这个商品丰裕时代是一件相当困难而又十分必要的事,在新闻消费领域或许更是如此。我们从来都在不遗余力地批判媒体的媚俗,却对媒体所媚之俗无能为力。克雷格的说法,对于职业新闻界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新闻业的进步,有赖于新闻业本身的改革,亦有赖于全民新闻素养的提高。
佩吉·诺南:不一定要上新闻学院,但一定要够专业
“我的第六版(2007)牛津英语辞典说,新闻工作者是‘靠为报纸或期刊撰稿或做编辑谋生的人,也包括广播电视记者’。这听起来有点定义过窄,有点老套过时,不过‘谋生’这个说法比较有趣:它意味着新闻工作者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从事新闻业上,把它当作一个职业。”
“我来试着下个定义:新闻工作者是专业性地致力于采集和发布公共利益相关问题的信息的人,他/她在一个公共论坛里从事新闻活动,譬如报纸、网站、博客、杂志、网络时事通讯、广播电台或有线电视台。新闻工作者应当了解并且坚守这个行业的规则与传统,应遵循某些原则进行报道,譬如力求准确,如实报道,杜绝编造。更为理想的是,他/她还熟知本行业的历史与文化。他们要受到诽谤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譬如涉及漠视他人安全的法律)的制约。新闻工作本身并不是一份‘特赦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获得一些特别保护,没人会介意,因为我们需要他们,没有新闻工作者民主机制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你不是非得去上新闻学院才能成为一个记者,当然去上新闻学院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也不至于会有什么害处。你可能天生就适合从事新闻工作。但是不管你是受过学院派的训练还是没有,你得够专业,你得知道所有的规矩。这些规矩以往都是由老编辑老记者们来传授的——有时是用他们起了茧子的‘老手’来手把手地传授。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都买断工龄退休了。没人能代替他们。与新技术相比,这对真正的新闻业是个更大的威胁,对未来的影响更加不容乐观。”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佩吉·诺南(Peggy Noonan)曾是里根与布什两任总统的御用写手,虽不直接从事新闻业,但在政治与媒体中浸淫日久,出书、写专栏、上电视,年逾六十仍旧十分活跃,影响力不可小觑。佩吉·诺南清楚地认识到新闻生态的变化,指出互联网技术使得公共论坛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而新闻工作者的定义的确该加以刷新了。
佩吉·诺南显然认为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新闻活动的平台,但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准则不该发生变化。无论你进不进新闻学院,无论你在哪种类型的论坛上从事新闻活动,一些基本准则始终都该坚守,譬如你要坚持公共利益原则,你要负责任地报道,你不要以为新闻工作者享有某些特权你就可以漫不经心地漠视他人的名誉和安全。
她对老编辑老记者们的退休感到忧心忡忡。我想她所担心的是新闻业的良好传统的断裂与消失。新闻传播的平台无限延伸,公共论坛已经“去中心化”,信息的海洋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佩吉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
弗兰西斯·克帕汀德:严谨与精确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推特
“做新闻不止是一个美丽的职业,它也是一种思维的状态。从事新闻工作可以培养人的恭谨谦逊,它要求从业者拥有卓越的通识、对他人敞开胸襟的气度、超强的分析能力,还要有真正的质疑能力,包括质疑自身以及那些对普通民众或者政府官员来说貌似确凿无疑的东西。要达到所有这些要求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你无法像个历史学家那样拉开距离来做审视或者没有时间去做必要的反思时。
“正因如此,并不是随便谁都适合从事新闻业,尽管新闻业本身为生存计,必须努力兼容并包。新媒体特有的直接与快速也不能改变这些基本要求,严谨与精确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推特,一如适用于塞内加尔官方日报所发表的报道。”
弗兰西斯·克帕汀德(Francis Kpatindé)是长住巴黎的法裔贝宁人,自由记者。1997至2005年曾任巴黎某新闻周刊的非洲版编辑;2005至2011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西非发言人。
理查德·金格拉斯:新闻须令我们保持诚实
“新闻须令我们保持诚实——对我们自身保持诚实,对我们的理想保持诚实,对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文化的阴暗面保持诚实。新闻应当是我们的集体意识之中的启示性力量,挑战普遍假设和预设的一种力量,要达到这种效果,需要每一个新闻人就任何形势或问题给出他们最明智的看法。不容躲闪,不容自欺欺人、不战自败。让各种说法自由呈现,它们自会在一定程度上找到平衡,这种平衡不是在新闻人表面上的不偏不倚上实现,而是在一个丰富的、多向度、多层面的世界中实现。”
作为谷歌公司的高级主管,理查德·金格拉斯(Richard Gingras)信奉的新闻理念既有经典新闻理念的高度和纯度,又有网络新媒体的开放度。以经典的报刊理论来衡量,会发现他的观点既有自由主义的一面,又有社会责任派的影子。他强调多向度、多层面的世界,主张各种说法自由流动,去自由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这和著名的自由主义“自我修正”报刊理论一脉相承:“自由主义者提倡的办法是让公众听取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报道和意见,其中某些可能是真实的,某些可能是虚假的,某些则可能有真有假。最后我们可以信任公众会把它们都消化了,抛弃那些不符合公众利益的东西,接受那些符合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社会的需要的东西。”作为当今最热门的网络公司的高级主管,他持有这一观点十分自然——网络是最大的意见自由市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有媒体所提供的话语平台都更宽阔、更自由。但他同时强调从业者的诚实与负责,这和谷歌“不作恶”(DON'T BE EVIL)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强调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都已见证网络的意见自由市场上是多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意的炒作、恶意的误导、无意的信谣传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值得信赖的媒体。
杰瑟琳·瑞达克:新闻业就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
“我母亲曾为凯蒂·格雷厄姆工作。我从小就相信新闻业意味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式的调查报道,揭发政府的犯罪,曝光误入歧途的、有时是不合法的政策,戳穿那些故弄玄虚的说法以及故意的传谣。这种气质鼓舞我为检举揭发者代言,他们就是现代的‘深喉’。”
“不幸的是,自9·11之后,主流媒体充任了——往好里说,速记员,往坏里说,宣传员——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方面。新闻业对匿名政府消息源的过度依赖(甚至常常是仅仅依赖)使得报道丧失了法律效力并且因此把记者变成了政府喉舌。 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全国新闻界在关于伊拉克武器的情报问题上的失察——而那是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我的工作是为检举揭发者代理法律事务,但在这个国家我愿意为其服务的记者不超过十个。”
“我希望新闻界可以找到来时的路,回归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职能:保证人民对政府行为的知情权,促进公开的讨论与辩论——这是实施公开监督的关键因素。为政府保守秘密保护不了国土安全和我们独特的美国生活方式。自由、严谨、富于怀疑精神的、独立的新闻界对于确保公众知情权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民主的核心所在。”
杰瑟琳·瑞达克(Jesselyn Radack)是“政府责任项目”(一个致力于保护政府及民间举报者的非盈利机构)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主管,其母曾为格雷厄姆家族工作,格雷厄姆家族的《华盛顿邮报》因曝光“水门事件”而在新闻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负责报道“水门事件”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成为调查揭丑报道的代名词。无论媒体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新闻业的边界如何被技术融蚀,我们仍旧需要邮报,需要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成就这一切,技术决不是根本性的因素,重要的是信念。整个媒体的信念和从业者个体的信念同样重要。信念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它通常意味着千锤百炼的经典传统。
没有深厚的专业素养,没有崇高的新闻理想,没有发问的身份,没有合适的平台,无论怎样先进的技术,也无法使一个普通网民成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言以蔽之:新闻仍旧需要专业。
雅斯敏·康佳:不是每个人都处在可以发问的位置上
“新闻工作者首先是发问者。我们提问,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责。在所有高水平的分析、即席评论或者深入调查之前,得有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发乎自然、有时是天真幼稚的并且常常是平淡无奇的问题。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问题总是应该在答案之前。只有通过提问,我们才能透过那些精心修饰的、随时可以见报的说法的光鲜表面深挖下去。”
“谁都好奇,谁都怀疑,谁都相信背后藏有更多,但不是谁都在可以发问的位置上,在那个位置上的是新闻工作者。为人们头脑中那些沉默的疑问发声就是我们的工作。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如何?这是些具有魔力的字眼。它们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新闻工作者最好的工具,在数字年代,它们依旧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可以发问的位置上。”一语中的,揭示了职业新闻界与公民新闻之间的区别,也表明了职业新闻界存在的必要性或者说存在的意义。雅斯敏·康佳(Yasemin Congar)是土耳其《TARAF报》的元老级副主编,现居伊斯坦布尔,同时还是若干媒体的撰稿人。
斯蒂芬·B·谢泼德:新闻业永远都会存在
“严肃新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系重大,不论在什么平台上,不论使用何种技术,也不论是什么人来做。”
“在这个信息过剩和媒介碎片化的时代,新闻业变得更加重要。它意味着你在谷歌上找不到的独树一帜的原创型报道,意味着与社区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意味着深度挖掘、深刻理解的重大报道;同时也意味着在我们最好的时代对智慧的追求。”
“也许我们的孩子们将通过植入脑子中的无线信息设备获取智慧,那很好,但不管媒介如何变化,人类对于自由社会中富于启迪的新闻业的需求永远都会存在。”
史蒂芬·B·谢泼德(Stephen B. Shepard)曾任《商业周刊》主编,还曾是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的首任院长。
由CJR的调查可知,以日本社交媒体达人上杉隆和美国新媒体新贵麦克·麦森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相当直率地表达了对传统主流媒体的失望与不满,认为职业新闻界处于倒退的状态,因而公民必须自己来寻求真相,这是新媒体兴起的原因,也是社交网络活跃的结果。
但总体来看,CJR的调查留给人们更深刻的印象是:不少职业新闻人对公民新闻抱有十分开放的态度,而一些新媒体新闻人和新闻公民则对经典新闻理念表示出信奉的敬意。许多答案以不同的表达诠释经典的新闻观念,这些答案在平淡无奇之中给人带来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稳定感:这世上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作为基石撑起整个世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仍有一座不灭的灯塔。或者说,信息的汪洋大海里迷雾重重,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一座不灭的灯塔。新闻业无需妄自菲薄,更需勇于担当。■
注释:
①Jay Rosen,A most useful defini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7/14/2008Press Think.
②http://techland.time.com/2013/08/05/the-25-best-bloggers-2013-edition/slide/andrew-revkin-dot-earth/,2013.12访问。
③Meyer, Michael?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 2011accessed May 172011.
④即Ku Klux Klan,美国历史上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恐怖活动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⑤[英]斯图尔特·艾伦:《隐藏在平实的视野中——新闻的批判议题》;斯图尔特·艾伦,《新闻业:批判的议题》第1~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