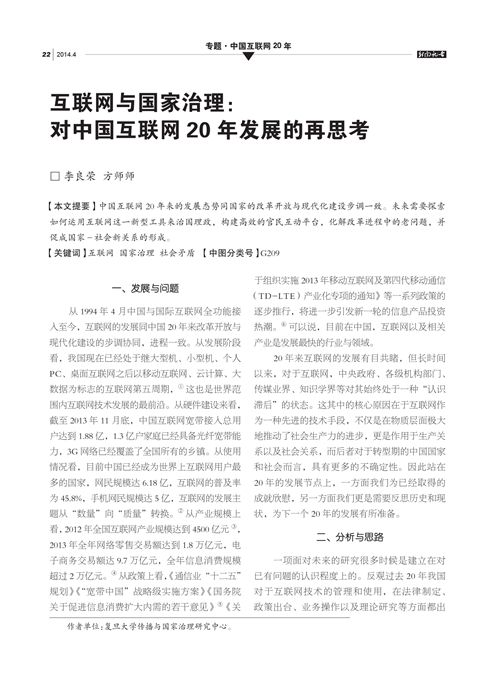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对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的再思考
□李良荣 方师师
【本文提要】 中国互联网20年来的发展态势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步调一致。未来需要探索如何运用互联网这一新型工具来治国理政,构建高效的官民互动平台,化解改革进程中的老问题,并促成国家-社会新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 互联网 国家治理 社会矛盾
【中图分类号】 G209
一、发展与问题
从1994年4月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接入至今,互联网的发展同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步调协同,进程一致。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现在已经处于继大型机、小型机、个人PC、桌面互联网之后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标志的互联网第五周期,①这也是世界范围内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从硬件建设来看,截至2013年11月底,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总用户达到1.88亿,1.3亿户家庭已经具备光纤宽带能力,3G网络已经覆盖了全国所有的乡镇。从使用情况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的普及率为45.8%,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互联网的发展主题从“数量”向“质量”转换。②从产业规模上看,2012年全国互联网产业规模达到4500亿元③,2013年全年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8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9.7万亿元,全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2万亿元。④从政策上看,《通信业“十二五”规划》《“宽带中国”战略级实施方案》《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⑤《关于组织实施2013年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产业化专项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的逐步推行,将进一步引发新一轮的信息产品投资热潮。⑥可以说,目前在中国,互联网以及相关产业是发展最快的行业与领域。
20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有目共睹,但长时间以来,对于互联网,中央政府、各级机构部门、传媒业界、知识学界等对其始终处于一种“认识滞后”的状态。这其中的核心原因在于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不仅是在物质层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更是作用于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而后者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而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站在20年的发展节点上,一方面我们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欣慰,另一方面我们更是需要反思历史和现状,为下一个20年的发展有所准备。
二、分析与思路
一项面对未来的研究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对已有问题的认识程度上的。反观过去20年我国对于互联网技术的管理和使用,在法律制定、政策出台、业务操作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制度落后于技术”的情况。互联网像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停地给国家和社会“提出新问题,带来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是否是“全新的”可以进一步商榷,但是国家和社会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和挑战的时候,几乎都是从原有的思维模式出发,采用分散的、零星的、救急的以及刺激-反应式的应对,缺乏对整个互联网技术、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逻辑的深刻反思。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零散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逐渐积聚起来形成社会性问题,最终只能自下而上地倒逼顶层制度的改革。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转型时期: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渐加剧;社会不公现象突出,腐败特权现象蔓延;群体性事件和上访数量居高不下,维稳成本和压力增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共识撕裂;民族分裂恐怖势力增多,民众公共安全感降低;政府公信力流失,政治体制僵化。概而言之,当互联网作为一股新型的“力量”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碰撞时,出现了四个类别的情况:
1.现象转移:社会结构中原有的被遮蔽的问题通过互联网反映出来,社会问题转移至互联网上,现实社会问题转化为网络社会问题。⑧
2.矛盾放大:社会结构中原有的问题上网之后,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关注,社会问题突破了当时本地的时空界限在互联网上得以“永存”。⑨
3.焦点变异:社会矛盾在互联网上传播,关涉的多方主体加入讨论,导致问题的重点产生了迁移甚至改变,最终的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⑩
4.多方共振:社会问题不仅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变异,而且还牵涉到了社会中的多个方面,不同的社会主体从多个层面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审视,最终产生了“舆论共振”,[11]问题的指向开始溢出事物本来的界限,矛头指向制度设计与意识形态这样的国家元概念。[12]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类现象有时候会在同一个案例中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问题的“发酵”程度逐渐增高,处理与解决的难度也在加大。[13]普通意义上的思路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得社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这种因果推断的问题在于没有认清或者遮蔽掉了“既有社会结构在当代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结构性问题”。[14]如果按照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给出的逻辑:现代性是一颗种子,落在了一块叫做中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现代中国”,而是一个有着中国血脉的“现代国家”[15]——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技术,进入到中国的语境,并非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问题,而是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思维模式和治理模式。
因此,站在中国互联网发展20年的时空状态下来看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我们需要明确:不仅要对互联网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做综合性的研究,探索如何将互联网更好地纳入到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来,以增强社会吸纳矛盾的容量和弹性;[16]还要思考如何用互联网的思维来帮助我们解决既有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打造新的社会关系。前者是传统思路中的管理互联网,后者则是运用互联网进行国家治理。
三、起点与视角
一般意义上的“治理”通常是指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的最高权威”,治理源自这个单一中心,而如司法、行政、立法或中央-地方关系都是从这一单一源头的分权。[17]福柯研究了明确稳定的两种权力形式——“统治”和“国家治理”认为:统治是一种传统的等级关系,在此关系中,下级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但现代国家治理目的在于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引导民众,[18]其意义比“国家的最高权威”要宽泛得多。治理在两个层面上将传统的统治和现代的治理结合起来:首先,它被视为一种旨在影响个体管理自身行为的行动,治理不是政府的专利,市民社会中的组织也可能进行治理;其次,治理考虑个体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以巩固和扩展国家控制范围为前提的。[19]之所以要强调这一视角的重要性,问题在于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社会结构日趋扁平化,社会关系相互渗透,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交互密切,底层权力彰显,[20]过去依靠单一力量、单独部门、单向权力的统治结构再也无法应对当前的情况。[21]国内最早研究国家治理的学者之一俞可平认为,人类的政治生活经历了管治—管理—治理的阶段,而“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22]但是,现在很多官员还停留在管治与管理的思路上,甚至还很怀念过去没有互联网的“清净”时光。需要明确的是:历史是不能开倒车的,网络封锁甚至断网是不可能的,不仅经济建设不允许,国民社会也不可能回到当初那个封闭的时代,所以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顺势而动寻找适合的接洽点。
实际上,对于技术如何服务于国家建设是我国的一项治理传统。从历史上看,自洋务运动兴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使用,突出的都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对于家国同构制度的贡献。传播技术也不例外,总是同国家整体的稳定与利益紧密不可分开[23],这也是我国同西方国家甚至亚洲其他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候的一个重要不同:国家作为集体利益的集合总是作为大背景被不断提及和回溯,并且所有的作为最终都被统一在这个大的召唤之下。[24]转变思路,不能将互联网简单地看作是麻烦制造者,而是要将其作为一种力量强大的治理工具,用来建立高效的沟通平台,解决老问题,促成新关系。[25]这种“反客为主”的视角才是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互联网和运用互联网进行国家治理的应有之意。
四、原则与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的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俞可平认为,所谓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其中三个最为重要的层次;而“治理能力”则是国家行政系统对于制度的执行与贯彻能力。“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有五大表现:1.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2.民主化;3.法治;4.效率;5.协调。[26]这五个表现既是我国现今国家-社会体制改革的标准,又是未来的目标。但问题是,方法和路径何在?
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技术特性为我们的目标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其一,互联网的跨域属性使得对于治理的讨论从民族-国家领域进入到了全球公民社会的辩论空间,对于政治生态、公共管理、国际关系甚至是经济制度的考察都需要“全球共治”的视角;[27]其二,互联网的互动沟通有助于强化协商民主沟通中的多元文化身份认同;[28]其三,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的5A传播形态对于应对和处理情境式危机传播(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29]最后,互联网可以有效地提高传播效率,缩减行政管理成本并具有创新性的思维特征。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互联网的思维来进行国家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如下:
1.制度化原则:应将互联网的沟通协调、舆论监督等作用纳入到国家体制之中,使其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为完善我国的民主协商制度、建立健全社会多方共建自治机制提供渠道和平台;利用互联网实行全民舆论监督反腐败,为打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经济环境创造保障条件。
2.法治化原则:即依法治网和以网治国。前者是针对互联网的使用与传播行为出台严格的法律法规,设立行业通行的标准与规范;后者则是设立一系列的互联网治国的准则与机制,针对多样的使用主体界定权责范围。
3.安全性原则: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要从互联网技术安全、互联网使用安全以及互联网与国家安全三个方面来综合治理。构建安全繁荣的互联网,力主建立起一个动态平衡的网络环境,以安全保繁荣,以繁荣促安全。
4.效率化原则:我国互联网发展至今,虽然技术进步较快,但是技术普及率和转化率依然不足,网络技术需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再生产。互联网的效率化原则一方面要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创新,扶持高新技术转化;另一方面则要精简行政管理成本,提高国家治理效率。
对于国家治理来说,不仅要从国内局势出发,还要考虑国际形势;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确保制度安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共建共治互联网。因此,运用互联网进行国家治理重点要处理好五个层面的问题:
1.国际环境层面:倡导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在国际上建立起最为广泛的国际互联网统一战线,打击国际黑客攻击行为和跨国数据盗用,为我国在网络空间中的利益和发展打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保护我国公民的网络隐私。
2.国家制度层面:运用互联网促进国家执政现代化建设,加强党和政府部门同公民之间的联系,建立迅速快捷的政务公开机制。
3.社会治理层面:倡导多主体共治,进一步完善在线民主协商机制;在经济体系中,中央以及各级政府应与银行体系、民间企业合作,规范征信系统和信息数据库,提升支付等业务的安全系数,维护互联网金融安全;通过互联网依法惩治网络黑客攻击、网络谣言、网络侵权等行为,切实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意识形态安全和公民个人权利。
4.媒体规范层面:就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部、互联网媒体以及自媒体在内容生产、信息来源、内容知识产权、以及信息发布等方面明确传播主旨,设定基本规则,规范步骤流程,并制定紧急事件预案;进一步强化全社会范围内的舆论监督,助推国家改革进程。
5.技术使用层面:提高对于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建立起“数据为数据生产主体所有”的数据所有制标准,就数据的生产、存储、授权、分析、挖掘等建立起一整套规范制度。
下一个20年,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将会更加蓬勃向上,充满活力。而同时,我国的国家体制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在今年的两会中,反腐、法治建设、公众参与、以开放促改革以及强化媒体和舆论对于国家机构和公权力的监督都是热议的话题,而探索将互联网这一技术工具纳入到中国国家治理的框架之中,充分发挥其技术的特性破解结构性问题,助推新一轮改革进程,重构互联网时代国家-社会关系,将是未来中国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的关键任务与核心要点。■
注释:
①Stanley M. Internet trends[J]. Report, June, 2010: 2009-2014.
②《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年1月
③《中国互联网产业规模达4500亿》,人民网2013年1月18日,http://it.people.com.cn/n/2013/0118/c1009-20245569.html
④⑥《2013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综述》,2014中国互联网产业年会官方网站,2014年1月9日,http://cynh.comon.cn/listinfo-267.html
⑤《2013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1月23日,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2858447/15861120.html
⑦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⑧张立:《网络舆论传播中若干算法的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王欢、祝阳:《群体性事件中网络的放大效应研究——以“微笑局长”事件为例》,《现代情报》2013第4期; 唐超:《突发型群体性事件网络影响力演进的实证研究》,《情报杂志》2012年第期
⑩李文娟:《网络舆情倾向性分析技术研究与实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黄永林、喻发胜、王晓红等:《中国社会转型期网络舆论的生成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1]丁汉青:《舆论形态的非线性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刘冰玉、凌昊莹:《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网络媒介环境中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变异》,《现代传播》2012年第9期; 罗坤瑾:《微博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研究文献综述》,《学术论坛》2013年第10期
[12]毛剑平:《公共舆论的哲学思考——舆论与制度互动的维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郭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舆情传播特点》,《科技传播》2012年第17期; 冀旭妍:《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7期
[14]陈新光:《后现代视野下的社会风险研究——以上海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6]Puppis M. Media governance: A new concept for the analysis of media policy and regulation[J]. 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 20103(2): 134-149.
[17]Aristotle. The Politic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8]Fornet-Betancourt RBecker HGomez-Muller Aet al.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on January 201984[J]. 1987.
[19]巴里·海因斯:《 权力、治理和政治》,出自[英]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第42~50页, 李雪、吴玉鑫、赵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Thomas P. The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RIS) Campaign Applying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to an Analysis of Global Media Reform[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0668(4): 291-312.
[21]梁健:《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26]《“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制”——专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3月10日
[23]孙藜:《“飞线”苦驰“万里天”: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25]Marche SMcNiven J D. E-Government and E-Governance: The Futur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J]. 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e l'Administration200320(1): 74-86.
[27]Castells M. The new public sphere: Global civil society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governance[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08616(1): 78-93.
[28]苏振华、郁建兴:《公众参与、程序正当性与主体间共识——试论公共利益的合法性来源》, 《哲学研究》 2005年第11期
[29]Coombs W T. Protecting organization reputations during a crisi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J]. 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 200710(3): 163-176.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