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新闻业?
——关于新闻业与新闻人社会角色的历史辨析
□ 王维佳
【内容提要】本文对欧美现代新闻业和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产生背景、社会角色和政治诉求进行了历史性的对比分析,试图在对比中探析现代新闻业的多重面向和多种道路。作者讨论了社会结构、地理空间、知识分子文化意识等决定现代新闻业形态的历史变量,以此反驳对现代新闻业性质和规范的普世性、封闭性解读,并敞开创造新型新闻文化的想象空间。
【关键词】新闻业 新闻记者 杰克逊时代 新文化运动 群众办报 【中图分类号】 G210
今天我们纪念记者节,已经不大谈起中国最初的记者节的由头:1937年11月8日,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记者在上海聚会,筹划成立一个爱国抗日的同盟组织。在那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时光,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的新闻人为了民族解放的共同期许,呼吁同仁以笔为枪、同心抗战。他们编辑了自己的刊物《新闻记者》,并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渐渐淡忘了当初记者节原本应有的政治内涵和历史意义,反而更愿意用现代市场新闻业中的普遍规范来看待记者的社会角色。然而,正是记者节的历史提醒我们,理解记者、理解现代新闻业,我们不能割断这个群体与历史和政治之间的连结:一方面,我们今天当作普遍规范的专业化新闻生产逻辑本身就是源于19世纪欧美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和政治意识也始终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构建和转型的政治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将在讨论西方现代新闻业兴起背景和中国新闻业发展独特性的过程中,以回归历史的方式重新认识新闻业和新闻人。
一、“杰克逊时代”的神话:自由主义的媒体史叙事
1838年,美国著名作家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一篇政论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新兴的大众化报纸:“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文学、艺术、戏剧甚至私人生活尽情施暴。在保护公共道德的假面具下,报纸其实是在彻底腐化道德;在保障自由的外貌下,报纸其实逐渐在建立一个暴政”。①对于熟悉了西方新闻史肯定性叙事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负面评价显然是非常令人惊讶的。19世纪出现的市场化媒体向来被认为是从政党报刊或封建专制中获得解放的自由力量,甚至是民主力量,怎么会在库珀的笔下成了公共生活的施暴者呢?
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中,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从反面引用了库珀的这段评价,并认为这些言辞“反映了既有势力对民主化(中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反抗”。②这种信手拈来的阶级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库珀本人就是纽约州显赫的大地主家庭子弟。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库珀的思想中,还有着深刻的联邦党人政治遗产,那就是对共和主义的坚守,以及将道德与善放在个人权利之上的伦理观念。面对商业利益对传统、稳定、理性、庄重的精英公共生活的侵袭,面对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伪善的中立主义,库珀的忧虑和愤怒当然有文化和政治上的理由。实际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批评也不过是这种忧虑和愤怒的学术版本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感谢舒德森的写作,他虽然延续了对现代市场新闻业那种简单的肯定性判断,却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些批评观点和丰富的历史背景。但是要把现代新闻业的兴起放回历史原境中,我们还是要对他这本报业社会史著作进行一些反思性的解读,并由此进入我们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状况造成了现代市场新闻业的产生?从这些历史状况中我们能认识到市场新闻业的哪些特性?
舒德森认为,造成现代新闻业勃兴的根本因素,不是传播科技上的革命,不是识字率的提高,也不是报纸自然进化的结果。他从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来认识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性变革,那就是“杰克逊时代”③的平等主义和民主。在对这个“平等主义”时代进行褒扬时,舒德森没有吝惜任何美好的词汇:人才就业开放、出身不论贫富贵贱、所有民众享受同等机会、传播公共教育、反对政府垄断、敦促权力下放、不再死死抱住贵族价值观不放、人的个体获得了新的地位、追求利己主义成为一种荣耀……④在这种叙述中,显然不见了当时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事实、不见了劳工对新兴资本主义的反抗(实际上舒德森的新闻史写作完全忽视了19世纪中期美国大量存在的劳工报刊),也不见了杰克逊们对奴隶制的顽固坚守以及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般“迁移”历史。
作为一个与东部辉格党人针锋相对的边疆开拓者,安德鲁·杰克逊及其追随者的政治观念远比“平等主义”和“民主”复杂得多。按照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的说法,正是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共同任务,以及面对底层奴隶阶级和东部贵族这两个异己力量的现实,把美国西南地区各阶级的白人男性维系在一起,使社会上层产生了安德鲁·杰克逊这样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而这一阶层可以在种植业经济的论争中完全站在保守派一边,却同时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领袖,无须为前后态度矛盾而内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类种植业上层表示绝对相信民众的判断时,将其斥为蛊惑人心者未免失之不公正”。⑤举例来说,安德鲁·杰克逊经济政策上最著名的反对国有银行的主张,非常类似今天部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指责金融业国家垄断的言辞,实际上根本不是出于对金融权贵独裁的抵制和对平等的要求,只不过是要为私人的债券投机打开大门罢了。要知道杰克逊登上政坛的坚强后盾就是美国西部的地产投机商和放债人。⑥由此看来,“杰克逊时代”的平等不过是美国西南种植园主、证券投机商与都市新兴资产阶级以“民主”为名联手对传统联邦主义发动的一场“哗变”而已。只是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书写中这出喜剧和闹剧才变成了“正剧”。
更进一步来看,舒德森对“杰克逊时代”的赞颂实际上是将当代的自由主义观念投射到19世纪的结果。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曾经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舒德森式的理论错置,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他提到:“杰克逊派对财富分配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反对与公正关系不大,而与财富、权力的巨大集中对自治构成的威胁却有很大关系。辉格党人促进经济发展的理由,与提高生活标准或最大化消费关系不大,而与培育国民共同体以及增强联邦的纽带有很大关系”。⑦虽然桑德尔完全从政治理念角度展开的论述忽略了这两股力量的经济背景,但至少说明了他们的分歧并不存在于“民主”或“精英”的理念上,而主要存在于“自治”或“联邦”的理念上。实际上,20世纪末兴盛于美国各地的“民兵与爱国者运动”,即那些宗教、文化、种族方面的极端保守主义势力和美国地方的反全球化、反联邦主义力量才是杰克逊政治理念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无政府主义、地方自治主义、反全球化意识与经济观念上极端放任主义奇怪地耦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可以稍作总结:以美国“便士报”为代表的现代市场新闻业的兴起,并非是拜“平等主义”和“民主”的政治气候所赐。美国现代商业媒体实际上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异军突起而出现的一股都市文化力量,它所创造的,正是这群爆发户和投机商所需要的相对主义文化政治。而从市场化报业自身的发展来看,其存续的前提也是扳倒一座文化上的大山,那就是正当性政治,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善和伦理的传统认同。否则,我们不能想象那些深入私人生活的膻色腥内容能够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美国19世纪中后期野蛮商业化过程中的道德悲情剧确实也常常被小报演绎,但其出发点绝不是正面的道德塑造,而是专门发掘丑陋现实来摧毁公众的道德信仰,从而引发轰动效应。这一点与当今的都市媒体的社会新闻报道并无二致。报业宣称的党派中立,也并非来自什么伟大的职业理想,只不过是现代新闻人“消费真实”和“贩卖受众”的逻辑前提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新闻业天生就是另一种保守力量,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这种消费意义上的平等和选择只能是一种“温柔的专制”。当然,一旦遇到复杂的政治经济纠葛,一旦受到细分市场和广告主的限制,一旦有反抗自由经济的力量威胁现有体制,市场化媒体会毫不犹豫地冲破中立的底线。
然而,现代市场新闻业进入社会主流的后果还不仅仅是政治正当性的消散,它不但压制了传统伦理的卫道士,还同时排斥了激进的文化力量。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的著作《媒体与权力》给我们展现了自由主义媒体史从未触及的一段史实⑧。在英国,19世纪后半叶广告税和印花税被取消一直被视为媒体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是自由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开端。然而,卡伦的研究指出,正是办报限制的解除使得原本发行量远远超过主流都市报刊的激进派劳工报纸迅速走向衰落。印花税的取消等于为资本力量大举进入报业打开了绿灯,而广告税取消则给小报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压力。都市商业报刊开始对印刷机器设备升级换代,并扩大经营规模。不断增长的办报运营成本和资金流动则有广告商埋单。这种状况最终拖垮了不能满足广告主需求的激进劳工报。
这段史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击碎了自由主义媒体史那种国家与市场相互对立的二元论叙事。卡伦的研究证明,19世纪中后期,英国传统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实际上有着近在眼前的共同威胁,那就是劳工运动及其强大的宣传攻势。传统贵族精英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对新兴商业力量做出了让步,将他们纳入统治集团,从而利用资本所构建的阻隔机制,成功地限制了激进民主力量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伦将报业税的取消这个被广泛认为开启了自由报业史的举措称作是“资本的自由”和一套“新兴的许可证体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用民主和进步来理解现代市场新闻业的诞生就意味着用迷信来解释历史。
二、中国经验:现代新闻业的另类尝试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新闻学科重建以来,西方现代进步史学对新闻业发展的肯定性叙事在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构成了一套理解新闻业的固定模式。它甚至成了反思中国新闻业发展的“照妖镜”,不断试图在这个显得有些另类的社会中推广早已成形的西方市场新闻业体制。
以研究中国新闻记者的各种文献为例,最流行的分析范式就是讨论国家、市场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思路中,“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作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威权力量”、“保守力量”、“传统力量”,而新闻从业者则幻化成“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成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力量和威权压制下的弱小反抗者(草根)。新闻从业者“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成了印证这种对抗性二元关系的论据。与此同时,“市场”的力量则常被当作消解威权的有力手段。有了前面对舒德森理论的解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分析框架与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媒体史观是如此相似,它基本是关于西方现代市场新闻业那种肯定性叙事在中国社会的投射。这样的思路既缺少对文化政治复杂性的把握,也没有对社会结构,特别是都市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审慎考量,更忽视了市场逻辑所制造的保守立场,甚至是压制性能量。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新闻实践范式一直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提供了一条西方现代新闻业之外的另类方案,而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新闻观念在对西方现代新闻业模式的顶礼膜拜中埋葬了20世纪中国新闻人的独特遗产,也抑制了我们对新闻业社会角色的想象力。
从中国近代新闻业产生伊始,中国都市新闻记者的文化意识就有着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个性正是成就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和被动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中国新闻记者的独特社会角色。
首先,与19世纪的欧美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反对传统权威的单一面向不同,近代伊始,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思想就蕴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脱离传统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奔向现代化的理念;二是反抗殖民的民族解放意识。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想构造称为“双重现代性”。支持商贸、意图发展科技和改革社会制度这些现代思想自然都是当时中国的新生观念。然而,人们往往会忽略“现代性精神”的另一面,即以新闻人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还具有强烈的反殖民意识。正如柯文在分析报人王韬的思想时所概括的,“从这种世界观念在近代中国刚刚出现的时候起,它就暗含着一种强烈的(有时是无声)向西方复仇的不满和义愤之情”⑨。作为近代最早的报人,王韬所提出的“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⑩,即学习先进科技文化,振兴中华,抵御外侮正是这代知识分子传播实践的主要政治诉求。因此,与同时期美国新闻业反对党国垄断,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和文化相对性的“杰克逊主义”刚好相反,近代中国报人始终将构建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当作一项重要诉求。这种政治理念兼具反侵略和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正如浦嘉珉在描述这一时代新闻业者的职业志趣时所指出的,这些人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而仅仅是那些他们最为关心的,有关中国富强的内容”[11]。齐慕实也曾提到,“一方面,梁启超等人意在运用新闻媒介来吸引君主的注意,以求说服国家权力核心推动改良;另一方面,战后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极端危急的状况也使得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传播内容相比西方更加严肃”[12]。
由此可见,欧美早期大众化报刊与中国近代报业虽然基本处于一个时代,但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这正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特征。19世纪中期,基本完成了资本所需的现代化和殖民化使命后,欧美社会中国家力量开始隐藏在市场的幕后,这一隐身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新闻媒体和知识界的文化创造。而此时,亟待解决国家建制促发现代化的中国,则面临构建现代政治组织的重大使命。从那时起的几代报人正是在文化上塑造国民认同的关键力量。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记者同盟组织和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直到20世纪末大量沿海都市媒体兴盛之前,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直是中国现代新闻人的正面宣示。
其次,在19世纪欧美现代新闻业快速兴起的过程中,几乎都出现了都市知识分子与劳工群体分台唱戏的局面。一边是都市中职业新闻记者的商业报刊迅速发展;另一边则是劳工报刊先崛起再衰落的过程。然而在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种世界新闻史上极为少见的现象,即知识分子走向劳工,与社会底层相结合,共同创造新型新闻实践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卡伦所使用的阶级分析范式在中国遇到了难题,因为“五四”以后中国新闻史中出现了新闻文化再造的现象,这段历史不是简单的阶级对立和资本排斥的历史。众多都市新闻人非但不是以与劳工阶层对立的面目出现,甚至也不是要代表底层劳工,而是创造一个与中国大多数民众共同发声,融为一体的新型新闻业。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五四”之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等刊物的迅速转向上。尤其是《新青年》开始集中精力关注劳工问题,陈独秀此时已经将“新文化运动”在产业层面的目标指认为“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层面的目标指认为“要创造出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13]。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不但介绍了欧美和日本的工人运动,而且集中刊登南京、山西、江苏、湖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直接面向工人的报刊。这些都市知识分子主办的媒体不但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沟通工人生产和运动的讯息,而且直接刊登工人自己的诗歌和文章。
“五四”时期这种倡导知识分子与劳工相结合的新型新闻理念和实践一直延续到延安时期。此时的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主管延安出版工作的博古曾经对即将奔赴基层蹲点驻村的记者说:“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14]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的通讯员制度,这一制度的思路是陆定一所说的“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15]。1942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已经有2000 多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 多人。新华社到1945 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拥有近3 万名通讯员。1948 年仅在华中解放区的新闻通讯员已经有4.6万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约3 万篇[16]。从当时新闻人的观念来看,大量基层劳动者以通讯员方式参与新闻活动并不是出于扩大新闻线索来源的目的,而是一种打破职业分工边界,强调新闻大众化的努力。新闻人努力的方向不是代表大众观察,代表大众发声,而是为大众提供观察和发声的平台,与此同时成为大众中的一员。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在民主的意义上是更加进步的。它甚至也超越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成为塑造新型政治主体的一股重要力量。
以上所总结的这些新闻人与社会底层相融合的新闻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后遇到了各种曲折和变革,并最终在市场新闻业大规模植入的过程中渐渐消散。一套源自西方的现代新闻规范逐渐成为中国记者的“目标”、“方向”和“正轨”。如今,19世纪欧美新闻业的理念不仅看起来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新闻理念更熟悉,而且已经在很大范围内转变成制度性的现实。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放权,抽空了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的中介协调力量,这为掌握媒体资源的都市新闻人创造了依附资本力量和官僚力量的机遇,客观上造成了这一群体文化意识的整体转向。在经济和市场属性更被传媒行业看重的今天,新闻记者整体上正在转变为服务业的劳动力,而不再是创造新社会的政治主体,更有甚者,由于新闻生产中的“去政治化”逻辑,他们也不再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
从欧美和中国的经验来看,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变革是无法规划的历史事件,是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然而,当前我们对新闻业的主流认知,却是规范性的,即使是名为新闻史的写作,提供的也常常是一套反历史的驯化观念。我们用欧美现代市场新闻业的诞生和20世纪中国新闻人的独特经验来讨论“什么是现代新闻业”,目的并不是展现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而是要展现一种认识新闻业,认识新闻记者的思路。今天,中国的新闻记者面对行业的种种诟病、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面对全球化的各种危机,更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新闻文化和新闻实践,让我们从反思新闻业的历史,反思自身的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开始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受清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基金2012年青年项目“中国新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的资助,课题号:2012WHQN013)
注释:
①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American Democrat, [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p. 183. 转引自【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是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年~1837年)。民主党创建者之一,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在美国政治史上,1820年代与1830年代的第二党体系(Second Party System)以他为象征
④【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⑥【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著:《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58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⑦【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民主的不满》第1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⑧【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第102~13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美】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1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⑩王韬著:《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第206 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
[11]Pusey, James R. Wu Han:Attacking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Pas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84- 85.
[12]Cheek, Timothy.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M],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97, p.17.
[1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七卷五号,1920年5月1日
[14]转引自田方:《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第98页,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内部发行,2006年版
[15]陆定一著:《陆定一新闻文选》第8~9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16]朱联营:《延安时期中共新闻传播思想的创新实践及当代启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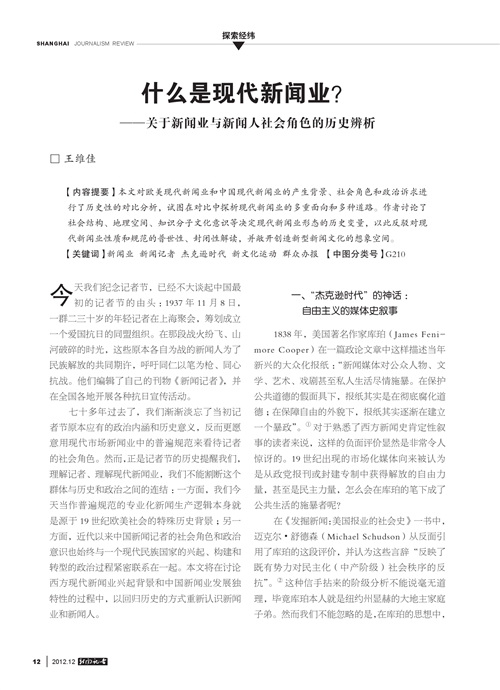
 制作维护
制作维护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