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传播的概念与范式初探
□吴飞 黄超
【本文提要】软实力传播是一个(或一组)体现了国际社会关系和经济贸易的时空、机制变革的过程,并且产生了跨地理区域、虚拟区域的信息流动、文化活动、精神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传播现象。这个概念是在软实力定义的争论基础上推出的,其内涵与外延可以从历史、权力、技术等方面做出探索性分析。软实力传播虽没形成一个规范、标准的概念,但存在着三种分析它的理论范式,即硬实力-软实力、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与建构主义范式。
【关键词】软实力传播 理论范式 历史形态 动态比较
【中图分类号】 G206
2011年6月11日,《华尔街日报》刊载新华社社长李从军文章,文中指出:相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进程,世界国际传播场域却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这首先表现在极不均衡的国际传播结构状态上,信息的传播主要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更重要的表现是,像美国这样的欧美发达国家采取了更灵活的软实力战略。从大众传媒、宗教系统、教育机构到工商贸易、公益慈善、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都成为其运用软实力的传播渠道,从而推行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而近两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大力推行以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互联网外交(Internet Diplomacy)为代表的外交新宠——巧实力(Smart Power)战略①,也不过是软实力战略在外交上的一种延伸和新体现。
软实力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话语是20世纪最后十年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传播格局之间不平衡的加剧和危险的不平等,对软实力的研究依然保持持续高温。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国际传播现象。在各国软实力演变的过程中,传播始终处于在场状态。因此,从传播学角度将软实力置于国际传播场域中,认真研究软实力传播的概念、范式,反思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软实力的分析框架,对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软实力传播概念的提出
世界的历史、政治、文化发展正走向一个纷争不休的节点,国际间的相互依存、联系正逐步加强,信息、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跨国交往与日俱增,这已成为包括政治、经济、信息传播在内的国际秩序新局面。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健康等一些公认的国际性事务与许多有影响的重要力量紧密联系。这些力量来自一个国家的内部环境,从全国到地方,并能承担来自国际上的外部压力。②在这些环境和压力中,软实力传播就是一个复杂且关键的力量。本文基于争论中的软实力研究,试从传播学视角阐释软实力传播这个命题,希冀获得新的理论发现或收获。
(一)软实力传播的内涵
从19世纪传播第一次进入公共话语时,美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从认识论角度对传播概念进行内涵理解的传统,我们在描述中可以把传播的界定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③此外,还有两种则是从本体论视角对传播的内涵进行界定。第一种定义将传播视为一种讯息产生效果的过程。第二种定义则将传播看做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过程。④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不仅仅是采用任何形式来送出和接受信息,而是一个整体的情景和完整的体验,总而言之,是一种人类关系。⑤可以看出,这些都表明了软实力可以把一个国家、地区、社群与另一个国家、地区、社群联结在一起。将本体论、认识论结合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综合地认识软实力传播的内涵。
第一,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软实力既是一个“关系性实力”(relational power),又是一个“结构性实力”(structural power)。⑥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关系性实力是主体(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或国家)通过传播手段促使对象(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或国家)采取某种行动的实力;而结构性实力是塑造和决定国家、机构、群体(集团)或个人的活动必须在其中进行的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信息传播结构的实力。第二,由于新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过程的时空区间更加向外延伸,时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物理含义(空间包括人类的精神空间和信息技术带来的虚拟空间)。这同样适用于思考软实力所存在的传播时空。第三,在原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软实力的扩张和国家之间通常存在一股力量差(power distance),这正是诞生所谓“传播权力”(power of communication)的来源。⑦权力的差距使得世界呈现出传播权力的高地和洼地。传播权力的高地形成世界权力的中心,赋予主体中心化的优越位置,洼地成为世界权力的边缘地带。中心内核向四周边缘膨胀,四周边缘又产生张力,因此是一个由内而外、内外互动的双向性的运动,形成主体-客体间双向、非对等的互动。第四,软实力的成功取决于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更包括两者之间的信息流动。所以,人们常常把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软实力研究联系在一起。人们也已经习惯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作为软实力的一种来源,把它们当做是一个国家语言的传播手段、标准化的特殊机制。⑧而随着传媒娱乐化、商业化、消费化的变革过程,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和丰富的商品,会产生使他人适应其文化的黏度,避免了硬实力的高额开销。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所谓软实力传播(Communication of Soft Power),应被看做是:一个(或一组)体现了国际社会关系和经济贸易的时空、机制变革的过程,并且产生了跨地理区域、虚拟区域的信息流动、文化活动、精神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传播现象。
此处,我们仍旧将软实力传播作为国际传播场域中的一种交往形式,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软实力概念脱胎于国际政治理论以及国际关系实践中,其原初内涵仍是强调一国通过文化、外交、政策对另一国家所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其次,虽然强调考察的对象是国家,但软实力传播是一种泛国际传播的体现,国家之间仍存在着非国家的国际行为体(如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传播正由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迈进,且两者之间的学术研究边界正趋于模糊。再次,有一点可以肯定,市场、国家、社会相互依存。不同的社会力量和不同的阶层都希望通过国家体现自己的意志和实现自己的利益。⑨
(二)软实力传播的外延
从软实力传播的主体角度来看,与上述主张类似但进行了更加详实阐述的学者有奈森·嘉戴尔斯、麦克·麦德沃等。他们认为,软实力传播的参与行为体不仅来源于国家、政府,还来源于大众传媒。⑩这里,软实力传播是一种由各个国家的政府、通讯社、媒体的传播行为所体现的一种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和互动行为。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专栏文章指出,“世界各地的众多孔子学院正在传播汉语,中国媒体也加强了传播中国世界观的努力”。由此可见,对软实力传播的理解是以国家作为传播的一个划分单位,具体的传播行为还应包括跨国界政府间以及非政府机构、组织之间的传播。与此类似的表述是塞义夫的界定,他认为,“非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决定了国际间软实力的传播结构”。[11]
而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软实力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大众传媒的一些特性发生了变化。在Web2.0时代,“个人出版者”、“可读写的互联网”等新要素先后出现,传播者变成了非专业、非机械性的个体。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之间可能通过社会化网络保持人格化的交往关系。受众成为某一虚拟社区的组织成员,而非我们原先理解的“受众是非特定的人群”。比如,受众网络活动中主要存在着三种典型的关系:一是由受众的社会网络构成的传播网络;二是受众间由于种种目的而结成的同盟;三是受众在公民活动中自然形成的权力分化。[12]
此外,软实力传播经常见诸公共外交、国际政治等实践领域,其功能层面上的概念外延往往生发出其他理解。比如,国内学者明安香从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作用方式和效果方面提出了“硬传播”与“软传播”概念。他认为国际传播可以分为两大类传播:一是直接向受众传递政治思想、宗教观念等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即硬传播;一是传递休闲娱乐、文化风俗等非意识形态信息或非显性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即软传播。[13]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廖卫民由加拿大学者伊尼斯的理论渊源提出了“传播国运论”,探讨了世界上文明、文化、民族之间软实力的传播活动“究竟是通过什么机制、渠道或力量关系影响到整个国家命运”。[14]
总之,涉及软实力传播的外延界定,包括软实力传播的主体与客体、研究的理论背景与角度、作用与影响,学界还未完全统一。软实力传播可以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因为它的研究“是一种由各国或各文化的政府和人民的传播努力所体现的一种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和互动行为”。[15]国家是软实力传播的一个重要划分单位,然而具体的传播行为体则是在跨越地理区域中活动的政府、机构、组织、大众。因此,我们认为,软实力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软实力传播包括大众传播[16]、人际传播等。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人际、大众传播只是在国际社会关系和经贸往来的时空中以传播方式出现的,参与行为体包括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群体或个人等等。狭义的软实力传播仅指借助大众传媒进行的传播活动。我们无意于创造一个新的学术名词,仅仅提出一个解释性的概念,旨在找寻可行的方法论,跳出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来批判地研究这个问题。
二、研究软实力传播的理论范式
软实力传播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至今都没有形成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规范、标准的概念。就像其他任何权力形式一样,人们会运用软实力传播去达到积极、利他的目标,也会利用它传播达到消极的企图和暴力恐怖的结果。为此,我们应该从传播学角度梳理分析软实力传播的理论范式。纵观国际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范式。[17]
(一)“硬实力-软实力”范式
第一种是约瑟夫·奈的“硬实力与软实力”范式,来自约瑟夫·奈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的《软实力》及其后续相关论文。奈首次将国家的综合实力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并通过两种实力的行为类型、力量来源两个维度来评估软实力(见图1,见本期第61页)。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奈所提出的这个分析框架强调,软实力传播的参与行为体(不论是国家、政府、组织、群体或个人)遵循一条连续的、线谱式的行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传播主体(who)和客体(to whom)以及信息编码、解码过程。从左到右,软实力传播的行为强制性逐步软化。其中,议程设置能力和吸引能力是塑造对方期望的行动能力。所谓“设定议程”是指长期、有效控制其他国家政治议程使其目标改变或无法达成的行为。奈曾一直强调,要完成软实力的吸引、接纳,就必须不断通过议程设定来进行传播活动。
其实,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奈的这条行为类型坐标源自传统“三论”中的信息论与控制论。香农和韦弗曾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一书中描绘了传播的简图(见图2,见本期第61页)。[19]以奈的行为类型坐标为例,软实力传播渠道中噪音越多,就越需要冗余,这又降低了传播内容的相对“熵”值。例如,美国之音通过嘈杂的传播渠道以及复杂的传播环境时,需要重复、强调、把握信息的关键部分,亦即要控制议程的设定。然而奈对软实力中议程设置能力的讨论缺乏一贯性,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欧内斯特·J·威尔森三世(Ernest J. Wilson III)就对这套分析框架提出了批评,认为围绕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讨论未将制定国际政治游戏的实力涵盖其中,且议程设置多少还是具有强制性,缺少效果上的考察。[21]而源于“控制论”的香农和韦弗模式意味着,信源、信宿、发射器和接收器是相互独立的,在当时对机械系统而言这通常是正确的,但对于由人类参与的软实力传播系统而言却并非如此。此后,奥斯古德、施拉姆等学者都进一步更新了传播理论研究的模式。[22]他们克服了单向直线的确定,明确补充了信息传播的反馈、环节、渠道等要素,这些更符合软实力传播的特点。
(二)“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范式
第二种是英国学者斯特兰奇[23]的“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范式,它是结构主义理论的演变。[24]在这个范式中,结构性实力是在较长时期和较大空间内,国际社会关系中软实力传播的动力,比关系性实力更具有决定意义。在这个范式中,结构性实力是指在特定的国际社会和政治经济情景中国际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之间)讨价还价的实力(bargaining power)。而这种讨价还价实力即为关系性实力,其运用、选择的范围早已被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预先控制。[25]比如,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规模、结构性的变革,其间像欧美大国这些行为体控制结构的实力意味着它们拥有更多的优势和机会利用软实力传播缓和变革中的威胁。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有人觉得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及行为结果应反映这一现实。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推出《论中国》一书指出,鉴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和经济安全,具体的讨价还价战略将变得至关重要。[26]他说:“美国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我们既不能主导,又无法抽身退缩,但我们仍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实力最接近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巨大挑战。”他认为,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中所使用的软实力“基本上正确”。“我们跟中国人打交道(讨价还价),最必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的共识何在。”
分析软实力传播的“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范式根植于传统意义上的系统论。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考察传播行为、过程是理解软实力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仅仅从过程本身或过程内部考虑问题,还不能解释软实力传播的全貌,尤其是不能清晰确定其内部结构、关系的互动过程。德国学者马莱兹克曾在系统模式下提出了一套关系性-结构性的传播范式(见图3,见本期第62页)。如果将软实力传播置于这个系统中,关系性实力就体现在传播者通过传播手段促使受者采取某种行动(产生相互印象、发出反馈)的实力;而结构性实力则体现在软实力传播的行为体活动必须在其群体组织、社会环境等制约和压力中进行的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信息传播结构的实力。然而,即便是系统论生发出来的模式也存在缺陷,马莱兹克的传播模式虽罗列了各种关系、结构因子,却没有对这些因子的作用强度、广度和影响的大小差异进行分析。我们知道,软实力传播强调的是吸引力和影响力。如此,我们很难厘清软实力传播的基本形态。这说明系统论框架下的理论范式研究软实力传播亟待完善。
(三)“建构主义”范式
除了上述两种范式外,还有一种可以用以分析软实力传播的理论路径就是“建构主义”范式。建构主义主要代表人尼古拉斯·奥努夫认为,我们通过国际社会关系实现自我和国家的存在。他断言,我们拥有的是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其中“人创造社会,社会创造人”,在这种互动的过程总通过这样的沟通(communication),我们在机制内部形成了行为规范。[28]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定行为体是社会构建的。通常所定义的国家或民族利益是各种行为体社会认同的结果。[29]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决定未来冲突的是文化和文明,战争将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爆发。国家软实力传播的状况主要取决于其位置是否接近由文化划分的不同文明交界线。[30]可以说,建构主义者强调运用一组在意义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学概念要素来解释软实力传播(同时也作为一种世界政治现象),主要是“规范”(norms)、“认同”(identity)、“文化”(culture)等非物质要素。体现在软实力传播的语境中,“规范”属于一种国际社会关系的约定,包括软实力传播的规则、标准、法律、习惯(比如国际互联网公约、国际电信联盟等);[31] “认同”指软实力传播者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交流、沟通以及关系所形成的,所谓“国家身份/形象认同”便属于建构主义议题。至于“文化”,它不仅影响国家软实力传播的各种动力、诱因,也影响国家软实力传播的基本特质以及历史形态。总的来说,“建构主义”范式在动力学方面对软实力传播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软实力传播源于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本质上是一个建构过程。
然而,在软实力传播过程中,认为无论是规范、认同还是文化,要研究其互动建构的本质,我们都离不开跨文化传播的语境。布莱恩·斯皮茨伯格提出,在跨文化语境中,有实力的交流,就是以符合语境的方式完成行为体所应完成的动作目标。他强调跨文化传播是一种实力,并提出一个较之以往更有成效的方法,建立了一种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建构主义模式(见图4,见本期第63页)。该模式概括出了一系列命题,分为三个分析层:个人系统、情景系统以及关系系统。[32]个人系统包括在一般国际社会关系意义上,个人所拥有的有助于软实力传播的互动特征(比如姚明、刘翔通过体育竞赛、文化交流、访美让中国与国际社会产生互动对话)。情景系统包括在某一个特定互动情节中,一个特定行为体(主演者)所具有的,有助于同另一个行为体(合演者)成功互动的特征(比如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于2012年1月访美期间,观看NBA赛事、重访艾奥瓦州等公共外交行为扩展了中美两国及其民众的互动空间)。关系系统包括帮助某一行为体在整个国际社会关系范围内,而不是某个特定互动情节中,提高软实力传播的所有因素(比如希拉里提出“互联网自由”,让美国在全球信息传播空间免受传统主权束缚,与他国建立新的建设性关系,并使他国民众与美国民众可以通过不受限制的信息流动进行互动交流)。
根据斯皮茨伯格的观点,在个人系统中,软实力传播的参与行为体的动机、知识、交流技巧增强,其传播能力也随之提高[34];在情景系统中,软实力传播中主演者的传播地位、合演者对主演者传播能力的印象会影响软实力传播的效果;[35]在关系系统中,自主需要和亲密需要的互动实现、社会支持的渠道增多,相互吸引力、信任以及关系网的整合增强,软实力传播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借助斯皮茨伯格的建构主义模式,我们可以勾勒出了一个有效的软实力传播参与行为体的轮廓。斯氏的分析范式以指导实践的命题形式提出,在本质上是一套行动方案,且其命题都有所谓的上限。然而,软实力传播是基于国际社会关系和经济贸易变革组织过程中的社会建构,拥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社会传播的总过程。斯氏模式对于从宏观、中观、微观全面考察软实力传播来说,存在假设谬误和论证薄弱的危险。[36]
三、余论
实际上,软实力传播在传播学理论、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广泛认同,更没有准确的界定。在历史上,将信息作为文化、价值的传播载体并将其看做一种“特殊”实力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1976年在阿尔及尔、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国家会议。前者宣布,“帝国主义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政治与经济领域,还存在于文化领域”。后者则通过了著名的《新德里宣言》,其中提到:“当前全球信息流通存在严重的不足与不平衡,信息传播工具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当前的信息发送实力主要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的少数通讯社手中”。[37]可以看出,虽然这种观点没有提及“软”、“硬”实力这一对具有相对含义的名词,但是点明了这样一种观点:世界各国以政府、通讯社为主导的传播力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影响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软着陆于文化领域。
谈到软实力传播,我们以传播这个术语非常专业的意义为前提。一般而言,传播这个术语指有意义的信息的传输,这些信息经常以语言的形式来表达,但也可以用图像、手势或者其他根据共同原则或代码来使用的符号传达。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传播发生在面对面的社会交往背景下:信息传达给在现场的个人或人们,这些人的反应以直接、持续的反馈形式提供给传达信息的人。
然而,在软实力传播的情况下,传播过程的本质迥然不同。这里强调四个重要的差异。第一个差异是,尽管软实力传播中的信息是为受众生产的,但构成受众的个体并不一定出现在信息生产、传输或扩散的现场,软实力传播涉及我们所说的“在生产与接收之间存在一种已经制定的断裂”。第二个差异涉及软实力传播技术工具的本质。第三个差异是软实力传播中的信息普遍商品化,亦即信息可以作为在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存在。一切产生现实价值的传播产品必须与人们既有的信息消费经验、信息消费偏好和信息消费模式相契合,否则传播者就会沦落为“沙漠中的布道者”。如果内容是给别人看的,你就必须要和别人的需求方式以及偏好、口味相接轨。[38]第四个差异与传播过程中信息可获得性有关,也就是广大的受众获得信息的可能性。[39]
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研究视角认识这个问题呢?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借鉴意义。在美国,跨文化传播正式研究出现在1946年,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外服务法案,并建立了国外服务研究所,为外交人员提供语言和人类学方面的文化培训。在对外服务研究所之外,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通常与爱德华·霍尔在1959年所写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联系在一起。与对外服务的实践联系起来,并把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拓展,容纳进了传播学。[40]此外,跨文化传播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最早起源于爱德华·霍尔的研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工作,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他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被公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另外两个主要的视角:解释的和批判的。传统视角关注的是现实可行性,解释性视角关注的是彼此的理解,而批判性视角关注的是社会中不易觉察却真实存在的压迫形式,它已成为现代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领域。[41]有鉴于此,当了解更多关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之后,我们应该以三个视角以及认识论、本体论的角度进一步理解软实力传播的问题,比如软实力传播与现实(历史)的关系——只是反映、再现,还是相互建构或者是现实的单向影响;软实力传播活动的讨论——只是一个行动、过程、系统,还是符号的交流、大范围的文化建构、权力的社会网络;新的媒介技术对软实力传播参与者(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
(作者吴飞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学院教授、博导,黄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是2009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09ZJD0010〉最终成果的一部分)
注释:
①2004年,苏珊尼·诺瑟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巧实力》(Smart Power)的论文中指出,“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国际主义的旗号,实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宣称要扩展人权和民主。但是布什政府采取的军事危险政策同他们声称的理念根本不相符。“必须实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不仅能更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而且能走得更远,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促进美国的利益。”苏珊尼认为巧实力战略是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延伸。
②Mehd Semati,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p. 4.
③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第4~10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④陈力丹、易正林:《传播学关键词》第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⑤Nayyar Shamsi, Encyclopa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Delhi , Anmol Publications PVT Ltd., 2005, p.7.
⑥S. Strange, State and Markets, Lond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pp. 23~42.
⑦[16]吴飞、杨席珍:《后殖民视角下的殖民传播》,《新闻大学》2010年第3期
⑧Markus Karllson, Economic Warfare on the Silver Screen,.France24, http://www.france24.com/en/20110625-economic-warfare-on-the-silver-screen-cinema-cannes-festival-2011-hollywood-france, 2012-01-28.
⑨赵月枝、张海华:《传播、政治与新媒体:更广阔的多维视角——专访加拿大传播学者赵月枝》,郭镇之主编《全球传媒评论(V)》第14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⑩奈森·嘉戴尔斯、麦克·麦德沃:《全球媒体时代的软实力之争: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形象》第143页,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11]Saif Al-Islam Alqadhafi.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Democratisation of GlobalGovernance Institutions: From ‘Soft Power’ to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London, Ph.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2007, p.3.
[12]彭兰:《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3]明安香:《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硬传播和软传播》,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2008年11月
[14]廖卫民:《传播与国运:国家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研究》第8~15页,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15]姜飞:《传播与文化》总序第2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第12~1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8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19][22]沃纳·J·赛佛林、小詹姆士·W·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42、第49~57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C. Shannon & W. 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9, p.98.
[21]Ernest J. Wilson III, Hard Power, Soft Power, Smar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vol. 616, No.1, pp.110~124.
[23]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24][28]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112、15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25]Salvador Santino Regilme Jr., The Chimera of Europe's Normative Power in East Asia: A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ecurity Studies, 2011, 5, p.12.
[26]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p.493~508.
[2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67页,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4, Vol 88(2), pp.384~396.
[30]Samuel P. He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 72(3), pp.22~48.
[31]Martha Finn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23.
[32][33][3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第412~413、412、42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34]斯皮茨伯格认为在个人系统层面,软实力传播的动机与其参与行为体的信息、有关回报效果的信心、态度倾向以及某一情景的成本-效益比率有密切联系。软实力传播参与行为体的知识与传播任务相关的程序知识、获得知识的技巧、身份和角色的种类、知识倾向性有密切联系。行为体的交流技巧与传播中的他人中心主义、协调性、镇定度、表现力和适应力成正相关。同32,第414~418页。
[35]斯皮茨伯格认为在情景系统层面,软实力传播能力与主演者的动机、知识和技巧,行为语境障碍,获得的有价值成果,现有的特征性交流成正相关联系。合演者对主演者软实力传播能力的印象与主演者实现合演者的积极期望、以正常方式违背合演者的消极期望、完成合演者对其软实力传播能力的期望、对正面影响的正常抽搭和对负面影响的补偿、主演者对权力关系的补偿成正相关。同32,第418~423页。
[37]卡拉·诺顿斯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浴火重生的主张》,《中国记者》2011年第8期
[38]喻国明:《让中国声音在世界有效传播——关于对外传播的若干思考》,《新闻传播》2010年第10期
[39]转引自:约翰·B·汤普森:《大众传播与现代文化: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贡献》,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第69~7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40]Fred E. Jandt,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dentities in a Global Community, Fourth Edition, CA, Sage, 2004, pp. 38~39.
[41]Bradford J. Hall, Among Cultures: The Challenge of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Thomson Wadsworth, 2005, pp.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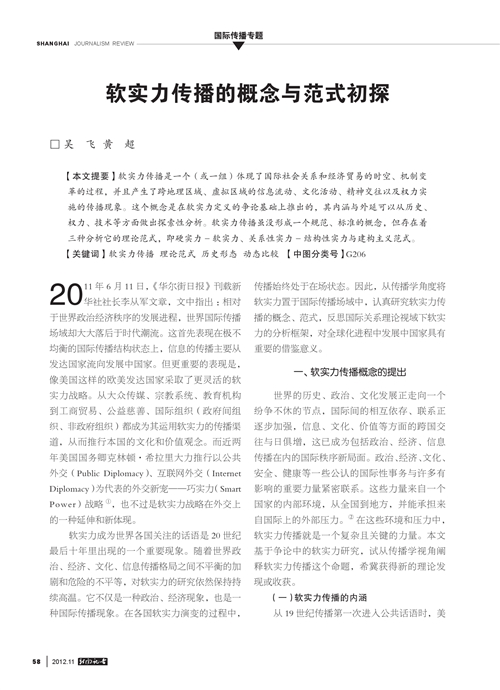
 制作维护
制作维护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