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范视角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新闻人员的职业规范
□熊壮 贺碧霄
【本文提要】市场化改革给新闻业带来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国传媒人职业规范的严重缺失。本文尝试从失范理论的角度切入这一现实问题,在对经验材料解读的基础上,展现这一现象背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个体从业者对此的适应性类型。最后,强调了基于哈贝马斯交往伦理理论的“道德即责任”的传媒责任模式来看待职业规范缺失问题在研究策略上的优势。
【关键词】新闻从业人员 职业规范 失范 交往伦理
【中图分类号】G210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程。经济层面的改革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给新闻业带来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比如,不少媒体逐渐摆脱政府的预算约束,官方媒体也开始注意受众的需求,新闻从业者或隐或明地对自身角色和媒介角色进行了重新界定,在计划经济时代鲜见的媒体间竞争日益加剧等等。①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我国传媒人职业规范缺失的问题“不容乐观”,“其中有一些由于普遍存在,而没有被传媒人意识到属于违规行为”。②这些违规行为既影响传媒发挥正常的社会职责,也成为影响其公信力的最大障碍。
那么,如何理解社会转型时期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缺失这种“不容乐观”的现状?它因何而发生?它是否是这个转型社会(或者说新闻改革)必然要承担的一种“命运”?本文尝试从社会失范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考察,突出的是对“失范现象”的理解及其“命运”的关怀。尽管已有不少文献尝试从社会失范的角度来描述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规范问题,③但本文力图展现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规范缺失现象及其背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
一、失范与社会转型
涂尔干最早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提出失范(anomie)的概念。在他看来,失范首先是一个社会基本事实,它“代表了社会秩序紊乱和道德规范失衡的反向动向”。其次,它又是“可以治愈的反常现象”。④涂尔干主要从集体意识层面来讨论失范,进而强调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尽快解决失范问题。
涂尔干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失范的讨论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失范也逐渐沦落成一个边缘性概念。直到默顿1938年发表《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分析越轨行为及其社会文化根源,才把失范这个概念重新拾起,并建立起自己的失范理论。默顿首先区分了个体层面的失范(anomie)与社会层面的失范(anomia)。⑤具体来说,社会层面的失范指在急剧的社会变迁情况下,整个社会系统所出现的目标匮乏和统一的价值观缺失;而个体层面的失范则指特定社会条件下,个体行动者所出现的失范。默顿的这一区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意识的价值效果,单纯将失范分析局限于社会系统和制度的水平上”⑥。但是,考虑到具体的经验研究层面,社会层面的失范这个概念确实具有可操作化的价值。由于社会行动者主观上所感受到或反映出来的失范,往往缺少明确的指涉对象,它可以是无所适从或迷茫,也可以是冷漠或颓废等⑦。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尽量客观地记录行动者的这些主观感受,而非从理论想象的角度去“规定”行动者具体(失范)行为的原因或动机。默顿的失范理论又从批判和修正结构功能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角度出发,界分了功能所形成的意图性和非意图性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失范既是对一般功能的反动,又可以对功能概念本身构成挑战”,⑧因此使得失范理论获得处理社会变迁这样的动态问题的能力和优势。
默顿之后,在失范研究方面涌现出各种风格迥异的失范理论以及与失范问题相关的理论。⑨本文的主旨不在失范理论本身,而是意在借用失范理论的视角来探讨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缺失的问题。因此,对失范理论的梳理到此打住,下面需要说明的是采用失范的视角来研究新闻规范缺失问题的优势。
在我们对于新闻职业规范的研究和讨论中,职业规范的缺失往往是作为“反常”现象出现的。这就使得它在肯定性和否定性两方面都不具有社会构成的意义,因此也就失去了社会解释层面上的意义。⑩换言之,一旦职业规范缺失这种失范现象不具备社会解释的实质性基础,我们就只能把它当作“另类”来处理,讨论则落在应然的规范层面。这里并非说应然性的讨论不需要,而是强调这种思路止于描述层面,无法回答本文引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即新闻职业规范的缺失是否是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是否“凝结着一种社会解释的因果关系” [11]换言之,我们既要从现象层面去讨论失范行为,又要关注其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即失范的成因。而且对失范原因的讨论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归纳层面,更应该提出机制性的解释。[12]
实际上,造成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规范缺失现状的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制度供给不足”,包括体制本身的问题以及转型过程中职业规范的不健全、不完善;二是“有规范不遵守”。相对应的措施则无非是强调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教育,使记者内化自己的职业角色。[13]这类讨论尽管必要,但仍旧是在“失范”的表面上看问题,而忽视了“原有制度结构中的失范,恰恰构成了新的社会常规化过程的一个环节”的可能性。[14]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假定在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结构作为制约性的因素存在,而人的行动附着于这个结构之上。但那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构能够准确地预测出每个人的行动,不合结构的行动(可以理解为失范行为或越轨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既有可能是因为结构对于人的行为的约束不是那么的彻底(如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不足),也有可能因为结构里面有缝隙(如行为规范本身无法穷尽所有可能情况),还有可能是因为结构里面本身就有矛盾的因素,或者大的结构下面会有次级的结构,这些都会导致行动者做出违背大的结构的行为。虽然这些不合规矩的行为每时每刻都存在,但在大多数时间里,这些行为对于结构本身是没有影响的。但有一些不合规矩的行动会在某些特定历史社会因素背景下被“放大”,对结构造成影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促成“放大”某些行为的特定条件,进而去讨论它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结构,这个过程又是怎么发生的。
因此,失范的视角要求我们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去,研究失范现象对社会构成所产生的创造作用。简言之,采取失范的视角,我们才能发现失范(行动)与社会变迁(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进而才能发展出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不但能够将大众传播过程的诸多层面彼此相互关联起来,而且将它们和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核心层面关联起来”。[15]当然,笔者并无那么大的野心,只是希望引入失范的视角,结合现代社会学中对结构和行动这对二元关系的理解,来探讨新闻职业规范缺失问题的特定社会结构性因素,进而提出转型时期新闻改革中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二、“失范”的社会过程
周俊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新闻失范行为稳定的高发状态”;[16]陈力丹则概括了当前传媒(人)在职业规范方面的15问题,[17]比如广告与新闻栏目(节目)或其他节目混淆、“媒介事件”频繁以及炒作明星绯闻和犯罪新闻等等。下文仅就其中的一些问题,结合媒体的不同性质来探讨失范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及其与社会转型、新闻改革的勾连。
1.党报:市场化改革的含义为何?
我国新闻改革的显著特征和主要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市场化,[18]市场化的效果如何却众说纷纭。[19]
对党报而言市场化是否意味着报纸所有权的改变,或者上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然而,市场化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从单纯的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转变为一个具体的利益单元”,[20]因为这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党报的一些经费来源,以及某些党报是否具有盈利能力的问题。笔者曾到某部委主管的一份报纸实习,主编对笔者说:报纸正在改版,希望能办得活泼一点,毕竟报纸要慢慢市场化。而笔者所观察到的报纸记者最紧张的事就是为×××(某单位)做了一个版,钱有没有打到账上,会不会影响到今年报社摊派下来的经营“指标”。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种变相的“有偿新闻”在“市场化”这一改革话语中获得了某种正当性。
正如某机关报部门主任级的编辑所说,“新闻改革如何搞?我们不清楚,上面也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向市场,否则没有出路”。[21]但这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原则带来的却是国家和市场的双重管制。从根本上讲,我国新闻媒体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而出现的“体制改造”,其动力恰恰源自新闻改革大环境下的不确定性。[22]
那么,完全的市场化是否意味着一个更好的结果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我们可以设想像《中国妇女报》这样的机关报,完全市场化的可能结果:要么是在现行“党的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下,被市场淘汰;要么是转变成一份时尚的、精英女性的刊物。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国会利用市场机制来“抵制”激进工人阶级报刊如出一辙。[23]何舟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两股力量的“拔河”模式来解释市场化后党报的发展演变。他认为,党报“不得不做而且可以做的是”,将自己变成“某种既能赢利又能从事舆论营造的‘企事业’”。[2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市场机制引发了利益、生存、发展之争,引发记者行为的多种选择”。[25]换言之,新闻职业内部的分层与流动的加剧,导致了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化,使传媒蜕变为一个所谓的“利益追逐的场所”,[26]职业精神的淡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媒体就是党政权力机关的一部分。市场化改革以后,传媒在名义上的社会职业色彩有所加强,但从业者的观念却很难很快相应有所改变。因此,媒体从业人员很容易产生“认知冲突”(cognitive dissonance)——虽然不是公务人员,但似乎拥有某种“公权力”。[27]这种简单地对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规律的接受,[28]就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现象,比如以权力换取报刊的发行量和广告额。
2.市场化媒体:商业化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
市场化媒体的情况迥异于党报。与市场化媒体的职业规范问题相关的一个议题是新闻专业主义,正如潘忠党和陈韬文[29]所说,经济改革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那么,它也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某种可能。亦如陆晔和潘忠党[30]所言,新闻专业主义本身就是“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表现”。这些话语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在强调市场化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某种因果关系。
当然,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只要回到改革前后的具体情境,我们就能明白,提倡新闻专业主义的那些学者们,往往看到的是国家权力的负面,即压制性的一面,而市场自然使他们联想到解放。[31]如果仔细检视陆晔和潘忠党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即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职业社区控制模式”,我们也不难体会到,该定义使得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挑战“党的新闻事业”模式的力量。[32]当然,“市场带来解放力量”这一命题也被不少对市场化媒体的研究所“证实”。[33]
笔者并非要否定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放性力量,只是想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其局限性的方面。专业主义的“碎片化和局域的呈现”,以及其“西方标准,中国表述”仅是一个显见的层次。另一个层次是其已然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后的置换效应。政府(包括从属于它的官方媒体)、媒体机构(非官方的)、新闻从业者、社会(或民间)都看到专业主义的巨大潜力和可塑性,都积极参与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新闻从业者宣扬专业主义为自身建立身份认同;媒体机构推崇一定的专业主义,“比如‘追求真理’、‘帮助公众’,以及‘反映社会黑暗面’这些受到公众欢迎的话语”,而实际上是其一种占有市场的策略,传媒之“公共性”却付之阙如;党和政府也对专业主义有诉求,以此显示出党的纯洁性;而当大众面对转型期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官员的贪污腐败时,人们希望专业主义媒体能够“充当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纽带”。[34]一言以蔽之,中国大陆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并非是从新闻业职业化进程中自然生发和演化出来的,而是从西方辗转舶来的,其本土化过程中又裹挟着特定转型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带着很强的权宜性和策略性。当然,不同的专业社群恐怕对专业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35]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专业主义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性。就美国的情况而言,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客观性”,就是一个历史产物,[36]而专业主义本身也不过是一个已然过去的“现代主义高峰”(highmodernism)。[37]中国的情况其实亦如此。我们固然不能否定改革初期随市场化而来的专业主义的解放性活力,但是随着商业化的侵蚀,专业主义恐怕早已随着市场与国家的紧密结合而荡然无存。[38]正如赵月枝所说,“商业化导致中国媒体的繁荣,使媒体体系的某些部分更能回应受众的要求,也使媒体工作者的精英主义有所调节,出现了对民众的关注……但是市场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结构性偏差,它本身不是一个价值中性的机制”。[39]例如,在笔者亲历的一次媒体宣讲会上,某都市报的老总在谈到最近报纸准备提价(从原来的5角涨到1元)时说,“我觉得报纸的价格和它的质量是要相称的……如果某个读者因为上涨5角钱而不买我们的报纸,那他就不是我们报纸的读者……我们读者就是那些知识白领,那些住窝棚的人显然不是我们的读者……”而检视该报的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该报最早是做市民新闻起家,读者对象大多就是那些所谓“住窝棚的人”!但是,在谈到该报的宗旨时,老总却声称报纸“力求推动社会进步”。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质疑他所谓的“社会进步”是什么样的社会进步,其受益者又是哪些人呢?可以想象的是,所谓的“推动社会进步”,无非是传媒自己策划的且并无多大新闻价值的人为“事实”而已。这种“媒介事件”通常以“党和国家正面的口号、美好的追求作为切入口,似乎很高尚,其实超越了传媒自身的社会职能,目的是通过大肆报道而提高传媒的威望”。[40]此外,媒体在商业逻辑下,为吸引广告商而创办的诸如“汽车周刊”、“住房周刊”,却被合理化为“服务公众”。
3.“失范”的个体适应及其类型
正如默顿在《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强调:“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发现某些社会结构怎样对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明确的压力,使其产生非遵从行为而不是遵从行为。” [41]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的影响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个体在社会失范中的适应类型。默顿依据个体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接受或拒斥,把个体的适应类型划分为五个类型: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42]但是,其中“遵从”本身不属于越轨行为;“退却主义”“却可能是最不常见的”。[43]而把失范作为一种力图建立新结构的“反抗”,已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所以,下文将着重分析较有参照意义的创新和仪式主义两种类型。
所谓“创新”,是指“当个体接受了对目标的文化强调,却没有同样地将决定达到此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的制度性规范内化,就会出现这种反应。” [44]举例来说,当在体制内“成名”是一种“想象”[45]的时候,新闻从业者就会寻求其他的方式去寻求所谓的“成名”。比如,把自己的社会资本(如从业经历所积累的人际关系)“变现”为利益[46]。当然,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失范的可能性也不尽相同。比如,何舟就观察到,从总体上看,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情况存在地区差异。[47]一般地,如果新闻从业人员有相对丰厚的收入和较好的福利,因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而获得处罚甚至开除的代价较大,则不太可能去“失范”。此外,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异,形成诸如“送红包”等陋规的条件不同,也会影响到从业者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情况。
“仪式主义”(ritualism)可以理解为某种从众行为。特别是在从业者自身“从来都不清楚具体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时候,以及因“人情社会”导致新闻道德的界限十分模糊的时候,仪式主义就可能出现。比如,一位记者就困惑于因工作关系的请客吃饭和被请吃饭:“我怎么才能划分道德界限?我怎么做才能既保持新闻职业道德而不得罪人?” [48]又比如,在接受被访者的红包、招待用餐和免费旅游等可能影响新闻品质的问题时,不少记者就认为这是“风气所及,不接受反而会被视为异数”。[49]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分析假设社会结构产生了某种导致失范行为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我们在分析中指出不同个体对导致失范的压力的不同适应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就提出了导致这些压力产生的某些机制。[50]
三、讨论与结语
当今中国的新闻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因为它本身就嵌入在社会变革的动态过程之中。新闻职业伦理规范问题往往交织着媒介性质、新闻文化、媒体负责人的素养、新闻教育和培训、管理体制、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51]本文只是尝试从失范的角度切入,初步展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规范缺失现象背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并希望能从这个角度引发一些新的讨论和反思。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职业规范缺失。以往的讨论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加强制度建设和从业者的自律,这些应对措施都基于具体的新闻道德条文或规范的存在。但实际的情况是,新闻职业道德规范问题往往是一种悖论或困境,具体的条文或规范往往是抽象的,未必能给出具体的解答;而且条文或规范亦不可能面面俱到,穷尽所有可能情况。因此,美国学者格拉瑟和艾特玛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ethics)而提出道德即责任(being-ethical-means-being-accountable)的传媒责任模式。该模式强调了雄辩的作用,认为伦理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是一种论证,而不仅仅是一个选择。新闻伦理道德问题不是新闻从业者无法辨识对错,而在于他们是否能清晰、系统、反思性地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新闻伦理道德最终要求从业者能公开地、令人信服地合理化对道德悖论或困境的应对(resolution),而道德的目的则是落实传媒的责任。[52]
该责任模式并不旨在提供解决伦理道德问题的答案,而是提供寻求答案的途径。这一看法在对我们如何看待伦理道德问题上极具启发性。正如在开篇所强调的,社会变迁是我们探讨新闻失范的背景和前提。简言之,如果我们不去追问社会变迁这一常规性在“新闻失范的社会过程”中所具有的实质涵义,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这一过程。这里所谓的实质涵义,不在于区分对与错,而在于一种话语建构过程,即在面对道德、法律、政经等具体情境下,新闻从业者的行事逻辑何在?[53]从研究策略上讲,该模式启发我们不是去用所谓的“专业主义”或“传统文化”等来“解释”新闻失范,而是去看不同的“专业主义”、或“文化传统”等话语在具体的情境下如何被从业者组合利用来合理化其行为。■
(熊壮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候选人,贺碧霄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博士后)
注释:
①He,Z.,"Working With A Dying Ideology:Dissonance and Its Reductionin Chinese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2000,Vol.1,No.1
②[13][17][25][40]陈力丹:《内化传媒人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规范》,传媒学术网2005
③[16]周俊:《转型社会中我国新闻失范行为状况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④⑦⑧⑨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第17、39、40、58~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Merton,R.“Anomie,Anomia,and Social Interaction”,InM.B.Clinard(ed.).Anomieand Deviant Behavior:A Discussion and Critique,Glencoe:Free Press
⑥李汉林、渠敬东、夏传玲、陈华珊:《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以社会团结为视角》第3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⑩[11]渠敬东:《失范理论大纲》,《韦伯:法律与价值》第353、3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参考Hedstrom,P.&Swedberg,R.(eds.),Social Mechanisms: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4]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5]Golding,P.,&Murdock,G.,"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Communication Research,1978,Vol.5,No.3
[18]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文化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Lin,F.“A Survey Reporton Chinese Journalist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June 2010,Vol.202
[21]转引自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湾)1997年第54期
[22]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23]参看Curran,J.Media and Power(pp.79-103),London;New York:Rout ledge,2002
[24][28][47][48]何舟:《从喉舌到党营舆论公司:中共党报的演化》,载何舟、陈怀林编著《中国传媒新论》第66-101页,(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8年版
[26][46]尹连根、王海燕:《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舟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2008年,http://linmingkeziju.blogbus.com/logs/17595162.html
[27]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第24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Pan,Z.&Chan,J.M.,"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3,Vol.30,No.6
[30][32][45]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71期
[31][39]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制度与权力的关系》,《传播与社会季刊》(香港)2007年第2期
[33]参见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34]童静蓉:《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话语》,《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6年第1期
[35]参考孙藜、张志安:《“学者型记者”:中国语境下的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以〈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理论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6]Schudson,M.,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New York: Basic Books,1978
[37]Hallin,D.,"The Passing of the 'High Modernism' of American Journalis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2,Vol.42,No.3
[38]Lee,C.,He,Z.&Huang,Y.,"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Conglome rated: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Media,Cultureand Society,2006,Vol.28,No.5
[41][42][43][44][美]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224、233、234、249、235页,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49][51]陈力丹、王辰瑶、季为民:《艰难的新闻自律——我国新闻职业规范的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理论分析》第40、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50][美]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254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52]Glasser,T.L.&Ettema,J.S.“Ethicsand Eloquencein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2008,Vol.9,No.4
[53]比如Lin,F.“A Survey Reporton Chinese Journalist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2010,Vol.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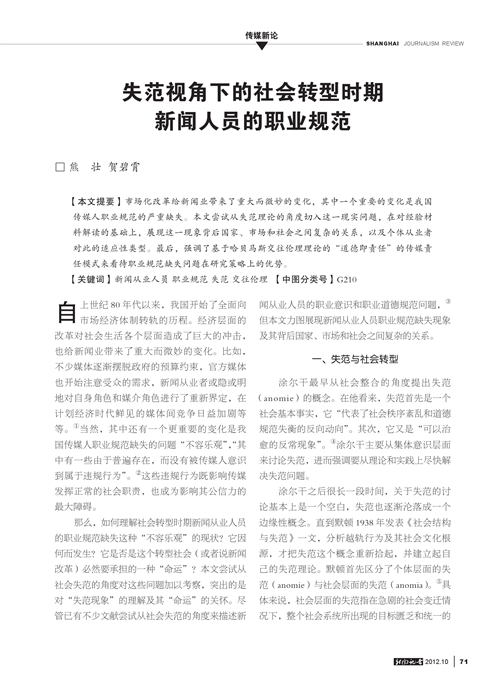
 制作维护
制作维护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