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上言论自由法律边界的有益探索
对网上言论自由法律边界的有益探索
——评“微博第一案”两审判决
□ 魏永征
【本文提要】随着数字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体制内的大众媒介(包括它们的网站)和众多网民使用各种自媒体进行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传播体制。“微博第一案”判决肯定公民网上言论的宪法权利地位,对网上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作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 言论自由 互联网 微博 名誉权 【中图分类号】 G210
北京金山安全软件公司诉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侵害名誉权案,因号称“微博第一案”而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论。本文认为,此案之值得关注,不仅因为是我国第一起微博言论承担侵权责任的判例,更在于初审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①和终审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②与时俱进,在审判中充分而审慎地注意到在网络环境中公民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两项法益的平衡,就如何厘定网上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提出了若干富有启示的观点。鉴于两审判决在被告删除微博言论和赔偿数额方面虽有变动,但结论和论点基本一致,故予以合并引述。
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崭新方式
判决书指出:“个人微博作为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为实现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平台”。判词还认为:“个人微博的特点是分享自我的感性平台而非追求理性公正的官方媒体,因此相比正式场合的言论,微博上的言论随意性更强,主观色彩更加浓厚,相应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尺度也更宽。”这些话,明确肯定了公民网上表达的宪法权利地位,并且触及了这种表达的特征。
我国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体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把它概括为“公民有自由,媒体归国家”③。法律(行政法规)肯定公民可以“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同时规定报刊和其他出版单位实行主办单位和主管机关制、电台电视台实行政府台制等,确保大众媒介必须直接或间接隶属于党政机关之下,也就是将大众传播纳入党领导下的体制以内,承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正确舆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等使命。这种体制体现了“党管媒体”和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之间的现实关系。大众传播的重要特点是管道决定内容。传播学研究证明,在大众媒介传播管道的各个环节上布满了把关人,个人言论可否表达、如何表达都要经过把关人的过滤和加工。所以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内容。公民有通过大众传媒表达的自由,而大众传媒也有选择是否发表的自由,这是各国通例④;至于主管机关对下属大众媒体的内容进行调控,则属于内部纪律管理,都不涉及宪法问题。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国际上通常把互联网服务方式分为ICP和ISP(不同于我国互联网服务商许可证种类)⑤,ISP特点就是管道与内容分离。互联网用户可以在ISP提供的管道上以BBS、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社交网站(SNS)等方式自由表达诉求、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等等,管道上不可能事先设置把关人。这种传播可以有大众传播的效果(即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播),但却不存在大众媒介特有的组织,而是用户个人的表达,人们称为“自媒体”(self-media),或称UGC(User-Generated Content)。自媒体的行为主体大都是公民个人,与我国大众媒介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的行政许可不同,他们行使表达行为的权利来源于《宪法》,是受《宪法》保障的,在规制网上言论时如何注意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
据国新办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评估报告》⑥,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4.57亿,中国境内现有网络论坛上百万个,博客用户2.95亿个。网民每天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这样庞大的规模,表明一个有别于前述体制内大众媒介的另类传播体制已在我国形成。这个报告同样肯定互联网是公民行使表达权利的新渠道,显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可见我国从行政到司法对此有高度共识。
“微博第一案”两审判决书都对公民网上表达即自媒体的特点作了一定描述,如说:它是个人的,不同于前述体制内的大众媒介;它具有随意性,并非大众媒介上经过加工整合的正式言论;它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即不一定服从某个统一的“旋律”,而呈现多元的特点。判决书对这类表达的主导面持肯定态度,如指出“往往起到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所以,判决书认为“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尺度也更宽”。
当然,个人的、随意的、主观的,何尝不是又描述了自媒体的弱点。随意、主观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造成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损害,诸如捏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诽谤、侵害隐私等情况已经屡屡发生。但是对体制外的自媒体不可能像对体制内的大众媒介那样通过宣传纪律进行调控,这样依法规制就成为规制自媒体的重要手段。本案判决正是对违法的自媒体言论的一种规制。
寻求言论自由和名誉权的平衡
判决书明确指出言论自由的相对性。国际人权公约认为言论自由属于可以予以限制的权利,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负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⑦。本案属于名誉权案件,所以判词着重指出言论自由“以不得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利为限”。
在学界曾经讨论过言论自由和名誉权等人格权何者优先的问题,有的论者主张言论自由对于其他公民权利具有凌驾地位,这种从美国某些学者那里搬来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混乱,有的判决甚至提出受批评者应该“忍受”媒体和公众的“苛责”⑧,还被说成是为支持舆论监督树立了“标杆”。本案判决明确遵循平衡论:“在微博上,当公民言论自由与他人利益发生权利冲突时,……对微博上人们的言论是否受言论自由的保障、是否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不当伤害,应该进行法益衡量”。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名誉权在我国宪法中都明文予以保护,并无高下之分,平衡论是有根据的,“凌驾论”不符合我国宪法框架。
判决书指出应该“综合考虑发言人的具体身份、所发布言论的具体内容、相关语境、受众的具体情况、言论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体后果等加以判断”。其中对发言人身份的分析富有创意,这里着重予以述评。
本案发言人即被告人周鸿祎,是我国著名的从事互联网安全软件与互联网服务的在纽约上市的奇虎360公司的董事长。判决书就此做出如下分析(本文略有整理):周鸿祎是一位公民,但并非普通公民。他的公司与他所指责的金山公司存在着竞争关系,在将竞争对手的负面评价公之于众时,理应三思而行、克制而为。他在现实社会中是一位重要人物,投射在微博领域也是重要的层级,拥有众多的关注者,亦即享有更多的话语权,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他对自己微博言论及其后果应有更为自觉的认识,应避免因不实或不公正客观的言论造成对竞争对手的诋毁,进而损害其商誉。所以对于周鸿祎通过微博行使言论自由的限制和注意义务的要求应当适当高于普通网民或消费者。这是判决周鸿祎承担侵权责任的重要理由。
这段分析堪称精辟,完全符合民事侵权的归责理论。侵害名誉权案件采取普通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是主观的,而判定过错的途径只能是客观的。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要看他对于自己行为可能发生的损害是否应当注意却未予注意。注意义务因人而异:英美法提出的“合理人”(a reasonable man)标准或大陆法所持的“善良家父”(a bonus paterfamilias)标准适用于大多数人,而对于专业人士在与自己专业有关的行为中则适用较高的注意义务。本案对周鸿祎适用高于普通人的注意义务是有根据的。
对于侵权过错的注意义务的区别对待,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虽然人人都可以在互联网行使言论权利,但是不同人们的话语影响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许多博客或微博只有自己亲朋好友几十位浏览者、关注者,而我们知道现在人气最高的大号微博其关注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是《人民日报》日发量的5倍。这些大号微博往往又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知名人士,并且“深悉网络传播之快之广”,要求他们对自己言论承担较高的义务和责任毫不为过。判词说到对网上的言论自由把握尺度应该更宽,还蕴含着对体制内的大众媒体和专业新闻记者的报道和评论应有更严格的责任要求的意思,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本案判决体现的这一原则,对于规制网上言论、形成良好网上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只是行为的最低底线,言论表达尤其如此。很多错误言论并不违法,但是公开传播同样会有社会损害,特别是在快捷、互动的互联网传播中,已经发生过多起此类个案。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化,一味禁制有违言论自由,而且不能收效,甚至会适得其反,只能通过说服、讨论、沟通、教育来达成正确的共识。那些大号微博和博客,具有“意见领袖”的地位,他们对网上言论应该起到引导和表率的作用。事实上有些“意见领袖”已经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如已经产生一定影响和效果的“辟谣联盟”,就是由几位知名的教授、律师等发起组成的。网民自律应该是网上道德自律的主要形式。本案判决及其理由,可以从反面警戒“意见领袖”,提升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
慎重行使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力
本案还有一个也许被忽略、然而十分重要的情节:判令被告人删除的微博数量,一审判决有20条,终审判决减为2条。
言论自由是宪法权利,行使言论自由必须承担谨慎的注意义务,限制言论自由同样需要谨慎。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提出限制言论自由应该具备三项条件:1.以法律规定;2.有正当的目的;3.为民主社会所必须(necessary),在国际学术界阐述和流传颇广⑨。本案两审判决对判令删除的微博予以反复考量,固然不能说一审判令删除而二审改判可以保留的那18条微博一定都是正确的,但至少可以理解为并非必须删除。这体现了我国司法对行使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力的慎重态度。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本案原告不是上法院起诉,而是直接通知微博服务商要求删除这些言论,那又会怎样呢?《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服务商在接到通知后,为了不致日后涉讼时承担连带责任,肯定会照单删除不误。而该法并未规定用户方面有任何反制措施,这就会产生与司法裁判不同的结果,连像二审改判那样的更改可能性都不存在。一项言论是否应予删除连法院判决都会有不同,那种按被侵权人通知一锤定音的做法显然不利于保护言论自由。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称为“通知-移除”(notice-take down procedure)程序,它产生于美国1998年《千年数字版权保护法》(DMCA),鉴于互联网服务商不能事先确知用户发布的内容有侵权性质,所以设立这样的前置程序以免除一旦发生纠纷服务商可能承担的共同责任,故有避风港(safe harbor)之称。2006年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引进了“通知-移除”程序,包括用户在内容被移除后若认为不当可以要求服务商予以恢复的措施。2010年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将“通知-移除”推广到所有网络侵权纠纷,但是可能由于法律条文不能像行政法规那样具体,这个第三十六条如何实施尚有待于订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作出细则规定。
在当下,至少应该明确服务商对用户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它需要对内容进行必要的规制只是在于法律规定的清除非法内容的责任,而用户不仅是言论自由的权利主体,还对自己作品以及上传后形成的版面结构享有知识产权。这两个方面的权益只能以协议平衡。在我国具体国情下,服务商的格式合同存在很大模糊区间、内容删除标准高于法律底线等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着民事行为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似应建立将删除措施通知用户的机制、用户提出异议的机制以及将被删除内容退还用户以示对其知识产权的尊重等。据互联网研究学人魏武挥观察发现,有的服务商采取秘密规制手段,如内容仅用户自己可见、不可搜索、不可转发不可评论、关注不上等⑩。这种暗中限制言论自由的手段有违诚信原则,会有严重副作用,应当停止。
对互联网言论的保护和规制,是一个探索中的新课题,“微博第一案”判决为此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谨引一段判词结束本文:“鉴于微博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每个网民都应该维护它,避免借助微博发表言论攻击对方,避免微博成为相互谩骂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 汕头大学特聘教授)
注释:
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海民初字第19075号
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终字第09328号
③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三版)》第27页、第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就是在标榜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媒体选择什么内容,对内容做哪些限制,这是主编的权利,政府无权干预。[美]彭伯:《大众传媒法》第45~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我国向接入服务商颁发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许可证,向内容服务商颁发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许可证。国际上通指ICP是直接提供内容的服务商,ISP是提供管道或空间的服务商。本文按国际概念使用。
⑥《人民日报》2011年7月15日
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
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2193号
⑨See A. Nicol QC etc: Media Law & Human Rights, pp.19-22,Blackstone Press,2001
⑩http://weiwuhui.com/436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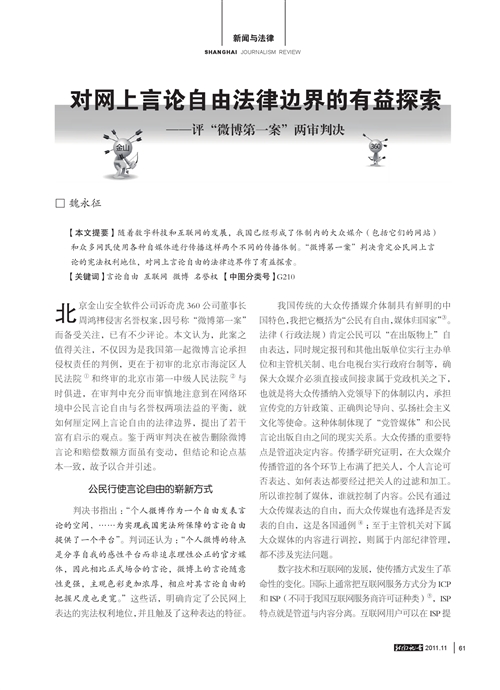
 制作维护
制作维护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