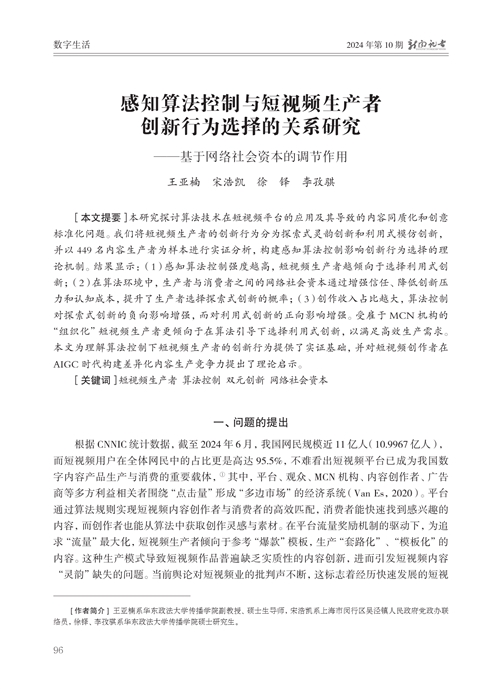感知算法控制与短视频生产者创新行为选择的关系研究
——基于网络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王亚楠 宋浩凯 徐铎 李孜骐
[本文提要]本研究探讨算法技术在短视频平台的应用及其导致的内容同质化和创意标准化问题。我们将短视频生产者的创新行为分为探索式灵韵创新和利用式模仿创新,并以449名内容生产者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感知算法控制影响创新行为选择的理论机制。结果显示:(1)感知算法控制强度越高,短视频生产者越倾向于选择利用式创新;(2)在算法环境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网络社会资本通过增强信任、降低创新压力和认知成本,提升了生产者选择探索式创新的概率;(3)创作收入占比越大,算法控制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增强,而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增强。受雇于MCN机构的“组织化”短视频生产者更倾向于在算法引导下选择利用式创新,以满足高效生产需求。本文为理解算法控制下短视频生产者的创新行为提供了实证基础,并对短视频创作者在AIGC时代构建差异化内容生产竞争力提出了理论启示。
[关键词]短视频生产者 算法控制 双元创新 网络社会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CNNIC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而短视频用户在全体网民中的占比更是高达95.5%,不难看出短视频平台已成为我国数字内容产品生产与消费的重要载体,①其中,平台、观众、MCN机构、内容创作者、广告商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围绕“点击量”形成“多边市场”的经济系统(Van Es,2020)。平台通过算法规则实现短视频内容创作者与消费者的高效匹配,消费者能快速找到感兴趣的内容,而创作者也能从算法中获取创作灵感与素材。在平台流量奖励机制的驱动下,为追求“流量”最大化,短视频生产者倾向于参考“爆款”模板,生产“套路化”、“模板化”的内容。这种生产模式导致短视频作品普遍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创新,进而引发短视频内容“灵韵”缺失的问题。当前舆论对短视频业的批判声不断,这标志着经历快速发展的短视频行业正面临如何提升内容质量的挑战。
当前技术环境下算法控制已被视为平台化生产环境下的新型劳动管理工具,学界关于算法控制与平台劳动生产的研究主要有三类视角: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关注由算法控制引发的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及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曹晋,2020;Purcell & Christin et al.,2020);二是媒介研究视角,侧重于探讨算法控制对参与式文化和社交媒体内容生产的影响(刘战伟等,2022;何威等,2020);三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聚焦于算法广泛应用带来的平台治理与劳动控制的研究(刘金河,2022;全燕,2022;皇甫博媛,2021)。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平台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技术优势,通过算法控制工具延伸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导致数字劳动层级剥削、劳动资料独占和劳工规训等问题,加剧了阶层间利益分配不均、社会歧视和文化公共性贬损。
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算法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平台与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关系异化问题,而忽视了对算法管理下平台生产者劳动行为的考察。算法技术对平台中的内容创意生产者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由于内容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如何判断消费者的内容消费偏好一直是困扰创意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算法技术可以通过计算内容消费者的停留时间、点赞数量等,推算出潜在消费者的偏好类型,为创意工作者带来市场消费偏好的稳定预测,从而为以短视频创作者为代表的创意生产者生产标准化、可预期的内容产品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内容创作者若仅依赖算法的指引,往往难以洞察内容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实际上,内容消费的核心价值在于消费者希望获得超出预期的体验,而算法规则倾向于引导创作者满足平均化的消费偏好。这使得创作者需要在利用算法的同时,突破其设定的框架,将“潜在的消费者偏好”转化为“实际的内容需求”,从而生产出超越算法预设、真正满足用户期望的短视频内容,进而获得超额经济利益。因此,在短视频创作过程中,是否应严格遵循算法管理,构成了一个悖论。
为深入理解上述悖论背后的理论逻辑,本研究在平台劳动的研究框架内,探讨算法控制对平台上创意劳动行为的影响,旨在分析感知算法控制如何影响内容生产者创新行为选择,主要边际贡献如下:一是构建了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模型,拓展了平台劳动研究中算法与内容创意生产者劳动关系研究的领域,将研究焦点从劳动关系转移到劳动行为,研究对象从一般数字劳动者,聚焦到创意劳动者;二是引入双元创新理论,明确了算法控制对内容生产行为异化的影响机制;三是通过引入网络社会资本概念,强调了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真实情感与信任连接的重要性,为改善内容市场“繁荣式衰败”提供了新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平台时代的创意生产:从“为爱发电”到“算法驱动”
随着平台化市场的日益成熟和技术对内容生产者的广泛赋权,创意内容生产正经历着从精英化向平民化、从组织化向个体化的深刻转变。特别是短视频的兴起,吸引了UGC(用户生成内容)、PUGC(专业用户生成内容)、PGC(专业生成内容)生产者积极参与短视频内容的创作。平台运营者采用基于大数据的内容推荐算法机制,有效管理分布在不同“时空”的自雇佣短视频生产者。这一算法机制类似于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成为引导短视频生产者、消费者与广告商生产与消费行为选择的重要信号(Basukie et al.,2020)。算法遵循平台内置的技术规则和标准化流程,自动化地实施控制职能,形成了数字化的管理实践,学术界将此过程称为“算法控制”(Kellogg et al.,2020)。作为一种“无形”的方式,算法控制重新配置了平台、工作者和顾客之间的生产关系。鉴于算法控制具有即时性、个性化与不透明性的特点,平台中的数字劳动者对其的感知存在个体差异,这种感知差异进一步影响了数字劳动者后续的工作行为(裴嘉良,刘善仕,2021)。
平台化不仅改变了新闻、信息和娱乐的传统工作方式,还催生了以脑力、精神和情感劳动为核心的创意劳动者群体,实现了从“数字零工”到“数字灵工”的劳动升级(Cunningham et al.,2019)。“数字灵工”特指在内容平台从事创意生产的用户型创意劳动者(Hartley,2005)。在“创意”或“创新行为”的研究中,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90/2008)在其著作《模仿律》中提出,新事物的产生多源于对发明的模仿与重复。创新研究学者进一步提出双元创新理论,将创新活动划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种类型(Scott et al.,1994)。其中,探索式创新侧重于依赖新知识或脱离现有知识进行创新,旨在创造新市场或新需求,是一种“突破性”的创新行为,但其伴随着较高的失败风险和更多的投入。而利用式创新则是在现有知识基础上提升组织的现有技能、过程和结构,以满足现有市场和顾客需求,是一种“渐进性”的创新行为,其难度和风险相对较低。基于此,本研究将内容创作者的创意生产行为划分为探索式的灵韵创新与利用式的模式化创新两类,分别对应塔尔德所提出的“创意”与“模仿”行为。其中,灵韵创新强调内容创作中的原创性和突破性,而模式化创新则侧重于对既有创作框架的优化与应用,以高效生产出符合市场预期的内容。
在探讨算法控制对创意生产行为影响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创意劳动者感知算法控制的程度越高,其创意内容生产行为选择越偏向于进行利用式的创新而非探索式的创新(裴嘉良等,2021)。具体来说,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影响其创新行为的选择:
第一,“普通人”为获得平台中流量最大化带来的阶层跃迁可能性,更倾向于受到“算法机制”的引导,选择易于获得“流量”的利用式创新行为(Kellogg et al.,2020)。传统的创意劳动研究专注于对大都市“创意中心”的研究,研究对象通常是名校毕业、中产阶级、城市白领为代表的创意工作者(Howkins,2002)。而平台经济兴起之后,短视频创意工作让普通人借助短视频平台参与文化生产,获得了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性,使“普通又不平凡”的个体成为“微名人”(Lin et al.,2019;汪雅倩,2021)。平台经济带来显著的工作收入增加,提升了短视频生产者的社会地位认同,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阶层流动性。基于此,短视频平台中大量“普通”生产者出于对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增加的“希望劳动”内生动机驱使,会主动研究算法机制,以获得更多的被看见的可能性,这种追求高流量的压力减少创作者对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尝试。
第二,“加速竞争”的生产环境迫使短视频生产者必须遵循算法引导,采用利用式创新方法快速实现内容产品的迭代以及维持自身的平台可见性(Cotter,2019)。平台的算法机制可以总结为:流量池、冷启动、数据加权、叠加推荐和精品推荐池,共同构成去中心化的推荐机制(刘善仕等,2022)。原则上,不论是名人还是第一次进行内容生产的创作者,每个人都被算法机器公正对待。实际上,这种去中心化的算法推荐机制也加深了竞争的残酷性(Danaher et al.,2017)。创意短视频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潮流时尚变幻无常,持续创新的难度极高。然而“平台坚如铁,创意者如流水”,在算法权力的管控下,创作者一旦不能保持持续更新或者创新内容不符合平台推荐的法则,很快就会被平台淘汰,其生产的内容也会淹没在不断涌现的海量内容中。这可能导致那些认为受到算法高度控制的短视频生产者更倾向于制作与当前热门话题或流行风格相关的内容(Petre,2019)。
事实上,探索式创新的实现需要短视频生产者拥有相当大数量“自由的”或富余的时间资源,以便寻找和探索“灵光乍现”的时刻,而以加速竞争为逻辑的平台化生产环境没有为短视频生产者的“探索式”创新预留空间(哈特穆特·罗萨,2018)。短视频平台中的生产者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帮助他们保持稳定更新的利用性创新行为,即在已知的成功范式和内容类型上进行变体和再创作,以确保相对稳定的观众反馈和关注度。借助媒介依赖理论可解释为创作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了对观众期望和平台算法的依赖,倾向于在熟悉的内容框架内进行微创新,以维持观众的持续互动和平台上的可见性(Ramizo, 2022)。
综上所述,感知算法控制越高的短视频生产者,越容易受“希望劳动激励”和“加速竞争”环境的共同作用,而更倾向于选择利用式创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感知算法控制抑制了短视频生产者探索式创新行为
假设2:感知算法控制促进了短视频生产者利用式创新行为
(二)虚拟场域的网络社会资本:从“流量规则”到“以人为本”
社会资本指的是在人际、群体及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资源,既有研究通过对传统社会资本概念的借用,同样将“网络社会资本”概念划分为结构、关系与认知三个维度。其中,结构维度的网络社会资本指的是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社交网络形态;关系维度的网络社会资本涉及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认同等情感要素;认知维度的网络社会资本包括短视频内容社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共享符号意义与行为规范。具体来说,网络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与创新行为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影响机制如下:
第一,结构维度网络社会资本通过提升虚拟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与连接频率,使得短视频生产者逐步减少对算法引导的依赖,转向与消费者之间进行人际间的真实互动获取创新灵感,实现从利用式创新向探索式创新的转变。结构维度的网络社会资本体现了短视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评论区、微信群等空间为短视频用户提供讨论内容体验与新话题的平台,短视频生产者可通过参与观察消费者的交互行为,激发消费者潜在内容需求的表达,也能够在与消费者的互动中迸发新的创意。结构维度网络社会资本的构建不仅为短视频生产者建立了更为直接的用户反馈机制,也减少了其生产过程中对算法引导的依赖,从而使其能够在加速竞争的内容生产环境中保持创意的活力与持续的内容产出。
第二,关系维度网络社会资本积累通过建立紧密的虚拟社区联系,提高消费者对短视频生产者的信任度,为短视频生产者进行探索式创新提供有利的生产环境。关系资本反映着消费者对虚拟社区的信任程度。一个充满社会认同感和互信互助氛围的虚拟社区,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形成更为紧密的互动网络。这种信任关系构成了消费者与短视频生产者之间的沟通基础,加强了社交网络的稳固性,有助于短视频生产者真正了解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使虚拟社区成为一个互相信任与协作的生态系统,从而为探索式创新的内容生产提供相对宽松的“低压力”环境。
第三,认知维度网络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构建短视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共享价值观促进双方有效沟通、知识共享,降低了短视频生产者选择探索式创新的认知成本。短视频产消社区中高度共享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使得短视频生产者增加了对消费者需求的理性判断,进而降低了其选择探索式创新的认知成本。例如,知名健身类短视频创作者“别往嘴里炫了”通过在短视频评论区、微信群与观众的互动,帮助社区成员解决健身中的困惑,建立了稳固的信任关系。他的观众也通过评论为其提供内容创作建议,促使他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形成了一个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社区。这种互动不仅使得短视频生产者能够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也为他提供了创新的灵感来源,推动了他在健身领域的持续创作。因此,通过深化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短视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共同发展的社区,短视频生产者能够更具独立性地进行探索式创新,避免了对“高流量”内容的过度依赖。
综上所述,拥有高网络社会资本的短视频内容社群建立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充分的信任关系,消费者对内容创作者本人具有较高的情感依赖和用户忠诚,不单以热点话题或更新速度衡量短视频创作者的价值。这使得内容创作者拥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进行探索式创新,减少了平台“赶工机制”和“希望劳动”等劳动控制及流量规则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短视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构建的网络社会资本负向调节了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与探索式内容创新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即短视频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积累的网络社会资本越高,感知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探索式创新行为选择的负向影响越弱。
假设4:短视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构建的网络社会资本负向调节了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与利用式内容创新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即短视频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积累的网络社会资本越高,感知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利用式创新行为选择的正向影响越弱。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问卷数据来自抖音平台的短视频生产者,样本筛选遵循以下规则:(1)由于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感知算法控制对个体创新行为选择的影响,因此,在样本选择中剔除了团队运营的短视频账号;(2)由于行为选择需要具有时间稳定性,因此,要求受访者内容创作时长达到2年及以上,更新频率保持在一个月1到2次;(3)由于本研究着重考察作为创意主体存在的短视频生产者创新行为,考虑到品牌官方账号和视频内容以带货为主的账号在进行内容创作的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营销目的,故这两类账号也不纳入受访者范围。
调查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抖音的私信功能进行派发。前期,研究团队大量搜集、观看各平台播放量在2W+的内容,通过平台私信联系创作者,进行多轮访谈,再利用创作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扩散式、滚雪球式的问卷收集。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严谨性的影响,本研究采取三阶段的纵向数据收集方法。第一阶段收集控制变量与感知算法控制的问卷,共发放500份问卷,收回489份问卷;第二阶段收集网络社会资本问卷,针对第一次参与调研的内容创作者发放问卷,收回489份问卷;第三阶段收集探索式创新行为与利用式创新行为问卷,针对同时参加前两次调研的内容创作者发放问卷,收回480份问卷,剔除作答时间过短、问卷数据较为极端和规律性填写的问卷,最终获得449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率为89.8%。本研究使用统计软件SPSS2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变量测量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综述,本研究归纳了必要的成熟量表。对所涉及的英文量表进行了严格的翻译-回译处理,并对成熟量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适用性改进,从而编制了问卷内容。在完成初始问卷设计后,我们邀请了10位抖音平台的短视频生产者进行预调研,并根据他们的反馈对问卷进行了调整,以防止由于题目表达不清而导致的测量误差。所有量表均采用了李克特5点法进行评分,分数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具体的变量定义如何下:
1.感知算法控制:本研究参考裴嘉良等(2021)开发的11题项量表,根据研究情景选取6个题项对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程度进行测量,代表题项为“算法管理为我提供大量与完成创作相关的信息支持”、“算法为我实时动态地反馈与已发布作品相关的数据信息”等。
2.网络社会资本:本研究参考Chiu等(2006)与Chang和Chuang开发的量表,采用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3个维度测量短视频社群中网络社会资本的密集度,共计16个题项,其中结构资本测量的代表题项是“我与平台中的用户维持着紧密的联系”;关系资本测量的代表题项是“我对与我频繁互动的短视频内容用户具有较强的信任感”;认知资本测量的代表题项是“我能够理解平台中其他用户发布的内容与信息”等。
3.探索式创新行为与利用式创新行为:本研究参考Mom等(2007)开发的双元创新量表,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分别设置5个题项,共10个题项进行测量,其中探索式创新行为测量的代表题项为“我总是乐于创作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新鲜内容”、“我总是尝试改变我的创作内容类型或创作形式”等;利用式创新行为测量的代表题项为“我的内容创作多数基于过往经验积累”、“我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对我现在的内容创作来说是完全够用的”等。
4.控制变量:为避免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等指标纳入控制变量。
(三)信度检验
表1中各项核心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6至0.7之间,略低于理想信度标准,但在当前的研究背景下,这一信度水平是可以接受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量表题项数量较少且问卷设计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本研究作为新兴课题,现有理论与文献基础相对较少,初期问卷设计以简洁的探索性研究为主。同时,考虑到受访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们设计了简短的问卷以提高完成率和回答质量。特别是在针对短视频生产者这一特定群体时,简短的问卷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回应。然而,信度系数受题项数量影响较大,题项较少可能导致信度系数偏低。
第二,样本群体异质性较高。由于短视频属于创意内容生产,不同的生产者对题项的理解和回答存在较大差异,这无疑影响了信度系数。因此,0.6~0.7的信度系数实际上反映了样本的多样性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生产者群体。
综上所述,考虑到研究的初期阶段性和样本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当前信度水平在研究中是可以接受的。
四、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1.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2的数据,从性别结构来看,参与调研的用户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分别为40.8%和59.2%,女性短视频生产者相对较多。从学历和年龄结构来看,本科学历的短视频生产者占总样本数的86.6%,主要集中在26至40岁,这一年龄段的受访短视频生产者占样本总数的87.3%。从收入与职业结构来看,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其短视频创作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20%,80%以上的受访者并非职业的媒体人。
2.相关性检验
表3展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其中,感知算法控制与探索式创新呈现显著负相关(β=-0.31,p<0.01),同时对利用式创新呈现显著正相关(β=0.453,p<0.01)。这两种创新行为与感知算法控制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符合理论预期,初步支持了本研究的部分假设。
3.主效应检验
在对“性别”、“学历”、“年龄”、“职业”等变量进行控制后,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按照研究逻辑依次置入自变量,表4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感知算法控制在10%显著水平下对短视频生产者采取探索式创新行为的选择具有负向影响(β=-0.117,p<0.1),表5中模型5的回归结果显示感知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利用式创新行为选择在5%显著水平下呈现正向影响(β=0.274,p<0.05)。由此,假设1和假设2得到了证实。
4.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2005)的实证方法进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了SPSS中的PROCESS插件来验证调节效应(Hayes,2017),使用PROCESS中的模型1(model 1)检验网络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表4中的模型3结果显示,网络社会资本在感知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探索式创新行为选择的影响中,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β=-0.155,p<0.05)。表5中模型6的实证结果显示:网络社会资本对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与利用式创新行为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p>0.1)。为了进一步验证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本研究还进行了 Simple Slope 检验和斜率差异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创作者所属社群的网络社会资本水平不同,创作者感知算法控制对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网络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感知算法控制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程度越小,这个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网络社会资本的抑制性作用。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调节效应,绘制了如图2所示的网络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图,进一步检验了以上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5.异质性检验
为深入了解在不同条件下感知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程度,我们基于视频创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受访者是否属于MCN机构两个维度,探索在不同情境下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对其创新行为选择影响的差异性。
(1)短视频生产者收入异质性分析
根据清研智库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9年两栖青年金融需求调查研究》数据显示,有85.6%的受访者表示,当副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达到20%及以上时,他们更倾向于将副业视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而非仅仅是调剂生活或拓展兴趣的渠道。基于这一发现,本文以短视频创作收入占总收入20%为界限,探讨收入异质性对创作者创新行为选择的影响。
表7中模型7与模型8的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短视频创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20%以下的受访者,占比在20%及以上的受访者的探索式创新行为选择受到感知算法控制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同时,模型9和模型10的实证结果表明,相比短视频创作收入在其家庭总收入中占比20%以下的受访者,收入占比20%及以上的受访者其感知算法控制对利用式创新行为选择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
上述两组模型对比分析共同验证了一个结论,即当内容创作者通过内容创作获得的经济收入较高时,高感知算法控制下,短视频生产者更倾向于采取利用式创新行为,可能的解释是当短视频创作收入成为创作者谋生的手段而非仅仅是其生活的调剂品,他们会更关注算法规则,希望能够生产相对标准化且符合市场需求预期的内容产品,以获取“稳定收入”,同时,这一实证结论也符合以利润最大化为创作目的的大多数工业文化产品的生产逻辑。
(2)生产组织方式异质性分析
短视频生产者是否隶属于MCN机构,决定了他们是独立的内容生产者还是组织化的生产者,生产组织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者的创新行为选择。因此,本研究从是否属于MCN机构的维度检验了短视频生产组织方式异质性的影响。模型11与模型12的实证结果显示,相比于不受雇于MCN机构的独立创作者,受雇于MCN机构且存在专业支持与组织的创作者的感知算法控制对其是否选择探索式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更高。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在以MCN机构为代表的专业化组织管理下,短视频生产者的探索式创新行为更易受到算法控制的影响;模型13与模型14的实证结果也可得出相似的结论,在利用式创新行为上,属于MCN机构的短视频生产者同样比不属于MCN机构的短视频生产者更易受到算法控制的影响。相对于自由随性的“无组织”创作者,MCN机构往往对创作者有更明确的生产目标要求,并规训创作者以更高效的方式生产。因此,无论是探索式创新行为还是利用式创新行为,在MCN机构的管理下,短视频生产者都更易被算法控制影响。
五、研究结论
(一)研究主要发现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第一,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强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利用式创新行为而非探索式创新行为。第二,短视频创作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比越大,感知算法控制对创作者探索式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越强,同时,对其利用式创新选择的正向影响越强。可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创新方式选择的影响更大。第三,相比于“自由”的短视频生产者,受雇于MCN机构的“组织化”短视频生产者更倾向于选择在算法引导之下的利用式创新行为,以完成组织机构对其高效生产的规训要求。第四,本研究的实证结论也证实了网络社会资本在短视频生产者感知算法控制与探索式创新行为选择的关系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短视频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沟通频次的提升,信任感的增强,能够改善算法引导的负面作用,增加短视频创作者选择探索式内容创新的概率。这一研究结论对我们的重要启发在于:归根结底短视频内容生产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符号意义传递的精神生产,若要对抗算法控制之下的内容生产的工业化、标准化趋势,或许只能回归到建立人与人之间真实连接的路径之上。也就是说短视频生产者与消费者基于真实的人际之间的沟通、信任与价值认同构建网络社会资本,不仅是支持短视频生产者进行探索式创新,创作出独特内容产品的重要途径,也是用户在内容消费中获得精神共鸣的重要通道。基于此,从长期来看,短视频生产者依靠与用户之间真实互动,获得内容受众圈层内用户的信任,建立圈层内的价值认同,依赖基于符号价值认同与人际信任创作的内容,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在AIGC时代利用机器进行内容生产能够更加准确地感知算法技术对内容消费需求的预测,进而能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利用式创新的内容产品,在这个发展趋势之下,人类内容创作者在内容生产中的生态位需要如何调整?本篇论文的结论在某些层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增强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连接,即建立广泛而深厚的网络社会资本,成为虚拟空间中一个“真实互动”的人,而非作为算法控制之下的赶工机器人,这是AIGC时代人类内容生产者应该选择的可持续创作路径。
(二)研究的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构建了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创新行为选择影响的实证模型,补充了对“算法控制”相关研究领域实证研究内容。
第一,算法控制相关的议题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已有研究一方面多从理论视角出发,探索分析算法控制对工作者劳动过程的影响(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另一方面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成果,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中又多以外卖骑手等传统零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莫怡青,李力行,2022),缺乏对于以创意为工作核心的“灵工”群体创新行为的讨论。本研究聚焦在以短视频生产者为代表的精神产品生产者的层面,在拓展了算法控制研究对象的同时,也丰富了该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成果。
第二,明确了创意生产质量的区分方法,将双元创新理论引入到对精神内容产品生产行为的分析中。以创意为核心的内容生产行为本身就是创新行为,而如何对创新行为进行界定和分类,以明确平台化生产环境下的算法规则对内容产品市场的具体影响机制缺乏讨论。既往研究在探讨算法对内容生产的影响时,更多关注的是算法对平台创意生产劳动的剥削与异化(曹晋,张艾晨,2022),而并未从内容生产质量的角度,探讨算法环境下内容产品的标准化、趋同化生产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通过引入双元创新理论,明确了算法对短视频生产者生产行为异化的具体影响机制,深化了对于当前内容市场“繁荣式衰败”局面的解释。
第三,本研究通过引入网络社会资本概念,指出在平台化生产与算法引导的环境下,建立短视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作为“人”的真实情感与信任连接的重要性。既有研究较多关注与讨论短视频生产者与平台之间关系对其生产行为的影响(吕鹏,2021),而忽略了在平台化生产与消费环境下,平台另一端用户与生产者之间互动对内容生产行为的影响。在内容平台的流量分配法则下,短视频平台的“公域流量”属性使得“粉丝”实际上归属于平台而非创作者。因此,短视频生产者一旦无法持续产出爆款内容,就会被平台算法边缘化,而注重内容社区构建,增强短视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网络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正向调节短视频生产者在高算法控制环境下对探索式创新行为的选择。换句话说,短视频消费者和短视频生产者之间的“强连接”能够给予短视频生产者“信心”与“勇气”进行更多的探索式创新内容的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善当前短视频内容市场普遍存在的以追求内容产品更新速度而不关注内容独特性为特征的“繁荣式衰败”的局面。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本研究为短视频生产者的创新行为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虽然将创新行为划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两类,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但这种划分可能简化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创新行为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探索与利用往往相互依存、交织进行,二元划分可能无法充分揭示其复杂的动态关系。其次,由于本研究在现有理论和文献基础较为有限的背景下展开,简短的问卷设计旨在提高受访者的参与度和回答质量。然而,较少的题项可能导致信度系数偏低,进而影响测量的稳定性。此外,短视频创作者样本群体的异质性较高,使用统一的问卷调查的数据获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信度水平。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算法控制对不同类型短视频生产者的影响,如专业与业余生产者在面对算法控制时的创新策略选择。此外,网络社会资本的作用值得深入挖掘。研究可以从多个维度分析其调节效应,例如它如何影响生产者的创新意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表现。揭示网络社会资本与算法控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短视频生产者创新行为的共同影响,能够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最后,短视频生产者的创新行为不仅影响个体的发展,也对整个短视频内容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未来的研究应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分析这一行为的影响,探讨其对市场竞争格局和消费者偏好的塑造。同时,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全面剖析算法控制对短视频生产者创新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干预策略,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注释
①CNNIC(2024)。《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态统计报告》。检索于https://www.cnnic.cn。
参考文献
曹晋,张艾晨(2022)。网络流量与平台资本积累——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考察。《新闻大学》,(01),72-85+123。
陈逸君,崔迪(2022)。用户的算法知识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视频类、新闻类和购物类算法应用的实证研究。《新闻记者》,(09),70-85。
段鹏(2022)。社群、场景、情感:短视频平台中的群体参与和电商发展。《新闻大学》,(01),86-95+123-124。
郭新茹,康璐玮(2022)。认知盈余视角下短视频平台内容创新生产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1),66-73。
(德)哈特穆特·罗萨(2018)。《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威,曹书乐,丁妮,冯应谦(2020)。工作福祉与获得感: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者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06),21。
皇甫博媛(2021)。“算法崩溃”时分:从可供性视角理解用户与算法的互动。《新闻记者》,(04),55-64。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90/2008)。《模仿律》(何道宽译)(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金恒江,刘圆圆(2023)。社会临场感和情绪响应:青少年移动短视频依恋的影响因素——基于混合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08),96-113+128。
赖楚谣(2022)。“算法的社会性知识”——短视频内容创作者的算法解释与知识的集体建构。《国际新闻界》,(12),109-131。
刘金河(2022)。权力流散:平台崛起与社会权力结构变迁。《探索与争鸣》(02),118-132。
刘善仕,裴嘉良,葛淳棉,刘小浪,谌一璠(2022)。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管理世界》,(02),225-239+14-16。
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07),42-58+127。
吕鹏(2021)。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的相遇: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数字劳动。《国际新闻界》,(12),53-76。
莫怡青,李力行(2022)。零工经济对创业的影响——以外卖平台的兴起为例。《管理世界》,(02),31-45+3。
裴嘉良,刘善仕,崔勋,瞿皎姣(2021)。零工工作者感知算法控制:概念化、测量与服务绩效影响验证。《南开管理评论》,(06),14-27。
裴嘉良,刘善仕,崔勋,张志朋,葛淳棉(2022)。算法控制能激发零工工作者提供主动服务吗?——基于工作动机视角。《南开管理评论》,(02),1-19。
全燕(2022)。平台文化资本的形成与消费社会的再结构化。《江苏社会科学》,(04),22-35。
师文,陈昌凤(2023)。平台算法的“主流化”偏向与“个性化”特质研究——基于计算实验的算法审计。《新闻记者》,(11),3-14。
汪雅倩(2021)。从名人到“微名人”:移动社交时代意见领袖的身份变迁及影响研究。《新闻记者》,(03),27-39。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心理学报》, (02),268-274。
吴鼎铭(2017)。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国际新闻界》,(06),124-137。
肖鳕桐,方洁(2020)。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创新研究。《国际新闻界》,(11),99-118。
晏青,陈柯伶(2023)。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短视频成瘾的媒介可供性。《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90-101+171-712。
叶妮,喻国明(2023)。基于AIGC延展的创新性内容生产:场景、用户与核心要素。《社会科学战线》,(10),58-65。
赵景林,赵红(2019)。虚拟品牌社区社会资本、品牌关系质量和消费者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08),71-86。
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06),942-950。
WoodA.J.Graham,M.LehdonvirtaV. & Hjorth,I.(2019). Good Gig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33(1)56-75.
Basukie, J.Wang, Y. & Li, S. (2020). Big data governance and algorithmic management in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s: A case of ridesharing in emerging market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6 (1)120-310.
BishopS. (2019). Managing visibility on YouTube through algorithmic gossip. New Media & Society21(11-12)2589-2606.
ChiuC.M.HsuM.H. & Wang, E . T . (2006).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sharing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n integratio of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ie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42(3)1872-1888.
CotterK. (2019). 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 How digital influencers and algorithms negotiate influence on Instagram. New Media &Society, 21(4)895-913.
CunninghamS.& Craig. D. (2019). Creator Governance in Social Media Entertainment. Social Media + Society5(4)1-11.
Danaher, J. et al. (2017). Algorithmic governance: Developing a research agenda through the power of collectiveintelligence. Big Data & Society4(2)1-21.
Gillet, N.Fouquereau E.Lafrenière M.A.K. & Huyghebaert T. (2016). Examining the Roles of Work Autonomous and Controlled Motivations on Satisfaction and Anxiety as a Function of Role Ambiguity.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644-65.
GrahamM.Hjorth, I. & LehdonvirtaV. (2017). Digital Labour and development: Impacts of global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the gig economy on worker livelihoods.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3(2)135–162.
Hartley, J. (2005). Creative industries.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YorkNY: Guilford Publications.
Howkins, J. (2002). The creative economy: 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 London, UK: Penguin.
Kellogg K.C.ValentineM. A. & Christin,A. (2020). Algorithms at work: The new contested terrain of control.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4(1)366-410.
Lin, J.& KloetJ. D. (2019).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5(4)1-12.
Mom, T.J.Van Den BoschF.A.&VolberdaH.W.(2007). Investigating managers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ctivities: The influence of top-downbottom-upand horizontal knowledge inflow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4(6):910-931.
NahapietJ. &Ghoshal,S.(1998). 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2)242-266.
Petre, C.Duffy , B. E.Hund, E. (2019). Gaming the System: Platform Pate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lgorithmic Visibility. Social Media + Society5(4)20-56.
Podsakoff, P.M. et al.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879–903.
Purcell, C.& BrookP. (2022). At least I'm My Own Boss! Explaining Consent,Coercion and Resistance in Platform Work.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36(3)391-406.
Ramizo Jr, G. (2022). Platform playbook: A typology of consumer strategies against algorithmic control in digital platform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5(13)1849-1864.
SchelewaldA. (2022). Theorizing:"stories about algorithms" as a mechanism in th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lgorithmic imaginaries. Social Media + Society8(1)1-10.
Scott, S.G. & BruceR.A. (1994).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7(3)580-607.
Van Es, K. (2020). YouTube's Operational Logic:"The View" as Pervasive Category. Television& New Media21(3)223-239.
[作者简介]王亚楠系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宋浩凯系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人民政府党政办联络员,徐铎、李孜骐系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