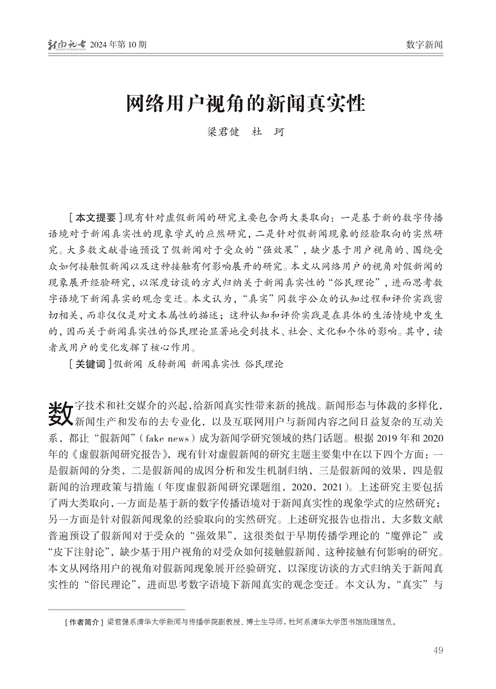网络用户视角的新闻真实性
■梁君健 杜珂
[本文提要]现有针对虚假新闻的研究主要包含两大类取向:一是基于新的数字传播语境对于新闻真实性的现象学式的应然研究,二是针对假新闻现象的经验取向的实然研究。大多数文献普遍预设了假新闻对于受众的“强效果”,缺少基于用户视角的、围绕受众如何接触假新闻以及这种接触有何影响展开的研究。本文从网络用户的视角对假新闻的现象展开经验研究,以深度访谈的方式归纳关于新闻真实性的“俗民理论”,进而思考数字语境下新闻真实的观念变迁。本文认为,“真实”同数字公众的认知过程和评价实践密切相关,而非仅仅是对文本属性的描述;这种认知和评价实践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因而关于新闻真实性的俗民理论显著地受到技术、社会、文化和个体的影响。其中,读者或用户的变化发挥了核心作用。
[关键词]假新闻 反转新闻 新闻真实性 俗民理论
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介的兴起,给新闻真实性带来新的挑战。新闻形态与体裁的多样化,新闻生产和发布的去专业化,以及互联网用户与新闻内容之间日益复杂的互动关系,都让“假新闻”(fake news)成为新闻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根据2019年和2020年的《虚假新闻研究报告》,现有针对虚假新闻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假新闻的分类,二是假新闻的成因分析和发生机制归纳,三是假新闻的效果,四是假新闻的治理政策与措施(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2020,2021)。上述研究主要包括了两大类取向,一方面是基于新的数字传播语境对于新闻真实性的现象学式的应然研究;另一方面是针对假新闻现象的经验取向的实然研究。上述研究报告也指出,大多数文献普遍预设了假新闻对于受众的“强效果”,这很类似于早期传播学理论的“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缺少基于用户视角的对受众如何接触假新闻、这种接触有何影响的研究。本文从网络用户的视角对假新闻现象展开经验研究,以深度访谈的方式归纳关于新闻真实性的“俗民理论”,进而思考数字语境下新闻真实的观念变迁。本文认为,“真实”与数字公众的认知过程和评价实践密切相关,而非仅仅是对文本属性的描述;这种认知和评价实践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因而关于新闻真实性的俗民理论显著地受到技术、社会、文化和个体的影响。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真实再思考
新闻真实性的议题是新闻学领域的核心议题。操瑞青(2017)将这一众说纷纭的话题拆解为三个命题,分别对应了新闻本体、新闻接受和新闻生产:一是“新闻报道应该真实”,这涉及新闻本身的定义和标准;二是“新闻报道是否真实”,这主要由接受者判断;三是“新闻报道如何做到真实”,这主要针对新闻生产侧的实践。在社交媒体时代,接受者在整个传播场域中的位置日益重要,这凸显出第二个命题的重要性,显著影响了对于新闻真实的定义和研究。
(一)以受众为中心的“新闻真实”
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受众转向(audience turn)(Costera Meijer,2020),社交媒体时代对新闻真实性的思考也出现了从生产到使用的延展,一批文献从受众角度对虚假新闻现象展开研究,强调了读者与受众的感受和实践在新闻真实性议题中的重要性。
相对于“假新闻何以被生产”的传统偏好,从受众视角出发探讨新闻真实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现实问题展开。首先,是对于“假新闻为何被相信”的研究。陈力丹(2002)曾指出,受众之所以会信任假新闻,是因为假新闻通常披着真实的外皮,其丰富且有趣的内容“为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刺激或松弛,赋予一种现实感很强的生活意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三个因素导致受众相信虚假新闻:刻板印象和先入为主的接受心理、对认知失调的极力避免,以及无意识层面的从众心理;虚假信息被信以为真,一方面常常是受众归因错误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往往是特定社会矛盾的反映(刘自雄,王朱莹,2011)。2016年美国大选中假新闻泛滥体现出“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对受众信息认知和接受过程的影响,假新闻往往能够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和民众“实现社会抗争的工具”(史安斌,王沛楠,2017)。Perach等人(2023)则研究了Twitter用户主动分享信息与谣言的六类动机。其次,是对于“如何辨别假新闻”的研究。在数字媒体环境下,受众判别信息真实度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信息源的权威性和接近性,内容是否符合自身价值观以及同自身的相关度,以及信息生产和处理的语境如信息是否过载等(Giglietto et al.,2019)。针对新加坡受众的问卷调查表明,个人判断和知识储备是受众辨别信息真假的基本手段;此外,消息的内容特征及其来源也是辨别信息可信度的重要途径;如若这些方式都无法奏效,受众往往会诉诸外部渠道,如查询参阅更多信息源、与他人沟通交流来求证等(Tandoc et al.,2017)。相比于文字信息,受众对于图像可信度的评估则受到了互联网技能、图像编辑经验、社交媒体使用,以及对特定议题的态度等因素的影响(Shen et al.,2019)。
针对受众的上述研究丰富了对于“新闻真实”的定义和讨论,反思了符合论、社群真知论和融贯论这三种新闻真实性的定义方式。由于普通用户和读者实际上不具备充分判定报道与事实是否符合的资源和技术,在实际中“符合论”只能提供关于新闻真实性的抽象定义,而无法提供真实性的具体标准和操作方式(李主斌,2011)。“社群真知论”更加符合受众接受的实际情境,它认为“事实”本身不是“新闻”,新闻是对于事实的反映,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反映出社群共享的知识和认知基础(芮必峰,1997)。从受众的角度看,由于自身不在新闻现场、只能通过文本来了解,因此对于新闻的真实性展开判断也主要依赖于文本,这时,新闻真实只能是依托“融贯论”的符号性真实,是社会文化体裁规定下的信任性真实(李玮,沈玉莲,2019)。当我们只能通过大众媒介的形态和符码来了解世界时,就进而进入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的状态;这时,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被极大弱化,符号的世界成为唯一真实的世界,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则不复存在(Baudrillard,1983)。因此,蒋晓丽等人提出了以新闻的“符号之真”来替代对其“客体之真”的定义(蒋晓丽,李玮,201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指出“信任”这个概念在新闻真实性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在他们看来,“真实”并不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信任”才是;新闻报道实践和新闻文本生产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围绕受众“信任”这一目标而展开的(操瑞青,2017)。
(二)作为个体想象实践的真实
从受众的视角审视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真实”的再定义,尤其是关于符号之真和新闻信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个体的认知过程这一话题。从古至今,个体对“真实世界”的认知都无法脱离想象活动。想象是一种社会实践,具有自己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区域的特征,而图像、故事、电影等都是想象的表现和结果,它对于个体的行动来说具有重要价值。正如康德指出的,想象是一种将不在场的人、物或事件带入思维的能力,它能够让知识得以综合,并在其中发现关联(Robinson & Rundell,1994)。语言和符号是人类进行想象的重要凭借,符号域(the domain of semiosis)是人类通过想象来认识社会真实的主要场域。与现实域相对立,符号域是人类大脑的复杂性给人类带来的独有特征。人类和动物都可以理解现实,但是只有人类可以运用语言符号,做出与现实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陈述,通过符号系统生产意义(Elder-Vass et al.,2023)。现实域和符号域之间的反差也构成了后者对前者的认知、阐释和评价功能。考虑到个体所处的语境,泰勒(2004)提出了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的概念,来关注普通人如何想象自己所处的社会。他认为,这种想象并不以理论话语的形态表述,而是通过图像、故事和传说在更广大的人群中得以表达和共享。“想象”这一概念延续和强化了社会认知的建构主义观念(Sneath et al.,2009);就像我们建构意义一样,想象是我们唯一的认知现实和真实的方式(Turner,1996)。
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想象实践不仅需要借助符号域来完成,还受个体与认知对象的关系的影响。近年来,个人化或者主体性的转向将个体或者主体置于文化的认识论、伦理以及修辞的中心位置(Santos,2022)。这种转向让我们重新思考个体与世界的不同关系对于认知实践的悠久影响。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2013)通过“狩猎”和“阅读”这两个比喻阐述了现代性的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它体现出对于以下两类世界的区分:一是培根提出的“自足的世界”,人类只能通过系统的科学调查方法才能够认清的自然的真相;二是各式各样的想象的世界,这是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所想象出来并信以为真的世界。在前现代的想象世界中,自然界被比喻为一本向人类隐藏了诸多秘密的书籍,人类在这个世界中进进出出,不断地体会和读懂自然之书;而现代科学则强调,人类应当像猎人追踪猎物的足迹和线索一样,来获知早已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知识(Ingold,2013)。可以看出,“阅读”的比喻强调认知主体置身于世界之中,行动和知晓是密不可分的,人们需要通过参与和表述来认识世界真相;“狩猎”的比喻则要求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明确区隔,世界的真相是一个需要被看见和捕捉的客观对象。上述两类认知方式,分别对应了具身的自我和旁观的自我。
与上述两种关系相对应,新闻中的叙事形态也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民族志现实主义的,采用全知叙述者以及与社会现实主义相配合的叙事技术;另一类是文化现象学的,是自我反射的、探索的和个体化的(Roberts & Giles,2014)。前者是在新闻专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定型的一整套新闻报道的惯例和语态,是对于客观真实的一种自证与修辞;而反过来,作为现代社会辞令的专业新闻学也围绕新闻专业主义定义出了制度化的真实。社交媒体打破了依靠传统新闻业而维系的受众与社会主客体之间的区隔,专业新闻机构的守门人和社会感知的功能大大减弱。社交网络不仅催生了更多个体化的表达语态,而且由于线上世界的无处不在和线上线下的复杂交织,人们史无前例地被深深卷入数字化的符号域世界之中。在认知主体与数字世界的主体间性的视角下重新思考当下新闻真实性乃至于真实性本身的定义,就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时代价值的议题。
本文从数字技术和社交网络语境下的受众的视角探究新闻真实的本体性话题。网络信息和网络空间所组成的符号域成为当代受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场域,在这种语境下,受众接受新闻和判断真实性,并不是静态的和一次性的。英戈尔德所提出的“阅读”的比喻在今天依然适用,它强调了个体置身其中与世界展开互动和探寻的连续性的过程。只不过,当下个体是置身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通过主动搜索和被动的算法推送而获取信息,对信息进行综合、评价或屏蔽、弃置,不断建构与调适自己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认知,从而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对于真实的想象。因此,在真实网络使用情境中,当下用户如何辨析和看待新闻真实性包括了如下具体的问题:用户日常的网络使用经验如何形塑了他们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个体在接触不同类别的假新闻后的主观感受和即刻行动,及其对于后续信息的跟进和评价是一个怎样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如何强化或者改变了他们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认识?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
为了研究真实网络情境下用户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认知和实践过程,本文以俗民理论为指导,结合网络民族志的视角和具体新闻案例进行深度访谈,从而获取研究资料。“俗民理论”(folk theory,亦称“民间理论”)这一概念最初来自于心理学对于归因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人们对行为和事件原因的解释以及由此产生的推断和评价。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们发现,相对于科学理性专业的归因方式,普通人对于行为和事件的归因常常受其个体特质和群体心智的影响而出现偏差和错误(Malle,1999)。不过,随着文化研究和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对于后现代和多元性的强调,俗民理论不再被视作“不正确”的归因,它的合理性的一面得到了发现,这成为我们理解不同群体如何解释他们眼中世界并获得积极效能感的一把钥匙(Levy et al.,2013:318-322)。近年来,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借助俗民理论的概念工具来探讨网络用户的实践与观念。其中,较为集中的领域是对网络产销者如何理解和运用算法推荐的研究(DeVito et al.,2018:1-12)。在新闻使用和新闻真实性的领域,胡杨和王啸(2019)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和网络问卷调查归纳出中国语境下受众对于假新闻认知的事实、呈现与动机的三维框架,并借助俗民理论从受众角度理解假新闻的不同维度以及受众对于新闻真实的辨别方式。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纳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将新闻用户的认知与想象实践置于具体的使用情景和事件中,目的是探索普通公众对于新闻是否真实以及什么是好新闻的具体归因方式。网络民族志关注围绕网络媒介和数字技术而展开的各类实践,以超越媒介文本和生产结构这样的既有认知范式,探究媒介嵌入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灵活多样的方式(Couldry,2004)。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特别有助于探究媒介嵌入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方式,并考察用户的主动性(Miller,2016);它可以将内容分析同观察、参与和访谈相结合,从而提供关于线上行为、习俗、期待和互动的丰富资料(Standle,2017)。深度访谈是研究受众网络实践的常用方法。它能够揭示出受众的意义生产过程,尤其有利于通过参与者丰富的个体经验描绘各方面的实践细节(Penney,2023)。针对假新闻现象,已经有学者采取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法,对记者和受众对虚假新闻概念认知展开对比分析(Carazo-Barrantes et al.,2023)。
本文采用现象学取向展开访谈,这种取向强调通过具体个体的视角理解社会和心理现象,以人们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来关注普通人是如何处置他们的日常生活的(Groenewald,2004)。
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结合研究者选定的近年来产生普遍影响的假新闻以及受访者自己提及的近期接触过的假新闻,在细微具体的情境中了解受众的新闻消费实践和主观感受,这种结合具体的案例和细节的讨论比一般性的抽象讨论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用户的所做所思;其次,从具体的事例讨论中延伸出来,了解受众一般性的网络使用习惯、新闻素养和网络素养,着重考察受众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语境和环境中自我定位(positioning),并以此为基础接受和评估新闻的真实性的。此外,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是否会通过设定自己的所在地,以及通过主动搜索和驯化算法的方式,来决定自己被推送什么样的新闻和信任什么样的新闻。本研究的深度访谈秉持建构性的方法,受访者的陈述并非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既有思考,还包含了研究者和受访者围绕具体案例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网络使用和真实观念的批评性反思与归纳。
为了最大程度地在具体的微观情境中分析和总结受众对新闻真实性作出评估和归因的依据、过程及其个体主观感受,本研究在兼顾不同类别和属性的基础之上,选取了近三年来出现反转的、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五个热点事件案例(见表1),并以人工收集的方式将所涉事件的关键性新闻文本进行整理汇总,作为开展深度访谈时与受访者共同探讨的文本材料。
对于现象学取向的访谈,Boyd(2001:93-122)认为比较合适的访谈人数是2~10人,Creswell(1998)也认为针对10人以内的长访谈即可达到研究目标。本文对16名20~30岁的在读研究生展开深度访谈(见表2、3),每人交流时间为35分钟至3小时不等。其中,中国大陆生源15人,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群体;另有1人为香港生源,在新闻媒体接触习惯方面有显著不同,为理解研究主体的特征提供了参照。15名受访的大陆研究生中男性8人、女性7人,学习工科类专业6人,文科类专业7人,商科类专业1人、医学类专业1人。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口头了解了访谈对象的日常网络使用和媒介接触情况,然后邀请受访者从五个案例中选择一个感兴趣或之前了解过的话题,通过手机链接、按照自己日常习惯、根据新闻发布的时间顺序浏览研究者事先收集好的新闻内容,然后针对新闻真实性的话题进行讨论与反思。
三、如何判断真实性:新闻信任的不同来源
从访谈过程来看,是否选择相信新闻的真实性,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受访者提及的因素包括了新闻文体特征、是否有明确的信源和证据,以及是否符合自己的认知框架和情感喜好等。
(一)文本与信源:新闻信任的制度性因素
新闻文本本身特征是新闻信任的重要来源,这包括了标题、文体、信源、题材、媒介形态等。这些要素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规则,是新闻实践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经过长期的社会建构而形成的一种围绕着“客观”、“中立”标准的制度性安排。虽然社交媒体显著挑战了传统新闻业和新闻专业标准,但后者仍然是很多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新闻信任的基本来源。
新闻要素的完整和新闻信息的丰富,是受访者选择信任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因。P将自己判断新闻真实性的标准总结为三点,一是新闻各要素的完整程度,二是标题和文本中个人情绪的含量及是否存在刻意诱导的嫌疑,三是涉及话题是否尽可能地覆盖更多地区、更多领域,以满足大众在阅读新闻和获取信息方面的需求。在对新闻真实性进行总结时,F认为新闻文本中是否包含确凿证据是首要的指标。王冰冰案例的第一条新闻正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让F从一开始就对真实性产生了主动怀疑。A对血奴案最初报道的信任也来自于新闻文本中包含的对不同方面广泛信源的采访,以及行文文体本身的官方媒体的报道特征。内容信息量同样是I和M对新闻真实性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他们均表示自己会更愿意相信时长更长、提供更多信息的文字和视频报道。
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也是受访者常提及的评价新闻可信度的重要参照。在社交媒体时代,第一人称叙事成为很多受众的信任来源,迥异于专业主义所强调的客观性原则。相较于那些以第三人称转述为主的文章,O表示自己会更相信以问答为形式展现当事人自述内容的报道。“它会激起你的同理心,让你在看的时候有很强烈的画面感和亲密感,你会觉得他(当事人)受到的伤害是那么真实,从而让你很愿意去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E谈及自己对血奴案反转之前的信息的态度时表示,第一人称的讲述视角和丰满的细节描述,将这个本应该距离自己日常生活与认知极为遥远的场景还原得历历在目,使得他在一开始就被这个事件所吸引和打动,反而忽略了对其真实性的判定。可以说,第一人称叙事的感染力增强了内容对受众的说服力。
最后,官方媒体也是新闻信任的关键词。尤其是在经历了多起新闻反转事件后,很多受访者最终会将相信官方媒体作为今后应对虚假新闻的方式。在C看来,真实性对于官方媒体而言的重要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媒体,因此除非有自身利益被牵扯其中,他更相信官方媒体不存在撒谎的动机。E指出自己首先会看报道媒体的类型,如果为官方媒体的话他会愿意给予更多信任,但同时鉴于官方媒体的公信力相较以前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他也会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也会去微博等平台搜索其他人对此是否有与官方媒体不一样的解读。在经历了诸多反转与辟谣后,H表示自己会有明显的被欺骗感和失落感,这样的感受也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她对官方媒体的信赖度;此外,她认为关注者多的媒体要比关注者少的媒体更可能会出于社会影响力的考量而选择尽一切可能反复核查信息真实性。
(二)预认知:新闻信任的文化因素
与文本形式相对,新闻题材、内容和人物也影响了人们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判断。即使叙述方式完全一致,某些类型的事件和人物总会显得更加可信。这是人们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习得的预认知所带来的结果,广泛地体现在受访者对于新闻信任的反思式讨论中。
对于事件的预认知大多来自于此前的新闻报道和知识偏向。在本文选取的讨论案例中,血奴案是这种预认知的典型体现。多名受访者在反思时认为,这条新闻的内容与自己的“预认知”十分匹配,这是让自己信任其真实性的重要原因。A自述,在第一次接触这条新闻时并没有任何的对于真实性的怀疑。得知全貌后反思,她认为最初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条新闻与对自己东南亚社会混乱的既有印象十分吻合。C同样指出,该案例之所以在最开始能够博得信任,关键的因素在于其十分符合公众对东南亚诈骗乱象频发的刻板印象。此外,各种反电信诈骗的新闻宣传报道及影视文艺作品对东南亚形象的刻画,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强化甚至是进一步形塑了受众的固有认知。
预认知也包括了特定的价值偏向。当新闻报道事件背后的价值指向与用户自身的价值偏好与价值判断相符时,就更容易获得信任。C认为,一个新闻之所以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不仅与受众自身的认知密切相关,社会既有的结构性矛盾也在无形中主导着大众注意力的方向。采访过程中J也提到了自己近期关注的“天津大学生助学金”事件,最开始在网上看到该男生声泪俱下地控诉学校助学金评审存在不公的视频时,他是十分同情并相信的。他在类似的事件中往往会下意识地偏向弱势一方的立场。直到当事同学全面退网后,他才通过网友的各种评论得知此事原来已完全反转了,一种被欺骗的无奈感油然而生,这令他对整个社会的公信力都开始产生了怀疑。
对于新闻人物的情感偏好也影响了新闻信任。这在王冰冰徐嘉余的恋情及“上春山”事件这两则案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B和G都表示出于对王冰冰外貌和能力的一贯肯定,无论反转前后,自己的立场始终都更偏向王冰冰一些。不过,有时候新闻报道也会反过来影响受众对于人物的情感偏好,尤其是与价值判断发生冲突时。L在自己初次得知“上春山”事件时,尽管过往的经验驱使他选择“让子弹飞一会儿”再下结论,但对职场“背刺”行为的反感使得他在内心仍旧会形成一个大致的倾向:“我之前其实还是蛮喜欢白敬亭的,但‘上春山’这件事儿如果说他没有难言之隐……我是不太喜欢这种行为的,所以现在不喜欢他了,也经常会对他参演的影视作品持一种抵触态度。”
最后,预认知也包括了受众此前对于反转新闻和假新闻的阅听经验。已经被证实过的假新闻会让受访对象在阅读类似新闻时对于新闻真实进行自觉反思。H是为数不多在最开始便对血奴案的相关报道保持观望态度的人,此前诸多例如“造谣女儿被班主任体罚致吐血”等反转事件令她对此类事件更倾向于“兼听则明”。E虽然对血奴案一开始选择了完全相信,但反转后的相关报道在他看来则是“意料之外也情理之中,但情理之中要显著大于意料之外”,因为自己之前已在B站看到过类似的自称在缅北打工被骗,随后被证实为编造的视频。这些既有经验表明,个人完全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选择杜撰故事情节以骗取受众的关注。
四、如何对待真实性:新闻信任的社会后果
如果说如何判断真实性展现的是新闻用户在技术和实践层面的特征的话,那么如何对待真实性,尤其是在社交网络和数字新闻的语境下用户如何理解、评价和使用“新闻真实”这一抽象概念,则更能体现出俗民理论所强调的归因这一心理过程。
(一)什么是好新闻:新闻真实与新闻评价
对于新闻真实性与新闻质量的反思和总结是访谈过程中的主要话题。尤其是在进行具体案例讨论之后,受访者均不同程度地对新闻真实性和好新闻的标准有了更多的思考。例如,A在阅读她所选择的柬埔寨血奴案例的过程中明确表示震惊,因为她此前关注到这条新闻,但并没有跟进到反转后的信息,这次访谈是她第一次得知这一系列报道的完整面貌,也因此对新闻真实性议题的重要性更加认可,在访谈结束后特地向两位研究者表达了对这一研究话题的强烈认同。总体来看,受访者对“什么是好新闻”的归因,固然首推真实性,但在具体讨论时常常将真实性置于关系结构中进行综合考虑,如真实与价值的关系,真实性与时效性的关系,以及真实性与报道者立场动机的关系等。
真实和价值,是受访者普遍提出的好新闻的最重要的品质,而且两者往往被表述为一对递进的关系。D眼中的优质新闻,第一要真实,第二要有价值属性,引发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关注。虽然他认为真实是基础,但是在讨论到凤凰网报道血奴案的第一人称新闻时,他认为评论区的一些留言证明了这则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带来了正面的社会价值,只是“可惜不是真实的”。L也将新闻的真实性判断和价值判断同时作为重要标准。他谈及近期在网上引发热议的“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认为当今时代很多假新闻的一大共性特征就是动机上的“博眼球”。但同时他也进一步表示:“如果说一则新闻博眼球是为了对某个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我觉得这算一个好新闻;不好的新闻就是那些基于部分特定事实进行了远超事件本身意义的、夸大性的、煽动性的牵强附会和添油加醋。”
一些受访者还主动将新闻真实性与新闻时效性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有机的真实”的观念,将真实视作一个过程而非与时间无关的抽象标准。G更看重新闻之“新”,好新闻应及时将获得的所有信息公开、透明地告知其受众;后续发生反转并不会影响公信力,但不及时、不公开、不透明则会。C认为,新闻对时效性的追求会不可避免地对其抵达真实造成负面影响;受众理应习惯“反转”,接受“反转”成为常态。E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对事件真实情况的趋近需要经历一个信息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反转”意味着对此前所披露信息的“证伪”,它与“证实”共同构成了新闻报道抵达真实的两大路径。
最后,受访者在谈论好新闻标准时,还常常提到立场和动机。他们认为,新闻真实性受立场和动机的影响,也因立场和动机才具备意义。出于对动机的判断,A认为报道血奴案这条新闻的记者本身也是受害者,假新闻的成因主要是新闻当事人有意编造谎言。因此她认为,血奴案这条新闻严格来说不属于假新闻,真正的假新闻应该是新闻报道者主动造假或者提供片面信息。I认为,从新闻的发布方视角看,任何媒体机构或个人的发声都一定会蕴含自身的立场在其中,而立场是不存在真假的。基于此,I对好新闻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动机和立场,而是实际的作用和意义,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就是好新闻。而在O看来,新闻自身的立场应当尽可能在报道中“隐身”,新闻应当是一个帮助大家思考并为思考提供话题的存在,是“我们跟社会连接的窗口”,决不能主导大众的想法。
(二)真实重要吗:后真相时代的认知过载
在讨论反转新闻和虚假新闻时,一些受访者透露出对真实性的“虚无主义”态度,体现出后真相时代的普遍心态。实际上,上文所讨论到的真实与立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态度的一种反映。而不少受访者持有更极端的观点,即真实性已经不重要,或者在认知过载的情况下放弃了对于真实性的要求。
在面对不断反转的新闻信息时,有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认知和立场并不是从一端被拉到另一端,而是被拉回到中间位置。尽管反转后的报道在他们看来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他们也很难指出这些报道存在何种问题,但当被问及看完事态反转后是否会完全被说服,受访者更倾向于表示“不能确定”。例如,G在看到血奴案发生反转的相关报道后,第一感觉是很荒谬,也对该名男子最初选择编造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的动机感到困惑和不解。但当被问及此刻对男子沦为“血奴”事件的真假判断时,她却表示尽管有大使馆和当地警方等国家层面的发声,但自己仍旧倾向于保持中立态度,认为此事的真实性已无法判断,“纯属虚构”的结论与最开始“全部属实”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类似地,来自香港的K是在访谈现场首次了解并阅读有关血奴案的新闻报道的,直到最后他也没能理解当事人编造谎言的动机,因此,即便有官方的通告在,他也不敢完全相信这件事就完全是假的。
放弃对真实性的追求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信息过载导致的疲惫,二是因新闻的贴近性不强或意义不大而无所谓真假。认知过载是传统专业新闻机构失去守门人功能之后给普通人带来的重要影响,这反过来会让网络用户重新思考传统媒体的正面价值。对于这种情况,J是一个典型代表。对于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的判断,经历了诸多反转事件之后的J选择放弃。在他看来,各方声音相互矛盾会让他感到混乱,即便后来表态的官方媒体或机构在他心里有着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但他仍会觉得自己已经很难完全去相信哪一方,这给他带来深深的无力感。
新闻议题的贴近性不强或者本身的重要性不大,也会让用户选择不再追求真实性。例如E和P均表示,自己对新闻真实性的在意程度是由该事件同个人生活的距离远近和关联程度共同决定的。只有那些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会对自己生活产生切实影响的事才最能引起他们对其中各类信息真假的兴趣和持续关注,这类新闻也往往最能调动自己对真假判断的主动性。I表示,对自己切身影响很小的新闻,他都会当成一般信息对待,其中的真假他并不在意;至于那些对自己切身影响比较大的新闻,例如宏观政策类或与个人职业选择高度相关的新闻,他才会进一步去思考真假问题。M同样在访谈中补充提及了近期热议的“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一事,在她看来此事并未涉及自身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她并不在意其真假,只当做一个有趣的事情看待。
最后,不少受访者对于缺乏真实性的新闻体现出谅解的态度,认为即使真实性有问题,这些新闻仍有其价值。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立场和功能。有访谈者甚至认为,新闻的真实性从属于新闻的价值和动机。J 认为,新闻的真假问题远不如其能激起多大热度来得重要,“如果一件事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么假一点也无所谓,只要能引发更多舆论的关注,最后能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这个新闻就算是好新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新闻本身即以真假难辨为主要特征的,访谈对象也偏向于谅解其中真实性的问题。例如在B看来,诸如王冰冰徐嘉余“恋情”一类的新闻,真假难辨即是其最大的“卖点”所在,受众本身对其真实性的要求和期望也并不高,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看就过去了,并不会特别在意其中各种信息的真假问题。
(三)反求诸己:新闻用户的能动性
虽然新闻真实性在后真相时代更加复杂和难以达成,但本次研究的受访对象仍然表达出对于新闻内容多样性和高品质新闻内容的诉求。除了依据文本、信源和预认知来主动判定真实性之外,一部分用户也意识到需要调整自身的新闻使用方式,增强自己的辨别能力。I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新闻主要承担的是提供信息的角色,对于信息真假的判断则属于受众在获取信息后的下一步动作。J也认为,在纷繁复杂的互联网世界里,尽管个人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认知局限,但他仍旧认为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首先,用户不断探索网络使用经验和习惯,积极设法改善自己的信息环境。从信源角度来看,虽然官方媒体仍然获得多数同学的信任,但是在阅读选择上官方媒体并不一定是首选。A获取新闻主要通过自媒体的渠道,因为官方媒体的可读性较差。F对于不同平台有自己的使用节奏,晚上睡觉前看微博,吃饭时刷B站,更偏好于从B站的知名UP主那里消费新闻。这是因为,这些视频不仅有对新闻事件的梳理,而且还提供了观点,让自己能够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待新闻。
其次,大多数受访者都意识到算法推荐的影响,部分同学尝试“驯服”算法、为己所用。为了不让算法和大数据知晓自己的喜好,K会特地关注一些不在自己兴趣范围内的博主,或给一些并不特别喜欢的内容点赞,他也会有意识地去比对不同平台的热搜榜单,来确保自己获取尽可能全面的新闻资讯。B和C都明确表示对微博的偏好,因为相比于小红书等,微博更能够带来多元信息和严肃新闻,避免自己的思维方式被算法所限定,C还常将微博用作交叉验证的平台。
在访谈中,每一位受访者均被问及是否会通过开定位和训练推送的方式给来让自己更有效获得信息。F主动提到了自己在网上获知的“信息茧房”这个概念,她会主动地在不同平台训练智能推送:在抖音上只点开和观看英语内容,因为这个平台对她来说主要是练习英语听力和口语;B站则主要看自己关注的博主。M比较担心算法通过获取用户位置,甚至靠技术手段“偷听”用户对话侵犯个人隐私,因此她会主动关闭定位功能。同样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H和O对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来驯化算法的行为是比较抗拒的,网友“一言不合就开喷”的强大网暴能力令她们对在网络中公开表达个人态度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O还认为网友的言论(尤其是经过反转的言论)势必会给当事人带来伤害,如果自己也参与讨论和发言,会产生愧疚感。
最后,不少受访者也通过消极的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认知和情感的均衡性。新闻回避一般是由新闻过载(news overload)导致的,影响因素包括了信息搜索的自我效能感(information-seeking self-efficacy)(Schmitt et al.,2018),以及新闻效能感(news efficacy)(Park,2019)。新闻过载会导致受众被动的和主动的新闻回避(Metag & Gurr,2022)。例如D在采访中表示,网络上常见新闻反转,这会导致他变得更抗拒接触新闻。在针对这一现象进一步讨论后我们发现,对于有的受访者而言,是否符合个人价值观和自身的情感认同度会成为影响其新闻回避的关键因素。例如,F对不同题材的新闻展示出不一样的态度:她以日本向大海中排放核废水一事为例,表示即使新闻内容较多,信息前后不一,她也会持续关注和搜索,因为“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而对娱乐类新闻,则会暂时放在一边不过多关注,一段时间后看最终的结果就好。这同时体现出关于新闻回避的两个不同的假设:在接触到新闻之后,主动搜索更多信息,进一步地强化或修正对于事件的真实性的认识;或者在不断接触同主题新闻后,主动进行新闻回避,不再关注。而影响是否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认知过载,还有新闻主题的重要性。
五、总结与讨论
在“受众转向”的理论主张下,本文对16位高校学生展开现象学取向的访谈,通过针对案例的讨论了解他们与新闻真实性相关的观念和实践。总体来看,本文的采访对象认同新闻真实性的价值,对于高品质的新闻和信息的多元性有自觉追求。研究发现,受访者在认识新闻真实性这一话题时存在双重归因。首先,用户认定“新闻是否真实”的依据被归结到制度性来源和文化来源两个方面,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信任的基本特征。其次,新闻真实性也被用户进一步地作为评价新闻品质、反思后真相时代以及调整自己新闻使用方式的依据。在他们看来,好新闻不仅应当是真实的,而且应当完整和及时,并且能够发挥影响人心及推动进步的功能;同时,新闻真实又是相对的、过程性的,受立场和价值所影响,在一定的情境下他们会放弃或者忽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此外,本研究的受访者中有不少都对算法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人选择积极尝试对算法进行“驯服”,将算法真正为己所用;有人则更加坚决地秉持回避态度,甚至有时还会特意去迷惑和欺骗算法。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鲜明地体现出算法通过用户的实践被整合进日常生活,进而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Siles et al.,2019),这与其他的文化要素共同影响了受访者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认知。
上述结论呈现出,面对社交媒体时代和人人都可以发声的情况,新闻真实性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发展出了不同于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新特征,也就是本文所定义的新闻真实性的俗民理论。欧美的新闻专业主义为我们思考记者、新闻、受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于真实性的“理想型”:肩负公共使命的记者根据专业标准将社会现实转化为标准的新闻文体,受众在真实性的行业承诺下通过新闻获取关于社会现实的可靠信息与知识,来指导他们的认知与行动。对于这一理想型的最初挑战可以追溯到李普曼和杜威关于记者与读者关系的争论,前者认为记者需要帮助读者了解过于复杂的政治世界;后者认为读者和公众应当参与到新闻生产中,这能让他们的公民性得到提升(Whipple,2005)。不过,上述争论尚未触及新闻与真实之间的不言自明的稳固关联;直到社交媒体时代和后真相时代、当新闻真实性成为问题并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实践、认知和思考后,上述的理想型才被显著地改写。
从新闻真实性的“理想型”到俗民理论,这种转变的核心动力是受众的变化。Frischlich等人以受众转向为大背景,区分出理想的参与者和行动者、被误导的人、批评性的使用者这三类受众(Frischlich et al.,2023)。Castro等人(2021)结合欧洲17国的大规模调查,定义出五类观众:几乎不看新闻的人、社交媒体新闻用户、传统主义者、在线新闻的搜索者,以及新闻的超级消费者。而社交媒体用户普遍被认为是积极的新闻使用者,记者应当回应他们的诉求,生产特定的信息(Ruotsalainen et al.,2021)。本文的访谈对象为高等院校的在校硕士博士,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看是一群独特的受众,普遍具备认知上的自觉,是批评性的使用者。由于社交媒体时代带来的信息过载和新闻文体本身的变化,受访者在接触具体新闻文本的过程中同时展现出具身的自我和清醒旁观的自我,也就是“阅读”和“狩猎”这两种认知模式;并且,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在受访者的新闻接受和新闻评价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这又与新闻本身的题材特点,以及他们对于新闻机构、新闻题材以及新闻人物的预认知密切相关。
正是受众的变化,改变了记者、新闻、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写了理想化的新闻真实性观念,发展出了新闻真实性的俗民理论。一方面,从受众与记者的关系来看,受众中心的新闻学(audience-oriented journalism)认为,记者所承担的角色中最为受众所认同的是作为解释者的记者(journalists as explainers)(Truyens & Picone,2023)。即,记者除了提供信息之外,还需要提供解释和评价。而受众自己也应当对自己负责,主动地搜集和辨析信息,并根据自己的新闻价值观调整使用习惯,防止陷入偏颇。最终,真实性并非来自于记者,而是记者和读者一起建构出来的(Dimitrakopoulou & Lewis,2022),尤其是当受众与新闻提供者的立场和价值达成统一的情况下。另一方面,从受众与新闻的关系来看,在社交媒体的情境中,用户有能力营造出个性化的信息环境,更主动地实现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将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题和观点屏蔽(Parmelee & Roman,2020)。同时,读者还会在认知过载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对于真实性的要求,在面对不确定的情境下借助“媒介失信”来降低复杂繁重的认知任务(Jakobs,2022)。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于,受访者对于新闻的态度兼具“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特点。前者倾向于认为新闻所实际发挥的社会功能比它本身是否真实更加重要,后者倾向于否认真实性的存在,二者都挑战了传统的新闻真实性观念。■
参考文献
操瑞青(2017)。作为假设的“新闻真实”: 新闻报道的“知识合法性”建构。《国际新闻界》,(05), 6-28。
陈力丹(2002)。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新闻记者》,(02) ,22-23。
胡杨,王啸(2019)。什么是“真实”——数字媒体时代受众对假新闻的认知与辨识。《新闻记者》,(08), 4-14。
蒋晓丽,李玮(2013)。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国际新闻界》,35(06),15-23。
李玮,沈玉莲(2019)。新闻何以为“假”?——兼论符合论、融贯论与社群真知论之于新闻证伪的作用机理。《新闻界》,(07),16-24。
李主斌(2011)。 符合论VS融贯论? 《自然辩证法研究》, 27(09),15-20。
刘自雄,王朱莹(2011)。被信任的假新闻——虚假信息的受众接受心理探。《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07),56-59。
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张恬等(2019)。2019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01),22-33。
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曹诗语等(2021)。2020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01), 23-37。
芮必峰(1997)。新闻本体论纲。《新闻与传播研究》,(04), 52-64。
史安斌,王沛楠(2017)。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美国大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生成机制。《新闻记者》,(06)4-12。
Baudrillard, J. (1983).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Los Angeles,USA: Semiotext(e).
Boyd C.O. (2001). Phenomenology the method. In Munhall P.L.(Ed.). Nursing research: A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pp. 93-122). SudburyMA: Jones and Bartlett Learning.
Carazo-Barrantes, C.Tristán-Jiménez, L.& Cajina-Rojas, M. (2023). Noticias Falsas: Dónde Se Encuentran Periodistas y Audiencias (y Dónde No). Contratexto(39)185-214.
CastroL.StrombackJ.EsserF.Van AelstP.De Vreese, C.AalbergA.Cardenal, A. S.et al. (2021). Navigating High-Choice European Politic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ews User Profile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7(4)827-859.
Costera Meijer, Irene. 2020. “Understanding the Audience Turn in Journalism: From Quality Discourse to Innovation Discourse as Anchoring Practices 1995-2020.” Journalism Studies. 21 (16): 2326-2342.
Couldry, N. (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14(2)115-132.
Creswell J. W. (199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Elder-VassD.FryerT. W.GroffR. P.NavarreteC.& Nellhaus, T. (2023). Does Critical Realism Need the Concept of Three Domains of Reality? A Roundtable. 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22222-239.
DeVitoM. A.BirnholtzJ.HancockJ. T.French, M.& LiuS. (2018). How People Form Folk Theories of Social Media Feeds and What it Means for How We Study Self-Present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CHI '18). (pp.1-12). New York, USA: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Dimitrakopoulou, D.& LewisS. C. (2022). The Generative Dialogue Framework and the Pursuit of Better Listening by Journalists: A Design-Centered Approach for More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s with Audiences. Digital Journalism, 11547-568.
FrischlichL.Eldridge, S. A.Figenschou, T. U.Ihlebk, K. A.Holt, K.& CushionS. (2023). Contesting the Mainstream: Towards an Audience-Centered Agenda of Alternative News Research. Digital Journalism, 11727-740.
Giglietto, F.Iannelli, L.Valerian, A.& RossiL. (2019). ‘Fake news’ is the invention of a liar: How false information circulates within the hybrid news system. Current Sociology67(4)625-642.
GroenewaldT. (2004). A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Design Illustra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3(1)42-55.
IngoldT. (2013). Dreaming of Dragons: On the Imagination of Real Lif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19(4)734-753.
JakobsI. (2022). Media Trust "Until Death"? Insights into Critical Media Users’ AttitudesTheir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and Mistrust Patter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Media4622-643624.
Malle, B. F. (1999). How People Explain Behavior: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1)21-43.
Metag, J.& Gurr, G. (2022). Too Much Informa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Avoidance of Referendum Information Prior to Voting Da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00646-667.
MillerD. (2016). Social Media in an English Village. London: UCL Press.
ParmeleeJ. H.& RomanN. (2020). Insta-echoes: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Avoidance on Instagram.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52101432.
ParkC. S. (2019). Does too much news on social media discourage news seeking? Mediating role of news efficacy between perceived news overload and news avoidance on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 Society5(3)1-12.
PerachR.Joyner, L.Husbands, D.& Buchanan, T. (2023). Why Do People Share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Online? Developing a Bottom-Up Descriptive Framework. Social Media + Society9(3).
PenneyJ. (2023). Entertainment Journalism as a Resource for Public Connec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Digital News Audiences. MediaCulture & Society45(6)1242-1257.
RobinsonG.& RundellJ.F. (1994). Rethinking Imagination: Culture and Creativity (1st ed.). Routledge.
Roberts, W.& GilesF. (2014). Mapping Nonfiction Narrative: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Analyzing Literary Journalism.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6(2)100-117.
RohrerI.& Thompson, M. (2022). Imagination The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3186-208.
RuotsalainenJ.Heinonen, S.HujanenJ.& VilliM. (2021). Pioneers as Peers: How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ts Imagine the Futures of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1(6)1045-1064.
Santos AlexandreR. (2022). Over the Ruins of Subjects: A Critique of Subjectivism in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3(4)292-312.
Schmitt, J. B.DebbeltC. A.& SchneiderF. M. (2018). Too much information? Predictors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news exposur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1(8)1151-1167.
ShenC.KasraM.PanW.BassettG. A.MallochY.& O’Brien, J. F. (2019). Fake images: The effects of source, intermediary, and digital media literacy on contextual assessment of image credibility online. New Media & Society21(2)438-463.
Sheri R. Levy, Luisa Ramírez, Lisa Rosenthaland Dina M. Karafantis. (2013). The Study of Lay Theories: A Piece of the Puzzle for Understanding Prejudice. In Mahzarin R. Banaji, and Susan A. Gelman (eds). Navigating the Social World: What InfantsChildren, and Other Species Can Teach Us, 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Neuroscience (pp. 318-322). New York, USA: Oxford Academic.
Siles, I.Espinoza-Rojas, J.NaranjoA.et al. (2019). The Mutual Domestication of Users and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on Netflix. 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 12(1).
SneathD.Holbraad, M.& Pedersen, M. A. (2009). Technologies of the Imagination: An Introduction. Ethnos, 74(1)30-35.
StandleeA.(2017). Digital Ethnography and Youth Culture: Methodological Techniques and Ethical Dilemmas. In Ingrid E. Castro & SwaugerM. (Eds.). Researching Children and Youth: Methodological Issues, Strategies, and Innovations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Children and YouthVol.22). (pp. 325-348). LeedsUK: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TandocE. C.Ling, R.Westlund, O.DuffyA.GohD.& LimZ. W. (2017). Audiences’ acts of authentication in the age of fake new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Media & Society20(8)2745-2763.
TaylorC. (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Truyens, P.& Picone, I. (2023). Does the Audience Welcome an Audience-Oriented Journalism? Journalism, 25(4)735-754.
TurnerM. (1996). The Literary Mind: The Origins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New York,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pple, M. (2005). The Dewey-Lippmann Debate Today: Communication DistortionsReflective Agency,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Sociological Theory, 23(2)156-178.
[作者简介]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杜珂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