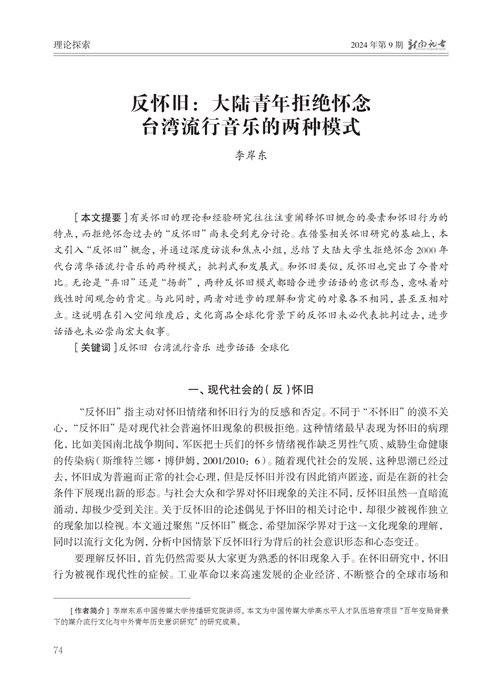反怀旧:大陆青年拒绝怀念台湾流行音乐的两种模式
李岸东
[本文提要]有关怀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往往注重阐释怀旧概念的要素和怀旧行为的特点,而拒绝怀念过去的“反怀旧”尚未受到充分讨论。在借鉴相关怀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反怀旧”概念,并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总结了大陆大学生拒绝怀念2000年代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两种模式:批判式和发展式。和怀旧类似,反怀旧也突出了今昔对比。无论是“弃旧”还是“扬新”,两种反怀旧模式都暗合进步话语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对线性时间观念的肯定。与此同时,两者对进步的理解和肯定的对象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这说明在引入空间维度后,文化商品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怀旧未必代表批判过去,进步话语也未必崇尚宏大叙事。
[关键词]反怀旧 台湾流行音乐 进步话语 全球化
一、现代社会的(反)怀旧
“反怀旧”指主动对怀旧情绪和怀旧行为的反感和否定。不同于“不怀旧”的漠不关心,“反怀旧”是对现代社会普遍怀旧现象的积极拒绝。这种情绪最早表现为怀旧的病理化,比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军医把士兵们的怀乡情绪视作缺乏男性气质、威胁生命健康的传染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2001/2010:6)。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思潮已经过去,怀旧成为普遍而正常的社会心理,但是反怀旧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展现出新的形态。与社会大众和学界对怀旧现象的关注不同,反怀旧虽然一直暗流涌动,却极少受到关注。关于反怀旧的论述偶见于怀旧的相关讨论中,却很少被视作独立的现象加以检视。本文通过聚焦“反怀旧”概念,希望加深学界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解,同时以流行文化为例,分析中国情景下反怀旧行为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心态变迁。
要理解反怀旧,首先仍然需要从大家更为熟悉的怀旧现象入手。在怀旧研究中,怀旧行为被视作现代性的症候。工业革命以来高速发展的企业经济、不断整合的全球市场和日新月异的交通通讯技术推动了人员的远距离流动和交往,人与乡土脱钩,乡愁应运而生。怀旧体现了对加速的反抗和对归属的渴望,反映出现代社会快节奏和流动性的特点(Shaw & Chase,1989)。作为一种与现代城市生活相伴的社会心态,人们对怀旧的认识已经从17、18世纪的耻化疾病发展到如今的正常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大众接受了怀旧这种沉溺于过去时空的忧伤,把它视作特定社会发展和人生阶段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情绪。如同斯维特兰娜·博伊姆(2001/2010:13)所说:“从18世纪起,探索怀旧的艰难任务就从医生那里转向诗人和哲学家。”
而到了20世纪末,这个艰难任务又从诗人和哲学家转向了商人和媒体从业者。大众媒体(尤其是影音媒体)迅速创造着“流行”,又因其易于重播的特点将昔日的“流行”转化为怀旧再度搬上台前。互联网出现后,怀旧内容的传播和怀旧群体的组织变得更加便利,大量怀旧主题的UGC内容和网络社群涌现出来。过去的媒介内容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怀旧充斥了日常的媒介消费,各类媒体成为“个人怀旧与社会怀旧交汇和扩散的大型储藏室”(Niemeyer,2014:1)。怀旧长久以来被视作对现代性的反叛,如今却在商业化浪潮中发展出了所谓“怀旧工业”。在中国语境里,吴靖将1990年代以来怀旧潮的兴起归结于两个因素(Wu,2006),其一是市场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如环境破坏、城乡差距扩大等)导致人们在时代巨变中渴求稳定与归属,其二是媒介市场和大众文化生产的兴起使文化产品遍布人们的日常生活,曾经受欢迎的怀旧媒介内容成为经济又保险的获利手段。这种晚期现代性(Giddens,1991)情境下市场与怀旧的结合,使得怀旧这门生意在如今的信息社会中随处可见。从电视时代不断重播的“暑期档”电视剧,到近几年火热的《声生不息》等流行文化怀旧类综艺节目,怀旧工业似乎已经发展成为个人难以回避的文化和经济现象。David Lowenthal认为当代媒介化、奇观化的怀旧已经脱离原有的怀旧实践,建构出自成一派的商业逻辑和媒介思维:“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充斥的不是怀旧,而是知识分子和大众媒体‘对怀旧的普遍关注’。”(Lowenthal,1989:29)以往“不怀旧”的人面对这样的“普遍关注”,也渐渐需要思考怀旧与自己的关系,转而成为“反怀旧”的人。
当下反怀旧心态的兴起与媒介化社会中怀旧内容的膨胀息息相关。但是,针对反怀旧的研究仍然少之又少。相关研究多见于文学学科,将反怀旧作为一种美学和诗学概念来考察。例如John M. Frankl解读韩国作家李箱的散文《倦怠》,认为作家通过“离开乡村”的反怀旧手法来抵抗日本殖民时期笼统的韩国民族主义思潮,以此基于个人经历而非国族叙事来定义作家本人与地方的关系(Frankl,2012;另见Zaritt,2013)。在社会科学领域,Emmanuelle Fantin(2014)认为雪铁龙公司的“反怀念”(anti-retro)广告把反抗式的姿态商业化,其目的仍然是唤起消费者的怀旧情感,以商品的伪个性包装来获取利益。Francesca Melhuish将英国脱欧团体在公投前的动员行动定义为“反怀旧式的帝国怀旧”(an anti-nostalgic form of empire nostalgia)(Melhuish,2022:1758),其面向未来、破旧立新的动员话语暗含了对大英帝国往日荣光的怀念。上述研究倾向于把反怀旧看做非黑即白的反抗性或霸权性力量,缺少对“反怀旧”概念化、类型化的机制分析。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文本和内容分析,较少通过访谈等研究方法探究大众如何理解和内化反怀旧话语。
反怀旧看似难成气候、不受学界重视,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作为社会现象较为分散、难以被建制性力量吸收。反怀旧存在明确的批判对象,不像怀旧心态那样易于被商业化。它往往诉诸个人情绪,而个人的不满尚未在社会层面形成合力。这样碎片的、个人的反怀旧给相关经验研究和材料收集提出了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怀旧现象不普遍、不值得研究。对怀旧的反感如暗潮汹涌,潜藏在社会思潮和怀旧心态之中。尤其在高速发展的社会,怀旧常常与停滞不前、不思进取挂钩。国内对于反怀旧较具影响的公共讨论来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0年对宋惠昌(2010)的一则访谈,他批评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怀旧“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思潮”,“是对新时期社会进步历史潮流的一种否定”。宋惠昌的言论引发了包括乌有之乡论坛在内大量社会主义怀旧人士的回应和抨击。宋的观点代表了社会迅速发展阶段人们对“历史美化论”和“以史为师”的排斥。这种排斥不只是三两个知识分子的牢骚,而是反映出社会变迁背后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在流行文化和社交媒体领域,这类反怀旧言论也并不罕见,例如Bilibili视频网站上各类台湾偶像剧尴尬剧情、“奇葩名场面”的盘点。可见,反怀旧与宏观社会情境密切相关,却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形成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因此并未得到理论界应有的重视。
基于以上不足,本文以大陆年轻人对台湾流行音乐的反怀旧为例,从理论和实证的视角分析反怀旧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意义建构机制。本文首先从进步话语入手,将“反怀旧”概念化,指出反怀旧是对现代社会线性时空观的再确认。接着通过对大陆年轻人拒绝怀念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反怀旧案例研究,进一步探索“反怀旧”的概念性框架。本文在经验研究中呈现了两种反怀旧的模式,它们虽然都反映了进步话语的意识形态,却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看待大陆与台湾、过去与现在的方式。以中国语境下的流行文化怀旧为例,本文认为应当将媒介化社会的反怀旧心态置于全球文化市场的比较视野中来考察。受众不再仅仅消费基于本土文化的流行文化产品,这提醒我们关注怀旧的空间对比(“此与彼”)与时间对比(“今与昔”)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会说明,随着空间问题在反怀旧实践中越来越凸显,反怀旧的意义建构过程也变得更加多元,反怀旧未必意味着厌恶过去,而是从全球语境下的时空对比中创造了重新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可能性。
二、反怀旧与进步话语
怀旧常常被视作进步话语的对立面。“进步”(progress)是启蒙时期兴起的一种认识时间的历史哲学。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循环时间和基督教的弥赛亚时间,进步话语中的历史时间是线性的、不断发展的,最终通向人类的解放和自由(Koselleck,2004)。西方启蒙哲学家将进步视作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说是均质化的“时间”转化为“历史”的必要条件。“进步”由此定义了人类社会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历史在进步的自然规律中发展,引领客观世界走向自由。进步话语不只是先人的学理探讨,更根植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社会。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人们开始期待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未来,进步话语也即暗含了“过去-现在-未来”的递进关系。进步话语秉持“向前看”的历史观,认为“明天会更好”;这种历史观基于当时社会迅速发展的现实,被视作人类天性和自然法则。康德的“普遍历史”、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体现了进步的线性时间观。
怀旧既是进步的副产品,又成为进步的反叛者。Kimberly Smith(2000:507)形象地把怀旧称做“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补遗”(an addendum to progressive ideology),认为怀旧既凸显出进步话语有限的解释力度和感召力,又让“现代化的受害者们”找到了慰藉的发泄口。这说明怀旧与进步之间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纠缠不清。怀旧不是对进步历史观的全然颠覆,而是给历史这架马车上的失意者提供了暂时的休憩所,是加速前进的历史时间中依靠回忆而获得的确定性与归属感。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进步话语和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等纪念文化同步兴起,这种“文化悖论”(Pickering,Keightley,2006:924)说明进步与怀旧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人们越发想要逃离过去,就越发怀念过去(Chaney,2002)。
反怀旧反映了进步话语中逃离过去的面向,是对线性时间观念的再确认。既然历史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就不需要拘泥于过去。反怀旧体现出Koselleck(2004)所说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的割裂。尤其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旧经验越来越难以指导新实践;或者现实地说,过去对于迈向进步的未来而言越来越微不足道,因此无需怀旧。进步主义的线性时间观使得反怀旧往往带有功利色彩。在这个层面上,反怀旧所反对的是“没有用”或者使人停滞不前的过去。这种反怀旧心态常常发生在对当下和未来持正面态度的情况下。正因为形势一片大好、进步浪潮高歌猛进,所以排斥怀旧。反怀旧暗含了对新与旧、少与老、过去与未来的好恶。20世纪初意大利文艺界兴起的未来主义是这种好恶的一个极端案例。这种艺术理念发轫于世纪之交西方科技高速发展、殖民活动加快扩张的鼎盛时期,崇尚速度、科技、青春,相信进步的未来是历史的终结,正如《未来主义宣言》中所写:“我们站在千秋万代的最后岬角上!当我们想要突破那扇名为‘不可能性’的神秘之门时,为什么还要回头看呢?”(Marinetti,1909/1973)
反怀旧和进步话语都不只是时间概念,更与空间息息相关。现代社会的移动性使人离开故乡,空间的位移创造了时间体验的割裂,过去成为Lowenthal(1985)所说的“异国”。“过去”这个怀旧的意向更像是前现代的残留物,保留着质朴的美好,但只能供现代人暂时伤怀。更重要的是,空间为进步话语划定了比较的坐标系。“进步不仅是对于时间进展的、也是对空间拓展的一种叙事方法”(斯维特兰娜·博伊姆,2001/2010:11)。孕育了进步话语的西方现代性,同时也见证了全球体系的兴起。进步话语在确立线性时间观的同时,也用这套线性逻辑来衡量进步的程度。从不同地域的对比视角来看,进步话语凸显了“人类发展的多个层面在进步程度上的不平等”(Schlegel,1795,转引自Koselleck,2004:266)。跨国贸易、殖民扩张和国家战争等第一波全球化的进展,同时也是“发现全球,以及发现各地人民处在不同发展阶段”(Koselleck,2004:266)的过程。进步话语与反怀旧与生俱来蕴含着以进步程度来衡量是非的国家想象。比如黑格尔认为,历史意识是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一环。只有意识到线性发展的历史规律,理解人类进步的时间进程和这种目的论式的人类使命,才能算觉醒自我意识、实现个人自由(Hegel,1824/1956)。黑格尔由此划分了不同地域的进步程度,认为只有普鲁士的政治制度才实现了历史意识的觉醒,而东方(中国、印度等)因为各自制度的缺陷,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进步的使命,仍然生活在混沌之中,无法达到“自觉的历史”。这种目的论的时空观脱胎于“线性的启蒙历史”(杜赞奇,1997/2009),通过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建构了“共时的不共时性”(the nonsimultaneous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Koselleck,2004:266)。就像“过去、现在、未来”一样,不同地域之间也开始形成差序。进步的区域代表着未来,落后的区域则停留在过去。
进步话语下的反怀旧既反对落后的时间,也反对落后的空间。沉溺于怀旧的区域和个人被斥责为不思进取。在如今商品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反怀旧的空间属性日益凸显。这是因为许多怀旧的对象不再是本地的文化内容。(反)怀旧由此被置于全球文化市场的时空脉络中。过去流行的文化产品可能来自世界各地,怀旧的商品化和媒介化使得怀旧逐渐与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挂钩(Ching,1994)。这种(反)怀旧的比较对象既是过去的个人经历,也是过去消费过的文化产品和该产品所包含的一整套品位、审美、生活态度和消费观念。反怀旧要么否定旧产品所代表的那套意识形态,要么认为新的文化内容更加优越。这其中还涉及两地文化生产和消费在过去与现在的发展对比。可以说,引入空间和市场的维度后,反怀旧现象变得更加复杂,其意义建构过程也更加多元。
和怀旧一样,反怀旧虽然指向过去,却表达了对当下的关切和诉求(Davis,1979;叶荫聪,2010)。反怀旧既可能通过批判“别处”的过去来肯定“此地”的发展,也可以借“别处”的进步来反思“此地”的不足。在文化产品全球流通的当下,普遍的商品和区域的(反)怀旧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和意义建构过程,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接下来,本文以大陆大学生群体对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反怀旧为案例,重点分析两种反怀旧模式:批判式和发展式。这两种反怀旧解读虽然都以进步话语肯定了线性时间观念、认为无需留恋2000年代台湾国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但通过大陆和台湾流行音乐的时空对比,它们反思的对象和对两岸文化产业发展的认识却大相径庭。
三、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台湾流行音乐深刻影响了大陆音乐市场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大陆文化政策逐渐开放、收音机等播放设备开始普及,大量台湾流行音乐作品通过各种途径涌入大陆市场(Kang,2022)。随着索尼、环球、百代等国际唱片公司于1990年代初期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台湾流行音乐融入全球文化产业版图,台湾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中心”(Ho,2006:188)。国际资本的进入标志着台湾流行音乐市场逐渐成熟,这不仅体现在其内容生产和发售的商业化运营,更体现在其有别于大陆革命传统的类型化音乐风格。这种风格被学界和业界称做“华语流行”(mandopop)或“港台”流行审美。台湾华语流行被视作表达个性、崇尚个人主义、关注情感体验、描绘“浪漫爱”(romantic love)的芭乐(ballad)情歌类型(Gold,1993;Baranovitch,2003;Moskowitz,2009;黄俊铭,2024)。这种音乐类型与大陆的民歌、革命歌曲中的集体主义和乡土特色形成对比,很快填补了音乐市场的空白,形塑了众多大陆听众对城市生活与西方现代性的流行想象。
2000年代是台湾流行音乐最后的辉煌时期,也见证了全球唱片产业的盛极而衰。在这一时期,台湾流行音乐的市场份额曾经达到80%以上(Moskowitz,2010a),周杰伦、蔡依林、SHE等现象级歌手在华语市场获得了很高知名度,流行音乐市场也越发成熟。但随着网络流媒体和大陆选秀节目的兴起,大厂牌的商业模式和台湾流行音乐的优势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台湾逐渐被大陆音乐产业迎头赶上,失去了在大陆市场的主导地位。台湾流行音乐在2000年代的领先地位已经不再,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歌手与歌曲也退回到怀旧的场域。
(二)研究方法
本文经验研究采取焦点小组法和深度访谈法,研究对象选定为大陆大学生群体(受访时年龄18~25岁)。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亲身经历过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鼎盛时期,曾经也是台湾华语流行的忠实听众。研究者通过豆瓣、微信等个人账号发布招募信息,采取自愿非随机抽样和滚雪球抽样(Schillewaert,Langerak & Duharnel,1998)结合的方式招募访谈对象。从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共进行了三轮访谈,由于新冠疫情影响,部分访谈为线上进行。最终组织了4组线下焦点小组和3组线上焦点小组,进行29场深度访谈。除了1人因为个人原因中途退出外,30名参与焦点小组的访谈对象都在后续接受了半结构式个人访谈。焦点小组的分组考虑了性别、专业和教育程度的多样性,并在线上焦点小组中确保了组内成员家乡和学校所在城市的差异性。
根据焦点小组和深度访谈各自的特点(Lune & Berg,2017:94;Hennink,Hutter & Bailey,2020),本研究对访谈对象采取先焦点小组、后深度访谈的顺序。焦点小组主要用来回忆印象深刻的台湾流行文化内容以及曾经接受此类内容的经历。个人访谈则偏重观点类的问题,主要考察访谈对象对于台湾流行文化和两岸关系的认知、态度及其变化。本文在焦点小组中采取“自由浮动式”(free-floating)访谈设计,以开放式问题展开讨论,减少研究者对讨论话题的干预(Cuc et al.,2006;Brown & Reavey,2013)。这种访谈设计被广泛运用于集体记忆研究中,用以探索对于访谈对象而言重要且印象深刻的记忆(Schuman & Rodgers,2004;Jennings & Zhang,2005)。在具体操作上,本研究参考Monique Hannink(2020)等人提出的“漏斗结构”(funnel structure)来设计焦点小组问题,焦点小组并没有选定具体的流行文化内容品类,而是让参与者自己回忆从小到大印象深刻的台湾文化产品。最终,所有7场焦点小组和29场个人访谈都频繁提及了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每组中都有访谈对象持反怀旧态度,而且他们往往会更加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访谈材料中涉及反怀旧的讨论,构成了本文的经验研究的数据。
本文经验研究考察的“反怀旧”,具体是指访谈对象对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抵触和拒绝怀念。他们的行为被定义为“反怀旧”而非“不怀旧”,是因为他们在访谈中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即普遍存在的台湾流行文化怀旧情绪。反怀旧的访谈对象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不是怀旧者,并对怀旧行为持负面看法。在自由讨论未被引导的情况下主动表达“我不怀旧”的观点,本身就预设了怀旧这个对立面。他们所反对的“怀旧”,有时源自焦点小组中其他参与者表达的怀旧情感,有时源自遍布于各类媒体中的怀旧内容,有时也源自访谈对象抽象层面上对“怀旧”观念本身的反感。反怀旧与怀旧密不可分,怀旧情绪是反怀旧观点的对话对象和“假想敌”。具体到本研究,其他访谈对象的怀旧言论往往是激起反怀旧讨论的导火索,而随后的讨论中,怀旧又常被视作普遍的社会心态和文化现象加以评判。总之如前文所说,(反)怀旧连接了个体和集体、微观和宏观的社会语境,当怀旧成为充斥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时,“怀旧与否”就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反怀旧是对怀旧现象的一种直接回应(Gray,2003)。
采取群体和个人访谈、将记忆作为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方法论和分析视角(Kuhn,2002;Keightley,2010),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再赘述。最终,本文区分了两种差异明显的反怀旧模式:批判式和发展式。由于案例和样本量的限制,这两种模式并不是对所有反怀旧类型的穷举。但是这两种模式反映出了反怀旧两个典型的不同面向,具有代表性。通过分析这两个面向,本研究希望展现反怀旧和进步话语在不同方向的时空对比中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接下来本研究将结合经验材料,分析大陆年轻人拒绝怀念台湾流行音乐的两种阐释路径。
四、台湾流行音乐的反怀旧阐释
在展开分析前需要指出,虽然个人对怀旧的态度与其所属的人生阶段密切相关(老年人被认为更偏好怀旧,而年轻人则往往排斥怀旧,Davis,1979;萧阿勤,2017),但是在当下怀旧商业化和媒介化的情况下,青年人群反而是“怀旧工业”的主要目标受众。音乐人高晓松在谈到港台流行音乐怀旧时说:“我觉得怀旧就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的时候才怀旧,谁老了还怀旧?老了早看开了,年轻的时候,一个是怀旧,一个是每个人都觉得上一个时代更美好。”(看理想,2019)年轻人经历升学、求职、工作等不同人生阶段,处在转折期和成长期,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和快速变化的生活时,更容易怀念过去。此外,各种媒体对怀旧文化推波助澜,将过去神话、塑造出各种寄托向往和渴望的“黄金年代”,这些高度叙事化、商品化的过去正是为了满足目标受众在当下无法实现的精神诉求。因此,当下年轻人的反怀旧情绪并不都是因为他们“还年轻”。相反,正因为他们年轻,怀旧之于这个群体成了洪美恩(Ang,1982)所说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怀旧的快感、屈服于大众文化的耻感和精英阶层的不屑感并存,将(反)怀旧塑造成不得不面对的热点文化话题——要么沉溺,要么抛弃。
此外,虽然本文指出当代的怀旧文化和怀旧消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类媒介的推波助澜,反抗怀旧也往往与批判消费主义和媒介奇观合流。但是,本文经验研究所讨论的反怀旧,更多针对普遍的流行文化怀旧情绪,而没有具体提及当下怀旧现象的媒介化、商品化面向。基于反对媒介策划和消费主义而产生的“反怀旧”,在表达方式、批判对象、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与本文所讨论的反怀旧有所区别,所以无法涵盖在本文的分析中,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跟进。
本文在文化商品全球化的背景下解析反怀旧。文化商品全球化意味着跨区域的消费,消费者接触的文化产品未必出自当地文化产业,反怀旧因此在“今与昔”(过去-现在)的时间对比之外,更涉及了“此与彼”(本地-非本地)的空间对比。在本文的案例研究中,反怀旧的对象是台湾流行音乐,与其对应的则是大陆流行音乐,并且有时还包含其他地区的流行文化对比,例如韩国(见下文)。如前文所述,“港台”流行文化在引入大陆之初就区别于当地的文艺作品,形成了其独特的类型、审美和意识形态,长久以来被视作区别于大陆的独特文化产品。客观的产业区隔、内容差异和主观的区别对待是两地流行音乐比较的基础。
反怀旧在时间维度上批判过去、肯定现在,体现了进步主义的时间观。但在引入空间维度后,批判和肯定的对象不同,所产生的效果和意义建构过程也不同。过去与现在、本地与非本地、批判与肯定,不同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展现了反怀旧意义生产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最终都通过时空对比来定位当下的自我。人们通过反怀旧赋予这些时空以不同的意义和情感寄托,由此将对于当下自我的想象与期待投射在那些或许在彼时彼地也从未存在过的世界中。
台湾流行音乐属于非本地文化产品,针对台湾流行音乐有两种反怀旧模式:第一种是批判过去的台湾流行音乐,其反怀旧的动因是昔不如今,所以往往伴随着肯定当下的大陆流行音乐;第二种是肯定现在的台湾流行音乐,其反怀旧的动因是此不如彼,所以往往伴随着肯定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并借此反思大陆流行音乐。这两种态度解释了大陆年轻人为何不再怀念台湾流行音乐,构成两类反怀旧路径:批判式反怀旧和发展式反怀旧。
(一)批判式反怀旧
批判式反怀旧对2000年代的台湾流行音乐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类音乐的内容水平不高,当时的流行也是因为过去同类内容匮乏、大众审美水平较低。在这种解读中,过去落后于现在,从如今大陆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后见之明来看,那时的大陆正处于文化商品全球化的初级阶段,曾经的听众缺乏对比、渠道有限。台湾流行音乐是商业化流行音乐类型进入大陆市场的“先头兵”,占有时间差优势,却并非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例如有访谈对象提到:“小的时候,周杰伦、蔡依林的歌还非常流行,因为当时内地不像现在这样,歌手们百花齐放。那时候比较火的歌手,印象中都是台湾那边的。”(G03-02,男,焦点小组,2020)另一位访谈对象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进步视角下的今昔对比:“现在像台北、高雄这样的大城市,和北上广比起来也就那么回事。你就像很多流行音乐、偶像剧,放在20年前就很厉害,现在也平平无奇……所以我们现在并不会觉得台湾更发达。”(G06-03,女,焦点小组,2021)
可见,批判式反怀旧不仅反对怀念台湾流行音乐,更是反对“过去”这个时态所代表的落后、贫乏、狭隘等意象。过去喜爱的事物如今看来“平淡无奇”,正反映了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这种线性时间观念与当代年轻人成长中所经历的国家实力崛起相对应,体现出社会变迁中进步主义的社会心态。这种今昔对比也与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进程相对应。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成长于流媒体兴起的时代,通过早期的音乐分享网站和如今的流媒体平台,可以很方便地收听和分享日韩、欧美的流行音乐。听众比较的对象不再限于港台和大陆,更拓展到全球其他文化市场。
文化市场全球化的底色是商品逻辑,台湾流行音乐不过是全球市场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在这个层面上,反怀旧将台湾流行音乐视作过时的、低质量的商品。一位访谈对象童年时是台湾组合飞轮海和韩国组合EXO的粉丝,经历了从“哈台”到“哈韩”的转变,她认为迷恋飞轮海是自己一段尴尬的“黑历史”(G05-05,女,个人访谈,2021):
现在再去看他们(飞轮海)当时的演出视频、听他们的歌,我会觉得:天啊,为什么每一句都不在调上?为什么一离开录音室就唱得这么烂?我当时可能是被炎亚纶(飞轮海成员)好看的外表蒙蔽了,戴上了女友的滤镜,然后就浪费了很多时间金钱。
有学者认为,流行音乐因其独特的情动效果和与个人经历的勾连,能够串联起个体情感与集体情景,“超越个体与集体、私密与公共、身与心的显著区隔”(Poga?ar,2015:216)。在这个案例里,反怀旧将对台湾音乐团体的批评编织进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中,曾经痴迷的偶像如今被视作低质量的文化产品,这种认知反过来又尴尬地证明了童年时自己的品位低下。在文化产业对偶像的标准下,过去的沉迷被访谈对象否定,反怀旧不仅是因为客观的产品质量,也包含了主观情绪上的尴尬和回避。这位访谈对象接着比较了不同区域的流行文化包装和偶像组合的专业素质(G05-05,女,个人访谈,2021):
研究者:那你现在回头看EXO,也会觉得他们和飞轮海一样过时、唱功差吗?
访谈对象:不会,我觉得EXO的实力还是很强。我现在有时候会听他们的歌、刷到他们的舞台,会觉得他们的业务能力依然在线,而且感觉越来越好……但是飞轮海,现在回头再看就一直觉得是我的“黑历史”。为什么青春期会喜欢的这样的人?哎,不过,当时也没有太多选择。
……
访谈对象:EXO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们的表情管理和情绪管理能力真的太强了。有可能上一秒还非常憔悴,下一秒看到粉丝来了,就能立马挂上笑脸。我感觉飞轮海做不到这样。
这段访谈展现出文化商品全球化背景下反怀旧的两个面向:其一是全球文化市场的空间对比,其二是反怀旧对象被视作“普遍的商品”。在论及亚洲主义与共同体想象时,姜子馨认为,如果把“大众文化的‘商品-音像’属性”视作想象同一性和共同体的基础形式,那么全球和区域文化内部的差异与摩擦都会被“文化权力全球分配中的通约与兼容”(commensurablility and compatibility)所掩盖(Ching,2000:235)。也就是说,反怀旧对象普遍的商品属性成为跨区域比较的标准,过去的事物只能在全球市场的这套标准中被比较,进而被怀念抑或抗拒。访谈对象并不反感EXO所代表的韩国流行文化,因为他们仍然符合进步话语的期待。相反,停滞不前的台湾流行文化已经被不断进步的“我”抛诸脑后,不必恋旧。访谈对象使用商品消费含义的“业务能力”一词来比较飞轮海与EXO,暗示了全球商品时代跨区域的比较标准。流行文化已经不是童年时“造梦”(fantasy-making)的欲望投射,不再服务于“女友粉”的浪漫想象;它被摘下了情感的光环,成为文化市场货架上一件大同小异的、可比较的商品。
上述案例展示了批判式反怀旧的一种模式。除此之外,对台湾流行音乐内容的直接批评也同样带有进步话语的底色。前文提到,“港台”流行音乐形成了区别于大陆音乐作品的独特审美和音乐类型,是音乐市场高度商品化的产物。这类作品以崇尚个人选择、关注内心情感的“浪漫爱”为主题,在作曲上带有“芭乐”音乐的特色,旋律舒缓、缺少律动、富有叙事性和抒情性。Marc L. Moskowitz(2010b:52-68;另见Lin & Chan,2022)指出,以“孤单寂寞”为主题的芭乐情歌是台湾流行音乐的特色,这类情歌尤其区别于大陆积极昂扬的革命歌曲,为当时个体化进程下的城市听众提供了私人情感共鸣的新渠道。到今天,这种绕开宏大叙事的“情情爱爱”仍然塑造了大陆年轻人对台湾的总体印象:“小时候听台湾音乐,他们的MV都拍得很小清新,那会儿听的那些歌,也都是情情爱爱的,给人感觉就是小清新、小确幸这一类。”(G07-05,女,焦点小组,2020)在本研究中,访谈对象们较少直接以进步话语来批评台湾流行音乐内容,但是,港台流行音乐所代表的“浪漫爱”、“痴男怨女”被认为是不思进取、沉溺于小情小爱的表现。例如(G01-01,女,焦点小组,2019):
我对台湾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浪漫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它的情感、人文气息很浓,整体上比较可爱,一直有种上世纪90年代的感觉……我觉得台湾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层的人,都很迷茫、幼稚,可以说很真诚也很可爱,但其实就是迷茫,缺少进取心,还有短视。
批判式反怀旧以“旧不如新”的本质主义观点看待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时态,同时把“向前看”理解成锐意进取的积极态度,而不符合这种态度的私人情感和消极情绪则被排斥、被认作阻碍进步的絮语。“短视”指沉迷于描绘浪漫关系之“小”,因而无法想象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之“大”。台湾左派学者赵刚(2014)认为“小确幸”的感觉结构暗含了经济停滞的台湾社会面对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的无力和失落:无从“大”繁荣,只得“小”确幸。从大陆的视角来看,批判式反怀旧即是对这种宏大叙事和进步话语的再确认。
总结来说,批判式反怀旧从两个维度上拒绝怀念台湾流行音乐。其一是将过去的音乐视作过时的、低质量的商品,随着审美和文化产业的进步被自然淘汰;其二是批评流行音乐的浪漫爱内容,认为这类音乐拘泥于个人情感和亲密关系,无法反映大时代的发展。这两种路径都把台湾流行音乐放置在流行文化产业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全球市场比较视野中。批判式反怀旧类似黑格尔式的“目的论进步话语”(Tam ,Meek Lange,2024),认为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遵循进步的规律达成自由和解放。个人的能动性被进步的客观性所否定,社会为了达成进步而努力进取,不遵循进步规律的怀旧和小情小爱则被贬斥为历史的逆流。
(二)发展式反怀旧
发展式反怀旧并不反感200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而是认可台湾音乐产业在当下的发展,认为如今的台湾音乐不断进步,同样可圈可点,所以不需要怀旧。怀旧往往源于对当下的不满或不安,而发展式反怀旧则体现对当下的认同。与批判式反怀旧类似,发展式反怀旧同样肯定了历史时间的线性发展,并通过肯定台湾流行音乐产业的进步来证成这种线性时间观。持这类态度的访谈对象虽然也承认过去的芭乐情歌已经不合时宜,但在他们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无需苛责。现在的台湾音乐好于当年,正好符合了进步的历史意识。一位访谈对象认为(G05-04,女,焦点小组,2020):
在我心中,流行音乐和偶像剧已经不能代表台湾了。现在的台湾已经不再流行了。它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流行文化,而是一种比较小众、比较独立的文化。到我长大了,价值观开始形成的时候,我会觉得台湾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依然很吸引我。
她接着将进步话语融入个人成长历程中,认为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她的长大同步,一直满足着她不断变化的情感需求和审美品位(G05-04,女,焦点小组,2020):
我对台湾的最初印象是小时候的偶像剧和流行歌手,那时了解得非常的浅显,感觉台湾就是比较甜美的那种、被包装着的感觉。然后直到初中我非常喜欢两个台湾的乐队,苏打绿和五月天,他们的歌一直陪伴我成长……台湾给人感觉是一个很青春的地方,会让人很向往。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我对台湾的了解更深刻了。这时期我开始喜欢台湾一些小众的独立乐队,我觉得跟大陆相比,台湾的独立乐队文化更丰富,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创作环境相对比较自由。我感受很深的是他们独立乐队的创作题材很深刻。比如在这种很压抑的现代社会,他们会去探求自我的价值、对这个社会发出一些质疑。台湾音乐有很多面向,我觉得会比大陆的歌曲更深刻一些。
在她的描述中,个人成长也是对台湾音乐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小时候流行的芭乐音乐是“浅显”的内容,以爱情主题的“甜美”为主调,充满商业化的“包装”。初中后喜欢的台湾乐队伴随她成长,让台湾在她印象中成为一个“很青春”的地方。到了现在的大学阶段,她对台湾的了解“更深刻了”,开始接触独立乐队,并有意识地比较台湾与大陆流行音乐的区别。这样的成长叙事贴合进步话语的时空对比,把“我”的成长和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联系起来,进步成为和长大成人一样的客观规律。因为台湾音乐市场仍在蓬勃发展,也因为成长中的“我”对台湾的认识不断深化,所以没有必要怀旧。
对台湾音乐的肯定,最终落脚到对大陆的反思。在引入空间维度后,非本地的反怀旧与本地的怀旧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反观当下自身的不足。访谈对象在回忆中表达了对台湾独立音乐的欣赏,并将该音乐类型与“甜美”的芭乐情歌区别开,认为独立音乐直面社会问题、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独立思考。正如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与大陆音乐的分野那样,“独立”与“芭乐”的区隔也建构起了一套时空比较下的品味等级秩序。这基本符合了大众对独立音乐这一音乐类型的社会想象。David Hesmondhalgh(1999)总结了独立音乐反主流的两个特点,第一是更密切而本真地与青年文化相关联,第二是营造了创意与商业的新型互动关系和产业模式。通过区分过去/大陆的“流行”和现在/台湾的“独立”,访谈对象把独立音乐的发展视作进步的表现,因为这样的产业调整创造出了“更深刻”的音乐内容。
对台湾独立音乐的意义建构说明,衡量进步的标准取决于个人阐释。在这个案例中,音乐内容的多元和共鸣说明台湾音乐市场发展良好,而批判式反怀旧则更常以音乐产业的经济效益或宏观经济形势来判断进步与否。从宏观视角来看,台湾独立音乐的发展反而是唱片市场萎缩、台湾流行文化失去竞争力之后的无奈突围(Jian,2019;Lin,2021)。“小众”的独立音乐可以代表多元化发展,也可以被用来证明台湾文化影响力的减弱。换句话说,发展式反怀旧通过对比大陆音乐缺失的部分来建构起台湾音乐的优越性。认可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暗含了定义“何为进步”的阐释过程。另一位访谈对象也明确区分了小时候的流行音乐和长大后的独立音乐,并且从聆听中发现了两岸都市青年的相似性(G07-01,女,个人访谈,2020):
访谈对象:台湾现在其实已经不是小时候那种(流行音乐),我自己对那个东西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听的更多的是独立乐团,包括最近常听台湾摇滚……他们(台湾)在整个摇滚乐的范畴下是有高水平的作品的。我觉得他和大陆的摇滚乐是有呼应的,没有完全把自己隔离出去,并不存在和大陆音乐的分野,都是在说很相似的事、用摇滚乐相同的形式去表达,我觉得是差不多的。除了他们的水平比较高一点。
访谈者:你说的相似,具体是指什么?
访谈对象:……(提到台湾乐队“伤心欲绝”《一整个世代的宿醉》中的歌词:“台北盆地最大的哀愁就是,远不如华北平原唱来惆怅”)这首歌描写台湾现代青年面临的很多危机和困境……(听这首歌时)就会觉得大家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人。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更明显看出两种反怀旧比较方式的异同。两者都在流行音乐类型的范畴里,将台湾音乐视作文化产品来评价。批判式反怀旧的视角聚焦于过去,把2000年代的台湾芭乐歌曲视作过时的、缺乏格局的商品。发展式反怀旧则认为台湾乐坛已经进步,不需要再纠缠于过去,其比较视野立足于现在。在上述案例中,访谈对象关注两岸的空间对比,比较的坐标不再是芭乐,而是摇滚这一小众而反叛的音乐类型。两种反怀旧定义进步的标准也不相同。批判式反怀旧以宏大叙事和经济发展为标准,认为过去的台湾音乐“太小家子气”,不符合进步话语的进取精神;发展式反怀旧则以情感共鸣为标准,从台湾摇滚所蕴含的感情中自照,由此肯定当下台湾音乐的进步。只要台湾流行音乐仍然可以如同过去一样满足听众的心理需求、唱出代表他们的声音,就无需寄情于怀旧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态度。
虽然两种反怀旧模式对待台湾音乐的态度截然相反,但是它们都认可进步话语的线性时间观念,只不过批判式反怀旧以单一的宏大叙事为准绳,排斥个人情感;发展式反怀旧则强调多元、开放的进步标准:“他们感觉更自由,因为都是独立音乐人,自己写歌,自己唱。”(G07-01,女,个人访谈,2020)两者的比较标准互斥,要么崇尚“大局”,要么珍惜“小众”。持批判式观点的人,往往对台湾乐坛的新动向并不了解;发展式反怀旧则持续关注台湾音乐在当下的走向,对新的音乐人和音乐类型如数家珍。声称“向前看”的批判式反怀旧,却恰恰不关注台湾音乐的现在,只看到过去。又或者说,如今走入小众市场的台湾流行音乐,在他们眼中只是进一步佐证了台湾音乐市场的衰败。在目的论式的进步话语中,批判式反怀旧的这套时空观念仍旧自洽。
最后,虽然两种反怀旧模式都体现出文化商品全球化的思维模式,但两者空间比较的基础并不相同。这里所说的“比较的基础”,是指作为可比性(comparability)基本要素的“共性”(commonality)。在区域比较视野的建构中,酒井直树(Sakai,2019)敏锐地指出,有限度的共性是可比性的前提。只有确立了互相关联的“属内共性”(genus similarity),才能在共同的维度进一步讨论比较对象的“种间差异”(spices difference)。面对全球文化市场,批判式反怀旧的比较共性来自普遍的商品属性——飞轮海和EXO都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业务水平”决定商品优劣。发展式反怀旧则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共同境况——在普遍的资本逻辑下,两岸青年“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人”。除了强调共情和社会关怀,其他访谈对象还提及了尊重多元民族和语言(如原住民音乐、金马奖设置闽南语歌曲奖项等)、扎根乡土(如现今仍然活跃的独立音乐人林生祥)等衡量进步的面向。这些多元的价值观念挑战了唯经济发展论的单一评价标准,后者常被认为是现代进步话语的意识形态基础(Bonnett,2010)。可见在时空对比中,发展式反怀旧虽然坚持进步话语的线性时间观,但未必厌恶过去,也未必独尊宏大叙事,而是保有另类的阐释空间。
总结来说,发展式反怀旧更贴近康德式的“非目的论进步话语”(Tam ,Meek Lange,2024)。进步虽然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却不是其最终目的,也绝非客观不可逆,而是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倡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制度的约束力,才能在不断反思中达成进步。访谈对象们多次提到的台湾音乐的创作环境和产业政策,也是在强调“人”的因素。在现实的产业发展中,台湾自2007年以来推出的乐团补助政策“大大协助了非主流的音乐录制出版”(简妙如,2013:105)。这符合访谈对象们的观察和反思,说明制度的扶持的确促进了台湾音乐由“流行”向“小众”、由商业化大厂牌向独立音乐的转型。
五、结论
Michael Pickering和Emily Keightley(2006:919)在《怀旧的模式》(The Modalities of Nostalgia)中指出,怀旧的意涵多种多样,“难以被化约成某个唯一或绝对的定义”。反怀旧也是如此。通过台湾流行音乐这一案例,本文重点分析了两种迥异的反怀旧模式。虽然它们都遵循了进步话语的线性时间观念,认为历史在不断进步,新好于旧、未来可期、往事不必回首,但是,它们对于进步的定义、聚焦的时态和对反怀旧对象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尤其是将流行文化怀旧置于全球文化市场中来考察后,本文发现,今昔两地的时空对比使得反怀旧的意义阐释更加复杂多样。大陆年轻人不再怀念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可以是因为“弃旧”——批判过去音乐类型的过时和低劣——也可以源于“扬新”——认可台湾音乐在当下的新发展。这两种观点虽然有不相容之处,但都反映了“弃旧扬新”的进步话语。同时,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提醒我们关注反怀旧和“进步”概念的异质性:在引入空间维度后,文化商品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怀旧未必代表批判过去,进步话语也未必崇尚宏大叙事。
本文从反怀旧的意义建构出发,有别于以往关注反怀旧文本的研究路径,以访谈和焦点小组的方法探究个人如何通过反对大众化、媒介化的怀旧情感来理解社会变迁,并在时空对比中定位自我、他者与世界的关系。本文跳脱以往研究对(反)怀旧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而是引入全球文化市场的空间维度,将反怀旧的文化实践与社会经济背景相接合,通过类型学分析指出了当代反怀旧现象的复杂肌理与多元阐释模式。
本文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发现为理解当代(反)怀旧现象和怀旧工业提供了三点思路。其一是怀旧的商品化和媒介化。一方面,怀旧越来越成为有组织的经济行为,新旧媒体的推波助澜造就了一场场“怀旧媒介事件”;另一方面,怀旧对象展现出商品化特征,各类流行文化产品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可被怀旧的潜在对象,等待怀旧产业的发掘。对于反怀旧而言,媒体策划所导致的普遍怀旧、消费者的商品比较视角,以及对消费文化的反抗,都可能成为拒绝怀旧的理由。
其二是怀旧商品的全球化。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的转型,文化领域开始融入全球市场,针对文化商品的比较视野也由此跨越了区域界限,成为全球视角下的多维度时空对比。对(反)怀旧而言,这意味着(反)怀旧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本地文化产品,而是拓展到区域之间的比较。这使得(反)怀旧的意义建构更加复杂。原本去政治化的娱乐商品,也可能在(反)怀旧的话语实践中被再政治化、卷入地缘政治的时空变迁中。
其三是(反)怀旧消费的解读,即(反)怀旧者的意义生产。面对成体制的怀旧工业,个人是怀旧的参与者和消费者,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成为怀旧的“受众”,半自愿半强迫地被裹挟到怀旧内容的内爆式生产中。前述的商品化和媒介化特征使怀旧成为难以回避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这侧面促成了反怀旧情绪的崛起。正因为怀旧现象变得如此普遍、如此重要,围绕怀旧的意义建构才越来越成为定义自我与他者的关键文化过程。无论是认可怀旧还是反怀旧,都是对怀旧话语的主动回应,也因此都被纳入了自我叙事的一部分,成为重要的个人和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杜赞奇(1997/2009)。《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黄俊铭(2024)。音乐、文艺机构与身份:中国的《人民音乐》(1950–2019)如何论述台湾流行音乐。《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台湾),36(2),1–42。
简妙如(2013)。台湾独立音乐的生产政治。《思想:音乐与社会》(台湾),24,101–121。
看理想(2019)。《高晓松X梁文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港台流行音乐》。检索于https://m.huxiu.com/article/280686.html?f=member_article。
宋惠昌(2010年7月19日)。党校教授谈“怀旧”情绪: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思潮。《北京日报》,检索于https://news.cntv.cn/china/20100719/101723.shtml.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2001/2010)。《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萧阿勤(2017)。记住钓鱼台:领土争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与怀旧的世代记忆。《台湾史研究》(台湾),24(3),141–208。
叶荫聪(2010)。《为当下怀旧: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硏究所。
赵刚(2014)。“小确幸”:台湾太阳花一代的政治认同。《文化纵横》,(6),46–52。
Ang, I. (1982). Watching Dallas: Sope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Baranovitch, N. (2003). China’s new voices: Popular music, ethnicity, gender, and politics, 1978–199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nnett, A. (2010). Left in the Past: Radic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Brown, S. D. & Reavey, P. (2013). Experience and memory. In E. Keightley and M. Pickering eds. Research Methods for Memory Studies (pp. 45–5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haney, D. (2002). Cultural Change and Everyday Life. Basingstoke: Palgrave.
Ching, L. T. S. (1994). Imaginings in the empires of the sun: Japanese mass culture in Asia. boundary 2, 21(1), 198-219.
Ching, L. T. S. (2000). Globalizing the regional, regionalizing the global: Mass culture and Asianism in the age of late capital. Public Culture, 12(1), 233–257.
Cuc, A., Ozuru, Y., Manier, D. & Hirst, W. (2006). On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role of a dominant narrator. Memory & Cognition, 34, 752–762.
Davis, F. (1979).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Free Press.
Koselleck, R. (2004).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in, C.-Y. (2021). From the center of Mandopop to indie music capital? The concep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hallenges for Taiwanese musicians. In N. Guy ed. Resounding Taiwan: Musical Reverberations Across a Vibrant Island (pp. 197–212). London: Routledge.
Lin, Y. and Chan, M.K.M. (2022). Linguistic constraint, social meaning, and multi-modal stylistic construction: Case studies from Mandarin pop songs. Language in Society, 51(4), 603–626.
Lowenthal, D. (198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wenthal, D. (1989). Nostalgia tells it like it wasn’t. In C. Shaw and M. Chase eds. The Imagined Past: History and Nostalgia (pp. 2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Lune, H. & Berg, B. L. (2017).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9th ed. Harlow: Pearson.
Fantin, E. (2014). Anti-nostalgia in Citroen’s Advertising Campaign. In K. Niemeyer ed. Media and Nostalgia Yearning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95–104). Basingstoke: Routledge.
Frankl, J. M. (2012). Distance as Anti-Nostalgia: Memory, Identity, and Rural Korea in Yi Sang’s “Ennui”.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7(1), 39–68.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 T. B. (1993). Go with your feelings: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907–925.
Gray, J. (2003). New audiences, new textualities: Anti-fans and non-f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1), 64–81.
Hegel, G. W. F. (1824/1956).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J. Sibree tran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Hennink, M., Hutter, I. & Bailey A. (2020).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Hesmondhalgh, D. (1999). Indie: The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a popular music genre. Cultural studies, 13(1), 34–61.
Ho, W.-C. (2006). A historical review of popular mus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4(1), 120–147.
Jennings, M.K. & Zhang, N. (2005). Generations, political statu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7(4), 1164–1189.
Jian, M. (2019). How Taiwanese indie music embraces the world: Global mandopop, East Asian DIY networks, and the translocal entrepreneurial promoters. In E. Tsai, T.-H. Ho, M. Jian eds. Made in Taiwan: Studies in Popular Music (pp. 213–228). New York: Routledge.
Kang, L. (2022). Metamorphosis of the dragon: The collectivist reconfiguration of Hong Kong-Taiwan pop in the reform er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3(2), 288–301.
Keightley, E. (2010). Remembering research: Memor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3(1), 55–70.
Kuhn, A. (2002). Everyday Magic: Cinema and Cultural Memory. London: I.B. Tauris.
Marinetti, F. T. (1909/1973). The founding and manifesto of futurism. In U. Apollonio ed. Documents of 20th Century Art: Futurist Manifestos (pp. 19–24). Brain, Robert, R.W. Flint, J.C. Higgitt, and Caroline Tisdall trans. New York: Viking Press.
Melhuish, F. (2022). Euroscepticism, Anti‐Nostalgic Nostalgia and the Past Perfect Post‐Brexit Future.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60(6), 1758–1776.
Moskowitz, M. L. (2009). Mandopop under siege: culturally bound criticisms of Taiwan’s pop music, Popular Music, 28(1), 69–83.
Moskowitz, M. L. (2010a). Introduction. In M. L. Moskowitz ed.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 Charismatic Modernity (pp. 1–22). Abingdon: Routledge.
Moskowitz, M. L. (2010b). 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 Chinese Pop Music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Niemeyer, K. (2014). Introduction: Media and Nostalgia. In K. Niemeyer ed. Media and Nostalgia Yearning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1–26). Basingstoke: Routledge.
Pickering, M. & Keightley, E. (2006). The modalities of nostalgia. Current sociology, 54(6), 919-941.
Pogacar, M. (2015). Music and memory: Yugoslav rock in social media. Southeastern Europe, 39(2), 215–236.
Sakai, N. (2019). The regime of separation and the performativity of area.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7(1), 241–279.
Schillewaert, N., Langerak, F. & Duharnel, T. (1998).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for WWW surveys: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40(4), 1–13.
Schuman, H. & Rodgers, W. L. (2004). Cohorts, chronology,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8(2), 217–254.
Shaw, C. & Chase, M. (eds.) (1989). The Imagined Past: History and Nostalg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mith, K. (2000). Mere nostalgia: Notes of a progressive paratheory. 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3(4), 505–527.
Tam, A. and Meek Lange, M. (2024). Progress. In E. N. Zalta and U. Nodelman ed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4 Edi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4/entries/progress/.
Wu, J. (2006). Nostalgia as content creativity: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popular senti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9(3), 359–368.
Zaritt, S. N. (2013). Ruins of the present: Yaakov Shabtai's anti-nostalgia. Prooftexts: A Journal of Jewish Literary History, 33(2), 251–273.
[作者简介]李岸东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讲师。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高水平人才队伍培育项目“百年变局背景下的媒介流行文化与中外青年历史意识研究”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