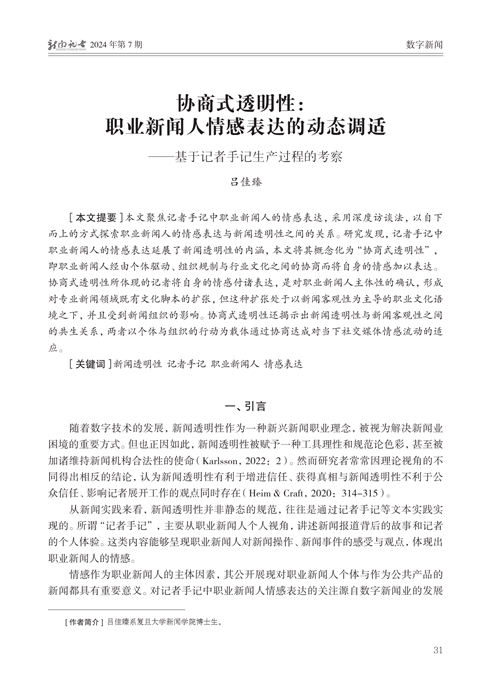协商式透明性: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动态调适
——基于记者手记生产过程的考察
吕佳臻
[本文提要]本文聚焦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采用深度访谈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探索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新闻透明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延展了新闻透明性的内涵,本文将其概念化为“协商式透明性”,即职业新闻人经由个体驱动、组织规制与行业文化之间的协商而将自身的情感加以表达。协商式透明性所体现的记者将自身的情感付诸表达,是对职业新闻人主体性的确认,形成对专业新闻领域既有文化脚本的扩张,但这种扩张处于以新闻客观性为主导的职业文化语境之下,并且受到新闻组织的影响。协商式透明性还揭示出新闻透明性与新闻客观性之间的共生关系,两者以个体与组织的行动为载体通过协商达成对当下社交媒体情感流动的适应。
[关键词]新闻透明性 记者手记 职业新闻人 情感表达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透明性作为一种新兴新闻职业理念,被视为解决新闻业困境的重要方式。但也正因如此,新闻透明性被赋予一种工具理性和规范论色彩,甚至被加诸维持新闻机构合法性的使命(Karlsson,2022:2)。然而研究者常常因理论视角的不同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新闻透明性有利于增进信任、获得真相与新闻透明性不利于公众信任、影响记者展开工作的观点同时存在(Heim & Craft,2020:314-315)。
从新闻实践来看,新闻透明性并非静态的规范,往往是通过记者手记等文本实践实现的。所谓“记者手记”,主要从职业新闻人个人视角,讲述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和记者的个人体验。这类内容能够呈现职业新闻人对新闻操作、新闻事件的感受与观点,体现出职业新闻人的情感。
情感作为职业新闻人的主体因素,其公开展现对职业新闻人个体与作为公共产品的新闻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关注源自数字新闻业的发展对传统新闻职业理念的冲击。有研究者关注记者手记体现出来的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并将其视为新闻透明性的一种展演形式(张洋,2023);研究者也认可新闻实践中新闻行动者情感表达的合理性,并试图将这些情感纳入衡量新闻报道的标准体系加以规制(常江,何仁亿,2022)。但是,新闻学界在考察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时,未能深入新闻编辑部内部,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关注职业新闻人的情感流动。故本文从实践的角度聚焦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并采用深度访谈法,探究影响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因素,进而审视既有的新闻透明性理念。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对话
(一)新闻透明性的理念与实践
1.新闻透明性的理念
美国新闻学者Kovach和Rosenstiel(2001:80)提出“透明原则”(Rule of Transparency),因针对专业媒体而又被广泛称为新闻透明性(journalistic transparency)(Vos & Craft,2016)。尽管两位研究者试图将透明性视为新闻工作者遵循客观性原则的一种方法,并且列举了这一方法在实践中该如何应用,但在后续的论述中他们逐步将透明性视为一种规范性原则,倡导新闻工作者遵循透明性原则(Kovach & Rosenstiel,2001:77-82)。因此,透明性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后便主要带着规范论的视角指导新闻实践。Plaisance(2007)进一步将新闻透明性纳入伦理学的学术脉络,认为透明性根植于康德提出的“人性原则”,意味着对他人的真诚和坦率,是一种道德义务并决定着道德行为的本质。
Karlsson作为新闻透明性的重要研究者,在研究早期提出“披露的透明性”(disclosure transparency)和“参与的透明性”(participatory transparency)(Karlsson,2010);之后从“披露的透明性”中区分出“环境透明性”(ambient transparency)(Karlsson,2020)。Heim和Craft(2020:309-312)进一步将新闻透明性最基本的内涵视为公开(openness),他们主要关注公开的内容,认为信息的获取(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信息的披露(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以及公众参与(participation)构成新闻透明性内涵的基本维度。这种理解新闻透明性的方式强调信息披露的程度与目标,甚至追问决策者的动机,却也意识到人的动机往往难以说清楚。Singer(2007)在文化规范意义上将新闻透明性与责任(accountability)联系起来,甚至将其等同于责任。他认为新闻透明性是指一种以公开为导向的责任延伸,对真相负责,并且涵盖行动前、行动中以及行动后的真实披露。这种对新闻透明性的界定强调新闻从业者对责任的承担,并且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内容负责。Wasserman将真实披露的内容分为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并认为应该披露结果而非过程,因为新闻过程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争论过程,甚至存在一定的冲突,需要空间和隐私(Heim & Craft,2020:315-316)。上述研究对新闻透明性的理解侧重关注信息披露的结果,虽然有研究者意识到新闻工作者的动机难以言说,但在界定新闻透明性时并未充分考虑这一点。事实上,正如Karlsson(2022:78+86)在其总结性著作《透明性与新闻业》(Transparency and Journalism)一书中对既有研究加以反思而指出的,将新闻透明性等同于公开(openness)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更诚实的做法是将其视为“对可见性的战略性管理”(strategically managed visibility)。这一观点卸下了加诸新闻透明性之上的规范性迷思,也启发我们跳出对新闻透明性结果的关注,进一步探索新闻透明性的展开过程。
回到中国语境,国内研究者对新闻透明性的论述也主要沿着规范性的视角展开,强调新闻机构主动披露新闻生产过程、将新闻生产的“元信息”告知公众(张超,2020),其“核心理念是‘后台披露’”(王斌,胡杨,2021)。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新闻透明性概念可能意味着新闻业理性与情感关系的重要转向(涂凌波,张天放,2022),关于“新闻透明性”的探讨亦被视为对以客观性为主导的传统新闻生产价值准则的一种回拨(赵立兵,2023)。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也关注到新闻透明性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差距(白红义,雷悦雯,2022),甚至对新闻透明性的实践根基存在疑虑(常江,杨惠涵,2023)。不过,有研究者针对职业新闻人公开展现自身的情感,提出“主体透明性”(张洋,2023)的概念,这有助于在经验研究层面进一步破除新闻业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些研究在理解新闻透明性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规范或理念,虽然有研究者关注到新闻透明性与职业新闻人情感之间的关系乃至新闻透明实践中新闻工作者个人的情感表达,但或者属于理论层面的探讨,或者将职业新闻人情感的呈现视为一种“展演”。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在使用新闻透明性这一概念时有意无意地对其加以界定,但这些界定没有充分注意到新闻透明性的实践语境,也没有进一步关注到新闻透明实践中影响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具体因素,整体上还是将新闻透明性视为一种规范或理念。基于此,有必要从实践出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与新闻透明性的概念对话,发现具体实践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对新闻透明性内涵的影响。
2.新闻透明性的实践
新闻透明性的实践是理解新闻透明性的落脚点,因为只有透过实践,才能捕捉影响新闻透明性的各种因素。当前研究者关注到的新闻透明实践包括在线显示事实性错误的更正、提供新闻报道中引用文件的链接、提供记者的联系方式、呈现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等做法,但认为这些举措以一种有限的、易实现的方式展现透明,使得作为规范的处于想象层面的新闻透明性与日常新闻生产执行的新闻透明性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Chadha & Koliska,2015)。Mor和Reich(2018)考察了一个鼓励记者上传新闻背后的文件的在线平台,通过分析这些文件,发现这一新闻透明实践允许受众直接接触原始材料并对信息做出独立判断。随着播客的兴起,Perdomo和Rodrigues-Rouleau(2021)认为,播客通过揭示新闻过程、建构记者角色形象、重申新闻文化,展示了一种“自我庆祝的透明性”(self-celebratory transparency)。Haapanen(2022)聚焦的是解释新闻从业者重要决策的编辑文本(editorial texts),如扩展性采访(extended interviews)、解释新闻生产决策的推特等,他指出应该注意编辑文本的语言使用,充分理解语言使用与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的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提醒我们将类似文本置于其生成的具体语境中,而不是就文本谈文本。
中国专业媒体的新闻透明实践可以追溯至以记者手记为代表的专业媒体对其后台操作的呈现(张洋,2023),这些内容在传统媒体时代常常通过报纸、图书等方式获得传播。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报道的幕后呈现获得了更多的表达空间,拓展到视频、音频等方式。有研究者关注到中国记者在使用视频博客(Vlog)和视频日记(video diary)过程中对其工作情况的披露,并指出这些叙事形式拓展了新闻透明性的实践空间(Meng & Wang ,2023),也呈现出记者的情感及其对自身的反思(Meng & Zhang Ivy,2022)。
针对记者手记呈现出的新闻从业者对自身决定和行动的阐释,可以结合元新闻话语相关理论进行分析。Carlson(2016)将新闻业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并将其置于一个话语领域中,这个话语领域持续地建构新闻业及其社会位置的意义。他用“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描述这一领域,将其定义为:“对新闻文本及其生产实践或接收条件之评价的公开表达。”Carlson强调这类话语的产生并非只局限于新闻业内部,而是由新闻业内部和外部的行动者竞相构建。这种区分新闻业内部和外部的视角来自Carlson对新闻职业的文化权威的关注,并着重考虑社会认可对建立新闻权威的必要性,这实际上为“元新闻话语”赋予了一种权力视角(Carlson,2017:5-6+90-93)。如果我们跳出权力视角,便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关于新闻业的讨论要被赋予“‘元’新闻话语”的地位,这种所谓“元”话语来自何处?事实上,这种赋予新闻话语“元”地位的分析方式预设了这类话语与新闻职业的文化权威之间的关系,而容易忽略行动者在表达这类“元”话语时,其具体目的是什么?其中的情感表达承载哪些用意?与读者有何关联?回答这些问题需深入“元新闻话语”的生产情境中。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启发,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从静态的视角看,文字、视频、音频等不同形式呈现出来的记者手记是一种元新闻话语或文本类型;但从其动态生成的视角看,这些内容还是一种实践。这里对“实践”的理解承接在以夏兹金为代表的实践理论之中,夏兹金等将理解实践的重点放在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实践中的主客观元素通过相互协调使得行动者之间达成对相应实践运行规范的“共识”,最终使该类实践的运行模式得以形成(顾洁,2018)。本文将记者手记视为一种实践,在具体的新闻生产语境中考察记者手记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发现实践对新闻透明性内涵的影响,另一方面弥补仅从文本或话语层面考察这类内容的不足。
(二)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情感在新闻生产与消费中的重要性获得广泛认可,形成了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Wahl-Jorgensen,2020;常江,田浩,2021)。在新闻生产研究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能否公开表达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基本面向,相关观点经历了从否定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在新闻报道中的呈现(Schudson,2001),到承认职业新闻人对新闻人物的情感共鸣并认可情感化的报道风格(Schmidt,2021),再到倡导将情感化、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普遍化(常江,王雅韵,2023)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在认识论层面,研究者借助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审视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客观性原则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现象学对体验的强调唤醒了研究者对职业新闻人情感的关注,情感意味着身体在场,构筑起超越理性的生活世界(赵立兵,2023);二是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关注情感性(emotionality)如何通过惯例、行业会议获得新闻业的认可,并将情感性视为专业新闻的组成部分(Schmidt,2021);三是倡导调适新闻生产者的社会角色,认为新闻生产者不仅提供外部信息,而且倡导一定的理想、价值与情感(赵立兵,2023;Steinke & Belair-Gagnon,2020),甚至需要承担公民的情感教育(袁光锋,2017)。
就围绕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具体研究而言,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新闻文本出发,将文本中的情感视为中介性情感(mediated emotion)(凯伦·沃尔-乔根森,田浩,2021),考察职业新闻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如何使用和呈现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的情感(Steinke & Belair-Gagnon,2020),进而引导受众(陈阳,周子杰,2022),甚至引发用户的情感参与(陈阳等,2023),但将职业新闻人自身的情感排除在新闻文本之外(Wahl-Jorgensen,2013);二是将职业新闻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付出的情感视为一种情感劳动,这些情感劳动是新闻工作的展开所必不可少的(Glück,2016),但因与客观性相悖而常常处于无法谈论的境地(Richards & Rees,2011);三是关注职业新闻人对新闻职业的感受,包括职业新闻人对新闻业的情怀(柳旭东,张瑞瑶,2019)、由于新闻业的不稳定特征而产生的情感压力(Ekdale et al.,2015)。这三类研究的特点是将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局限于新闻业的范围内,从新闻业的视角出发看待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将其视为在公共空间中流动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情感。
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在公共空间中的流动,即是说,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不仅面向新闻业内部,而且面向整个社会空间。这种站在新闻业外部看待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视角,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新闻生产的语境发生了由职业性转向社会性、从封闭性转向开放性的根本性转变(杨保军,2020;姜华,张涛甫,2021;Moran & Usher,2021)。因此,本文将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置于广阔的数字空间中,与此同时,跳出新闻文本,透过记者手记的实践,探察职业新闻人情感的表达与展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深入构建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新闻透明性乃至新闻客观性之间的关系。
以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作为切入点,需要厘清的一个前提问题是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的关系。情感体验是人们内心感受到的情感,情感表达是指人们以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不同方式所表达的情感(孙一萍,2018),既有研究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主要呈现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存在不一致,表达出来的情感的真实性存疑;第二种观点认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并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因为情感体验本身就是被塑造的结果,追问情感的真伪没有意义(孙一萍,2018)。Scheer(2012)采用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将情感从体验与表达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认为作为实践的情感(emotion as practice)依赖以具体的言语(sayings)和行动(doings)表现出来的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s),并与这些言语和行动交织在一起。这种对情感的理解强调情感本身作为实践,是社会背景下身体参与的行动,并且可以从动员(mobilizing)、命名(naming)、交流(communicating)和管理(regulating)等具体的情感实践中加以捕捉和理解(Scheer,2012)。此时,无论是对情感本身的理解,还是对情感实践的理解,都离不开对身体的关注,一方面情感本身并不是简单地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身体执行的受惯习塑造的行动(Scheer,2012);另一方面情感实践亦体现为生物意义上的身体所执行的言语与行动。基于此,本文认可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情感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达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特别是情感表达作为Scheer(2012)所认为的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s)的一种具体表现,可以使研究者进一步聚焦情感表达的展开过程与展开方式,而不是情感表达的结果。正如Eustace所指出的,作为研究者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个体内心的真实感情,但是研究者能够通过解读情感表达的方式来揭示个体所处的组织与社会的相关信息(Eustace et al.,2012)。
就本文所关注的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而言,其关键在于情感的可言说性,而且由于职业新闻人所表达的情感指向的是具有公共属性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尽管这些情感来自个人,但当这些情感在公共空间中被言说、被了解时,就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本文透过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进一步探索这些情感的呈现与职业新闻人所处的组织、行业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1.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的呈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2.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如何影响新闻透明性的内涵?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材料来自一项针对专业媒体新闻透明实践的田野考察。为了深入新闻生产情境,研究者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间以实习生身份分段深入专业媒体S中展开研究。在此期间,研究者采用以深度访谈为主,以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为辅的方式展开研究。依照目的性抽样和机遇式抽样的原则,研究者对30位职业新闻人进行了访谈。访谈时间约为0.5~3.5小时不等;访谈形式包括面对面、语音通话、书面访谈以及极个别的微信即时通讯聊天。面对面访谈和语音访谈在征求访谈对象同意后全程录音,未获得访谈对象同意录音的情况则在访谈后的第一时间记录访谈对象的描述和观点。基于研究伦理中的保密原则,本文隐去了所有研究对象的身份信息并以编码代替,对相关新闻报道作了模糊化处理。
展开深度访谈时,研究者并非带着“新闻透明实践”的“预设”去了解具体的新闻实践,而是通过开放性访谈,“发现”具有新闻透明特征的实践。因此,访谈问题经历了前期从开放到半开放的过渡,在后期则以半开放半结构的形式展开。开放式访谈一般着眼于受访者的个人情况、日常工作情况、对本研究的看法等方面的内容;半开放式访谈主要是围绕受访者撰写或制作的相关记者手记等内容进行提问,涉及采访过程、写作或制作缘起、写作或制作过程、编辑过程等,尤其关注受访者对自身情感体验与观点的讲述,并且与相应公开发布的内容形成参照。对于田野考察期间形成的观察笔记与访谈记录等原始资料,研究者使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进行编码分析。
具体到本文使用的案例,则是专业媒体S发布的文字形式的记者手记和记者讲述新闻背后故事的短视频、播客。这些案例分别以文字、短视频、音频的方式记录了专业媒体重大报道背后职业新闻人的情感流动和所思所想,使职业领域的情感进入公共领域。
四、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动态调适
什么是记者手记?这一概念对职业新闻人来说如同常识一般,笔者编码并提取受访者的相关描述发现,记者手记的内容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向信息,即记者在做报道过程中的“见闻”、“素材”,是新闻报道里不会或者不方便呈现的,对新闻报道起到了解释、说明、补充的作用,甚至提供了“非常一手和独家的信息,是之前媒体都没有披露过的”(11号);另一个方面是感受,“就是讲我体表的感觉”(10号),是记者在做报道过程中的“情感”、“冲击”、“困惑”、“感触”。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不能通过新闻报道本身加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记者手记可以被视为一种新闻透明实践,分别从信息与情感两个层面呈现职业新闻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见闻与感受。
根据文献回顾部分对情感的阐释,即,跳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的二元对立,通过建立在言语与行动基础上的情感实践来捕捉和理解情感,记者手记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作为情感表达的体现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探索职业新闻人的情感。本文透过相应的记者手记文本与对职业新闻人的深度访谈发现,职业新闻人的情感与他们对自身情感的记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其中涉及职业新闻人调适自身情感的方式、作为组织的专业媒体的发展目标与规制、新闻业整体的行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
(一)情感表达的内在驱动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消息来源作为连接职业新闻人个人与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桥梁是激发职业新闻人情感的关键因素,是否对这些情感在记者手记中加以表达以及如何表达与新闻从业者调适自身情感的不同方式有关。研究发现,职业新闻人协调自身情感的方式大体可归为两种。
第一种是接纳情感。职业新闻人将自己跟消息来源的接触作为事实的一部分,进而将自己在接近新闻事实的过程中产生的感受通过记者手记加以表达。例如,11号受访者带着善意面对身处人生困境中的消息来源,其作为中间人在观察消息来源生活境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介入对方的生活,由此产生的连接使其思考自己与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并促使其付诸表达。“我跟他(指采访对象,笔者注)接触的这个过程,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的一部分。比如,他第一次不告诉我,或者说要透过我去传递一些话,这不就是他正身处的一种很尴尬的现实;他第二次又是一个更可能不同的说辞。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会有更多的话想说的一种心情”。透过受访者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采访对象的处境,这种处境对于揭示新闻事件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也使记者形成了较强的情感表达的内在驱动。“虽然我内心觉得那个稿子(指新闻报道,笔者注)已经体现出了这个复杂性,但是我好像有一种还想再解释一下的那种心态,但这里面肯定就不合适用那种稿子去呈现,因为里面确实有一些东西是我个人主观的想法,包括有很多我跟他们接触下来的一些事情”。由此可看出,职业新闻人之所以借助记者手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想法,是因为新闻报道无法容纳记者个人主观的想法,也就无法呈现记者个人视角的感受,记者手记成为职业新闻人表达情感的一种选择。
不难看出,职业新闻人对自己与消息来源之间的情感有着明确的感知,并且通过记者手记这一专业媒体新闻生产可以接受的写作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观察。记者对自身情感的表达意味着将自己置于新闻人物的生活世界之中,并且携带着作为职业新闻人的情感;但这种情感是复杂的,其复杂性在于,记者是基于跟消息来源的接触而成为新闻事件所构筑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其中既有“以朋友的方式”与消息来源展开交流而获得采写素材后产生的“愧疚之心”,又有对身处困境中的新闻人物的善意乃至同情,还有作为职业新闻人与消息来源所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天然的冲突。当这些复杂心绪逐步走出职业新闻人的内心,由专业媒体公开发布时,本身就是对他们情感的接纳。此时,无论是职业新闻人个人,还是专业媒体,都认可他们情感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种是排除情感。职业新闻人将自身的情感与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分离开来,记者外在于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所构筑的生活世界,这种调适自身情感的方式影响着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有的职业新闻人从选题阶段开始便以一种疏离的态度面对新闻事件及消息来源,对其采取一种怀疑态度,同时有意识地与新闻人物保持距离,这使得相应的记者手记偏重对新闻人物相关信息的呈现,即使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在记者手记中有所呈现也主要服务于对新闻人物的描述。“我写我的心理活动也是为了阐述她(指采访对象,笔者注),帮助读者去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呈现情感的方式与职业新闻人的工作方式有关,“我自己做新闻比较抽离”,“我甚至尽量地不触碰跟我过去很有关系的选题,因为会不客观。……我就情愿去写一些没有什么感性认识的东西”。不难看出,上面的10号受访者对自身情感表现出很高的觉察,会有意识地区分自己的感受与消息来源的感受。这种对自身“感性认识”的排除,使得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程度相对较低。有的职业新闻人虽然在与消息来源的接触过程中经历了情感冲击,并在记者手记中有所呈现,但认为记者手记是个人化的感受,是不重要的信息,这本质上也是对情感的排除。“当时我采访她的时候,哪怕只能共情一部分,但是那一部分已经让我有点难以承受的感觉……我至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采访,很需要消耗那种情感能量”(6号)。尽管如此,受访者认为这些内容并不能为新闻事件提供更多的“增量”,因为重要的是新闻事件本身的信息。“我这个手记对于整个事情,没有提供什么增量,它其实也是一家之言。……在我看来,它是可有可无的”。
由此可以看出,这类受访者虽然在采访过程中对消息来源采取不同的情感态度,有的相对疏离,有的投入其中,但记者自身都是外在于新闻事实的。这种做法源自于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记者应该是藏在报道背后,应该站在角落里观察。这种观念影响着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程度。
上述两种职业新闻人协调自身情感的方式形成了对比,这两种方式在新闻界,甚至在同一家专业媒体中同时存在。这从侧面反映出职业新闻人所处的工作境遇,一方面新闻客观性的传统强调记者是新闻事件的客观记录者,另一方面职业新闻人的情感真实地存在于新闻工作中,而且这种情感的力量相当强大。这种冲突使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处于矛盾之中,这也正是Thoits所关注的个体的真实情感与“情感规则”的期望不一致的情形(特纳,斯戴兹,2005/2007:42)。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手记提供了职业新闻人表达情感的空间,使职业新闻人在矛盾的工作境遇中获得一定的“情感自由”(雷迪,2001/2020:171),使他们的情感得以在公共空间中流动。8号受访者点明了记者手记使职业新闻人的情感从不公开到公开的过程:“我把我自己所想的东西发出来了,我不写,不代表我没有。我有自己的想法,以前只是发在自己私人的领域,我在朋友圈里、在微博上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发。现在我是公开地发,它其实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只是把一部分抑制住了。就是你在写报道的时候,你要抑制那个‘你’,你的主观的评判,然后写手记的时候你把那个‘你’释放出来。”这个从抑制到释放的过程与职业新闻人的内在驱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建立在其个人对自身情感觉察的基础上,并且需要注意到这种情感对新闻报道产生的影响。只有职业新闻人个人接纳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才有可能在记者手记中有所表达。
(二)情感表达的组织约束
霍克希尔德(2012/2020:71-73)认为,包括组织在内的任何制度都可以充当导演的部分功能,不仅使行动者的情感表达符合制度所赞同的方式,而且制度会规制情感表达的前台布置,并引导观众看待事物的方式。研究发现,制度化的组织也会对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施加影响,进一步体现在与情感表达紧密相关的身体实践中。
在短视频和播客兴起的背景下,除了传统的文字呈现方式,记者手记的内容也会以短视频和播客的形式呈现。这些形式使职业新闻人的身体、声音等个人生物信息广泛地进入公众视野,也进一步影响着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根据笔者所做的深度访谈,以短视频和播客形式呈现的记者手记在专业媒体S内部所处的整体制作背景是专业媒体在已经完成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抖音、B站等平台媒体扩展影响力。“App太多了……所以一个新闻媒体,它可能不一定只自建平台。……它要在各个平台取得成功,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它的影响力、传播力、公信力和引导力。所以你只有自己的一个平台可能远远不够,对品牌的塑造可能也是远远不够的”(7号)。就短视频形式的记者手记而言,其拍摄想法源于“单位想孵化一批IP,鼓励我们自己去做一些号”(2号);播客也是如此:“领导鼓励大家每个部门都去搞搞新媒体项目,搞一些这种个人的IP,比如说你去开个抖音号。”(6号)由此可以看出,相关内容的制作来自专业媒体内部自上而下的号召,是专业媒体拓展影响力的一种尝试。
受访者将短视频形式的记者手记称之为“视频版的记者手记”。就本文考察的案例而言,视频版记者手记的具体内容依托的是此前已在专业媒体S的新闻客户端以及各大平台发布的暗访类调查报道,由从事相应调查报道的记者讲述采访过程。透过视频版记者手记的制作过程,可以进一步发现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组织印记。
视频版记者手记的制作始于平台账号的创建,根据笔者的访谈,账号的创建有着一定的考虑,特别是要开发不带机构属性的个人化账号。在开发账号的过程中,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些自媒体账号作为参考样本。之所以采用个人化账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内容审核受到过多限制,另一方面是避免与专业媒体自身的“品牌调性”相冲突。专业媒体创建自媒体化账号的做法一方面为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身体实践提供了平台基础,另一方面使职业新闻人有机会突破常规的新闻生产,去制作另类内容。
在具体内容方面,视频版记者手记首先是在披露与隐藏的矛盾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制作角度看,“当时我们会构思怎么样让他(指记者,笔者注)把所谓暗访背后的有趣的点,或者是一些大家平常不知道的点,披露出来”(5号);因为此前的报道是暗访,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把脸遮掉,把声音变掉”。由此可以看出,视频版记者手记使暗访过程中更多的细节获得了呈现机会,作为一种“后台的呈现”带来了一定的“信息增量”(4号)。其次,视频版记者手记在社交媒体与专业媒体的不同风格之间寻求差异。短视频“更偏‘社媒’一点”,“通过加进去一些特效,一些花字,或者记者本身特色的一些口播、slogan之类,想让它更有记忆点,更方便网络传播”(5号),从而使短视频更契合社交媒体的属性,以“区别于本身做的那个暗访”。整体来看,职业新闻人在视频版记者手记中呈现出来的情感表达是一种幽默的风格。最后,视频版记者手记会考虑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所涉及的法律界限,避免牵涉其中。“涉及公众利益的话,我都站在公众一边……相对来说,它(指暗访报道的内容,笔者注)的法律的界限很清晰”(2号)。塔奇曼(1978/2008:94+104+108)指出,新闻报道需要构建一张互相证实的新闻事实网,这张新闻事实网中没有记者的声音,以避免专业媒体陷入纷争。同样地,对于可以容纳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记者手记,专业媒体也需要避免“卷入事端”。因此,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是经过一定平衡之后的结果,这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风险控制,不止由作为个体的职业新闻人来把控,而且体现在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流程之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暗访是新闻从业者为了公共利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隐藏身份进行采访的一种方式(牛静,2021:81),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为了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新闻机构会尽可能不透露记者的个人信息。视频版记者手记则是让记者走进公共领域,出现在读者的注视下,其中的风险固然可以采用遮脸、变声等方式加以排除,但也可能会因整体形象的出现而使人产生一定联想。因此,暗访与视频版记者手记之间的张力仍然存在,职业新闻人表达出来的担心便是这种张力的体现。“相对来说,我肯定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很多知道我的人都跑过来给我发消息,你怎么还拍这种(东西),有的人就夸我,赞美嘛,但对我来说,压力肯定是大于赞美的”(3号)。职业新闻人的压力主要出于对身份暴露的担心,这种担心胜过来自外界的正向反馈,正如1号受访者所指出的“还是要保护他”。因此,在视频版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对身体的敏感性使得其在展开情感表达时相对谨慎。
由此可以看出,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身体实践受到制度化组织的多重影响。在整体上,相关情感表达与身体实践被纳入了组织的发展目标之中。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些情感表达又受到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的影响,既有突破组织局限的尝试,如创办具有个人色彩的账号,又有出于组织压力而产生的部分情感隐身,最终需要在内容制作的独特性与职业新闻人个人生物信息的保护之间做好平衡。
从根本上说,包括视频版记者手记在内的不同形式的记者手记因职业新闻人代表新闻组织行使采访权而得以生产,其中尽管呈现的是职业新闻人个人的情感表达,但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组织的印记。“他(指记者,笔者注)就算再怎么说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代表这个媒(体),虽然他也是‘个人’,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点代表媒体在说,这里面的分寸就很难说”(11号)。12号受访者在评价手记这类内容的撰写时说道:“我们这个东西,希望有鲜活的,但它一定还是代表单位的。”这句话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可以说是指出了所有涉及专业媒体新闻透明实践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新闻组织在推动记者手记的形成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不仅对职业新闻人情感的收放程度加以调适,而且需要在新闻组织的发展与职业新闻人个人的信息保护之间达成平衡。
(三)情感表达的职业伦理考量
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建立在职业新闻人对情感自我觉察的基础上,但情感表达的内容作为一种公共叙事由专业媒体公开、正式地加以发布,故职业新闻人在记者手记中展开情感表达时会从职业伦理的角度加以考量,使之符合新闻公共叙事的要求。
首先,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或主动、或被动地受限于新闻业对客观性的强调。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主导的专业理念要求记者不得表达个人想法(曾庆香,2005:209),以免产生倾向性或刻板成见。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记者手记中,“这一块(指记者手记的写作,笔者注)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要求平衡的,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这种倾向性、观点太过于(明显),除非界定性很明确”(2号)。总体而言,作为主导理念的新闻客观性使新闻业在整体上形成了排除职业新闻人情感的行业文化。正如13号受访者所说:“大家可能认为媒体(人)没有什么情感的取向,他们有偏向的话,就说明他们有倾向,就不客观理性了。”因此,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不可避免地受到新闻客观性的职业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并不意味着记者一定会产生倾向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新闻客观性,展现出更具反思性的道德意涵。这是因为记者手记中的情感表达来自记者对自身情感的觉察,这种觉察非但不是让其肆意地表达个人主张,反而有助于其保持反思的态度。“他(采访对象,笔者注)虽然是一个公众人物,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被监督,或者说他也让渡自己的一部分隐私。但是他又是一个事件的受害者,又是一个普通人。如果真的把很多审视的目光,或者说把他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又不是很合适。我觉得这个度特别难把握”(11号)。在撰写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受访者做了很多平衡,但仍想进行解释。“我可能觉得这种善意还不够,我还要再跟大家通过我自己的方式解释一下,可能我自己心里有这个愿望”。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受访者的部分情感表达源自对新闻工作的回顾与审视并且在相应的记者手记中书写自己心中的困惑。这类情感表达反映出的不是记者的倾向性,而是记者对自己作为人的情感的感知与反身性思考,体现出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此时的新闻透明性非但不是Karlsson(2010)所说的“透明性仪式”,反而形成了超越新闻客观性的驱动力量。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职业新闻人在撰写新闻报道时已经考虑到了对消息来源隐私的保护。Walt Harrington指出,经典新闻学认为记者须将读者置于首位,而不是他所报道的对象和他所为之写作的对象,但是当报道普通人的个人生活时,他认为“记者必须采取一种混合的道德观”,即“尽其所能保护他们的身体、社会和心理福利,尊重他们的尊严和隐私”(Coward,2013:150)。事实上,除了新闻报道,在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同样出于对消息来源隐私的保护而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有所保留。正如6号受访者所认为的:“哪怕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也不是说一个公共事件里面的人物所有的信息都要被大家知道。”(6号)由此可见,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需要谨慎对待消息来源相关内容的呈现。
最后,新闻职业伦理塑造的专业媒体作为合法的新闻报道者的身份使职业新闻人在制作或发布记者手记时会平衡个人叙事与公共叙事之间的关系。Carlson(2017:30+49)指出,专业主义既是影响记者行为的一种约束力量,也塑造着新闻业的合法性。新闻职业伦理是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下的新闻叙事以陈述的口吻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在缺少第一人称的情况下,新闻报道似乎是无可指摘的(Carlson,2017:36+58),专业媒体的权威性不言自明;而记者手记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除了指向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还指向职业新闻人自身,这种“卷入人物”的叙事使文本的情节携带一定的主观性,进而增加了人的意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赵毅衡,2013:11),这影响着“文本权威”(textual authority)(Carlson,2017:50),也影响着专业媒体的权威性。9号受访者指出:“以这种个人视角发东西的时候,它会给人一种不权威(的感觉)。……肯定是在以你专业媒体S记者的身份有一个很详实的调查之后,再发这篇稿子(指一篇记者手记,笔者注)”, “这些内容,作为补充信息可以,它只能作为配菜,肯定不是主菜,不是硬菜”。由此可以看出,新闻报道与记者手记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新闻叙事,它们所包含的新闻生产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前者因超然的叙事方式而成为权威叙事,后者因个人视角的出现会弱化文本的权威性。因此,记者手记的叙事方式影响着其文本地位,即一般作为辅助性文本出现。但不容否认的是,记者手记作为在专业媒体上正式发布的文本仍是面向公众的新闻产品,属于公共叙事。因此,它的文本仍是“一个有故事结构的稿子”,而不是把整个采访过程和写作过程都“一五一十地”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记者手记的叙事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职业新闻人个人的情感表达,也是对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一种记录,这决定了这类内容的制作需要平衡个人叙事与公共叙事。正如8号受访者所说,记者手记中的“那个‘我’,他不是自说自话,他不是说,‘我’那天,‘我’自己在想什么……他只是说‘我’那天在场,‘我’看到了什么,以及‘我’做了什么,对方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馈,其实记者也不是主角,只是把记者袒露在了读者面前”。因此,记者手记虽然是以职业新闻人的个人视角展开叙事,但其文本重心并不完全是职业新闻人个人的心绪,而是具有双重属性,即透过“我”去理解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这也反映出Carlson(2017:77)所区分的“新闻叙事”(narratives of journalism)与“关于新闻的叙事”(narratives about journalism)在新闻实践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混杂的。
五、总结与讨论:协商式透明性
与此前的研究相比,本文延续新闻学界对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关注,但将视角转向记者手记的生产过程,通过深度访谈和编码分析提炼出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个体、组织、行业三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作为新闻透明实践的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个体的内在驱动紧密相关,并且在情感的调动与收放程度方面受到组织的影响,与此同时,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需要考虑既有的新闻专业理念与职业伦理。由此而生成的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是不同方面的因素协商的结果,这一经验发现延展了新闻透明性的内涵,本文将其概念化为“协商式透明性”。协商式透明性是指,职业新闻人经由个体驱动、组织规制与行业文化之间的协商而将自身的情感加以表达。通过将情感社会学中的拟剧理论与情感文化理论相结合,可以进一步理解在专业化的新闻生产中,不同层面的因素之间如何协商进而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
在行业层面,以新闻客观性为主导的职业文化会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程度。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把社会互动看作戏剧,社会互动在文化所创造的“脚本”的指导下展开,行动者能够觉察到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对自身的影响并据此指导行动(特纳,斯戴兹,2005/2007:22-24)。作为新闻业主导理念的新闻客观性使得职业新闻人在整体上处于情感遮蔽的职业文化语境之中,个体的真实情感与“情感规则”的期望并不一致,这使得他们的情感处于新闻生产的后台且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尽管记者手记提供了接纳职业新闻人情感的空间,但其中的情感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闻客观性的职业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新闻专业理念塑造的专业媒体的权威形象反过来进一步淹没了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但是在记者手记的情感表达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职业新闻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戈登区分了看待情感文化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情感的组织(institutional)意义,强调个体在情感表达时以组织情感规则而行动;另一种是情感的冲动(impulsive)意义,强调游离于组织规则和惯例之外的自发的情感表达。这两种对情感表达的理解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说“同样一种情感可以携带不同的意义”(特纳,斯戴兹,2005/2007:27-28)。戈登对情感文化的认识使我们关注到,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或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组织的期待,是对组织规则的遵守;但与此同时,部分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也融入了自发的情感流露,甚至会在书写过程中注入内心深处的情感,这使得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展现出行动者内在自我的一面。因此,将拟剧理论与情感文化理论加以结合,能够使我们在关注到社会文化规范与组织规制的同时,避免对行动者能动性的忽视,进而让我们在理论层面理解个体驱动与组织规制以及行业文化之间的协商。
总的来看,协商式透明性首先是对职业新闻人主体因素的确认,意味着将职业新闻人视为情感与理性兼具的能动者。当前对既有新闻理念的哲学反思与对数字新闻情感转向的关注都反映出研究者对人类如何存在的体察,其中,职业新闻人像其他公民一样,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其次才是被赋予社会身份的记者、编辑(赵立兵,2023)。意识到并承认职业新闻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理所当然地为其戴上理性的“面具”,是协商式透明性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协商式透明性并非一味强调主体的作用,而是将其置于记者手记的生产实践中,看到职业新闻人的主体性如何与组织规制、行业文化进行协商。这一点回应了Karlsson(2022:78+85-86)指出的将新闻透明性视为“对可见性的战略性管理”(strategically managed visibility),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公开”。因此,协商式透明性意味着,职业新闻人将自身的情感付诸表达并对这种情感表达持有一定的道德自觉,形成了对专业新闻领域既有“文化脚本”的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是隐性的,处于以新闻客观性为主导的职业文化语境之下,并且受到新闻组织的影响。
协商式透明性所揭示的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受到新闻客观性的行业文化的影响,也表明了新闻透明性与新闻客观性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近年来,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短视频等的兴起拓展了记者手记这一类内容的叙事空间,也激发出职业新闻人相较以往更加多样化的情感表达,打破了新闻客观性的神话(张洋,2023)。但与此同时,经由代际传承的以新闻客观性为主导的专业理念仍是专业媒体及其新闻从业者的重要考量,即使是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的表达,也需要在新闻客观性面前加以动态调适,尽管这些考量中还夹杂着专业媒体自身的发展目标与对纷争的规避。因此,协商式透明性揭示出新闻透明性与新闻客观性之间的共生关系,两者以个体与组织的行动为载体通过协商达成对当下社交媒体情感流动的适应。
随着新闻透明性话语地位的凸显,中国新闻学界开始进一步关注新闻透明性。本文为中国专业媒体的新闻透明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即以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作为切入点,基于具体的实践,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深化对新闻透明性的理解,同时,也弥补了当前对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研究的不足。本土化的经验材料阐明了协商式透明性何以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新闻客观性与新闻透明性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过,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本文对记者手记的考察是基于相关案例的探索,由于不同专业媒体的资源禀赋不同,自身的新闻业务文化也不同,故未来需要在更多类型的专业媒体中展开研究。其二,数字技术时代专业媒体的发展处于瞬息万变之中,其创新实践更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故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反映了专业媒体在当时的实践情况,更长时间的纵向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协商过程的动态发展。■
参考文献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2012/2020)。《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白红义,雷悦雯(2022)。作为策略性仪式的新闻透明性:一种新职业规范的兴起、实践与争议。《全球传媒学刊》,(1),129-145。
常江,何仁亿(2022)。《物质·情感·网络:数字新闻业的流程再造》。《中国编辑》,(4),29-35。
常江,田浩(2021)。《论数字时代新闻学体系的“三大转向”》。《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44-50。
常江,王雅韵(2023)。《作为故事的新闻:观念、实践与数字化》。《新闻大学》,(1),16-27+118-119。
常江,杨惠涵(2023)。《告别客观性:介入性与数字新闻专业性》。《全球传媒学刊》,(1),148-159。
陈阳,李宛真,张喆喆(2023)。《数字新闻消费与人机关系——一项关于阅读机器人新闻的在线实验》。《新闻记者》,(8),40-50+85。
陈阳,周子杰(2022)。《从群众到“情感群众”:主流媒体受众观转型如何影响新闻生产——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为例》。《新闻与写作》,(7),88-97。
盖伊·塔奇曼(1978/2008)。《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顾洁(2018)。《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6),13-32+126。
姜华,张涛甫(2021)。《传播结构变动中的新闻业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8),185-203+208。
凯伦·沃尔-乔根森,田浩(2021)。《数字新闻学的情感转向:迈向新的研究议程》。《新闻界》,(7),25-32。
柳旭东,张瑞瑶(2019)。《解构新闻情怀:新闻从业者利他主义、社会价值感知与组织承诺研究》。《新闻记者》,(10),41-54。
牛静(2021)。《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理论及案例评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2005/2007)。《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孙一萍(2018)。《情感表达: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史学月刊》,(4),20-24。
涂凌波,张天放(2022)。《数字时代如何理解新闻透明性?》。《全球传媒学刊》,(1),146-162。
王斌,胡杨(2021)。《新闻透明性的理念、内涵与限度——对社交时代媒体转型路径的一种考察》。《江淮论坛》,(2),161-166。
威廉·雷迪(2001/2020)。《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保军(2020)。《理论视野中当代中国新闻学的重大问题》。《国际新闻界》,(10),18-30。
袁光锋(2017)。《情感何以亲近新闻业:情感与新闻客观性关系新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57-63+69。
曾庆香(2005)。《新闻叙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张超(2020)。《“后台”前置:新闻透明性的兴起、争议及其“适度”标准》。《国际新闻界》,(8),88-109。
张洋(2023)。《展演透明性:作为副文本的记者手记》。《新闻记者》,(4),14-25。
赵立兵(2023)。《“情”从何起:数字新闻“情感转向”的现象学反思》。《新闻界》,(7),31-43。
赵毅衡(2013)。《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Carlson, 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Carlson, M. (2017).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dhaK.& KoliskaM. (2015). Newsroom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ism Practice, 9(2):215-229.
CowardR. (2013). Speaking personally: the rise of subjective and confessional journ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EkdaleB. TullyM. HarmsenS.& Singer, J.B. (2015). Newswork within a culture of job insecurity. Journalism Practice, 9(3)383-398.
Eustace, N. Lean, E. Livingston, J. PlamperJ. ReddyW.M.& RosenweinB.H. (2012).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5)1487-1531.
GlückA. (2016). What maks a good journalist? Empathy as a central resource in journalistic work practice. Journalism Studies17(7)893-903.
HaapanenL. (2022). Problematising the restoration of trust through transparency: focusing on quoting. Journalism, 23(4)875-891.
HeimK.& CraftS. (2020). Transparency in journalism:meaningsmerits, and risks In Wilkins L.& Christians C.G.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ss media ethics (2nd) (pp.308-320). New York: Routledge.
KarlssonM. (2010).Rituals of transparency:evaluating online news outlets’ uses of transparency ri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Sweden. Journalism Studies11 (4)535–545.
KarlssonM. (2020). Dispersing the opacity of transparency in journalism on the appeal of different forms of transparency to the general public. Journalism Studies21(13)1795-1814.
KarlssonM. (2022).Transparency and journalism. London: Routledge.
KovachB.& Rosenstiel, T. (2001).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1st).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Meng J.& Wang H. (2023).Performing transparency in vlog news:self-disclosure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n vlog reporting on COVID-19. Journalism Practice, 2169189.
Meng J.& Zhang S. I. (2022).Conteste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journalists’ discourses in a time of crisis. Journalism Studies23(15)1962-1976.
Mor, N.& ReichZ. (2018). From “Trust Me” to “Show Me”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12(9)1091-1108.
Moran, R.E.& UsherN. (2021).Objects of journalism, revised: rethinking materiality in journalism studies through emotionculture and “unexpected objects”. Journalism, 22(5)1155-1172.
Perdomo, G.& Rodrigues-Rouleau, P. (2021).Transparency as metajournalistic performance: The New York Times' Caliphate podcast and new ways to claim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1-17.
Plaisance, L.P. (2007).Transparency: an assessment of the Kantian roots of a key element in media ethics practic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2(2-3)187-207.
RichardsB.& Rees, G. (2011). The management of emotion in British journalism. MediaCulture & Society33(6)851-867.
ScheerM. (2012).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and is that what makes them have a history)? A Bourdieui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emotion. History and Theory, 51 (2)193-220.
Schmidt, T.R. (2021). It's OK to feel: the emotionality norm and its evolution in U.S. print journalism. Journalism, 22(5)1173-1189.
SchudsonM. (2001).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2149-70.
SingerJ.B. (2007).Contested autonomy: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claims on journalistic norms. Journalism Studies8(1). 79-95.
Steinke, A.J.& Belair-GagnonV. (2020).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constructing emotion and emotional labor in social justice news. Mass Comunicaiton and Society23(5)608-627.
Vos, T.P.& CraftS. (2016).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tic transparency. Journalism Studies1-18.
Wahl-Jorgensen, K. (2013).The 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articles. Journalism, 14(1)129-145.
Wahl-Jorgensen, K. (2020).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 Digital Journalism, 8(2)175-194.
[作者简介]吕佳臻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