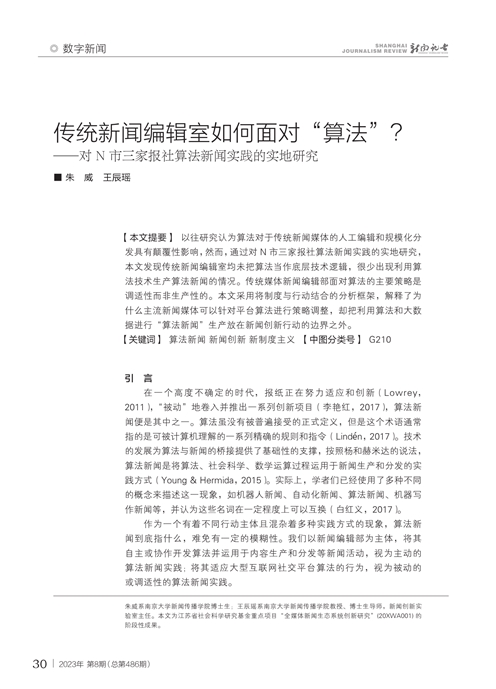传统新闻编辑室如何面对“算法”?
——对N市三家报社算法新闻实践的实地研究
■朱威 王辰瑶
【本文提要】以往研究认为算法对于传统新闻媒体的人工编辑和规模化分发具有颠覆性影响,然而,通过对N市三家报社算法新闻实践的实地研究,本文发现传统新闻编辑室均未把算法当作底层技术逻辑,很少出现利用算法技术生产算法新闻的情况。传统媒体新闻编辑部面对算法的主要策略是调适性而非生产性的。本文采用将制度与行动结合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为什么主流新闻媒体可以针对平台算法进行策略调整,却把利用算法和大数据进行“算法新闻”生产放在新闻创新行动的边界之外。
【关键词】算法新闻 新闻创新 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0
引言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报纸正在努力适应和创新(Lowrey, 2011),“被动”地卷入并推出一系列创新项目(李艳红,2017),算法新闻便是其中之一。算法虽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正式定义,但是这个术语通常指的是可被计算机理解的一系列精确的规则和指令(Lindén, 2017)。技术的发展为算法与新闻的桥接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按照杨和赫米达的说法,算法新闻是将算法、社会科学、数学运算过程运用于新闻生产和分发的实践方式(Young & Hermida, 2015)。实际上,学者们已经使用了多种不同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如机器人新闻、自动化新闻、算法新闻、机器写作新闻等,并认为这些名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白红义,2017)。
作为一个有着不同行动主体且混杂着多种实践方式的现象,算法新闻到底指什么,难免有一定的模糊性。我们以新闻编辑部为主体,将其自主或协作开发算法并运用于内容生产和分发等新闻活动,视为主动的算法新闻实践;将其适应大型互联网社交平台算法的行为,视为被动的或调适性的算法新闻实践。
新闻编辑部主动的算法新闻实践可分为自动化新闻、基于受众分析的算法推荐和分发(Jamil, 2020),主要机制是自动化和过滤(方师师,2018)。自动化新闻是将数据转换为叙事文本的算法过程,除了最初的编程,新闻生产不再需要人工干预(Carlson, 2015)。自动化新闻的原理在于,通过利用数据库和自然语言生成技术,完成事件驱动的自动化叙事(Dorr, 2016;Caswell & Dorr, 2018)。自动化新闻需要记者重新定义他们的核心技能(Van Dalen, 2012),如加强对计算机思维的训练,更紧密地同工程师、程序员合作以开发不同的算法,能够批判性地审视算法决策系统等(Lindén, 2017)。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新闻业的核心任务是不可能由算法自动化完成的(Flew et al., 2012)。从长远来说,人工智能和算法只会增强记者的新闻实践(Young & Hermida, 2015),而不是取代他们(Hansen et al., 2017)。
在基于受众数据的算法推荐和分发方面,国外研究者发现,新闻编辑室中的决策越来越多地基于与受众相关的大量自动生成的数据(Napoli, 2014;Arsenault, 2017;Christin, 2020),这些数据通常由安装在网站服务器上的跟踪技术捕获。在美国,超过80%的在线出版机构都在使用实时分析程序如Chartbeat进行受众测量(Christin, 2017)。基于用户数据的算法新闻推荐技术,如新闻机构根据预定的原则自动构建和排序新闻项目的实践,也纳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Moller et al., 2018)。现有研究总结了基于人气的过滤(即向用户推荐受欢迎程度较高的新闻作品)、基于内容的过滤(即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新闻作品、可与用户以前接触过的内容进行关联推荐)、协同过滤(即通过其他用户的行为来预测用户的口味),以及混合方法(上述方法的混合应用)这四种算法新闻推荐的方法(如Bozdag, 2013;Devito, 2016;Jannach et al., 2010)。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算法推荐与新闻机构传统规范之间的冲突,比如,北欧地区19家全国性报纸虽大都以某种形式使用了算法新闻推荐系统,但由于对公共新闻领域的担忧及不愿意转移编辑控制权,它们的使用范围仍然有限(Moller, 2022)。
国内学者研究更多的平台媒体算法,对于新闻机构来说实则是一种外部力量。研究者们考察了这类外部算法的推荐机制(王茜,2017;毛湛文,孙曌闻,2020)、对新闻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方师师,2016;王斌,李宛真,2018),以及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不同行动主体如何看待和阐释算法(白红义,李拓,2019)等。
从算法机制与新闻业的结合来看,主动的算法新闻实践对新闻编辑部的技术要求较高,而外部平台算法则日渐成为新闻业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环境因素。新闻业在这样的结构下如何采纳和面对算法,就构成了一个需要实际考察的问题。目前的文献中,对中国传统新闻媒体如何采纳和面对算法的经验研究还很缺乏。鉴于此,本文对我国某省会城市三家报社采纳算法新闻的实践过程进行了考察,试图厘清我国主流新闻媒体在新闻创新过程中使用算法技术的基本逻辑。
一、算法实践:制度环境下的新闻创新行动
算法技术是传统新闻媒体未曾经历的新事物,面对算法技术的行动,对于传统新闻媒体而言,无疑是一种新闻创新行动。但新闻媒体以何种方式进行新闻创新,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新技术能提供的可能性,还有新闻媒体组织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本文采用新闻创新研究中的组织路径(王辰瑶,2020),运用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制度环境”与“行动”关联起来考察我国主流新闻媒体的算法实践。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效率逻辑认为组织内部的正式结构,是组织追求效率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精神的现实反映。经典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也把新闻媒体之所以形成各种常规归结为对效率的追求。但在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开山之作《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中,作者迈耶和罗恩却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政策或者规章制度的采用并不完全出于效率的目的,而是为了追求合法性,从而获得对于组织生活至关重要的各种资源,增强组织的稳定性(Meyer & Rowan, 1977)。该理论对本文的启发在于,首先,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重视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这与以往将组织视为封闭系统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为人们所“广为接受”(taken-for-granted)的社会事实(周雪光,2003)都是其制度环境的构成要素;其次,“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组织领域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它是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的这样一种制度力量。在组织结构内部以及在组织与制度环境互动中,合法性机制起到重要作用(张永宏,2007:5)。在制度化的组织中,由于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时常会发生冲突,解决的方式就是把组织的正式结构和实际运作分离,保护正式结构免受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冲击(Meyer & Rowan, 1977);第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会迫使生存于其中的组织在正式结构上逐渐“趋同”,甚至完全一致(Meyer & Rowan, 1977)。
这里的“趋同”是新制度主义中的另一关键概念。机构领域内的组织倾向于同质化,模仿主导的做法和形式,从而维持合法性。“制度同构”的三种方式是:强制趋同,主要是组织所依赖的上级组织向它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所处社会中的文化期待对它的压力等;模仿过程,指当某个组织的技术难以被理解和评估,或者当组织的目标含糊不清时,组织会倾向于模仿那些已经成功或者它们感觉更加合理的同类型组织;规范压力,指会产生一种在专业内部共享的规范标准和思维方式(DiMaggio & Powell, 1983)。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点模仿过程,如果一个组织陷在多重的制度环境中,面临多个可以模仿的对象时,组织到底会模仿谁?2016年,马奎斯和蒂尔奇克提出了“制度对等”概念。如果两家公司在同一行业运营,并且总部也位于同一地理社区,那么这两家公司在制度上才是对等的。企业将更有可能模仿制度对等的企业,而较少关注那些仅仅是同行业或地理相近的其他企业(Marquis & Tilcsik, 2016)。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关注外部环境对组织行动的影响,而新闻创新本身即为新闻组织在外部环境变化下采取的新行动(王辰瑶,2020)。本文认为要对算法新闻这一新闻创新实践进行考察,必须考虑到行动所处的环境及环境对组织带来的影响。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命题,有助于我们回应相关问题。在此研究视域下,本文的问题是:第一,传统媒体新闻编辑室如何进行算法新闻实践?第二,哪些因素影响着传统新闻编辑部形成上述算法新闻实践?
2020年4月至2021年12月,笔者在N市A、B、C三家报社开展了实地研究,深度访谈了30位新闻从业者(本文实际使用了28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研究现象的背景,以参与观察和访谈为主要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法(风笑天,2001:177)。选择N市一方面因为它是省会城市,坐落在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拥有较多新闻机构;另一方面也因为笔者开展研究的便利。考察的三家报纸中,A报是省级党报,B报是省级都市报,C报则是主打N市新闻的区域性报刊。
本项实地研究分以下步骤展开。首先,笔者通过朋友,于2020年4月进入C报融媒编辑部进行了为期10天的实习,此后通过在C报实习的指导老师,于2020年4月至8月间,每周有1到2天时间在C报融媒编辑部进行实习。此后以同样的方法,于2020年8月至12月间,每周安排1天或2天在B报客户端编辑部进行观察与访谈。对A报的实地研究时间则安排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间,观察与访谈的部门是客户端首页编辑部。2021年3月至7月间,笔者对访谈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编码。经过编码,针对一些尚未厘清、仍需阐明的问题,笔者于2021年7月至12月间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访谈。应受访者的要求,以及笔者对可入场机构“保守行业机密”的承诺,笔者对这三家报纸的名称及受访人进行了匿名处理(见表1)。
二、以调适为主的算法新闻实践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三家新闻组织都没有正式发布或利用相关算法技术进行自动化新闻生产。A报的技术人员表示,研发人员尝试利用算法做一些新闻生产的自动化探索,如天气预报和股市,但目前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属于“浅层次的产品”,还不能对外发布(访谈1,A报)。B报的技术人员则坦言:没有听说过,还没有尝试(访谈2,B报)。C报的技术人员则表示,之前也与相关科技公司谈过合作,但是价格有点高,就没有进一步谈下去(访谈3,C报)。
在信息过滤筛选方面,三家新闻组织也均未将算法应用到自有新闻聚合端口(如客户端、网站)的底层设计和信息分发中。主要原因正如B报技术部的负责人JS所说,商业大数据是输出的、交流的、互碰的,然而传统新闻媒体的数据是无法碰撞的,至少目前没有看到。我们传统媒体的大数据,更多地是抓取的信息内容的大数据,量比较小。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数据仅仅是“新闻”,没有能跟你的服务对象有延伸关系的大数据,数据量不足,我们就很难做筛选和分发(访谈4,B报)。调研到的传统新闻编辑室都没有像已有文献介绍的国外一些媒体那样,使用自己开发或合作开发的算法来辅助新闻生产和分发,也即没有主动的算法新闻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编辑部与算法无关,调研发现,算法主要是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在影响传统新闻编辑部。传统新闻编辑部对大平台媒体所用算法的“猜测”、“预判”已经深入到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
首先,在发现选题上,平台媒体通过算法机制生成的“热点”已成为记者新闻判断的新标准之一,并辅助记者进行“数字跑口”。“数字跑口”是对数字时代记者“跑口”方式的概括,它是指传统媒体记者将互联网作为长久而定期的获取信息(白红义,2013)的重要路线(beat)的过程。当海量的网络线索对记者开放之时,传统媒体时代“混熟”条口的方式显然已“不够用”(访谈5,A报)。调研的三家新闻组织的技术团队均开发出自己的发稿平台,拥有自己的热点库(各个平台媒体热点的集成),方便编辑记者在其中找寻选题。选题会上,各个机构也会利用“大屏”显示的各种热点数据,如客户端热点、微信热点、微博热点、抖音热点等来辅助决策。以微博为例,“(搜索热度+讨论热度+传播热度)×互动率”这一热度计算公式目前已经在《热搜榜规则说明》上进行了透明化的展示,受访人也普遍有通过“热搜”找寻选题的经历。寻找“热搜”与本地关联度的结合点,再进行二次加工,成为记者们的一个新工作方式。甚至有些按照原来的新闻价值判断,编辑认为不会成为选题的内容,但因为是算法提示的“热搜”,也被当作了新闻选题。如B报的微博编辑说:比如某冷饮融不融化这种事,在以往的判断中实在是太小太碎了。但是没办法,现在就是热搜第一,而且有传统媒体专门直播看是不是真的难融化(访谈6,B报)。对于地方性媒体来说,热搜也改变了新闻人对原有新闻价值判断中“地理接近性”和“时效性”的看法。A报微博编辑D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有的选题其实并不是我们本地的,例如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已经预判会登上热搜,所以有时候也会去外省采访报道。时效性这个更夸张,比如有一个防脱发洗发水究竟有没有用的视频,不知道是多久之前的了,但每次看到有媒体发出来点击量都很高,也许是因为当代人脱发太严重了吧(访谈7,A报)。
平台媒体通过算法机制呈现出的事件传播力大小的榜单在深刻影响专业媒体新闻选择的同时,的确让一些新闻人感受到了诧异、不解,但观察发现新闻媒体在与算法的调适中自信心是在增长的。比如当记者基于专业判断采写的新闻登上热搜后,哪怕不是本媒体的,也有利于提升传统新闻编辑部面对平台算法的信心。也就是说,虽然热搜上有一些琐碎的内容,但媒体人认为高质量的新闻还是可以冲上热搜的。如A报的一次业务研讨会上,总编辑QS表示:在报题方面,跟着热点走的选题我们需不需要?需要。但是不得不说,这些选题有的的确太碎了。我希望我们能报一些更高质量的选题,这些选题是围绕国家、围绕省里的中心工作的。要把第二落点变成第一落点。而且这样的选题也是可以冲上热搜的(访谈8,A报)。
其次,三家新闻组织均采用了针对不同平台的差异化新闻投放策略。笔者统计了A报新媒体运营人员2021年11月3日至11月9日在不同端口和平台上选用的新闻稿件类别(见表2)。A报在线新闻部门的编辑YQ说,不同平台的判断不一样,这其实是不同的算法在起作用。
B报客户端编辑SX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有两种新闻类型是网友非常关心的:第一类是重大时政类新闻。比如涉及省长、市长的稿件,再比如人事任免稿件。这些稿件通常自带流量,能够关联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第二类是社会热点,比如某些案件的宣判,新闻性、可读性强,相关文章阅读量都非常高(访谈9,B报)。
然而针对微博和抖音,传统媒体的编辑却较少选用时政新闻。C报微信编辑LL说:这些分发平台的受众驳杂,偏年轻化、娱乐化,娱乐明星、网络红人频频登榜,这并不是主流媒体主攻的方向。换句话说,重大政经、民生服务、人事任免这些传统媒体的优势在微博、抖音等分发平台上发布,效果就不理想了。所以绝大多数本地主流媒体还是重点打社会热点牌。而且与客户端、微信不同,这些平台更倾向于选择视频类稿件(访谈10,C报)。
第三,传统新闻媒体编辑倾向于采用“新闻聚合”策略进行内容生产,以适应平台算法的规则。从2004年开始,谷歌、百度的新闻(或资讯)频道,就已经依赖搜索技术和算法来进行新闻的聚合以及在网页上的呈现。美国学者安德森也曾分析过“作为新闻聚合网络生产”的美国费城Philly.com的实践情况(Anderson, 2013)。数字时代,新闻人已经可以在搜索引擎和平台媒体算法的辅助下,通过对各类信息要素的划分、筛选和组合来重写新闻,达到反映新观点、提炼新角度、启发新思考的目的。这意味着,新闻写作已大量由对即时事实的描述转为对过往事实的阐释。那些在互联网中“沉默”的信源被唤醒了,那些公开或隐蔽的数据也可以成为记者发现新闻选题,加强新闻深度的资源。
专业新闻媒体人还发现平台算法似乎也更鼓励聚合而不是原创,这进一步强化了“新闻聚合”策略在内容生产中的应用。被访对象认为,这是因为聚合可以把热点事件“叠加”。在A报的一次微博发布讨论会议上,小编YQ在小结一周工作时说:前两天其他媒体都纷纷发了入秋的话题,大家都在发,我们能push(被平台弹窗推送)上的几率不大。我在看选题的时候,在一个特别“犄角旮旯”的号里面发现了某地入秋的话题,当时别人还没有发现,我一发就push上了。另外,那天有两个大风预警,每一个单独的都被别家媒体抢先push上了,我把这两个新闻重新合了一下,起了一个#双大风预警#的话题,一下就push上了(访谈12,A报)。在这个案例中,“被push”意味着有更多人看到,以及由此而来的更多点击量。
第四,传统媒体在大平台上投放内容的点击量数据被纳入考核指标。调研发现,以往传统媒体人的考核主要依据机构自己设定的质量指标,考评人会根据稿件的篇幅、版面、内容等来打分,虽然记者如果对评分结果有不同意见可以申诉,但传统新闻生产质量的考核体系是带有评审人鲜明主观因素的专业评价体系。而现在,在笔者观察与访谈的N市三家纸媒中,点击量均被纳入了考核的范畴,只不过方式不一。有的是作为“增量”:“我们如果拿到了微信10万+,上了微博热搜、抖音热榜就会加分。”(访谈13,A报);有的是“基础项”:“我们每个月微信点击量必须有X条超过5000或者微博热搜超过X条才能拿到基本绩效。超过得越多,绩效越高。”(访谈14,C报)传播评价体系的算法化不可避免地给编辑部带来“度量焦虑”(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2022)。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C报的微信编辑:我们现在压力非常大,每年第三方平台都有新闻媒体微博微信排行榜,算法基本上是阅读指数、在看指数、点赞指数的平均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根据流量的判断来找选题,那我们的排名就会落后(访谈15,C报)。但B报编辑的看法也有一定代表性:我们肯定不能跟着这个榜单走,否则我们很多专业判断就没有了。个人认为榜单排名在中上就可以了,我相信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如果跟着流量走,你的内容生产也是有目的性的,一旦丧失了我们坚持的价值,以后不可想象。更何况你也无法判断哪些人是“水军”(访谈16,B报)。可以这么理解,“度量焦虑”在传统新闻编辑部中存在,但程度不一。编辑部和新闻人对平台算法呈现的点击率和媒体排名的重视程度,又与专业观念、单位领导的重视、与绩效绑定方式等相关。
三、传统新闻编辑室为什么对算法新闻“浅尝辄止”?
按照王辰瑶对新闻创新行动的分类(王辰瑶,2022),本文发现,传统新闻编辑室的算法实践主要是一种“调适性新闻创新”而不是“生产性新闻创新”。为什么主流新闻媒体采用调适性策略而不是更加进取的算法采纳策略生产算法新闻?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出发结合访谈资料,提出如下解释:
首先,编辑部对算法新闻的采纳,需要匹配一定的制度安排,比如重新设置编辑部的组织结构等,这必然涉及一系列人力财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而此类安排的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业内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这是三家传统新闻组织都对自建算法并用于新闻实践均抱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一般来说,对待创新项目,传统新闻组织会在现有的组织架构(符合制度合法性逻辑)之外,另设计补充性、灵活性的结构,且这一结构不会影响原来的制度安排。如成立新闻创新项目的“工作室”,此类工作室绝大多数都以记者、编辑为主,技术人员为辅。因为制度化的组织倾向于采用把组织的正式结构和实际运作分离的方式,来缓解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的冲突,保护正式结构免受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冲击(Meyer & Rowan, 1977)。非正式手段让组织变得更加灵活,从而让组织可以更好地应对实际运作中遇到的问题,提高组织的效率。相比而言,在微博、微信和其他社交平台上建立“新媒体矩阵”,前期动用的制度安排较少,可以在不改变媒体原有结构的情况下用增设“新媒体部门”的方式实现,因而创新扩散的阻力较小。而算法新闻实践的前期就高度依赖技术,需要技术人员和采编人员密切合作,这意味着要对原有组织结构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并把两类在知识结构上相差甚远的成员组合到一起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如果要采纳算法新闻,新闻组织必须要生成适合其发展逻辑的新制度安排,而且还要承担没有成功经验的先行者风险。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A、B、C三家报社在是否采纳算法新闻上都询问过彼此的做法。当算法新闻带来的影响无法评估之时,组织倾向于减缓创新。这三家新闻组织目前对主动进行算法新闻的尝试都是自上而下的:传媒组织管理者采取非正式的方式请技术部门“看看有无可能”(访谈17,A报)。而新闻组织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新闻知识、数据、成功范例,绝大多数都不会主动提出要进行算法新闻的尝试。C报技术部的负责人ZM在访谈中谈道:算法是大数据的核心功能,目前普遍被大数据公司垄断。讲白了,算法是应用数学专业,编辑部偏文科。新闻组织鲜少有这样的人才储备,因为养人太贵,招了也用不上。而且隔行如隔山,不可能由“外行”领导“内行”(访谈18,C报)。传统新闻组织内部要进行主动算法新闻实践创新的制度安排,难度可见一斑。
其次,算法新闻与新闻业目前的观念制度存在较大冲突。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认为,算法新闻挑战了新闻业长久以来坚持的某些信条,并不利于新闻组织树立行业权威,建立“新型主流媒体”的形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平台媒体算法制造出来的流量景观挑战了传统新闻业一贯坚持的信条,这些信条被认为是新闻专业的核心观念,是新闻组织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受访者认为,平台推行的算法与新闻应服务于社会根本利益的信念冲突。如A报在线新闻部门技术部的负责人XL在访谈中表示,算法是“(平台)机构意志”的延伸,有很强的功利性,而不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
算法不是公共的,而是机构自有的,以海量的数据为前提。它貌似公正,但始终是以机构的目的为前提,因此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比如有些商业网站,需要流量变现,以流量作为其算法的核心,可以想见,耸人听闻、猎奇的事件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谣言也会甚嚣尘上。(访谈19,A报)
平台算法也被一些受访者视作对新闻真实原则的挑战。真实是传统新闻理念的基石,虚假新闻被认为是“行业失范”的表现,也是数字新闻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受访者DM是C报的记者,他对“算法”深恶痛绝却又倍感无奈:
现在很多信源都是来自社交媒体,我们要做很多核实的工作。2019年,我印象很深,有一个热搜说是教科书里面有些耳熟能详的字改字音了。我查了一下,很明显是一个不准确的“旧闻”。但糟糕的是,读者似乎已经不那么在乎新闻的真实与否了,和“真相”相比,网友似乎对传播者所谓的“付出”更看重,“写得这么长还能有错?还有长图呢!”哪怕是翻一下教科书就能知道答案,却没有人做全面的调查。尽管我后来也写了核实的文章,但是点击量却没有那么高了。(访谈20,C报)
还有一些受访者对要根据算法提示的“热点”快速生产新闻的工作方式产生了“不安”。A报两微新闻部的编辑PP表示:一旦我们跟风去追求流量,就难免会出现“蹭热点”的行为。一个热点出来,比如谷爱凌,她的身世、家乡、各种亲戚什么的全都被扒出来,我觉得是违背新闻伦理的,令人不安(访谈21,A报)。
追求流量的“恶果”被B报记者XF描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深度报道的部分放弃,“深度报道有,但是不多。因为热点来得太快,你必须要迅速做出来,做不出来流量过了,你这个新闻就不‘香’了。最终结果是,做出来的稿子我也忘记了,受众也忘记了”;另一方面,导致新闻选题同质化,行业竞争愈加激烈。“本来新闻应该广撒网,不过现在大家都会重点关注能够带来流量的选题,都往同一个地方去了” (访谈22,B报)。
还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算法混淆了新闻的边界,搞乱了到底“什么是新闻”的标准。B报的微博编辑JJ对此感同身受。JJ有着将近20年的从业经历,曾做过社会新闻记者、国际新闻编辑,2013年调到B报新媒体部,从事微博编辑工作:
我们以前做报纸编辑的时候,对什么是新闻,大家是有共识的,比如最基本的5个“W”,这是必要条件。但是到社交媒体这个就变了,有可能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有可能这个事情是多少年前就发生的,但在网络上却变成了一个现象级别的讨论话题。你看,纸媒或者电视台做的深度报道或人物特写,好像就不如一个小朋友的萌视频传播得广。当然这个是有好多原因的,平台算法一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访谈23,B报)
新闻工作的主导文化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化”的规则。从访谈情况看,专业新闻工作者对平台算法与新闻专业观念冲突的感受还是很强烈的,虽然他们在努力适应并做出新闻生产上的策略调整,但也认为算法逻辑与新闻的文化制度的不匹配难以解决。
第三,算法新闻能给组织带来何种社会及商业上的收益尚不明朗,缺乏能让传统新闻媒体产生创新趋同性的力量。经过调研,笔者发现三家媒体组织的管理者基于评估认识到,主动进行算法新闻生产目前还是一种“性价比”很低的形态。三家新闻组织对创新的成本及周期均有“收益”方面的考量。B报技术人员RY表示,算法新闻的研发基本上是两个模式,一个是与技术公司合作,一个是自己研发,但投入都很高:我们跟业内一些知名的公司谈过,价格非常高;二是自己的技术人员开发,但是这类技术人员的薪资水平非常高(访谈24,B报)。除了高额的投入,A报的版面编辑ZQ说:不知道是技术水平没达到还是怎样,我看到的自动化的新闻作品都是有不少错误的,在我们这里,初审都过不了,还得慢慢改,这跟重写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发生导向问题,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访谈25,A报)。B报的气象记者DD认为:其实气象新闻是很难写的,每天需要变换各种语言,模式化的内容感觉会失去读者(访谈26,B报)。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令新闻组织放弃了“自动化新闻生产”的赛道。此外,新闻生产中有很强的随机决策的特点。C报融媒编辑中心的记者ZY说,新闻表面上有很多规则,但是实际操作上,大家不一定按照这个规则来。比如说之前有一位研究唐诗名家的讲座。按照新闻的规则,我在报道中应该写他讲座中比较新鲜、吸引人的部分,比如给诗人颁奖、诗人的趣事等,但跟演讲者本人沟通之后,他觉得还是应当写唐诗本身的气韵。为了维护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我最后还是尊重了他的想法(访谈28,C报)。这个例子说明了新闻标准与新闻实践结果之间的差异。算法是基于设定好的规则和标准的,但绝大多数新闻报道具备灵活性和反思性。算法新闻的开发投入高、对新闻生产实践的适配性低,出于理性计算,传统新闻媒体编辑部不会轻易试水。但传统新闻编辑部并非明确“放弃”了主动的算法新闻实践,而是处在一种保持敏感的观望状态。三家新闻组织对业界信息均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并对国外前沿媒体的创新尝试也有案例收集。它们倾向于模仿与自己处在共同制度环境中的组织行为,但目前这样具有明确创新收益的模仿对象还未出现。
结论:算法采纳的边界
本文以新闻组织为新闻创新采纳的主体,考察三家报社新闻组织围绕算法的实践。研究发现,我国综合性日报的传统新闻编辑部面对算法的新闻实践有相似的特点,以主动适应平台算法的一系列新闻生产策略调整为主,但很少出现利用算法技术生产算法新闻的情况。这与当前研究中对算法技术深度卷入新闻业、对新闻文化可能形成颠覆性改变的论调很不一致。本文认为,如果纳入制度因素对新闻组织及其创新行动影响的视角,可以解释在实际的新闻生产中为什么会出现算法采纳的边界。
传统新闻媒体在边界内积极进行了适应算法的策略调整,包括改变对新闻选题的判断、差异化新闻投放、采用新闻聚合等新的内容生产方式、将算法导向的传播结果纳入考核体系等。
但主动利用算法和大数据进行“算法新闻”生产,目前仍然处在新闻创新行动的边界之外。因为传统媒体在对算法新闻这种技术难度大、收益不明确、缺乏模仿案例的创新项目进行过理性考察后,发现算法新闻不仅需要调动的组织制度安排幅度很大、技术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与支撑新闻业的文化制度目前看来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算法新闻”仍然停留在传统新闻编辑部创新行动的边界之外,但又处在传统新闻媒体密切关注的视线之内。
本文的经验材料是基于同一个城市的三份综合性报纸,地域与媒体类型可能会对本文结论产生一定的限制。比如财经类等专业性媒体对算法新闻的采纳程度可能会比综合性新闻媒体的采纳程度高。但本文认为该研究的结论仍可解释较大范围内的主流新闻媒体的算法新闻实践。新闻媒体已经走过了盲目追捧新技术的阶段,面对新技术也可以进行不同的应用策略。比如这三份日报在面对算法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调适性策略而不是生产性策略,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在现实制度空间下的理性选择。这种状态是否会持续下去,取决于一系列的变化条件,比如算法技术自身的进化是否可能与新闻业的文化制度很好地相融、在新闻业竞争中是否出现了可被模仿的对象等。本文的另一收获是发现新闻创新研究文献中可能存在“先行者偏差”,率先进行某种创新的行动者容易获得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但这类创新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是否能够扩散,却少有持续的探讨。这可能也是未来的研究者们需要警惕的方面。■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3)。冲击与吸纳: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常规。《现代传播》,(8),44-45。
白红义(2017)。大数据时代的新闻学:计算新闻的概念、内涵、意义和实践。《南京社会科学》,356(06),108-117。
白红义,李拓(2019)。算法的“迷思”:基于新闻分发平台“今日头条”的元新闻话语研究。《新闻大学》,(1),30-41。
方师师(2016)。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围绕“Facebook偏见门”事件的研究。《新闻记者》,(9),39-50。
方师师(2018)。算法如何重塑新闻业:现状、问题与规制。《新闻与写作》,(9),11-19。
风笑天(2001)。《社会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艳红(2017)。在开放与保守策略间游移:“不确定性”逻辑下的新闻创新——对三家新闻组织采纳数据新闻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9),40-60。
毛湛文,孙曌闻(2020)。从“算法神话”到“算法调节”:新闻透明性原则在算法分发平台的实践限度研究。《国际新闻界》,(7),6-25。
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2022)。2021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新闻记者》,(1),38-56。
王斌,李宛真(2018)。如何戳破“过滤气泡”算法推送新闻中的认知窄化及其规避。《新闻与写作》,(9),20-26。
王辰瑶(2020)。新闻创新研究:概念、路径、使命。《新闻与传播研究》,(3),37-53。
王辰瑶(2022)。新闻创新的行动主义立场。《全球传媒学刊》,9(4),140-141。
王茜(2017)。打开算法分发的“黑箱”——基于今日头条新闻推送的量化研究。《新闻记者》,(9),7-14。
周雪光(2003)。《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永宏主编(2007)。《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Arsenault, Amelia H. (2017). The Datafication of Media: Big Data and the Media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Politics 13 (1): 7-24.
BozdagE. (2013). Bias in Algorithmic Filtering and Personalization.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5 (3): 209-227.
Caswell, Davidand Konstantin Dorr. (2018. Automated Journalism 2. 0: Event-driven narratives: From simple descriptions to real stories. Journalism practice, 12(4):477-496.
Carlson, Matt. (2015). The Robotic Reporter: Automated Journalis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LaborCompositional Forms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Digital Journalism 3 (3):416-431.
ChristinAngèle. (2020). Metrics at Work: Journalism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 of Algorithms.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ristinAngèle. (2017). Algorithms in Practice: Comparing Web Journalism and Criminal Justice. Big Data & Society4(2)1--14.
DeVitoM. A. (2016). From Editors to Algorithms: A Values-Bas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tory Selection in the Facebook News Feed. Digital Journalism 5:753-773.
DimaggioPaul J. and Powell, Walter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147-160.
DorrKonstantin N. (2016). Mapping the Field of Algorithmic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4(6): 700-722.
FlewT.Spurgeon, C.Daniel, A.& SwiftA. (2012). The promise of 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6(2):157-171.
HansenMark, Meritxell Roca-Sales, Jon M. Keegan, and George King. (201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actice and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m. In 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Jamil, Sadia. (202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journalistic practice: The crossroads of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Pakistani journalists. Journalism Practice, 1-23.
Jannach, D.M. Zanker, A. Felfernigand G. Friedrich. 2010. Recommender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dén, C. G. (2017). Algorithms for journalism: the future of news work. 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4 :60-76.
LowreyW. (2011). Institutionalism, News Organizations and Innov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2:64-79.
Marquis, C. & TilcsikA. (2016). Institutional equivalence: How industry and community peers influence corporate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 Science27(5)1325-1341.
Meyer, John and Rowan Brian. (1977) .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340-363.
MollerJ.D. Trilling, N. Helbergerand B. Es. (2018). Do not Blame it on the Algorithm: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Multiple Recommender Systems and Their Impact on Content Diversit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 (7): 959-977.
MollerL. A. (2022) Recommended for You: How Newspapers Normalise Algorithmic News Recommendation to Fit Their Gatekeeping Role, Journalism Studies23(7): 800-817.
NapoliP. M. (2014). Automated media: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perspective on algorithmic media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4(3): 340-360.
Van DalenArjen. (2012). The algorithms behind the headlines: How machine-written news redefines the core skills of human journalists. Journalism Practice, (6): 648-658.
Young, M. L.& HermidaA. (2015). From Mr. and Mrs. outlier to central tendencies: 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and crime reporting at the Los Angeles Times. Digital Journalism 3(3):381-397.
朱威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王辰瑶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新闻生态系统创新研究”(20XWA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