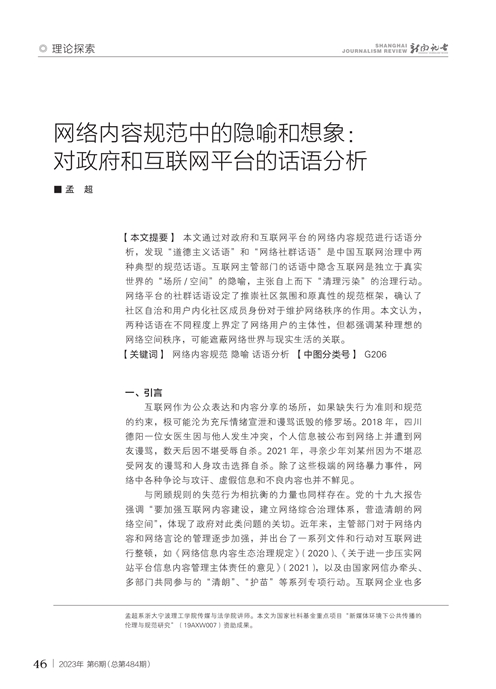网络内容规范中的隐喻和想象:对政府和互联网平台的话语分析
■孟超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政府和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内容规范进行话语分析,发现“道德主义话语”和“网络社群话语”是中国互联网治理中两种典型的规范话语。互联网主管部门的话语中隐含互联网是独立于真实世界的“场所/空间”的隐喻,主张自上而下“清理污染”的治理行动。网络平台的社群话语设定了推崇社区氛围和原真性的规范框架,确认了社区自治和用户内化社区成员身份对于维护网络秩序的作用。本文认为,两种话语在不同程度上界定了网络用户的主体性,但都强调某种理想的网络空间秩序,可能遮蔽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关联。
【关键词】网络内容规范 隐喻 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互联网作为公众表达和内容分享的场所,如果缺失行为准则和规范的约束,极可能沦为充斥情绪宣泄和谩骂诋毁的修罗场。2018年,四川德阳一位女医生因与他人发生冲突,个人信息被公布到网络上并遭到网友谩骂,数天后因不堪受辱自杀。2021年,寻亲少年刘某州因为不堪忍受网友的谩骂和人身攻击选择自杀。除了这些极端的网络暴力事件,网络中各种争论与攻讦、虚假信息和不良内容也并不鲜见。
与罔顾规则的失范行为相抗衡的力量也同样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体现了政府对此类问题的关切。近年来,主管部门对于网络内容和网络言论的管理逐步加强,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行动对互联网进行整顿,如《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2020)、《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2021),以及由国家网信办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清朗”、“护苗”等系列专项行动。互联网企业也多有积极回应,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对平台内容和言论的审查和管理责任。
那么,网络用户的行为如确有限定,其遵循的伦理规范是什么?政府和互联网企业如何制定网络规范,又何以确定网络用户的行为准则?本文认为,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政府和互联网平台治理逻辑和行动策略的梳理;通过识别话语中的隐喻和框架,可以发掘二者构建互联网规范的过程和内在逻辑。
二、文献综述
(一)网络规范与治理逻辑
在中国,互联网已成为社会交往、民意表达和内容发布的重要空间,网络治理也成为政府面对的实际问题。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互联网的治理模式逐步完善,其意涵的丰富性也激活了研究者考察网络治理逻辑的多重视角。如果互联网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体,而是一个包括基础设施层(物理层)、软件代码层和内容层的分层组织,那么互联网治理的内容也必然是多维和复杂的(梵·迪克,2020:33)。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将互联网治理简化为技术治理和内容治理两个部分,但是网络环境的复杂多变使得政府的某个或某几个部门难以独自应对,因此维护网络规范的行动者往往是多主体的。在梳理中国网络治理的发展历程后,杨国斌指出,2004年以来中国形成了一套包含制度、法律、道德、技术、话语的完整成熟的网络管理框架,这套框架是由各类机构协同行动、各种规则相互配合的产物(杨国斌,2013:55-56)。亦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的网络内容治理进入到超级治理阶段,治理的行动主体是包括政府、传统媒体、商业机构等多种类型来源的行动者网络,“以数据要素为抓手调整信息内容秩序,通过治理信息内容生态来整合社会组织与群体”的“双重中介”治理模式已渐成熟(年度网络内容治理研究课题组,2022)。
上述研究确认的网络治理模式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针对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制定相应的政策本质上是政府的一种政策学习过程(李永刚,2013:115-116)。因此,研究者往往将中国互联网内容治理的发展分为若干阶段。例如,杨国斌(2013)认为中国互联网治理可分为政策制定阶段、控制扩张阶段、规管和治理阶段;王梦瑶和胡泳(2016)则将其划分为科教兴国与现代化发展、产业开放与社会管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几个阶段。尽管划分的依据不同,政府监管由弱至强,由粗放迟缓发展为严密精细,应能在研究者中达成共识。
如上,多维性和演进性可视作理解中国网络治理的两个关键角度。而政府关于网络治理的话语框架,有助于理解如上治理行动的底层逻辑。首先,对中国媒体的治理存在一种道德秩序诉求。有学者指出,中国媒介治理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特征,其特点是“以伦理审判和道德训诫取代法律和政策的规制”(龙耘,赵春光,2013)。这种家长式和道德主义的管理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对互联网的言论管理和对良好道德风气的倡导。杨国斌(2013)认为,中国政府将互联网视作大众媒体的延伸,注重对互联网的管理和舆论引导,因此国家对互联网秩序的管理诉求,可以部分通过政府对大众媒体的管理来说明。李永刚(2013)指出,互联网主管部门对互联网的治理是父爱主义(paternalism)的,即主张出于善意、维护当事人利益而对其行为进行限制。
Cui等(2016)指出,互联网治理隐含的另外两种框架是社会稳定话语和全球化话语。社会稳定话语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诉求。破坏稳定就是破坏经济发展、破坏人民的幸福,因此“维稳”就成为官方话语和议题的关键。而全球化话语则体现了一种内在张力,具备全球多中心分布的互联网具备脱离监管的内在属性,而政府仍然需要把互联网视作拥有主权的领地进行管控。总之,政府对于互联网的内容治理,无论是方法和手段还是逻辑和目标都绝非单一,而是囊括了维护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防范风险的安全诉求、促进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经济诉求,以及弘扬向上的社会风气和正能量的道德诉求,等等。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发现,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与社会治理模式密切相关,社会治理和政策制定的视角显然有助于把握互联网治理的逻辑。但是以往的研究极少涉及网络问题及其治理方案的话语建构,这需要我们对不同话语模式及其可能引发的治理行动进行细致梳理。
(二)互联网、话语与隐喻
话语是理解复杂问题的工具,为议题讨论提供了语言资源,同样也影响人们谈论和思考某件事物的方式(莱考夫,2015;Branch,2020)。在互联网的传播学研究中,对隐喻的分析并不鲜见。在早期研究中,Stefik(1996)将互联网的隐喻分为四种:图书馆、邮件、市场和数字世界。图书馆和档案馆等隐喻的使用反映了互联网作为储存数据和知识的“仓库”的概念。在今天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将互联网类比于石油和金矿,则反映了信息作为待开发资源的重大意义(Wyatt, 2021)。
如果提升抽象层次,我们会发现这些隐喻的背后存在一些支配性的元隐喻(Krippendorff, 1993)。Markham(2003)指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采用“场所”(place)和“工具”(tool)等隐喻来建构关于互联网的知识。首先,“场所-空间”隐喻很可能是关于互联网的最关键隐喻之一。Maglio和Matlock(1999)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人们需要开发新的方式去表述互联网这一新事物时,就“自然地”运用和空间相关的语汇了——研究者将其总结为“网络空间就是物理空间”和“获取信息就是在空间中移动”两种隐喻。“场所”隐喻暗示要将互联网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地方,这一隐喻强调了互联网与线下体验的差异,将其构建为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空间(Markham, 2003)。类似地,Wilken(2007)认为,互联网被表述为一个“场所”意味着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空间,把网络理解为场所对于其社会交往的属性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人们已经习惯于互联网存在的数十年之后,网络访问体验已与互联网出现伊始存在巨大差异,空间隐喻依然普遍存在于网络用户对网络活动的描述中(Matlock, 2014)。
Markham(2003)认为作为“工具”的互联网也包含了三个子隐喻:“人体的延伸”(prosthesis)、“管道”(conduit)和“容器”(container)。“人体的延伸”表明互联网可被视为身体功能的延展,“管道”暗示互联网是一种信息传输的通道,“容器”则强调了互联网容纳和存储数据和信息等特性。总之,作为“工具”的互联网可以被理解为用来完成一项任务的技术,为不同人掌握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作为一种“工具”的互联网被用于正面用途,则能创造巨大的价值和福祉;落入坏人或不法之徒之手,互联网就会被滥用、造成巨大的危害。
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指出,对某个事物的隐喻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还影响到对该事物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Thibodeau等,2019)。关于互联网的隐喻实际上也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它们会为某种特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提供潜在的支撑,或隐含对互联网采取干预方式的差异。例如,Wyatt(2021)指出,1990年代中期的美国存在两种对立的互联网隐喻:“边疆”(frontier)和“高速公路”(highway)。自由主义者们用“边疆”一词强调互联网的边缘和独立;相反,政府使用“高速公路”一词则暗示互联网是如公路一样的公共基础设施,由国家进行管理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优方式。因此,把互联网比作“高速公路”实际上强调了国家监管互联网的必要性(Dekavalla, 2021)。不同群体使用的隐喻和话语框架也是相异的。Droog等(2020)指出,不同群体表述大数据基础设施的话语框架存在很大差异;相较于专家的表达,记者使用的隐喻框架更加模糊,倾向于描述其危险性,从而可能导致公众对技术产生负面态度。因此话语限定了互联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及对它“应该有和不应该有什么期望”(Gillespie, 2010)。
综上,国外对于互联网和网络治理相关隐喻的研究十分丰富。国内学界对于互联网的话语和隐喻的研究仍然较少(陈彦蓉,2021;陈秋心,2022;刘战伟,2022)。如陈彦蓉等(2021)指出,早期中国互联网出现过“盗火”、“信息高速公路”、“第二人生”、“家园”等隐喻,可能反映了政府、市场和网民等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此类分析更多侧重于社会学视角下的互联网史研究,而极少采用话语分析或认知语言学的分析视角。考虑到对话语或隐喻的解读必然考虑社会文化背景的约束,思索中国互联网内容治理话语中的独特性,对于理解中国互联网的治理特点是颇有意义的。
(三)研究问题
如果某种语言表述可能反映或限定了人们对某个事物的理解方式和行动方式(莱考夫,2015),那么关于互联网内容治理的文本中也可能隐含了行动者对于网络问题的理解,限定了网络治理的方式和手段。基于认知语言学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本文试图解决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大众媒体中关于网络内容规范的话语有哪些?这些话语有何相同之处,又存在什么区别、矛盾或悖论?
研究问题2:互联网内容治理是如何被表述和问题化的?这些话语如何试图确立互联网用户的行动规范?
研究问题3:为减少网络内容的危害,如何进行话语更新?换言之,如何创造对网络空间规范和治理的新颖表述,才能更有效地认识这一现象和处理该问题?
三、研究方法
(一)语料库的构建
为探究以上问题,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语料库。区别于构建一个体量巨大的文本库进行量化文本分析(如“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本文基于研究者的经验和主观判断选择关键文本,再进行细致的定性分析。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考量是,涉及互联网内容治理的话语的数量相对较少,且具备相当的同质性;同时量化文本分析可能有失精细,“需要辅之以更为深入和详尽的质性文本分析”(费尔克劳,2021:8)。
本研究将文本发布的时间范围划定于2020年1月至2022年8月之间。我们注意到在2019年7月之后,政府较为密集地出台了关于网络治理的指导意见和治理行动,如2020年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2021年《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主体责任的意见》、2021和2022年的“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等,标志着主管部门对网络问题的认识进入新的阶段。
此外,我们观察到互联网规范至少与三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有关,包括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互联网用户。因此,本研究构建的语料库包括如下文本:
网络主管部门的话语。通过在网信办的官方网站中检索,本研究搜集了网络主管部门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关键文本,如《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等。这些文本设定或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门对于互联网治理模式的理解。
主流媒体话语。主要包括官方媒体关于网络规范和网络治理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研究者在“人民网”(people.com.cn)中分别以“清朗行动”、“网络暴力”、“网络生态”、“网络环境”、“网络治理”、“网络文明”等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共得到搜索结果1400余条,并对搜索结果逐条阅读,删掉内容重复和较低相关度的文章。
网络平台话语。本文重点搜集了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小红书和抖音三个网络社交平台的关于内容治理的官方公告、规范文档和宣传视频,如B站的《社区规则》、《小黑屋处罚条例V1.7》,抖音的“安全中心”和“创作者中心”发布的视频等。选择如上三个互联网平台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社交属性、巨大的用户数量和受欢迎程度。
研究者直接复制文本或保存相关网页,经过人工阅读筛选和剔除,共获得相关文本90余篇。以上文本的引文在文中出现时,会注明篇名和发布日期,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发布会》,2021-05-08”。
(二)话语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进行分析,我们尤其关注网络失范问题和网络规范是如何在上述话语中被表述和呈现的。首先,本文将识别有关互联网和网络行为规范表述中采用的隐喻和话语框架(frame)。隐喻指借助想象力用一个领域的框架将另一个生活领域进行概念化构建,而框架则是指在两个直接相关生活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因此“隐喻是一种特殊的构架”(斯提比,2019:74)。人们从源域中获取概念,并将此性质类推到目标域,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某种认识;因此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同时也建构了现实(莱考夫,2015)。对此,研究者对文本进行细致阅读,以识别词语和视觉符号的引申含义,指出隐喻背后的意涵,即话语中将源域的何种性质类比于目标域,也将试图说明关于互联网的隐喻是如何影响对互联网的规范想象,又如何限定了互联网的规范。
另外,本研究旨在发掘互联网内容规范如何在话语中“再现”。费尔克劳(2021:159)指出,话语是现实的一种再现;一个事件嵌入的物理世界中的属性,在语言中可以被表述为“过程-参与者-环境”,即发生了什么事情、事件中有谁参与、在哪里发生。同样,作为一种过程的互联网治理和规范设置可以被转述为“问题-行动者-行动”的叙事模式。故本研究试图发掘下述过程的呈现方式:(a)互联网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如何界定问题);(b)谁应该为这些问题负责(网络规范的破坏者是谁);(c)谁来解决问题(行动者是谁);(d)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采用何种行动策略和行动方式)。对此,本文将分析如上文本的句法结构或叙事结构中的主语(识别主要行动者)、动词(识别具体行动)和宾语(识别施加行动或影响的对象)。
四、研究发现
(一)官方话语
1.道德话语与污染隐喻
本文发现,官方话语中的互联网往往被表述为明显具备空间特征的“网络空间”或“网络生态”,而一些关于道德和价值规范的词语(“健康”、“风清气正”、“风气”、“正能量”、“积极”、“价值导向”)常常被用来修饰理想状态下的互联网。例如:“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2021-01-18)、“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十项“清朗”专项行动!2022年国家网信办深入整治各类网络乱象》,2022-03-17)。
如上话语可被理解为一种 “道德语言”(moralistic language);换言之,中国互联网内容治理并非欧美式的保护市场竞争、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伦理框架,而是一种“道德主义”的伦理框架。网络主管部门倾向于对互联网“应该是怎样的”进行说明,认定互联网应该是积极向上的、不违反主流价值观、具备良好道德风尚的场所。与之相对的,“风清气正”的反面是一个道德秩序混乱的网络空间:
涤荡网上的歪风邪气,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人民网评:让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2021-11-21)
网络空间出现“泛娱乐化”倾向,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泛滥,造成网络空间道德秩序混乱(《特别策划|“清朗”专项行动:网络治理的“五治”协同》,2022-04-08)
表述网络空间的秩序混乱时,官方话语中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隐喻:“污染”和“疾病”。这两个隐喻暗示,如果理想中的互联网应该是具备良好道德风尚的场所,那么现实中的互联网也有可能会被“污染”,变得“肮脏”或者“生病”。例如:
直播行业诸多痼疾顽症并未彻底消除。(《国家网信办等8部门推进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2020-08-04)
力求有效遏制网络乱象滋生蔓延。(《全网开展“大扫除”,力求有效遏制网络乱象滋生蔓延》,2021-05-11)
相信随着监管体系的日益成熟,那些“牛皮癣”一般的顽疾将得以铲除。(《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云中漫笔)》,2021-12-03)
破坏网络秩序的行为如“疾病”和“垃圾”一样,是完全不应出现的、反常的、多余的事物。理想的网络空间不可能处于清洁和肮脏之间的中间状态;一个空间只要存在垃圾或者污染,那么它就是被污染的、肮脏的。网络主管部门定义失范行为的话语和为其背书的主流媒体话语,实际上用“道德规范”和“污染隐喻”重构了网络秩序问题,唤起了“互联网正在遭遇威胁”的紧迫感。因此,两种隐喻也在为外部干预的必要性提供支持,没有外部力量干预(去“清洁”或者“医治”),“污染”或“疾病”是不会自动消除或自我治愈的。
2.清除污染的治理行动
如果互联网被定义为一个物理空间(类似于广场、街道的“公共场所”),它正在被一些污染物变得肮脏,那么采取强力手段将污染物“清除”,使之恢复到一种“清洁”或“清新明朗”的状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官方话语常常将恢复网络空间“洁净”状态的行动表述为“净化”,且这种“净化”往往是强力、有效和绝对的(“零容忍”、“说不”、“以铁的决心”、“铲除”、“扫除”、“根除”)。如:
要在全网开展“大扫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发布会》,2021-05-08)
以铁的决心、铁的手段、铁的作风整治网络乱象(《整治网络乱象,重锤要敲在“点”上》,2022-03-19)
“清扫”隐喻的视觉呈现更为直观。在新华社以“清朗运动”为主题刊发的一组漫画中,“清洁”网络空间被表现为一个身着西装、貌似政府官员的人(象征网络空间的维护者为政府相关部门),用扫帚将“乱象”扫出房间(见图1)。理想的网络空间大多用绿色的树木和山、干净的房间和地面、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空来表述。同时,“扫把”、“清扫”的隐喻在几幅漫画中反复出现(见图2、图3、图4)。与“清扫”类似的隐喻还有“铲除”(见图5)和“用网捕捉”(见图6)。这些图像暗示,如果屋子、墙壁(公告板)这类真正的物理空间/场所“应该”也“可以”被清扫干净,那么互联网也“同样”可以。
被清扫对象往往以非人化或物化的形象出现。如在上述几幅漫画中,“网络乱象”被表现为垃圾、灰尘、小广告、被污染的空气,暗示污染物是无生命的、不堪一击的、容易被清除的——因此对互联网的扫除也是容易的。另外,垃圾、灰尘等是外在于空间的,而不是空间本身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表明它们是很容易从网络中“切割”和“分离”出去的,对它们的清除并不会破坏网络空间的完整性。因此,官方话语可能强化了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的有效性,淡化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
除了将网络乱象表述为“非人”的事物,官方话语还暗示网络问题是由一些“幕后黑手”蓄意制造的。如“饭圈”(即明星的粉丝自发形成的、组织化的追星团体)“对社会秩序造成明显冲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背道而驰”(《整治“饭圈”乱象 清朗网络空间》,2021-08-12)。通过造谣和蹭热度获得利益的“营销号”和以“祖安文化”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亦是官方点名的整治对象(《“祖安文化”,网络语言中的“隐秘角落”》,2020-09-14)。这种表述强调了网络乱象背后“黑手”的危险性、有组织性和目的性,从而为使用强力手段加以制裁或惩处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网络用户的角色和受害者所受到的具体伤害,在官方话语中少有提及。网络使用者也极少出现在行动发起者的位置上,而是被描述为政策行动的受益者和被动接受保护的人群。例如:“着力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安全干净的网络环境,重点清理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妨碍青少年上网学习的不良信息”(《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任务公布,重点整治这些问题!》,2022-03-17)。“打击”、“营造”、“清理”、“整治”这些动作的执行者都是政府的相关机构(如司法机关、网信办等)。出现在受害者位置上的人群往往是青少年和未成年人,他们是被“影响”、“妨碍”的对象,是不能自我保护的群体。由此,数量庞大的互联网用户被设定为被动的受害者,需要有力的外部帮助以维护权益,因此确认了政府干预的合法性。
(二)平台话语
1.社区隐喻
作为互联网治理的统摄话语,官方话语为社交媒体的规范话语提供了大量话语资源,因此网络平台的秩序话语与官方话语存在清晰的互文性。例如,小红书和抖音等平台的社区规范中,就出现了类似官方话语的表述:
小红书倡导用户发布符合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小红书社区规范》,2021-12-24)
为了营造直播平台合法健康的娱乐环境,让大家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下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抖音短视频平台制订此直播行为规范,让我们一起建设绿色、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直播环境”。(《抖音短视频直播公约》,2022-05-19)
平台的自我审查的行动逻辑与政府对网络乱象的清除逻辑颇为近似。例如,抖音安全中心发布的平台规则宣传短视频中,出现了捕快、关禁闭的小黑屋和神秘的黑衣人、执法者(图7)的形象,显示出互联网平台的执法者角色。网络平台的“执法”是不容辩驳、不容置疑的;只要违反了平台规则,就要接受平台惩罚,被“关进小黑屋”(即“短时间禁言”)或被清除出社交平台(即“永久封号”)。网络平台服从政府的管理安排,以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和处罚,是无可厚非的。维护社区秩序也符合平台方的商业利益,因为混乱的平台环境有可能造成互联网用户的流失。 因此,主管部门和互联网企业两者形成了治理目标和行动策略的合流。
尽管如此,“社区”隐喻,以及类似的“班级”隐喻(“风纪委员会”、“节操”)和“家庭”隐喻(“小管家”)在平台话语中仍然十分突出。和官方话语对互联网的表述一样,“社区”也是一个关乎“空间”的隐喻,该隐喻强调线上空间是脱离真实世界的一个独立的场所,从而淡化了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关联。相较于官方话语中对于空间“物理性”的强调(类似于“广场”或“街道”的公共空间),“社区”更侧重空间的“社会性”,隐含小型共同体内部的和谐氛围和融洽关系。
另外,网络社区规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原真性”(authenticity),即重视情感真诚,强调真实而非商业化(Maares et al., 2020 ),鼓励用户(个人)对社区(集体)付出、贡献,而非寻求经济回报;推崇积极、真诚、不造假的行为:“提倡记录美好生活,表达真实的自己”(《抖音网络社区自律公约》,2022-05-19)。另外,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被设定为面对面的“对话”,用户有责任维护这种友好的对话氛围不被破坏。如B站关于平台规则的说明,格外强调对“评论氛围”和“弹幕氛围”的维护,暗示有些话语可能促进对话友好展开,不恰当的发言则破坏了谈话的和谐氛围。志愿审查者被要求评估“评论和弹幕在当前语境中是否适宜”(《2022年7月第三周风纪委员周报》,2022-07-18),即评价表达内容和语境的和谐程度。
对于社群主义、原真性和融洽对话氛围的推崇,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平台没有意识到违反规则的行为存在。但是互联网平台并没有对违反社区规则的用户使用强烈的措辞,而是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积极的方式界定问题。在平台规范话语中,违反行为规范的人只是没有遵守社区规则,而不是道德败坏、破坏社会稳定的人。网络问题也不外在于互联网;麻烦的制造者本身就是一个社区的内部成员,而不是外来的某种威胁或组织化的幕后黑手。因此,平台话语很可能弱化了网络问题的危险性和对受害者的严重影响。
2.社区自治话语
对于社区的管理和社区成员的约束,互联网公司使用了一种自我管理的话语。首先,社区成员通过对“公约”(由社区成员共同确定、共同遵守的软性规定)的学习,内化社区的要求,从而实现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和软约束的内化。例如,《小红书社区公约》(2021-12-24)、《bilibili创作公约2.0》(2021-04-06)等,暗示平台用户需要遵循社区的某种内部规范,这种规范与社会的公序良俗并不绝对一致,更多是社区内部的文化规则。通过社区对用户行为进行约束行之有效的关键在于,用户必须认可自己社区成员的身份。社区成员越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认可社区的价值,他们破坏社区规范的可能性就越低。
类似地,互联网平台推崇社区自治,积极鼓励社区成员承担维护社区氛围的责任:
申请成为风纪委员,意味着你将肩负起更多社区主人翁的使命,不断净化不良内容,帮助推荐优质内容,以营造友好和谐的社区氛围。(《哔哩哔哩风纪委规范》,2022-02-24)
社区氛围的维护离不开社区和所有用户的共同努力。……小红书社区之所以广受欢迎且长期繁荣,核心原因是社区活跃着一群乐于为他人提供真诚建议和帮助的成员。(《小红书社区公约》,2022-05-05)
社区自治话语的产生原因还在于,对于社区内发言适宜与否,往往取决于沟通者对于亚文化语言和符号的理解。首先,网络语言和符号是快速产生和变化的流动体,其含义往往因语境不同而异。其次,互联网的对话往往发生在亚文化圈子中,圈子中的成员有相似的背景,对于用语含义的理解取决于成员的理解。例如,在一位B站用户自发整理的审查规范中,对一些可能引发攻击行为的名词进行了说明。“不能接受的行为是进行恶意辱骂、人身攻击、带节奏、钓鱼和引战”,但是在某个圈子之外的人很难识别出这是否是人身攻击,因此“圈内的事物最好还是交由当事圈处理,过度介入会造成不必要的争端”(《收集给风纪委员的部分名词与解释3.1》,2020-04-09)。因此,对网络语言或“梗”的大量使用,要求社区成员能够对其含义进行确认。
如上所述,互联网平台的内容规范话语存在着一种张力。Gillespie(2010)指出,“互联网平台”中的“平台”(platform)一词,实际上就反映了其复杂的角色。如YouTube这类互联网平台试图展现出开放和包容的形象,同时小心隐藏其作为广告和营销平台的商业化角色;一方面鼓励用户进行自由表达和分享,另一方面却有意识地通过资助和内容审查对平台内容进行控制。Gillespie(2010)认为,貌似中性的“平台”一词实际上正表明互联网公司在几种相互矛盾的角色之间进行调和的努力。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同样试图在管理用户行为和维持社区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五、结论与讨论
表述事物的语言至关重要。本文发现,官方话语中网络问题被建构为一个道德问题。政府确立的秩序话语,主张互联网是受法律和道德约束的空间;网络主管部门致力于建设一个纯净的、无污染的网络环境,保护民众免受不良信息和不法行为的侵害。政府主管机构将网络问题的产生归咎于一些有组织、有目的、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人群,部分网民受到他们的蛊惑、充当其帮凶。只要清除掉这些不应该出现在网络中的“破坏分子”,互联网就会变得“清朗”。网络空间的清朗是通过消灭网络中的危险成分或“麻烦制造者”来完成的——或发动强烈的舆论道德抨击,或将其绳之以法。总之,官方话语会导向一种事后的、惩罚式的治理方式。
互联网平台更温和地将网络问题建构为一个“社区氛围”问题,这种话语源自平等、互助和共享的互联网原初精神,其规范的核心在于判断某个行为是否会破坏“共同体”或“原真性”。社区话语也是一种社区自治规范,要求成员内化社区秩序和志愿审查。这种话语与平台的商业属性存在着某种契合;如果平台氛围恶化,那么积极分享、友好交流的互动将会不复存在,用户流失会导致企业的盈利目标难以实现。平台对于网络问题的表述则是相对积极的,秩序破坏者被视作是一些不遵守社区公约和网络规范的成员,不应也不能被区隔于网络空间之外。
政府认为“扫除”可以净化网络空间,而网络平台则寄希望于社群的约束。两种话语本质上都是一种空间隐喻,割裂了网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而不认为它本身就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事实上,互联网并不外在于世界,也不是脱离真实的纯净之地——如同在现实中我们永远无法消除犯罪一样。正如Markham(2003)指出的,作为“一种存在方式”(a way of being)的互联网并不与现实世界脱离,它是人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自我、信息技术和日常生活充分融合、紧密相连。此外,由于法律维权的滞后和失范行为绕过平台技术监管的可能性,即使是强力的法律约束和先进的平台管控技术,也不能保护互联网用户完全免受威胁。如果互联网的使用者必须长期与失范行为共存,那么既可以消灭“污染物”或“有毒物质”,也可将提升易感者的“抵抗能力”作为一种替代的叙事范式。换言之,网络用户应该被塑造成为积极承担自我责任、抵抗网络风险的主体,而并非只能被严密保护的对象。通过用户教育、提升用户的网络素养,可以成为现有网络问题应对方式的有益补充。
本研究仅构建了一个较小规模的语料库,话语样本可能并没有涵盖所有关于网络规范的表述。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也没有进行计算机辅助的文本分析或历时性的比较研究。此外,如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阐明。第一,互联网本身及其治理方式都呈现出明显的演进性,因此话语的演变值得探究。第二,需要更加细致地刻画不同群体的话语差异,如分析对互联网技术专家、法律专家、记者、政府的不同部门、互联网从业者等群体使用或创造的隐喻和话语框架。第三,受众研究,即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受众对于不同话语的理解。第四,借助大规模语料库对文本间的互文性、词语关联和话语模式开展系统的量化研究。■
参考文献:
阿伦·斯提比(2019)。《生态语言学》(陈旸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陈秋心(2022)。从“赛博空间”到“元宇宙”:互联网隐喻分析的学术脉络与进展。《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195-215+223-224。
陈彦蓉,曹钺(2021)。早期中国互联网的技术隐喻与话语实践(1987-2003)。《新闻界》,(9),75-85+96。
简·梵·迪克(2020)。《网络社会》(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李永刚(2013)。《我们的防火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战伟(2022)。凸显什么?遮蔽什么?——作为隐喻的“平台”:连接、中介与基础设施。《新闻记者》,(6),54-66。
龙耘,赵春光(2013)。中国媒介治理中的泛道德主义:成因与影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63-67。
玛丽·道格拉斯(2020)。《洁净与危险》(黄剑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度网络内容治理研究课题组(2022)。要素治理与关系协调:2021年网络内容治理报告。《新闻记者》,(1),19-36+76。
诺曼·费尔克劳(2021)。《话语分析》(赵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2015)。《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王梦瑶,胡泳(2016)。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8(4),127-133。
杨国斌(2013)。《连线力》(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詹姆斯·保罗·吉(2011)。《话语分析导论》(杨炳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BranchJ. (2020). What’s in a Name? Metaphors and Cyber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1)39-70.
Cui D.& Wu F. (2016). Moral goodness and social orderliness: An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media discourse about Internet governance in 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40(2-3)265-276.
Dekavalla, M. (2021). Understanding Online Safety Through Metaphors: UK Policymakers and Industry Discourses About the Internet. Television & New Media152747642110420.
Dekavalla, M.& Montagut, M. (2018). Constructing issues in the media through metaphoric frame networks. DiscourseContext and Media2674-81.
Droog, E.BurgersC.& KeeK. F. (2020). How journalists and experts metaphorically frame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case of cyberinfrastructure for big dat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9(8)819-834.
Gillespie, T. (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12(3)347-364.
Hou, Y.JiangT.& Wang, Q. (2017).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online sham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619-25.
KrippendorffK. (1993). Major Metaphors of Communication and Some Constructivist Reflections on Their Use. Cybernetics & HumanKnowing, 2(1)3-25.
MaaresP.Banjac, S.& HanuschF. (2021). The labour of visual authenticity on social media: Exploring producers’ and audiences’ perceptions on Instagram. Poetics84101502.
Markham, A. 2003. “Metaphors Reflecting and Shaping the Reality of the Internet: Tool, PlaceWay of Being.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Conference, TorontoON, Canada. http://markham. internetinquiry. org/writing/MarkhamTPW. pdf.
Matlock, T.Castro, S. C.FlemingM.Gann, T. M.& Maglio, P. P. (2014). Spatial Metaphors of Web Use. Spatial Cognition & Computation14(4)306-320.
StanfillM. (2015). The interface as discourse: The production of norms through web design. New Media & Society17(7)1059-1074.
StefikM. (1996). Internet Dreams: Archetypes, Mythsand Metaphors. CambridgeMA: MIT Press.
Thibodeau, Paul, Teeny Matlockand Steven Flusberg. 2019. “The Role of Metaphor in Communication and Thought.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13: e12327.
WeningerC.& Williams, J. P. (2017). The Interaction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uthenticity: “Real” Identiti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a Transylvania Internet Forum: Interaction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uthenticity. Symbolic Interaction40(2)169-189.
WilkenR. (2007). The Haunting Affect of Place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Virtual. Ethics, Place & Environment10(1)49-63.
Wyatt, S. (2021). Metaphors in critical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 Society23(2)406-416.
孟超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讲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的伦理与规范研究”(19AXW007)资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