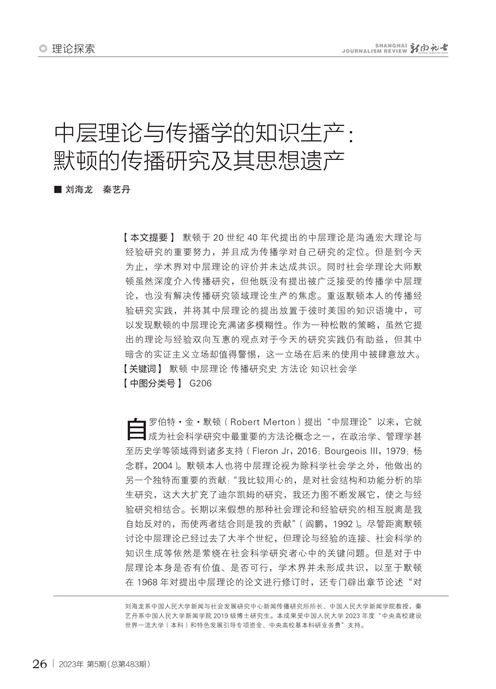中层理论与传播学的知识生产:默顿的传播研究及其思想遗产
■刘海龙 秦艺丹
【本文提要】默顿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中层理论是沟通宏大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重要努力,并且成为传播学对自己研究的定位。但是到今天为止,学术界对中层理论的评价并未达成共识。同时社会学理论大师默顿虽然深度介入传播研究,但他既没有提出被广泛接受的传播学中层理论,也没有解决传播研究领域理论生产的焦虑。重返默顿本人的传播经验研究实践,并将其中层理论的提出放置于彼时美国的知识语境中,可以发现默顿的中层理论充满诸多模糊性。作为一种松散的策略,虽然它提出的理论与经验双向互惠的观点对于今天的研究实践仍有助益,但其中暗含的实证主义立场却值得警惕,这一立场在后来的使用中被肆意放大。
【关键词】默顿 中层理论 传播研究史 方法论 知识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206
自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中层理论”以来,它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之一,在政治学、管理学甚至历史学等领域得到诸多支持(Fleron Jr, 2016;Bourgeois III, 1979;杨念群,2004)。默顿本人也将中层理论视为除科学社会学之外,他做出的另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我比较用心的,是对社会结构和功能分析的毕生研究,这大大扩充了迪尔凯姆的研究,我还力图不断发展它,使之与经验研究相结合。长期以来假想的那种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互脱离是我自始反对的,而使两者结合则是我的贡献”(阎鹏,1992)。尽管距离默顿讨论中层理论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理论与经验的连接、社会科学的知识生成等依然是萦绕在社会科学研究者心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对于中层理论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可行,学术界并未形成共识,以至于默顿在1968年对提出中层理论的论文进行修订时,还专门辟出章节论述“对中层理论的两极反应”,并一一回应(默顿,1968/2008:66)。
除了对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本身做概念的讨论外,观察默顿本人对这个理论的实际应用也是一个有趣的角度。默顿本人的传播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此问题的绝佳案例。1940年代,他曾参与了传播学哥伦比亚学派的许多经验研究,出版了《大众说服》、《影响的模式》等成果。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在这些学术成果中他并未成功地提出被后来的传播学者接受的传播学中层理论。
如果说中层理论方案是合理的,又如果说默顿与拉扎斯菲尔德之间的合作真如后来者所赞誉的那样颇有成效的话,那么为什么传播领域后来还会屡屡陷入理论生产的困境?按照默顿的规划,为什么传播学领域还没有通过中层理论的累积建立起统一理论?——这个问题及其背后的理论焦虑也是一直困扰传播学者的心结。
本文将通过对默顿的几个经验性传播研究的分析,重访暧昧的中层理论的方法论,讨论传播研究的中层理论的理想与现实。
一、同时作为教练员与运动员的默顿
20世纪40年代是默顿集中思考方法论问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经验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和《社会学理论对经验研究的影响》两篇文章,这两个姊妹篇与《论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一起被收录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
中层理论提出的一个基本背景是默顿对于当时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互相分离的状况感到不满:一方面存在一些高度散乱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关于某个具体的人类行为领域,但缺乏关键的理论取向”,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的一般取向和概念分析,由于不同于一组组相互联系的假说,又转过来反映出使理论活动从经验研究中分离出来的趋势”。基于这种分离的现状,默顿特别强调,“只有当经验研究是理论导向的并且当理论是由经验证实的,才能获得连贯性而不是分散”(默顿,1968/2008:187-188)。
这种不满集中在默顿对宏大理论的挑战。两者的观念冲突在1947年的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大会上得到凸显。在这次会议上,帕森斯在宣读的论文《社会学理论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中提出,美国社会学构建统一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默顿随即对帕森斯的判断进行了反驳,并提出美国社会学发展的重点是建设“特殊的理论”,而不是“单一的”能够推衍出上述这些以及其他理论的“概念结构”(Merton, 1948)。到1948年,默顿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想法,并明确提出中层理论的主张。
根据默顿的定义,“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默顿,1968/2008:50)。不过,中层理论只是桥梁,而非默顿的最终追求。顺着中层理论的提出,默顿也为社会理论规划了一条进步之路,即首先创立可以推导出能够接受经验研究检验的特殊理论,然后逐步发展概括化的概念体系,即能够综合各种具体理论的概念体系(默顿,1968/2008:63-64)。
乍一看,默顿的调和方案顺理成章,因为恐怕没有社会科学研究者会否认理论和经验及其互相接合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中,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在受到热烈追随的同时也饱受
批评。
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层理论的提出似乎并没有平息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理论与经验分离的危机和担忧。当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拉扎斯菲尔德的“抽象经验主义”和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两面开火的时候,他就没有明确地提及默顿及其中层理论。与米尔斯比较相似的是,布尔迪厄对于默顿综合两个传统的努力也不甚满意,认为中层法则是必须拒斥的实证主义做法(布尔迪厄,1992/1998:132)。到20世纪末,布尔迪厄仍然认为社会学的基本图景是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脱节,“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和理论主义的理论探讨携手共进,互相帮衬,彼此吹捧”(布尔迪厄,1992/1998:230-231)。
这不由得让我们对中层理论及其有效性充满疑惑。作为中层理论的提出者,默顿是一名教练员,但是作为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的默顿也是一名运动员。1940年代默顿提出中层理论的时候,他同时正在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从事传播经验研究。《大众说服》(Mass Persuasi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 War Bond Drive)(1946)和《影响的模式》(Patterns of Influence:A Study of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and of Communications Behavior in a Local Community)(1949)就是其中两项完成度和相关度较高的研究成果。
这两个研究项目都是当时传播研究哥伦比亚学派典型的行政研究,受到外部资金资助,并由默顿亲自组织领导实施。前者主要关注的是1943年一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争债券促销节目,该节目由凯特·史密斯主持,取得了良好的说服效果,资助方关注的是能够提升劝服效果的因素。后者与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的《人际影响》相似,都是《人民的选择》的后续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意见领袖与人际影响(Kazt, 1957)。该项目受到《时代》杂志的资助,在东海岸小镇罗维尔实施调查,也因此被称作罗维尔项目。
聚焦默顿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自反性问题:默顿是其训练标准下的优秀运动员吗?默顿本人究竟如何在其研究中保持理论与经验的互惠?他的传播经验研究是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吗?从这些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中,默顿是否成功地提出了传播的中层理论?
二、默顿提出传播研究的中层理论了吗?
当我们问默顿是否成功地提出传播研究的中层理论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中层理论到底要符合什么标准?但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层理论表述得非常模糊。
雷·鲍森(Ray Pawson)就曾指出,社会现实的多重性产生了解释社会的多重方式,而这也会将研究者推向态度、身份、个体、互动、实践、关系、集体、经验、文化、秩序、结构、系统等多个方向。而研究者本身的倾向会使其决定究竟应该研究什么样的案例、从事何种层次的研究。显然,这些研究策略本身将决定对数据的选择和分析(Pawson, 2000)。然而,默顿在中层理论中提出的知识建设方案则几乎没有明确触及这些由来已久的本体论问题,比如结构抑或能动、个体抑或社会、宏观抑或微观的问题(Pawson, 2000)
另外,默顿中层理论的一个特征是它仅处理范围有限的经验现象。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不幸的是,默顿并没有进一步考虑这一理论的‘限制’特征。没有一个操作性的标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现象的范围进行限制”(Smith,Bealer & Sim, 1962)。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想要发展出有关传播的中层社会学理论(middle rang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communication),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对此,他们的策略是要对传播与传播的后果进行区分,即传播理论不应该考虑对传播后果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这种限定有利于集中精力去发展理论。但如后文将论及的,有趣之处在于默顿本人恰恰特别在意将传播后果纳入自己的传播理论中。
中层理论的另一个模糊之处在于它仅仅指出经验与理论互惠的必要性,却没有明确地提出互惠和连接的具体方式。在上文提及的方法论姊妹篇中,默顿强调了一般理论取向、概念对于经验研究的作用,强调了在经验研究的构思和报告中应该明确提出假说并且论述假说的理论依据(默顿,1968/2008:174-189)。他同时还论及了经验的作用,并提出了经验研究的四功能说,即“创立理论”、“修订理论”、“转变理论”和“澄清理论”四项主要功能,并强调在“偶发”(serendipity)模式下,那些“未曾预料的、反常的和事关全局的资料”对于理论创立具有推动作用(默顿,1968/2008:191-192)。
在理论与经验连接过程中,默顿似乎赋予经验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近年来社会学仅仅赋予经验研究检验和证实假说的功能,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因为“它夸大了清晰理论的创造作用,而贬低观察的创造作用”(默顿,1968/2008:191)。同时他也抱怨说,现在的社会学理论中大多数只是对于数据的一般定向,它们能够提供理论必须说明的“变量”,但不能对“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做清晰的表述和可验证的判断”,其结果就是我们有许多概念,但只有很少被证实的理论,有很多观点,但很少有定理(默顿,1968/2008:64-65)。中层理论所要做的,就是弥补这种不足。理想状态是,通过中层理论能够架设起一道沟通经验与概念体系的桥梁,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也被从经验的视角加以界定。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中层理论,它首先要被经验“证实”。正是基于这种经验“证实”,默顿规划出一条比较顺畅的“经验-中层理论-一般理论”的知识发展逻辑。
行胜于言。由于默顿本人对中层理论如何操作的表述比较模糊,他自己亲自下场演示可以为我们理解“何为中层理论”提供许多语言表达之外的默会知识。
《大众说服》研究是默顿从事的最重要的传播研究,他的团队对歌手史密斯连续18个小时的战争债券促销广播直播的内容与受众反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希望纠正早期宣传研究中过于依赖思辨和主观判断的倾向,通过经验证据,确定广播宣传的社会心理效果。
在这项研究中,默顿的主要结论来自100个收听史密斯广播直播的听众的焦点小组访谈。在这100人的样本中,有75个人购买了战争债券,有25人没有购买(Merton, Fiske, Curtis, 1946:114)。默顿按照既有倾向对这些购买者进行了划分,其中对战争债券有情感涉入又准备购买的人被称为既有倾向者(predisposed),有情感涉入但不准备购买的人被称为易受影响者(susceptible),没有情感涉入但打算购买的人被称为冷漠者(indifferent),既没有情感涉入又不打算购买的人被称为无倾向者(undisposed)(Merton, Fiske, Curtis, 1946:114)。
对35位既有倾向者来说,他们实际上几乎并未留意史密斯的说服,史密斯的说服对这些人来说仅仅是催化剂。但对28名易受影响者、8位冷漠者和3位无倾向者来说,他们被史密斯的行为、与史密斯的情感关系,以及史密斯诉诸牺牲的劝说所打动①(Merton, Fiske, Curtis, 1946:114-135)。也就是说,真正对战争债券并无情感投入又不打算购买,但最后做出购买行为的人就只有3位。
不过奇怪的是,默顿的数据分析并没有涉及25位收听了史密斯广播却没有购买的人,尤其是没有将75位响应者与这25位未响应者进行对比分析(Mcgranahan, 194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默顿的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存在漏洞。并且默顿也没有像拉扎斯菲尔德之前主持的《人民的选择》研究一样,得出有限效果的结论,也没有从中提炼出有关于传播流的任何结论。
因为方法与结论不符合后来哥伦比亚学派主流的效果范式,默顿的《大众说服》虽然很重要,但却因为不够典型,而被主流传播学渐渐遗忘(刘海龙,秦艺丹,2023)。
罗维尔项目也存在这个问题。在罗维尔项目中,默顿以“对于当地或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取向’”为标准划分了“地区性影响力人物”和“世界性影响力人物”两类,并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这两类意见领袖在传播行为、影响力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但正如卡茨所观察到的,在默顿最后的研究呈现中,它几乎完全利用最初的访谈来定位意见领袖,而基本没有探索意见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个研究主要关注了意见领袖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沟通行为和意见领袖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去关注意见领袖和被影响者之间的互动(Katz, 1957)。卡茨的总结很到位,对于有影响力人物和被影响人物之间的互动,默顿的确关注得很少。研究的主要创新集中于“有影响的人物和被影响的人物”这一小节,并且相关分析非常粗糙,体现出默顿在事先的研究设计中未能将这些问题考虑到位。
由于这个研究在实施之前缺乏研究问题和目标,在报告撰写阶段才发现有一些关键数据没有获得,不得已又追加了第二次调查,补充了数据,才勉强得出结论(默顿,1968/2008:508-509)。但是和后来研究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相比,这个理论突破不明显的研究是一个近似失败的研究。
默顿所说的这些“程序和方法上的弯路”(默顿,1968/2008:508),首先是对于实证研究经验不足导致的。在194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正在经历由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的范式转化之中,作为一个擅长概念抽象和理论综合的学者,默顿的这些失误情有可原。
不过除了这些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默顿的传播研究及理论建构经常超出经验可以支持的结论,不再把传播视为“信息刺激-心理反应”的过程,而是旁逸斜出地产生一些偏离主题的想法。比如默顿在《大众说服》研究中有时会超越关注人们是否被史密斯刺激而做出购买行为,转而将这种关系看作一种符号行为(Merton, Fiske & Curtis, 1946:135),研究这种符号行为(或者近似大众操纵行为)对于大众提供的意识形态安慰剂功能及其长期存在或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罗维尔项目中,当默顿提出“地区性影响力人物”和“世界性影响力人物”的时候,“一些新的一致性立刻就显露出来。原来‘相同’的材料,经过这些概念重新检查和分析之后,呈现出许多相当新的内涵”(默顿,1968/2008:515)。例如地区性影响力和世界性影响力并不完全由两类人的社会地位决定,而是受到他们的知识类型、交流方式、影响方式等文化因素的复杂影响。地区性影响力人物更多的是因为情感、人际关系等获得追随,而世界性影响力人物则更多是因为专业技巧和经验获得追随;地区性影响力人物更倾向于阅读《时代》这样的全国性杂志,但这对于地区性影响力人物来说常常是多余的,因为它并不能提供很多关于罗维尔及其周边的故事。
不仅如此,默顿还试图将传播问题进一步放到社会结构的层面进行思考。他认为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行为的宣传”在失范的社会中是否比在整合程度更高的社会中更有效②;罗维尔项目中,默顿也提出这样一个预设——两种类型影响人物的分布和社会境况会随着社会的结构变化而变化。
默顿的这种宏观视野使他要处理的问题以及做出的解释已经超越了“刺激-反应”的基本框架。它一方面深化了对于传播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也使研究难以操作化。默顿本人也没有继续在经验层面推进上述研究所提出的问题。综观默顿的传播经验研究,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他总是将自己的定性分析视为下一步实证研究的序章,但他本人似乎从来没有亲自在这方面作出过努力。和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意见领袖”、“两级传播”相比,默顿提出的这些更具张力和想象力的概念和理论假设为什么缺乏后来者的响应和继续开掘呢?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默顿的理论发展与后来成为传播理论主流的实证效果研究范式、有限效果论不相符合,对于实践界来说,这些理论不仅没有实用价值,其中包含的道德批判锋芒甚至令人避之不及。
其次,默顿的传播研究远远溢出了传播过程本身,而更关注文化、意识形态及社会结构问题。这些理论不像有限效果理论那样,聚焦于传播的片断,而是将传播问题作为社会学问题的一个表征。在传播研究学科化过程中,这样一种倾向显然不利于凸显传播研究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所以,它们会被作为非传播学的问题或者传播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被还给社会学或人文学科。
最后,默顿提出的这些理论假设,尤其是他花了很大篇幅论述的“意识形态安慰剂”、“伪礼俗社会”、“地区性影响力人物”、“世界性影响力人物”等概念,在实证研究中很难被操作定义、测量和检验。如果对比同样研究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就会发现后者以“社会地位”、“生命周期”、“合群性”三个指标定位意见领袖,不仅对于实践更有指导意义,也更容易测量。
三、中层理论的困境
如果以笼统的中层理论概念来评价,默顿的传播研究还是比较具有启发性的,它向上连接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向下则与具体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比如,在罗维尔项目中,“地区性影响力人物”和“世界性影响力人物”这两个核心概念直接来源于卡尔·C.齐默尔曼在翻译滕尼斯对“地区的”和“世界的”所作区分时使用的术语;史密斯研究中,“伪礼俗社会”概念及相关分析也明显受到迪尔凯姆、西美尔、马克思等经典社会学家的影响。如果我们将默顿的传播研究作进一步延展和抽象便可以提出“作为符号的传播”,这为后续的不少研究打开了空间。这种理论的想象力以及对于传播的独特理解体现了默顿作为社会学理论大家的能力。
克罗瑟斯曾评价说,“很少有人能够以一种既能抓住社会结构运行的本质特征,又能避免过多的历史特殊性或保留某些制度领域特有风味的方式来推销社会理论,中层理论策略的一个难点在于以最佳的抽象度和经验关联度表达理论的艺术,而这也是为什么默顿所列举的理论几乎都是他自己的理论的原因”(Crothers, 2020:61)。
但如果以更为明确且苛刻的标准来评价,默顿的《大众说服》和《影响的模式》并不算成功,因为它们对于传播现象的限定比较宽泛,很难用实证主义的经验数据加以验证。而就默顿中层理论方案的公开表述而言,他恰恰提倡的是严苛意义上的中层理论。这与其实际操作相反。
总体来看,默顿关于中层理论的论述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中层理论的概念笼统、暧昧,更偏向实证主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默顿对于“证实”的强调,也表现了他对中层理论的最终期待。默顿希望通过中层理论的中介,实现对帕森斯所说的概念体系的搭建。默顿强调,尽管概念对于经验材料具有重要作用,但概念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社会理论也是“鲜活的和演进的社会学思想”,它受事实的压力而始终处于演化之中,“理论不仅仅是品位的问题,而且不论起点是什么,如果科学方法被加以运用,都会通过事实的压力而朝着兼容理论的方向而去”,一系列社会学思想所能表现出的“可能模式”就包括“死胡同、趋同(有意识和无意识)、分歧、累积”(Swedberg, 2019)。
不仅如此,他还将社会学的发展与物理学等学科进行比较:“……在二十世纪自然科学与二十世纪社会科学之间差着数十亿个人时的坚持不懈、训练有素的累积研究”(默顿,1968/2008:58-60)。这一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期待后来也出现于施拉姆、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的反思中,也是这一时期科学统一运动的原动力,其中著名的代表就是贝雷尔森和斯坦纳(Gary Steiner)出版的《人类行为:科学发现成果》(Human Behavior: An Inventory of Scientific Findings)。
但果真能够如此吗?以后见之明来看,这项工作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充满困难。休伯特·摩斯·布列拉克(Hubert M. Blalock JR)提出,由于多元因果(multiple causasion)的存在、非接触测量(indirect measurement)的必要、缺乏普适常数(universal constant)以及高度可重复事件等问题,都使得我们在基本概念的定义及测量上难以达成一致,也很难在构建理论系统的方式上达成一致。事实上,经过默顿所说的概念澄清和提升抽象程度,最后发展出科学法则的过程中会遇到的方法论困难要比他预想得更大(Blalock Jr, 1990)。如前文所言,即便默顿本人反复将对史密斯的研究视为一次探索性研究,并希望它能够为后续的实验研究提前铺路,但他本人并没有从事后续的工作。从认识论角度来讲,这一任务也充满困难。如果我们承认事实是概念图式的结果,那么仅使用“科学方法”是否就能跨越不兼容的概念和理论图式?
比照默顿的具体研究实践与其在中层理论中的公开承诺,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默顿中层理论的方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理论取向对于经验研究的重要作用,似乎经验中会自动产生理论,这是其“乐观的”中层理论的基础。
与这种忽视一致的是,默顿的中层理论方案也几乎没有涉及“知识究竟是什么”、“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是否以及有何差异”等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特纳也观察到,默顿在讨论方法论问题时几乎并未涉及自己对于科学社会学议题的思考,也并没有涉及韦伯、齐美尔等欧洲学者留下的方法论遗产。由此,特纳批评说,这正是整个哥伦比亚社会学所试图做的——创造自己对于这些经典方法论议题的答案(Turner, 2009)。叶启政也批评说,美国社会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不涉及社会学作为一个学门的知识“本质”以及其可能具有的种种后设命题(叶启政,2018:14)。
不过,以默顿本人对上述学者的了解以及从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他不可能忽视这些思想传统。如果深入到更多细节中去,我们会发现默顿对于经验、理论问题的认识似乎远比他在中层理论中所显示出来的要更为深刻。比如,在默顿这一时期教授的“应用于社会研究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Applied to Social Research)这门课上,他就没有止步于其公开宣称的一般理论“仅仅为经验探索提供着最宽泛的框架”这一轻描淡写的说法。对于事实,默顿不仅引用了韦伯的观点,指出事实不是所有存在的东西,而是具有选择性的;他还引用了劳伦斯·亨德森(Lawrence J. Henderson)对于事实的定义,“根据概念图式对于现象的经验可验证的陈述”(Swedberg, 2019)。在这一点上,默顿与帕森斯恰恰是一致的(帕森斯,1937/2012:46)。
但是矛盾的是,如果事实只能是某一概念图式下的事实,那么我们又如何寄希望于通过事实的累积或者“科学”方法的运用来推动社会学朝着物理学等“成熟学科”的方向发展呢?
因此,中层理论的困境就在于,如果承认理论的重要作用与知识的建构性——事实上,这是必须承认的——那么就意味着无法实现默顿对于社会学的自然科学式的期待;而如果严苛追求知识的可验证性,那么就不得不舍弃对更为宏大的问题的关注,严格限制问题的范畴,这又容易使得研究陷入琐碎经验主义的危机,而且即便是这样,也并不等于我们就能够取得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成就。默顿有关中层理论的“言”强调的是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有关中层理论的“行”则强调对宏大问题的关注。默顿言语意义上对中层理论终极目标的规划不仅客观上难以实现,而且以“行”观“言”,可以发现言语意义上的规划似乎也并非默顿的本意。相反,真正令默顿感兴趣的,恰恰是一些具有批判性与价值关怀但却很难在实证意义上确证的宏大问题。
四、另一个默顿:调停者还是牺牲者?
这些疑点都指向一个更为复杂的默顿。一个猜测是,默顿对一般理论取向的模糊态度,以及对确证知识的追求、对宏大理论的尖锐批评,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对于社会学科学化的期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其彼时的知识身份有关,也与其所处的美国社会学的知识氛围
有关。
按照叶启政的归纳,20世纪20到30年代是美国社会科学史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整个研究的基本走向就是量化与反规划性论述的“科学”方向,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叶启政,2018:39)。这种走向与美国社会学本身的实用主义、受自然科学影响、注重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等因素有关(叶启政,2018:39-40)。而早在默顿对宏大理论和琐碎经验主义研究提出双重批评之前,美国社会科学界就已经对这些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回顾详见叶启政的《实证的迷思》以及特纳等人的《不可能的科学》(The Impossible Science)。
总的来说,默顿与更加青睐方法论工具制造的拉扎斯菲尔德能够同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本身就是当时美国社会学经验取向与理论取向两派彼此分离,尔后又相互妥协的结果,当时也正是战后美国社会学老一代学者退休、新生力量得以迅速崭露头角的时期。为这段合作神话所强调的一个细节是,默顿与拉扎斯菲尔德这两位拥有完全不同学术背景和学术兴趣的人此前互不相识,甚至都从未听说过对方(Merton, 1987)。这当然不是事后夸张的说辞,默顿出身于哈佛大学,师从社会学家索罗金、帕森斯和萨顿等,并广泛吸收了涂尔干、齐美尔、马克思等欧洲社会学传统思想的影响(Simonson, 2004:xiv)。
不过至少从表面上看,两人的合作是和谐的。一方面,对于当时正在转型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来说,正面临着与商业机构的亲缘关系,研究过于琐碎、过于量化而缺乏理论性等批评,默顿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对于研究局的批评(Morrison, 1976:367-369)。另一方面,以社会学理论家的知识“介入”经验研究,默顿也将自己的知识身份定义为一个“带有经验倾向的坚定的社会理论家”(Swedberg, 2019)。整个20世纪40年代,默顿在从事经验传播研究的同时,也深耕于“理论”、“知识”、“方法”等相关议题(什托姆普卡,1986/2009:39)。比如,他在这期间就开设了上文提及的专门讲授如何理论化的研究生课程“应用于社会研究的社会理论”(1942-1954),教授学生如何“将经验材料转化成社会学”(Swedberg, 2019)。两相结合,哥伦比亚大学与研究局也出现一波明显的思考经验与理论结合的热潮。莫里斯·斯坦(Maurice R. Stein)提及这段研究生岁月时就说,当时的学生在研究“如何同时拉动理论、方法之马”以及“理论和方法各自又是如何运作”的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Morrison, 1976:328)。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默顿提出了中层理论的知识建设方案。因此,即便是一种调和方案,但它更多反映的是经验研究的立场,反对的则是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在此情况下,强调一般理论取向的强大作用无疑是颇为奇怪的;而呼吁回归经验以推动社会学的发展,亦很难再承认可能存在多元并存的社会学解释。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默顿在其中层理论方案中忽视了理论与经验的复杂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一般理论取向的重要作用。
理查德·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甚至认为,默顿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理论化课程或只是为了对二战后哥伦比亚大学出现的新型社会学做出贡献,而这并不是他自己感兴趣的那种社会学——实际上,默顿许多重要的研究并不是基于系统数据,比如未预期结果、自我实现的预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意外之旅等(Swedberg, 2019)。而默顿的确曾经说过,“对于理论建构来说,经验研究相比于其他观察而言是否具有更大的刺激作用,这是个开放的问题”(Swedberg, 2019)。客观而言,默顿本人也从中获得学术声望。对此,贝雷尔森就说:
我并不是说默顿本人有什么样的动机,但结果就是默顿从中获得了一些积极的好处……当你环视哥伦比亚大学想要找到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时,拉扎斯菲尔德不可能是那个人,而默顿成为最后可能获得这一称号的人……他从拉扎斯菲尔德和帕森斯那里都获得不少……他“把两个传统结合起来”(转引自Morrison, 1976:328-329)。
不过,我们当然不能将默顿综合两个传统的努力全然归于谋求学术资本。比起这种解释,本文倾向于将默顿看作介于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种形象之间,一方面默顿的游移的确受制于其当时的知识身份,另一方面也很难说默顿本人对科学化知识没有期待。客观而言,默顿这种“居间”状态是颇为珍贵的——一方面它避免了宏大理论的抽象而亲近经验,另一方面它也从一开始就使默顿与机械的实证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说,就理论与经验的连接而言,默顿的传播研究是颇为成功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与经验之间始终是双向互惠的关系。理论的追求首先将默顿导向对社会结构文化和功能问题的分析而不仅仅聚焦于说服的效率问题,但与此同时相关分析也相当谨慎地建立在对经验材料的把握上。事实上,默顿对于一些未能达到理论要求的研究,都不会允许出版,比如其在研究局负责的一项关于住房项目的研究就因此而未能问世(转引自胡翼青,2012:83)。
但默顿这种“居间”状态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它不仅使得默顿在《大众说服》等具体研究实践中显得颇有矛盾,也使得中层理论颇为模糊。正是前期实证主义的这一面,使得默顿及其中层理论的方案遭受批评。比如,布尔迪厄对默顿的方案就颇有不满。对于经常被问及的为什么布尔迪厄从来不提出任何中层理论的法则,布尔迪厄回应说,中层法则首先是一种满足实证主义要求的做法,而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满足正是科学必须予以拒斥的东西(布尔迪厄,华康德,1992/1998:132-133)。
类似地,尽管吉登斯认为默顿的方案是有益的、合理的,并且启发了一代学者,但还是想将社会学召回一个宏大的问题(grand question)。他认为中层理论的失误之处就在于预设了它自己要比更加包罗万象的理论探索更容易“验证”(test),这种把“可验证性”等同于“将(研究)限制在某一范围”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想法(Giddens, 1987:42)。
到20世纪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不断遭到批评之后,默顿本人的立场开始有所修正。在1975年的《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Structure Analysis in Sociology)这篇文章中,默顿重新明确将其中层理论与库恩的范式理论及相关科学哲学的理论关联起来进行讨论。其中,默顿再次强调了多元范式对于社会学发展的益处,而结构主义也仅仅被视为社会学的一种范式(Merton, 1975:39-52)。
科罗瑟斯也观察到默顿的这种转变,他将其归纳为:开始强调经典社会学传统对于当代社会学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强化社会学“人文主义”的面向;弱化了功能主义分析作为社会学主要方向的强调,认为社会学是多元化的,不同理论取向推导出来的理论是互补的而不是不可通约的;更加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发展阶段不同的问题,也是两者研究对象的本质差异,并由此呼吁社会科学应该将历史博学与当代知识界的研究取向相结合(Crothers, 2020:57,59)。但是,观察默顿本人的传播经验研究,就会发现这种转向实际上一直处于潜在状态。
五、重思中层理论及其知识后果
如果我们将默顿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理解为是想要为美国社会学做出贡献的话——或者创建社会学的哥伦比亚模式的话,那么客观而言这一知识方案及其被后来者强化的版本的确给美国社会学带来了一些知识后果。有研究者就指出,默顿的中层理论方案再加上拉扎斯菲尔德以及斯托弗(Stouffer)等人的实践,使得美国社会学对于理论的界定越来越狭窄,古典理论研究在此情况下几乎成为绝响(叶启政,2018:11),“社会思想史”也被赶出社会学(Turner & Turner, 1990:124)。
即便是作为“无可救药的理论家”、“宏大理论家”的帕森斯实际上也与此前的理论家不同。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所做的是从过去的理论中提取成分以建构其系统工程,并力图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这与传统的社会思想史的理念是不同的(Turner & Turner, 1990:121-123)。作为一个异国的、后入场的社会学者,布尔迪厄曾以“卡皮托利神殿之三神”来比喻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的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这三位重要人物(布尔迪厄,2017:73),他们构成的“强大的美国主流社会学传统”——其特征是功能论结合经验实证的变项因果研究,尤其是以中层理论的形式——尽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受冲击,但直到20世纪末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叶启政,2018:11)。
传播学领域亦是如此。从默顿传播经验研究的亲身实践来看,他本人显然更偏向于概念的建构和质化经验研究,他本人也将自己称为一个“长期的定性研究者”(Swedberg, 2019),这是他对理论与经验进行连接的基本方式——尽管默顿也屡次想要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确证。在《大众说服》中,深入的焦点访谈在经验材料的挖掘以及理论解释方面就扮演了重要作用(默顿,1968/2008:200)。其中,默顿特别强调保证焦点访谈的开放性。③这与《人际影响》产生区别。在《人际影响》中,作者说“在所有这类研究中,最后的结论是要对研究对象的行为进行回溯,找出‘动机’、‘原因’或是‘决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泛泛地去问‘为什么’毫无意义。这个问题应该被转换为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以发现某些特定的因素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176)。结果导致更希望开展深入访谈的前期项目负责人米尔斯被解雇,这成为传播学史上的著名公案(秦艺丹,2018)。
在这一点上,默顿与霍夫兰的差别更加显著。对于霍夫兰实验法的说服研究,默顿也曾颇为直接地指出,“控制实验法的结果只能表明宣传对于人们的某种态度的净影响,而不能表明导致这种净影响的比较复杂的原动力……采访材料使我们能够对在实验的结果中可能表现不出来的反应进行心理学的解释”(默顿,1968/2008:676)。在默顿看来,相比于实验法,焦点访谈的优势是更能够接近人们实际生活经验的“现象学层面”,它的用处在于其能够产生新思想和新假设的源头(Merton, 1956/1990:xxi-xxii)。
但遗憾的是,在施拉姆正式建立传播学后,整个学科日益朝着量化研究方向发展,焦点访谈等其他经验研究方法被边缘化。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就发现施拉姆列出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在理论上都非常敏锐(theoretically astute),但却不是宏大理论家,同时都是熟练掌握方法论的量化倾向学者(Peters, 1986:546)。施拉姆对于传播的界定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非经验性的反思与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关系(Peters, 1986:544)。当施拉姆回忆起《大众说服》的时候,曾非常惊喜地说,“对我来说,《大众说服》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像默顿这样的理论家也可能会对媒介研究产生足够的兴趣,直至亲身操作。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拉扎斯菲尔德有效地起到了研究催化剂的作用”(施拉姆,1997/2016:68)。
以中层理论以及社会学大师默顿的加盟为外衣,传播经验研究迅速获得学术正当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证研究方法与中层理论逐渐剥离(胡翼青,2010)。传播研究领域便持续处于渴望但又始终难以实现的理论焦虑中——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到1983年《领域的躁动》专刊的卷首论文中,施拉姆依然对传播研究未能形成议题“集中而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从而能够“统一”(unify)传播研究者的学术思考而倍感忧虑(王金礼,秦艺丹,2016)。如果我们上述论述大体不误的话,这一知识的焦虑恐怕会一直存在。
但是,默顿的传播中层理论与后来逐渐被建构起来的效果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存在两个明显的区别。其一,默顿的传播中层理论所处理的经验现象更为宏观,远远超出了“谁对谁说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的传播模式。其二,如果以现在的标准进行衡量,默顿的传播经验研究更多的是阐释主义而不是实证主义的。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基本上都是质化的。从默顿的亲身实践来理解他的中层理论,我们可以避免将默顿中层理论的方案与狭窄意义的实证主义捆绑。
当下的语境与默顿提出中层理论的语境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默顿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中层理论主要是想规避社会学理论脱离经验的风险的话,也许在今天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端的琐碎经验主义,在此意义上我们恰恰更加需要珍视默顿作为社会学大师赋予理论的优先权。这种理论优先权体现的不仅仅是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延展,更体现在理论本身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关怀,这从根本上与仅关心效率问题的专家型学者划开界限。
具体到传播研究,我们今天已经具有了很多与默顿标准类似的中层理论,但是如何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提出更宏大的理论?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却好像与此渐行渐远。这里面当然有默顿的影响,但这却并不是他的本意。因此,重访默顿、反思默顿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或许能让传播研究走出舒适区,突破这种自我设置的限制。■
注释:
①其中1位被调查者无法纳入这四个分类中的任何一个。
②“行为的宣传”是默顿在该研究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设。比起人们究竟是否购买债券,默顿更在意的一个细节是很多人都认为史密斯是真诚的。但实际情况是史密斯并不“真诚”,她经常出现在各种商业节目中,并且在默顿研究的这次直播节目中,史密斯更多地将债券购买描绘成神圣的爱国行为而不是经济的投资行为,且丝毫没有提及销售战争债券的真实经济目的在于应对经济膨胀。默顿发现,人们之所以认为史密斯真诚,多是缘于史密斯长达数小时的坚持。也就是说18小时的连续广播合法化了史密斯的真诚性。由此,默顿提出“行为宣传”(propaganda-of-the-deed)的假设。有趣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史密斯的劝说恰恰是富有效果的。
③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取一手经验材料,默顿等在焦点访谈环节设计了非常严格的程序,比如每次访谈大约进行3-4个小时。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很少询问直接、预设的问题。访谈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非指向性的”,它允许被访者对他们自己的关注点以及这些关注点对他们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报告。只有当被访者汇报完自己的反应之后,访谈者才会从事先基于内容分析得出的访谈指南中提出新的问题,并开始下一轮谈话(Merton,1946:14)。
参考文献:
彼得·什托姆普卡(1986/2009)。《默顿学术思想评传》(林聚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翼青(2010)。传播实证研究: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新闻与传播研究》,(3),9-16+108。
胡翼青(2012)。《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赖特·查尔斯·米尔斯(1959/2005)。《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海龙,秦艺丹(2023)。在效果研究与批判理论之间:默顿与早期传播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1-11。
罗伯特·默顿(1968/2008)。《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1992/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2002/2017)。《自我分析纲要》(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塔尔科特·帕森斯(1937/2012)。《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王金礼,秦艺丹(2016)。重塑传播研究的知识边界——美国《传播学刊》专刊“领域的躁动”的思想史解读。《现代传播》,(8),47-53。
威尔伯·施拉姆(1997/2016)。《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王金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阎鹏(1992)。真正的知识超越国界——访当代社会学大师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社会学研究》,(3),1-6。
杨念群(2004)。当代中国历史学何以引入中层理论。《社会观察》,(7),34-35。
叶启政(2018)。《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伊莱休·卡茨,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1995/2016)。《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张宁译)(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lalock Jr.Hubert M. (1990).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ClarkJ.Modgil, C. & Modgil, S. (Eds.). Robert K. Merton: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pp. 387-398). London, New York & PhiladephiaPA: Falmer Press.
Bourgeois IIIL. J. (1979). Toward a method of middle-range theoriz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3)443-447.
CrothersC. (2020). Reintroducing Robert K. Merton. Routledge.
Fleron Jr, F. J. (2016). Russia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Views from metatheory and middle-range theory. LanhamMD: Lexington Books.
Giddens, A.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atzE. (1957). 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An up-to-date report on an hypothe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1(1)61-78.
McGranahanDonald V. (1947)Reviewed work: Mass persuasi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 war bond drive.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1(2)266-268.
MertonR. K. (1948). Discus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4-171.
MertonR. K.FiskeM. & KendallP. L. (1956/1990). Focused interview: A manual of problems and procedures.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MertonR. K.FiskeM. & Curtis, A. (1946). Mass Persuasi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 war bond drive.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MertonR. K. (1975). Structural analysis in sociology. In Blau, P. M. (Eds. ).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PP. 21-52). New York, NY: Fress Press.
MertonR. K. (1987). The focused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s: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51(4)550-566.
MorrisonD. E. (1976). Paul Lazarsfeld: The biography of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or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eicesterLeicesterUK.
PawsonR. (2000). Middle-range re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41(2)283-325.
PetersJ. D. (1986).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4)527-559.
SimonsonP. (2004). Introduction. In Merton, R. K.FiskeM.& Curtis, A. (Eds. )A. Mass persuasi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 war bond drive. New York, NY: H. Fertig.
Smith, J.Bealer, R. C. & SimF. M. (1962).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ommunic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SSy32(1)10-15.
SwedbergR. (2019). How do you make sociology out of data? Robert K. Merton’s course in theorizing (Soc 213-214).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50(1)85-120.
TurnerS. & Turner, J. (1990). The Impossible science: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TurnerS. (2009). Many approaches, but few arrivals: Merton and the Columbia model of theory construc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9(2)174-211.
刘海龙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秦艺丹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本成果受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