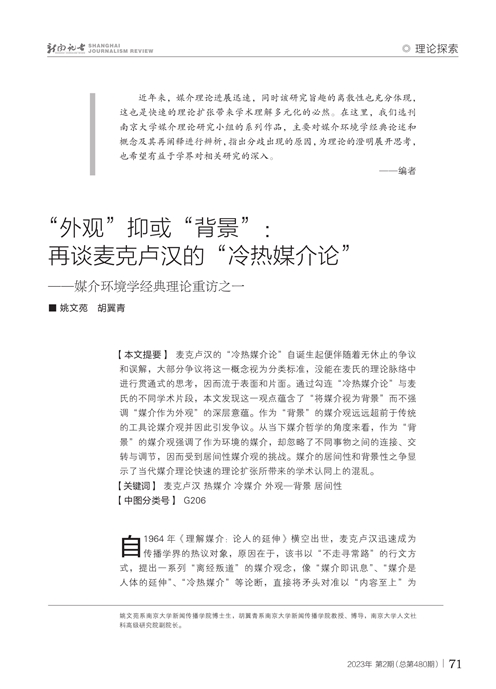“外观”抑或“背景”:再谈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论”
——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一
■姚文苑 胡翼青
近年来,媒介理论进展迅速,同时该研究旨趣的离散性也充分体现,这也是快速的理论扩张带来学术理解多元化的必然。在这里,我们选刊南京大学媒介理论研究小组的系列作品,主要对媒介环境学经典论述和概念及其再阐释进行辨析,指出分歧出现的原因,为理论的澄明展开思考,也希望有益于学界对相关研究的深入。
——编者
【本文提要】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论”自诞生起便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议和误解,大部分争议将这一概念视为分类标准,没能在麦氏的理论脉络中进行贯通式的思考,因而流于表面和片面。通过勾连“冷热媒介论”与麦氏的不同学术片段,本文发现这一观点蕴含了“将媒介视为背景”而不强调“媒介作为外观”的深层意蕴。作为“背景”的媒介观远远超前于传统的工具论媒介观并因此引发争议。从当下媒介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背景”的媒介观强调了作为环境的媒介,却忽略了不同事物之间的连接、交转与调节,因而受到居间性媒介观的挑战。媒介的居间性和背景性之争显示了当代媒介理论快速的理论扩张所带来的学术认同上的混乱。
【关键词】麦克卢汉 热媒介 冷媒介 外观—背景 居间性
【中图分类号】G206
自1964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横空出世,麦克卢汉迅速成为传播学界的热议对象,原因在于,该书以“不走寻常路”的行文方式,提出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媒介观念,像“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冷热媒介”等论断,直接将矛头对准以“内容至上”为准则的主流大众传播学研究,几乎挑战了当时所有人的媒介观。在这些论断中,“冷热媒介论”无疑是争议最大的一条,哪怕在“讯息论”、“延伸论”至少在表面上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的今天,“冷热媒介论”仍然深陷争议的泥淖,甚至连麦克卢汉的坚实拥趸和信徒内部都没能达成一致。像麦氏理论的捍卫者罗伯特·洛根(Robert·K. Logan)就难掩对该理论的厌弃和反对,直言“冷与热对于理解新媒介并不是有用的分类法”(洛根,2012:325)。但是,享有“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之称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则竭力捍卫冷热二分法的有效性,盛赞其为“了解新媒介最有用的工具之一”(莱文森,2014:207)。
相较于麦克卢汉阵营内“两极分化”的争议,“冷热媒介论”在麦克卢汉阵营外几乎引发了一边倒的恶评。一些学者完全否定这一论断的合理性。譬如,唐纳德·菲斯曼(Donald A. Fishman)言辞犀利地表示(2006):“冷/热媒介并不是进行有意义的分类的可靠基础,这一理论是肤浅的,前后不一致的。”另一些学者则从理论性和实用性的视角评判其合理性。例如,乔治·道格拉斯(George H. Douglas)认为,冷热二分法是一种修辞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虽能够自圆其说,但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推广和应用(Douglas,1970)。而麦克卢汉曾经的信徒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甚至因不赞同麦克卢汉将“电视”归为“冷媒介”的分析而与其“反目成仇”,多次出言挑衅并著书攻讦,以至麦克卢汉不厌其烦,不得不公开回应。①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正是意识到学界的恶评,麦克卢汉罕见地改变了往日“只探索,不解释”的风格,在《理解媒介》第二版序言中对“冷/热媒介”进行了专门的回应和补充阐释(麦克卢汉,2011:10),但由于他延续了一贯的晦涩文风和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这样的解释似乎并未起到多大的效果,盘旋在“冷热媒介论”之上的争议仍然不绝于耳。那么,从媒介理论的角度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冷/热媒介”?这一理论是否因为不是一种有用的分类法就没有意义?这一理论的背后到底体现了麦克卢汉的何种媒介观,而这种媒介观为什么会引发大家的不适应?本文尝试将这一概念复归到麦克卢汉的理论脉络中,以媒介为入射角重访“冷热媒介论”,剖析其背后潜藏的逻辑,并基于当前的媒介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重构。
一、“冷/热媒介”为何?
与“冷/热媒介”所引发的错综复杂的争议相比,这一概念在《理解媒介》中的表述简洁明了到了极致,其定义紧紧围绕着“清晰度”(definition)和“参与度”(participation)两个子概念展开: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具有‘高清晰度’”,“并不留下那么多空白让接受者去填补或完成”;而冷媒介具有“低清晰度”,“要求的参与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麦克卢汉,2011:36)。循着这样的思路,麦克卢汉将电话归入冷媒介范畴,因为电话通话依赖低清晰度的、低频率的声音,并且必须通过通话双方的参与才能进行;像会话和言语也比较冷,因为交流时需要参与者充分利用身体手势,并结合在地情境展开互动;与之相对,收音机则“竭力提供完全的信号,不要求收听者补充”,因而是一种热媒介(林文刚,2007:138)。需要指出的是,麦克卢汉看似“杂乱”的论述实则潜藏着一种规律:大部分用于分析的媒介都是成对出现的,这意味着“冷/热媒介”是一个相对性和语境化的概念,所谓的“冷”或“热”基于比较而产生(Anton, 2015)。例如,照片比漫画更“热”,口语传统比印刷传统更“冷”,广播比电话更“热”。即便同一种属性的媒介,其冷热程度也有所区别,例如,无声电影比有声电影“冷”,但又比电视和广播“热”。
问题的关键在于,“清晰度”和“参与度”这两个概念给人们一种错觉,仿佛这是可以区分出“冷媒介”和“热媒介”的两个普适性概念。以中国学界的理解为例,凭着社会科学训练中进行概念界定的习惯,学者们会把这两个概念理解为可以用来进行一切媒介划分的科学标准。不少研究将“人的参与”当成理解“冷/热媒介”的关键切口(范龙,2011),认为只要牢牢抓住主体在现实中的互动和参与,就能辅证“冷”与“热”标准的合理性。还有一些研究则希望补充拓展“清晰度”和“参与度”两个指标,通过将前者区分为“抽象数据清晰度”和“具象数据清晰度”,将后者区分为“感官参与”和“知觉参与”进行细化(张景云,2011);或者从认知科学视角,从符号认知和信息维度糅合这两个子概念,试图将冷热二分扩展为适用于数字媒介的标准(白旭晨,2022);抑或将其拓展至视觉传播的维度,对“冷/热媒介”折射出的媒介技术关系进行技术理性的批判(李岩,2004)。这些视角看似在不同的维度丰富了“冷/热媒介”的内涵,实际上都是站在一种科学主义立场上的言说,都是罗伯特·默顿科学理性思维的传人。然而不幸的是,麦克卢汉是个不会写诗的印象派诗人,是个没有科学思维的人文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所以,麦克卢汉根本没有想将“冷/热媒介”作为一种媒介的分类标准,“冷/热媒介”仅仅是语境化的一种隐喻。
那么,当麦克卢汉谈论“冷/热媒介”的时候,他在谈论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到麦克卢汉对“冷”与“热”这两个概念的初始理解上。根据莱文森的考证,麦克卢汉划定冷热的灵感来自人对于不同爵士乐形式的体验:“热”的铜管乐喧嚣热烈,震撼人心;“冷”的速写乐则如“清风拂面”般扣人心弦,调动人的感觉与灵魂(莱文森,2014:20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冷”与“热”并不意指行为和行动上的参与,而触及不同媒介调动人之感官的方式和程度。这一点也见诸麦克卢汉对象形文字、拼音文字和印刷文字的分析:象形文字之所以是“冷”的,是因为它本身以相对具象的象征符号的方式表达意义,因而人需要充分调动多重感官知觉理解其意义;而印刷文字将拼音文字的视觉抽象程度推向高峰(麦克卢汉,2011:36),使人专注于调动视觉,进而抑制其他官能,将“感知体验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感官”(麦克卢汉,2014:220)。可以说,麦克卢汉延续了他一贯以来的技术(媒介)观:媒介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是影响人的感官比率,打破人体感官系统的平衡,人因此逐渐披上一层技术皮肤,获得技术加持。
麦克卢汉在论及媒介与人体感官的关系时提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麦克卢汉,2011:61)。“延伸”,意味着媒介技术引入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麦克卢汉,2011:18),对人而言,新的尺度就是某一种或几种感官比率的强化或放大,像望远镜便是增强了人的视觉,使人可以看到肉眼无法企及之物。“截除”,是因为“人体是各种器官构成的一个整体,维持和保护着中枢神经系统,是对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突然刺激的缓冲装置”。故而当技术介入人的感官系统,“延伸”其中一种官能时,保护性的中枢神经系统就会截除刺激性的器官、感觉或机能,以维持神经系统的平衡(麦克卢汉,2011:59)。可见,媒介以技术的形式延伸、外化人的感官,人自身的官能因此截除;更重要的是,媒介作用于作为“整体场”的感官系统,任何一种感官的外化都将引起整体感官平衡比率的变化。而“冷/热媒介”恰恰承接了这种“二律背反式”的思路:当媒介本身是“热”的,意味着它通过技术的方式延伸了人的多重感官,或强化了其中一种感官,人要么无需调动更多的感官系统去理解和认知媒介信息,要么专注于强化的官能而抑制其他感官,其结果都是:人出于自我保护回撤注意力和想象力,保持较低的参与度。反之亦然。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一概念似乎与常识理解不相匹配,即为何“冷”对应着“高参与度”,而“热”对应着“低参与度”——因为“冷/热媒介”实则意味着媒介与人体官能的互补与互构。
从感官的角度剖析“冷/热媒介”的概念,是理解麦克卢汉的重要切口,也有助于回应最令人费解的“冷电视”与“热电影”的争议:二者同样是呈现动态影像的视听技术,为何被纳入不同的冷热阵营?麦克卢汉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电影给观众提供的是一帧帧像照片一样高清晰度的、完整的形象,而电视是由“细节很少,信息度很低”的马赛克图像构成(麦克卢汉,2011:358),它处在射线和光点的不断构造之中,因而需要看电视的人“始终处在参与和补充的状态之中”(莫利纳罗等,2005:329)。在这个过程中,人实际上通过“深刻的听觉参与和触觉参与”去填补电视马赛克网络中的空隙(麦克卢汉,2011:359),即像用手触摸和摆弄物品一般不断探索和重构电视图像的轮廓,用自身的“感知系统组装电视形象的外观”(林文刚,2007:140)。也就是说,电视不像电影是视觉的延伸,而是听—触觉的延伸,后者“不是肌肤和实物的接触”,而是能够激发各种感官互动的“通感”(或称“联觉”)机制(麦克卢汉,2011:129),正因如此造就了电视的“冷”和观众的高度参与。
当然,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足以扫清笼罩在“冷/热媒介”之上的疑云,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为何偏偏电视就是“听—触觉”的延伸,又为何一定要执着地在“冷电视”与“热电影”之间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在麦克卢汉对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电子文化的不同态度中找到踪迹。在麦克卢汉眼中,不同的媒介不仅是在不同程度上延伸了人的感知,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后果,制造了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式的视觉延伸和电视式的听—触觉延伸自然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环境。他根据感官延伸的结果划定了三个媒介史分期,其中,口语社会创造了“受听觉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人们通过各种感官互动而达成平衡与同步,形成了可以深度共鸣的封闭部落文化;而拼音字母的出现破坏了这种原始的平衡,“视觉被置于感官系统的最高等级”,“牺牲了丰富的感官互动”,而谷登堡印刷术加剧了这种线性的、分割的意识,致使个人主义和专门化分工大行其道;与之相对,电子媒介则引发了一种新型的深度参与模式,使人回到自己与他人密切接触的状态,非集中化的、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就此生成(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63-370,376)。显然,麦克卢汉式的文化演进是技术延伸感官的结果,他向往一种感官平衡自处的原始环境,电子媒介则通过延伸和外化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被印刷术割裂的部落文化状态,复归了麦氏的愿景。
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下,麦克卢汉认为,电影观众通过镜头的方式观看,很难令人产生移情效应,而电视观众在观看电视时则变成了屏幕,图像成为他们的肌肤,可听可触,可感可知。麦克卢汉做出这样的推断是参考了一项“非洲土著居民无法接受电影却能够理解电视”的人类学观察,他对此的解释是将“电影”对标“书面文化”,将“电视”对标“电子文化”,前者的视觉逻辑沿袭自书面文化,因而破坏了感官的综合体系,使自然的移情效应“土崩瓦解”;而后者的听触感知则削弱了视觉所占的比重,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感官互动的领域(麦克卢汉,2014:107-108)。可以说,麦克卢汉树立了一个“电影稻草人”,目的在于凸显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如何使人“摆脱他们在书面文化中所习得的固定视点”和培养出来的想象立体空间的三维视像意识,在无意识的层面适应“共振的、同步化的二维平面的世界”(吴畅畅,2022)。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这个过程便是“再部落化”。所以,电影之“热”和电视之“冷”本质上是由技术所造成的两种不同文化的感官平衡状态和人的在世存有状态:“热电影”造就了其他官能急剧收缩的、线性的视觉性“工业人和机械人”,而“冷电视”复归口语传统的部落文化,创造了感官平衡互动、深度卷入和参与的“电子人”。因此,冷/热并非简单的媒介分类标准,而是人与世界相连互动的方式,而这个世界,就是由媒介延伸人之感官所创制的文化环境,或称媒介本身。
分析到这一步,“冷/热媒介”的意涵才算真正浮出了水面。麦克卢汉真正在意的,是媒介与人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通过影响感官平衡状态生成不同的环境,进而重新塑造人本身。因而,“冷/热媒介”其实鲜少关注一个个原子化的、固定的单个媒介实体,更无意于建立一套媒介分类标准,而始终强调任何环境如何根据事先接触的媒介而被体验为“冷”或“热”,以及这种温度变化如何发生的过程(Anton, 2015),其焦点在于媒介对人的建构及其文化后果。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像米勒一样以为麦克卢汉纯粹在分析视觉和听觉所蕴含的信息量差异(Jonathan, 1971:102);或像施拉姆那样因其无法用研究数据进行验证而对此嗤之以鼻(施拉姆,波特,2010:129),抑或从现代技术发展的角度否定其“冷/热媒介”划分。
这件事提醒学界:理解不仅仅只有科学主义这一种立场,自培根以来人们的学术思维方式不能被视作唯一的认识论。把所有媒介都放到“冷/热媒介”的标准下去衡量是否有特例,这是归纳逻辑的体现,也是平时所有国人选择题答题的一种技巧,但这样的逻辑把所有人都绑架并走向常识和经验,把所有学术问题都导向归类、评估、程式化和机械唯物主义。电视和电影到底是冷还是热并不重要,“冷/热媒介”是否是概念的划分标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出“冷/热媒介”的人到底是怎么理解媒介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麦克卢汉是对的,在非科学主义的立场看来,麦克卢汉的观点对不对这种问题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麦克卢汉对“冷/热媒介”的讨论到底显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媒介观。
二、“冷”与“热”:“外观”与“背景”的动态互动
在麦克卢汉的世界里,媒介总是互联着发挥作用,“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麦克卢汉,2011:40)。表音文字的升温伴随着表意文字的降温,其结果是线性思维的养成和文化时空的转换,神圣世界的社会形态和宇宙时空于是提升为去部落化或世俗的时空,并塑造了实用主义的人(麦克卢汉,2014:121);传统部落的石斧在“热技术”钢斧进驻后迅速降温,导致封建等级制度的瓦解与破裂(麦克卢汉,2011:37-38);19世纪给机械的、分裂切割技术加温,形成了整体和联合的意识,而电力技术则使其降温,并使社会走向非集中化(麦克卢汉,2011:51、55)。由此可见,“冷/热媒介”是相对于整体环境而言的过程性概念,媒介的温度总是处在与环境和文化的联通互动中。谷登堡印刷术诞生自低温的口语环境,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持续给环境升温,虽然口语交往并不会因此完全消退,但整体环境的温度还是为线性的、视觉性的、“热”的书面文化所奠定。简而言之,媒介可以“炒热”社会的整体文化环境,与之相对,“热文化也常常刺激冷媒介的兴起”,整个社会环境因此维持“恒温与平衡”(莱文森,2014:216)。
“冷/热媒介”与环境的勾连集中反映了麦克卢汉将单个媒介置于更大的整体中进行考察的思路,而这正是麦氏构建自身学理框架的关键所在,媒介“温度变化”的背后不仅蕴含着媒介形式区别于内容的力量,也隐含着更深层的“外观—背景”的关系。麦克卢汉借鉴格式塔心理学的概念,将所有情境划分为一个“受关注之处”(外观,figure)和另一个更大的“不受关注之处”(背景,ground),“外观与背景通过共同的边界或间隙产生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进而同时定义二者”(Mcluhan, Mcluhan, 1988:5)。在这种二元关系中,背景起到奠基性的作用,它产生于外观之前并塑造外观,但外观总是因意识中的在场而更受瞩目,从而遮蔽了背景本身。而背景的重要性在于,“任何技术和人造物的背景既是产生技术的情境,又是整体的环境(媒介);这个利弊同在的环境是技术带来的。这些影响是技术附带的影响;不管人愿意不愿意,它们都强加在人身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莫利纳罗等,2005:467)。以汽车为例,汽车延伸了人的速度,使人能够以独处的方式出门,但使人改变的并不是汽车本身,而是与汽车相伴产生的公路、石油公司、工厂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和服务,而汽车不过是“诸多服务背景中的外观”而已(麦克卢汉,2006:163)。所以,当麦克卢汉说出“媒介即讯息”的口号时,他实际上指涉由技术革新所创制的一整个隐蔽的服务环境,人以媒介为身体的延伸在这种背景中生存,来感知和理解外部世界的事物,而改变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东西并非技术,而是背景和环境。
简而言之,外观是可见的、在意识中在场的,而背景则是隐蔽的,为人所忽略的,外观的“显露”常常伴随着背景的“隐没”,但恰恰是后者起到结构性和奠基性的作用。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对物的观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海德格尔认为,当人与形形色色的物/工具打交道时,需要通过目的性、使用性的“操劳”与物建立一种“上手状态”,在这种具身关系中,物仿佛在人的意识中“抽身而去”,人与存在物的原初关联就此固定;只有当工具损坏之时,其本身才会变成一个陌生的认识对象,重新进入人的意识中(海德格尔,2018:89-92)。换言之,海德格尔眼中的诸物总是扮演着理所当然的工具角色,当人的意识放在其他事物中时,这些事物就会暂时被遮蔽或隐没在背景之中,直至它们“以某种方式出现功能障碍”,才会以可见表象的方式“猛然进入我们的意识觉知”(哈曼,2018:133)。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都试图在意向性的基础上理解技术与人产生关联的方式,并且都认同缄默的背景在构成生存环境时的作用(戴宇辰,2018),只不过,海德格尔在意的是技术以何种方式“解蔽”事物的存在或真理,物之存在在背景中的隐没是一种纯粹的意识缺席,并不关涉其他;而在麦克卢汉那里,外观与背景不仅意味着意识和知觉空间的转换,还可能形成动态演进的关系,进而以不同的方式延伸人体,重塑周遭世界的关系结构。正如演讲时人的注意力可能从演讲者的话语转向他的手势或电灯的嗡鸣声,转向街头来往的车马声或回忆、联想和气味,外观和背景并非铁板一块,因为“外观产生于背景之中,复又退回背景”,“每一个新的外观都可能取代其他外观而成为背景”(Mcluhan, Mcluhan, 1988:5)。
正因如此,麦克卢汉批评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忽略了外观与背景的交互,因为后者仅是抽象和模糊地运用这一概念,泯灭了其动态性、不连续性和异质性(Mcluhan, Mcluhan,1988:63)。那么,外观与背景交互到底如何发生?这就不得不提及麦克卢汉在其遗作《媒介定律:新科学》中提出的“四个定律”:媒介提升(enhance)或增强了什么?新媒介使哪些事物过时(obsolesce)?又再现(recur)了哪些先前的行动和服务?当新媒介被推向极致时,将逆转(reverse)成何事物(Mcluhan,Mcluhan, 1988:99)?在麦克卢汉看来,这四个过程同时发生,互为补充,它们共同揭示了新技术对原有模式的挑战,并且适用于“一切人造物”。其中,“提升”和“过时”在媒介研究中最为常见,就像货币增强了交易的便捷性,催生了统一的定价服务,淘汰了传统的讨价还价和以物易物模式;照片增强了绘画的清晰度和真实度,使肖像画过时;计算机加快了计算和检索的速度,淘汰了簿记员(Mcluhan,Mcluhan, 1988:100)……“提升”意味着新的经验和生活方式,更伴随着新背景的生成;“过时”也不只是简单地淘汰或扬弃某些事物,而是使旧背景成为外观。另一方面,“逆转”则是因为“媒介被填满了过多的细节和信息”,以至“过热”超越其界限,所以逆转为其对立面(哈曼,2018:227);“再现”则体现在新媒介取代旧媒介的过程中,此时的旧媒介褪去背景身份,重新为新媒介所挪用,成为一种用于怀旧或展示的艺术或美学外观(Mcluhan, Mcluhan, 1988:5)。
由此观之,“冷/热媒介”与环境温度的动态互渗一方面体现了背景的形塑力,“冷”与“热”实则隐含着不同技术进驻原有媒介场域后对整体社会文化结构产生的变革性影响,这是背景层面的革新。“每当社会开发出使自身延伸的技术时,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功能都要改变,以适应那种技术形式,一旦新技术深入社会,它就立刻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制度中”(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62)。而这种技术渗透将改变社会的交往模式、教育模式和感知模式,创造一种新的环境(麦克卢汉,2011:40),也即催生一种新的温度和一种新的背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外观与背景的交互作用,因为媒介的冷热是促使外观与背景相互转化的关键:当旧媒介“遇冷”,就会从背景变成外观,新的媒介形式将默默从旧媒介手中接过塑造社会文化的权力,隐身为基础性的背景;而一旦媒介“过热”,也可能触发生活方式(或背景)的深层逆转,就像汽车本该延伸人的速度,为人提供出行便利,最终却造成了拥堵和骇人的车祸;或如19世纪的去部落化推进到极致,便激发了再部落化的潜力,而电子媒介以新技术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Mcluhan, Nevitt. 1972:24),这恰是电视之“冷”的缘由——印刷术“过热”导致媒介逆转,使社会复归古老的、参与式的口传文化。
所以说,麦克卢汉口中的媒介“冷”或“热”并非因内容而生,与信息的不同属性和结构也关系不大,而是因隐没的媒介背景而生,在新旧媒介技术的交转中涌现,在外观与背景的交互中生成。在这个意义上,“冷/热媒介”承接了麦氏最为旗帜鲜明的“媒介即讯息”的思路,将目光从媒介的信息效应转移到媒介本身的变革性作用,从媒介功能转移到媒介的社会组织性,从外观转移到背景。正因如此,麦克卢汉犀利地反驳了施拉姆主持的电视节目研究,后者将“节目”和“内容”之外的电视视为中性的媒介(麦克卢汉,2014:244),像技术白痴一样仅关注“如何使用媒介”(麦克卢汉,2011:29),却没能意识到,是潜藏在内容之下的这种深层的媒介威力重塑了人的感官比率,才进一步形成了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与环境之间的温差。不难发现,当美国大众传播学对内容推崇备至,孜孜不倦地测量内容的效果和功能时,他们只看到了显在的外观和表象,却忽略了作为背景的媒介技术对文化的深刻影响和雕塑,难怪麦克卢汉会将这类研究形容为“失于全局观察,未能发现媒介运作原理和力线”的“鸵鸟政策立场”(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60)。以此类推,如果以信息和符号的方式理解“冷/热媒介”,无疑是用外观的方式理解背景,或是用可见的表象指称不可见的结构,其结果势必南辕北辙。
必须承认,由于麦克卢汉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这一概念确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连其本人也在回应一个诘难者时承认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他说:“各种各样的‘热’与‘冷’的悖论模式,指向一个新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法分类的……既然‘热’和‘冷’不是分类,而是过程,不是观念,而是感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索媒介,我们的办法是注意视觉剥夺其他感官的结果”(莫利纳罗等,2005:500)。而“冷”与“热”的悖论性就体现在,过去文化中的“热现象”在今天被形容为“酷/冷”(cool),而1900年之前用以表示“拉开距离、不感兴趣、不去卷入”的“冷”则对应着无线电技术分割知觉,形成专门化的个体意识之后的“热”(莫利纳罗等,2005:500)。因而,源自俚语的“酷/冷”(cool)本身表达着“热”的含义,“热”也很快会“遇冷”。根据洛根的说法,由于“冷”、“热”的表述本身并不稳定,因而麦克卢汉本人对此也不甚满意(洛根,2018:55)。但若因此而称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之后已然放弃这一概念也过于武断,因为麦氏始终立足于“作为背景的媒介形塑外观”的思路内核,努力地更新与丰富这一概念,而媒介与环境的温度互渗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体现为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电子文化的不同感官平衡状态;在《把握今天:出局的行政执行官》中是新旧媒介、身份的更迭和过热媒介的逆转;在《媒介定律:新科学》中则是外观与背景的动态演进。不得不说,“冷/热媒介”是连接麦克卢汉的学术脉络,在哲学语境中发掘其媒介思想的关键钥匙。
三、作为居间的媒介和作为背景的媒介
“冷/热媒介”最终与媒介四大定律汇流成一套“媒介科学”,这彰显了麦克卢汉的学术野心,也再次佐证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借助媒介“冷”、“热”的变化过程,媒介与环境、外观与背景之间得以相互转化,进而形塑人与人所在的生活世界。围绕“冷热媒介论”的诸多争议大多未能深入考察此概念与麦氏更深层媒介观的关联,因而流于表面和片面,事实上,“隐没的媒介背景”和“可见外观”之间的关系才是麦克卢汉的终极命题。
媒介环境学会前会长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曾经如此诠释麦克卢汉的思想:“媒介环境的观念,是把媒介视作一种包围或弥散的物质,它不是在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连接二者,而是用一个圈包围两点,就像鱼儿在水中游动,人在空气中生存一般”(Lance,2010:74)。这番论断的高明之处倒不是他对“媒介环境”的概括,而是他无意间将两种理解媒介的思路——“作为背景/环境的媒介”和“作为连接的媒介”放在了同一个坐标系,而后一种“居间性”恰恰是“媒介”(medium)一词的原初意涵。简单来说,“居间性”其实是任何媒介的共有属性,它既指媒介是“在两种程度、数量、质量、阶段之间起调节作用的东西”,即一种“中间位置”;也关涉单个媒介物所具备的象征性或物质性,即媒介物的属性(米歇尔,汉森,2019:4)。与之相对,无论背景、环境抑或生态,背后都蕴含着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而作为“居间”的媒介特征在于连接、交转和调节,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相较于斯特拉特的“无心之举”,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观念在格拉汉姆·哈曼(Gramham Harman)那里产生了交汇的可能性,而后者借助的理论工具恰恰是“冷/热媒介”与媒介定律。哈曼察觉到,麦克卢汉虽然将媒介视为一种背景,却疏忽了另一种“起到中介作用的媒介”,而正是对内容(即外观或中间物)的轻视和对背景的过分聚焦,才导致麦克卢汉错失后一种媒介视野,并长久地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淖(哈曼,2018:220-221,229)。因而,哈曼试图在“客向本体论”的思路下发掘麦氏思想中的“中介观”。他认为,麦克卢汉眼中的媒介只有通过“逆转”和“再现”的方式才会发生转化:正是内容意义上的“信息、细节或者数量的过度渗透”导致媒介“过热”而发生逆转,而再现则是“让死去的媒介经历‘过冷’的过程”,以至其向死而生,重新以鲜活艺术媒介出现在新环境中;由于两种转化都发生在外观层面,所以可以说是“外观的表层事件触发了背景的逆转”,也即媒介的内容改变了媒介,使外观与背景颠倒,“终止其原初的历程”(哈曼,2018:231-232)。概言之,虽然人常常被可见的外观所蒙蔽而无法接触背景,但人可以通过外观,通过引起媒介的过冷或过热,间接地接触并控制我们认识之外的背景和媒介环境,如此一来,外观便成了人与背景之间的媒介(哈曼,2018:233)。
哈曼借助“冷/热媒介”提出的“外观即媒介”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不过,他煞费苦心地重新诠释麦克卢汉,更多是为了佐证其事物间接联系的物向本体论,而他对“中介”的理解也停留在连接两个实体物的初始内涵上。但他确实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居间者的媒介物的力量,开启了一条从“作为居间的媒介”关照“作为背景的媒介”的崭新道路。而在本文看来,两种媒介观有无必要汇流、为何汇流的问题,必须回到麦克卢汉媒介观所生发的大众传播学语境中进行分析。
从其学术旨趣来看,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与其余诸论一样,都是对当时主流大众传播学观念的纠偏,目的在于驳斥将媒介视为“透明容器”、“中性传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主义定势思维,首肯媒介自身的技术逻辑和符号逻辑。当然,麦克卢汉反对的并不是内容本身,而是根植于其中的“只见外观而不见背景”的思维方式,所以,早在《理解媒介》问世前10年,他就直言“‘大众媒介’一词的使用令人遗憾”,因为它无端将传播设定为“信息、讯息或思想的传输”,却忽视了“传播的形式是基本的艺术情景,艺术情景比信息或‘传输’的理念更为重要”(戈登,2016:167)。通过分离形式与内容、外观与背景,麦克卢汉确实建立了一套发现媒介威力的强大逻辑,借此,他相继预见了电子媒介压缩整个世界时空,推动集体参与的“地球村”、人人成为表演者并陷入全景监视空间的“全球剧场”、封闭人意识和精神的“全球膜”(朱豆豆等,2022),由此可见“作为背景的媒介”的诠释力与生命力,而这恰恰是困囿于表象的大众传播学所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
在麦克卢汉的世界观里,“结果走在原因前面,背景产生在外观之前”(麦克卢汉,2006:134),而他从“背景”入手反思大众传播学“外观取向”和“工具取向”的媒介观可谓是切中肯綮,但这样的反思带来了新的问题。哈曼指出,没有任何主体可以直接认识一个实体的全部,他以对岩石的理解举例:“地质科学并不能完全认识岩石的存在,因为岩石总是有实在的存余,比我们拥有的关于岩石的最全面的知识都要深——但是我们在建筑工地上使用石头和我们在街上争吵时使用石头都不能穷尽其功能。这种结果并不是因为人或者动物意识具有令人惋惜的局限性。相反,岩石并没有彻底展开,或者因为任一行动或关系被穷尽”(哈曼,2018:44)。如果把哈曼的这个观点看作是物向本体论的起点的话,那么哈曼就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麦克卢汉一旦选择了从“背景”的角度来理解媒介,恐怕就无法再有效地从“外观”的角度来理解媒介,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效地将这两种媒介观统一或汇流在一起。因为我们在建筑工地上使用石头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以我们在街上争吵时的方式使用石头。当我们讨论媒介作为中介物进行连接时,其实并不等同于讨论媒介作为背景物的嵌入和渗透,而当我们讨论媒介作为背景物的嵌入和渗透时,也并不等同于讨论媒介作为中介物的连接和前景关系的生成。而这恰恰是媒介的“波粒二象性”,顾此就会失彼,但它们又彼此联系。
当讨论作为外观的媒介时,研究者当然会以媒介居间性为当然的理论视角,认为一切社会场景的建构和生成都以媒介为前提,否则人们甚至无法通达其所在的世界。“技术的传媒却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经验的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克莱默尔,2008a:7-8)。这种媒介等于世界的判断就必然导向媒介本体论:“社会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以媒介为起点,中介化与被中介化的整体存在。正是因为媒介,世界被建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存在者。媒介之外,别无他物。以媒介为起点的社会存在方式使研究者普遍看到了从生成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媒介本体论的可能性”(胡翼青,马新瑶,2022)。而当讨论作为背景的媒介时,情形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时候,媒介的具身性就体现出来了,媒介以透明化的方式出现,其外观比如媒介界面中的内容恰恰用以遮蔽媒介本身,只有当媒介物失灵的情形出现时,作为背景的媒介才会出现。作为背景的媒介在不知不觉中调试着我们的生活。这两种尽管有关联,但视角和结论可能完全相反的关于媒介的“第一哲学”,恰恰说的都是媒介。
“居间性”的问题在于无法看到媒介的多种角色,因此在麦克卢汉看来,什么是居间,这会是一个问题。但如果从“居间性”入手,麦克卢汉这种“作为背景的媒介”的媒介观可能遭到这样的反驳:他只看到将不同事物容纳其中的环境,却忽略了不同事物之间的连接、交转与调节,所以他很难从媒介作为背景的角度意识到媒介与人体的关系应该是“媒介是人的连接点,人体也是媒介的连接点,展现的是技术与人和世界的关联”(黄旦,2022)。但这不是麦克卢汉的问题,只是他理论视角的必然局限。与之相比,立誓与媒介环境学划清界限的“媒介生态学”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居间媒介的灵活性,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挪用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资源,发掘复杂媒介系统之间的动态关联,即“对媒介生态中的一系列介质组成进行逐一考察,以期建立一种能够理解其性状及其相互关系的方法”(富勒,2019:14)。由于捕捉到了媒介“在不同场景中渗透连通、构建关系的能力”,富勒所构建的“媒介系统”就与静态的“媒介环境”拉开了距离,前者内部充满能量的流动和物质交换,不同媒介因可供性的差异与其他媒介相互生成,相互通达,形成一种生成性的、动态性的媒介生态,而非后者那种稳定的整体形式(胡翼青,李璟,2022)。
尽管如此,麦克卢汉从作为背景的媒介入手来理解媒介,在20世纪60年代简直相当于在中世纪僧侣的寺院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那些将实证主义奉为神学的传播学者被炸得不知所措。这一观念太过超前,根本是那些把媒介理解为机构和组织的实证主义者无法想象的。在实证主义看来,媒介就是工具,甚至是个玩具,怎么就成了决定存在境况的决定性力量,又怎么就成了活生生的动力漩涡?对此,抵抗者只能从科学分类依据不科学的角度去反驳,而被唤醒者也只能试图用科学验证的方式去证明他的每一个具体结论,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对“冷/热媒介”的感受和讨论。不过,很快就有学者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麦克卢汉在做什么。基特勒非常感慨麦克卢汉对他的启发,但他惊讶地发现,麦克卢汉找到了正确的起点却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麦克卢汉原本可以在媒介本体论上走得更远,但他却回到了“感官比率”和“人体延伸”这些问题上。于是在多个场合,基特勒批评麦克卢汉“没有必要将所有媒介都挤向人类感觉器官的瓶颈”(杰弗里·温斯-扬,2019:147),还认为麦克卢汉“对感官的了解要胜过他对电子学的了解,因此他会试图依据身体来思考技术而不是依据技术来思考身体”(Kittler, F., 2002:29,转引自杰弗里·温斯-扬,2019:147)。在这一点,基特勒可能更好地捍卫了海德格尔的视角和方向。笔者同样认为,麦克卢汉将媒介作为背景的哲学思想用之于“冷/热媒介”的讨论,有点不伦不类,还因之将自己的结论导向了自身出发点的反面。
正如彼得斯所说,“麦克卢汉的很多观点今天也站不住脚了,但这不是因为它们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而是因为从上世纪60年代这些观点第一次被提出时就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一直以来,我们阅读麦克卢汉是为了从他身上获得灵感,而不是严格推敲他的学术水平”(彼得斯,2020:19)。麦克卢汉对科学主义的抗争是他给人带来灵感的根本原因,但他的奇怪旨趣同样来自于他与科学主义割舍不掉的关联。幸运地摆脱了培根爵士,麦克卢汉怎么也没能摆脱斯宾塞爵士。躲过了数理逻辑,麦克卢汉没有躲过功能主义、心理学和进化论(甚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这三者都是自然科学征服人文社会领域研究对象的重要手段。即使在当代人类学和社会学那里,“感官比率”也是一个高度科学主义的概念,而“媒介延伸论”则直接导向功能主义。麦克卢汉坦言自己与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殊途同归”(莫利纳罗等,2005:322),并颇为赞赏汉斯·哈斯对“人创造额外器官的能力”的论点(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562-563)。但这些人几乎完全是在生物进化和功能完善的意义上论及“研究人就是研究其延伸”,像霍尔就将延伸的唯一目的视为增强生物体的机体功能和实现内在与外在的共同进化(霍尔,2010:34-36)。当麦克卢汉将这种“延伸观”应用于媒介分析时,他其实并未指明“是谁的延伸”(“技术”还是“媒介”),只是在“延伸什么”(从“功能”转向“中枢神经系统的官能”)以及“延伸的结果”(延伸产生隐秘的背景)上动了手脚,这种混同“媒介”与“技术”的伎俩很快被克莱默尔发现并招致其批评:“麦克卢汉因此加入人类学的观念中,即根据两极图式功能性等价模式来概括人与技术的关系”,于是“传媒所显示的东西”,就变成了“传媒所造成的某种技术人工物”(克莱默尔,2008b:66-67)。
除此以外,麦克卢汉还受到系统论和生态学的影响,这导致他在理解媒介环境时也同样出现了“科学主义”的倾向。“将媒介理解成一种生活环境”和“将媒介理解为一种狭隘的技术实体或系统”原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米歇尔,汉森,2019:5),但麦克卢汉恰恰在这一点摇摆不定,媒介既是塑造人之生活生存环境的“背景”,又是一个个具体的实体物,概念上的暧昧不清最终导致其原本充满睿智的整体性的背景隐喻在波兹曼等媒介环境学派手里土崩瓦解。
结语
重访“冷热媒介论”,不是为了给麦克卢汉正名,也无意于逐一反驳盘旋之上的无休无止的争议,而在于追问媒介观及其分歧的根源。事实已经证明,“冷热媒介论”在今天的阐释力已经日暮穷途,因为在当前的媒介实践中,数字技术已然改写了大众传播时期的技术逻辑,仅凭一套强大的二进制系统,技术不仅能将图像、声音、文本等内容转化成统一的数据流,而且能通过界面使人卷入数码网络之中,将人也变成数据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任何一个节点位置的改变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瞬间改写整个关系网络的样貌,也正是在这样的连接、中介和交转过程中,世界得以形成,媒介才成其为媒介。所以,媒介并非通过“延伸”人的感知而产生了环境,而是在“居间”和“桥接”不同事物的过程中“生成”了整个世界,并以这种方式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当人与技术相互纠缠共生,以节点的方式生存在“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的社会,就不可能只有感官比率受到影响,而在于全身心的外化和转化,如此情境下仅以“冷”、“热”论之,无异于蚍蜉撼树。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麦克卢汉。哈曼曾给麦克卢汉冠以“哲学家”的身份,强调麦克卢汉的重要价值不只是因为他是“媒介理论家”,还因为“哲学最终可能只不过是媒介理论而已”(哈曼,2018:219)。就当前的媒介研究发展趋势来看,这一判断正在不断成为现实,事实上也对媒介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今天来看,媒介理论从其元理论层面就出现了诸多分歧。媒介的居间性和背景性正在形成两种无法融合和汇流的媒介哲学,甚至连居间性和居间物、背景性和背景物的讨论都没有达成共识,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焦虑的问题。媒介理论能够保持对话的有机性和通约性吗?笔者认为,如果要保持这种有机性和通约性,我们就必须要先知道深层次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分歧双方分别看到了大象的哪个部位,就如媒介的“外观”与“背景”之争一样。■
注释:
①乔纳森·米勒是BBC的导演和编辑,他曾在一档节目采访中自称是麦克卢汉的“热情信徒”,并将麦克卢汉比喻为弗洛伊德,获得麦克卢汉的赞赏。但在“冷/热媒介”上的分歧导致米勒与麦克卢汉渐行渐远,后者多次写信与麦克卢汉商榷,还在《聆听》杂志上多次投稿发表异议。起初麦克卢汉还能耐心进行解释并多番回应,但米勒充满主观偏见的解释和立场的倒戈最终让麦克卢汉恼羞成怒,因而在米勒出版《麦克卢汉评传》之后称其为“反麦克卢汉的十字军”。这段往事可见诸《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版》第470-471页、《麦克卢汉评传:信使及媒介》第166页。麦克卢汉对米勒的回应和评价可见诸《麦克卢汉书简》第362、500、503、505、507-511页。
参考文献: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2021)。《麦克卢汉精粹》(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爱德华·霍尔(2010)。《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白旭晨(2022)。信息维度:理解冷热媒介的认知转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9),26-32。
保罗·莱文森(2014)《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第2版)》(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戴宇辰(2018)。“在媒介之世存有”:麦克卢汉与技术现象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0),82-96+127-128。
范龙(2011)。“主体间性”视域中的人媒交互与共生——麦克卢汉“冷热媒介”学说新解。《国际新闻界》(07),19-22。
格拉汉姆·哈曼(2018)。《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海德格尔(2019)。《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胡翼青,李璟(2022)。媒介生态学的进路:概念辨析、价值重估与范式重构。《新闻大学》(09),1-13+117。
胡翼青,马新瑶(2022)。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考察。《新闻记者》(01),66-76。
黄旦(2022)。延伸:麦克卢汉的“身体”——重新理解媒介。《新闻记者》 (02),3-13。
杰弗里·温斯-扬(2019)。《基特勒论媒介》(张昱辰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李岩(2004)。视觉传播中的技术理性批判——来自麦克卢汉“冷媒介”说的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04),34-40+95。
林文刚(2007)《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伯特·洛根(2012)。《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罗伯特·洛根(2018)。《被误读的麦克卢汉——如何矫正》(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2006),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2011)。《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2014)。《谷登堡星汉璀璨》(杨晨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马修·富勒(2019)。《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麦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梅蒂·莫利纳罗,科琳·麦克卢汉,威廉·托伊编(2005)。《麦克卢汉书简》(何道宽,仲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特伦斯·戈登编(2016)。《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2010)。《传播学概论.2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W.T.J. 米歇尔,马克·B.N.汉森(2019)。《导言》。载W.T.J. 米歇尔,马克·B.N.汉森编,《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3-12)(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吴畅畅(2022)。“人人都是一台精神机器”:麦克卢汉媒介观隐藏的线索。《新闻与传播研究》(05),5-23+126。
西皮尔·克莱默尔(2008a)。《传媒、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有何关系》,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1-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皮尔·克莱默尔(2008b)。《作为轨迹和作为装置的传媒》,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64-8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2020)。《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景云(2011)。麦克卢汉“冷”、“热”媒介悖论:基于“清晰度”与“心理参与”的研究。《国际新闻界》(05),35-40。
朱豆豆,王淑花,高慧敏(2022)。北美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选择性译介及学术盲点——以麦克卢汉和哈弗洛克为例。《国际新闻界》(08),111-128。
Anton, C. (2015). Hotter Than and Cooler Than: Reappraising McLuhan’s Hot and Cool Distinction. 16th Annual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Denver, CO ,US. Retrived from: https://mcluhangalaxy.wordpress.com/2015/07/05/reappraising-marshall-mcluhans-distinction-between-hot-cool-media-by-corey-anton/.
Douglas, G. H. (1970). THE HOT AND COLD MEDIA PRINCIPLE: Theory or Rhetoric?.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27(03)339-344.
Fishman, D. A. (2006). Review and criticism: Research pioneer tribute—Rethinking Marshall McLuhan: Reflections on a media theoris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50(03)567-574.
Jonathan M. (1971). Marshall Mcluhan. US: New York . the Viking Press Inc.
Kittler, F.(2002). Optical Media:Berlin Lectures 1999. Anthony(trans.).UK:Cambridge. Polity Press.
Lance, S. (2010).Studying Media as Media:McLuhan and the Media Ecology Approach. In Paul Grosswiler(ed.) Transforming McLuhan: cultural, critical,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67-80). New York: Perter Lang Publishing Inc.
McLuhan, M.Nevitt, B. (1972). 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McLuhan, M.McLuhanE.(1988).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姚文苑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胡翼青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