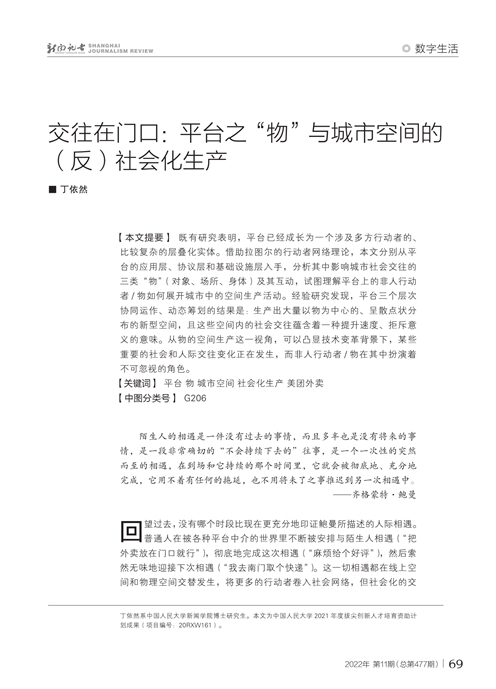交往在门口:平台之“物”与城市空间的(反)社会化生产
■丁依然
【本文提要】既有研究表明,平台已经成长为一个涉及多方行动者的、比较复杂的层叠化实体。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本文分别从平台的应用层、协议层和基础设施层入手,分析其中影响城市社会交往的三类“物”(对象、场所、身体)及其互动,试图理解平台上的非人行动者/物如何展开城市中的空间生产活动。经验研究发现,平台三个层次协同运作、动态筹划的结果是:生产出大量以物为中心的、呈散点状分布的新型空间,且这些空间内的社会交往蕴含着一种提升速度、拒斥意义的意味。从物的空间生产这一视角,可以凸显技术变革背景下,某些重要的社会和人际交往变化正在发生,而非人行动者/物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关键词】平台 物 城市空间 社会化生产 美团外卖
【中图分类号】G206
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是一段非常确切的“不会持续下去的”往事,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在到场和它持续的那个时间里,它就会被彻底地、充分地完成,它用不着有任何的拖延,也不用将未了之事推迟到另一次相遇中。
——齐格蒙特·鲍曼
回望过去,没有哪个时段比现在更充分地印证鲍曼所描述的人际相遇。普通人在被各种平台中介的世界里不断被安排与陌生人相遇(“把外卖放在门口就行”),彻底地完成这次相遇(“麻烦给个好评”),然后索然无味地迎接下次相遇(“我去南门取个快递”)。这一切相遇都在线上空间和物理空间交替发生,将更多的行动者卷入社会网络,但社会化的交往行为却不必然被生产出来,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临时交往地带:拼车时共享的前后排座位、小区楼下的快递柜、餐馆的取餐柜、学校铁栅栏后的外卖架,以及一个个不足一平方米的被称为“门口”的区域。
换言之,在当下城市空间中,平台参与打造了一系列新空间。最直接的,淘宝、京东等交易平台改造了原有的城市运输和交付系统,使得人们不再前往邮局等固定的物理实体机构收寄快递,而逐渐习惯在一定时段内从小区内或门口的不同快递车、快递柜自取邮件。无论是相对固定的快递柜,还是具有一定容量、需要移动前往交付地点的快递车,都成为平台参与打造的新型空间。此外,各领域的服务平台已逐渐成为确保人们日常生活正常运行的组成部分,使人们进入由数层新程序包裹的“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之中(van Dijck, Poell & de Waal, 2018),也预示着多元空间的涌现。那么,平台是如何生产出这类空间的?
2014年,刘涛用多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讨论了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现多译为“社交媒体”)的空间生产过程。一个例子是,“在微信的‘摇一摇’中,如果两个人同时摇动手机,两个陌生的空间便极具戏剧性地建立了某种微妙关系。当一个空间被其他空间所识别、所认领、所发现,它便从其原始的属性和状态中抽离出来,进入社会关系领域,这一过程对应的正是空间的社会化生产”。不可否认,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协助人们建立连接,但两人所处的陌生空间是否被互相识别、认领,乃至“进入社会关系领域”却不得而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跳跃,很可能是由于,“当人们手握手机浏览社交媒体时,吸引他们的是屏幕上的文本,手中的手机此时似乎‘抽身而去’……无疑忽略了作为基础设施的计算机、通信技术以及身体的知觉经验等传播的物质性基础”(丁方舟,2019)。 在不了解两人的意图、缺乏其他行动者信息的背景下,仅仅凭借微信的“摇一摇”功能和人的共时参与,我们无法确保二者能够产生能动的交集,因而也无法判断其空间生产的结果。
不过,上述案例肯定了媒介再造空间关系的能力。除社会化媒体外,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都有可能成为具有自主性的“物”的力量,参与到现实的建构之中(Couldry & Hepp, 2018)。为此,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平台的空间生产活动中,有哪些关键的“物”的行动者?它们的活动空间是如何被拓展的?这种物质性实践对其所对应的人际交往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研究视角与理论向度
晚近十年,学界出现“物质性转向”的思潮(Mukerji, 2015),传播学者开始从技术、身体、空间、话语等方面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等对象的物质性维度。不过,遵从不同的理论源流,当前学界对“物质性”的理解、关注点差异较大。例如,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认为物质性就是支持传播行为的基础设施等物品,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理解(如Murdock, 2018);基特勒(2009)强调媒介和物质技术自身较为稳定,且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与之相比,“新物质主义”代表学者布鲁诺·拉图尔(2005)的观点独树一帜,他提出,要以关系主义本体论打破主客二分,将自然的历史、物的历史和一切生物摆放到和人一样的位置。“不仅去考察人是如何能动地使用物,也去考察物是如何能动地‘利用’人”(戴宇辰,2020)。
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关注社会联合(association)和关联(connection)的过程(Latour, 2005),提倡人与非人都可以成为行动者。平台中的“物”(包括技术物和以物理形式存在的各种物)通过“转译”(translate)等方式制造差别,改变事物的状态,因此也属于行动者。孙萍(2020)在对外卖平台的研究中考察了电动车的速度、外观形态、电瓶等物,它们不仅同时拓展和限制了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还影响了“平台经济外延媒介的加速过程”以及“平台资本形塑快速消费意识形态的过程”。丁未(2014, 2021)先后研究了攸县的哥和滴滴司机使用的无线电装置和刷单软件等物,发现前者在一定时间段内帮助移动农民工社群建立了身份共同体,而后者则帮助早期进入平台经济的司机成为补贴大战中的数据生产者和盈利者。Boyd(2014: 53,57)发现,脸书等社交媒体上支持美国青少年在隐私与公开之间横跳的可供性设置,帮助他们摆脱了父母的监视、同辈的羞辱,而非拓展他们的社交圈子。不过,很大程度上,上述研究虽然看见了物,但侧重点仍是“人如何能动地使用物”(例如外卖骑手剪断限速线、攸县的哥自发给无线电调频组成空中共同体、青少年基于技术可供性调整隐私设置),至于物如何“利用”人或者操弄、影响其他行动者这一面向尚不十分清晰。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给人和非人行动者/物的行动之间划定先后顺序。相反,使用行动者网络就是为了克服传统的、线性的逻辑关系,强调“一种集体行动的结果”(Latour, 1986:265),关注“诸行动者的多重互动”,因为“它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时间、空间、目标、手段和目的”(Latour, 1996:173)。以此逻辑,我们有必要给非人行动者/物同等的关注。
那么,如何理解平台上的非人行动者/物的物质性?首先,平台是“利用市场中介地位,凭借数据、算法和算力,通过互联网连接生产者和用户,并从供求匹配中获取佣金的经济组织”(齐昊,李钟瑾,2021),西方学者将其更简单地界定为“数字化基础设施”(斯尔尼赛克,2018)。但无论是从界定方式还是平台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平台都已成长为一个涉及多方主体的、比较复杂的层叠化实体(layered entities)(Langlois, 2006):对用户而言,平台可能是一个支持交换信息或完成交易的功能界面,因而用户习惯从自身需求出发判定某平台的功能和效用。对平台技术员和算法工程师而言,平台要包揽存储数据、交互设计、软件程序运作以及接入各类协议的性能,以更好地服务于用户和平台自身发展的需求。此外,平台的运行还得益于各种物理的、信息的乃至人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其中,物理基础设施包括电动车、网约车、道路、高架桥、保温车和手机支架等设备,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等设施(国家发改委,2020),而作为基础设施的人则主要指向为平台工作的媒介化的劳动力状况(丁未,2021)。由此可见,在平台的应用层、协议层和基础设施层中分别存在着大量的非人行动者/物。
目前学界对于平台的理解也大致以上述三个层次中的某一点作为切口。其中,对平台应用层的讨论往往介于界面和其使用者之间,较少以其他非人行动者/物作为研究焦点(如Andriessen & Vartiainen, 2006; Jansson, 2021; Goulden, 2021)。例如,Rosenblat和Stark(2016)提出,变换的算法使得被监控者很难察觉、无从把握,因而掩盖了劳动剥削。对平台协议层的研究更多地与批判理论对话,试图揭示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或对人的异化作用(如Zuboff, 2015;胡泳,2019; Lin & de Kloet, 2019)。例如,格雷和苏里(2020)指出,亚马逊机器人(Mechanical Turk)等众包平台的API接口设置偏向“卖方市场”,同时平台对劳动者匿名化和原子化的技术设置进一步使其陷入孤独、不可见、被压榨的困境。而对基础设施层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获得国内学界关注,其物质属性和市场、政府规划等更为中观层面的分析单位产生关联(如陈龙,孙萍,2021;Delfanti, 2021;束开荣,2020)。这些研究具有较强针对性,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平台的某种技术在某一层面对人、社会、劳动、时空秩序等对象产生的影响。但其问题在于,对平台应用层、协议层和基础设施层的切割不免将平台视为“一个静态的物”(a static object),这与拉图尔的意图相违背。从拉图尔(2017)的主张出发,平台应该被视作一个“动态的筹划”(a moving project)。平台的各个层次的设计、使用、优化总是与其发生关联的行动者产生互动,并产生影响。这启发我们在理解平台之物的物质性时动态地关注平台三层次之间的联系及与之关联的关系网络。
此外,凝结着整套动态关系的网络平台被放置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时,发挥着不同作用。城市空间有其特殊性。列斐伏尔强调城市空间的生产性是一个基础性要素,就其内涵而言,空间生产包括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前者“通过改变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分布,从而实现空间‘重构’,来实现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提升”(庄友刚,2010)。例如,在城市空间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成城市工厂、铁路、运河等空间结构的建造,它们又反过来为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齐埃利涅茨,2018:30)。后者指在前者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空间的扩张”(庄友刚,2010)。列斐伏尔(1996:101)指出,城市是生产、社会关系作用的处所,而非一种单纯的物质性产物。由于空间中的生产影响着社会生活空间本身的生产,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城市空间中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城市生活的速度与繁忙。这种关系正如延森(2016)所言,某个物质性特质在促成社会交往形式的同时,也可能对人产生限制。
上述城市空间生产的两重内涵使得列斐伏尔对城市的描摹具有了一种整体观的面向,即“城市不是一定数量的人口、一种地理位置或者建筑群的一个集合……它是所有一切的合成”(Lefebvre, 1991:145,148)。因此,城市空间便以一种“结果”的姿态呈现自身(Lefebvre, 1991:73),其间囊括着其所生产的物和各种社会关系。这一观点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形成了某种互文,也凸显出此种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合成性特质。
戴宇辰(2020)基于物质性的建构主义路径,归纳了影响城市社会的、互相交织的物的“类别”:其一,城市中充满具体社会互动发生所借助/面对的“对象”(object),其中包括科技产品、人造物和自然物。在此种意义上,平台所调用的各种交通工具、装置、手机等物即为“对象物”。其二,城市中有大量承载社会互动发生的“场所”(place),例如广场、公园、交通枢纽和购物中心等。支撑平台存续的“大厂”、平台工作者往返停留的商铺和家属区,以及共享单车和电瓶车充斥的交通道路都可被视为这类“场所”。其三,面对面互动中个体的“身体”也包含物质性维度。这既涉及身体的生理性属性,也囊括其社会化属性。前者的案例如健康状况不达标的外卖骑手无法完成平台分配的工作。而身体的社会化属性涉及个体的着装、品位、认同、价值观等。例如,骑手的社会交往行为可能随着他/她对平台或外卖行业认识的加深发生变化。
综上,为比较清晰地说明问题,本文将分别从平台的应用层、协议层和基础设施层入手,分析其中对城市社会互动起限制作用的三类“物”(对象、场所、身体)及其互动,试图理解平台上的非人行动者/物如何展开城市中的空间生产活动。
二、研究问题与资料来源
通过上文的文献梳理,本文试图从物的视角来切入平台的空间生产研究,并据此提出以下问题:
1.在城市中,平台各个层次上的不同类别的“物”的行动者如何拓展活动空间?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国内传播学界对平台物质性的讨论主要还是从“物”本身的物理性质及其对人类行动者的影响出发,以“物”的空间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验考察尚不丰富。
2.依托平台产生的空间在社会交往方面具有什么特征?这个问题试图从空间中的生产过渡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进一步将物同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实践网络勾连。
基于此,本文选取一个中国的典型平台“美团”进行经验分析。美团平台的前身是于2010年始创的美团网。2010—2018年间,美团平台逐步推出电影票线上预定、酒店预订、餐饮外卖及配送等服务。2018年,美团确定“Food+Platform”(“食品+平台”)战略,对组织体系进行升级(美团企业官网,2021)。从市值和平台对用户日常生活的影响力综合评估,美团都可被视为头部平台之一。①
本文着重讨论与空间问题联系较紧密的外卖配送服务。
研究的经验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依循本·莱特等人(2018)提出的“漫游方法”(walkthrough method)考察美团平台的界面、技术机制以及文化指标,以此理解平台应用层的非人行动者/物如何形塑用户经验。二是研究者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就该议题所撰写的观察笔记。期间研究者选择总计一个月的时间段,有意识观测自己、周围人在点外卖时与平台的互动表现,并在每次观测后写作观察笔记。外出吃饭时,研究者亦随时记录了商铺与外卖员的互动过程。同时,研究者还以北京海淀区某小区为主要区域,观察外卖员在城市空间中的行动动线和互动行为。这部分材料用于理解平台基础设施层的非人行动者/物所产生的影响。三是美团研究院和其他国家相关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及问卷数据,用以理解平台方如何设计和完善平台的应用层和协议层。国内新闻媒体所生产的事实性材料与媒体话语则作为对局部观察的补充材料。笔者在这些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交叉验证和统合分析。
三、平台之“物”的行动者及其空间生产活动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即便平台的不同主体处于不同层次(应用层、协议层和基础设施层)上,它仍应被看作一个“动态的筹划”。因此,本文首先尝试绘制出美团外卖平台空间生产大致涉及的动态关系网络(图1 图1见本期第73页),并在下文中针对各层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分层讨论只是暂时将单个层次作为着眼点,实际上三个层次的运作相互依赖和勾连,无法截然分开,在下文中会有更清晰的说明。
(一)应用层
如前文所述,对于用户而言,平台往往只是一个支持交换信息或完成交易的功能界面,用户习惯从自身需求出发判定某平台的功能和效用。作为主要人类行动者的用户的身体状态和所处地点不会对这种交互产生太大影响,因此本节主要讨论对象类“物”的运作和影响。
在应用层,最直观的对象是交互界面。交互界面的设计和优化深受协议层的影响。根据平台收集的用户数据和市场调查情况,交互页面变得日益对“用户友好”。以旨在辅助用户决策的知识图谱②领域为例,它在用户端呈现为包含筛选项、特色标签、榜单、推荐理由等信息的页面。美团平台搜索团队已经将其对用户需求的调查和了解融入页面呈现当中:
筛选项的维度受当前查询词对应品类下用户关注的属性类别决定,例如,当用户搜索查询词为薯片时,用户通常关注的是它的口味、包装、净含量等,我们将会根据供给数据在这些维度下的枚举值展示筛选项……商品的推荐理由通过评论抽取与文本生成两种渠道获得,与查询词联动,以用户视角给出商品值得买的原因,而榜单数据则更为客观,以销量等真实数据,反映商品品质。
——《美团商品知识图谱的构建及应用》
每样商品背后都有复杂的图谱体系支持(图2 图2见本期第74页),而用户的认知、偏好都是在其中占重要比例的要素。
呈现在具体页面上,鼓励用户快速“选择”即为平台的首要目标。打开美团点击“外卖”选项,首先跳入眼帘的是一份打开的具有较短天数时效的“大额红包”,刺激用户抓紧时间享受优惠。关闭红包页面后,占领上半个屏幕的是“美食”、“甜点饮品”、“蔬菜水果”等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细分品类,下半个屏幕则罗列着具体商品信息。用户经常点选的商品很可能排列在靠前位置。在每一条商品介绍中,按照显眼顺序(根据占据屏幕面积、位置、字号、字体颜色评判)可将信息排列为:商品图片/店铺logo图片、商品名与分店名称、商品/店铺优势(如“海淀区螺狮粉回头率榜第3名”、“大众点评高分店铺”、“回头客多”、“近期3399人下单”、“近30天280人复购”等)、评分和满减信息、销量与人均价格、起配送费、配送时间和距离(图3 图3见本期第75页)。
这些信息足够专业、具体、直接,且很大程度上是量化的,帮助用户专注其需求。在此氛围中,即便外卖的抵达涉及商家、骑手、用户等多方,用户却几乎只需关注“我”的需求,即我喜爱的口味、我愿意花费的价格(可以凑单满减)和我能够等待的时间。用户在这一阶段对相关各方的认知可以从下面这段观察中体现出来:
晚上8点15分左右,文文准备点外卖,她说想吃辣的,且很快决定吃螺蛳粉。她之前已经多次点过这个品牌的外卖。过了十多分钟,我问她是否已经点完外卖。她说要等到9点再点,因为她有一张限时段使用的满40减15的“夜宵神券”。她凑好单,等待9点付款。9点之后,我进入美团,发现在附近可以搜到两家该品牌的螺蛳粉店铺,距离分别为3km和4.5km,我问她点了哪一家。文文说4.5km那家,因为凑单下来距离远的那家反而更便宜。(2021.12.04)
此外,界面也是用户掌握骑手动态数据和催单的窗口。在等餐时,呈现在用户眼中的是一张二维地图。如果当天有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地图上方也会出现相应画面。骑手被标示为一个身着黄色制服,带着头盔和口罩、骑着电动车的卡通形象。在他上方的信息框标注着“骑手已到店/正在送货/即将到达,距您X千米/米,X分钟”。由于美团总是会在顾客点餐时提供一个精确到分钟的送达时间,在那时用户会格外关注骑手动向。五仔就常因为赶时间盯着地图界面咒骂:“这家伙咋停到那了,600多米路走多久了,不是一拐就到了吗?马上超时了,他敢先点送达我就举报他。”
Baez(2013)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社会认知加工过程中,个体要聚焦和整合相关的情境信息和社会线索,才能产生对目标刺激的理解。这些情境包括面部表情、物理场景、声音、他人的肢体动作、语言等(Barrett, Mesquita & Gendron, 2011)。那么,当除了“我”以外的情境都被呈现为二维卡通图像,诸如骑手逆行/伤亡、道路曲折难行、天气恶劣等一切丰富的社会线索都被省略时,人们自然难以对骑手的遭遇产生理解乃至共情。
五仔提到的“举报”也发生在应用层,这里涉及的对象是交互界面下更深层次的交互模式,即目前平台广泛应用的“智能客服+人工客服”系统,由协议层搭建。近年来,随着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对话系统受到很多企业关注,许多大中型企业都已构建自己的智能客服系统(如阿里巴巴的AliMe)。相较于注重文本匹配能力的初代客服系统,新型智能客服系统的服务范围扩大至泛业务场景(宋双永等,2020)。美团的年交易用户量为6.3亿,面对覆盖售前、售中、售后环节的大量沟通诉求,客服系统的搭建具有一定必要性。
简单说来,美团用户的交互服务旅程如下:当用户表达需求之后,美团的智能机器人响应、理解问题,再尝试自助解决,如无法解决,则“及时地流转到人工进行兜底服务”(会星,2021)。为提升匹配效率,问题的标准化(即知识库中的“标准问”,相对于现实中具体的“拓展问”)在其中发挥触发相应任务流程的关键作用。美团拥有近2万个标准问,其特征是多且杂,且其知识也在不断更新。此外,为使机器更好地“理解”用户,机器会进行多轮话题引导:
在用户问完“会员能否退订”后,机器人回复的是“无法退回”,虽然回答了这个问题,但这个时候用户很容易不满意,转而去寻找人工服务。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除了给出答案外,还去厘清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引导询问用户是“外卖红包无法使用”或者是“因换绑手机导致的问题”,基于顺承关系建模,用户大概率是这些情况,用户很有可能会选择,从而会话可以进一步进行,并给出更加精细的解决方案,也减少了用户直接转人工服务的行为。 (会星,2021)
在多轮改进下,用户便比较容易对人机交互方式感到满意,并逐渐对此感到习惯。另一方面,人工沟通也有走向“标准化”的趋势,主要体现为美团的人工座席和商家都依赖“常用通用话术库”来提升沟通效率。“我们采用了自动记忆每个座席及其同技能组的历史聊天话术、商家及其同品类商家的历史聊天话术,根据当前输入及上下文,预测接下来可能的回复话术”(会星,2021)。这里产生了一种交互悖论:由于平台将注重理解面向的对话能力进行了技术改造和收编,将其工具化和流程化,平台在试图兼顾用户情感需求的同时,生产出一种少量/无需情感卷入的中介化会话模式,用以高效解决用户问题。
在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交互界面和便捷高效的交互模式的配合下,用户在家、工作地点等任何感到方便的“地点”都可以顺畅地完成点外卖的动作,而承载这些行动的地点本身便被消解了。
总体而言,虽然在应用层并不直接涉及空间生产,但平台的交互界面等“对象”物却为消解“我”与商家、骑手三方之间的距离做好准备,强化“我—平台”的对子关系,为“我”形成依赖中介化交往的习惯提供温床。
(二)协议层
协议层依托平台的物质性基底存在,依靠软件和程序的可编程性(马诺维奇,2020),平台核心的流程规划、交互设计、派遣任务、存储数据、实现优化等工作都在这一层实现。协议层充斥着大量对象类的“物”,无法一一展开。且本研究中协议层的物的作用往往在应用层和基础设施层显现,本文将在其他两层分析中结合探讨。此处主要论述推动这些对象物开展活动的自动化逻辑。
在有限时间内,平台内庞大的行动者阵列必须借助技术进行持续管理。美团2020年的一份技术报告(晓飞,王鹏,江伟,2020)这样理解“持续”一词——“外卖团队将外卖的业务拆分成不同维度的子业务,每个子业务持续通过这个迭代流程不断地优化各个子业务达到最优,从而使整个外卖业务达到最优”。其中,“迭代流程”指美团经典的交付模型需要经历的需求调研、需求分析、程序设计、代码开发、测试、部署上线等多个环节(图4 图4见本期第77页)。
显而易见,“持续”这样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抽象词在这里被转化为可以拆解的一套流程。各种子业务、步骤和环节成为保障“持续运行”甚至“达到最优”的配件,这是一种化整为零的机器逻辑。实际上,在报告中,美团技术人员也将持续自动化、持续分解改进、持续反馈列为持续交付过程中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以期“开发人员可以更加聚焦在完成功能本身的工作”,“快速定位问题”,“将整个交付过程转变成一系列小而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持续地解决这些小问题”(晓飞,王鹏,江伟,2020)。
自动控制逻辑落实到生活世界时,作为达成交易中必须完成的“步骤”,骑手和商铺自然要被系统整合和控制。平台的理想愿景是“美团外卖,送啥都快,平均28分钟内到达”,那么在既定时间内,平台便要根据数据信息自动制定出“最优方案”。美团配送技术团队算法专家王圣尧(转引自赖祐萱,2020)曾简述系统如何为骑手的多点劳动建立秩序:“从顾客下单的那一秒起,系统便开始根据骑手的顺路性、位置、方向决定派哪一位骑手接单,订单通常以3联单或5联单的形式派出,一个订单有取餐和送餐两个任务点,如果一位骑手背负5个订单、10个任务点,系统会在11万条路线规划可能中完成万单对万人的秒级求解,规划出最优配送方案。”作为“最优方案”,平台预设的情况便可能是:接多单的骑手在前往商家、用户所在地路上不会遭遇意外(如突发疾病、电瓶车故障、交通管制、导航错误、电梯检修、社区封闭等),而商家也能够按照平台掌握的数据按时出餐。虽然《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2020)一文的出现让许多人了解到骑手面临的种种危险和困境,甚至推动平台作出回应和些许整改,但整条自动控制逻辑却丝毫没有被撼动,商铺、骑手作为螺丝钉仍在这条流水线上活跃着,即便已经有少数参与者开始进行“微弱的反抗”(如涂永前,谢文曦,熊赟,2021)。
(三)基础设施层
基础设施层涉及的物更为多元,包括外卖骑手的健康和安全状况等身体类的物,外卖包裹、交通工具、导航、保温箱、手机、界面等对象物,以及覆盖了众多取餐地点、城市道路、用户住宅区等场所类的物。
首先是以携带着手机的骑手为核心的身体类物。刘海龙(2021)等人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网络化身体”的概念,指人的肉身被接入网络后,可作为网络扩展硬件,成为网络的延伸。其中,被网络或平台收编的身体被称作“补丁”,以人肉的方式帮助网络跑完“最后一英里”。数据显示,中国外卖用户规模达到约 4.6 亿人(美团研究院,2020),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补丁”)达百万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
为确保这些身体类的物在以平台为中心的网络中有秩序地行动,受平台协议层控制的种种对象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主要呈现为各种“规则”。最基本的,骑手需要根据应用层界面的指引才能完成工作。例如,系统内的“热力图”等工具能够将骑手调度到单量大的区域(束开荣,2021);骑手当下所处的位置会被征用,成为系统预估送达时间、分配订单的依据;平台的超脑系统负责提供最优路线,催促骑手在任务与任务之间的地点流动起来。
为进一步刺激骑手“多劳”,美团不断升级其奖惩机制。《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2022)显示,美团外卖正在绍兴等15个城市试行新的“服务星级评价体系”:“骑手每个月的服务星级,将根据个人月累计总积分在本站点的排名确定,服务星级越高,获得的单均额外奖励越多”,除基础分外,加分项包括完成配送服务、参加安全培训、模范事迹等,扣分项包括超时、差评、提前点送达等。从这份报告可推知:其一,平台将其对骑手的工作要求转化成为可被量化的、便于纳入自动化逻辑中的计分体系;其二,骑手的一切活动都须接受系统的记录和管理;其三,以功绩、失误为核心的简单化评价标准限定着骑手收入乃至行为。骑手就是在此种规则的推动下完成工作。
消费者线上评分体系则在其中扮演着骑手监督者的角色。既往研究主要着眼于分析线上评议机制对于用户的有用性,其他行动者在其中受到的影响被谈及较少。例如Hu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大量线上评分网站都呈现出高度的正向偏见(即用户更倾向于表达满意态度)。在美团等消费者密集的平台上,系统以各种福利(包括抵现积分、升级奖励、专享霸王餐等)激励消费者参与评价,“维护”自身权益。给商家或骑手打低分后,用户能够直观地看到店铺排名、骑手评分下降,还可能获得补偿。平台在其中几乎将自身管理者的角色隐形,将监督商家和骑手的任务很大程度上转嫁和分发给了广大消费者。
在上述这些对象物的统合作用下,作为身体物的骑手的活动形式、轨迹、速度被框定,变得有秩序起来。除种种规则外,还有一些对象物辅助骑手完成任务。例如,针对骑手自身,美团研发了智能头盔,通过嵌入蓝牙耳机、麦克风、快捷按键、自感应尾灯等功能,赋能骑手更方便、安全地应对复杂的工作场景;针对交通工具,美团2021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落地换电柜,改善外卖配送中的硬件条件(美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会,2022)。
更重要的是,由于骑手在应用层接单,在物理城市空间中完成任务,因此作为身体物的骑手打通了线上、线下空间。物的空间活动和生产的结果便集中地在这一层显现。
在城市中,由于空间本身就是稀缺资源,摆放不下诸多支撑平台之物(例如外卖骑手休息区、专门的电动车道),于是便产生了两种空间活动策略:其一,征用或转化场所类的物。在平台经济出现之前,城市中已存在大量的商铺和道路,外卖平台将原有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广大商铺基础设施数字化、平台化,让分布于全城各地的食品、生活用品显现在同一界面上,打造出一张能够触及更远距离、更多行动者的关系之网。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空间没有产生增量,但场所类的物使用和调动频率激增,骑手正是在这样的空间内穿梭。这里很能体现出各种物如何协同发挥作用:在征用这些场所类物时,协议层制定的种种规则敦促骑手长期处于主动工作状态,确保他们的身体与电动车等物不会长时间挤占乃至撑爆某固定空间,在成就效率的同时解放了空间压力。
其二,生产非地方空间。鲍曼(Zygmunt Bauman)曾根据城市中人的交往特征提出“非地方”(non-places)概念,用以指称“空间转换时间交错的节点”,如机场、地铁等场所,其存在是为了敦促人们尽快通过或绕行(2017:171)。与之相仿,在外卖服务的取餐、配送环节,一批以物为中心的非地方空间被生产出来。最典型的,外卖取餐区域几乎已经成了所有入驻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的商家的标配。商家在商铺门口开辟出一小块区域,放一张长桌或一个多层简易支架,按平台名称摆放餐品。在高校、写字楼等需求密集的场所,也出现了大量的中介区域。笔者观察的某综合性大学就在各个门口设立了标注着区域、号码的外卖架(也受疫情防控因素影响)。居民楼区除了设置中介区域(取菜点、快递柜等),各家各户的门口也充当暂时的交接场所。此外,专门的外卖柜正在大批涌现。美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会(2022)表示,“截至2021年12月,外卖柜在全国已铺设上千台,并且还有更多点位在推进中”。
这些空间策略在平台对物的调度中应运而生,它们是平台三个层次之物一同作用、动态筹划的结果。
四、空间中的社会交往:赋能或限制?
不可否认,上述平台之上的种种物亦有潜力为城市中的社会互动赋能。它们调动、聚集诸多人和非人行动者,推动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相遇。然而,相遇并不能确保交往发生。实际上,平台三类物协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在制造人际相遇的同时限制社会交往。具体说来,位于核心的协议层以持续自动化逻辑统筹应用层与基础设施层;应用层虽不直接涉及空间生产,但平台的交互界面和模式等对象物却强化了用户对自身需求的关注;而在基础设施层,骑手、商家的繁忙也使得他们将更多注意力放在物的交付上。非地方中介区域的出现把交易直白地凸显出来。由于双方都明确对方的意图,沟通成为多余,效率得以确保。因此,这些空间的存在本身蕴含着一种提升速度、拒斥意义的意味。笔者在目标区域一家面店观察到,在商家—骑手交付阶段:
骑手盯着手机急匆匆地推门进店,嘴里喊道“89(号)美团”。店里有两位年轻服务员,女服务员背对着外卖架一边跟着音乐唱凤凰传奇的歌一边灌酸奶,没有理睬骑手。男服务员在接餐窗口趴着,低头看横放的手机。见无人答话,男服务员头也没转地低声说“美团在下面”。骑手无言,取餐后直接转身离店。(2022.01.15)
一般情况下,骑手到店后会根据外卖上的票据直接在快递架区域找单。如顺利找到,骑手和店家全程无沟通。在午晚餐高峰时段,这些区域旁偶尔有人看守,帮助骑手找单,防止因拿错产生额外成本。即便交流,也是“语境接力式”的交流:骑手催促商家尽快出餐,而商家则抱怨出餐需要时间。所谓的语境(规定送餐时间的流逝)只出现在平台界面内,显得有些因出餐慢而导致的线下争吵场景极为突兀。
在骑手—用户交付阶段,“门口”、快递柜、快递架就是交接的地点。多数情况下,骑手会在到达后通知订餐人,并将外卖放在交接区域后直接离开。订餐人到达时便只见外卖,不见骑手。送餐到人时,虽然已进入对方的亲密区域(18英寸内)(Hall, 1963),双方均不主动也不被期待做更多交流:
我从美团界面上看到骑手距我只有23米后,起身准备接餐。之后我听到“咚咚”地上楼声,随即抓紧门把手将门打开一条缝向下望,看见他的身影后我又把身子探回来,等待他走到门口。因为我家在顶楼,我逐渐听见他很大声地喘气。还有四五级台阶时,他就把餐递了过来,我伸手接住,“谢谢”刚脱口,他就转身下楼了,我都没看清他长什么模样。(2021.12.23)。
这显然与美团广告③里那种双方满脸微笑、用户真诚道谢、骑手充满满足感的画面相去甚远。长期地看,这种被中介的相遇场景有可能使得双方不再认为这种场合的短暂相遇需要交流。如需沟通,在平台上完成即可。
总体看来,在上述这类空间,系统的催促和各方对效率的遵从加高互动成本。因为“任何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将让他们远离个体从事的行动……不会给购物的愉悦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会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手头的任务彻底地离开”(鲍曼,2017:171)。一位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吐槽具有一定反思性:“XX平台搞了这种貌似高大上的无接触取餐柜,真的智慧啊,移除了开个小门和店员询问取餐的最后一点点交流,越来越像一个活死人的城市,也许疫情只是催化剂而已,我们终将要走向这样一个冷冰冰的世界。”
五、结论
德·塞托(2009:200)说,“空间就是一个被实践的地点。因此,在几何学意义上被城市规划定义了的街道,被行人们转变成了空间”。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来看,参与此类空间转化活动的行动者不止人,还有众多物。平台正是通过组织各种物的行动者直接或间接地形塑着城市空间,以及空间中的社会交往。美团外卖这一案例即显示出平台各层次上的物是如何协同完成空间活动,且征用既有空间、生产“非地方”空间的。
诚然,限于功能定位和体量等因素,美团外卖平台这一个案例无法涵盖所有平台的情况。但由平台多层次物协同推动的空间生产活动并非个例。实际上,网约车、共享单车平台和其他走向平台化的大型商企(例如麦当劳等)也在参与这种空间生产。例如,据笔者对海淀区某居民区的观察,共享单车极少在24小时占据同一地点。在上下班时段,人们会将单车比较集中地骑行到地铁站、公交站附近,下班后,单车又将流向各个住宅区门口。平台亦派有专人停放、搬运单车。由是,以物为中心的“非地方”便被进一步延伸到交通枢纽和住宅周边,甚至随着单车流动在城市道路之上。
在这样的空间内,平台调动并聚集众多陌生人,却无意让他们产生交流。只有平台界面内的购买记录成为用户、骑手、商铺之间存在过联结的证明,由于这种关系的消极性,这一条记录既是“出生证明”亦充当“死亡证明”。换言之,在平台及其各种物的介入下,社会互动的赋能和限制成为一体两面的存在,人际之间的联结和交往可以以一种不会造成任何一方尴尬的方式分解,然后组装进线上或线下空间的适当位置。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城市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和反社会化生产得以同时发生。
这一结论虽然还在空间研究的范畴内,但对空间生产的关注视点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无论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还是哈维(1989)的“时空压缩”、福柯(1980)的“空间规训”等至今仍有深远影响的空间理论,空间生产往往旨在揭露不平衡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乃至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博弈。而本文认为,受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发,空间和空间生产的概念有望被推至更日常、更微观、更去中心化的情境中。
换言之,上述案例中生产出的新型空间并非全然是由掌握权力或资本的人刻意设计或统筹的,而是众多人和非人行动者共同参与、持续互动的结果,其背后是技术物之间、人与各种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生成。拉图尔(2005:59)启发我们,“如果媒介/载体(vehicles)被视为触发其他中介(mediators)的中介(mediators),那么很多新的、不可预测的情况将随之而来”。通过对平台之“物”与空间生产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在平台社会诸多技术变革下,某些重要的社会和人际交往变化正悄然发生,这有赖于未来研究者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①具体数据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859500905319988&wfr=spider&for=pc&searchword=互联网平台市值。
②2018年,美团知识图谱团队开始构建美团大脑。具体来说,美团大脑会对美团业务中涉及到的千万级别商家、亿级别的菜品/商品、数十亿的用户评论,以及背后百万级别的场景进行深入的理解和结构化的知识建模,构建人、店、商品、场景之间的知识关联,从而形成生活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知识图谱。检索于https://tech.meituan.com/2021/09/02/meituan-commodity-nlp-practice.html。
③见https:/ /m.baidu.com/video/page?pd=video_page&nid=7026946768699252954&sign=575000309339422465&word=美团外卖广告片&oword=美团配送广告&atn=index&frsrcid=5373&ext=%7B%22jsy%22%3A1%7D&top={%22sfhs%22:1%22_hold%22:2}&next_nid=10706725663291921000&sl=4&lid=11697498673835116464&fr0=A&fr1=C&xb=3&fr0=A&fr1=C。
参考文献:
安杰伊·齐埃利涅茨(2018)。《空间和社会理论》(邢冬梅译)。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
陈龙,孙萍(2021)。超级流动、加速循环与离“心”运动——关于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劳动的反思。《中国青年研究》,(04),29-37。
戴宇辰(2020)。“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理解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03),54-67+127。
丁方舟(2019)。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新闻界》,(01),71-78。
丁未(2021)。遭遇“平台”:另类数字劳动与新权力装置。《新闻与传播研究》,(10),20-38+126。
丁未(2014)。《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家发改委(2020)。发改委举行4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检索于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 fzggw/Document/1677563/1677563.htm。
胡泳(2019) 。我们缘何进入了一个被平台控制的世界?《互联网经济》,(05),78-83.
会星(2021)。美团智能客服核心技术与实践。检索于https://tech.meituan.com/2021/09/30/artificial-intelligence-customer-service.html。
赖祐萱(2020)。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231323622016633&wfr=spider&for=pc。
列夫·马诺维奇(2020)。《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网络化身体:病毒与补丁。《新闻大学》,(05),40-55+122-123。
刘涛(2014)。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05),48-63.
玛丽·格雷,西达尔特·苏里(2020)。《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左安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团企业官网(2021)。发展历史。检索于https://about.meituan.com/details/history。
美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会(2022)。携手同舟,关爱同行——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检索于https://s3plus.meituan.net/v1/mss_e602b0ee72a245fd9997b7276211d882/waimai-pc/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pdf。
美团研究院,中国饭店协会外卖专业委员会(2020)。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检索于https://about.meituan.com/research/home。
米歇尔·德·塞托(2009)。《日常生活实践》(方琳琳、黄春柳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尼克·斯尔尼赛克(2018)。《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齐格蒙特·鲍曼(2017)。《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齐昊,李钟瑾(2021)。平台经济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10),14-2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检索于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6/content_5537493.htm。
束开荣(2020)。社交媒体研究的媒介物质性路径——以微信API开放与使用项目为个案的研究。 《新闻界》,(05),80-90。
束开荣(2021)。 送外卖:传播实践的物质网络及其时空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宋双永,王超,陈成龙,周伟,陈海青(2020)。面向智能客服系统的情感分析技术。《中文信息学报》,(02),80-95。
孙萍(2020)。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国际新闻界》,(11),39-53。
涂永前,谢文曦,熊赟(2021)。平台经济下劳动者职业安全探究——基于对北京X站点外卖骑手的劳动社会学调查。《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2),26-38。
晓飞,王鹏,江伟(2020)。美团外卖持续交付的前世今生。检索于https://tech.meituan.com/2020/02/13/meituan-waimai-continuous-delivery.html。
雪智,凤娇,姿雯,匡俊,林森,武威(2021)。美团商品知识图谱的构建及应用。检索于:https://tech.meituan.com/2021/09/02/meituan-commodity-nlp-practice.html。
延森(2016)。《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庄友刚(2010)。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学习与探索》,(01),14-18。
AndriessenE.& Vartiainen, M. (2006). Emerging mobile virtual work. In Mobile Virtual Work. Heidelberg, Berlin: Springer.
BaezS.HerreraE.Villarin, L.TheilD.Gonzalez-Gadea, M. L.GomezP.. . . Ibanez, A. M. (2013). Contextual social cognition impairments in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PLoS One8(3)e57664.
Barrett, L. F.Mesquita, B.& GendronM. (2011). Context in emotion percep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5)286–290.
boydD. (2014). Its’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uldry, N. & Hepp, A. (2018).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Polity.
DelfantiA. (2021). Machinic dispossession and augmented despotism: Digital work in an Amazon warehouse. New Media & Society23(1)39-55.
FoucaultM. (1980).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Gordon, M. (Ed.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Goulden, M. (2021). ‘Delete the family’: Platform families and the colonisation of the smart hom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4(7)903-920.
HallE. T. (1963). A system for the notation of proxemic behavior 1.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5(5)1003-1026.
Harvey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UK: Blackwell.
HuN.ZhangJ.& Pavlou, P. A. (2009). Overcoming the J-shaped distribution of product review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52(10)144-147.
Jansson, A. (2021). Beyond the platform: Music streaming as a site of logistical and symbolic struggle. New Media & Society14614448211036356.
Kittler, F. (2009). Towards an ontology of med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6 (2-3)23-31.
LangloisG. (2006). Networks and layers: Technocultural encodings of the World Wide Web.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0(4). 565-583.
LatourB.& Yaneva, A. (2017). “Give me a gun and I will make all buildings move”: An ANT’s view of architecture. Ardeth. A Magazine on The Power of The Project(1)103-111.
Latour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B. (1996). Trains of thought: The fifth dimension of time and its fabricationSwiss Monographs in Psychology, 4173-187.
LatourB. (1986). The powers of association. In LawJ. (Ed. ). Power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UK: Routledge & Kegan Paul.
Lefebvre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 Blackwell.
Light, B.BurgessJ.& Duguay, S. (2018). The walkthrough method: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 New Media & Society20(3)881-900.
Lin, J.& de KloetJ. (2019).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5(4)1-12.
Mukerji, C. (2015). “The material turn”in ScottR. A.KosslynS. M. & Buchmann, M. (ed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n InterdisciplinarySearchable, And Linkable Resource. John Wiley & Son Inc1-13.
Murdock, G. (2018). Media Materialties: for a moral economy of machin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8(2)359-368.
Rosenblat, A.& StarkL. (2016). Algorithmic labor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 case study of Uber’s dri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03758-3784.
van DijckJ.PoellT.&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uboffS. (2015).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0(1)75-89.
丁依然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项目编号:20RXW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