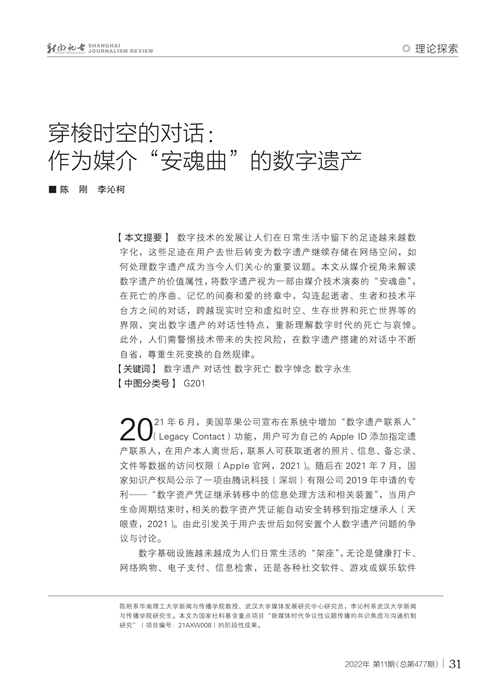穿梭时空的对话:作为媒介“安魂曲”的数字遗产
■陈刚 李沁柯
【本文提要】数字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足迹越来越数字化,这些足迹在用户去世后转变为数字遗产继续存储在网络空间,如何处理数字遗产成为当今人们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媒介视角来解读数字遗产的价值属性,将数字遗产视为一部由媒介技术演奏的“安魂曲”,在死亡的序曲、记忆的间奏和爱的终章中,勾连起逝者、生者和技术平台方之间的对话,跨越现实时空和虚拟时空、生存世界和死亡世界等的界限,突出数字遗产的对话性特点,重新理解数字时代的死亡与哀悼。此外,人们需警惕技术带来的失控风险,在数字遗产搭建的对话中不断自省,尊重生死变换的自然规律。
【关键词】数字遗产 对话性 数字死亡 数字悼念 数字永生
【中图分类号】G201
2021年6月,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在系统中增加“数字遗产联系人”(Legacy Contact)功能,用户可为自己的Apple ID添加指定遗产联系人,在用户本人离世后,联系人可获取逝者的照片、信息、备忘录、文件等数据的访问权限(Apple官网,2021)。随后在2021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一项由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2019年申请的专利——“数字资产凭证继承转移中的信息处理方法和相关装置”,当用户生命周期结束时,相关的数字资产凭证能自动安全转移到指定继承人(天眼查,2021)。由此引发关于用户去世后如何安置个人数字遗产问题的争议与讨论。
数字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架座”,无论是健康打卡、网络购物、电子支付、信息检索,还是各种社交软件、游戏或娱乐软件的使用等,都在有意无意间把人们的数字足迹编织进代码,存储在云端。人们信息沟通、消费行为与交往行动的深度网络化使其部分生命在网络中延展,当人们将生活轨迹与情感联结填充进赛博空间,其数字痕迹也逐渐具有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价值。而当肉体生命终结、用户无法再直接与数据交互时,这些散落在赛博空间的个人数字痕迹就变为“数字遗产”。数字遗产(digital legacy)关切着每一个接入互联网的人。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边界模糊的灰色地带,用户的信息管理权及隐私权难以被明确界定并保护,联网意味着公开。活着时用户尚且能维系自己的“前台形象”,肉体死亡后这些遗留的信息是否会走向失控?个人的数字遗产该何去何从?个人在网络中的多重自我化身该如何交付?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认知死亡与悼念?数字时代的死亡禁忌正在经历着重新编码,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认为,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对后现代人而言就是“自然”(彼得斯,2020:342),包括生者的人间数据库和逝者的天堂数据库。数字遗产可被看作一种存储在云端的人类活动数据库,对此,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重新解读数字遗产的价值属性。
一、理解数字遗产: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死亡”
在德布雷(2014a)看来,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其记忆和传承的能力,在历史范畴中形成人类文明的延续。媒介技术的演进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也改变着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记忆传承。在人类文明早期,人们用符号和图案将记忆及情感铭刻在石头、骨骼、岩壁等外部存储媒介上,生成各种形式的纪念物,用以抵抗遗忘与死亡。物质化或者是建立成纪念性建筑物,实际上多多少少是要使事物形成群体(faire groupe),产生某个地方(faire lieu),使其得以延续(faire durer)(德布雷,2014a:27)。这种对集体意义和延续性的强调凸显了纪念物的传承价值,“媒介”也成为“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德布雷,2014b:4),在不同媒介技术主导的时代形成不同的记忆铭刻与保存的方式,传承着积淀深厚的人类历史文明。在数字技术“接管”记忆存储的时代,信息记录具有即时即地性、便捷性、虚拟化、个性化等特点,人们日渐成为“算法的实践者”,在赛博空间留下大量个人数字痕迹。生命最终要面对死亡,而在赛博空间留存的数字信息可能被长久记录并流传。如何安置这些带有个人标记的“数字遗产”,是数字时代人们必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03年制定并发布了《保存数字遗产宪章》等重要文件,将“数字遗产”界定为“人类知识及表达的资源”,包括各种文化、教育、科学、管理等数字信息,以及技术、法律、医学和其他以数字形式生成或从原有模式转换成数字形式的不同类型的资源,呼吁各成员国及早重视数字遗产保护工作(UNESCO, 2003)。这里的“数字遗产”,特指“我们的过去,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我们传承给后代的东西”(our legacy from the past, what we live with todayand what we pass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是具有传承价值的文化、艺术、观念等公共文化遗产。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和互联网设备个人普及率的提升,社会各界对“数字遗产”的关注逐渐彰显至个人研究领域,关于“digital legacy / inheritance”的讨论不断增加,相较于“inheritance”对遗产可继承性的强调,“digital legacy”更偏向逝者的主动遗留,本文亦是在这一范畴中展开对个人数字遗产相关议题的讨论。
虽然研究者们对“数字遗产”有不同界定,但共性在于对数字存储形式的强调和以自然人死亡为前提,而在数字遗产内容划分上存在差异。从其概念上看,数字遗产首先是作为一种“遗产”而存在。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首次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法律保护范围,此外《民法典》也规定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数字遗产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譬如电子账户及密码、虚拟货币、游戏装备等可转化为实际货币的数字资产,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各种网络原创作品等,都属于数字遗产。其次,数字遗产的“数字特性”使其并不仅限于财产范畴,譬如电子邮件、个人文档和相册、社交媒体账号及相关内容、软件和网页的浏览使用记录等具有人格属性的各种数字足迹,这些已故用户遗留下来的数字信息也属于数字遗产。相较于传统遗产,数字遗产具有虚拟性、易失性、复杂多样性、占有主体双重性①等特点,在法律界定、遗产保存与继承问题、逝者的隐私权和被遗忘权、生者的缅怀与悼念等方面存在更多争议。
目前关于“数字遗产”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展开。如国内大多从法学角度探讨数字遗产的概念界定、法律规定、继承纠纷、隐私保护等内容,突出数字遗产的财产价值(赵荔等,2012;陈奇伟,刘伊纳,2015; 顾理平,范海潮,2021);亦有从档案管理视角探讨数字遗产保存和文化传承意义(蒋银,吴倩,2014);还有学者从媒介化视角探讨数字遗产的联结、交互及展演特征(高嘉遥,蒋璐璐,2021)等。国外对于数字遗产议题的讨论起步更早,研究视野更为开阔,除了关注相关理论及制度层面的建设等,也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用户在生前对数字遗产的管理议题。例如,运用定性访谈法探讨Facebook账号的继承和数据管理问题,发现参与者较少关注数据所有权,而更关注账号维护相关的职责和潜在冲突,提出以“管理”代替“继承”,创建逝者的数字遗产管理方案(Brubaker et al., 2014);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人们对数字足迹的总体看法及去世后的数字遗产规划,强调管理个人数字遗产的重要性(Peoples & Hetherington, 2015)。此外,国外研究也积极探讨数字遗产内容设计,并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在线数字悼念(digital mourning)、数字死亡(digital death)与数字来世(digital afterlife)等相关领域。如通过联系数字技术和物理材料,设计新型数字遗产代理方式(Pitsillides, 2019);运用内容和主题分析研究Facebook上的逝者纪念页面以及访问者与已故名人的对话(Gil-Egui et al., 2017),引入虚拟死者(VDP)的概念探讨数字永生及生者与逝者之间社会纽带的维系(Hurtado, 2021)等。
这些研究拓展了数字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也渗透着不同社会文化氛围的研究者面对“死亡”的不同态度。受传统丧葬文化避讳谈论死亡以及宗族观念的影响,东方文化对生的体验更深刻,研究更加关注生者对于逝者遗产继承纠纷和保护等制度建设层面。而西方文化对死亡的乐观态度使其更能自在谈论生死、谈论逝世后个人数字遗产的管理方案等,相关研究更为多元灵动,这些视角也为本文重新解读“数字遗产”提供了新思路。此外,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影响着数字时代的死亡意识,关于媒介与死亡的探讨日渐丰富。如章戈浩(2020)在梳理不同源流对媒介与死亡关系讨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存媒介研究的视角来分析数字背景下生存与死亡的联结,也为生存媒介研究带入了东方视角。
媒介连接起过去和现在、远方和近地、逝者和生者。数字时代的“媒介”更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个体的人与媒介的人以及媒介的结合体,背后是媒介与媒介、人与媒介、人与人之间交错复杂的网状关系(姜华,张涛甫,2020)。媒介基础设施为数字遗产搭建了信息生成及存储空间,数字遗产成为这些网状关系聚散的“自然”场域,不仅关切着逝者和生者,还关切着存储信息的中介性平台。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的碳基生物,在肉身自然死亡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记忆与爱的情感联结。本文拟从逝者、生者与平台三者之间的关联来探讨数字遗产的媒介属性,逝者与平台、生者与平台、逝者与生者的联结中也隐含着数字时代对死亡、记忆和爱等命题的再理解,通过“赋予算法以意义,赋予代码以情感”,思索在技术文明中人类生命尽头的数字参与。
二、死亡的序曲:当数字足迹成为互联网“骨灰”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在谈论死亡时指出,“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长久以来,死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感,当真实时空里的生命个体被生活庸常包裹,生存和死亡之间隔着不可见的“天堑”,肉身死亡便处于一种尚未到来的隐退状态,与死亡相关的事宜也往往不被纳入日常考量。而在数字时代,媒介技术搭建的中介性平台让死亡正在变得可接近、可感知。
随着人们留下的日常足迹越来越数字化,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娱乐活动、订阅服务,甚至随手标记一部电影,都可能被存储进信息管理与服务的各种平台。通过在不同网络站点创建海量数据存储库,数字足迹让信息使用者和版权所有方彼此关联,这种关联在用户去世后更为凸显。牛津互联网研究所分析预测,据2018年Facebook用户水平显示,至少有14亿会员将在2100年之前死亡;到2070年,死者人数可能会超过生者(OII, 2019)。当数字足迹成为互联网骨灰,大量逝世用户的数字尘埃在以太中漂浮,这些信息具有流动性、公开性、超越时空性等特点,死亡气息在赛博时空中随处可感。数字足迹作为自我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当人们越参与网络世界的互动,去世后互联网骨灰的潜在影响力就越大。戈梅尔和贝尔(2014:13)以“圆形监狱”形容数字化带来的影响:行为信息被转化为数字碎片,经过算法,这些碎片将还原与现实相对应的数字化个体,由此每个人都在数字空间中被凝视着。2018年浙江乐清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一案引起社会热议,受害者的微博也被迅速找到,网友们翻看其生前发布的照片和各种动态,甚至留下评论或转发传播,无论这些举动是否带有恶意,都行了窥探之实,也为逝者家属带来二次伤害。随后,新浪微博平台将逝者账号转交其家属保管,并呼吁网友停止保存和转发被害人信息,保护被害人隐私,家属也发布相关声明并注销此账号,才逐渐平息这一风波。
数字时代的死亡让逝者的身后事变得复杂,鉴于目前法律对数字遗产缺乏统一明文规定,如何处理个人数字遗产成为逝者、生者和平台方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于平台方而言,除去信息所有权、隐私权等内容纠纷外,管理海量信息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维护成本,面对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过载趋势,技术平台方也担忧会出现存储空间危机,所以也在积极推进关于逝者数字遗产管理的优化方案。而逝者为了避免个人信息在离世后走向失控或被公众围观,同样也参与到生前对个人数字遗产的规划中,数字时代的死亡禁忌正在被逐渐打破。死亡的“序曲”勾连起平台和逝者,互联网骨灰是随风吹散还是装进小盒管理?如何管理?需要双方共同来谱写。
新浪微博平台一项关于数字遗产的问卷调查显示:2512名网民愿意在突然去世后将账号转给他人,7669名网民表示不愿意;16.8%的网民愿意在去世后让家人浏览其社交账号内容,另有83.2%表示不愿意(环球时报,2022)。这两组数据反映出用户对逝世后个人信息及隐私的重视,数字遗产是该留存给后代还是“死后即焚”也引起广泛热议。早在2009年的“Vanish”项目中就谈到“信息的生命周期”,提议网络中的数字足迹应该到指定日期便自行销毁或隐藏,保护个人数据及隐私免受合法、意外和恶意攻击(Geambasu et al.,2009)。人的记忆具有有限性,为信息设置生命周期不仅有助于优化信息管理,也能让人更好地平衡过去、当下和未来。数字技术能抵抗遗忘消亡,但前提是人类愿意。技术所运用的复杂运算逻辑的软件程序,以及体现着技术霸权的芯片硬件,使人类在技术媒介面前表现出仅有使用权,而无控制权的趋势(郭小安,赵海明,2021)。扭转这一趋势的关键在于技术平台方与逝者在生前的协商,如软件使用前签订用户协议,以各项条款来明晰用户及平台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2021年苹果公司、腾讯公司相继推出了数字遗产相关规定。此前大部分技术平台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在用户协议中会明确规定,用户仅享有账号及服务内容的使用权,其账号的所有权仍归平台所有。如苹果公司曾在服务条款中规定,用户的账户不可转让,且Apple ID及账户相关内容在用户被证明去世后将被删除。腾讯旗下微信、QQ等平台的注册协议中也指出,账号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用户享有账号使用权,但严禁用户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账号;若账号长期未登录或使用,腾讯有权将账号进行回收处理。由于腾讯旗下的产品涉及价值较高的数字资产(如虚拟货币、游戏装备等),平台方严格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防止用户私下交易,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充分考虑用户的权益,在面对属性复杂的数字遗产问题时,易引发用户与平台间的各种纠纷。
作为最早设置数字遗产保护的公司之一,Facebook在2009年推出纪念账号模式,用户去世后可由其他用户出示其死亡证明,向Facebook申请将此账号转为纪念模式,相关页面功能也会更改,实质仍是由平台负责打理其数字遗产。在2015年Facebook又推出遗产代理人(Legacy Contact)功能,用户可在生前指定一位亲友作为代理人来处理其数字遗产,拥有注销账号、发布讣文、更换头像及封面图片、下载或删除逝者分享的内容等权限。Google在2013年推出了类似服务——闲置账户管理员(Inactive Account Manager)功能,帮助用户建立自动处理数字遗产的流程。当Google账号闲置超过3个月至1年时间,Google系统将主动通知账户使用者指定的受托代理人,每位用户最多可指定10位代理人来打理Google系统中的不同服务,如 Gmail、Google drive等,托管范围由用户自行决定。若用户未设置数字遗产处理方案,Google会与其直系亲属合作,协商逝者账户停用事宜。包括苹果公司2021年推出的“添加数字遗产联系人”在内,这些代理人功能实质上是将数字遗产的处理权限交给用户自己,相当于逝者保存在平台方的一份遗嘱,以期能协助逝者实现合理隐私期待。
然而并非所有平台都能适时推出数字遗产管理方案,这些方案也仅能覆盖部分数字足迹,更不用说制定系统的个人数字遗产规划。所以近年来也涌现出一批数字遗产相关的信托服务、数字遗嘱等新型产业,在目前缺乏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协助用户做好数字遗产规划。如Entrustet、Legacy Locker、Digital Dust等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定制的数字资产管理方案,可将逝者的数字遗产发送给指定继承人;The Digital Beyond、My Wonderful Life等网站让用户能自己设计葬礼,并可留下自己将如何处理数字遗产的说明;My Farewell Note网站则以文字、音视频等方式为逝者提供告别服务,这些告别信将在用户去世后发送给指定联系人。由于这些数字遗产规划公司利润不高,且通常提供免费服务,也存在倒闭或消失的风险(Kneese,2019)。在国内人们也开始关注数字遗产安置问题,据中华遗嘱库2022年3月发布的白皮书显示,00后人群的遗嘱中有17.3%是虚拟资产;在90后人群中这一比例上升至21.75%,包括虚拟货币、游戏装备、网络店铺等内容,遗嘱办理的年轻化趋势也愈加明显(中华遗嘱库,2022)。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指出,越来越多年轻人并不忌讳谈论死亡,反而认为提前考虑“身后事”是为了更认真地生活、对自己和亲友负责(光明网,2022)。
数字时代人们的生死观念正发生变化,尤其是对于在网络空间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的互联网原住民,生命中的一切数字足迹都可被铭刻进代码,具有物质和情感的双重属性。数字足迹是自我在赛博空间的延伸,所以规划个人数字遗产也可看作一个阶段性的生命总结,在死亡预设的对照中探寻自我本真、反思生命的存在。海德格尔(2014:287)认为,死亡悬临(bevorstand)于此在的境域中,它挥之不去、如影相随。数字遗产以死亡为序曲,在可感知的死亡氛围中勾连起逝者与平台的对话,为妥善安置互联网骨灰争取更多可自我支配的权利和自由。
三、记忆的间奏:数字公墓悼念与“扫墓人”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谈到,“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人类生命存在于世,必然会与其他存在物及环境产生碰撞,并在人脑中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生成记忆。然而,人脑的生物结构使记忆存储量具有有限性。如同希腊神话中爱比米修斯对人类的遗忘,致使人类存在“缺陷”,普罗米修斯则盗取了神火送给人类作为替补,成为超越“缺陷”的“代具”象征(斯蒂格勒,2012:54),人的记忆也伴随着技术特性。人脑不断在遗忘中对过往记忆内容进行筛选,也创造了能够存储记忆的外化于人脑的媒介技术物,即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持存”,使记忆以生命之外的形式得以延续。由于大脑中存储的记忆不具备可遗传性,当肉体生命终结,那些铭刻于技术物上的记忆痕迹会成为逝者曾存在于世的验证,也是生者得以与逝者继续维系的寄托。
数字技术开启了人类记忆存储的新时代。在数字媒介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人们的各种行为及思想都会在有意无意间被记录到“0-1”的数字矩阵中。相较于人脑的记忆功能,数字记忆具有海量存储、高速传输、精确运算、便捷提取等特点。生物记忆会褪色、消失、合并或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面目全非,但数字记忆却会永恒不变,而且数字记忆包罗万象,它能够包含每一个细节(戈梅尔,贝尔,2014:60)。当死亡真正发生后,这些数字记忆并不会随着肉体消逝,而是作为一种数字遗产继续存储在网络空间。相比于逝者,活着的人似乎更能掌握对逝者记忆遗存的处理权,在数字遗产生前管理等业务尚未普及的当下,如何处理逝者的数字遗产成为平台与生者(尤其是亲属)的“纠缠”。技术平台存储着关于逝者的数字记忆,生者头脑中存储着关于逝者的生物记忆,记忆作为死亡进行时的“间奏”,勾连起平台和生者对于逝者数字遗产处理问题的协商。
托尼·沃尔特(Tony Walter)等(2012)将死亡分为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三种类型:传统死亡发生在具有附近性的社区中;现代死亡发生在医院或家中,死亡与哀悼具有公共与私人的区隔;后现代死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使私人情感在公共空间中得以表达,形成公私结合的多元哀悼场域。数字技术搭建的媒介基础设施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真实时空和虚拟时空的边界,改变了传统物质性的丧葬与哀悼仪式,将死亡带到逝者直系亲属之外的公共社交网络空间。数字时代的丧葬和哀悼日趋公共化、虚拟化,甚至重塑着悼念活动的参与群体。作为一种新型记忆装置,社交媒体平台存储着大量逝者的数字记忆,为生者提供了开放式的哀悼与情感诉诸空间,成为存放逝者互联网骨灰、生者缅怀悼念的数字公墓。Facebook在2019年推出新版纪念账号功能,若选择不注销逝者账号,该账号在用户去世后会转为纪念账号,主页会被添加“Remembering”(纪念)的字样,逝者生前发布的信息动态也会被及时冻结不可更改。根据用户生前的隐私设置协议,亲友可继续在逝者账号主页发布照片和帖子来共同缅怀逝者,延续逝者的账号动态,使账号成为一个关于逝者的数字纪念馆。Instagram也推出了类似功能,只需提供用户死亡证明、遗嘱副本以及与逝者的关系证明,即可申请纪念账号。而Twitter、LinkedIn等社交平台目前尚未推出该功能,只可在提供死亡证明后注销逝者账号。此前Twitter曾在2019年提出不活跃账号清除计划,包括那些不会再更新的逝者账号,遭到用户的强烈反对。随后Twitter表示,在找到合适的纪念逝者账号方法前,暂不执行此计划。
国内也存在生者与平台在逝者账号问题上的纠纷。2018年3月豆瓣大量已故用户页面“失联”无法访问,引起豆友们的激愤与恐慌,质疑平台将已故用户清除。豆瓣官方在澄清并恢复账号页面后,逐步完善用户账号保护机制,为逝者账号设置已故状态、悼念图标,并锁定保护。豆瓣相关负责人解释,账号的存在本身是用户精神财产延续的方式,能够继续长期辐射其社交圈层,所以只要用户或其近亲属、委托联系人没提出注销,豆瓣会保留其账号及其在世时的内容创作,也是保留用户之间的精神联系(凤凰网,2022)。新浪微博也于2020年9月发布《关于保护“逝者账号”的公告》,在提供用户相关死亡证明后,对逝者账号设置保护状态,即不能登录、不能新发内容、不能删除内容、不能更改状态,以应对频发的逝者账号被盗取、隐私泄露等乱象。作为国内首个推出纪念账号的社交平台,B站于2020年12月发布公告称,在取得逝者直系亲属确认和同意后,将该账号冻结并转为纪念账号,逝者主页配有灰色蜡烛及文字:请允许我们在此献上最后的告别,以此纪念其在哔哩哔哩留下的回忆与足迹。网友可继续在逝者账号主页发送弹幕和评论来表达情感与哀悼,部分用户也向平台反馈,因为纪念账号功能开始关注数字遗产问题(光明网,2022)。虽然冻结逝者账号、设置悼念功能等,目前仍是比较粗线条的数字遗产处理方案,但也使用户生前的数字足迹通过平台得以长期保存。技术平台成为数字公墓,纪念账号主页成为逝者的数字墓碑,生者通过在主页点蜡烛、送花、留言等在线悼念行为,成为赛博空间里的“扫墓人”,而“扫墓”这一赛博悼念行为本身又丰富了被哀悼者的数字遗产。
此外,生者与平台方的“纠葛”也体现在逝者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上。数字遗产混杂着财产、文化、人格等复杂属性,在用户去世后能否被继承、如何被继承也一直存在争议。在美国数字遗产继承纠纷第一案——艾斯沃斯诉雅虎案中,逝者父亲向雅虎公司请求继承其子的雅虎账号及密码以此寄托哀思,而雅虎则以侵犯逝者隐私权为由予以拒绝。最终法院以折中方式判决雅虎平台继续享有逝者账号所有权,但需将账号内容的副本交予家属。此后不少案例都仿照了这一判决思路。而在2015年德国的一起数字遗产继承案中,逝者母亲为查明女儿死因而请求以继承人身份登陆其Facebook账号,Facebook同样以隐私保护为由拒绝,由于案件逝者是未成年人,最终法院判决作为其监护人的父母可享有逝者社交账号的进入权限。数字遗产继承牵涉到逝者本人、逝者生前与平台签订的使用协议及逝者遗嘱、隐私保护等各方面的问题,在目前已有案件的司法实践中,需根据具体案情谨慎处理,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完善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我国在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也规定了“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中国人大网,2021),与《民法典》内容协同呼应,为逝者相关主体处理其数字遗产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具体内涵也需在案例实践中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然而记忆没有规则书。生者在与这些数字遗产的交互中感知逝者的数字灵魂,关于逝者的生物记忆和数字记忆相互交融,延续逝者的“存在”。尤其是对逝者亲属而言,数字遗产所带来的情感触动更为强烈也更持久。2013年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了一名少年因网络欺凌而自杀的案件,在儿子去世后,其父常打开衣橱感受儿子衣服上残留的气味。但气味难存储、易消散,父母又转向逝者的Facebook账号来感知其存在,“100万年过去,我们都不会删除他在Facebook上的资料,不可能”(伊莱恩,2020),收到其他用户的悼念信息也让父母觉得儿子并没有被遗忘。《纽约时报》“当代情感”栏目年度获奖文章:“我的姐姐在多年前失踪,但想她时却随时都能见到”(Leddy, 2019),源于作者的真实故事。姐姐失踪后,作者通过浏览其之前在Facebook上发布的文字、照片、视频等来记住姐姐的形象,感知她的喜悦与悲伤,仿佛姐姐仍活在身边。基特勒(2017:11)以记忆的解放与终结来形容电子时代视听数据可被存储到同一媒介,从而给文字阅读的幻觉力量带来的冲击,不再“只有通过书写,死人才将会保留在活人的记忆中”。而数字技术对信息的存储、复刻方式及不同媒介的融合特性,让数字时代的死亡变得更鲜活,逝者的数字灵魂在技术平台搭建的数字公墓游荡,生者关于逝者的记忆在遗忘与唤醒之间循环往复,死亡成为一个动态过程。
电影《寻梦环游记》讲述了关于亡灵的故事,提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止,遗忘才是”。人一般都会经历三重死亡:生物肉体死亡、社会价值殆尽和精神上被遗忘,生者打理数字遗产也是在抵抗遗忘中重建逝者“存在”的意义。记忆作为“间奏”连接起生者和平台,在生物记忆与数字记忆的共振中延续逝者的“生命”。当然,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信息存储设备,也存在硬件设施故障隐患、存储寿命和容量限制等潜在问题,如何更好地保存逝者数字遗产、安置数字亡灵,需要不断寻求技术突破。
四、爱的终章:生死联结与数字DNA提取
西班牙作家曼努埃尔·比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奥德萨》以时空为经纬,从丧亲纪实追思过往记忆,在爱与死亡的缠绕中探寻生命联结,提出“死亡应是万事万物的广袤基础”。长期以来,生存与死亡之间的二元对立支配着人们对死亡的感知,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二元划分也包括心与身、人与动物、文化与自然等,死亡处于被贬抑甚至被污名的状态。数字时代重新定义了死亡的价值,死亡并非存在的终结而是生命的间歇。由于生者往往需要借助各种媒介来与逝者交流,铭刻着逝者痕迹的数字遗产成为生者通达逝者、连接生与死的重要纽带。
当前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重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模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真实时空和虚拟时空的边界同时,也在消弭生存世界和死亡世界的“隔阂”。卡拉·索夫卡(Sofka, 1997)首创“死亡技术学”(Thanatechnology)一词来描述在互联网出现早期技术对死亡的介入,指交互式视频光盘和计算机程序等用于获取信息或帮助学习死亡相关主题的技术机制。在其2012年出版的《在线世界的临终、死亡与悲伤》一书中,索夫卡等人将死亡技术学的概念拓展至所有通信设备,分析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平台对逝者数字遗产进行的数据化存储,探索互联网如何改变了以往的死亡禁忌与悼念方式,指出死亡技术正在为传统死亡系统带来根本性变化(Sofka & Gilbert, 2012)。每一次的在线互动都会创造可被视为我们数字灵魂的数字碎片,存储在不同网络平台,构成自我的多重分身。这些灵魂碎片不再是宗教意义里上帝才能收集的特权,任何能上网的人都可在与数字技术的交互中拼凑逝者的数字灵魂,创建生者与逝者之间新的连接感。技术已不仅仅是生者和逝者建立联系的媒介,逝者就存在于数字技术之中。
日本设计师山崎琢磨(Yamazaki Takuma)创作的作品《灵魂密码》(Images of Anima Code)获得了A’设计大奖赛2020—2021年度创意设计类奖项。灵魂密码是一款刻有二维码的个人印章,相当于个人数字遗产的访问密钥,亲属可通过扫描事先盖章的二维码来访问逝者的数字档案,这一设计探索了在数字时代如何安全而私密地安置个人数字遗产,印章实际上成为逝者有形的数字骨灰盒。国外有些殡葬公司也推出交互式墓碑服务,其中代表性的QR Memories项目中,亲属可在相关网站上传关于逝者的文字、照片、视频等,以二维码的方式生成逝者的数字档案并铭刻在墓碑上,悼念者通过扫描二维码来了解逝者的故事,在互动中感知逝者的存在。殡葬公司也会提供二维码相关程序的网络托管和定期维护等服务。数字技术可将人的生平足迹以数据化的方式编织到代码中,逝者的数字灵魂附属于技术系统,“作为生物有机系统的人与技术机器系统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人与技术机器系统‘共创生’的崭新状态”(孙玮,李梦颖,2021)。在数字技术时代,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能由代码编纂“生命之书”,人也由此成为“码之人”。
生物体与机器系统不断耦合,日趋智能化的机器不仅能嵌合人的肌肉系统,也能理解人的中央神经系统,催生人机混合的赛博格(Cyborg),个体生命的存在属性在技术的加持下开始改写。2022年6月,世界上首位赛博格在社交媒体上被宣告死亡。这位在5年前被确诊渐冻症的英国科学家彼得·斯科特-摩根,通过多次手术将自己的器官替换为机械,“我将不断进化,作为人类的我已经死去,未来我将以‘赛博格’电子人的身份继续活下去”(澎湃新闻,2022)。彼得将自己改造成赛博格的实践具有开创意义,虽然肉身与机器的结合目前尚未实现跨越生死的设想,但近年来关于人的肉体死亡后,意识在云端永存、创造数字永生的尝试越来越多。2015年俄罗斯程序员尤金妮娅·库达(Eugenia Kuyda)在好友意外离世后陷入哀伤,为缓解失去挚友的痛苦,其将手机里存储的关于逝者的对话文本输入Google开发的神经网络系统,根据这些数据创建了拥有逝者生前讲话风格的聊天机器人。库达认为,所有信息都是关于爱的或是曾经没来得及跟逝者说的话,即便他不是真人,但至少有个可以倾诉和表达情感的地方,这些表达也能得到回复,缓解孤独和思念(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6)。2017年《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弗拉霍斯(James Vlahos)在父亲去世前录下父亲的声音和生平,利用编程创建关于父亲的记忆库,也开发出可以聊天的Dadbot来缓解丧亲之痛。这些利用逝者在社交媒体、电子邮箱等不同平台留下的数字遗产而创造的AI聊天设备,称为“Griefbots”(Jiménez-Alonso & Brescó de Luna, 2022)。在个体生物死亡后,Griefbots能延续逝者的意识,模仿逝者表达的节奏、语气和特质,让生者能与数字化逝者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双向交流。收集数字遗产的过程也是提取逝者数字DNA,创造数字自我的过程。人们与数字世界的互动越多,留下的数字足迹越多,数字自我就会越接近真实自我。
从研究长生不老秘籍到各种基因飞升、机械飞升、生物克隆实验,人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进行过寻求永生的尝试,数字时代的新兴技术也为探索永生可能性提供了新思路。美国一个基于网络的实验项目LifeNaut,通过“数据化+人工智能”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备份自己”的服务。用户可在LifeNaut官网上传一份DNA采集的生物文件(bio file)和一份关于自己的文本、声音、影像等人格文件(mind file),而后LifeNaut将凭借这些材料以人工智能算法孕育出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用户虚拟化身,等到基因技术成熟后再结合生物和人格文件在物理世界再造用户,以期实现人在数字时代永生。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目前人工智能仍处于初级阶段,仅能实践基于逝者数字遗产的思维克隆,通过生成逝者的虚拟形象或将逝者意识嵌合到AI机器人中,实现自我在算法层面的“永生”。但这种数字自我的化身弥合了生与死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死亡带给濒死者的恐惧与牵挂,抚慰生者对逝者的思念与哀悼。
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因盗取象征技术的火种给人类,而被宙斯挂于高加索山的悬崖上经受酷刑。技术具有神性根源,现代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但也潜在危险,人们运用各种新兴技术试图改变生死规律的行为是否会引起自然的惩戒?再造逝者的数字化身也牵扯着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梅斯梅尔催眠术说明,浪漫的精神交流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既意味着幸福的罗曼蒂克,又意味着令人恐惧的心灵践踏(彼得斯,2017:131)。生者与逝者之间模糊不清的边界,可能会让生者从失去亲友的悲痛中振作,但也可能会因过度沉迷带来精神上的混乱,造成对生者的折磨。《寻找意义:悲伤的第六阶段》(Finding Meaning: the Sixth Stage of Grief)的作者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指出,应当以更多的爱而不是痛苦来纪念逝者,创造逝者的数字化身来缓解悲伤并非完全放弃悲伤,而是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将痛苦融入生活(The Washington Post, 2019)。人类作为情感的集合体,在面对亲友尤其是至亲离世时难免存在未完成情结(unfinished business)的本能反应,或许与逝者的数字化身进行交流能达到缓冲情绪的效果,“庄周蝶梦”之后,生者还是要回归现实世界继续生活。
在拉丁文中,爱(amore)与死(morte)一字相联,情感深处的死亡怖惧与哀恸潜藏着对现实世界的爱的联结。无论是逝者与平台在死亡的序曲中协商去世后数字遗产的规划,还是生者与平台在记忆的间奏里沟通逝者数字遗产的安置,都隐含着生者与逝者之间跨越生死时空的对话。在技术的加持下,数字遗产作为逝者的数字DNA被提取并创造出数字化身,更将这种生死连接推向直观可感的高潮,在爱的终章里重新理解死亡。爱向死亡敞开,走向死而不亡。生物有机体会消失,但生命精神不会消亡,保存数字遗产如同保存了一份携带意识DNA的文明火种,承载着人类爱与智慧的延续。
五、结语:数字遗产的复调与对话性
人与媒介共在(Mitsein)于自然系统,生命从诞生到凋零殒落也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技术的更迭则不断颠覆着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也重塑着人类对生死规律的理解。在数字技术时代,人的一生都可被编织进代码系统,这些有意无意间留下的大量数字足迹,让死亡及身后事处理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价值属性更复杂,关切着多方主体的数字遗产问题。
“复调”作为一个音乐术语, 指演奏中有两段或者两段以上既独立又相关的多声部音乐,巴赫金将这一术语运用到小说理论中,提出文学作品里具有的多声部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白庆华,2018)。价值属性复杂的数字遗产也相当于一种复调音乐,包含财产属性、文化属性、媒介属性等。本文将数字遗产视为由媒介技术演奏的“安魂曲”,在媒介属性的主旋律中凸显数字遗产的对话性特点,逝者的数字灵魂成为在“0-1”的数字矩阵中跳动的音符。整首曲子以死亡为序曲,在预设肉身死亡的氛围中,引出逝者在生前和各平台方关于数字遗产规划的协商,涉及逝者隐私权、被遗忘权、数字遗嘱等内容。曲子以记忆为间奏,在死亡进行过程中,连接起生者和各平台方对于逝者数字遗产安置问题的沟通,涉及遗产所有权、继承纠纷、数字悼念等内容。曲子以爱为终章,阐明整首曲目中隐含着生存世界和死亡世界的对话,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模糊了生死边界,将整个演奏推向高潮。数字遗产的媒介“安魂曲”具有复调音乐的特性,连接逝者、生者与技术平台之间的对话,跨越虚实时空和生死时空,导向一种互通性交流。
然而,安魂曲的宗教特质是让人们能在死亡中感受超脱,给予虚幻的安慰和永生的安宁,与人类尝试利用逝者的数字遗产“复活”逝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技术似乎成为“上帝”。所以在强调数字遗产对话性的同时,也需警惕技术蔓延失控而带来的存在性危机。人类的认知具有局限,生命的轮回也有其自在规律,若过分沉溺于技术的幻象,索拉里斯之海对人类的警示将不止是科幻作品的寓言,即便“飞向太空”,人类要面对的还是自己。由此,我们更应在数字遗产搭建的对话中学会自省,在尊重自然法则中保持生命的朴素,或许当面对死亡时也能如庄子般感慨:“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
注释:
①占有双重性: 数字遗产是网络运营商和网络用户通过网站等特定的服务平台共同创造的产物,其中网络运营商搭建数字遗产赖以生存的场所——服务平台,网络用户则拥有开启数字遗产库的钥匙——特定账号和密码,双方以不同的方式占有数字遗产。
参考文献:
Apple官网(2021)。如何为您的Apple ID添加遗产联系人。检索于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12360。
贝尔纳·斯蒂格勒(2012)。《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白庆华(2018)。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对我国戏剧创作的借鉴。《甘肃社会科学》,(02):108-112。
陈奇伟,刘伊纳(2015)。数字遗产分类定性与继承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6(05):78-84。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2017)。《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凤凰网(2022年4月5日)。数字遗产里的哀思:那些花、留言、跟帖、转发里的“朋友再见”。检索于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QqaYKa2nDVbgZ4q47JnEGWEyUGfM-_IvjmCW4jW3t1Eo。
顾理平,范海潮(2021)。作为“数字遗产”的隐私:网络空间中逝者隐私保护的观念建构与理论象。《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3(04):140-146。
高嘉遥,蒋璐璐(2021)。联结、交互和展演:数字遗产的媒介化生存。《当代传播》,(05):109-112。
郭小安,赵海明(2021)。媒介的演替与人的“主体性”递归: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思想及审思。《国际新闻界》,43(06):38-54。
光明网(2022年4月6日)。一个人去世后,他的数字遗产该如何处置?检索于https://m.gmw.cn/baijia/2022-04/06/1302885573.html。
环球时报(2022年3月5日)。日媒:如何处理“数字遗产”,在中国网络上引讨论(曾茂译)。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227079478222659&wfr=spider&for=pc。
吉姆·戈梅尔,戈登·贝尔(2014)。《全面回忆:改变未来的个人大数据》(漆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蒋银,吴倩(2014)。个人数字遗产的概念、管理与对策。《图书情报工作》,(08),10-17。
姜华,张涛甫(2020)。媒以达通:媒介学视野下的“金庸传奇”。《新闻记者》,(12):45-55。
雷吉斯·德布雷(2014a)。《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雷吉斯·德布雷(2014b)。《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马丁·海德格尔(2014)。《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澎湃新闻(2022年6月20日)。人类首个“赛博格”与渐冻症斗争5年后去世,享年64岁。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163671308602335&wfr=spider&for=pc。
孙玮,李梦颖(2021)。“码之城”: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探索与争鸣》,(08):121-129+179+122。
天眼查(2021)。数字资产凭证继承转移中的信息处理方法和相关装置。检索于https://zhuanli.tianyancha.com/e6009878022419a92654ea3b8de17be4。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2017)。《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2020)。《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伊莱恩·卡斯凯特(2020)。《网上遗产: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张淼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赵荔,李曦烨,杨舒惠(2012)。与账号有关的“数字遗产”继承问题。《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03):33-39+45。
章戈浩(2020)。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死亡盲点:一个生存媒介研究的视角。《全球传媒学刊》,7(02):21-34。
中国人大网(2021年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50028355286.htm?ivk_sa=1024320u。
中华遗嘱库(2022年4月18日)。一图了解《2021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主要内容。检索于https://www.will.org.cn/portal.php?mod=view&aid=2238。
BrubakerJ. R.Dombrowski, L. S.GilbertA. M.KusumakaulikaN.& HayesG. R. (2014April). Stewarding a legacy: responsibilitie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management of post-mortem data.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4157-4166).
GeambasuR.KohnoT.Levy, A. A.& Levy, H. M. (2009August). Vanish: Increasing Data Privacy with Self-Destructing Data. In USENIX security symposium (Vol. 316pp. 10-5555).
Gil-EguiG.Kern-Stone, R.& Forman, A. E. (2017). Till death do us part? Conversations with deceased celebrities through memorial pages on Facebook. Celebrity studies8(2)262-277.
Hurtado, J. (2021). Towards a postmortal society of virtualised ancestors? The Virtual Deceased Pers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ocial bond. Mortality1-1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6-10-07). An app for talking to the dead? Woman brings best friend back to life as AI chatbot. 检索于:https://www. ibtimes. co. uk/app-talking-dead-woman-brings-best-friend-back-life-ai-chatbot-1585318.
Jiménez-AlonsoB.& Brescó de Luna, I. (2022). Griefbots. A New Way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Dead?. 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1-16.
KneeseT. (2019). Networked heirlooms: the affective and financial logics of digital estate planning. Cultural Studies33(2)297-324.
Leddy K. (2019-05-03). Years agomy sister vanished. I see her whenever I want. The New York Times. 检索于https://www. nytimes.com/2019/05/03/style/modern-love-sister-vanished.html.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2019-04-29). Digital graveyards: are the dead taking over Facebook? 检索于https://www.ox.ac.uk/news/
2019-04-29-digital-graveyards-are-dead-taking-over-facebook.
Peoples, C.& Hetherington, M. (2015November). The cloud afterlife: Managing your digital legacy. In 2015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STAS) (pp. 1-7). IEEE.
Pitsillides, S. (2019). Digital legacy: Designing with things. Death studies43(7)426-434.
Sofka, C. J. (1997). Social support“ internetworks” caskets for sale, and more: Thanat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Death Studies21(6)553-574.
Sofka, C.& GilbertK. R. (2012). Dyingdeathand grief in an online universe: For counselors and educators.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The Washington Post (2019-08-29). Hey Google! Let me talk to my departed father. 检索于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19/08/29/hey-google-let-me-talk-my-departed-father/.
UNESCO (2003-10-17). CHARTER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IGITAL HERITAGE, Adopted at the 32n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 检索于:https://unesdoc. unesco.org/ark:/48223/pf0000179529.page=2.
WalterT.HouriziR.Moncur, W.& PitsillidesS. (2012). Does the internet change how we die and mour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64(4)275-302.
陈刚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沁柯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时代争议性议题传播的共识焦虑与沟通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XW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