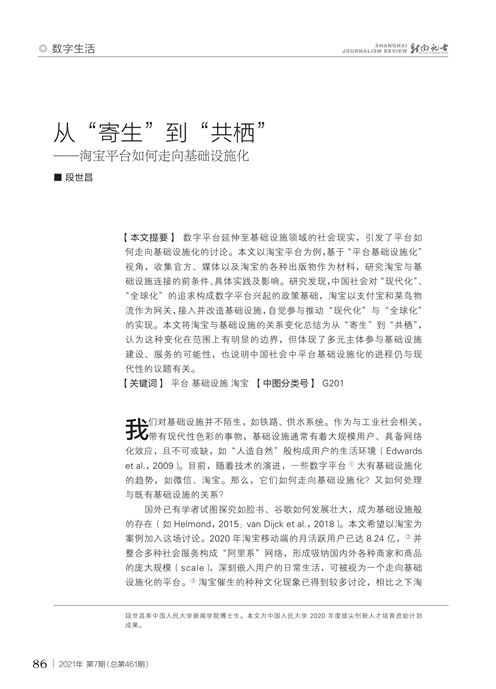从“寄生”到“共栖”
——淘宝平台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
■段世昌
【本文提要】数字平台延伸至基础设施领域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平台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的讨论。本文以淘宝平台为例,基于“平台基础设施化”视角,收集官方、媒体以及淘宝的各种出版物作为材料,研究淘宝与基础设施连接的前条件、具体实践及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对“现代化”、“全球化”的追求构成数字平台兴起的政策基础,淘宝以支付宝和菜鸟物流作为网关,接入并改造基础设施,自觉参与推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实现。本文将淘宝与基础设施的关系变化总结为从“寄生”到“共栖”,认为这种变化在范围上有明显的边界,但体现了多元主体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可能性,也说明中国社会中平台基础设施化的进程仍与现代性的议题有关。
【关键词】平台 基础设施 淘宝
【中图分类号】G201
我们对基础设施并不陌生,如铁路、供水系统。作为与工业社会相关,带有现代性色彩的事物,基础设施通常有着大规模用户、具备网络化效应,且不可或缺,如“人造自然”般构成用户的生活环境(Edwards et al., 2009)。目前,随着技术的演进,一些数字平台①大有基础设施化的趋势,如微信、淘宝。那么,它们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又如何处理与既有基础设施的关系?
国外已有学者试图探究如脸书、谷歌如何发展壮大,成为基础设施般的存在(如Helmond, 2015;van Dijck et al., 2018)。本文希望以淘宝为案例加入这场讨论。2020年淘宝移动端的月活跃用户已达8.24亿,②并整合多种社会服务构成“阿里系”网络,形成吸纳国内外各种商家和商品的庞大规模(scale),深刻嵌入用户的日常生活,可被视为一个走向基础设施化的平台。③淘宝催生的种种文化现象已得到较多讨论,相比之下淘宝所依赖的基础设施(比如支付与物流)在研究中的“可见度”却明显降低。实际上,被讨论较少也正符合基础设施的可见性(visibility)特征:基础设施出故障之前,人们通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Sandivg, 2013)。
一、文献探讨
从淘宝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处理与既有基础设施关系的核心问题出发,本研究基于Plantin等人(2018)提出的“平台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platforms)视角,通过聚焦平台借助“网关”(gateway, 指在技术系统之间起连接作用的事物)连接基础设施的前条件、具体实践以及相关影响,做一个在理论上结合技术社会学与媒介研究的尝试。
1.“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提出语境与内涵
“平台基础设施化”理论视角的提出,涉及平台研究与基础设施研究④逐渐交汇的理论脉络。在媒介研究中,“平台”(platform)一词早就被使用,这个称谓的建构涉及平台企业、用户和广告商等群体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Gillespie, 2010;Langlois & Elmer, 2013)。也正是对平台的不同理解构成三种主要的平台研究路径:关注平台技术层面的软件研究路径、强调平台影响社会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路径,以及探索平台如何构建多边市场从中牟利的商业研究路径(Poell et al., 2019)。当平台持续发展壮大,将触角延伸至基础设施层面之后,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结合基础设施研究来理解平台并解释相关现象。比如斯尔尼塞克(2017/2018:50)明确提出平台为不同群体的互动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设施,由此也可以轻易获取各种数据。van Dijck等人(2018:4)则认为谷歌、脸书等可被视为基础设施性平台(infrastructural platforms),在社会各种行业衍生出子平台,也支撑着其他的功能性平台(sectoral platforms)。不难想见,淘宝大致也是从简单的功能性平台逐步成长为基础设施性平台。⑤
Plantin和几位长期致力于基础设施研究与平台研究的学者,沿此理论线索在当下对两者的交汇做出了直接发言,并引起广泛回应。⑥他们结合前者的历史取向和后者的批判取向,提出以“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以及“基础设施的平台化”(platform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s)作为综合性的分析视角(Plantin et el., 2018)。
“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是指借助基础设施研究之理论资源,将平台的崛起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平台成为基础设施的具体过程与社会环境。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分析维度。首先是平台成为基础设施之前,作为主导权力的国家所奠定的前提性条件。政府长期占据大量社会资源,拥有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⑦但由于基础设施若发生故障会波及整个社会,即使是民主政体也会注意使基础设施的相关决策过程与公众“绝缘”(Keane, 2006)。一些在地分析进一步指出,特定国家赋予基础设施的想象,又会因当地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等因素而有所不同(Furlong, 2014; Essex & de Groot, 2019)。因此,研究基础设施要有意识地了解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意图,尤其是在政府通常占有更多资源与权力的后殖民国家与发展中国家(Larkin, 2013),从而明确特定社会中基础设施发展的前条件(pre-condition)。而探讨淘宝兴起的过程时,也要先回溯我国政府层面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寄予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想象。
另一个维度是平台与既有基础设施的关系。在“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过程中,Plantin等人还提到,商业力量进入后会在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替代性产品,传统垄断性的基础设施模式转向了去管制化、私有化以及碎片化(splintered)的状态,他们称之为基础设施的平台化(platformized)。⑧同时,新入场者会挑战既有基础设施,比如销售机顶盒的平台会挑战陈旧而垄断性强的有线电视系统(Sandvig, 2015)。Plantin等人敏锐地指出,普遍的网络化计算、持续变化的政治氛围,创造了一个适于平台扩张取得极大规模的环境,而迈向基础设施化的平台,与基础设施既要并存,也会构成补充或竞争的关系。
2.问题的聚焦:平台如何通过网关与基础设施连接
整体来看,这个框架有综合不同理论资源的优势,但解答其核心议题——平台与基础设施的关系如何变化、有何社会影响——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具体的研究问题仍可聚焦。比如Mukherjee(2019)就以印度一家快速崛起的通讯运营商Jio为例,分析其如何利用印度政府的“数字印度”政策,通过投资信号塔等手段来与基础设施连接,进而扩大自身规模,获取网络化效应,实现平台基础设施化。其次,Plantin等人提供的案例,如谷歌的基础设施化,侧重于平台与基础设施的融合(convergence),可能缺少对其他关系类型的考量。在现实生活中,平台逐渐成为一种“软基础设施”,与传统“硬基础设施”(Mattern, 2016)之间存在着诸如叠加、取代、加速“模糊”等多种复杂的情况。本文也是试图用“寄生”与“共栖”这样的生物学隐喻来描述淘宝平台与基础设施的动态关系。
另外,已经有学者沿此视角考察中国社会中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如Liang等人(2018)通过研究中国社会中信用系统的基础设施化,指出在这一过程中信用平台转换成对公民的监督机构,中国政府与私有化企业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Plantin和de Seta(2019)也分析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对国外互联网的限制而促成了本土互联网企业的快速成长,展现了国家对商业力量的促进作用。Zongyi Zhang(2020)则批判性地使用这一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中抖音迈向基础设施化时所引起的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但整体来看,这些研究比较少关注平台如何处理与国家及基础设施的关系,也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过程的本土化特征(de Kloet et al., 2019)。
基于此,本文选择聚焦“淘宝平台如何通过网关接入基础设施”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兼顾中国社会中影响平台发展、连接的前条件(主要是国家的政策)以及平台连接基础设施的具体实践(图1 图1见本期第88页)。网关是基础设施研究中的概念,用以说明不同的技术系统连接时,会依靠特定的事物来确保顺利互通,如当全球运输系统贯通时,有统一的运输标准和规定作为网关来确保彼此互联(Jackson et al., 2007),在本文主要指支付宝和菜鸟物流,下文会展开论述。
所以,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
1.淘宝如何成为接近于基础设施的平台?有哪些重要的社会(政策性)条件?
2.淘宝又是如何通过网关的连接,成为他者的基础设施?
3.这种连接对既有基础设施有何影响?
二、研究资料及获取途径
收集材料时,研究者通过互联网检索、筛选1990年到2003年⑨有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的相关公开文件、期刊论文,梳理关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践以及话语内容。同时搜索查阅淘宝官方出版的资料,整理马云的公开信、出版书籍、演讲,梳理有关平台、支付宝、快递系统与基础设施关系的叙述。
此外研究者还使用了中华数字书苑—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分别以“信息基础设施”、“支付宝”、“菜鸟物流”为关键词,同时重点检索2003年淘宝刚兴起时、2009年“双十一”开始之后的报纸文章,并结合虎嗅、钛媒体上的相关报道,作为理解社会多元主体话语实践的材料。
三、连接的前条件:“现代化”、“全球化”想象及实践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过程复杂、成本高昂,其建立常要依靠各国政府或公私合作的机构在资金、法律以及政治上的支持。同时,基础设施被干扰的话容易产生大范围危害乃至灾难,出于安全考虑,可干预基础设施的主体数量也被严格控制。在极权政治体系里,建设基础设施的决定一般由少数人垄断,而即使在民主政体里,基础设施的制定过程也会被黑箱化。比如,高铁的发车、抵达时间公开透明,每日固定,但这个时间如何决定、铁路规格如何选择,却常不得而知。也因此,彼得斯认为,“从奇阿普斯开始,基础设施一直都是独裁者和暴君的掌中玩物”(彼得斯,2015/2020:36)。为了在研究时将基础设施“化暗为明”,研究者需要有意识地厘清千丝万缕的头绪,凸显肇因的关键性(唐士哲,2020)。
要了解如今淘宝怎样得以逐渐走向基础设施化,就需要先回溯信息传播技术在中国社会中被重视进而大规模建设的历史节点。尤其是要对中国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得以发展的政策性条件加以解读,澄清最初构想和资助技术的意图和意识形态(布莱恩·拉金, 2008/2012:10)。毕竟,即使是日后中国社会中高度数字化的平台在走向基础设施化时,也需要依赖既有基础设施并且在其上生长(Horst, 2013)。而且,我们也会发现,正是这些早期有关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政策性条件,很大程度上形塑了2000年以来中国主要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基本环境。
1.实现现代化
从冷战时期开始,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越发激烈。基于互联网的通讯技术悄然崛起,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到新加坡的“智慧岛”,以及韩国的“国家基础信息系统”方案,国家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信息技术研究投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国家的信息政策也是其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情境的反映(Kahin et al., 1995:3)。“第三次浪潮”的声音传到正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中国,首先吸引中国社会眼球的,自然是信息基础设施的经济功能。按照郑保卫、谢建东(2018)对我国历代领导人互联网建设思想的梳理,邓小平比较早地强调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1984年2月,邓小平(1993:52)在谈及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时说,曾有日本朋友给他提过两个建议:一是“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二是“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考虑到中国国情,他认为第二个建议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但第一个建议很重要,应该加以实行。同年,邓小平给新华社新创办的《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郑保卫,谢建东,2018)。之后的领导人江泽民(2009)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四个现代化,哪一个也离不开信息化”。两位领导人的判断——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化过程的必要步骤——也成为日后讨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必要性时,常使用的话语资源(如乌家培, 1995;高新民, 1997;钟义信, 2000)。⑩
与之一致的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成当时社会中现代化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推进信息化……首先要规划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作”(乌家培, 1996; 朱伟, 1997),电子商务则是这种认知的具体延伸。根据1997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朱伟的发言,当时理解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国家信息网络、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人才,信息政策、法规和标准(朱伟, 1997)。信息基础设施的直接目标是要“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装备”,“为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体系运行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服务”,缩小地区差距,为国民提供优质服务。信息基础设施与“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等不同的话语变体组合在一切,被当作“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各种挑战的基础”(刘志迎,黄志斌,1998)、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当时的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其实也已经表示,电子商务是信息化过程中一种应用(吴基传,1998)。当时语境下人们所说的电子商务仅仅是指网络上甚至偏向国际间的交易活动,毕竟人们无法预料到今天以淘宝、京东等为代表的如此普及的互联网商业活动。但是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也能看到,今日的淘宝在社会使命上自觉地采取了与当时类似的叙述。
2.应对全球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其实践过程来看,也与应对全球化的进程有关。1993年开始启动的“金”系列工程,包括推动金融电子化建设的“金卡工程”,将外贸部门用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国内外贸易信息化的金关工程,以及相对来说更为重要的金桥工程,将前两者与全国重要企业集团连接起来,建设全国性的经济信息公用网。大多数讨论在提及这些项目的必要性时,常以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工程作为背景或论据(如:邓寿鹏,1992;金建,1994;吴赣英,饶艳超,1997)。其中或是将信息高速公路简化为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手段,或是提到,在我国基础设施条件差一些的情况下,无法建“高速公路”也要建“中速”或“低速”公路(刘纪兴,1996)。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信息高速公路”只是“信息基础设施”的一种表达,并不真的存在“高速”与“低速”之分,但美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内激起的热切想象可见一斑。
美国的具体策略也被作为模仿的对象,比如由于美国实行市场经济,大量投资来自私人企业,中国在本身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也提倡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企业信息经济化,大力吸引外资(钟义信,1995;汪冰,张海峰,1995)。整体而言,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中国积极学习和模仿的直接对象。今天中国腾讯、阿里、百度的开创者,也大多受到硅谷产品的启发,吴晓波(2017:3)则直接称之为美国的克隆版。2003年5月10日,于杭州湖畔花园小区的一栋别墅里诞生的淘宝网,本身就是对标易趣的产物。
但细究之下,以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等类似国外计划为参照,不少媒体也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到“信息高速公路争夺战”的层面,类似的表述包括“新一轮科技竞争启幕”、[11] “参与世界科学技术竞争迎接新产业革命挑战”(张涛,1995),“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后发优势”等提法也屡见不鲜。这种叙事,与李金铨(2004:294)提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媒介注重宣传民族主义的整体氛围也符合。Schiller(1999:86)则更准确地提到,后起国家对于信息技术的恶补源于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落后以及更深依赖的恐惧。而这个案例则显示,这种恐惧具体落地时会转化为积极模仿与谨慎防备的微妙结合。与此对应,在谈及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时,互联网上“中文信息太少”、英文信息主导等突出全球化风险的“信息安全”问题(朱伟,1997)被一再强调。“金”系列工程中,最终也包括了对中国互联网环境影响巨大的防火墙项目。
统合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理想中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他者——正在迈入信息化的西方社会,这个他者既构成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一定参照,又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应对对象。这种态度构成中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的总体背景、对信息基础设施的社会期待。多年后,淘宝在通过网关连接基础设施、逐渐走向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也对在中国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自己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有着明确的理解和实践。
四、连接的实践和影响:接入与改造
如果说,我国早期的现代基础设施理想构建了平台快速崛起的外部环境,真正要走向基础设施化,平台还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网络(Star, 1999; Edwards, 2003)。而网关则是起连接作用的社会技术体系组成部分,它们提供了“插座”和“插头”,使得新系统可以轻易接入到现有架构中(Jackson et al., 2007)。在基础设施从互不相通的单个社会技术体系到相互连接发展成为网络时,各种设备、社会机构都会作为网关出现。比如直流电和交流电的转换器、硬件和软件得以连接的以太网(Ethernet)、规制互联网交易的法律等。
如何解决在线交易和物流系统的障碍,则是中国电子商务行业从早期就一直面临的难题(Tai, 2007:119)。在这个意义上,支付宝和菜鸟网络从建立到壮大的实践过程,正是淘宝扩大自身规模、通过网关与既有基础设施连接的重要步骤。这也带来新的问题,随着淘宝的接入,影响力强、规模巨大、有着一定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Dooms et al, 2013)的既有基础设施,又是否会产生变化呢?
1.接入基础设施
无论是支付宝还是菜鸟网络,在连接过程中,都要面临如何获得既有基础设施认可、扩大规模和影响力的问题。而支付问题作为网络交易的重要一环,首先摆在淘宝面前。在2003年,非典速成了大批网上消费者(邓瑾,2003年7月14日),易趣作为主要的交易网站收益颇丰,马云认为“要等到支付问题解决了,就没机会了”。[12]在他的促成下,阿里巴巴5月份先成立了淘宝网作为线上交易平台。至于尚未完全解决的支付问题,则留待和与银行接洽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支付宝与金融基础设施的连接,其意义不单是在技术层面简化最初邮寄货款、虚拟账户充值等繁琐的交易流程,更重要的是,支付涉及资金流动,牵扯到社会信任,与银行的连接有助于强化用户的安全感。相关报道中也直接提到,支付宝通过与银行合作,不只是“为网上交易提供网上银行支付结算的新模式”,也有助于“消除市民的担忧”(邵庆义,朱聚强,2003年10月28日)。
但在中国社会中,包括银行在内的公有制国企,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的基础设施,本身又有一定惯性(inertia)(Strand,2010),支付宝能与基础设施网络连接成功,也不乏一些“偶然”因素。在电子支付尚未普及、电子支付牌照没有放开的2003年,支付宝试图接入金融基础设施,既有如何处理大量数据的技术问题,也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好在,支付宝的合作方恰巧是在工商银行中有较大影响力的西湖支行,向总行反映能够得到重视。工商银行调动北京、珠海和浙江三地的技术中心一起开发,在2005年改造系统完成后,才初步缓解了转账的工作压力(由曦,2017:35)。或许中国广阔并且存在地方差异的社会环境本身就是天然的实验室,也难怪在淘宝大获成功后,有上海的领导提出这样的问题,“上海为什么没出马云”。[13]这样看来,既有基础设施对网关及其背后平台的优势地位,以及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与之类似但又有区别,菜鸟网络与既有物流基础设施的连接,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以及微妙的权力关系。菜鸟网络的建设本身,来自于意想不到的“爆仓”问题。2009年,随着“双十一”首次启动,快递运力的问题逐渐凸显,之后快递公司常要提前紧急调集上万名服务人员进行“备战”。[14]2010年起,阿里巴巴自行筹建“菜鸟网络”,在其官方网站上,菜鸟网络自身的定位目标是“建设整个物流行业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面向未来的、基于新零售的智慧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打造一张全球化的物流网络”。
但是,菜鸟网络最开始该如何连接既有的物流基础设施,却并没有绝对明确的定位,是要构成一个实体性质的快递公司?还是别的形态?[15]直到伴随着阿里对不同快递公司的入股和投资,以及菜鸟网络自身技术体系的成熟,菜鸟网络的连接方式才逐步清晰并稳定下来,即主要利用自己的数据优势,来与快递公司合作。
具体来说,在连接过程中,依托阿里巴巴所具备的平台优势,菜鸟网络既研发先进的数据技术,也投资配套智能仓库等硬件,逐渐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16]在经历了初期摸索之后,菜鸟网络的革新性得到了普遍认可,也成为其接入物流基础设施的优势所在。比如电子面单、配送路线智能规划系统,被视为实现了物流快递最基础单元的数字化、在线化,极大提高了整个快递行业的信息化水平。[17]但这种合作是否存在权力的倾斜,则是到连接完成后,在平台对基础设施的改造实践中才显示出来。
2.改造基础设施
初期的连接完成后,支付宝对金融基础设施产生了以数字化为突出表现形式的改造。支付宝将钱转化为数据(Westermeier, 2020),被认为给普通居民带来了更便利的交易方式,同时直接促进着无现金社会的形成。[18]这种对既有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方式的改变,也得到了大力推广,比如支付宝小程序上线了提供政府服务的“电子政务”,到2019年,全国共计已经有46个国务院部门、32个地方政府、200多项服务上线支付宝,[19]这种举措被视为政府部门通过数字化推动城市管理、提升服务质量、迈向现代化的一种体现。[20]同时,支付宝以基于既有基础设施但又有差异的服务大力在海外开疆拓土,比如支付宝在2018年实现了40个境外目的地九成以上商户的使用支持,是全球范围内用户破10亿的最大非社交类型应用,由此也被归入到新华社设立的“民族品牌工程”之中。[21]在构成现代化的生活以及推进全球化的出海方面,支付宝的正面作用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不过,这种改造也必然要面临既有基础设施的惯性。2016年金融管理机构央行颁布《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被认为是遏制支付宝衍生产品余额宝对银行利益造成的威胁。同时期马云在演讲中提到,“有时候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纸文件”,被不少文章作为支付宝的回应加以引用(苏曼丽,2014年3月19日)。即使支付宝从2003年起就已经颇具声势,但直到2011年,拿到央行颁布的国内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宝才被认为是成功“上户口”(由曦,2017:102)。实际上,平台固然可以使得非正式活动标准化(Ticona & Mateescu, 2018),但是否能构成真正的改造,则仍有诸多变数。
与之形成映照的是,由于数据方面的优势,淘宝通过菜鸟物流不单是接入物流基础设施,同时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嵌”而独立,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传统物流公司。这种改造的积极意义同样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从国内来说,菜鸟物流的作用包括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诸多就业岗位、普通用户的生活得到了极大便利、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促进,[22]被肯定成为中国智慧物流网络重要力量(李心萍,2018年11月22日)。在国际方面,菜鸟物流改造传统物流,促进了国内物流企业与世界市场的连接,构建了中国的智慧物流网络,成为走向全球的中国经验。[23]马云也提出,由于中国本身的商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这个平台还将推动商业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合作,促进国内不同地区、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马云,2015)。马云(2018)曾做出这样的表述,“终于作为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这是划时代意义的。一直以来基础设施是国有企业做,今天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希望为这个时代、为这个社会做……”不难看出,菜鸟物流也纳入到以促进国内发展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全球化为目标的叙事和实践之中。不过,菜鸟物流这种新自由主义式的表达技巧并不罕见,van Dijck、Poell和De Waal(2018:23)认为,像Uber和Airbnb这样的平台在发展初期也认为自己不同于一些低效的政府部门。事实上,淘宝离不开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和科技民族主义情结(管泽旭,张琳,2020),而且看似不同的表述最终都指向“现代化”、“全球化”的目标,殊途同归。
另外,菜鸟物流对物流行业的改造是否要有明确的限度,也越来越成为行业中的重要话题。目前快递公司中体量最大的中通在其财报中提到:“尽管阿里巴巴不是我们的直接客户,但它可以对其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交易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包括通过指示每个订单的首选快递公司来履行订单。” [24]淘宝的竞争性对手京东更犀利地提出,“快递利润会被菜鸟吸走”。阿里巴巴则一再声明,菜鸟物流并不会介入硬件和整个作业层面的管理,不会跟物流服务商去抢“饭碗”,而是要做“信息服务集成商”。[25]但实际运行过程中,菜鸟物流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既有基础设施,仍然没有确定的共识。甚至于2017年,菜鸟物流与顺丰因为数据问题而发生争执,最终要靠国家邮政局出面,要求双方进行协调。[26]总结来看,淘宝通过网关连接基础设施的过程,分别以获得管理机构的认可、充分利用数据优势作为比较重要的节点,既涉及了物质体系的变动,也卷入不同的行动主体,还可能激发政府层面的管理和介入。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淘宝在实践和话语上延续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国家与市场的力量如何进行互动。同时,平台与既有基础设施的关系,也因为这种连接实践而悄然发生了变化,网关最终起到的作用,又不单单是连接,还有对既有基础设施的一定改造,推进了整体的数据化(datafication),这在两个网关的连接、后续影响上都得到了体现。笔者尝试将这个过程以表格的形式总结如下:
五、结论与讨论:从寄生到共栖
到此,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如下:
1.实现现代化与应对全球化是中国进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时的重要叙事与直接动力,体现在初期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并构成日后淘宝等互联网企业产生、发展的前提性条件。
2.淘宝在连接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根据面对的支付和物流问题,构建了作为网关的支付宝和菜鸟物流,并自觉沿袭了有关“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叙事,也通过具体实践得到了国家的一定认可。
3.在整个连接过程中(图2 图2见本期第93页),淘宝依托于既有基础设施的支撑,同时又对其进行了一定改造。
如果说,最初淘宝还“寄生”于金融、物流等基础设施,那么走向基础设施化的淘宝,则能够推进货币的电子化、物流的数据化,实力逐渐壮大到能与既有基础设施“共栖”的地步。需要说明的是,用“寄生”、“共栖”这样的生态学隐喻,只是为了强调动态的网络中淘宝与既有基础设施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个从“寄生”到“共栖”的变化,其发生范围,包括淘宝的基础设施化程度,有着明确的边界。一方面淘宝始终寄生于国家所构建的基础设施网络以及社会环境中。早期淘宝得以产生、发展的基本条件受益于国家的相关政策。淘宝进行连接的具体过程中,国家的管理机构极大左右着网关的发展和扩张。在淘宝与既有基础设施连接成功、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认可的今天,商业力量也仍然要服从国家的引导和规范来实现良好发展,比如今年蚂蚁金服的上市风波、阿里巴巴被处以反垄断罚款。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的基础设施始终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彻底私有化,淘宝基础设施化之后也要与既有基础设施共栖于社会结构之上。商业化力量无论如何壮大,平台基础设施化无论如何如火如荼,都一定会止步在政策规定的楚河汉界之内。这也是与西方社会中,商业力量强大到可以左右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社会生态而不同的现象。
从寄生到共栖的变化也带有一定的积极意味。在中国,平台对于基础设施的介入和改造,体现了多元主体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也为普通人提供了单一服务的替代性方案。如支付宝提供银行之外财富交易的便捷手段,民营物流成为消费者在邮政之外的多选项。当然,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后期容易滑向垄断,斯尔尼塞克(2017/2019:123)也忧心忡忡地问道:互联网世界会因为基础设施性平台的竞争走向割据吗?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了。
此外,不难看出,“追寻现代中国”的诉求仍然贯穿于我国社会中平台基础设施化的过程,商业力量也很敏锐地与这种社会需求接合。如阿里巴巴以“服务中小企业”、“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为口号,声称要推进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重构,提出“电商扶贫”并被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而实行,大量淘宝村由此涌现。对比来看,西方社会较早实现了工业化,平台之类的商业力量则常被描述为对公共性的威胁。这种差异似乎也印证了萨义德(1993:190)所言,“在非西方,现代性还是方兴未艾,对那些被传统与正统束缚的文化来说,仍是巨大的挑战”。这其实也体现出以中国作为方法(沟口雄三,1989/2011:130),生产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最后,淘宝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也提醒我们再思考“平台”的含义。淘宝最初是用于网上交易的功能性平台,通过吸纳大量小资产者,渗透到不同的社会部门,成为基础设施性平台。这种划分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平台”概念有联系又有区别,平台及相关概念(如平台型媒体)如何缘起、如何在中国跨文化旅行(谭小荷,2019),仍有待观念史层面的深入挖掘。■
注释:
①平台的定义众多,最初指游戏设计平台,再到内容分享网站,再到社交媒体应用。本文使用van Dijck等人提出的定义,下文会详述。
②检索于https://www.alibabagroup.com/cn/ir/earnings。
③现实依据是:淘宝截至2020年12月31日活跃用户达9.02亿,与全国地区乃至海外的大量商家合作,规模(scale)巨大;集纳支付宝、菜鸟物流、盒马等彼此互联的产品,有网络化效应。
④基础设施研究大致有历史学和社会学(包括现象学)两种取向,可参阅文末列出的Edwards的文章。
⑤早期淘宝形式简陋,但也作为中介为不同群体提供服务,促成网上交易,发挥着“平台”的功能。
⑥截至2021年5月5日,在这篇文章已有543次引用,诸多学者继续探讨平台研究与基础设施研究如何结合。
⑦Graham与Marvin(2001)的经典著作《Splintering Urbanism》中提出的概念“现代基础设施理想”(modern infrastructure ideal),涉及基础设施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至今仍有许多研究与之对话。
⑧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与基础设施的平台化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也可以用于讨论不同的对象。
⑨1990年,我国开始比较集中讨论“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2003年,淘宝网正式上线。
⑩国家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对此较早做了大量研究,当时也常被引用,故这部分参考文献相对集中。
[11]《信息高速公路争夺战》,《环球时报》,1994年5月22日;《时事新一轮科技竞争启幕》,《浙江日报》,1994年7月18日,4版。
[12]《电子商务的另类圈钱》,《经济观察报》,2003年b10月20日A19版,作者鲁珺瑛。
[13]人民网(2008年2月22日)。沪粤两位书记探讨上海为何不出马云。检索于http://finance.people.com.cn/GB/6912033.html。
[14]《包裹战争》,《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1月11日,21版。
[15]钛媒体(2014)。《马云的菜鸟网络去哪了?》。检索于https://www.tmtpost.com/88715.html。
[16]《菜鸟网络卡位“五新”智慧物流基建》,上海证券报,2017年3月30日,作者温婷;新华网(2017)。《阿里巴巴增持菜鸟 未来五年再投1000亿建设全球物流网络》。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7-09/26/c_ 1121726471.htm。
[17]虎嗅网(2019)。《马云走后,留下一个怎样的物流江湖?》。检索于https://www.huxiu.com/article/317702.html;钱江晚报(2019)。《菜鸟智慧物流催生5类新职业新岗位员工收入翻一番》。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0413161474215993&wfr=spider&for=pc。
[18]新华每日电讯(2017)。“无现金社会”的喜与忧。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04/18/c_ 136216594.htm。
[19]光明网(2019年6月5日)。46个国务院部门、32个地方政府200多项服务上线支付宝。检索于http://it.gmw.cn/2019-06/05/content_ 32895788.html。
[20]浙江在线(2019)。电子政务,浙江领跑。检索于http://www.huaxia.com/ztlx/zjxw/2019/05/6100451.html。
[21]新华网(2019)。《支付宝首席架构师王维:支付宝成为全球最大非社交App》。检索于http://www.sh.xinhuanet.com/2019-05/10/c_138048866.htm。
[22]新华网(2017)。《菜鸟宣布新品牌战略 让中小物流搭上智慧快车》。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7-05/22/c_ 1121013996.htm。
[23]人民日报(2018)。《物流方案走向全球 中国经验功不可没》。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908918679730284&wfr=spider&for=pc。
[24]虎嗅网(2019)。《中通、圆通宣布双十一涨价,民营快递游走低价刀刃》。检索于https://m.huxiu.com/member/1871009.html。
[25]澎湃(2016)。《刘强东说快递利润会被菜鸟吸走,菜鸟:他不懂什么叫平台共享》。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500214;人民网(2016年11月17日)。菜鸟网络CEO童文红:智慧物流引领换道超车。检索于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1117/c14677-28876935.html。
[26]新华网(2017c)。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7-06/02/c_ 129623869.htm。
参考文献:
布莱恩·拉金(2008/2014)。《信号与噪音》(陈静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邓瑾(2003年7月14日)。《阿里巴巴雾中淘宝》,《经济观察报》,A31版。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高新民(1997)。信息化和我国的现代化。《再生资源研究》,(2)。
沟口雄三(1989/2011)。《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管泽旭,张琳(2020)。阿里巴巴的进化史与小资本主义的平台化:对本土语境平台化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28-49。
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心萍(2018年11月22日)。新物流,长啥样。《人民日报》。
刘纪兴(1996)。正确认识建设我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必要性。《情报资料工作》,(3),38-39。
刘志迎,黄志斌(1998)。知识经济与产业结构重整。《宏观经济管理》,(7)。
马云(2011)。《马云写过的公开信》。检索于https://www.cnblogs.com/zhenjing/articles/mayun.html。
马云(2015a)。《马云发布致股东公开信5000字详解阿里战略》。检索于https://tech.qq.com/a/20151008/059727.htm。
马云(2015b)。《中国将成为美国中小企业的下一个希望》。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18182249_115565。
马云(2018)。《完整版:2018全球智慧物流峰会——马云演讲实录》。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235569581_100157149。
尼克·斯尔尼塞克(2017/2019)。《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邵庆义,朱聚强(2003年10月28日)。阿里巴巴“淘宝”工行信誉,《杭州日报》,2版。
苏曼丽(2014年3月19日)。马云: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新京报》。检索于https://finance.qq.com/a/20140320/007876.htm。
谭小荷(2019)。从Platisher到“平台型媒体”—— 一个概念的溯源与省思。《新闻记者》,(4),28-37。
唐士哲(2020)。海底云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探问。《新闻学研究》,(145),1-48。
乌家培(1995)。关于中国信息化道路的几个问题。《中国科技资源导刊》,(8),7-10。
乌家培(1995)。中国信息化道路探索。《经济研究》,(6),67-72。
乌家培(1996)。关于我国发展信息产业的若干思考。《情报学报》,(5),350-353。
吴基传(1998)。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谈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国科技资源导刊》,(10),7-7。
吴晓波(2017)。《腾讯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谢雨蓉(2018年8月13日)。《物流“跑得快”也要“跑得好”》,《人民日报》。
由曦(2017)。《蚂蚁金服——科技金融独角兽的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
约翰·彼得斯(2015/2020)。《奇云》(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涛(1995)。参与世界科学技术竞争迎接新产业革命挑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40-44。
郑保卫,谢建东(2018)。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互联网思想的主要观点及理论贡献。《国际新闻界》,(12),50-66。
朱伟(1997)。中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现状。《情报学报》,(6),403-407。
De KloetJ.PoellT.Zeng, G. & Chow, Y. F. (2019).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infrastructuregovernance, and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3)249-256.
Dooms, M. , VerbekeA. , & HaezendonckE. (2013).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nd path dependence in large-scal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port of Antwerp case (1960-2010).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2714-25.
Edwards, P. N. (2003). Infrastructure and modernity: Forcetim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technical systems.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1185-226.
Edwards, P. N. , Bowker, G. C. , JacksonS. J. &WilliamsR. (2009). Introduction: an agenda for infrastructure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10 (5)6.
Essex, S. , & de GrootJ. (2019). Understanding energy transitions: The changing versions of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ideal and the ‘energy underclass’ in South Africa, 1860–2019. Energy Policy, 133.
Furlong, K. (2014). STS beyond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ideal”: Extending theory by engaging with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in the South. Technology in Society38139-147.
Graham S and Marvin S . (2001) .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Gillespie, T. (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12(3)347-364.
Jackson, S. J. , EdwardsP. N. , Bowker, G. C. &KnobelC. P. (2007). Understanding infrastructure: Historyheuristics and cyberinfrastructure policy. First Monday, 12 (6).
Helmond, A. (2015). The 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 Making web data platform ready. Social Media+ Society1(2)1-11.
Horst, H. A. (2013). The infrastructures of mobile media: Towards a future reseach agenda.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1(1)147-152.
Kahin, B. , & Abbate, J. (Eds. ). (1995). Standards policy for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MIT Press.
LangloisG. , & ElmerG. (2013). The research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Culture machine1-17.
Larkin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327-343.
Liang, F. , DasV. , KostyukN. &Hussain, M. M. (2018). Constructing a data‐driven society: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state surveillance infrastructure. Policy & Internet, 10 (4)415-453.
Mukherjee, R. (2019). Jio sparks Disruption 2. 0: infrastructural imaginaries and platform ecosystems in ‘Digital India’. MediaCulture & Society41(2)175-195.
Mattern, S. (2016). ScaffoldingHard and Soft. Infrastructures as Critical and Generative Structures. Spheres: Journal for Digital Cultures, 31-10.
Plantin,de Seta, G. (2019). WeChat as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 (3)257-273.
Plantin, Lagoze, C. , EdwardsP. N. & Sandvig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20 (1)293-310.
Plantin, J. C. , & PunathambekarA. (2019). Digital media infrastructures: pipesplatformsand politics. MediaCulture & Society41(2)163-174.
SaidE. W. (2012).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Sandvig, C. (2013). The Internet as infrastructur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
Sandvig, C. (2015). The Internet as the anti-television: Distribution infrastructure as culture and power.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225-245.
Schiller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MIT press.
Star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43(3)377-391.
StrandJ. (2010). Inertia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ome analytical aspectsand reasons for in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choices. 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2(1)51-70.
Tai, Z. (2007). The Internet in China: Cyberspace and civil society: Routledge.
TiconaJ. , & Mateescu, A. (2018). Trusted strangers: Carework platforms’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New Media & Society20(11)4384-4404.
van DijckJ. , PoellT. , &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stermeier, C. (2020). Money is data–the platformiz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3(14)2047-2063.
段世昌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 2020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