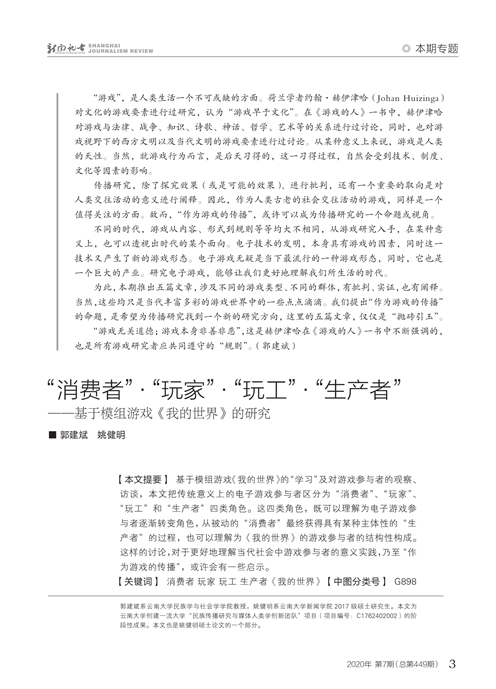“消费者”·“玩家”·“玩工”·“生产者”
——基于模组游戏《我的世界》的研究
■郭建斌 姚健明
【本文提要】基于模组游戏《我的世界》的“学习”及对游戏参与者的观察、访谈,本文把传统意义上的电子游戏参与者区分为“消费者”、“玩家”、“玩工”和“生产者”四类角色。这四类角色,既可以理解为电子游戏参与者逐渐转变角色,从被动的“消费者”最终获得具有某种主体性的“生产者”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我的世界》的游戏参与者的结构性构成。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中游戏参与者的意义实践,乃至“作为游戏的传播”,或许会有一些启示。
【关键词】消费者 玩家 玩工 生产者《我的世界》
【中图分类号】G898
“游戏”,是人类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对文化的游戏要素进行过研究,认为“游戏早于文化”。在《游戏的人》一书中,赫伊津哈对游戏与法律、战争、知识、诗歌、神话、哲学、艺术等的关系进行过讨论,同时,也对游戏视野下的西方文明以及当代文明的游戏要素进行过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当然,就游戏行为而言,是后天习得的,这一习得过程,自然会受到技术、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传播研究,除了探究效果(或是可能的效果)、进行批判,还有一个重要的取向是对人类交往活动的意义进行阐释。因此,作为人类古老的社会交往活动的游戏,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故而,“作为游戏的传播”,或许可以成为传播研究的一个命题或视角。
不同的时代,游戏从内容、形式到规则等等均大不相同,从游戏研究入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透视出时代的某个面向。电子技术的发明,本身具有游戏的因素,同时这一技术又产生了新的游戏形态。电子游戏无疑是当下最流行的一种游戏形态,同时,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研究电子游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为此,本期推出五篇文章,涉及不同的游戏类型、不同的群体,有批判、实证,也有阐释。当然,这些均只是当代丰富多彩的游戏世界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们提出“作为游戏的传播”的命题,是希望为传播研究找到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里的五篇文章,仅仅是“抛砖引玉”。
“游戏无关道德;游戏本身非善非恶”,这是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不断强调的,也是所有游戏研究者应共同遵守的“规则”。(郭建斌)
引言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开篇就有这样一句话——“游戏早于文化”(约翰·赫伊津哈,2014:1)。并且,“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创活动从一开始就全部渗透着游戏”(赫伊津哈,2014:1)。这意在表明游戏并非“本能”,又非“思想”或“意志”,而只是“游戏有意义”这样一个事实。进而言之,游戏也是人类交往、沟通的一种方式、形态,值得从传播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像人类学家格尔兹借鉴边沁的“深层游戏”(deep play)概念对巴厘岛斗鸡的分析一样,去“了解在其他山谷放牧其他羊群的其他人所给予的回答,从而把这些答案收入可供咨询的有关人类言说的记录当中”(克里福德·格尔兹,1999:34)。虽然本文还暂时无法对“游戏与传播”这样一个巨大的命题做出回答,与格尔兹所说的“深描”尚有差距,但这却是本文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和追求的目标。
随着科技的发展,游戏内容、表现形式在不断发生改变,游戏的边界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游戏实践也随之变化。1971年,Atari公司创始人Nolan Bushnell和Ted Dabney早期开发的Computer Space,是第一款上市销售的视频游戏;1972年,第一台家用游戏主机Magnavox Odyssey发布。①此后,电子游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据伽马数据发布的《2019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330.2亿元,同比增长8.7%;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4亿人,同比增长2.5%。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款名为《我的世界》(Minecraft,简称MC)的模组游戏。2015年,市场研究公司Octoly发布当年2月份的YouTube热门游戏视频排行榜,这份榜单显示,当月《我的世界》的YouTube游戏视频观看次数超过43亿,占榜单所有20款游戏的40%;③
YouTube在其2019 Rewind年度盘点视频中公布了一个游戏观众统计数据,《我的世界》相关内容在一年之内获得了1002亿次浏览量,成为游戏相关视频的浏览量之最,排在其后的游戏相关内容《堡垒之夜》只获得609亿次浏览量。④
这是我们选择《我的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模组”是创作游戏修改版本(modifications,简称“mod”)的音译,是指人们对游戏中的道具、武器、角色、事物、地图、故事情节等进行的修改。最高级别的mod是把原游戏中除引擎外的所有内容全部换掉后,形成“完全修改版”,游戏修改者被称为“模组制作者”,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与一般的“玩家”不同,模组制作者在游戏实践中显示出利用游戏本身作为独特工作的表达行为,即除了玩游戏外,还参与了游戏制作的过程,表现出了较强的主体性、参与性、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影响力。这是本文选择《我的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一、文献综述
“游戏”的概念在古典主义时期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中就已经出现,早期关于游戏的讨论大多是从艺术哲学切入的。在过去二百余年中,康德、席勒、斯宾塞、朗格、谷鲁斯、弗洛伊德、胡伊青加、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或主张艺术游戏论,或对艺术与游戏的关系进行讨论。有学者把上述学者们对于游戏的讨论归纳为自由论、和谐论、虚拟论、融合论和内在目的论五种(董虫草,2006)。
在既往关于游戏的定义中,或是将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活动,或是定义为一种艺术品的存在方式,或是将游戏界定为一个特殊的系统,不一而足。关萍萍在其博士论文中总结了近现代7个具有代表性的“游戏定义”(关萍萍,2010),此处不再赘述。
随着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游戏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商业娱乐媒体的形态进入大众生活,并逐渐成为当时日本、美国和欧洲娱乐工业的重要基础,“电子游戏”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开始涌现。1971 年被外国学者称为游戏研究元年,教育学家布赖恩·萨顿·斯密斯(Brian Sutton Smith)出版了专著《游戏研究》(The Study of Games),此后的四十多年间,他又陆续出版了研究游戏的专著十余本。⑤
在“电子游戏”时代,玩游戏的人通常也被称为“玩家”。玩家行为是游戏研究者们的研究重心之一,早在古典时期,学者就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个体游戏时的心理需要、行为动因和个体特征。其中,“席勒—斯宾塞理论”以及“松弛理论”对于游戏的讨论影响较大(周逵,2016)。
Richard Bartle通过对MUD(Multi-User Dungeon,多用户虚拟空间)类游戏玩家行为的观察,从目标对象(游戏中的其他玩家还是游戏世界本身)和行为模式(单向影响还是双向交互)两个维度来理解玩家行为,认为游戏中存在杀戮者、成就者、探索者以及社交者这四种类型(Bartle, 1996)。这成为后来游戏玩家研究的奠基之作。
Ben Cowley等运用心流理论(flow theory)分析游戏玩家,为玩家研究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综合方法,以更深入地研究游戏的沉浸(Cowley et al., 2008)。Nichlas Yee基于Bartle的玩家类型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游戏玩家动机的实证研究,发现成就、社交和沉浸等关键动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类型”,而是可以进一步细分并且相互关联,同时确定了更多样化的玩家行为模式(Yee, 2006)。
国内学者同样主要通过量化的方式来研究玩家的游戏行为,尤其是玩家玩游戏的动因。如钟智锦根据问卷调查,探讨了玩家在参与网络游戏过程中追求个人成就、享受社交生活、沉浸虚拟世界以逃避现实的三种动机,以及每个动机对游戏时长和游戏黏着度的影响(钟智锦,2010)。
在心理学领域的玩家研究中,成瘾问题是相关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⑥由于本文不是从这一角度来进行讨论的,因此不再展开对这些文献的详细说明。
还需说明的是,以往玩家游戏行为相关研究中,角色扮演类(RPG)游戏由于具备较多拟真的特征成为被重点关注的部分,目前关于游戏行为研究的成果亦大多围绕角色扮演类游戏研究而得出。但市场上仍有大量流行的、非RPG类游戏存在。与此同时,玩家行为也随着游戏类型、游戏媒介的变化而变化。
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在对模组进行研究时提出了“玩工”的概念,认为模组游戏爱好者是游戏公司重要的创造力来源,同时,“玩工”是“无偿劳动力”,并且,“玩工”的普遍化与“弹性资本主义”制度是高度匹配的(尤里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2018)。库克里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模组游戏的“玩家”进行讨论,进而提出“玩工”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较之既往关于玩家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角,还是概念的使用上均是一种进步。但是,库克里奇的讨论是建立在21世纪初的经验观察基础上的,时隔近20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库克里奇文章的最后,他提出游戏模组制作社区的成员面临三个问题:首先,如何将自己定位为游戏产业价值的创造者;其次,如何对模组游戏拥有所有权;最后,如何消除游戏模组仅仅是一种休闲活动的意识形态(尤里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2018)。这三个问题,在过去近20年模组游戏的发展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部分解决。简单地说,就是那些模组游戏的“玩工”具备了更多“生产者”的意义。还有,库克里奇的讨论,主要是从较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入手,缺少对于“玩工”的游戏实践的较为深入观察,对于“玩工”主体性的关注和体现不够。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模组游戏在中国有大量的实践者,但在既往的相关文献中,较少对这个群体进行深入研究。
二、研究问题及方法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为:《我的世界》模组游戏的实践者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她)们是如何进行游戏实践的?他(她)们的这样一种游戏实践具有怎样的意义?更具体地说:他(她)们是普通的游戏消费者?还是已经具备了“玩家”的意义?进而,这些“玩家”是否又具有库克里奇所说的“玩工”的意味?他(她)们仅仅是库克里奇意义上的“玩工”,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生产者”的意味?这样一些身份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在此,需要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做一个简要交代。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本文作者之一⑦
就加入了一些模组爱好者社群进行参与观察,实际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其游戏行为过程,并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此外,还在《我的世界》国外著名的游戏玩家论坛Minecraft Forum,国外著名模组分发网站CurseForge中《我的世界》专栏,国内官方游戏论坛MCBBS及其附属QQ群“MCBBS矿工茶馆”、“Mod大区咖啡屋”,以及非官方模组开发者相关QQ群“minecraft mod 开发/插件”、非官方服务器群“USTC Minecraft(中科大《我的世界》服务器群)”、“fantasy古灵域”等服务器群中收集相关资料。
作者对重点游戏网站中相关的游戏模组上传情况(包括类型、发布时间、相关可查询数据)进行记录,并且参与相关的线上社群交流,入群后进行了3个多月的观察,并不定时地根据群内话题进行交流。同时,作者也和部分社群中的用户共同进行了数次游戏实践。在完成初期的情况了解和文献整理后,通过半结构化的访谈,对12名《我的世界》模组制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主要是《我的世界》相关网络社群中较为活跃的用户,以及在社群中地位特殊的用户(如群主、版主等),作者表明意图并经受访对象许可后进行访谈。找到最初的访谈对象后又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找到了其他访谈对象。
三、“消费者”or“玩家”
在成为模组制作者之前,除特殊情况之外,每个人首先是《我的世界》的内容使用者,或者称之为游戏内容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通过不同的渠道,逐渐成为“玩家”。
由于mod本身是一项比较独特的数字信息内容,它不是以可视的图片、可听的音频或者是可以理解的日常语言文本方式出现和进行传输,而是以供给系统读取的特殊文件格式出现的。mod文件本身不能被日常语言所解读,mod文件的使用则必须经历文件传输(即上传和下载)的过程,要知道mod中的内容必须装载进游戏中运行或者通过传播者的二次转述,要使用mod,下载者必须进行正确的配置。这样的载体特征意味着哪怕是面对面的两位玩家,仍需要通过特定的媒介才可以进行mod的传输,网络在线或具备长期稳定的存储、传输功能的媒介更加适合编程文件的传播。
模组制作者在制作出了模组之后,将mod以讨论帖加上附件的方式发送到论坛讨论区内,供用户浏览以及下载。随着mod的讨论增多和流行,《我的世界》的多个论坛上还逐渐分出专门的“mod板块”供玩家们进行交流和讨论,论坛成为《我的世界》mod传播的重要发源地。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描述了自己接触模组的方式:“2013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玩MC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玩mod了,当时是在百度贴吧上知道这个游戏的,而且当时看到的还是一个装了mod的内容,自然我就知道mod了。” ⑧
除了这些集合了综合内容讨论的论坛之外,随着mod数量的增多以及影响力变大,一些专门收录mod信息的网站也开始收录《我的世界》mod并开设独立的游戏分区。另外,一些以《我的世界》为主题的非官方兴趣网站也渐渐崛起,在提供《我的世界》游戏相关资料之余,也形成如同门户网站般的网络服务,为玩家提供mod的目录、引导页、上传/下载区(如《我的世界》百科)。
之后,一些关键性的基础mod,即提供了反编译功能和简便接入功能的mod,如bukkit、forge的流行,使得其开发者本身吸引了巨大的关注。在关注的驱动下,它们以单个关键功能的mod为基础核心,聚合并利用了这些基础mod的其他mod,组成全新的mod内容网站,如Bukkit Forums、Minecraft Forge Forums等,提供基础功能的同时也提供额外的、丰富的mod内容。
另外,一些以整合《我的世界》私人服务器的信息为主的网站也陆续开始提供mod信息查询、上传和下载的功能。再者,在游戏多人模式的开发之下,部分服务器的管理者在自身管理的服务器里预装了服务器mod,使得加入这些服务器的玩家即使没有预装客户端mod也能直接体验mod的内容,玩家在联网模式下可以搜索到这些服务器,并在服务器中接触到mod内容。正如“如花”所说:“2017年左右,那个时候是我们学校的服务器开设的6周年,这个服务器正好是mod服,我就知道了mod了。” ⑨
在接触到游戏以及mod相关的内容之后,玩家开始进入mod里面。玩家使用mod主要有两种情景,一是玩家的主动使用——部分玩家对原本的游戏内容有一定的熟悉后,接触到mod相关内容并开始尝试在自己原有游戏过程中添加mod。这是一个基于原本游戏行为而发生的额外行为,或者说是游戏内容的主动“增值”行为。
另一种情况是被动使用,部分玩家一开始接触到的就是经过修改的、安装了mod的游戏,他们被修改过的游戏内容所吸引,于是在装载游戏本体过程中,不自觉地加入了mod。一名受访者在谈及其接触《我的世界》的最初经历时说:“(20)13年左右,(玩《我的世界》时候)我第一个玩的游戏内容就是mod。说实话我当时还真不知道自己玩的游戏内容就是mod,就觉得游戏本来就是这样的。” ⑩
此外,一些不了解mod的玩家在加入预装了mod的服务器时,也会被动地使用mod。这些mod的分发站点“加载了塑造用户知识并与代理进行干预的软件和代码,直接影响了个人理解、下载和制作mod的方式”(Hong & Chen, 2014)。
加入了mod之后的游戏体验和原生的游戏内容是有明显差异的。以《我的世界》中较为著名的《暮色森林》模组为例,这个2015年发布的mod,截至2020年1月,仅在CourseForge上就已经累计有超过2500万的下载次数。这一个mod为原本的游戏加入了一个永远处于暮色状态的游戏场景,并在里面放入了大量游戏本体中不存在的生物和建筑物,玩家装载了mod之后通过特殊的方式就可以进入这个特殊的场景,对于玩家而言,它是“一个新的世界”。
不同的主题性mod会给玩家带来不同的内容体验,如访谈对象所言:
神秘时代吧,它诞生的设定就和当初其他mod不一样,其他基本都是工业化的机械模式,千篇一律,集中在自动化设备上的思路,但神秘时代给我的感觉是更加集中在内涵上的一个mod。[11]GT4(GregTech,格雷科技),当年最早玩的是GT4,那会(游戏里面)钨钢就是最高级材料了,还要做冰冻、高炉,还有早期聚变,主要是gt算是不那么魔幻的模组,算是给我一个初步的世界观吧。还有就是外星科技AE(Applied Energistics),能懒就懒,能点菜的绝不跑路。[12]上述从“消费者”成为“玩家”的案例中,模组制作者围绕着单一开发商开发的游戏进行活动,刚开始他(她)们只是普通的消费者,随着他(她)们对游戏的深度参与,逐渐具备了“玩家”的意味。同时,随着“玩家”们的创造性劳动,他(她)们的实践也具有了“生产者”的意味。
四、“玩家”or“生产者”
Postigo曾指出PC游戏玩家制作模组背后的三个主要动机:首先,爱好者认为制作模组是一种艺术尝试和创造性的出路。第二,制作模组可以让人们对游戏产生认同感,增加他们对游戏的享受。最后,一些游戏爱好者将模组制作视为在游戏产业中获得工作的渠道(Postigo, 2007)。但在调研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哪位模组制作者明确表示将“mod”作为其寻找工作的途径。从访谈材料看,模组制作者进行mod的动机使得“玩家”具有了更多“生产者”的意味。
受访者之一梨木利亚(下称梨木)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21岁的大学生,所读的专业是商业管理以及法律,而在《我的世界》网络相关社群里面,他却有着多重身份——既是百度贴吧“minecraft吧”的吧主,也是《我的世界》中国官方论坛MCBBS中的一名版主,同时还是《我的世界》国内游戏资讯网站“MC百科”的总编辑。关于驱使他制作mod的主要原因,他是这样描述的:
还是感觉国内modder(模组制作者)太少了,想要一起帮忙出一份力而已。但是,一个mod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的,所谓自己的东西就是创作者的理念,现在(我正在做的)这个mod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有了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能展现给玩家吧。
做mod和单纯地玩游戏之间,(我的个人感受)是从玩家到开发者角度上的区别,作为玩家玩游戏可以不用考虑的,(但是)开发者会考虑,比如平衡性、某些物品的意义。(我)不会觉得在做mod其实也是在玩,(这个感受)基于个人而不同,至少我觉得做mod和玩有很大差别,和(自己)纯粹在玩MC时的心态和感受已经很不同了。[13]Olli Sotamaa曾经对《闪点行动》 (Operation Flashpoint, OFP)及其模组文化进行研究,认为在游戏中并没有“普通的游戏模组制作者”(average modder),在OFP中模组制作者可以根据他们是否专注于制作任务、插件、大型模组来进行分类,他们之所以会对制作模组感兴趣,是因为本身就对游戏感兴趣,更深层的动因可以归为自我表达和交流的欲望(Sotamaa, 2010)。
2017年,梨木“找到了一些朋友”并开始制作mod,并最终将完成的作品——日式风格模组樱(Sakura)上传到了MCBBS以及CourseForge上。在梨木的个案中,他制作mod的原始动机属于具有比较强烈的“表达欲望”,希望通过制作mod为国内的模组制作者群体“出一份力”。
在另一些受访者身上,情况却有些不同。komeiji现实生活中是一名高中生,参与过非常多的小型mod工程,他给自己在模组制作过程中的定位是“贡献点子”,即为团队提供编程方面的技术服务。关于他参与制作mod的原因,他是这样描述的:
因为能做mod,当时没有别的游戏做mod比MC更方便了。我本身就对做mod比较感兴趣。后来入坑了还会尝试去做别的游戏的mod,譬如《钢铁雄心4》,但是最想打开ide(集成开发环境)的时候还是因为写mcmod。我有点偏完美主义者,看到某些mod的瑕疵就马上要去修。[14]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受访者的身上:
从知道mod之后我就想制作mod了,就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不过当时肯定不知道怎么写,用模组制作器整了半天也没整出来什么,正儿八经用java写出第一个mod是初一的时候。那个mod是我出于学习目的制作的,它的功能仅仅是能显示作者信息,它相当于自学mod的一个小练习。[15]从上述两个受访者的访谈可以看到,最初促使他们制作mod的原因于他们而言似乎与“游戏”之间没有过于紧密的关系,他们制作mod的最初驱动力更多是为了提高自身编程语言能力,制作mod的过程如同个人学习过程的一个校验,功利性和目的性并不明显。
综上,在从“玩家”向“生产者”转变过程中个人内在动机是多样的,既有自我表达的需要,也有出于功利性的“获利”驱动,更多的只是将“参与”当作一个验证能力的工具。
但是,即便“玩家”具备了适当的动机以及一个允许进入的开放文本,通过模组制作的方式参与到游戏文化中,他(她)们是否就是完全具有自主性的“生产者”?是否就具有库克里奇所说的“玩工”的意味?
五、“生产者”or“玩工”
对于“玩工”,库克里奇这样写道:工作在当下充满即时性、流动性和制度性的环境中越来越呈现出弹性(flexible)的特征,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生计而‘玩’”(play for a living)。“为了生计而‘玩’”并非完全没有自由,而是“他们赞同已有的规则仅仅是因为服从规则所获得的乐趣,因此,他们的自由建立在对游戏规则的服从之上”(尤里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2018)。
电子游戏的mod种类繁多,复杂程度各有不同,但不论其复杂程度如何,制作mod都要求制作者自身拥有一定的程序语言技术、计算机专业技能和社会技能。地图制作者和模组制作者都必须掌握一定的脚本语言、图形开发程序语言、软件开发工具语言等相关知识(在《我的世界》中主要是java编程语言)。游戏内材质制作者、皮肤制作者在编程语言的基础上,还需要拥有一定的设计知识。如果模组制作的地图或者mod里面涉及一些与现实、历史相关的内容时,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这种制作mod的相关知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额外的、增值的知识内容。
《我的世界》最初版本是以java为代码基础开发出来的游戏。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java代码本身较为容易被反编译(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也称为计算机软件还原工程),即容易被他人对软件的目标程序进行“逆向分析、研究”,以推导出软件产品所使用的思路、原理、结构、算法、处理过程、运行方法等设计要素,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能推导出源代码。为了保护自身的成果,使用java进行开发的开发者通常会对源代码进行“混淆”处理,以防源代码轻易地被窃取修改。
因为开发者对MC的源代码进行了混淆,那些源代码中原本好看好记的诸如Item这样的类名、方法名、变量名等,通通被混淆成了难以阅读和辨认的符号,在MC发布之初,即便一个掌握了基础程序语言知识的人,想要对游戏的源代码进行修改,想要制作mod,也需依靠更加高难度的编程知识技术。这个学习知识技能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对于模组制作者而言也是一个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访谈对象所说:
做mod时,我学会了git和备份,在日常工作中我也开始使用git,比如图像处理,为了做mod也了解了不少photoshop知识,以及网页设计的知识,这些也都在其他方面(对我)能够有所帮助。[16]在初中时候,做一个mod需要拿MCP反编译Minecraft的代码,然后进行对应的修改,然后编译混淆。为此学了不少编程知识,我现在也在读计算机专业。[17]直到2010年中Minercraft Coder Pack(后来更名为Mod Coder Pack, MCP)的游戏脚本和工具集的出现,制作mod才绕过了对代码进行反编译的过程。随着MCP的完善以及提供类似功能工具的发布,掌握编程语言的游戏玩家可以更加轻易地绕过原本混淆的难题,模组制作的技术难度有所降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模组制作对技术依赖程度的降低,对于mod制作者而言,编程语言的习得是基础,是规则,也是门槛,只是说大部分模组制作者在实现文本的改写过程中变得容易了,制作者们可以在前人经验、技术的积累上更加容易地实现特定的目标。正如一个访谈对象所说的:“现在大部分mod作者不需要关心一些较为底层的东西了,但对于coremod(底层代码模组)而言,要关心的东西变得更多了。” [18]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除了特殊的服务器服主之外,所有的模组制作者都掌握了制作mod的相关技术语言——java,部分受访者更是有其他计算机编程语言的知识,只是他们获取这些技术知识的途径各有不同。
有部分受访者通过自学的方式来学习编程语言:
(学习做mod的时候)自己买《java从入门到精通》加朋友教导下自学完成,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在假期的时候自己去弄(学习)的。[19]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对mod感兴趣,于是就开始自学做mod。(当时)自己摸索eclipse,自己摸索mdk,能踩的坑都踩遍了。在学做mod之前,没有接触其他的编程课程。在自学的过程中,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名为lambda Innovation的团队,当时这个团队正在制作一款名为LambdaCraftd的mod,我在项目中承担一定量的工作。虽然后来参与到的这个项目“坑了”,但我认识了一众大佬,也发现他们在搞NOI,后来我也去搞了一段时间NOI(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且拿了个NOIP(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省赛)二等奖,借此进入了一所市重点高中。[20]最开始做mod的时候,是通过MCBBS论坛的教程以及某大佬的口头指导学习的,但那位大佬已经很久不接触MC了。在那之前,大概初中的时候,学校有组织,好朋友在搞NOIP,我也跟着去了。为了参加NOIP,学过一些pascal和C++,不过Minecraft的mod是用java编写的。[21]这一自学的过程包括相关教程的寻求以及相应行为的练习,以网络论坛为代表的网络社群始终是他们获取技能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有部分受访者由于自身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在未接触mod之前,就已经通过校园教育中的课程安排学习过一些计算机编程语言:
之前有一定的编程基础,C(语言)大一学的,java大四学的,js和其他的制作网页技能是自学的。在上大学之前了解过一点qbasic一类的知识。之后在着手做mod的时候,有做过一些额外的学习和准备,需要额外学习游戏中的命令知识以及json、nbt、资源包等内容。(这些知识)通常是在需要使用的时候去了解就可以了。[22]即便掌握了一定的计算机编程语言,《我的世界》模组开发者在进行模组开发的时候,仍然需要面对游戏版本迭代、工具更新、知识缺乏等多种情况带来的mod开发困难。“如花”是这样描述他制作一个原版模组《更多的合成》(crafting)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经历:
(这个mod)第一个版本只有极少的功能,并且本体就是用基岩包裹的CB构成的结构,是使用结构文件+OOC安装的。后来(我为这个mod)添加了一些有用的工具,对结构也做了美化。一直到(游戏的)1.6~1.7版本,java1.12中有了function,(于是我)改用function实现(功能),安装变得简单了。1.8版本(java1.13)(游戏)开始支持数据包,局部坐标的引入也使得方块和物品设计更加便于使用,同时引入了资源包,此时我找到一位叫RubberTree的材质作者,让他帮我设计了大部分的材质,1.9版本(java1.14)开始物品数量不再受限制,更加美观,工具也更多。[23]如同游戏的开发过程一样,无论是mod本身还是制作mod,都是动态的,不会因为“完成可运行版本”就结束,其后依然会经历维护更新、内容更迭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是要求模组制作者继续提升模组制作知识和能力,改良原来的mod。
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单是开发mod的门槛在逐渐降低,模组制作者使用mod的流程也在发生变化。随着mod开发增多,一些为解决用户使用mod中出现的问题而诞生的mod在游戏社区中也流传开来,诸如forge加载器的出现和完善,使得制作者在装载mod、使用mod的时候变得更加容易,mod的兼容性产生的错误问题也在技术优化的情况下减少。
与此同时,模组制作者身份转变也意味着“文化圈”的突破,即计算机知识文化圈与游戏娱乐文化圈的交融。在普通玩家那里,电子游戏是游戏文化圈的内容,而编程技术语言则属于计算机技术文化圈,两者之间在开发、模组制作的行为中实现了交集和突破,并且计算机技术文化以一种“高位”的、掌控生产权力的角色进入到游戏文化中。
尽管这些“生产者”在模组实践中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但是在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或资本体系)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同时具有了库克里奇所说的“玩工”的意味。
六、“玩工”or“生产者”
如前所说,“玩工”们掌握编程代码的过程,也是掌握与游戏开发商对话权力的过程。普通玩家java代码、编程知识的获取,打破了作为生产者的游戏厂商通过编程语言进行文本表达的垄断,成为模组制作者的“玩工”们有了参与、实现表达的可能,冲击了“开发者”的地位。与以往攻略、同人、小说、视频等游戏附属文本相比,模组制作带来的这种冲击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摆脱了对生产者产出具体产物之后才可建立的过程,直接干预“生产”进程,进而获得一种具有更多主体性的“生产者”地位。在这种“生产者”地位的获得过程中,通常伴随着为“合法性”进行的抗争。
从模组游戏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修改游戏内容在游戏产业中早就存在着“正邪”之争。mod曾经被定义为“黑客行为”,它们的传播最初更多是通过趣缘社群、技术社群进行私人化的、小范围的网络传播,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开发者的利益,破坏或重构了游戏的原文本。mod的行为甚至不太被接受,只是伴随着玩家对mod认同感的增加以及官方从mod中发现有利可图的情况之下,关于mod的负面评价才逐渐减少了。《我的世界》mod的发展历史并非一帆风顺,早期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这些声音既有来自最普通玩家的,也有来自《我的世界》游戏开发商的,开发商的态度在《我的世界》mod发展的过程中则渐渐发生变化。
2009年7月,Minecraft Forum论坛有用户发起了一条关于游戏被mod的内容讨论,这可能是目前可查证的、最早的提及游戏mod的讨论。一名玩家在论坛中发帖指出,他在进行多人游戏时发现有其他玩家在游戏中“飞行”:
一个关于有人在飞的问题
最近我看到一些过度强势的玩家在他们的服务器上飞来飞去。它(飞行)看起来对检查游戏里面的物品、地图情况非常有用。然而,当我去问这些飞的人他们是怎么飞的时候,他们都回避了我的问题。他们是怎么飞的?他们是黑客吗?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以便可以更好地缓和我的服务器。有人能告诉我是怎么做的吗?[24]尽管“飞行”后来被正式加入这款游戏的创作模式中,但在这一时期官方释放的版本里面,角色飞行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功能,即在当时可供下载的官方游戏版本中,玩家不可能通过游戏原本的设置实现“飞行”。因此,这位用户怀疑游戏客户端已被某些玩家成功修改了,该帖的跟帖用户lguana、liq3等更是认为这样的修改,已经构成了一种“黑客行为”(hack)了。
事实上,此前许多游戏发行商或开发者反对游戏修改和模组制作者。这些公司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大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力度,禁止通过复杂的终端用户许可协议(EULAs)或第三方版权控制进行修改,以及将修改游戏的行为描述为不合法的行为。
《我的世界》的创建者Notch曾在2012年参与一次粉丝问答活动,并坦承他最初对mod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担心玩家修改内容会威胁到他对游戏的看法,“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mod对于游戏来说有多棒。我们(最终)决定顺其自然,我为这样的决定感到高兴,(现在)mod是《我的世界》重要组成部分了”。[25]2010年7月5日在新版本发布之后,Notch决定开启游戏定制API的计划,并称为Mod API(模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为应用程序与开发人员提供了基于一些软件或硬件得以访问一组例程的能力,开发人员可以通过官方、正式的途径理解《我的世界》这一电子游戏中内部工作机制的细节。
2012年,Mojang声称正在开发《我的世界》模组的知识库,并且在他们网站的帮助列表中列出了教导玩家如何安装模组并游玩模组的一系列教学影片。同年,Mojang还聘请了Bukkit插件的开发人员开发官方的Modding API,目标是希望允许模组开发人员能够更简单地调整或修改《我的世界》游戏内容。[26]同年,《我的世界》迎来商业上的重大变迁。Mojang工作室及《我的世界》被微软以25亿美元收购。微软在收购了《我的世界》之后并未对Mojang进行内部干预,也没有对当时正在运作的《我的世界》相关内容进行修改限制。
2015年4月,微软宣布为《我的世界》提供一个mod开发套件,为模组开发者提供了一种更简单的《我的世界》模组创作方法。[27]同年7月,微软发布了一个《我的世界》windows10版本,这一版本与以往版本有很大差异,游戏的底层代码是由C++编写完成的。C++破译mod的难度比java大,此消息引发《我的世界》模组社群担忧,玩家认为其可能是《我的世界》java版本被逐步淘汰的一个征兆,并担心《我的世界》模组的发展受到阻碍。当然,最后Mojang开发人员并没有停止开发java版本。[28]2016年,《我的世界》的1.9版更新发布,在这次更新中,Mojang承诺会在底层代码上简化mod的创建和更新方式,使得模组制作者更加容易进行mod的开发。[29]不过这次更新最后破坏了在此之前已发布模组所使用的架构,使得许多模组创作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更新模组作品,最终导致一些模组停止更新开发而停留在旧版本1.8甚至是1.7.10上。
2016年,官方发布了一个《我的世界》特殊版本——教育版,[30]教育版的前身是一款叫做MinecraftEdu的mod。MinecraftEdu是由一个名为TeacherGaming的团队开发的,可以让玩家探索、互动和修改游戏内容,学生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下学习各种科目,老师可以更改设置制定游戏的内容。2016年1月19日微软宣布从TeacherGaming收购MinecraftEdu的同时,也宣布了该游戏将在原来的模组基础上开发新的教育版本。这样一来,《我的世界》通过商业化的路径将玩家自主自觉对游戏的修改进行了“收编”。这次收编揭开了《我的世界》游戏开发商公开对优秀模组内容加以整合、统一管理的帷幕。
之后,原本以C++为开发语言基础的、难以被mod的基岩版也开始对mod内容进行关注。2017年4月,Mojang宣布建立一个名为Minecraft Marketplace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普通游戏玩家可以通过官方途径贩卖基于基岩版制作的用户自定义内容,亦即对应的java版本中的mod内容。这个全新的平台允许玩家通过游戏获取利益,不过它主要集中在冒险地图、皮肤和材质包等非程序修改的内容发布上。
同年,国内代理商引进代理并运营的《我的世界》中国版正式发布,在中国版中,《我的世界》运营商改变了游戏原来的商业模式。国外版本玩家只需要一次性购买游戏本体,就可以“合法地”体验游戏所有内容,包括那些由玩家制作分享的、符合游戏用户条约的mod。但国内游戏代理商代理了游戏之后,却改变了游戏的收费方式,打造了一个融合的游戏本体、mod以及服务器租赁的服务平台。游戏的本体成为免费内容供给玩家下载,但玩家若想在国内官方版本的基础上加载其他玩家制作的mod、开启服务器,则只能通过代理商服务器提供的官方平台完成。在这个官方提供的渠道上,游戏不再完全无偿地为玩家提供由其他玩家制作的mod和稳定的服务器,一些完成程度较高、较为大型的mod,大量的插件、辅助工具以收费的形式提供给玩家。
《我的世界》中国版也对在官方游戏平台上发布mod的玩家给予一定的创作支持。在中国版官方网站中,官方提供了一个显眼的MC开发工具下载入口,通过官方渠道为玩家提供一些基础的开发工具如MC studio、Mod Sdk、Apollo。在引入初期,更是开启《我的世界》创造者大赛,出资500万元奖金征集包括插件、地图、材质、皮肤等mod的内容,而在日常运营中,《我的世界》中国版更是明确指出“开发者将获得绝大多数的收益,即扣除渠道分成和支付通道费之后的70%收益(官方获得30%)”。[31]到2018年10月6日,Mojang开源了部分java版的代码。现在,只要查看《我的世界》官方在其用户协议中的相关内容,就大致可以了解到官方对mod的态度:
如果您购买了我们的游戏,您可以尽情试用或通过改动、添加工具或插件(我们统称为“mod”)来修改它。所谓“mod”是指您或其他人的原创作品,不包含我们有版权的代码或内容的实质部分。当您将您的mod与Minecraft软件进行组合时,我们将这种组合称为游戏的“mod化版本”。我们对哪些内容构成mod、哪些不构成mod拥有最终决定权。您不得分发我们的游戏或软件的任何mod化版本,如果您没有使用mod来激怒或骚扰其他玩家,我们将不胜感激。基本上,mod可以分发;游戏客户端或服务器软件的mod化版本的破解版本不可以分发。[32]除此之外,《我的世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多次mod开发比赛和计划,诸如“《我的世界》创造者大赛”、“《我的世界》建筑大赛”、“《我的世界》创作者计划”等,最终吸纳了一批专业开发者以及各个阶层玩家的参与,产出了一系列新的mod及游戏内容。
官方的态度随着mod数量的变多、玩家对mod的认同接受程度变高、使用频率变高,以及mod创造出的商业价值而渐渐发生转变,官方不在公开渠道表达压制mod增长的态度,而是转向允许mod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模组制作的氛围,而普通玩家也在官方支持、推广mod的情况下,以更方便的方式、更低的门槛接触到由其他玩家创作的游戏内容。mod成为官方所承认的游戏部分,并被以“收编”、“鼓励”的态度来对待,正式宣告以玩家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模组文化在《我的世界》中获得了“合法性”。
也正是在为“合法性”不断地抗争的过程中,使得某些“玩工”获得了“生产者”的地位。
结语
本文以模组游戏《我的世界》及其模组制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游戏实践进行观察(以及参与)、访谈,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结合相关的理论讨论,本文对既往笼统的“玩家”概念进行了细分,区分出了“消费者”、“玩家”、“玩工”、“生产者”几种角色。在我们看来,《我的世界》的游戏实践者的角色十分复杂,虽然从宏观的权力关系来看,“玩家”们具有库尔克里所说的“玩工”的意味,但是并非完全如此,除了“玩工”,他(她)们还具备“消费者”、普通“玩家”和“生产者”的角色,[33]并且,随着模组制作者的不断抗争,其“生产者”意味不断得以凸显。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实践中的不断抗争,“玩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游戏的资本市场中的“玩工”。
以上几种角色,既可以理解为某些特定的游戏实践者身份转变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模组游戏的实践者的一种结构性的构成。同时,这样一些角色是作者结合经验材料并按论述逻辑区分出来的,在模组制作者的游戏实践中,对于某些制作者而言,也可能是多种角色混杂在一起的。
当然,即便是那些具有较高主体性的“生产者”,并非说他(她)们完全不受束缚,和“玩家”、“玩工”、“消费者”相比,只不过是其自主性相对大一些而已。同时,《我的世界》作为一个资本市场中的产品,其核心技术、市场走向等,则仍然牢牢地由资本所有者控制。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游戏有意义”,同时游戏也是一种特定的传播方式、形态。游戏与技术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在以计算机、互联网为表征的“网络社会”中,游戏形态、传播方式较之以往均有巨大的变化。这样的景象,自然与格尔兹所考察的巴厘岛上的斗鸡这样一种纯粹地方性活动有较大差别,需要从“全球化”的资本市场的角度进行观察。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我们只能从这样一个个案的某个方面(游戏参与者)来进行讨论,对于资本市场的运作等等,还较少涉及,也希望以后的研究能够更多地去关注。■
注释:
①资料来源:https://www.dugoogle.com/gaoxiao/1013790.html
②《2019中国游戏产业年度报告首发:国内2330.2亿 电竞增16.2%》。资料来源:http://www.joynews.cn/jiaodianpic/202001/0332402.html
③资料来源: Top 20 Game Franchises on YouTube. http://www.newzoo.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Newzoo_Top_20_Game_Franchises_on_YouTube_January_2015_V1-Custom3.png
④资料来源:https://rewind.youtube/#!/top-stories.
⑤详见Brian Sutton Smith的个人主页。Retrieved from https://www.museumofplay.org/about/library-archives-play/brian-sutton-smith.
⑥如GoldbergI. (1996).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OL]. from http://www.rider.edu/suler/psycyber/supportgp.html; YoungK. S.(1999). Internet addiction: symptom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Innov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A Source Book, 1719-31; SoperW. B. & Miller, M. J. (1983). Junk-time junkies: An emerging addiction among students. The School Counselor31(1)40-43; GriffithsM. D. (1996). Internet addiction: An issue for clinical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Forum9732-36;杨眉,崇健,张雅如:《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原因剖析及对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魏华,周宗奎,田媛,鲍娜:《网络游戏成瘾:沉浸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年第6期,等等。
⑦本文的前期调查均由本文第二作者完成。
⑧2020年1月4日对流年访谈。
⑨2020年1月11日对如花访谈。
⑩2020年1月10日对komeiji访谈。
[11]2020年1月9日对梨木利亚访谈。
[12]2020年1月7日对末影超人访谈。
[13]2020年1月9日对梨木利亚访谈。
[14]2020年1月10日对komeiji访谈。
[15]2020年1月5日对萌妹访谈。
[16]2020年1月11日对如花访谈。
[17]2020年1月7日对旅行者访谈。
[18]2020年1月8日对gooding300访谈。
[19]2020年1月6日对 Roach访谈。
[20]2020年1月10日对komeiji访谈。
[21]2020年1月8日对gooding300访谈。
[22]2020年1月11日对如花访谈。
[23]2020年1月11日对如花访谈。
[24]资料来源:https://www.minecraftforum.net/forums/mapping-and-modding-java-edition/minecraft-mods/mods-discussion/1339431-question-about-people-flying-around.
[25]资料来源:Notch: ‘Minecraft mod used to threaten my vision’ - Minecraft creator speaks https://www.vg247.com/2012/08/01/notch-minecraft-mod-used-to-threaten-my-vision-minecraft-creator-speaks/
[26]资料来源:Mojang hires Bukkit server-mod team to make official Minecraft API https://www.eurogamer.net/articles/2012-02-29-mojang-hires-bukkit-server-mod-team-to-make-official-minecraft-api
[27]资料来源:Microsoft embraces Minecraft modding with new Visual Studio tools https://www.geek.com/microsoft/microsoft-embraces-minecraft-modding-with-new-visual-studio-tools-1621890/
[28]资料来源:Why gamers are worried about “Minecraft: Windows 10 Edition”http://motherboard.vice.com/read/why-gamers-are-worried-about-minecraft-windows-10-edition
[29]资料来源:Minecraft developer explains Mojang’s viewpoint on mods https://attackofthefanboy.com/news/minecraft-developer-explains-mojangs-viewpoint-mods/
[30]资料来源:Microsoft turns a Minecraft mod into an education busines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1-19/microsoft-turns-a-minecraft-mod-into-an-education-business
[31]资料来源:http://mc.163.com/developer_cn/question/20190704/31078_821236.html
[32]《MINECRAFT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来源:https://account.mojang.com/documents/minecraft_eula.
[33]就研究中我们的真实体会而言,在《我的世界》游戏中,这四类角色中的某些角色(如消费者、玩家)特征还不是十分明显,这或许由于游戏的特殊性所致。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对其他的游戏进行考察,以便丰富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
董虫草(2006)。西方艺术游戏论述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36-40。
关萍萍(2010)。《互动媒介论——电子游戏多重互动与叙事模式》。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论文。杭州。
约翰·赫伊津哈(2014)。《游戏的人》(傅存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克里福德·格尔兹(1999)。《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尤里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2018)。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6),196-206。
钟智锦(2010)。使用与满足: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国际新闻界》,(10)101-107。
周逵(2016)。作为传播的游戏:游戏研究的历史源流、理论路径与核心议题。《现代传播》,(7),25-31。
BartleR. (1996). Hearts, clubsdiamonds, spades: Players who suit MUDs. Journal of MUD Research, 1-19.
CowleyB. , CharlesD. , BlackM. & Hickey, R. (2008).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flow in video games. Computers in Entertainment6(2)1-27.
HongR. & Chen, V. H.-H. (2014). Becoming an ideal co-creator: Web materiality and intensive laboring practices in game modding. New Media and Society16(2)290-305.
KivikangasJ. M. , Chanel, G. , LeyB. C. , EkmanI. , Salminen, M. , & JaervelaeS. , et al. (2011). A review of the use of psychophysiological methods in game research. Journal of Gaming & Virtual Worlds, 3(3)181–199.
Postigo, H. (2007). Of mods and modders: Chasing down the value of fan-based digital game modifications. Games and Culture2(4)300-313.
Sotamaa, O. (2010). When the game is not enough: Motivations and practices among computer game nodding culture. Games and Culture. 5(3)239-255.
Yee, N. (2006). The labor of fun: How video games blur the boundaries of work and play. Games and Culture1(1)68-71.
郭建斌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姚健明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云南大学创建一流大学“民族传播研究与媒体人类学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C176240200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也是姚健明硕士论文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