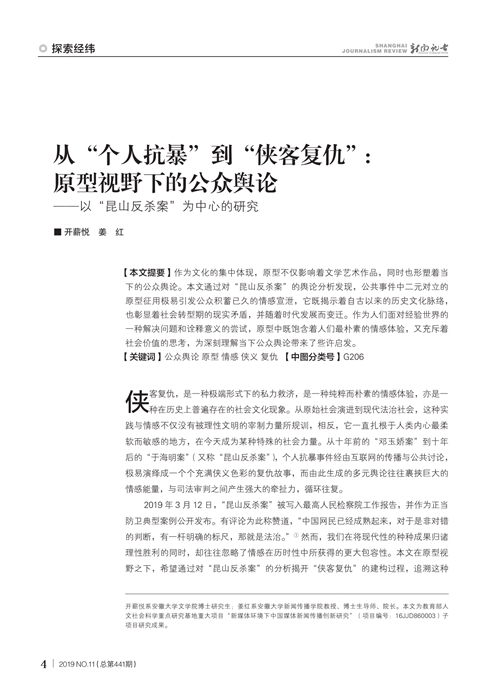从“个人抗暴”到“侠客复仇”:原型视野下的公众舆论
——以“昆山反杀案”为中心的研究
■开薪悦 姜红
【本文提要】作为文化的集中体现,原型不仅影响着文学艺术作品,同时也形塑着当下的公众舆论。本文通过对“昆山反杀案”的舆论分析发现,公共事件中二元对立的原型征用极易引发公众积蓄已久的情感宣泄,它既揭示着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脉络,也彰显着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矛盾,并随着时代发展而变迁。作为人们面对经验世界的一种解决问题和诠释意义的尝试,原型中既饱含着人们最朴素的情感体验,又充斥着社会价值的思考,为深刻理解当下公众舆论带来了些许启发。
【关键词】公众舆论 原型 情感 侠义 复仇
【中图分类号】G206
侠客复仇,是一种极端形式下的私力救济,是一种纯粹而朴素的情感体验,亦是一种在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从原始社会演进到现代法治社会,这种实践与情感不仅没有被理性文明的宰制力量所规训,相反,它一直扎根于人类内心最柔软而敏感的地方,在今天成为某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从十年前的“邓玉娇案”到十年后的“于海明案”(又称“昆山反杀案”),个人抗暴事件经由互联网的传播与公共讨论,极易演绎成一个个充满侠义色彩的复仇故事,而由此生成的多元舆论往往裹挟巨大的情感能量,与司法审判之间产生强大的牵扯力,循环往复。
2019年3月12日,“昆山反杀案”被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为正当防卫典型案例公开发布。有评论为此称赞道,“中国网民已经成熟起来,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有一杆明确的标尺,那就是法治。” ①然而,我们在将现代性的种种成果归诸理性胜利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情感在历时性中所获得的更大包容性。本文在原型视野之下,希望通过对“昆山反杀案”的分析揭开“侠客复仇”的建构过程,追溯这种原型召唤背后复杂的情感动因、历史根源与现实困境,并试图探讨原型对于公众舆论和法律理性更加多元的意义和价值。
一、原型:理性与情感的交汇
长久以来,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和制约,公众舆论被普遍视作理性思维的产物。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秉持“人生来皆理性”的信念,认为“公众意见”可以成为除政治法、民法、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②到哈贝马斯认同“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③尽管对舆论认知不断更迭,但始终难以跳脱传统理性主义桎梏,从而导致情感遮蔽。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情感”对于形塑现代公众、重构公共领域和重新理解公众舆论的意义所在。林郁沁(Eugenia Lean)在探讨“施剑翘案”的时候,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众的情感是如何卷入了国家和社会、法律事务的”,她意识到,“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探索‘公众’问题时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持续影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寻找一个真正理性的、独立的、且具解放作用的公众的证据中”,但“理智和情感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在中国现代“公众”兴起的过程中,“情感”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理智和情感、理智和道德进行二元划分。④不仅如此,“公共领域未必仅仅是冷冰冰的话语,激情反而可能给公共领域带来活力”,⑤情感不仅是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动力,它还可以成为公共领域中被讨论的主题。⑥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情感”表达以及经由“情感”形成的关系,催生了各类带有“情感”色彩的“诠释社群”,它们相互冲突和展开竞争,构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网络公共性的理解。⑦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中的表达机制,“情感”被社会规训的同时,也具备社会行动的能力,在历时的维度中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此称为“情感结构”,即社会经验和社会关系的特殊品性。⑧它描述的是“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⑨换言之,“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体的私人体验和心理过程,它也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⑩
对于当下的舆论研究来说,“情感”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重构了公众的表达形态和情感关系,特别是“后真相”时代的到来,相较于传统的理性动员,今天的网民更容易受到“情感”左右而产生舆论。李彪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而网民也由“想象的共同体”演变成“偏见共同体”。[11]在涉及敏感身份问题时,中国网民往往“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12]甚至,公众在“发言的盲目性”、“立场的偏执性”以及“动机的娱乐性”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新的公众舆论参与行为模型,即“游戏模型”。[13]于是,大量研究探讨了舆论的失范,并进一步确认了对情感的批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肯定了“情感”对于舆论不可或缺的意义。郭小安认为,“情感具有复杂的发生发展逻辑,它是认知心理的一部分,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资源”,“只要引导得当,公众也可以形成情理交融的公共领域和‘意见的自由市场’,产生自我净化能力”。[14]而“后真相”所带来的也未必是恐慌和担忧,它也可以是新媒体语境下关于真相新内涵的探讨,是一种反思、一种价值的审视,有利于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15]更有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精英主义下的专业权威、阶层分裂下的权力威信未必比个人信仰更加可靠,因此群体在不断变动中的分化与聚合可能比稳固的状态更有朝气,更能推动言论的自由。[16]尽管多学科领域逐渐重视情感的生成逻辑及它对舆论的建构作用,并尝试提出各种新的诠释框架,但是,如果想要读懂当下中国的舆论内涵及意义,除了结构性因素之外,还必须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错中找寻答案。
随着新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浸透,传统媒体的单极叙事文本逐渐消失,网络事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书写体验。而在千奇百态的叙事之中,支流繁多的观点却总能在某些情感共鸣处得以交汇,并趋于一致。其中,原型的力量不容小觑。正如有学者所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原型实现的。” [17] “原型(archetype)”一词源自希腊语architypos,后被引申为“原始模式”或“某事物的典型”。荣格(Carl Gustav Jung)将这一概念理论化并声名远播,他认为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大脑携带着人之为人的全部历史,即一种集体性的“种族记忆”,当这些“种族记忆”被凝缩、积淀在大脑结构之中,就形成了各种“原型”。[18]作为一种先验形式,原型先于个体而存在,是“集体无意识”的组成单位,[19]并且,“它向我们指出了这些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并关系到古代的或者可以说是从原始时代就存在的形式,即关系到那些亘古时代起就存在的宇宙形象”。[20]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在阐述神话相位时,将原型视作“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并用这个术语来表示文学“结构单位的稳定性”,[21] “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或是一种可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22]费德莱尔(Fiderel)认为,原型是“由观念和感情交织而成的一个模式,在下意识里广泛为人们理解,但却很难用一个抽象的词语表达”,“这种复杂的心理情结需要通过某种模式的故事,既体现它又像是掩盖它的真正含义;待到它的原型意义被分析出来,或者根据表达它的语言找出了它的寓意之后,整个奥秘才会昭然若揭”。[23]总体来看,无论是荣格将“心理情感”与“模式性”相糅合,还是弗莱将“文学”与“程式”相嫁接,亦或费德莱尔把明确的“观念”与难以言表的“感情”相关联,对“原型”的阐释本身具备理性与情感的多元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两者互相对立的阐释维度。并且,因其贯通历史与现实,将种种意象和主观感受紧密相连,这对于理解社会转型期的舆论与情感之间关系有着极大启发意义。
二、公共事件里的原型:传统文化与现实矛盾的碰撞
目前,原型理论在国内一般出现在文学领域,例如闻一多先生的相关研究被认为是接近或类似原型批判的;李泽厚先生在荣格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淀说”,主要阐述如何运用有效的方法把文化积淀成为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叶舒宪先生则利用该理论研究中国神话,[24]等等。但是,原型的产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面对经验的一种解释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模式,体现了人类的共同思维。[25]因而它不应也不会只出现在文学领域中。在当下新闻话语中始终存在着一些亘古不变的意象,那便是世代相传的原型。
曾庆香将“原型”引入新闻传播领域,认为“原型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象征、人物、母题、思想或叙述模式即情节,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是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其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26]她从上古“大禹治水”等一系列中国神话中,发现了“人定胜天”的英雄原型,并且认为这种原型沉淀、复现在今天许多灾难性报道之中,正是这种“沉淀和烙印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上的、融合了或多或少的权力意识的英雄原型”,造就了我国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灾难认知方式和新闻话语体系。[27]另有研究指出,早期英雄母题的结构模式包含着英雄、非法者、受害者和英雄的宝物这四大要素,而在大众媒介时代,媒介和记者因为拥有国家和公共舆论所赋予的话语权力这一宝物,故扮演着英雄的替身和英雄故事的叙述者双重角色。[28]还有在民粹主义舆论的叙事模式中,也常常通过将新闻主角塑造成草根英雄,来隐瞒或者故意忽略某些事实,从而达到为尊者讳的目的。[29]除了“英雄”原型之外,在当下公共舆论中还存在大量中国传统的原型意象。例如,在饱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反腐反贪”事件中,无论是前些年的“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还是2018年被广为关注的“严书记”,官员穷奢极欲、以权谋私的作风早已深入人心,甚至“贪官原型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核心原型”。[30]然而早在《儒林外史》中就有俗谚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无官不贪”的原型意象不仅在公众心中长期扎根,在新的时际之下还引发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尤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在这类议题上舆论得以高度共识,公众由原型想象引发的愤慨之情也获得短暂平息。
与此同时,阶层矛盾和群体污名化也加剧了公众“仇官”、“仇富”的心理,传统文化中关于“公子王孙”、“纨绔子弟”的原型意象,在当下网络事件中集中表现为对“官二代”、“富二代”的极端认知;还有对漂亮女性涉及权钱事件所产生的“红颜祸水”原型亦可追溯至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这些历史与文学记忆,反映出人们自古以来存在于文化深处的性别歧视。与此相对,在公共事件里处于弱势的一方在与贵胄强权的二元对立之下,也往往被赋予一定原型色彩,如“中国第一烈女”邓玉娇、“无罪义士”夏俊峰等等。
不难发现,在当下社会转型期,阶层矛盾、民粹主义、道德败坏等典型问题中的原型极易得到传播并产生认同,这或许是通过原型叙事来解决问题的一种实践,正如人们向往英雄情结,恰恰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缺失物——英雄品质进行补偿的一种无终止渴望。[31]然而,当下不少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原型对形塑公众舆论的负面影响,如有研究基于互联网的传播偏向,认为当下舆论受民粹主义思潮的支配,通过原型叙事,把历史引入现实,唤醒了国人集体记忆,催生了社会悲情,用二元对立思维框限了转型中国的复杂关系,助长了社会仇恨,阻碍社会共识的形成。[32]还有学者认为“彭宇案”作为一个深入人心的当代“原型”,致使老人在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中作为“异项”被不断污名化。[33]值得提出的是,“原型”理论与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之间既有相似,亦有差异。李普曼认为媒介制造了“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于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34]这里强调的是公众借助新闻机构的选择和呈现作出判断,因而“刻板印象”的形成离不开媒介环境的温床。而原型指向在情感体验中、精神领域内,深层而有力量的“最原初的结构范式”,[35]它一方面可脱离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而存在,另一方面它比“成见”更具情感的偏向。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framing)理论也与之有所区别。“框架”是“指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36]而原型则是在历史更迭、文本互构和记忆再现中的某种深层结构,与人类感受息息相关。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的集中体现,蕴含着特定群体固有的认知方式和情感体验,凝聚着特定社会文化的诸多符码。[37]由此观之,既然原型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在原型视野下探讨公众舆论之时更应正视其包含的情感色彩,并尝试加以理解和疏导,而非盲目强调理性的秩序统治。
三、原型的征用:二元对立下的情感激活
在众多原型之中,“侠客复仇”的原型包含着多重意象的交织,极具戏剧张力和情感冲击,在近些年的网络事件中屡见不鲜,“昆山反杀案”便是其中典型。
事件缘起于2018年8月27日晚,一辆宝马汽车与一辆电瓶车因变道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汽车内男子随即用长刀砍伤了骑车人。在持续争执中,长刀不慎落地,被骑车人迅速捡起并反砍数刀,致使对方受伤倒地,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事件的视频经由媒体的加工与传播,瞬间引爆公众舆论。除了围绕“正当防卫”这一核心事实的争议,大众媒体、自媒体与公众重点将目光聚焦在死者与反杀者的身份起底之上。8月29日,《新京报》揭露了砍人被“反杀”的宝马男刘海龙曾多次入狱的经历,包括抢劫、盗窃、敲诈、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毁坏财物等多重罪名,[38]一时间引发舆论的集体讨伐。很快,关于刘海龙更多的个人隐私被挖掘出来,有媒体报道其经营的“聚业典当”属于无证无照非法经营,[39]网络上四处流传着其上身赤裸、纹身满布并混迹于各种娱乐场所的照片,更有网友传言他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天安社”的成员,以“放贷”和“中介”为主要收入来源。尽管经过侦查确认,刘海龙与该组织并无关系,也未有相关涉黑行为,相反,他还曾因协助抓获贩毒嫌疑人被授予“见义勇为”奖,[40]但“花臂男”的个人形象与种种事迹却不免让公众将其与黑恶势力的原型联系到一起。
从商周直至明清,纹身一直作为刑罚手段而存在,被称之为“墨刑”。如今,虽然“墨刑”早已烟消云散,但在儒家传统教义所宣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熏陶之下,刻龙画虎的纹身并非一种美的艺术,而是“蛮夷”才热衷之事,许多社会不良分子常利用纹身来标记自身属性,加之大量影视作品的角色渲染,久而久之,公众渐渐在脑海里建构起纹身者等同于黑恶势力的联想。正如原型不一定限于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而可能是意识、观念、习俗、文化等等,生活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可以是一个故事、一个形象、一个过程等等。[41] “花臂男”不仅在外形上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的恶势力原型,加之其前科累累,劣迹斑斑,在该事件中还非法藏匿携带管制刀具,并率先动手砍人,其“黑化”程度足以令公众心生怨恨。
在恶势力的比照之下,人们迫切期望代表正义之“侠”的原型出现。起初,一些网友谣传反杀者的身份是一名“退伍特种兵”,或许这正是在原型力量引导之下对正义化身的天然期待。8月29日早上,有发帖透露(原帖已被删除):“于海明生活压力挺大,不是网传退伍军人,一个手机用了四年都没舍得换,他家中很不幸,去年十几岁的儿子患癌症,年底父亲又走了。”其后北青报记者通过众筹平台证实了其子患病的事实,《新京报》记者通过采访其同事,确认了他工程主管的身份,“他(于某明)在我们单位是很好的一个人,非常随和、乐观,和同事的关系都很好”。[42]于是,“家庭不幸”、“工作勤奋”又“随和乐观”的“老实人”于海明的形象被建构起来,公众“一边倒”地对其投以深切的同情。
在破除身份谣言后,媒体与公众并没有放弃对反杀者“侠客”身份的刻画。8月30日,国内知名媒体人陈安庆在其评论里直接以“白衣侠”和“花臂社会人”来代称于海明和刘海龙;[43]8月31日,有公众号通过于海明同学和朋友的口述,将他刻画成一个“为人仗义”、路见不平“出手相助”、“孝顺善良”的“白衣大侠”,而对刘海龙的定性则为“史上最悲催的恶霸男”。[44]还有报道称,据目击者描述,“刘海龙身高不足1.65米,于某明的身高目测约有1.8米左右”,[45]身形的高大魁梧也契合了公众对“侠”的美好想象。
无论是外形、经历、人格品性,事件中两位当事人的原型始终处于鲜明的对比与冲突之下。有人为于海明立传,称其曰“游侠”——“海明为人深沉,嫉恶如仇,好读书击剑”,并赞其反杀行为乃“为民除害耳”,与此相对,刘海龙被描述为“亡命”之徒,“性暴虐,好矜伐,专事盗窃欺诈,与人消灾,尝五度入囹”。[46]于海明的“反杀”之举不仅没有被视作一种施暴行为,反而在“宝马男”这一形象的不断比对之下,公众心中“仇富”、“仇恶”的情感被激活并迅速产生集体认同,进一步确认了复仇的必要性和报应的必然性。不少声音认为刘海龙之死为“死有余辜”,或是“因果报应”,一方面体现出人们对复仇正义这种道德情感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中国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善恶报应观,有媒体评论道,“这桩刑案未必就是一个替天行道的故事,而更像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老话的注脚”。[47]不可否认,一个事件之所以能引爆网民的注意力,主要是该事件刺激了网民乃至所有社会公众“最绷紧的那根弦”,而这根神经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逻辑和社会价值诉求。[48]正义与黑恶这一对具有天然对抗性的文化符码,在分裂中形成巨大的紧张感,与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贫与富、官与民、精英与草根等不同原型的对立一样,背后沉淀着大量社会想象,在强烈的冲突之下刺痛着公众心中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而原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就在于能够激活个体情感,而且这种情感体验是强烈而本能的。[49]通过二元对立的原型征用,公众对复杂事件进行了简化甚至极端的认知,在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恶势力的怨恨中群情激愤,达成了舆论的阶段共识。
四、原型的召唤:“侠客复仇”的情感溯源
在荣格眼中,原型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共同的遗传物”,[50] “由于它是原型,它就具有历史性一面,我们不懂历史就不能理解那些事件”。[51]而弗莱则认为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52]因此,要理解“侠客复仇”的原型意象被频繁召唤背后的观念与情感,必定离不开对中国“侠”文化与“复仇”观念的传统认知与当代解读。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群体,“侠”的原型意象曾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反复出现。在公权力缺失时代,不同群体对“侠”始终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官方体制将“侠”看作是“以武犯禁”、“肆意陈欲”、“不轨于正义”的社会蠹虫,因其非官方的正义力量严重冲击了专制政体下的统治秩序,故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民间百姓则将“侠”视为惩恶扬善、替天行道、路见不平的英雄好汉,源于其在传统既有的体制和秩序之下无法收获公正时,对于体制之外正义力量的期望和认可,故千古歌咏传颂。[53]官方的不断打压以及随着社会发展,以个人力量挑战法律秩序所付出的代价愈加惨痛,现实里“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渐渐地,“侠”抛开了历史书写的负面形象,经由文学的浪漫想象和人类价值的自然选择被塑造成一种理想的人格精神,象征着正义的化身,流淌进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尤其成为文人墨客的“千古一梦”。有学者给传统政治生态的“侠”作了一个概括:即有着高超本领和高尚人格,以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来反抗社会黑暗,为此不惜挑战社会既有法律秩序以匡扶社会道义,并以此为己任的人。[54]或许,正是由于现实中“侠”的衰落,为世人对侠的重新想象与文化再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55]于海明被公众冠以“现代侠义之士”的称号,恰是因为他“临危自奋”、“不惜用武”、“直截了当自掌正义”的自救行为满足了诠释群体对今天“侠”之勇敢无畏、不落平凡理想人格的幻想,而反杀“暴徒”的举动又契合了“侠”之“为民除害”、“替天行道”的朴素正义逻辑。通过对原型的共同想象,公众之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所做所感”和“意识”的了解,于是“他们就会强烈地体验到其共享的情感,如同这种情感已经开始主导他们的意识一样”,[56]声援于海明的舆论浪潮此起彼伏。
作为被构建的文化符码,原型并非一成不变。如果说在神话叙事和文学叙事中远古的原始经验已经变成“集体无意识”,不能被明确意识到,需要通过原型批评(archetypal criticism)加以还原和认知的话,那么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原型”则具有现实性,通过相关事件的抽象分析就可以把握。[57]文学研究认为,侠文学漫长的历史和侠意象的原型意义,使读者对侠文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期待”。这种“期待”被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观念所支撑,具有强大的社会渗透力和统摄力,在读者与作者,甚至作者与作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58]而回到互联网世界,这种“契约”的签订与履行并不仅限于读者与作者,或作者与作者单方面的信息传递,而是公共书写下的一种仪式共享,它勾连着历史文化、记忆图景与现实矛盾,通过特定的人物、事件、情境,利用既有的叙事和认知框架,激活了“集体无意识”中被压抑的某种情感需求和潜在动机,“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余物”。[59]人们迫切需要它,正是因为“如果个体不与大量的传统经验及情景发生联系,则维持连续感和同一感的纽带就会绷得过紧,甚至导致精神分裂”。[60]由此观之,公众之所以对“侠客”原型津津乐道并不断产生角色想象,正是因为人们需要一种文化模式来整合外界信息、释放精神焦虑,并且期待某种被理想化的力量来弥补理性未得以及时建构价值秩序时的彷徨与无奈。事实上,对刘海龙的愤恨和对于海明的同情,其中夹杂着公众对“侠客”原型、“英雄”原型、“复仇者”原型、“恶棍”原型等多重原型的重叠想象,但这些原型都在二元对立中才得以成立和强化,并早已超越了具象情感本身,既是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所形成的“永恒性、共通性和重复性” [61]的情感模式,也是在“集体无意识”下所共同体验的文化仪式。
而对“侠”的原型认同也带来了对“抗暴”行为的美化。在“昆山反杀案”中,媒体、专家和公众将焦点放在了关于“正当防卫”的探讨之上,并且大部分声音倾向于认同于海明的行为已构成正当防卫。从形式上看,正当防卫应该是同态复仇依旧保留在当代法律制度中最直接的体现,它是基于同态复仇思想对当代法律制度公力救济可能导致的不正义情形在一定意义上的弥补与救济。[62]也可以说,正当防卫来源于人类自保的本能与天性,其渊源亦可追溯至私力复仇,复仇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私力救济。在法律尚未形成之前,复仇作为一种“矫正正义”曾被视为理性的替代品,建构起了一种依靠私力威慑和惩罚报复来获得的稳定社会秩序。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刑罚体制正是以报复观念为主宰即以报复为基本理性的刑罚体制。[63]相比于中性色彩的“抗暴”、“复仇”更能彰显情感上的歇斯底里。滥觞于原始社会的复仇在历史上盛行不息,为亲复仇者有之,为友复仇者有之,侠义复仇者有之,甚至连妇女、儿童都参与到复仇者的悲壮行列之中。[64]它是“受侵犯者对施加侵犯者予以的回复性侵犯”,[65]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此来慰藉自己的愤恨”的方式,[66]也是一种“原始的”、“直觉的”、“就像爱一样”的情感体验。[67]不仅如此,植根于人之本性的复仇,往往裹挟着血性的冲动、怨恨与同情,以及正义的宣泄,为侠义复仇的母题书写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因为“人们渴望痛苦、愤怒、仇恨、激昂、出其不意的惊吓和令人窒息的紧张”,于是“把艺术家当作呼唤这场精神狩猎的巫师召到自己面前”。[68]当人们遭受侵犯或不公的对待时,这些“心理中明确的形式的存在” [69]便被瞬间激活并发挥
作用。
大多数情况下,“杀人”会遭受法律制裁与道德伦理唾弃,但一旦被想象为“复仇”原型则往往不尽如此。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复仇并不是一个暴力野蛮词汇。相反,它是古典中国礼乐文明出现后的产物。[70]宋代理学家胡寅认为,“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71]在儒家思想教义的熏陶之下,复仇在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具有正当性,即符合“天理”、“人情”与“道义”。“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虽若变,然变而不失其正,斯为常矣”。[72]尤其是“父母之仇”不仅“杀之无罪”,甚至被认为是“孝义之行”。《礼记》有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73]《孟子》亦有云“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也,一问耳。” [74]而且,当复仇主体未尽复仇义务时,还会遭受口诛笔伐:“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 [75]从“个人抗暴”到“侠客复仇”的舆论共鸣,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植根于人性要求和生物本能的一种最原始、朴素且凭借直觉的正义反应、心理感受和道德情感,同时也说明中国礼法社会所形成的原型意象至今仍然是影响公众认知与行为模式的文化基因。荣格曾经把原型比作“结晶的轴心系统,是先定的,好像是饱和溶液中结晶的结构一样,本身没有可见的外形”。[76]或许正因如此,原型才得以具备无法想象之力量,因为无论什么物质,都摆脱不了被纳入晶体的结构,“都会遵守这种新的、觉察不到的秩序”,原型支配下的内在秩序“构成了我们在生活的不测及骚乱时的庇护所和帮助”。[77]而原型得以建构,除了历史与文化的形塑,还必须诉诸现实情境的激活,因为“一个原始意象只有当其被人意识到,并因此而被人用意识经验的材料充满时,它的内容才被确定下来”。[78]不难发现,“昆山反杀案”的背后也反映着转型期当下中国的现实矛盾。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诉求的多元驳杂,普遍存在的紧张感和相对剥夺感的加深,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成为公众的普遍愿景。因此,由原型的召唤而形成的期待恰恰成为“能够在各个舆论主体之间进行交际的深刻根源”。[79]更进一步说,由原型所引发的公众舆论之所以能够与司法审判之间产生巨大牵扯力,正是因为“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他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80]
五、原型的导向:朴素情感与法律理性的合理妥协
在原型的影响之下,裹挟着“侠义复仇”色彩的公众舆论通常被法律理性所排斥,如“侠义”被视作个人正义的代名词,而“复仇”的观念更被看成是社会的“毒药”或“疾病”。然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深入发展,网络事件早已成为公共参与的产物,公众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原型的呼唤产生强大的舆论浪潮,另一方面在沟通博弈的过程中又不断建构和填补着原型的具体内容,强化了原型最初的深层力量。正如社会学理论所认为,社会交往及其社会组织的压力是原型发生和形成的重要社会因素,社会强制性常常以社会无意识的形式改变和影响着原型的发生和更新。[81]因而,理性的价值秩序在公众舆论的情感偏向面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这时候,倾听舆情或许是一种合理的妥协。[82]从“辱母杀人案”到“昆山反杀案”的接连发生,公众在表达朴素正义感的同时,主流媒体渐渐改变了过去“法不容情”的冰冷态度,转向倡导法律与舆论也需要互相倾听与尊重的观点。例如“@人民日报”在评论“辱母杀人案”的时候,呼吁公众思考法律的社会功能其实“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83]在点评“昆山反杀案”的判决时,更直接表达这是“众望所归”的结果,并且强调“法律不是镌刻在大理石上,而是铭刻在公民心中,让公民沐浴正义之光,让法治温润公民信仰”。[84]《法制日报》也认为“昆山反杀案”的判决是“司法与民意达成了宝贵的共识”的结果,而“进一步完善法律”的目的也是“让法律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85]必须要承认的是,“侠义复仇”原型背后导向的是情感正义而非法律正义,这本身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其包含仇官情绪、仇富心理和以暴抗暴的情结,具有强烈现实批判性和破坏性,若缺乏有效的疏通与消解机制,势必演变成为动摇社会秩序的原生力量。但是,原型的产生既有历史文化的溯源,更有符合时代需求的价值逻辑。
社会是特定情感的“触发器”,它决定了哪些情感和思想能够显现于意识层面,哪些则继续存留在无意识层次。[86]就像人们对“侠”的原型期待在当下被固化为“惩恶”意在“扬善”,“除暴”旨在“安良”,“劫富”为了“济贫”,其方式虽破坏法治,其目的却充满善意;而法律的起源又与复仇的“私力公权化”紧密相关,正是私人无限制的复仇权让渡给国家之后,才形成了司法审判的权力。[87]因此,“侠义复仇”背后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亦是法律精神永恒的旨归。荣格认为,“当原型的情境发生之时,我们将会突然体验到一种异常的释放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力所操纵”。[88]换言之,公众对“侠”的“千古一梦”和对“复仇”的本能冲动经由历史的反复实践被证明无法通过社会控制等理性手段根除,那么换个角度思考,回归情感本身或是解“毒”、治“病”的一剂良方。
对“侠客”的期待和“复仇”本能的唤醒并不是社会疾病,它们犹如“普罗透斯似的脸”,[89]形塑了公众在具体事件里的认知与表达,折射出一个时代最基本的道德诉求和正义观念。由于法律的威慑力始终存在,公众的侠客情结和复仇感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具体实践。而通过原型征用,他们却能够在言论表达中释放和消解部分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已久的复杂情感,短暂弥补了法律未能及时到场时的价值失序。与此同时,饱含情感色彩的观点之间不断碰撞,引发关注,致使舆论骤然升温,也倒逼着法律及时地作出合理回应。相反,在不理解舆论的基础上,过度宣讲理性秩序的控制可能会造成情感焦虑与堵塞,当人们无法感受公平正义的内在力量时,最终会选择更加极端的方式进行反击与报复,致使悲剧产生。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曾说过:“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是人类生活本身。” [90]法律的生命力恰是来源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原理。因此,中国的法律必须凝结传统中国司法文明中的智慧,必须符合中国人本身过日子的规则与逻辑。[91]诚然,法律不是解决社会冲突,尤其是自古以来的秩序矛盾的唯一出口,正如康德所言:“在每个共同体中,都必须既有根据(针对全体的)强制法律对于国家体制机械作用的服从,同时又有自由的精神”。[92]公共事件里嘈杂鼎沸的舆论声音纵使指向人类本性里的朴素正义,但当千万个相似的情感意见同时集中出现,法律便有必要放下高冷的姿态,认真倾听并重新审度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核心价值,这也迫使法律不断更新与完善。律条和司法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修复破裂的情感关系,维护人伦秩序。[93]原型视野下的情感表达与法律本身并不相悖,两者只有在互相倾听与尊重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共赢的出口。
结语
经历了岁月的沉淀与传播,“原型”的力量不仅被证明无法根除,更迫使公众在面对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时候能够迅速建立起相似的认知模式和诠释视角,在某些公共议题上得以达成舆论的高度共识和情感的有效满足,短暂弥合了当下中国由于社会断裂所带来的舆论撕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集体无意识”所带来的情感偏向会遮蔽事实与真相,造成舆论偏激,但因人们在每个阶段的心理创伤和现实矛盾皆有不同,“原型”的内涵亦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更迭。正如在“昆山反杀案”中我们看到,“侠”从“非法”演变成“合理”,“复仇”从“合理”逐渐被宣布为“非法”,原型变迁的“本质不在于具体的叙事模式或者叙事策略的改变,而是将更多时代精神纳入其中”。[94]一种文化的传播技术与人们如何理解和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感受有着复杂的关系。[95]通过对原型赋予想象并抒发意见的文化仪式,媒介和公众在宣泄情感的同时,未尝不是在一次次具体实践中找寻面对经验世界的解决问题和诠释意义的范式。因而,与其遏制或纠偏原型中存在的情感导向,不如用发展的眼光和包容的心态去把握每一种原型得以沉淀和传播的历史动因、文化脉络和社会矛盾,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中去看待情感与理性的共同成长。不过,情感在释放与消弥之后,究竟如何与舆论之间建立真正的合力,这条博弈之路仍然漫长且艰辛,但我们满怀期待。■
①长安剑:《从邓玉娇于欢到于海明,这个国家发生什么变化?》,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51129253_357727,发表日期:2018-08-31
②[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第70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③[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13页,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④[美]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⑤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
⑥袁光锋:《互联网空间中的“情感”与诠释社群——理解互联网中的“情感”政治》,《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4年
⑦袁光锋:《互联网空间中的“情感”与诠释社群——理解互联网中的“情感”政治》,《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4年
⑧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31.
⑨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2002年第5期
⑩袁光锋:《公共舆论中的“同情”与“公共性”的构成——“夏俊峰案”再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11期
[11]李彪: 《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12]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13]郭锋:《后真相时代的公众舆论“游戏模型”》,《新媒体研究》2018第3期
[14]郭小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期
[15]张庆园、程雯卿:《回归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反思自媒体时代的后真相及其原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9期
[16]陈文育、任丽雪:《“后真相”时代终将延续下去——论数字空间里的社会分化与群体聚合》,《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
[17]延俊荣、戴建东:《论隐喻建构的基础》,《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18][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载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第9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9][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载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第10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53页,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21][加]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第99页,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2]班澜:《外国现代批判方法纵览》第224页,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
[23][美]费德莱尔:《“好哈克,再回到木筏上来吧!”》,蓝仁哲译,载司各特编《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第170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24]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25]李红:《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叙事原型》,《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1期
[26]曾庆香:《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27]曾庆香:《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28]邹建达、李宇峰:《英雄的叙事与叙事的英雄——论当代新闻叙事中的英雄母题与英雄情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9]汤景泰:《偏向与隐喻:论民粹主义舆论的原型叙事》,《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9期
[30]李红:《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叙事原型》,《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1期
[31]邹建达、李宇峰:《英雄的叙事与叙事的英雄——论当代新闻叙事中的英雄母题与英雄情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2]汤景泰:《偏向与隐喻:论民粹主义舆论的原型叙事》,《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9期
[33]郑宏民:《从原型视角看“老人碰瓷”事件中的公共叙事》,《新媒体研究》2018年第23期
[34][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第62页,阎克文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35]刘芳:《荣格“原型”概念新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6]甘莅豪、樊小玲:《“精品”与“合作”:两岸“XX制造”形象广告的框架分析》,《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2期
[37]蒋晓丽、何飞:《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38]王煜、王露晓:《昆山砍人被“反杀”男子:曾多次入狱 刑期总计近10年》,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8/29/501918.html,发表日期:2018-08-29
[39]孔令晗、付垚:《“昆山龙哥”参与经营的典当行 系无证无照》,@北京青年报,https://weibo.com/1749990115/Gx3eu0IFE?type=comment#_rnd1562749128764,发表日期:2018-08-30
[40]北晚新视觉综合:《于海明属正当防卫,“花臂龙哥”这些作为咎由自取》,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1558819.html,发表日期:2018-09-01
[41]程金城:《原型的内涵与外延》,载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第12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2]吴靖、秦宽、张彤、刘洋:《昆山“反杀”事件现场:白衣男一直握着刀 警察来才松手》,新京报网,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18/08/30/502060.html,发表日期:2018-08-30
[43]陈安庆:《白衣侠PK花臂社会人,扫黑除恶正当防卫行为,无罪!》,南方传媒书院,https://c.m.163.com/news/a/DQEP0MVN05259DOV.html,发表日期:2018-08-30
[44]小胖虎:《揭秘“龙哥终结者”于海明》,网易号,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QHE3JJ10529U03U.html,发表日期:2018-08-31
[45]吴靖、秦宽、张彤、刘洋:《昆山“反杀”事件现场:白衣男一直握着刀 警察来才松手》,新京报网,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18/08/30/502060.html,发表日期:2018-08-30
[46]强哥谈历史文化:《史记游侠于海明列传》,搜狐号,http://www.sohu.com/a/282623066_100153483,发表日期:2018-12-19
[47]团结湖参考:《不是“白衣侠士”,就得不到公正裁决吗?》,网易号,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QCCPUK50514BF90.html,发表日期:2018-08-29
[48]喻国明、李彪:《2009年上半年中国舆情报告(下)——基于第三代网络搜索技术的舆情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9]蒋晓丽、何飞:《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50][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119页,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51][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176-177页,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52][加]诺斯洛普·弗莱:《作为原型的象征》,载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第157-15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3]才圣:《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下的“侠”文化剖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期
[54]才圣:《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下的“侠”文化剖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期
[55]白贤:《现实与观念:中国侠文化的双重性解读》,《安康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56][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87页,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57]李红:《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叙事原型》,《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1期
[58]李欧:《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59][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载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第9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0]转引自周宪(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第4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1]刘芳:《荣格“原型”概念新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62]王龙飞、刘志:《试析同态复仇》,《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0期
[63]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第30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4]张钰:《试论中国古代复仇现象盛行的原因》,《天中学刊》2018年第4期
[65]袁锦晖:《法律与复仇:理性的替代与秩序的重构》,《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0期
[66][日]穗积陈重:《复仇与法律》第3页,曾玉婷,魏磊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67][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第472页,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8][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第115页,载熊伟(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9][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概念》第100页,载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0]蒋楠楠:《法律与伦理之间:传统中国复仇行为的正当性及限度》,《法学评论》2018年第4期
[7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第4955页,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
[72](明)丘濬:《慎刑宪·明复仇之义》第945-951页,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73]《十三经注疏》(中)第125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
[74]《孟子·孟子·尽心下》第7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5]《十三经注疏》(下)第221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
[76][英]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第185-186页,吕廷和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77][英]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第185页,吕廷和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78][美]霍尔、诺德拜:《荣格心理学纲要》第36页,张月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79]李红:《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叙事原型》,《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1期
[80][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第818页,载亚当斯(编)《自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原著出版于1922年)
[81]蒋晓丽、何飞:《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82]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第1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3]《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326/c1003-29169272.html,发表日期:2017-03-25
[84]《人民微评:每一次司法公正都会温润人心》,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902/c1003-30266104.html,发表日期:2018-09-02
[85]法制日报评论员:《昆山反杀案的有益启示》,人民网,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8/0903/c58278-30267700.html,发表日期:2018-09-03
[86][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斯克和弗洛伊德》第93页,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7]马骏:《复仇行为及其法律控制》,《理论观察》2018年第6期
[88][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第96页,载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9][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38页,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90][德]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第24-33页,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91]陈景良:《寻求中国人“过日子”的逻辑》,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020/c1003-28792254.html,发表日期:2016-10-20
[9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评文集》第199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93]蒋楠楠:《法律与伦理之间:传统中国复仇行为的正当性及限度》,《法学评论》2018年第4期
[94]齐蔚霞:《论现代广告的原型叙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95]Malin,Brenton J(2014).Feeling Mediated:A History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Emotion in America,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开薪悦系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姜红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JJD860003)子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