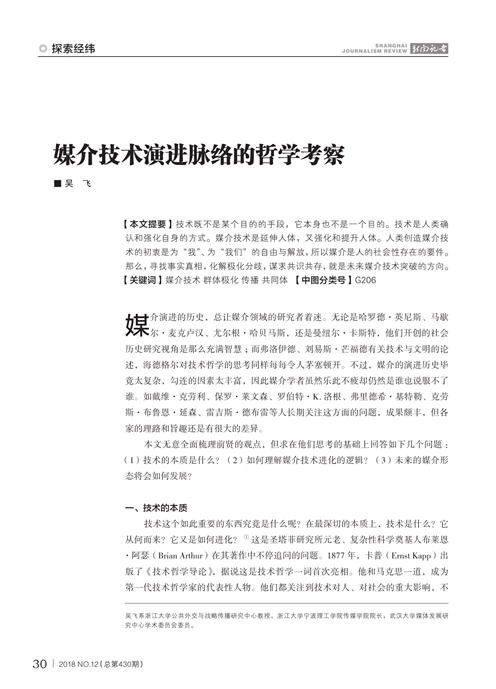媒介技术演进脉络的哲学考察
■吴飞
【本文提要】技术既不是某个目的的手段,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目的。技术是人类确认和强化自身的方式。媒介技术是延伸人体,又强化和提升人体。人类创造媒介技术的初衷是为“我”、为“我们”的自由与解放,所以媒介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要件。那么,寻找事实真相,化解极化分歧,谋求共识共存,就是未来媒介技术突破的方向。
【关键词】媒介技术 群体极化 传播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
媒介演进的历史,总让媒介领域的研究者着迷。无论是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尤尔根·哈贝马斯,还是曼纽尔·卡斯特,他们开创的社会历史研究视角是那么充满智慧;而弗洛伊德、刘易斯·芒福德有关技术与文明的论述,海德格尔对技术哲学的思考同样每每令人茅塞顿开。不过,媒介的演进历史毕竟太复杂,勾连的因素太丰富,因此媒介学者虽然乐此不疲却仍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戴维·克劳利、保罗·莱文森、罗伯特·K.洛根、弗里德希·基特勒、克劳斯·布鲁恩·延森、雷吉斯·德布雷等人长期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成果颇丰,但各家的理路和旨趣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本文无意全面梳理前贤的观点,但求在他们思考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技术的本质是什么?(2)如何理解媒介技术进化的逻辑?(3)未来的媒介形态将会如何发展?
一、技术的本质
技术这个如此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在最深切的本质上,技术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它又是如何进化?①这是圣塔菲研究所元老、复杂性科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在其著作中不停追问的问题。1877年,卡普(Ernst Kapp)出版了《技术哲学导论》,据说这是技术哲学一词首次亮相。他和马克思一道,成为第一代技术哲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都关注到技术对人、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不过马克思更趋向于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积极正面影响,而卡普则视技术为人类器官和身体功能的延伸。他的思想是否影响了后世麦克卢汉的观点不得而知,但他们观点的相通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技术与人类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的思考向度:其一,强调技术是一个科学的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二,强调技术让人类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两种观点都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1949年,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提出:“不能低估现代技术的侵入及其对全部生活问题造成的后果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历史思想盲目地依附于错误的观念,即认为现代技术是过去的直接继续,并把我们的存在和我们以前的东西固执地作错误的比较。” ②在谈到技术对于人类的目的性时,雅斯贝尔斯写道:“技术是一个科学的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免于匮乏,并使人类环境具有诸事取决于自己的形式。人类技术给自然造成的面貌,以及这一技术过程又如何作用于人类,形成各条历史基线中的一条,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工作方式、工作组织和环境发展改变了人类自身。” ③由此,自然而然地,雅斯贝尔斯发现了马克思所提出的技术与物的异化问题。他指出:“人类靠电影和报纸生活,靠听新闻和看电影生活,到处都在机器因袭性的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成为机器的零件”。④雅斯贝尔斯指出,“属于精神和信仰范围内的一切,只有在用于机器目的的条件下才被接受。人类本身变成被有目的地加工的一种原料。……文化传统,在其包含的绝对要求方面已被摧毁,人们变成一盘散沙,他们越缺少根基,就越容易被利用。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求生的感情同私生活脱离。但是生活本身也变成空虚,业余时间也机械化了,娱乐成为另一种工作。……原来的精神解放通过无所不在的新闻,转变为通过控制新闻来控制一切,通过通讯体系,国家意志能在任何时刻在广大地区生效,甚至直到每个家庭”。⑤
海德格尔进而将这两种有关现代技术的解释化约为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技术是目的的手段;第二,技术是人的行动。是的,正是因为有了技术,传统的时间观念发展了变化(自然天象的时间替换为机械时间),而空间也在缩小,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得以可能。曾经人们只能远望的星球,今天可以成为人类星际航行的中转站。远方的故事,可以即时转遍全球——我们可以一起观看英国皇家婚礼,可以即时分享战争与灾难的现场影像。不同语言背景、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可以借助谷歌翻译之类的工具,在互联网上直接交流,我们甚至可以与故人在虚拟现实中再见。芒福德就写道:“显然现在的交流范围更广了,更多的联系、花费更多的精力、花费更多的时间,不幸的是,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即时交流,并不意味着能够避免狭隘和琐碎的个性。及时的联系确实方便,但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阅读、写作和绘画是思维的高度提炼,也是深刻思想和深思熟虑的行动的媒介,现在却被这种即时交流削弱了。与直接而有限的接触相比,人们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更善于交流,有时看不见对方的时候的交流进行得更顺畅……从社会角度看,过分频繁而重复的个人交流可能并不有效。” ⑥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在最短时间内走过了最漫长的路程。人类把最大的距离抛在后面,从而以最小的距离把一切都带到自己面前”。不过,海德格尔警告说:“这种对一切距离的匆忙消除并不带来任何切近,因为切近并不在于距离的微小。在路程上离我们最近的东西,通过电影的图像,通过收音机的声响,也可能离我们最远。在路程上十分疏远的东西,也可能离我们最近。小的距离并不就是切近。大的距离也还不是疏远。” ⑦那么什么是切近(die Nahe)呢?海德格尔解释说:“物化之际,物居留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⑧居留之际,物使在它们的疏远中的四方相互趋近,这一带近即是近化(das Nahren)。近化乃切近的本质。切近使疏远近化(Nahe nahert das Ferne),并且是作为疏远来近化。切近保持疏远。在保持疏远之际,切近在其近化中成其本质。如此这般近化之际,切近遮蔽自身并且按其方式保持为最切近者。” ⑨由此,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我们思物之为物,那我们就是要保护物之本质,使之进入它由以现身出场的那个领域之中。物化乃是世界之近化(Nahern)。近化乃是切近之本质。” ⑩有学者评价说,在《存在与时间》、《艺术作品的本源》系列演讲以及《物》的演讲中海德格尔“从基础存在论分析之于认识存在者的关系通达物之物性之于理解对象物的关系,以及天、地、人、神的意蕴整体之于呈现物的意义关系三个方面,对物之切近之思之于物的表象之思的基础作用作出了深刻的阐析”。[11]在《物》的演讲中海德格尔用了一个著名的壶的例子,分别从天、地、人、神的关系视角解释壶之为壶的切近思考。海德格尔认为:“作为这种壶-物(Krug-Ding)的壶是什么,如何是?这是决不能通过对外观即‘相’的观察得到经验的,更不消说由此得到合乎实事的思考了。” [12]他的结论是:“壶的本质是那种使纯一的四重整体入于一种逗留的有所馈赠的纯粹聚集。壶成其本质为一物。壶乃是作为一物的壶。但物如何成其本质呢?物物化。物化聚集。在居有着四重整体之际,物化聚集着四重整体的逗留(Weile),使之入于一个当下栖留的东西(ein je Weiliges),即:入于此一物,入于彼一物。” [13]可见,海德格尔的物是一个汇聚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他所描述的黑森林中的农家院充分体现了“物”的这一本性。这个两百多年前由农民筑造的院子坐落在“大地上”,它的木石结构取自大地,且终将返归大地。院落位于避风的山坡上,屋顶承载着冬日的积雪。“风雪”透露出它在“天空下”。公用桌子后面的圣坛、死亡之树是终有一死者的归宿,暗示着院内人的终极命运,院落在“护送终有一死者”。圣坛上的十字架让诸神在场。一家人在这个院子里生活和享受着收获的喜悦,天、地、神、人在这个院子里和谐地栖居,这是人真正的家园。但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解蔽方式拆散了这种聚集,把院落还原为可供享用的物质资料。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展现(revealing),而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Ge-Stell)——是一种将世界遮蔽起来的具有“挑衅逼迫”性的、预置式的展现。迪亚斯(W.P.S.Dias)解释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无论是古代技术还是现代技术,都是一种展现,但现代技术不是“带出”,而是“挑衅逼迫”。[14]可见,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现代技术消解了物的世界,使人始终处于无家可归状态。
20世纪末,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艾尔伯特·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推出了他的技术哲学三部曲:《技术和当代生活特征:哲学研究》(1984)、《跨越后现代的界线》(1992)和《抓住现实:千年之交信息的本质》(1999)。在这些著作中,鲍尔格曼继承并超越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他用“设备范式”(device paradigm)观念代替了海德格尔“物”的观念。[15]他所指的“设备范式”是指现代社会人在追求可用性共同信念的指引下,根据可用性法则决定自己的行为活动和生活方式。[16]鲍尔格曼认为古代技术(物)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人要想实现目的,就必须参与物,而同时在参与中体认物的“与境”(世界)。如此,世界也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了。但现代技术(设备)则是手段(机械)和目的(用品)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就使现代技术(设备)具有卸负和提供用品两个特征。卸负是指设备通过手段即机械接管了人的参与,从而卸除了人的负担,同时也意味着卸除了物的与境,因而也就遮蔽了世界。不过,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面是“设备在卸除物的与境和人的负担的同时,为人提供了美好的前景,即为人提供了用品(可用性)。这些由设备的手段(机械)部分生产出来的可用性具有即时性、普存性、安全性和容易性的特征”。[17]可见,虽然艾尔伯特·鲍尔格曼同海德格尔一样,也是从“人-技术-世界”的多元维度来分析技术,但却立足于技术本身(技术人工物)来研究技术。在海德格尔那里,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预置的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在座架下,人丧失能动性和主体性。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绝不只是单纯的人类行为。因此之故,我们也必须如其所显示的那样来看待那种促逼,它摆置着人,逼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那种促逼把人聚集于订造之中。此种聚集使人专注于把现实订造成持存物。” [18]鲍尔格曼的设备范式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社会的建构性,认为人可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实践手段改变和控制技术的可能性。[19]鲍尔格曼指出,在这种技术范式之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既不能概括为技术对人类的绝对统治,也不能将技术概括为如前技术时代中的“物”那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而是一种“人类自身被牵入到技术之中的关系”。[20]18世纪法国学者拉·梅特里(La Mettrrie)在《人是机器》一书中使用“驯顺”这一概念,旨在说明科技让人的身体变成可解剖和可操纵之物。当代技术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在《技术社会》(1954)一书中指出:“技术已成为自主的;它已经塑造了一个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遵从技术自身的规律,并已抛弃了所有的传统。” [21]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先后出版了《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中的主题的技术失控》(1977)和《鲸鱼与反应堆》(1986)两本著作,对由现代技术引起的政治和文化的统治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技术在自身设计的过程中就包含了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描绘了技术是如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的,并倡导技术设计的变革。技术不仅仅产生社会后果,而且技术重构了社会,为社会“立法”,人类要反过来“适应技术”。温纳称之为“反向适应”。[22]所以,我认为单一地讲人是主体,或者物有自主性,都缺少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技术共同进化的视角,仍然没有超越二元论的思维框架。[23]在这一方面拉图尔的观点值得重视,他将这个世界称作“集体”(collective),所谓集体就是“人与非人(non-human)在一个整体中的属性交换”。[24]因此,科学进步不再是“分裂”式的,而是“杂合”式的;不再是“纯化”式的,而是“转译”式的。也就是说,进步是一个自然与社会的杂合过程,拉图尔称之为“集体实验”、“万维实验室”、“物的议会”或“杂合论坛”。实验室的范围越广,人类和非人类因素被征募到集体内的数量就越多,集体也就越进步。这一进步的方向是“指向在更广范围内将人类与非人类动员起来,将各种‘行动者’‘联结’起来的能力”。[25]
二、作为“焦点物”的媒介
鲍尔格曼受海德格尔之四重“聚集”的影响,提出了“焦点物(focal things)”的概念。鲍尔格曼在考证“焦点(focus)”一词的来源时,发现它最初的含义即是一“物”:“火炉”。“火炉(focus)”之为“焦点”,是因为它在前技术时代的屋子里,“构建了一个温暖、光明和日常生活实践的中心。对于罗马人来说,火炉是神圣的,是屋中神灵居住的场所。在古希腊,当婴儿被抱到火炉边,并放在前面时,他就算真正加入这个家庭和家族了。在火炉边举行的罗马婚礼聚会是神圣的。至少在早期死者是由火炉焚化的。一家人在火炉边用餐并在餐前饭后为屋居神灵献祭。火炉维持着房屋和家庭,维持其秩序并且成为其中心”。[26]在象征意义上,“焦点”就是会聚其与境中诸多关系的中心。看来,鲍尔格曼就是在“焦点”象征意义的基础上使用焦点物概念的。
焦点物是指具有会聚其所在与境中诸如自然、传统、文化和历史等各种要素能力的事物。鲍尔格曼认为焦点物可以在技术社会漫无目的的生活中为人类提供一个中心,有助于人们在新时代中重新定位自身。他写道,焦点物“使人的身心共同参与和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中心。威严的在场(commanding presence)、与世界的联结(continuity with the world)和汇聚力(centering power)是焦点物的标志”。[27]显然,鲍尔格曼将“焦点物”看成是区别于“设备(device)”的东西。他写道:“物和它的语境(context),也就是它的世界不可分也和我们与该物及其世界的交往,即参与不可分。关于一物的经验,总是既包含与该物之世界在质料上的参与,又包含社会的参与。在唤起多方面的参与时,一个物必然提供了不止一种用品。因此,火炉在过去远不仅被用作取暖,而是被用作家具。” [28]有学者解释说,“聚焦物是这样的一些事物它以邀请人们自身参与的方式要求人们在场实现他们的能力”。[29]这就是鲍尔格曼所说的“焦点实践”,即要跳出技术模式的限定和统治,“在不降低其深刻性和一致性上保卫居于实践中心之物,就是保护它,使它免于被技术地分割为手段和目的”。[30]切特罗姆曾指出:“媒介这个词所产生的多种含义,表现出一种潜藏在全部现代传播方式历史中的矛盾因素在语言学上的遗留物。……这些矛盾一方面是由新的传播技术提供的进步的或是乌托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这些技术被用作统治和剥削手段的性质,广义地说,矛盾是由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表现出来的。” [31]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认为:“媒介首先是交流互动的资源,其次才是成为表达的形式或思考的客体”。[32]库利认为,媒介技术是指“包括表情、态度、姿态、声音的语调、词语、作品、印刷、铁路、电话和一切可以成功征服空间与时间的技术”。[33]公元前51年,古罗马政治家兼演说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西里西亚就任总督期间,便充分利用在莎草纸上抄录的文件来了解远方的情况。他写道:“其他人也会给我写信,很多人会向我提供新闻,哪怕是谣言,我也能从中听到不少消息。” [34]那个时代,虽然没有印刷术,也没有今天我们熟悉的大众传播媒介,但传播信息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事。
那么如何理解媒介技术的本质呢?海德格尔指出:“技术本质上既不是某个目的的手段,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目的。技术的本质在目的和手段领域之外,这个领域是有因果作用规定的,因而被界定为现实领域。技术本质上根本不是其他种种现实中间的一种现实,技术乃是如今一切现实领域的现实性的基本特征。现实性的基本特征乃是在场状态。技术之本质乃是在集-置之本质形态中的存有自身”。[35]他在论及广播和电影时说:“广播和电影也属于那种定制的存料,通过这种订置,公众本身受到摆置,受到促逼,并因此才被安排。广播和电影之机组乃是那种存料的存料-部件,这种存料,把一切都带入公共领域之中,并且因此毫无差别地为一切存在事物和每一件事物订置公众。” [36]“一切知识在一定意义上都取决于技术;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有力地断言:如果没有技术,人的知识就不可能存在”。[37]借用鲍尔格曼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传媒是典型的“焦点物”。“抽象的观念几乎完全依赖传播,传播则完全依赖抽象”。[38]而且“与其他技术不同的是,媒介技术具有创造想象环境的能力”。[39]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人是符号的动物或者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们都必须承认,人无法离开媒介所创造的想象环境而生存。
从鲍尔格曼的“焦点物”观念出发,对于媒介技术的理解,就“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40]在鲍尔格曼那里“物”之所以成为“焦点物”,“不仅仅在于‘物之为物’,还在于它的‘在场方式’、‘呈现’形式、‘场域’、与‘周遭’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以及那些‘不在场’却是这个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要素。它们共同组成了以‘物’为中心的人们生活的有机场域,生活世界由此得以展开,社会由此得以构建,文化由此得以产生”。[41]从这一观点来理解,显然与传统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按照威廉斯的总结,“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设想是一种新技术——一种印刷的报纸,或者一颗通信卫星——‘产生’于技术研究和实验。接着,它会改变它从中‘出现’的社会或者部门。‘我们’要适应它,因为它是新的现代方式”。[42] “我们怎么去使用电视,事实上也就突显了我们现有的某些社会秩序,某种人性,而这些社会秩序与人性又另由其他因素决定——即使没有电视的发明,我们还是免不了要受摆布,免不了的要茫无所知地渡过我们的娱乐生活。没有电视,也许只不过是这种受摆布与茫然的状态,要轻微一些罢了”。[4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技术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铁笼,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充满问题但可以从内部加以改变。” [44]
三、媒体进化的逻辑
技术是人身延伸观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曾提出,钱、商品和机器这些不同的实体,实际上都是对人类基本生产力或者说劳力的转换或者延伸。弗洛伊德则讲得更明确,在1930年的一本著作中,弗洛伊德写道:“人类利用每一件工具,完善企业劳动器官和感知器官,便逐渐消失了人类能力方面的限制……通过望远镜,人类看到了更远的距离;通过显微镜,人类克服了视网膜结构对视力的限制。人类发明了照相机,这种可以保留瞬间的仪器,发明了留声机来保存听觉的印象,这两者都是对人类回忆和记忆的物化,在电话的帮助下,人类可以听到远方的声音,即使是在童话故事中,这都是难以想象的。写作从最开始,就是来自心灵的呼唤,而房子则是母亲子宫的替代品。” [45]不过,媒介是人体延伸的观点,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被发扬光大,成为他的代表性观点之一。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写道:“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性增长,现在它正在经历内爆(implosion)。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electric technology)发展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致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地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到延伸一样”,[46] “我们的神经系统己经延伸而成一个全方位的信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进化的延伸。进化不再是千万年来生物学意义上的延伸,而是过去几十年那种信息环境的延伸”。[47]这一著名的媒介是人体延伸的观点,虽然看起来讲清楚了媒介技术演进的方向,但同样没有回答这一演进的逻辑是什么。
布莱恩·阿瑟有关技术进化的观点,也许有利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在布莱恩·阿瑟看来,“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来自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的组合”,[48]而且“技术的建构,不仅来自已有技术的组合,而且还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捕捉和征服”。但是技术不是随机的现成技术进行组合而成的,它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49]而且“技术具有递归性:结构中包含某种程度的自相似组件,也就是说,技术是由不同等级的技术建构而成的”。[50]雷蒙德·威廉斯以电视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电视的发明乃是非单一的事件或事件的系列。它有赖于一个在电学、电报、摄影与电影,还有无线电方面的发明和发展的复合体。它可以说是“在1875至1890年间作为一个确定的技术目标分离出来,接着,相隔一段时间之后,从1920直到1930年代的第一个公共电视系统,作为一个确定的技术实体而发展起来的。然而在其中每一阶段,它就各部分的实现而言都有赖于原本着眼于其他目的所获得的发明”。[51]布莱恩·阿瑟讲到一个核心的观点,那就是技术进化需要从人的需求的角度去思考。他指出:“技术是那些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我还可以说,现象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被驾驭、控制、缚住、应用、采用,或者开发的。” [52]英国作家Dougald Hin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坐着进城的那辆大巴上,每一位青少年和每一位成年人都坐在座位上,眼睛盯着他们那个小巧的、无所不能的机器:在这个口袋大小的窗口里,有我们永远也读不完的文章、永远也听不完的音乐、永远也看不够的裸照。可就在几年前,这种信息宝库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面对它们的时候,像我们这些现在已经多多少少成年了的人都会想:要是现在再变年轻,那该得有多不一样啊。我记得听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有了 Google,哪个小孩会觉得无聊啊?’” [53]著名的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认为:“一种革新,只有符合支持它和强制它的社会动力才有价值。” [54]雷蒙德·威廉斯显然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关于技术对需要的反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与实际决策集团的优先考虑相一致的需要,显然可以更快地吸引资源的投入和官方的允许、批准或者为任何实际使用着的技术,它有别于可供使用的技术设计所依赖的赞助”。[55]所以他指出,政治权力的中心化导致了对于从那个中心沿着非官方渠道而来的信息的需要。早期的报纸便是那种信息政治与社会消息和扩展着的贸易系统特有的信息分类的广告与一般商业新闻的结合体。“从机械与电子传输,到电报、摄影、电影、无线电广播与电视,这些技术手段互相激荡辉映,构成社会转型期的一大部分。个人意向汇整以后,形成了社会的要求,预期了某种科技的出现。在这一过程里,意向与需求固然会因为优势团体如资本家的塑造而变形,但也要在最小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得到其他人如一般劳动者的首肯”。[56]雷蒙德·威廉斯指出,“传播是个人独特经验转变成共同经验的过程……我们对自己经验的描述,组成了人际关系的网络,所有的传播系统又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我们对经验的描述中,必然有选择和解释,从而蕴含了我们的态度、需求、利益和兴趣,他人的描述亦然……这样说来,我们看事情的方式即是生活的方式,而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共享的过程——共同意义的分享,然后分享共同的活动、共同的目的,更有新意义的提出、接受与比较,导致了张力、成长和变迁”。[57]“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不得不经过一个神话阶段,在科学思想的历史上,炼金术先于化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科学只有靠着引领一种新的尺度,一种不同的逻辑的真理标准,才能超越这些最初的阶段。……科学不是要描述孤立分离的事实,而是要努力给我们一种综合观”。[58]那么技术的追求是什么呢?
技术的进化,毕竟包含着创造者对于他们理想生活的想象,如脸书原本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平台,可以更方便地约会女生,这种设计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但技术最终的呈现却超越了发明者最初的想象。因为在技术的演进过程中,加上了其他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想象。如此,技术便越来越与更多的人的理想生活(至少是某一面向上)更接近了。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赛博空间中,“虽然我们面对的不是现实的人和物,但是它却给我们真切的感受,实现着人与网络世界的真实互动。虚拟现实技术为感官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显得更为‘真实’的空间世界,人的感官在虚拟技术中被最大程度地调动、强化,使每一个参与者具有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真实’感、沉浸感”。[59]这种虚拟现实技术与增强现实的技术发展,正是对人类感官的一种抚慰,给人一种沉浸式的快感,对于越来越忙的人来说,那是一剂安慰的良药和一刻休息的港湾。
那么媒介技术进化、成长与变迁的目的是什么呢?
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每一种生物体都是一个单子式的存在物:它有它自己的世界,因为它有着它自己的经验。在某些生物种族的生命中,可以看到的一些现象,并不就可以转移到任何其他证书上去。两类不同的生命体的经验——因此也就是这两类生命体的实在——是彼此不能比较的。” [60]从生物学的视野看,不同的生命体虽然形态不同,结构有异,但却“各有一套察觉之网(Merknetz)和一套作用之网(Wirknetz)——一套感受器系统和一套效应器系统。没有这两套系统的互相协作和平衡,生命体就不可能生存。靠着感受器系统,生物体接受外部刺激;靠着效应器系统,它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这两套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紧密交织、互不可分的”。[61]人类世界当然也没有发现什么例外,但“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起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与动物的功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之外,在人类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他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人类生活”。[62]恩斯特·卡西尔的这番发现,宣示了人的独特本质——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媒介技术进化的逻辑,是否就在于它可以强化人类至关重要的符号系统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否可以强化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是一把打开理解媒介技术进化迷宫的钥匙。保罗·瓦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和其合作者在《人类沟通的语用学》中就指出,传播的原理之一是“人不可能不沟通(one cannot not communicate)”。[63]换言之,沟通是人类本质的基础。而沟通的前提,就是人类可以“创造”[64]和“使用”符号系统。
人类需要沟通,社会因为沟通而存在。沟通的本质,是彼此的相知、相识与相融,是手拉手,是心连心,是命运共同体,这是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这种类的存在的本质所在。传播的前提是有他者的存在,人类不过是希望通过传播去了解他者的生活,没有“你”,只有“我”的世界是不需要传播的。所以,传播的目的是发现并成就“我们”,大写的“我们”就是人类共同体,就是社会。也就是说,传播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得到有效实现。雷蒙德·威廉斯曾断言:“作为人类的生存共同体在现代传播技术营造的传播社会中也具备了建构的现实条件。传播技术时代的必然逻辑就是生存共同体的存在或建构,尽管当前的传播中仍存在一种支配性的气氛。” [65]他还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这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文化,我们将不能生存下去。” [66]这一观点与芝加哥学派很类似。罗伯特·帕克与欧内斯特·伯吉斯在研究广播和移民报刊时,就指出通过现代媒介技术的物质力量,能够实现社会组织化。
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曾指出,电报的发明激发出无数的世俗幻想:和平、和谐、沟通、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传播与人性、启蒙、进步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理想的引擎。[67]摄影技术的发明,则使得照片中的过去就是现在,逝去之物得以栩栩如生地留存。人类发明照相技术,不过是因为照片“意味着‘逝者回归’到自身形象及自身形象现象的结构之中”。[68]而电脑中介的通信使得即时对话成为可能,能够基于个人的兴趣将人们聚在一起,交互式沟通得以实现。[69]莱文森就发现,一边走路一边说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这是人最原初的人性化传播方式,今天这样的本能在人们使用手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个自古便形成的需要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表现之一。因为,人这个有机体要用声带和舌头发出有符号意义的声音,他要用下肢直立行走,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70]电脑和网络将人的本性与需求割裂开来,莱文森就希冀通过手机这种媒介来进行补偿。手机把我们送回大自然,使我们恢复同时说话和走路的天性。[71]沟通对于人的重要性之外,我们也许还要补充一环,即沟通媒介与信息的关系问题。麦克卢汉称“媒介即讯息”,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72]在麦克卢汉那里,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这个“讯息”是媒介自身所带的,而不是它所传播的内容,这个媒介自带的讯息才是决定人类结构调整和变化的关键。
鲍尔格尔认为,焦点实践(focal practices)是人们在焦点物的指引下,依照焦点物自身的秩序,维护焦点物深刻性和完整性的实践活动。他指出,焦点实践守护着焦点物,将其放置在中心位置,防止其被割裂为手段和目的,沦丧为设备。它使会聚在物之中的存在展现出来,进而克服了设备范式这一技术危机感性的现实基础,使人自由地栖居和游走在存在之中。[73]如果说,人类创造媒介技术是需求的产物,那么媒介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创造物,人如果被物役,成为物的对象,比如说,媒介变成权力控制的工具,成为商业的营利手段,便偏离了人类创造媒介技术的初衷——为“我”、为“我们”的自由与解放。
四、总结: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1999年鲍尔格曼出版了《抓住现实:千年之交信息的本质》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按照信息与现实的体验方式将信息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即自然信息、文化信息和技术信息。他认为信息能照亮、转换或取代现实。他这样写道:“为了避免陷于无尽无休的和没有结论的评论性的纠缠我们需要一种信息理论和信息伦理学……我们会看到,美好的生活需要在三种信息之间进行调节,需要在信号与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74]在“前技术”时代,人们看见颜色和三维空间,听见各种来源的声音,这些声音通常是与视觉同步的。人类已经能够接受直接环境中呈现出来的一切信息,并在这些环境中具有完全的主动性,也就是说,“在任何地点,人类都能够在其直接物理环境中,随心所欲地接收或者发送信息。但这样的交流只能发生在直接物理环境之内,因为不借助技术的交流要受到视力和听力范围的生物限制,而且只能通过人类的记忆过程得以延伸”。[75]即使到了今天,在一些不通电,没有电讯网络的偏远乡村,人们仍然如此。他们需要登高才能远望,需要高喊才能传出大约不到一公里的距离。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传播技术环绕的现代都市人,我们的信息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吗?鲍尔格曼所谈到的如何在三种信息之间的平衡问题处理得很好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有太多的冗余信息,而且大多数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我们的私人信息,因为各种移动技术和监控技术,而变得越来越难以保护了;我们渴望交流,而且我们在交流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我们仍然很孤独;微博上充满广告和商业代理,我们关心的信息得不到准确的报道,我们不想看见的“脑残”与恶俗却随处可见。所有这一切,都是生活在现代传播技术高度发达时代人类沟通的痛点,也自然是技术创新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把握媒介演进的未来走向了。
首先是信息的质量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信息的真实性核查问题。2016年,“后真相”成为热词。但“后真相”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不需要事实、不关心真相了。事实上,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追求的是“‘人人皆可进行信息表达的社会化分享与传播’的技术民主”,媒体技术的更迭与变迁自然不会改变人们对新闻基本品质的要求——真实、客观、全面、公正。诚如李良荣所言:“新媒体确实是打破了新闻生产由专业人士所垄断贩售的局面,但其作为一个理念在今天还是有用的。即使是个体化的小媒体,新闻报道也要求真实、客观、全面、公正。”近几年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事实核查类媒体分支部门或者专门机构,以帮助我们获得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据杜克大学新闻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2月,全球共有96个正在活跃运营的“事实核查类新闻”(FCJ)项目,其中大都以独立网站的形式存在,遍布在37个国家和地区。调查显示,他们的组织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北欧和西欧主要以依附于传统新闻媒体的模式为主,东欧和南欧则是以NGO建立的独立调查机构为主。如总部位于伦敦的事实核查慈善机构Full Fact于2016年开始开发自动事实核查工具,已获得来自谷歌公司的5万欧元经费支持,最近又宣布获得来自Omidyar基金会和Open Society基金会的50万英镑的额外资金支持。现在很多机构公开了核查方法和原则,推动这个行业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目前全球来自27个国家的35个事实核查组织在2016年9月签署了一项共同行为准则,标志着他们不仅自己作为独立事实核查者行事,也遵从共同的规范准则。美国的杜克记者实验室已部署使用ClaimBuster,向PolitiFact、FactCheck.org、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提供可能值得核查的信息。但截至目前,此类软件只能识别简单的陈述性语句,无法辨别那些人类能轻易识别的复杂句子中的隐藏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物联网时代,人与人、人与物,加上大数据存贮和分析能力的提升,是非常有利于对于真相的寻求和核查的。如据路透社2018年10月4日报道,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找到了沙特著名记者贾马尔·哈苏吉的遗体,确认是谋杀,贾马尔·哈苏吉被称为是沙特最敢言的批评者,生前供职于美国华盛顿邮报。贾马尔·哈苏吉未婚妻表示,由于贾马尔·哈苏吉担心沙特报复他对王储的批评意见,一直生活在华盛顿。他于10月2日进入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准备办理结婚所需的文件,之后失踪。一位土耳其高级警察说:监控录像显示,沙特记者贾马尔·哈苏吉遭到残酷折磨,被杀害以后切成碎片。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哈苏吉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时戴上了Apple Watch,它可能记录下哈苏吉进入领事馆后的过程。另外,使馆内外的监控录像也可以记录到当天使馆内的人员流动,甚至会有相关的视频。透过多个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人们便可能找到事实的真相了。
其次是网络巴尔干化以及群体极化问题。“信息技术不仅重构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也改造了人际关系的结构。社交媒体一方面卓有成效地完成了相同背景、相同观点、相同兴趣个体的组织聚合;另一方面也因本能的利益驱动,通过个性推荐、定制推送等算法机制将业已隔离的网络社群进一步割裂”。[76]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通纳·詹姆斯·芬奇(Stoner James Arthur Finch)于1961年就发现了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他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群体决策情境中,个体的意见或决定,往往会因为群体间彼此相互讨论的影响,而产生群体一致性的结果。[77]1996年,阿斯汀和宾杰桑(Alstyne & Brynjolfsson)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突破地理障碍而进行,但由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个有限的常数,而且人们在接触信息和建立联系时会体现出一定的偏好,所以网络传播带来的未必是地球村,而只是人们交流方式的一种转换,从原先地域性交流转变为以共同兴趣和偏好为基础的交流。[78]维尔姆(Wilhelm)对网络群体的研究也发现,即使那些通常被认为最容易卷入多元意见的政治议题的讨论群体也经常发展成意识形态同质的“兴趣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est)。[79]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平台算法,就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偏好来推送内容,这自然更容易形成信息茧房,进而导致群体极化。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贾斯汀·卡塞尔对此建议说,媒体将新闻传递给每家每户每一个人时,每一个人收到的内容应该是不一样的,同时能够确保每一个观点都能够得到不同受众的认可,不仅可以听到官方的观点与信息,还可以听到大众的观点。人工智能在聚合大众的同时,需要把不同的观点融合到一起,不能存在偏见,“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我们需要去排除一切的性别、年龄、种族以及背景的歧视”。[80]由于各种不同的舆情传播造成的分裂是当今矛盾与冲突的来源,群体极化盖源于此,这便需要通过更为有效的专业技术手段去统合。蒋纯认为,商品、精神产品都可以个性化分发,但新闻是不能个性化分发的。“对新闻的个性化,让部分真理自我传播、自我加强,是制造社会分裂的行为。而我们回想到我们新闻专业主义的初心,理性、中立、客观,是要让整个社会有一个共识,然后在真相的客观、理性、中立上找到国家前进的方案。如果我们造成整个世界分裂的话,这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81]三是新闻的“公共服务”问题。在莱茵报工作时,马克思指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82]在新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再次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83]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也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习近平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必须“着眼于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84]显然,新闻出版的重要使命是为公众服务,这就是一个公共服务的追求。潘忠党和陆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即各群体表述和交流其诉求、巩固共同体的内部纽带、形成协调性行动、建造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亦可以单数形态译作‘公共善’)的社会活动,必需共享的事实性信息,而这事实性的判断不能由资本或政治权力所垄断,必须由独立的社会机构、具有必要技能而且获得社会认可的专业人士按照公开、可循的程序和规则来确定。” [85]他们在文章中介绍说,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吉尔·阿卜拉姆森(Jill Abramson)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新闻并非仅仅是一份工作或一个职业,它还是(或应当是)一份收入和社会声望不错的工作,它更是一种“服务公众的召唤”(a calling for public service)。在中国,“铁肩担道义”是卓越新闻人的追求,也是社会公众对新闻业的期许。从“公共服务”这一点看,至少中外理念上是相通的。但今天已经进入了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如何确保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还具有这种公共性显然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每一个公民都有传统媒体时代的专业记者与编辑的媒体素养,那么传媒技术在多大层面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为传媒技术未来最大的挑战之一了。
四是私域信息的安全问题。“电视的一大实力便是比其他任何技术都能更充分、更有力地进入当下的、当代的公共行为和——在某种意义上进入——私人行为的领域”。[86]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让私域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更是越来越模糊。私域是公众权利得以保护的空间,是自由主体自由的空间,在过度社交时代,这更是一个人得以修复和补充能量的空间。但梅洛维茨指出,“电视和其他的电子媒介,把敌对的外部社会带到家里来,这既改变了公共领域也改变了家的领域”。[87]威廉斯认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两种既矛盾但又深深相互关联的趋势:一方面,人们在工业社会往往需要四处流动;但另一方面,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愈来愈可以在家庭中得到满足。早期的公共设施,以铁路最为明显(只能满足流动的需要),逐渐被新起的技术条件,如收音机、汽车等所取代。对于后一种可以同时满足流动,并且满足家庭作为生活中心的现象,威廉姆斯称之为“流动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他解释说,“外在世界是人生活的依靠,他在闭锁的空间里,却短暂的以为他是独立自主的中心。这种既能‘流动’,又可以‘藏有’个人财货,并且达到‘隐私’目的之现象”就是“流动的藏私”。[88]在工业社会,打破了家庭手工作坊一体模式,将工作单位与家庭拆解开来,呈现出流动的特点。家庭的生活支撑需要依仗外部世界的支持和保障。在威廉斯这里,“藏私”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通过工作获得金钱可以购买私有的物产,另一方面也指家庭这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移动网络平台,正在不停地收集我们的数据,他们随时入侵大众的私域——如我们生活消费习惯、阅读习惯、生活与工作场景、交友的偏好等等。我们已经无处可以藏私了。未来的沟通技术,显然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花更多的努力。
五是时代精神的救赎。我们从哪里来?如今身在何地,又将向何方?各种不同的媒介渠道向我们传递着各种不同的信息、知识和答案,人们应该越来越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吧?事实正好相反,太多的选择或者只有唯一的选择都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数的答案其实就没有答案。“每个钟点,每一天里,他们都为广播电视所迷住。每周里,电影把他们带到陌生的,通常只是习以为常的想象区域。那里伪装出一个世界,此世界其实不是世界。到处是唾手可得‘画报’。现代技术的通讯工具时刻挑动着人,搅乱和折腾人——所有这一切对于今天的人已经太贴近了,比农宅四周的自家田地,比大地上空的天空更亲近,比昼与黑夜的时间运转、比乡村的风俗习惯、比家乡世事的古老传说更熟悉”。[89]我们听和读到某些东西,也即简单地知道某些东西,这是一回事情;而我们是否认识到,也即思考过所见所闻,却是另外一回事。20世纪相继出现的飞机、电视和互联网,“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空间感、时间感、图像意识和视觉经验等”。[90]地球村得以成为现实,人类的普遍交往网络也得以形成,但人并没有得到期望的全面解放,手虽然可以拉着手,但心无法连着心。个体与孤独与群体的焦虑,并没有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得到片刻的缓解,相反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敢“与陌生人说话”。各种恐怖组织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现代传播技术来宣传他们的主义并呈现他们的暴力恐怖手段,狭隘的政治家和阴谋家通过煽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通过分裂社会而谋利。人类命运共同体至今还是一个梦想,如果传播技术不能在人类精神救赎上找到一条可靠的方式,那么我们仍然是上帝的弃儿。
在本文的最后,引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人与野兽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类自身那种心高气傲、永不知足的主观精神取向。人类后来能够超越野兽,纯粹由于人类的需求特性——包括他的物质需求、道德需求、审美需求以及知识和智能需求——无论在数量上或它那种奇妙又似乎全没必要的特性上,都绝对超过了野兽。人类能超越野兽,原因仅此一点,而非其他。……人类还可以汲取一个重要教训和启发,这就是:他的这些需求都是正当的,是可以信赖的,甚至即使恣纵放任,放浪形骸,那么,随即引起的不安和自责,也会成为人类下一步的最佳向导,引导他们思索如何面对目前尚无力解决的各种重要难题。你若把他们身上这些毛毛躁躁的东西全部去除,让他们回归冷静理智状态,你可就把他们彻底毁掉了。” [91]■
①[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第5页,曹东溟、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②[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115页,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③[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113页,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④[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128页,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⑤[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140-141页,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⑥[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第213页,陈允明、王克仁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⑦[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和论文集》第1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孙周兴译,2011年版
⑧马丁·海德格尔认为,大地(die Erde)承受筑造,滋养果实,蕴藏着水流和岩石,庇护着植物和动物。天空(der Himmel)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是周而复始的季节,是昼之光明和隐晦,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日的温寒,是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诸神(die Gottlichen)是暗示着的神性使者。从对神性的隐而不显的支配作用中,神显现而成其本质。神由此与在场者同伍。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乃是人类。人类之所以被叫做终有一死者,是因为他们能够赴死。赴死(Sterben)意味着有能力承担作为死亡的死亡,因此只有人才能说赴死,而动物只是消亡而已。
⑨[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和论文集》第185-18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孙周兴译,2011年版
⑩[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和论文集》第19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孙周兴译,2011年版
[11]蒋红雨:《表象之思与切近之思:海德格尔物的分析思想》,《哲学研究》2015年第7期
[12][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和论文集》第1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孙周兴译,2011年版
[13][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和论文集》第18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孙周兴译,2011年版
[14]WPS Dias ,Heidegger’s relevance for engineerin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Science & Engineering Ethics, 20039(3):389-396
[15]技术是人类与世界交往的特殊方式。传统社会中,人们使用工具与世界打交道,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所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化,因此鲍尔格曼将其称之为“设备”(device)。“设备”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大大强于传统技术模式下的“工具”。参见董晓菊、邱慧:焦点技术观是本质主义技术观吗?《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6期
[16]参见顾世春、文成伟:《物的沦丧与拯救——鲍尔格曼设备范式与焦点物思想探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7]顾世春、文成伟:《鲍尔格曼和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分岔口》,《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1期
[18][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17-18页,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15年版
[19]顾世春:《从海德格尔到鲍尔格曼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研究》,大连理工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20]BorgmannA. Technology and the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p.104-105
[21][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第12页,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2][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第203页,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3]吴飞:《新闻传播研究的未来面向: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
[24]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93.
[25]刘鹏、蔡仲:《法国科学哲学中的进步性问题》,《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
[26]Albert Borgman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96.转引自邱慧:《焦点物与实践——鲍尔格曼对海德格尔的继承与发展》,《哲学动态》2009第4期
[27]Borgmann A. Crossing the Postmodern Divide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19-120.转引自顾世春、文成伟:《物的沦丧与拯救——鲍尔格曼设备范式与焦点物思想探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8]转引自邱慧:《焦点物与实践——鲍尔格曼对海德格尔的继承与发展》,《哲学动态》2009年第4期
[29]傅畅梅:《论“装置范式”研究纲领的核心——技术信息》,《科技管理研究》2011年第2期
[30]阿尔伯特·鲍尔格曼:《设备范式与焦点物》,录信邱慧译、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第409-432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1][美]丹尼尔·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第199页,曹静生、黄艾禾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32][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第88页,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3]Coolev C. Social Organizition: A Study of the Lamer Mi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7.61
[34]引自[英]汤姆·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第4页,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35][德]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第120页,孙周兴编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36][德]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第103页,孙周兴编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37][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第103页,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8][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第153页,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9]Kirsty Best,Rdefining the Technology of Media: Actor,World,RelationTechne: 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2010,14( 2) :140-157.
[40]南帆:《双重视野与文化研究》,《读书》2001年第4期
[41]翟源静、刘兵:《从鲍尔格曼的“焦点物”理论看新疆坎儿井角色的转变》,《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
[42][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第171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3][英]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与社会形式》第24页,冯建三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44][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第2页,陆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5]转引自[美]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的回放:媒介进化论》第22页,邬建中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引用时,对译文略有改动。
[46][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第4页,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4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第104页,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8][49][50][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第14、26、37页,曹东溟、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1][英]R.威廉斯:《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技术与社会》,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2期
[52][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第53页,曹东溟、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3]Dougald Hine:《既然每天都能读到大量信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感到无聊?》,《好奇心日报》公众号2016年2月11日
[54]转引自[法]帕特里斯·费里奇:《现代信息交流史: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第3页,刘大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5][英]R.威廉斯:《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技术与社会》,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2期
[56]冯建三:《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译者导言》,见[英]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与社会形式》第15页,冯建三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57]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196138-39.转引自许继红:《雷蒙德·威廉斯技术解释学思想研究》,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58][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288页,甘阳译,上海译出版社2004年版
[59]李宏伟:现代技术的社会文化后果,《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4期
[60][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33页,甘阳译,上海译出版社2004年版
[6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34页,甘阳译,上海译出版社2004年版
[6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34-35页,甘阳译,上海译出版社2004年版
[63]WatzlawickP.BavelasJ. B.& JacksonD. D.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1967.p.51
[64]这里也许用“更新”更合适。因为基于乔姆斯基和史蒂芬·平克等人的观点,语言符号不过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参见[美]诺姆·乔姆斯基:《语言与心智》,熊仲儒、张孝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美]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5]转引自许继红:《雷蒙德·威廉斯技术解释学思想研究》,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66][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395页,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7]丁未:《电报的故事: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新闻记者》2006年第3期
[68][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第15页,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69][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561页,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70]参见[美]保罗·莱文森:《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第17页,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第9页,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第19页,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73]参见顾世春:《从海德格尔到鲍尔格曼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74]Albert Borgmann. Holding on to reality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转引自傅畅梅:论“装置范式”研究纲领的核心——技术信息,《科技管理研究》201131(2):216-219。
[75][美]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的回放:媒介进化论》第149页,邬建中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76]虞鑫:《语境真相与单一真相——新闻真实论的哲学基础与概念分野》,《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77]StonerJ. A. F.(1961). 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8]转引自陈红梅:《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和群体极化——整合视野的思考》,《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
[79]Wilhelm, A.(1999). Virtual Sounding Boards: How Deliberative is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in B.N. Hague and B.D.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Routledge. pp.154-77.
[80]郜晓文:《当AI是遇见传媒业》,《人民政协报》2018年5月23日
[81]蒋纯:《以新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重建社会共识》,2016年中国全媒体高峰论坛(杭州)的发言内容。http://www.zjdj.com.cn/zl/gd/yxt/201701/t20170105_2699515.shtml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61版。本处引用时采用了陈力丹的译文。参见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2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4]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6-01/31/c_135060747.htm
[85]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86][英]R.威廉斯:《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三)——电视的形式(续完)》,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6期
[87][美]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第42-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8]冯建三:《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译者导言)第13页,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89][德]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第180页,孙周兴编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90]孙周兴:《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之思》,录入[德]海德格尔:《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第201页,孙周兴编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91][美]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上卷):技术发展与人文进步》第45-46页,宋俊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
吴飞系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