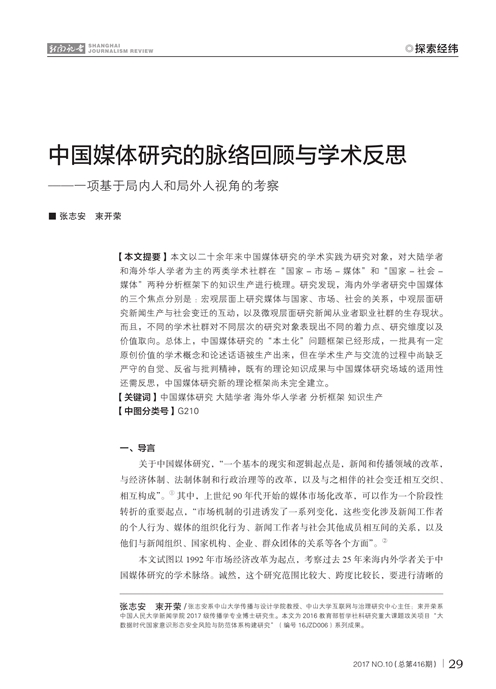中国媒体研究的脉络回顾与学术反思
——一项基于局内人和局外人视角的考察
■张志安 束开荣
【本文提要】本文以二十余年来中国媒体研究的学术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大陆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的两类学术社群在“国家-市场-媒体”和“国家-社会-媒体”两种分析框架下的知识生产进行梳理。研究发现,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媒体的三个焦点分别是:宏观层面上研究媒体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中观层面研究新闻生产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以及微观层面研究新闻从业者职业社群的生存现状。而且,不同的学术社群对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表现出不同的着力点、研究维度以及价值取向。总体上,中国媒体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框架已经形成,一批具有一定原创价值的学术概念和论述话语被生产出来,但在学术生产与交流的过程中尚缺乏严守的自觉、反省与批判精神,既有的理论知识成果与中国媒体研究场域的适用性还需反思,中国媒体研究新的理论框架尚未完全建立。
【关键词】中国媒体研究 大陆学者 海外华人学者 分析框架 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导言
关于中国媒体研究,“一个基本的现实和逻辑起点是,新闻和传播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法制体制和行政治理等的改革,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变迁相互交织、相互构成”。①其中,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媒体市场化改革,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转折的重要起点,“市场机制的引进诱发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涉及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行为、媒体的组织化行为、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其他成员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新闻组织、国家机构、企业、群众团体的关系等各个方面”。②
本文试图以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为起点,考察过去25年来海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媒体研究的学术脉络。诚然,这个研究范围比较大、跨度比较长,要进行清晰的梳理和细致的爬梳,无疑具有不小的难度。为此,我们尝试将大陆学者、海外华人学者作为两类学术社群,大体采取“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从学术群体、研究对象、分析框架以及知识生产等四个维度来梳理这25年来中国媒体研究的基本脉络和总体图式,以期为后续中国媒体研究提供一些反思。如果说,本文还有一些更高的期待,则是希望这篇文章对“过去”的描绘轮廓不仅在于说明“现在”的意义,还在于创造出各种交汇点,实现我们与过去的重逢。③
(一)研究问题
针对中国媒体的研究,“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产生于社会变革的具体历史场景”。④本文的研究重点不在于发掘中国媒体研究的“知识存在基础”,而是将作为知识生产的中国媒体研究,嵌入特定的社会语境与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勾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改革和互联网技术作为社会变迁的两个重要变量的双重作用下,海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媒体研究的知识地图,并继而探讨转型社会的中国媒体研究不断提升的路径、理论与方法。
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这个阶段,中国媒体研究的知识生产特征和变化过程是怎样的?本土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媒体的研究,在问题关注、现象阐释以及理论建构方面,具有哪些特征和异同?后续关于中国媒体的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来着力提升?
(二)分析图式
本文试图从学术社群、分析框架、研究对象和知识生产四个维度来展开本文的分析,以此来阐明连贯、矛盾甚至对立的问题、方法、概念与理论。相关概念,分别简要说明如下:
1.学术群体
本文将中国媒体研究的学术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中国媒体场域内部直接经历新闻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的大陆学者,一类是受过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社会学训练的华人学者(包括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外国学者,他们主要是从场域外部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媒体。
李金铨曾对大陆与华人学者之间的知识生产特点作过简单的描绘。他认为,“从知识论来看,‘局内人’靠经验与观察求知,局外人以反省和阐释见长,各有千秋,各具盲点。华人学者看华人社会更能解读微言大义,更能掌握各种网络关节,但这不是必然的或与生俱来的趋势”。⑤如果将身处转型社会语境中的大陆学者视为“局内人”(insider),那么,海外学者则可以被视为“局外人”(outsider)。
当然,“局内人”和“局外人”并非界限分明,而是互有交集。譬如,华人学者由于既有中国大陆生活经历又身处海外高校从教,介于“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但总体更接近于“局外人”;“局内人”和“局外人”在研究视野、关注问题以及研究方法上相互启发,而且两类学术群体间进行合作研究、联合发表论文已屡见不鲜。
2.分析框架
本文将两类学术社群对中国媒体的研究纳入到两种分析框架中考察。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既有研究主要围绕着国家、市场、社会与媒体等四个解释变量,形成“国家–市场–媒体”与“国家–社会–媒体”两类分析框架展开描述、分析和阐释。
这两种分析框架并非二元对立,也并非分析中国媒体的理想模型,只是在研究国家和媒体关系时对市场和社会这两个变量的侧重有所不同。转型社会的中国,国家并不必然与市场、社会相对立,而市场和社会也不必然与媒体形成紧密或脆弱的联盟。为此,本文试图将“国家–市场–媒体”与“国家–社会–媒体”这两个分析框架置身于中国社会的特定语境,考察其呈现的复杂互动关系和不同作用机制。
3.研究对象
在上述的两种分析框架下,中国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三个层次上:相对宏观的“媒体组织”、相对中观的“新闻生产”,以及相对微观的“职业社群”。同时,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之间又形成理论对话、实践交织及多重影响。其中,媒体组织与政府(权力)、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新闻生产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过程,以及新闻从业者这一职业社群的生存现状,是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媒体的三个关注点。此外,不同的学术社群对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表现出不同的着力点、研究维度以及价值取向。
4.知识生产的层次
一般来说,“描述特征”“现象阐释”“概念提炼”以及“理论建构”可以视为知识生产逐步递进的四个层次,如何从描述特征、现象阐释走向概念提炼和理论建构,是学者在研究中国媒体时的普遍追求。本文试图运用知识生产的层次来作为分析视角,考察不同类型的学术社群(局内人、局外人),在两种分析框架下(国家–市场–媒体与国家–社会–媒体),针对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媒体组织、新闻生产与职业社群),在知识生产的不同层次上如何着力、怎样实践,并进一步探讨在对中国媒体变迁特征与现象描述的基础上,原创概念提炼和理论建构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可能。
二、局内人:社会变迁语境中的媒体实践研究
在中国媒体研究的学术场域内,大陆学者“如何言说”往往要比“言说什么”更加重要。本文将“局内人”与“局外人”分开论述,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凸显特定政治经济环境对于局内人研究中国媒体的特殊影响。总体上看,如何在现行新闻体制和政经格局中去解释中国新闻体制变革轨迹以及新闻业的自主性状况,始终是作为“局内人”的大陆学者长期关注的重要命题。
(一)描述与阐释: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与话语建构
为何选择将“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作为梳理和反思国内学者对中国媒体研究的嵌入点?主要是基于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一方面,新闻专业主义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发展脉络、建构与消解等方面的探索兴趣。⑥而且,立足这个概念对中国媒体格局的描述与阐释,呈现出多个面向的学术立场乃至争议。另一方面,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经验与理论探索,远不能反映中国媒体改革发展的复杂格局,以及此格局内政经作为决定性力量与行动者网络之间的博弈过程。
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媒体场域中既是建构媒体话语的重要资源,也是规范媒体实践的主导价值。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学者试图将中国媒体的改革实践置于“国家–市场”“国家–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中,解读这种话语实践与中国媒体自主性寻求之间的关系,并体现出增强中国媒体自主性的愿景。
不少研究者将其运用于对新闻业自主性的考察。其一,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新闻专业主义是1990年代新闻改革的表征,它与稍早兴起的信息、传播、受众等西方观念一起,标志着“新闻模式的扩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⑦其二,作为一套话语,它论述着中国的新闻体制与新闻改革实践,并日益成为中国新闻界和新闻传播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议题。⑧其三,作为一种操作原则,新闻专业主义在职业意识形态“前台”的复现推进了中国新闻业变革,激发和鼓舞了更多新闻人的专业自主意识和职业道德勇气。⑨
有研究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媒体,是通过改造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活动空间而发挥影响。⑩陆晔、潘忠党研究发现,长期以来,在宣传管理、市场驱动、媒体自主性这三种力量的拉扯当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形态始终是碎片化和局域性的。[11]这里的“三种力量”对应了我们考察中国媒体时常用的三个变量,即国家、市场与媒体。研究表明,“国家–市场–媒体”的分析框架可以比较清晰地揭示媒体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复杂勾连和张力特征。虽然芮必峰曾指出,能否用新闻专业主义来描述和规范中国的新闻生产实践尚且存疑,[12]但仍有不少本土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当成一种主导范式来研究中国媒体。
黄月琴进一步认为,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话语工具的特殊性在于,自专业主义理念引入国内以来,就始终处于“可欲与可得”的困境之中。作为一种自由精神的实验与实践,其重要性不是再现或者规范,而是激发新闻工作者对中国媒体体制变革的不同思考,以发现、链接和开创不同的逃逸路线与可能性空间。[13]陈阳进行相关研究的梳理后发现,新闻专业主义被描述为与党报传统截然不同的新闻范式,对专业主义的内部差异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很多涵义不同的行为都被视为专业主义的表现。[14]樊昌志、童兵跳出话语实践的层面,认为在媒体–政府–公众的传播结构中,政治和经济权力建构了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向政经权力实行了反向的建构,进而建构出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15]近年来,一些学者更多侧重考察互联网代表的新技术语境和当下媒体所处的变迁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的新变化,或对专业主义可能面临的消解风险表示出隐忧,或对其核心内涵和价值予以重申。比如李艳红针对当前新闻业转型话语进行分析,指出由于新闻业整体面对新媒体冲击,逐渐失去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专业主义话语赖以生成的两个重要条件——政治空间的相对放松和商业利润丰厚带来的“从容”,从而导致缺乏体制空间的专业主义话语基本让位于商业主义话语。[16]陆晔、潘忠党指出,尽管受到国家权力、资本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挑战,“构成新闻专业主义内核的那些信念和原则依然闪耀,激励着新媒体创新的种种实践,蕴含于去职的无奈,影响着创业的价值目标,隐藏在沉默的背后”。[17]此外,也有学者倾向于质疑与反思新闻专业主义被赋予的解放与规范力量。王海燕从批判的视角出发,[18]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本质上是一套趋向保守的新闻操作规范,其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具有突破单一宣传模式的进步意义,但其意义不能过分被夸大。比如在社会利益分化和舆论极化日渐加剧的当下,新闻专业主义在促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平衡发展上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因此,在发展新闻专业主义的同时,中国媒体也急需发展替代性媒体和补充性的新闻操作规范。
总体上,大陆学者在意识到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问题的同时,更倾向于建立新闻专业范式与传统党报范式的二元对立范畴,而对专业主义范式阵营内不同媒体间的差异却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这对范畴之所以被作为知识生产出来,可能是大陆学者在市场化进程中,运用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话语工具建构“国家–媒体”“国家–社会”张力空间的诠释策略。这样做的一个现实目的或在于通过区分新型市场化媒体与传统党报机关报的界限,以凸显新闻专业主义所形塑的媒体组织模式、新闻生产方式以及职业社群的力量。
(二)受到限制的演绎:“国家-市场-媒体”的整合框架
中国的媒体系统是被其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形塑的,从“政府–媒体”的关系视角开展研究是理解中国媒体的基础。转型中的中国媒体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扮演“协调人”的角色,贯通两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实现国家与市场的融合。[19]大陆学者对中国媒体组织的特征及变化、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职业社群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这三类研究对象的考察,所采用的理论架构之一就是“国家–市场–媒体”的整合框架(integrated frame)。所谓“整合”,总体上看是通过构建复杂现实与多元意义,以冲淡市场化过程中“媒体与国家”“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对这两组关系的考察中,作为“局内人”的大陆学者在多数研究中把国家这个共同变量作为一种“既定概念”(established concept)悬置于研究的边缘地带。这一“非全景式”(non-overall perspective)的学术视野,反映在学术价值取向上,恰在于“局内人”对中国媒体研究的阐释实践相对缺乏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考察。
大陆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问题中对这个“整合”框架的阐释和演绎是受到限制或者有所保留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讨论中国媒体系统时,研究者或公开或含蓄地表达他们希望使用替代性的文化传统来对新闻体制改革有所引领,意在通过适当强化和凸显媒体与国家、市场之间的矛盾,描画三者的现实张力。二是,囿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研究者对市场化进程中国家与媒体、国家与市场的现实关系及相互影响缺乏足够充分的“论述机会”(discourse opportunity),遂代之以“社会控制”概念范畴中的“政治因素”和“新闻管制”,并在媒体组织、新闻生产以及职业社群等不同层面的具体探讨中建构出“理想与现实”“对抗与控制”“博弈与妥协”等二元对立的学术话语。
1.针对媒体变迁轨迹的宏观论述
李良荣曾对不同阶段新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有过总体性论述。他认为,作为政治、经济、社会深刻变化的伴生物,中国新闻体制的变迁逻辑总体上是由观念变革作为驱动力的;[20]从1992年开始,权力中心对中国媒体系统的定位开始跨越上层建筑的范畴,“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是媒体“双重属性”在转型中国的现实反映,他将这个思路总结为“稳住一头、放开一头”;[21]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新闻改革的重点不在媒体的功能及其传播内容上,而是转移到媒体的外围即经营管理上;进入新世纪,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出现重大变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但“管办合一”体制仍是培养真正市场主体的主要障碍。[22]面对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李良荣认为,中国的传媒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双转”,即体制转轨和形态转型,前者强调国家和市场的双重调控,后者在于媒体融合。[23]在他对中国新闻体制的描述和阐释中,国家与新闻业的关系视角时隐时现,但国家作为解读中国新闻体制的关键变量,基本上是被整合进与市场、社会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中去考察的。由于中国的媒体系统根植于体制和国情,媒体变革的现实是政府、市场、公民及媒体相互关系的结果,[24]这种介于博弈与妥协、对抗与控制之间的解读和阐释有其认识和公共表达上的合理性。
回顾中国新闻体制改革30周年,黄旦认为,中国媒体不可能自然由量变导致质变,相反,结构上的突变才是关键。[25]陈力丹认为,中国的媒体政策已经制度化了,遏制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26]李良荣也强调,新闻体制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新闻改革的制度性壁垒就无法突破。[27]如果将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放在国家–市场–媒体的分析框架中解读,“市场”的激活力量已经基本释放,为进一步激发新闻体制改革的动力,学者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国家”这个变量,寄望于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媒体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中国媒体自主性的寻求和建构,依托的主要是市场机制的引入,较长时间里的关注重点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国家”作为相对静态的变量是被淡化或隐去的。不过,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国家”变量被学者们再度重申,强调这是决定未来中国新闻业发展的主导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周翼虎考察“国家与新闻业”关系时,也始终强调“国家”在形塑中国新闻体制及其变迁轨迹中的主导地位,只不过“国家”不是近年来才被“发现”,而是一直被“忽略”。[28]为了建构“国家–新闻业”的二元对抗性政治模型,从上世纪9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市场”被界定为“一种依附性而非能动的机制”。以至于在周的论述中,“市场”甚至不能够作为分析单位来搭建“国家–市场–新闻业”的解释框架,“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容纳国家目标、社会思潮、经济体制改革诸多综合现象的‘杂货框’,还缺乏进一步展开分析的经验基础”。所谓的国家与新闻业30年来的“攻防游戏”,其结果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国家力量使得中国媒体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国家结成有条件的联盟,最终形成一个满足国家、新闻记者、公众需求的三元次优结构”。
2.基于复杂现实的中观与微观考察
一些研究者基于对新闻职业社群和新闻生产的中微观考察,凸显国家与市场、媒体之间的张力关系,为受限制的“国家–市场–媒体”分析框架增添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张力,呈现出特定语境中的复杂现实。
对新闻生产的考察,芮必峰以“制约”和“使动”概念来解读中国语境下的“宣传通知”现象,强调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宣传管理兼具制约和使动两个方面的作用。[29]使动和制约表面上是一个二元对立组合,但前者的加入形塑了一个双重且多维的“宣传通知”现象,这一现象之于新闻生产的复杂性便得以揭示。陆晔、周睿鸣以澎湃新闻的灾难报道为个案,以“液化共同体”描述新媒体环境对新闻职业共同体以及新闻生产的复杂影响,认为新闻生产中的“机构与个体”“专业与业余”“边界内与边界外”“前台与后台”等由专业主义意识形态支撑的二元对立表述逐渐融合、消解。[30]王海燕通过对广州一家以记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酒吧进行民族志考察发现,新闻工作者的诠释性共同体不仅存在于新闻编辑部组织内部,也可能在新闻编辑部之外的空间形成并发展。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组织外的空间,新闻从业者摆脱了日常工作中必须面对的政治、经济、新闻机构和常规等局限,得以建构出一套不同于组织内部的新闻工作职业价值观。[31]虽然“国家(权力)”在宏观论述中被或多或少地淡化,但在中微观的职业社群研究中,新闻从业者的行动和言说仍然反映了权力实践的深层逻辑,“理想与现实”这个新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被建构起来。丁方舟将理想和新媒体视为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的两个核心话语,[32]两者均建基于二元对立的逻辑,所谓“理想/现实”“新媒体/传统媒体”,以此批判新闻业现状、重塑专业准则,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在变动的场域结构中重新寻找得以安身的位置感。赵云泽等认为,当下中国记者的职业地位在转型社会中显著下降,原因主要是记者“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两者导致了职业神圣感的丧失、职业伦理下滑等一系列问题。[33](三)建构自主性:“国家-社会-媒体”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
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曾经因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论争而变得比较敏感。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媒体–社会”关系的讨论步入正轨,包括媒体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是解读和建构这对关系的主力军。同时,由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他们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34]这种影响反映在中国媒体研究的知识生产中,则呈现出两种值得反思的路径。一是,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常常被简化为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二是,在讨论“媒体–社会”关系时,很少把“国家”概念引入批评话语,“国家–社会–媒体”的分析框架并未完全展开。
1.新闻职业社群与媒体公共空间的建构
近年来,媒体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转型社会语境中,“媒体–社会”关系经历了变迁与重构。在“国家–社会–媒体”的分析框架中,媒体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命题之一就是“媒体公共空间”的建构。
黄旦认为,“中国媒体公共空间的建构,宏观上源于整个改革开放的情势。迄今为止,媒体的公共空间都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力所能及的即兴表演”。[35]陈力丹则认为,中国媒体只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充当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大多数情况下,传媒作为公共领域“其实说的不过是传媒的民生新闻”。[36]两位学者从媒体公共空间建构的视角对“媒体与社会”关系的讨论,都是运用公共领域理论对媒体进行的本土化解读,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黄旦更加关注“即兴表演”在媒体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作用。
伴随着新闻生态系统的变化,作为组织化的个人,职业记者的身份认同与公众的社会认同之间发生的冲突,重构着职业群体对媒体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继而调适着职业社群的话语实践。一些研究者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对“媒体–社会”关系进行历史梳理和逻辑反思。比如,孙玮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在媒体领域中的变化,描绘了1978年以来大众化报刊的媒体话语变迁,指出大众化报纸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不同社会主体的话语建构展现了媒体与社会变迁的动态关系。[37]面对中国社会明显加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和阶级意识的感知,赵月枝认为,简单地建构媒体消费者、公众和受众这些全称概念会掩盖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模糊媒体和传播在中国社会新旧权力关系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38]此外,不少研究者以职业社会学方法测量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知,采用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研究新闻生产的特征、过程及后果,以此来揭示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从事新闻职业的社会行动者对“媒体公共空间”的认知和行动。首先,职业社群的观念认知呈现明显变化。陆晔发现,新闻记者的职业选择动机更多处于道德传统中所强调的个人与社会关系。[39]陈阳梳理记者职业角色从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到观察者的变迁轨迹及其趋势,[40]认为四种职业角色共同影响中国新闻界的现状及走势。张志安、沈菲研究发现,[41] “价值理性”与“倡导者”对中国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具有显著影响,其职业满意度与忠诚度整体一般,且都比较低。白红义对调查记者群体职业角色认知状况的研究也发现,[42] “倡导式”和“中立式”职业角色共存于调查记者的职业认知中。
其次,由职业社群参与的新闻生产及其所在媒体机构,表现出“媒体公共空间”建构在实践层面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比如,曾繁旭、黄广生研究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媒体体系对都市社会维权运动新闻生产机制的影响。[43]黄月琴在厦门反PX散步事件的案例研究中,将官方论述描述为“恶承认”与“恶分配”权力关系的综合体,而异地传媒的传播话语实践是为“承认”的斗争政治。[44]2.媒体组织、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互动
媒体组织、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互动,是新闻生产社会学长期关注的重点议题,这个路径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十余年来,一些大陆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复旦大学三篇博士论文,立足于转型中国的社会语境,从话语分析、编辑部观察以及政治经济学视角,就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考察,比较具有代表性。
洪兵对1983-2001年期间的《南方周末》进行新闻生产社会学分析,[45]将其置于中国社会各系统发生全面和深刻变化的历史场景中,肯定了《南方周末》的新闻生产对转型中国的深远影响,其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供了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与媒体系统进行连接和分析的尝试。张志安对《南方都市报》新闻生产的内部观察,[46]以新闻生产自主性为线索,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使用或借用“默契协同”“不即不离”“创造性遵从主义”等概念,对编辑部场域中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复杂现实和张力特征进行厚重描述和理论阐释。芮必峰则通过对政府、市场、媒体在我国新闻生产中相互之间“社会权力”关系的考量,试图打破学术界对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媒体与政府“要么对抗、要么合谋”的二元描绘,代之以“冲突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冲突”的阐释框架,以此来解释新闻生产的“体制内空间”之所以“被一次次构筑,又一次次被打破”的现实缘由。[47]在关于中国媒体新闻生产的系列研究中,从业者和媒体机构的自主性始终是研究焦点。陆晔、俞卫东对上海新闻从业者的系列调查,把新闻生产这一社会过程和其中的权力实践形态,具体化为新闻编辑部内部的专业社区控制因素、新闻机构外部和内部对新闻生产各个环节的影响因素,将转型社会的背景嵌入新闻生产中考察新闻业的自主性状况。[48]杨银娟与李金铨就中国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边界问题,提出“议价”(bargaining)概念,认为媒体与报道对象的权力距离、空间距离、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媒体领导人的趋向和媒体报道议题对政治合法性威胁程度等因素,决定了媒体的议价能力。[49]张志安对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进行“事件–过程”个案研究,提出在中国转型社会的语境中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具有自我控制内化和边缘突破的双重内涵。[50]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越轨社会学、集体记忆、新闻叙事学、文化社会学等不同视角拓宽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李小勤发现,当“传媒越轨”问题被放在一个“意识形态发生松动的非民主社会中”,新闻从业者及其修辞被作为传媒越轨的合法化工具,将“隐蔽的文本”渗透进入“公共话语”中。[51]李红涛、黄顺铭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的研究,将中国媒体置于文化、政治、技术和社会的场景中进行考察,试图厘清媒体记忆研究领域的边界。[52]张志安、甘晨研究大陆新闻界关于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发现,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媒体对此事件有着不同的记忆诉求、动机和叙事策略,由于体制、定位及价值等差异因素的存在,真正具有“共同体”特征的新闻阐释社群尚未形成。[53]
三、局外人:国家话语中的多维视野研究
海外华人学者中的不少人先在大陆或港台接受新闻传播学或相关学科教育,又前往欧美国家深造并留在海外任教,他们在国际学术场域中浸淫多年,熟练掌握了西方传播学研究方法和问题视野。对这批华人传播学者在大陆新闻研究中的贡献,吴飞曾给予高度评价:“由他们主导的几套新闻传播方面的译丛,奠定了大陆新闻传播学子的阅读基础文献。他们所带入的研究话题,对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4](一)跳出“媒体中心论”:将“国家”纳入批评话语
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新闻体制变革性质及发展趋势的界定和评价,具有较为一致的学术实践特征,多是将“国家”纳入批评话语进行研究,对“国家与新闻业”的关系多有比喻式描述和概念化阐释。譬如用“鸟笼”来比喻新闻自由的受限[55],以及总结出“模糊与矛盾”[56]、“未独立的商业化”[57]、“即兴的改革实践” [58]、“谁出钱谁做主” [59]、“没有保证的专业化” [60]、“国家–市场复合体” [61],“党的逻辑与市场逻辑的混合” [62]、“一个脑袋多张嘴巴” [63]、“不一律的自由化” [64]、“权力与市场的‘拔河比赛’” [65]等概念。在这些描述中,国家要么被建构为控制新闻业的“施动者”,要么被看作与“市场”的“共谋者”和“联盟者”。在这两种解读视角所搭建的“国家–市场–媒体”分析框架中,不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思辨研究,国家始终是一个被警惕和被质疑的解释变量。
李金铨、何舟对中国媒体系统在“国家–市场–媒体”分析框架中的位置作了总体概括,[66]认为在1992年之后的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开始迈向由执政党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媒体作为“政党的股份公司”,同时拥有着社会主义的面容和资本主义的躯体。[67]不过,将国家纳入批评话语并不意味着华人学者对“国家与新闻业”关系的全面批判。权威政体下的市场也许不具备充分的解放力量,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媒体的自主性,初期的商业化过程更是拉近了媒体与社会的关系。
主流媒体理论继续重申“喉舌论”和限制对“社会公器论”的倡导这一现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媒体特别是市场化媒体在呈现和构建新的统治性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68]中国媒体本身逐渐开始以一种市场导向的机构来建构身份认同,形成自身的利益诉求。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环境下的中国媒体,其混沌不清、变动不居的“面孔”背后,作为意识形态、经济产业及公共意见的平台,媒体正深刻地卷入了中国改革这一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市场内生发的集团或阶级利益等相互博弈、协调的政治过程。[69](二)国家与新闻业:竞争、共谋、还是侍从?
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媒体场域的研究兴趣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给“国家控制与市场化”的关系定调,所谓定调是指将“国家”纳入批评话语,并以此为框架或者前提对媒体组织与新闻生产进行中观与微观的经验研究,分析、阐释中国媒体体制变革的特殊性,从多种角度对“国家与新闻业”这个核心命题进行概念化描述。二是注重从“国家–市场–媒体”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变迁与媒体转型。尽管中国媒体格局中,政党(国家)与市场的整合远未达到稳定状态,运用这一分析框架也必然牵扯到对媒体变迁与社会转型相互影响等问题的考量。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海外华人学者对“国家–社会–媒体”分析框架的演绎是从属于“国家–市场–媒体”分析框架的,他们较少单独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少数相关研究也多集中于媒体化抗争。这或许是因为由执政党掌控的市场化改革“在突出‘经济’与‘国家’的同时,很少给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留有余地”,国家社会主义对社会活力的限制没有给学者们提供足够重要的研究问题或经验材料。
1.媒体集团化与国家资本主义
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媒体的集团化(conglomeration)趋势,成为众多华人学者探讨“国家与新闻业”关系的新切入点。在结构形态方面,媒体集团化是通过“双层级(two tiers)的管理体制”建立起来的,[70]第一层强调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坚持既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第二层强调一种“软性”的出版政策,为民众提供有利于增强人际和谐、提高人民知识水平的娱乐内容与新闻信息。基于此,华人学者对中国媒体集团化的学术实践基本是将“权力的逻辑”与“金钱的逻辑”这两层并置,将“国家与新闻业”的关系具体化为“媒体集团化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
海外华人学者对媒体集团化性质的界定趋于一致,即权威政体下的“权钱共谋”,同时,将媒体集团化视为东欧剧变之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表征。有研究对中国的媒体集团化进行概念化描述,[71]认为后贸易组织时代的中国媒体,从社会主义市场模式(market socialism model),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公司模式(state-controlled capitalist corporation model),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媒体,是一个拥有社会主义面容(a socialist face)的资本实体(a capitalist body)。还有研究进一步将“媒体集团化”的出现解释为一种新机制(neo-mechanism),[72]不过对这一新机制的阐释视角有所不同——赵月枝将其视为新的控制机制,李金铨等“从外向内看”、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一种新的防御机制。
尽管海外华人学者对作为“新机制”的媒体集团化存在阐释差异,他们的论述却都在强调,由国家主导的媒体结构转型所遵循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路径。在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中,“国家–媒体–市场”的分析框架被重新解读,在“党管媒体”的刚性政治前提下,“市场”不是一个中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而是“国家”用以实现“媒体和市场”双重控制的手段。市场机制的引入对于执政党来说不只是挑战、更多是机遇,是既可以掌控媒体又可以积聚资本的方式。由此,新闻体制改革所造就的“国家与新闻业”之间的那种张力关系,在媒体集团化的表述中不复存在。
2.对媒体组织、新闻生产的复杂解读
无论是将国家纳入批评话语还是对媒体集团化的解读,都是海外华人学者对1992年以来中国新闻体制变革态势的整体观察,属于一种轮廓性的概述。此外,他们对特定媒体的个案分析、不同地区媒体生态格局的比较研究、新闻生产的范式竞争与叙事话语分析、职业社群的行动模式、话语实践研究等,也同样做出了富有贡献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从中观和微观视角切入,搁置宏观的批判论述框架,对媒体组织、新闻生产以及职业社群的“非常规”(unregulated)表现展开研究,揭示中国新闻体制变革在不同层面的复杂特征。他们得出了一个与宏观论述互为补充的结论:中国的媒体变迁轨迹不仅是一个国家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过程,还是一个多种群体充满张力和斗争的过程,而且它始终还是一个方向未知的过程。
(1)对中国媒体变迁轨迹的多元解读
中国的新闻体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发生?这是海外华人学者在考察中国媒体变迁轨迹时聚焦的问题。潘忠党将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式:[73]一种观点认为,体制转变是一个“和平演进”的过程。这类观点的论述中,陈怀林认为中国的媒体体制改革遵循既有方向,媒体制度创新首先发生在财经制度层面,然后带动编采运作制度的变化,最后触及宏观管理制度。[74]另一种观点认为,体制转变是一个“转轨”的过程。这是不少大陆学者所持有的观点,前文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作赘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体制转变是一个行为主体与现存体制互动的改造过程。这类观点的论述中,潘忠党通过对“体制改造”“临场发挥”“空间重构”“补偿网络”“象征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一系列概念的提炼,[75]将改革实践从理论上阐释为一种新闻体制改造的动态过程。
不难发现,上述三种不同理论模式的复杂性是递增的,从“既定方向”到“制度(institution)变革”再到“体制(mechanism)改造”,在这个不断深化阐释的过程中,国家、媒体组织与新闻记者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地位被不断凸显,新闻体制变革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非常规性以及不可预测性的具体特征得以揭示。
(2)以地区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呈现中国媒体的复杂生态格局
李金铨、何舟、黄煜[76]在对上海媒体系统进行田野考察时,提出“国家–市场统合主义”(party-market corporatism),认为媒体体系与政治经济环境的互动,经由“市场”这一中介变量表现为“国家与媒体”的融合,两者在共谋的基础上不乏冲突。相比之下,北京的媒体生态因为具备相当异质性的权力基础,使得媒体系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管理”(managed diversity)模式。而广州的媒体系统则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激烈的媒体竞争与角色分化,为考察中国媒体系统与政经系统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博弈视角”(contending perspectives)。
此外,海外学者Kevin Latham[77]对广州媒体系统与西方主流媒体的比较研究,考察了真实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在两种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重要差别,借此消解南方系在中国媒体场域里的特殊性。其研究认为,碎片化社会与多元主体的历史变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新秩序的出现与旧秩序的式微。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政治与话语叙事通过中国的媒体系统,以“消费主义与个人责任的新修辞方式”形塑多元社会的观感。
(3)基于特定媒体组织对新闻生产张力特征的概念化描述。
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方面,潘忠党的系列论述获得较多关注。他认为,中国媒体系统遵循着一种非线性发展路径,其方向由新旧两股力量共同决定。一方面,“过去”常被用来为“现在”的合法化提供话语支撑(the past is used to legitimize present);另一方面,“现在”也常被用来合法化或者美化“过去”。[78]在对《南方周末》与《新民晚报》的比较研究中,他认为“执政党–新闻业范式”(party-journalism paradigm)和“专业主义范式”(professional paradigm)是大陆新闻业中并存的两大新闻生产范式,尽管它们的发展轨迹迥然相异,却都各自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79]通过对新闻编辑部的深入研究,他发现,[80]在新闻体制改革与政治、经济控制的双重环境下,市场化媒体善于利用既存新闻机构中的内在张力与新闻专业主义话语,通过即兴策略与创新实践,重构媒体系统的制度空间(reconfigure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of the party press system),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心–边缘”(center versus periphery)与“前台–后台”(front-back versus region)的媒体生态。
此外,一项针对《南方周末》的研究发现,[81]其调查性报道脱胎于官方倡导的“舆论监督”(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该报借用这种原本是政府利用媒体施行政治与社会控制的行政机制(administrative mechanism),施展进行的新闻生产实践“异地监督”(extra-regional media supervision),却在动态地再协商与再定义着“国家–媒体”的关系(dynamic renegotiation and redefinition of state-press relations)。
(4)媒介与社会:关系“紧密”还是“脆弱”联盟
关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多以“国家–社会–媒介”为分析框架,以国内、国际的横向比较视角切入,探讨当代中国的媒介体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描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体语境中媒介与社会的一种“奇妙的”紧密关系。
林芬、赵鼎新对中国媒介与社会运动独特关系的考察,[82]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发现在霸权文化缺失的转型社会,中国记者比其他同行更愿意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并且更有激情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实现作出努力。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往往被建构成一种在威权政体中的“脆弱”联盟,在看似平等互利的关系背后,是媒介组织被迫倚靠“公民社会”的变量来建构自己在新闻生产与经营中的自主性。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系统在遏制社会冲突,防止不同社会抗争势力的融合以及阻碍其他可能的政治替代选择出现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传播以及精英和大众话语之间的不同链接动态在促进和阻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83]同样,在“国家–社会–媒介”的分析框架中,因为“国家–媒介”关系的阐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媒介”关系的判断,由此可见,在“国家–社会”这一通常被认为是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中,加入“社会”这一解释变量,原来的分析框架其二元结构的阐释偏见便得到了消解,因为国家与媒介的关系,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些表面上二元对立的命题,可以得到不尽相同的多元解读。
有研究指出,后邓小平时代,政治及媒介环境的一系列变迁,也使得那种“两头讨好”的“看门狗式”的新闻业(watchdog journalism)在中国开始了制度化的尝试。这种类型的新闻业通过理顺中国社会改革的模糊边缘,界定威权化市场社会中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边界,来加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霸权。[84]调查新闻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新闻实践,同时发挥“监督官僚”的工具性作用,强化执政党之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掌控与意识形态霸权,这是后邓小平时代,中国调查新闻业所处的共同语境与社会意涵。
(三)理论遗产亟待反思,新的理论框架尚未确立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外华人学者开始聚焦变革中的中国媒介系统,多数研究者的旨趣基本在于揭示后毛泽东时代(post-Mao)中国新闻业的巨大变迁[85](Chang、Chen and Zhang,1993;Huang,1994;Lee,1994、2000;Zhao,1998)。近年来,他们对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的描述和阐释已经比较深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研究居多,政治经济学分析也不在少数。
不过,有关中国媒介的个案研究很少对既有的两个宏观理论框架,即“施拉姆的苏联传媒理论”(Schramm’s Soviet thoery)以及“阿特休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Altschull Marxist approach)提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与修补。[86]前者的理论观点不仅忽略了“即使是处于自由主义及社会责任理论描绘中的新闻媒介,也有被资本(private capital)而不是国家(state)‘工具化’(instrumentalized)的可能”。[87]而且,在逻辑表述方面,施拉姆的模型近乎没有给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媒介同样存在积极的社会功能留下阐释空间。相比之下,后者的理论框架更具意识形态中立性(ideologically neutral),作为一种辩证研究路径,阿特休尔的模型将中国描述为“全世界最大的以市场为导向(market-oriented)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时代的发展中国家(advancing state)”。但阿氏的研究路径同样没有给我们理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比如中国、古巴、朝鲜)的媒介系统提供具有操作意义的参考。[88]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传播研究所面对的“双重理论遗产”:[89]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这是大陆学者进行新闻传播理论建构的两大依归。前者在中国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权力概念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在分析新闻传播现象的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90]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历过“文革”一代的大陆学者,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有意回避,希图借此获得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后者所建构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构”的理论框架已经趋于僵化,在突出“经济”与“国家”的同时,轻视了国家与社会、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市场–媒介”的关系框架,在大陆学者的媒介研究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尽管是受到限制的演绎),但同时,因为缺少替代性的理论资源(中国媒介研究中运用重视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框架开展理论思辨的文献凤毛麟角),这是造成“国家–社会–媒介”的关系框架研究举步不前的原因之一。
诚然,上述的几个理论遗产可以在不同国家媒介系统的比较分析中提供一种宏观意义上的基本类型(basic types)。但就特定语境下的、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中国媒介体系来说,这几个理论遗产亟待反思。作为局外人的华人及海外学者,因为缺少直接的环境体验及经验资料,容易产生具有价值偏差的反省与阐释,虽能“上天”却未能“入地”;而作为局内人的大陆学者,虽然以经验和观察见长,但囿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对理论资源的运用、对关系框架的演绎也未必充分。仅就中国媒介研究这一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而言,新的理论框架尚未确立,但华人及海外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领域的经验考察,或许可为新理论框架的确立奠定基础。
如上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华人以及海外学者主要就一个焦点命题开展学术研究,这个命题或许可以表述为:聚焦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市场因素的介入是否减弱了国家对媒介的政治控制以及是否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媒介自由?换句话说,市场是不是仅仅作为国家的“利益代理人”(profit-driven agent)而存在,商品化给中国媒介系统所带来的现代性变迁是否会促进传媒内容的多样化?围绕这个核心命题,华人及海外媒介学者的阐释实践主要就两个方面的范畴展开,一是对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一系列重大变迁的描述,二是对媒介系统中的权力控制问题热切关注,两个范畴的研究是在“旧”与“新”的对比论述中建立起来的。
有研究者Betty Houchin Winfield and Zengjun Peng对这两个方面的范畴进行概括和列举[91]:首先,一系列重要变迁主要反映在8个面向上,分别是:媒介所有权、财政支持、管理层与编辑人员的设置、媒介功能、新闻生产的性质、传媒结构、新闻记者以及传媒内容。其次,国家对中国媒介系统的掌控主要体现在5个面向上,分别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经济控制、机构控制、法律控制以及行政控制。新的理论框架,其核心任务在于对上述的两类范畴、13个面向进行具有解释力度的整合,以此对动态变化中的中国媒介系统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分析和阐释。
结论与探讨
我们认为,“国家–社会–媒体”与“国家–市场–媒体”的分析框架并非研究中国媒体的理想模型,四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应该被某个分析模型所遮蔽。国家可以引入市场和社会关系重构自己,而市场和社会不可能脱离国家而孤立存在,国家和市场以及社会力量都有既能限制也能赋予社会表达的双重功效,[92]两者相互建构且彼此并不隔膜排斥。[93]所以,“国家–市场”和“国家–社会”不应被简单解读为不同分析范畴之间的二元对立,市场与社会应该被作为一组中介变量来看待,即便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两者与国家的关系也不必然具备价值倾向性。
从研究现状来看,大陆学者更倾向于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描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他们对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构建不是宏观层面的,而是立足中观和微观的学术场域,通过建构一系列具体的二元对立组合来暗示国家与市场的基本冲突与矛盾。他们在两者的张力关系中为中国媒体建构自主性的空间,对“市场”的解放力量寄予厚望,审慎运用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描述和分析着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实践,从媒体组织、新闻生产以及职业社群等不同层面的研究对象着眼,去阐释和论述中国媒体的复杂现实和多元意义。身处中国媒体场域内,大陆学者多从媒体中心视角来考察,容易有意无意地回避或简化“国家–社会–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同时,大陆学者在“有限疏离”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对媒体自主性建构所做的学术努力却值得肯定。他们对“媒体公共空间”的论辩和呼吁,对职业社群和新闻生产特征的探察和揭示,都为我们理解中国媒体生态及其变化逻辑提供了生动描述和细微阐释。
“置身彼处”(being there)的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媒体研究的学术贡献亦有目共睹。一方面,华人学者在其求学初期曾根植于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媒体体制变革有其自身经验,熟悉媒体研究的“中国问题”,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进程对中国媒体变迁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上“局内人”的体验;另一方面,作为从外向内看的“局外人”,他们至少具备两方面优势:首先,身处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国际学术圈,其学术研究更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对中国媒体所处的权力场域从国际话语层面进行批判性研究;其次,接受过欧美主流传播学的规范训练,具备研究中国媒体的问题视野、研究方法和理论阐释更加符合国际学术规范。
在本文所概括的两个分析框架中,海外华人学者对“国家–市场–媒体”以及“国家–社会–媒体”的阐释更加充分,对中国媒体体制变革的特征分析更加偏向批判政治传播经济学取向,对相关描述概念的提炼或理论模型的运用也更为注重。不过,华人学者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及研究框架大多来自西方媒体研究体系,所以他们也容易“以西方的体制作为考察我国新闻改革的自然参照物,无意之间将‘参照物’变为研究的起点或行动的终点”。[94]他们对中国媒体体系的关注比较容易陷入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路径依赖,始终聚焦“国家与新闻业”的权力实践过程,容易产生学术价值取向上的结构性偏差。
回到知识生产的维度来看,大陆学者更多在特征描述基础上进行现象阐释,海外华人则更多试图在现象阐释、概念提炼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总体上,关于中国媒体的研究更多还是停留于描述层面的“地方性知识”,真正具有持续性、广泛性的理论模型和阐释性理论依旧不足。如何立足社会转型的语境尤其是互联网重构新闻业的语境中考察媒体的话语建构、专业实践和生态变迁,也许是未来可期的重点突破方向。■
①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文化研究》总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③约翰·杜翰姆·彼得斯著:《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④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额理解与误解之反思》,参见简宁斯·布莱恩特(主编):《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⑤李金铨:《超越西方: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刊于附录
⑥参见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995年(春季号)
⑧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4月,总第71期
⑨黄月琴:《象征资源“褶皱“与”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7期
⑩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11]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4月,总第71期
[12]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13]黄月琴:《象征资源“褶皱“与”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7期
[14]陈阳:《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两种表现形态之比较——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为个案》,《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15]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之建构》,《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16]李艳红:《“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关于当前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5日第三版
[17]陆晔、潘忠党:《重提新闻专业主义》,来源: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16年5月10日
[18]WangHaiyan. (2016).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From journalists to activists.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19]Betty Houchin Winfield and Zengjun Peng(2005):Market or Party Control?Chinese Media in Transition.Gazette Vol 67(3):255-270.
[20]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995年(春季号)
[21]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3次跨越》,《新闻界》1998年第6期
[22]李良荣:《从单元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23]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传媒观察》2010年第1期
[24]李良荣、戴苏苏:《新闻改革30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
[25]潘忠党、吴飞:《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26]潘忠党、吴飞:《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27]潘忠党、吴飞:《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28]周翼虎:《自由的抗争与自觉的入笼:国家与新闻业关系30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未出版)2008年6月
[29]芮必峰:《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宣传通知”及其执行情况为例》,《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
[30]陆晔、周睿鸣:《“液化”的共同体:新传播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反思——以澎湃“东方之星”长江沉船报道为个案》,《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5)》论文集
[31]王海燕:《记者的另类诠释社群:对一个组织外新闻空间的民族志研究》,《传播,文化与政治》(台湾),2015年第2期
[32]丁方舟:《“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33]赵云泽、滕沐颖、杨启鹏、解迪迦:《记者职业地位的陨落:“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2期
[34]郭忠实、陆晔:《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35]潘忠党、吴飞:《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36]潘忠党、吴飞:《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37]孙玮:《媒介话语空间的重构: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媒介话语的三十年演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38]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总第2期
[39]陆晔、俞卫东:《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人职业状况——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03年第1期;陆晔:《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兼论舆论监督的记者主体作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3月第22卷第2期
[40]陈阳:《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轨迹——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2期
[41]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大学》2012年第4期;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及影响因素》,《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月第13卷第2期
[42]白红义:《奋不顾身的“哀愁”——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研究》,《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
[43]曾繁旭、黄广生:《地方媒介体系:一种都市抗争的政治资源》,《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总第24期
[44]黄月琴:《社会运动中的承认政治与话语秩序:对厦门“散布”事件的媒介文本解读》,《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年总第20期
[45]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2001)》,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46]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2006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中外媒介研究》2008年第1期
[47]芮必峰:《政府、媒体、市场及其他——试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2009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48]同引于上文陆晔、俞卫东的文献
[49]杨银娟、李金铨:《媒体与国家议价研究:中国大陆广州报业的个案》,《传播与社会学刊》2010年总第14期
[50]张志安:《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研究——以“毒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5期
[51]李小勤:《传媒越轨的替代性分析框架:以〈南方周末〉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总第2期
[52]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53]张志安、甘晨:《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54]吴飞:《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55]ChenH.L. and Chan,J.(1998): Bird-caged freedom in China. In J. Cheng.(Ed)China in the Post-deng era(pp.645-667). Hongkong: Chinese Univercity Press.
[56]Lee,C.C(1994):Ambigu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ssues in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C.Lee(Ed),China’s media , Media’s China(pp3-20).Boulder,CO:Westview Press.
[57]ChanJ.(1993):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Trends and tensions of media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J. Cheng and M. Brosseau(Eds)China review 1993(pp.25.1-25.21). Hongkong: Chinese Univercity Press.
[58]Zhongdang Pan(2000):Spatial configuration in institutional change:A case of China’s journalism reforms. Journalism Vol.1(3):253-281.
[59]ChanJ.(1995):Calling the tune without playing the piper:The reassertion of media controls in China In C.K.LoS.Pepperand K.Y.Tsui(Eds)China review1995(pp5.1-5.16).Hongkong: Chinese Univercity Press.
[60]YuX.(1994):professionalization without guarantees:Changes in the Chinese in the post-1989 years. Gazette53(1-2)23-41.
[61]MaE. K. W. (2000):Rethinking media studies: The case of China. In J. Curran, & P. M. Jin(Eds.)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pp. 21–34). New York. Routledge.
[62]ZhaoY. Z. (1998):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63]WuG. G. (2000): One head, many mouths: Diversifying press structures inreform China. In C. C. Lee (Ed.)Moneypower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45–67). Evanston,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64]HeZ.& Chen, H. L. (1998):A new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dia (in Chinese). Hong Kong: Pacific Century Press.
[65]HeZ. (2000):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of-war: A political–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In C. C. Lee (Ed.)Power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China (pp. 112–151).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66]Chin-Chuan LeeZhou He,Yu Huang(2006):‘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2006 Vol 28(4):581-602.
[67]HeZ. (2000):‘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pp. 112–51 in C.-C. Lee (ed.) PowerMoney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68]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总第2期
[69]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文化研究》总第7期
[70]Chin-Chuan LeeZhou He,Yu Huang(2006):‘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2006 Vol 28(4):581-602.
[71]Chengju Huang(2007):Trace the Stones in Crossing the River: Media Structural Changes in Post-WTO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07 Vol.69(5):413-430.
[72]Chin-Chuan LeeZhou He,Yu Huang(2006):‘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2006 Vol 28(4):581-602; Yuzhi Zhao(2001):Media and Elusive Democracy in China. 21 The Public Vol.8(2001),4,21-44.
[73]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74]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案例》,《新闻学研究》2000年总第62期
[75]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76]Chin-Chuan Lee,Zhou He and Yu Huang(2007):Party-Market Corporatism,Clientelism,and Media in Shanghai. Press/Politics 12(3):21-42.
[77]Kevin Latham(2007):Nothing but Truth:News Media,Power and Hegemony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3.(Sep.,2000),pp.633-654.
[78]Zhongdang Pan(2000):Spatial configuration in institutional change:A case of China’s journalism reforms. Journalism Vol.1(3):253-281,2000.
[79]Zhongdang Pan(2003):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30 No.6 December 2003 649-682.
[80]Pan, Z.& Lu, Y. (2003):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 C. Lee (Ed.)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 (pp. 215-236). London: Routledge.
[81]CHO Li-Fung(2007):The EmergenceInfluence and Limitations of Watchdog Journalism in Post-1992 China: 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Weeken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April 2007
[82]林芬、赵鼎新:《霸权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83]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总第2期
[84]Yuzhi Zhao(2001):Media and Elusive Democracy in China. 21 The Public Vol.8(2001),4,21-44.
[85]ChanJ.M. (1993) ‘Commercialis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 Trends and Tensions of Media Development in China’pp. 25.1–25.21 in J.Y.S. Cheng and M. Brosseau (eds) China Review .1993.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Lee, C.C.(2000)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Journalism Studies .1(4): 559–75;ZhaoY.Z. (2003) ‘Transnational Capitalthe Chinese Stateand China’s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in a Fractured Society’Javnost–The Public 10(4): 53–74;Huang, C.J.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Semi-Independent Press in Post-Mao China’Journalism Studies 1(4): 649–64.
[86]Chengju Huang(2007):Traditional Media VS Normative Theories: Schramm,Altschull,and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eptember 2003pp444-459.
[87]NeroneJ. C. (Ed.). (1995). 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88]Hachten, W. A. (1999). The world news prism: Changing mediaclashing ideologies (5th ed.).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89]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总第2期
[90]McChesney, R. W.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Culture & Society22109–116.
[91]Betty Houchin Winfield and Zengjun Peng(2005):Market or Party Control?Chinese Media in Transition. Gazette Vol 67(3):255-270.
[92]CurranJ. (2002). Media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93]BeesonM.& RobisonR. (2000). Introduction: Interpreting the crisis. In RobisonR.Beeson, M.Jayasuriya, K.& KimH. R. (eds.)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crisis (pp. 3–24). London: Routledge.
[94]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张志安 束开荣/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束开荣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为2016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编号16JZD006)系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