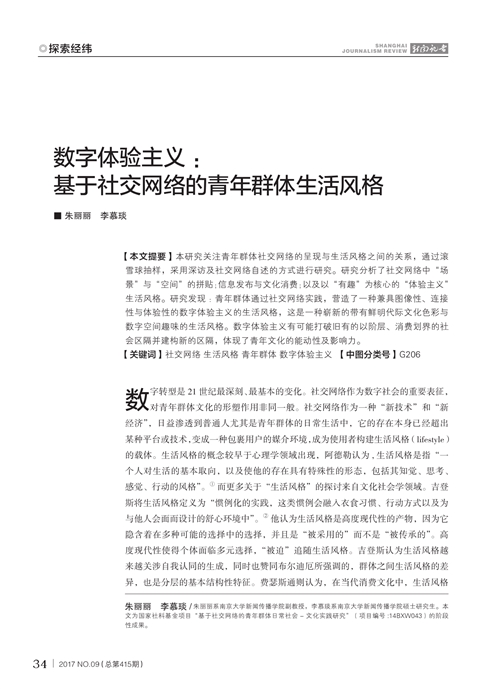数字体验主义:基于社交网络的青年群体生活风格
■朱丽丽 李慕琰
【本文提要】本研究关注青年群体社交网络的呈现与生活风格之间的关系,通过滚雪球抽样,采用深访及社交网络自述的方式进行研究。研究分析了社交网络中“场景”与“空间”的拼贴;信息发布与文化消费;以及以“有趣”为核心的“体验主义”生活风格。研究发现:青年群体通过社交网络实践,营造了一种兼具图像性、连接性与体验性的数字体验主义的生活风格,这是一种崭新的带有鲜明代际文化色彩与数字空间趣味的生活风格。数字体验主义有可能打破旧有的以阶层、消费划界的社会区隔并建构新的区隔,体现了青年文化的能动性及影响力。
【关键词】社交网络 生活风格 青年群体 数字体验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数字转型是21世纪最深刻、最基本的变化。社交网络作为数字社会的重要表征,对青年群体文化的形塑作用非同一般。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和“新经济”,日益渗透到普通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它的存在本身已经超出某种平台或技术,变成一种包裹用户的媒介环境,成为使用者构建生活风格(lifestyle)的载体。生活风格的概念较早于心理学领域出现,阿德勒认为生活风格是指“一个人对生活的基本取向,以及使他的存在具有特殊性的形态,包括其知觉、思考、感觉、行动的风格”。①而更多关于“生活风格”的探讨来自文化社会学领域。吉登斯将生活风格定义为“惯例化的实践,这类惯例会融入衣食习惯、行动方式以及为与他人会面而设计的舒心环境中”。②他认为生活风格是高度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它隐含着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的选择,并且是“被采用的”而不是“被传承的”。高度现代性使得个体面临多元选择,“被迫”追随生活风格。吉登斯认为生活风格越来越关涉自我认同的生成,同时也赞同布尔迪厄所强调的,群体之间生活风格的差异,也是分层的基本结构性特征。费瑟斯通则认为,在当代消费文化中,生活风格蕴含了个性、自我表达及风格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的身体、服饰、谈吐、闲暇时间的安排、饮食的偏好、家居、汽车、假日的选择等,都是品味个性与风格的认知指标”。③
布尔迪厄将“生活风格”与“惯习”“品位”联系起来,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术阐释路径之一。他认为生活风格是在“惯习”(habitus)中形成的。“惯习”是指“阶级条件和阶级条件施加的影响的内在化形式”,不同的生活条件产生不同的惯习,惯习由生产实践、作品和区分评价实践、作品两种能力构成,最终所形成的可分类的实践系统就是生活风格。生活风格是“特殊偏好的统一整体”,这些偏好通过“象征亚种”如家具、服装、语言或身体素养的特定逻辑来表达意图。他引用莱布尼茨的观点,认为生活风格的每个维度都和其他维度一起发挥象征作用,构成一个“搭配协调的属性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原则正是品味,品味是“生活风格之根源的发生公式”。④
在当下语境中,社交网络正在成为一种生活风格的“象征亚种”,生产和建构着新的区隔。本文沿着吉登斯、布尔迪厄等人的路径,选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社交网络使用和生活风格的关系。青年群体是否/如何通过社交网络构建他们的生活风格?现实的生活风格和线上展演是否一致?社交网络的特性如何影响品位和生活风格的形塑?本文选用的主要的理论视角是“体验主义”(experientialism)。德国学者舒尔茨提出了“体验社会”(Die Erlebnisgesellschaft,又译“经验社会”)的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远远超过贝克的“风险社会”,对现代社会做出了更为准确的时代性诊断。随着生存和经济压力的缓解,对个体而言不断面临着各种行为抉择,“对持续涌现的抉择处境,最终被视为准则的只能是个体自身以品位感触形式所体验到的倾向或偏好。随着关注点转向自身,内心体验就成为个体行为的基准点。由此导致过去时代的经济人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体验主体:对其而言,理性行为计划的目的不再是外在成功的实现,而是内在体验的提高。其生活理念由求生转为追求存在美学。其自我关系最终表现为对自身体验的持续观察。” ⑤韦尔施发现当代社会生活有“表层的审美化”趋势,体现在“装饰”“活力”和“体验”三方面,表层的审美化把现实世界变为“体验的世界”,旨在追求消费社会中的快乐主义。⑥社交网络强化并加速了“体验主义”世界的到来。本文认为,社交网络呈现的生活风格是一种数字生活风格,是经由媒介中介的数字“体验主义”,并尝试对其内容、风格及特质进行一定的描述及解读。
本研究采用质化方法进行研究。主要通过深访、社交网络自述和焦点小组的方法。本研究的对象是18-35岁的青年群体,包括在校学生、青年白领和蓝领。在地域、性别、年龄、职业,尤其是社会阶层等人口学特征上,尽量选取差异化样本进行收集。青年群体中的大部分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或刚刚进入工作初期,阶层和品位系统尚未固定,因而展现出动态的形塑过程可供研究,加上这一群体是社交网络使用者中的主力军,较之其他群体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寻找了15位研究对象进行深访,深访对象资料见(表1 表1见本期第36页)。
研究对象的年龄介于20-25岁之间,男女各半,教育程度绝大多数偏高,属于青年中产或准中产,但也有部分蓝领。他们的社交网络平台大多是微信、QQ、微博、人人等平台,也有快手等乡村用户偏多的平台,他们的社交网络发布的频率从低到高不等。总的来说,本研究的对象尽可能希望做到差异化,但总体比较偏向青年白领阶层,这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研究的推广性。研究参照了马杰伟在《时尚志》中采用的“图片自述”方法,⑦请受访者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条社交网络发布的内容,请他们进行社交网络自述。此外,考虑到一些受访者可能较少有跨阶层交往的经验,研究也使用了若干焦点小组访谈,邀请他们对其他组受访者的社交网络进行观看和评论。
一、场景与空间:“拼贴”的生活风格
德塞托认为,人们的空间行动会构成一种“道路修辞”,与组织语句的艺术类似,它是一种使路线转向的艺术,这种艺术还包含并组合了不同的风格和用法。“风格将‘一种在象征意义上展现个人生活方式的语言学结构’具体化;用法决定了使交流体系得以确实展现的社会现象;它与某种标准有关。风格和用法两者都指向一种‘行动的方式’”。⑧社交网络中的场景以及场景的表达方式组合成人们的“道路修辞”和空间行动的风格,也即是构成生活风格的元素之一,远离日常、出行频繁指向充实忙碌的、丰富的生活风格,获得较高的品位赞同。
社交网络通过移动设备的定位技术,提供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让人们在发布社交网络时能够标记地理位置信息。这意味着,社交网络的内容隐含着场景和位置的信息。人们在何时会倾向于标记定位信息?受访者HX观察到,社交网络中的好友会在“不一样的地方、在独特的地方”选择标记定位,“比如在台湾,或者在机场,很多人在机场,还有一些人在国外比较多”。梅洛-庞蒂把“几何空间”和“空间性”做了区分,他把后者称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空间性带有一种关于外部的经验,“是关于我们生命的基本结构,而我们的生命处于与某个环境一定的关系之中”。这是一种带有知觉的空间:“我游览巴黎时得到的每一个鲜明知觉——咖啡馆,人的脸,码头边的杨树,塞纳河的弯道——同样也清楚地出现在巴黎的整个存在中,都表明巴黎的某种风格或某种意义”。⑨“机场”则是一个典型带有“知觉”的空间所在,作为出行必经的地点,并且是各类交通工具中价格最昂贵、去往距离最远的一种,“类似于(表达)他要去玩了,或是工作等等,意思是他想展示他的生活很充实,很高大上”(HX,编号02)。
HX回顾自己使用社交网络的几年过程,发现定位的“等级是在不断地提升的”,“刚开始可能大家觉得去上海高铁站就标记一下,后来有更高逼格的人出现了,人家都飞美国或者飞去日本飞去欧洲,再不济飞去台湾会标记,大家都这样秀,我再秀一个这个(上海)会不会很村?”另一位受访者MYW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她的经验中,位置信息不仅仅限于出行或游玩:“大家都在十一出去玩儿,我十一怎么过的我忘了,好像在宿舍没有出去,也没有好意思发(朋友圈)。我保研(免试录取硕士研究生)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在晒自己出国(留学),我本来想说要保研,后来这件事没有发朋友圈,好拿不出手。”社交网络中的位置信息在他们心中已经存在默认的品位高下之分,出国游玩或留学占据较高的品位等级,MYW认为这是由于“出国”隐含了多重信息: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较高的英语水平,以及丰富的生活经历。她说:“我也想出国,但是我们家可能是那种经济条件不够……这是一个隐含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很厉害,英语很好。他们出国不单单学习还可以看更多的东西,看更多的风景,晒更多的东西,那样觉得更棒,虽然知道他们出去很苦,但是感官上面应该很棒的。”
除了公开标记的定位信息以外,很多时候,用户并不公开定位,但是他们所公开发表的内容仍然会隐含着场景或空间叙述。受访者LYF分享了一则网络红人写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提供了“在网路上塑造高端形象”的五十个建议(用台译词“网路”代替“网络”即是其一),其中包括“旅游不要定位,出国更不可以定位,高级炫耀只存在风中”。⑩LYF认为,这篇文章以讽刺的态度调侃了出游定位的炫耀心理,他使用社交网络时,也会尽量避免故意打开定位信息。LYF上一次在社交网络中主动公开的场景是深圳市政府,原因是他认为去深圳游玩并不稀奇,但是“觉得去市政府的机会比较少吧”,因此特意发朋友圈叙述了这一日常生活不大常见的场景。
伯明翰学派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概念,认为风格是一个“拼贴”(bricolage)的过程:在一套完整的意义系统之内,对一些物品或符号进行重组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以此来传播意义。这一风格概念的重点在于,人们利用了一套物品和意义,最终被制造出的风格,“它特有的象征性对一个完整的组合系统里的所有元素一起进行的整编,体现着和表达着这一群体的自我意识”。[11]社交网络是日常生活中的碎片时间的组接,使用者利用其碎片化呈现的特性,发布有品位的内容,用有格调的书写方式,拼贴出自己的生活风格。碎片化的筛选后,产生了连贯性的形象,青年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品位标准,生成一套个体化的使用策略。比起现实生活的风格生成,线上生活风格的拼贴是更为简易的方式,能够弥补人们现实自我和生活方式的遗憾。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社交网络寄托了这样的厚望,笔者在访谈中发现,每个个体对于社交网络式生活风格的自觉意识是不同的。例如XLP和GMT两位受访者,都无意在社交网络中营造自己的形象或风格,大量发布了被其他受访者视为低品位的内容,并且不以为意,“想发的时候就发,没想那么多”。同样不愿构建线上风格的DMX尽力在社交网络中隐藏自己,接受访谈时她全部的微信朋友圈不超过五条,其中一条是“没有屏蔽任何人,我只是不发朋友圈”的声明,最近她彻底关闭了朋友圈功能,“懂我的人可以体会出,我想隐藏自己”。
在西美尔看来,风格的概念更多是和消费品有关,是风格化了的物品或商品,而不是生活方式。“西美尔似乎并不认为某个人(比如现代中产阶级中的一员)的全部生活应该风格化,以遵循一条共同法则和与别人共享这一风格”。[12]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人的生活都可以或愿意被风格化。就像吉登斯所说,因为高度现代性使得个体面临多元选择,很多时候他们会“被迫”追随生活风格,体现在衣食习惯、行动方式或所设计的环境上。
二、信息发布与文化消费:资本形塑的生活风格
社交网络是人们传递和分享知识的重要传播渠道,构成一个知识扩散的互联网。[13]研究者邀请受访者为自己挑选最能代表其生活方式或品位的社交网络内容,构成社交网络自述,绝大多数受访者都选择了含有知识或文化消费类的内容。比如ZPY选择了自己转发的“为你读诗”公号的一篇文章:《我们总是爱不同的人,受同样的温暖和伤害|电影〈驴得水〉女主角任素汐为你读诗》,并解释说:“比如说我会转那种‘为你读诗’,或者是我自己写一些感悟这样的东西,好像比较有逼格的那种,或是发书的照片、电影的截图这种,我就会比较倾向于去发一点。”LYF挑选了一张近期参加的讲座照片和一首歌曲,“(讲座)的确很有收获,而且给人感觉蛮深刻的。这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虽然lady gaga很火,但这不是一首很烂俗的歌,是一首我很喜欢的小众的歌。”他最常公开发布的内容是看话剧、听讲座,“我明确觉得这种行为是装……就是觉得自己很充实,然后品位很高,但是这个不管我自己做还是别人做,都是一种比较装的感觉吧”。
人们在社交网络中展示自己的文化消费,以标榜自己的社会身份。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二是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三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例如教育资格的传递,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14]前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都能通过社交网络很方便地得到呈现——扮演出文化涵养和精神世界的“性情”,或是直接表现书籍、电影、音乐等文化商品;体制状态的文化资本则更隐含于关于自己教育信息的日常叙述中。社交网络呈现的是生活的断面,也即是说,通过碎片化的叙述,能够更轻易地表演出文化资本的占有状态。例如,ZPY自认并非爱阅读之人,而微信朋友圈给她提供了“扮演”阅读喜好的捷径:“就是写一些对这个书的感悟的话,然后大家都不会跟你讨论,或者他要跟你讨论,你知道的就跟他讨论,不知道的就不用讨论。但是你现实中如果面对面跟大家讲这个事,大家就会说那这本书里面后面几章说得怎么怎么样,就很容易露馅,因为你没有看,你可能只看了这几页,就说这几页写得好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们在社交网络上阅读和转发资讯,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消费,社交网络使用者常常通过一个人所转发的资讯内容来判断对方的文化知识品位。中文系大学生LYF说,“我周围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人,我们文院大家公认品位比较差的人,但是他就特别喜欢看个剧看个电影,然后把它(在社交网络上)摆出来。特别一点是,他的偶像是唐嫣,我们经常看到他转关于唐嫣的新闻,很喜欢看青春偶像片,我就特别受不了。他每次发朋友圈我们都会截图到我们寝室(微信群)里面,三个人一起吐槽他”。常有人在社交网络中表达对作家或知识分子的欣赏,LYF介绍了他所认为的品位层次:“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基本在我们圈里最低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一是太流行,二是我自己看并没有那么深的触动。他和很多作家比起来真的就是文字上小资的倾向特别明显,真的大道理他们好像也讲不出来……福柯、拉康再往上一个层次,但是有人在朋友圈张嘴闭嘴就拉康、福柯,但是真正读过福柯、拉康的人,(他们的内容大部分人)根本听不懂……”
资讯的品位也表现在它的来源。“我觉得南周(《南方周末》)、智谷趋势(财经观测公号)这种,它的文章就普遍水平比较高,这是我转发的一种标准”,受访者HX说。HX在受访前最近20条社交网络公开内容,近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智识类的,他认为这与自己在读硕士身份相符。访谈之后的几日,羽毛球运动员林丹出轨成为热点新闻,HX告诉笔者,大部分社交网络好友都在转发相关新闻,这时需在众多好友中让自己的资讯品位脱颖而出,于是他选择了BBC的新闻《China’s Lin Dan: Badminton star’s affair shocks fans》。但是,过多地转发资讯类内容对营造品位印象也会产生负效果。ZPY举例自己的一位老师,每天转发多条资讯,在她看来是过量的。“我客观印象不会觉得他很low,但我会觉得这些他都看了吗?他真的有这么闲吗?……我觉得特别高贵冷艳范的其实会很在意自己的信息输出,他会觉得这个是适合他输出的他才会发朋友圈。我相信他也不是看到一个信息就转发,但是他测量的那个水平就会比别的人要放松那么一点点,就是他可能已经很努力在控制自己了,但是他还是发了那么多。”当然,文化资本的呈现对研究对象如此重要,主要还是因为研究对象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区别于一般的收入中高群体的最大特征是受教育程度。文化资本是这个阶层品位区隔的重要来源。这也是一种基于现实体验的品位判断,在社交网络中可能是以量化的点赞、评论等形式呈现出来,也隐含在其他社交网络用户的线下评价中。
三、“有趣”与“丰富”:“体验主义”生活风格
人们通过自己的品位筛选和表达,究竟在社交网络中试图塑造怎样的生活风格呢?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惊讶地发现,受访者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极小的个体差异,他们在描述理想的生活方式时,几乎一致将“有趣”“充实”和“丰富”作为共同目标。
“想让大家觉得我的生活很多姿多彩,自己很在意生活质量。我特别羡慕那种人,经常出去溜,满世界晃荡,你经常看到他发他去这里浪去那里浪的照片,蓝天白云、青山绿水。”(ZPY,编号04)
“这个人要是积极开朗的,要是有生活品质的,从你的穿着、你看的书、接触到的人(表现出来)。一些生活习惯,比如经常旅行。说到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HX,编号02)
HJM讲述了自己最近的一次经历:一位久未联系的同学忽然向他发来短信,向他表达很羡慕他丰富精彩的生活,并且已经决定辞去家乡那份枯燥乏味的工作,外出寻找新的生活。HJM感到震惊,他认为自己经营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交网络形象,但也深刻地明白,虽然自己在社交网络中呈现的生活多半是社交、休闲、娱乐,但真实的生活远没有如此有趣,作为金融从业者的他工作繁忙,“根本没什么时间出去玩,只是朋友圈给人一种很丰富的感觉”。
事实上,“有趣”仍是一种将品位和等级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表述,并且早已有之,英国学者约翰·克拉克观察,“对于那些在更具‘新教伦理’的旧伦理当中成长并被它塑造的传统中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充满矛盾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现在需要的不是勤俭而是消费,不是冷静而是时尚,不是延迟的喜悦而是对需要的当下的满足,不是耐用品而是消费品:是‘多姿多彩的’而不是庄重严肃的生活方式。” [15]费瑟斯通认为,现代消费文化把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谋划,变成了对自己个性的展示以及对生活样式的感知,所以“他们有冒险精神,敢于探索生活的各种选择机会以追求完善,他们都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因此必须努力去享受、体验并加以表达”。[1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取向是时间的产物。青年们用社交网络来打破日常生活的连续性。Helen Grace研究了香港人的手机照片,发现人们用手机拍摄和上传照片的通常是“有趣”或“得意”(粤语,意为有意思)的时刻。他认为这是一种“白日梦的状态”——列斐伏尔认为“时刻”是非连续的,每一个时刻都应与先前的时刻区分开,是独特的——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目光游离,忽然被吸引到任何事物上,手机拍摄下的则是这些“独特时刻”,并赋予他们意义。[17]一方面,现代社会信息和协作的需要使时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于那些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费和体验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根本的短缺;从许多方面来讲,那些希望上述方式有所成就或有所征服的人所面临的是一个和奢华生活有关的问题: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做所有想做的事情”。[18]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生产了大量欲望,“那种要尽可能多地‘体味生活’、体味一切令人‘愉悦’的事情的愿望其实是一种最大的贪欲”,欲望与短缺时间互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自我实现要求——“资本家积累巨资并大笔投入,而个人在各种各样寻求快乐的活动中做出的时间投资也是资本家一种自我实现的形式”。[19]由此,“体验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使我们沉迷于不必要的物质追求之中,并因此播下了“体验主义”的种子。当不断创造出新的物欲的经济系统的能力开始受到一些限制时,这些欲望或需求也就转化为休闲体验。人们不是为了观看别处的风光,而是为了体验别处的生活。[20]体验主义的核心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生活经历,也在于个体的内在体验。HX感到自己在社交网络上表达的追求是“由浅及深”的:“我觉得有品质的生活应该他们能够从文字或者图片里找到一些共鸣点,或者是说他们能够有所思考,或者情感上的共鸣。”ASY也有类似感受,她最欣赏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真情实感的东西”:“他可能会写一大段东西,我很喜欢看,我觉得这样特别真诚……比如说这次我们旅行,一些姑娘说这次旅行对她们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她回去之后就写了一段很长的那种感悟。那种细节让你很感动,就是很‘戳’你。”同样是情绪呈现和情感表达,“真情实感”和“无病呻吟”不同,前者是足够真诚的、让人感受到情绪抒发的真实来由,后者则让人感觉纯粹功利地为引起他人的注意、满足自我迷恋的欲望。内心体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产物,人们将日常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之后,发现有必要追求内外在的体验,因此在社交网络中努力呈现出这样的生活风格。
四、结语:以数字体验主义为中心的生活风格
经由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窥见,无论是社交网络中“场景”与“空间”的拼贴,还是信息发布与文化消费,青年群体在社交网络都建构了一种关于自我的生活风格。从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看,以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有趣”为目标的“体验主义”成为社交网络世界中统治性的生活风格。而这种生活风格的营造是一种典型的数字时代的产物,很难区分它是纯粹的线上虚拟经验还是线下日常生活。在笔者看来,数字体验主义具备如下特质:
1.图像性
不论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时代”还是德波的“景观社会”,都指出近现代社会中视觉文化的转向,图像逐渐成为文化主因,图像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变得尤为重要和普遍,较之早先的话语文化形态更占优势地位。社交媒体的青年群体使用者除了喜爱使用图像、位置信息来直接编码社交网络的意义世界,还倾向于以表情包、漫画图片来表达与交流,除了由于直观,还因为契合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情绪和状态的艺术化再现。图像性表达正是社交网络时代一种直观的意义组织方式,从社交网络的内容上看,每个人在社交网络中既是内容发布者又是观看者,从场景、文化消费、身体实践和影像等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进行观看与被看的实践,建构起默认的品位规则。社交网络以及自媒体的传播模式,使得这些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成为一种可视化的数字存在。可以肯定的是,社交网络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图像化表征,必然影响着审美趣味和生活风格的运作,它的进一步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经验研究来进行详细论证。
2.连接性
社交网络作为数字社会的重要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在线互联深刻变革着社会交往形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也渗透到社交网络生活风格的建构中,在社会地位和品位尚未固定的主导用户——青年群体中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社交网络中的场景以及场景的表达方式组合成人们的“道路修辞”和空间行动的风格,远离日常生活而又构建了另一种日常生活。这也是潘忠党指出的由媒介所中介的社会生活,“不仅人类的传播或交往经由了传媒技术及其相关机制的中介,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通过如此中介了的传播或交往得以型塑”。[21]孙信茹在其研究中也观察到,微信通过西尔弗斯所说的“双重勾连”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借助微信,个体在生活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之间可以自由转换。[22]连接性(connnectivity)或曰勾连性(articulation)是社交网络的生活风格不同于线下生活风格的根本所在。
3.体验性
对于青年社交网络用户们来说,线上经验与线下经验的整合成为他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他们不仅仅是数字原住民,而且是社交网络原住民。数字时代规训了他们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感知、体验与表达。从社交网络所建构的生活风格来看,比起现实生活的风格生成,线上生活风格的拼贴是更为简易的方式,能够弥补人们的现实自我和生活方式的遗憾。以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有趣”为目标的“体验主义”成为社交网络世界中统治性的生活风格,既强调外在体验,也需要内心体验。社交网络将日常生活体验分为虚拟与自然经验,但是它们的边界逐渐模糊,出现一种相互重构的趋势。
青年群体作为社交网络使用的文化主体,通过社交网络实践,营造了一种兼具图像性、连接性与体验性的数字体验主义的生活风格,这是一种崭新的带有鲜明代际文化色彩与数字空间趣味的生活风格。作者认为,社交网络中的风格体现出的是当下的某种成为主导的流行趋势,或者说,在社交网络中占据主流的中产阶级青年的价值观念。风格的核心定义是“在一种对抗性的表达上——这种表达对外界社会的价值观持有几分协商性的对抗立场(partly-negotiated opposition)”。[23]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交网络世界的隐藏者或边缘者又以他们对共同风格的拒绝来表达自己的对抗性立场,仍然是争夺自我的一种行动,这些零散的个人行动又构成新的文化“飞地”(enclave),成为新的风格。在社交网络的生活风格的定义、形塑乃至划界中,不是别的,正是青年群体的生活体验本身形成了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及来源。研究观察到,“有趣”正在成为社交网络空间数字体验主义生活风格的核心。数字体验主义有可能打破旧有的以阶层、消费划界的社会区隔并建构新的区隔,体现了青年文化的能动性及影响力。但必须指出,它自身也处于流动的形塑之中,进一步认知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生活风格需要更持续的观察和深入思考。■
①阿·阿德勒:《生活的科学》第61-77页,苏克、周晓琪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②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9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21页,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④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第272页, 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⑤阿克塞尔·霍耐特:《日常生活审美化》,尹岩松译,《艺术百家》2012年第6期年版
⑥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第272页,陆扬、张岩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⑦马杰伟:《时尚志》第15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⑧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357页,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⑩姜思达:《50句话照亮你的高端网路》,网络来源:https://www.ishuo.cn/doc/wkzhffqf.html
[11]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第307页,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12]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第116页,向建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冯锐李亚娇:《社交网站中知识扩散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远程教育杂志》2014年第3期
[14]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第192-1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第15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16]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26页,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7]Grace,H.,《图像和亲密屏幕:流动性与手机照片的日常性》,《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年总21期
[18]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古德尔等:《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23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等:《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23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Godbey,G., Leisure in your life. An exploration[M]. 1985. p251-252
[21]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与“驯化”》,《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22]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
[23]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第305页,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朱丽丽 李慕琰/朱丽丽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慕琰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社交网络的青年群体日常社会-文化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4BXW0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