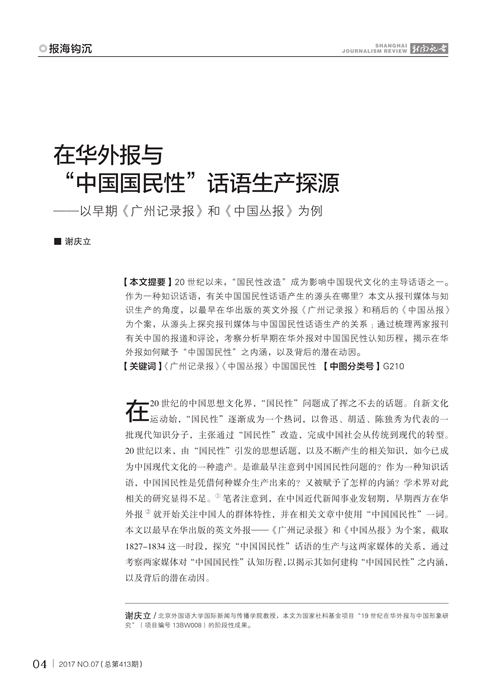在华外报与“中国国民性”话语生产探源
——以早期《广州记录报》和《中国丛报》为例
■谢庆立
【本文提要】20世纪以来,“国民性改造”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化的主导话语之一。作为一种知识话语,有关中国国民性话语产生的源头在哪里?本文从报刊媒体与知识生产的角度,以最早在华出版的英文外报《广州记录报》和稍后的《中国丛报》为个案,从源头上探究报刊媒体与中国国民性话语生产的关系;通过梳理两家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考察分析早期在华外报对中国国民性认知历程,揭示在华外报如何赋予“中国国民性”之内涵,以及背后的潜在动因。
【关键词】《广州记录报》 《中国丛报》 中国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G210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国民性”问题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自新文化运动始,“国民性”逐渐成为一个热词,以鲁迅、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国民性”改造,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20世纪以来,由“国民性”引发的思想话题,以及不断产生的相关知识,如今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遗产。是谁最早注意到中国国民性问题的?作为一种知识话语,中国国民性是凭借何种媒介生产出来的?又被赋予了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对此相关的研究显得不足。①笔者注意到,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轫期,早期西方在华外报②就开始关注中国人的群体特性,并在相关文章中使用“中国国民性”一词。本文以最早在华出版的英文外报——《广州记录报》和《中国丛报》为个案,截取1827-1834这一时段,探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生产与这两家媒体的关系,通过考察两家媒体对“中国国民性”认知历程,以揭示其如何建构“中国国民性”之内涵,以及背后的潜在动因。
一
“中国国民性”是指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在精神特质、道德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共同特征。“中国国民性”(Character of the Chinese)一词首次出现在1832年12月在华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中。在此之前,虽然在华外报没有使用“中国国民性”(Character of the Chinese)一词,但已关注中国人群体的共性特质。1828年初,澳门的英国人与附近的望厦村村民发生冲突。西方人发现,望厦村村民作为一个群体,对外国人表现出“排外”“高傲”的行为取向,很快成为最早在华出版的英文外报——《广州记录报》报道热点。
事件的起因是:1828年春,侨居澳门的英国人为举行赛马会,擅自在澳门与望厦村之间修筑道路。道路经过之处,恰恰是望厦村民先祖的墓地,也是当地的“龙脉”。这年4月,在一位乡绅带领下,望厦村民联合向清政府在澳门的管辖机构——澳门军民府投递禀帖,指责英国人越出中国规定的范围修筑道路,③望厦村村民因此举行集体抗议活动。
1827年11月8日,首家由英国人创办的在华英文外报——《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在广州口岸出版,这是一家由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支持创办的报纸。创办之初,收集中国资讯受到官方限制,有关中国报道,除了摘录《京报》外,其他报道多是“道听途说”,缺少报道者的“现场见闻”。望厦村民抗议事件爆发后,主编爱尔兰人阿瑟·基廷(Arthur S. keating)对此产生了报道兴趣:中国人为什么呈现共同的行为取向?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特殊群体?1928年4月26日,《广州记录报》对望厦村民集体抗议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其视点聚焦中国人的“群体特质”——自大与傲慢。阿瑟·基廷为此还发表评论,批评参与抗议活动的中国人,指责他们居高临下的“贵族式姿态”,“在信奉基督的人面前,表现得像一群恶棍,与那些狡猾、残忍、贪婪的野蛮人没什么两样”。《广州记录报》是在华独家发声的英文媒体,把望厦村民集体抗议活动作为新闻报道材料,这样,“居高临下的贵族式姿态”就具有了群像刻画的共性特质。④《广州记录报》还特别报道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一位姓何的乡绅,“他总是标榜爱国,把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人看作贪婪的野蛮人。他善于演讲,雄辩滔滔。但其中充满了谎言”。⑤
与传统的《京报》相比,近代报刊是当时的“新媒体”。在中国新闻史上,《广州记录报》首次以“新媒体”的手段,推出有关中国人群体事件报道,并以此设置议题,引发西方在华侨民的关注。之后,围绕这个议题,中国人的群体特性再次成为西方侨民关注的焦点。1828年5月17日,《广州记录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发现,几乎所有中国人发布的文告、官方来往的文书,凡涉及西方人与事一律都使用“夷”字。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中国人的‘夷’字,其意义就是‘野蛮人’,而‘野蛮人’一词,长期被中国人指除了自身之外的其他人类”。⑥他认为,这更证明中国人的自大和狂妄,值得嘲笑的反而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傲慢和自大意味着什么?西方人意识到,一旦被看成“野蛮人”,这将使他们受到歧视和侮辱。针对这个问题,《广州记录报》有意把讨论引向深入。1828年5月24日出版《广州记录报》发表文章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不仅受歧视,还普遍地受到侮辱,“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相互交谈时,外国人经常会听到一些具有污蔑性的叫法,例如外国鬼、红毛鬼、黑鬼、魔鬼、醉鬼等”。在他看来,“夷”与“鬼”不是用词问题,这关乎他们的尊严,其背后表现出中国人排外、自大和无知的群体特征。⑦
《广州记录报》对望厦村村民抗议活动的报道和讨论,为研究中国人的群体特性找到了典型样本。编辑以读者参与的形式,逐渐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力图从理性层面揭示中国人群体特性的根由所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出,儒家伦理道德导致了中国人自大。中国人视西方人为“野蛮人”,就是自视具备了这套“伦理道德”。因此,儒家伦理体系也塑造了中国人个性的另一面:无视其他民族的尊严,文化心理趋向封闭。⑧
《广州记录报》以望厦村村民集体抗议活动为报道切入点,把对中国人群体特性探究作为深入讨论的议题,这不是偶然的。首先,事件涉及西方在华侨民的直接利益;事件看似偶然,其实是中西商业体制、外交体制长期潜在矛盾的爆发;而中国人以群体方式“示威”所展示的性格特质,不得不让他们反思:为什么中国人长期对西方人充满敌意,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的群体特性等问题。作为在华出版的独家英文媒体,《广州记录报》显示它设置媒介议题、引领西方在华侨民舆论的优势。该报对中国人群体特性的关注和讨论,一直持续到1832年5月《中国丛报》创刊两年后,在有关中国人群体特性的(后称“中国国民性”/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报道和讨论方面,两家媒体形成呼应态势。
二
《广州记录报》报道和讨论呈现了中国人群体特性的一个侧面。与《广州记录报》相比,《中国丛报》对中国人群体特性的报道显得较有连续性和现场感。《中国丛报》1832年5月创刊于广州口岸,其创办者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之初,主编裨治文发现,大部分用欧洲语言写的有关中国著作,都充满错误内容,“整个关于中国的领域都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形象需要“重新建构”。⑨
1832年5月到1832年9月,《中国丛报》连续5期推出伦敦会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写的系列报道——《郭士立中国沿海考察日志》。之前,在华外报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多摘译自中国的《京报》,或转述他人的“见闻”,或记录道听途说之消息,没有围绕一个议题,以现场见闻的形式对中国进行连续性报道,《中国丛报》推出的《郭士立中国沿海考察日志》系列作品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在中国新闻史上,西方在华媒体首次以连续报道的方式,围绕中国人的群体特性进行“现场报道”。
《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特别重视这组游记作品,自创刊号起,一连5期均以重要位置进行编排,同时配发编者按语。这组系列“日志”,以旅行者的叙事视角,采用“移步换形”叙事结构,报道中国沿海的风俗民情,鲜活地展现“现场中国”的方方面面。⑩与转述报道中国的方式不同,郭士立置身于具体的“中国场景”中,把焦点对准“中国人”,通过不同的场景,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多层面考察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文化观念和人格取向,并以此呈现中国人的群体特性。正因为作者以“在场”的视角,他的中国报道显得更“真实”,其观点也更有“说服力”,较容易赢得西方读者的认同。
作者并不完全选择“阴暗面”来建构中国人的特性,他特别注意捕捉中国人的“亮点”。这样,他的新闻选择、观察视角和叙述立场都显得相对客观。郭士立从泰国登上一艘中国商船,开始对中国的“现场报道”。他发现大部分中国船员出身贫寒,文化程度很低,但很喜欢阅读,就把宣传基督教小册子散发给这些船员。他因此相信上帝,“会让每一个人都领悟到真理、永生、以及极乐世界的含义”。[11]船行至海南,郭士立考察一番,认为“海南岛上民风淳朴,对外国人热情友好,具有勤勉、坚韧的品质”。[12]在山东沿海的刘公岛,作者称赞这里民风淳厚,居民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对外人非常热情,“甚至受邀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叫白河的地方,这里的人同样友善、有礼貌,登上陆地,“好多人称呼我为‘先生’”,“还有‘许多张脸’冲着他笑”,欢迎他不远万里来到天朝上国。
郭士立以“观察者”的角色“报道中国”,作为一个传教士,中华帝国臣民的道德状态是他最感兴趣的。从泰国沿海登船,郭士立就注意观察船上的中国人,这艘船就成了他报道中国的“切入点”。船上,除了郭士立,其余全是中国人。这就有了象征的意味:这艘“货船”作为缩微的“中华帝国”,船上的“西方人”郭士立是自觉的观察者——
和我同屋的是6个中国人。其中有个60岁的老头,他以前是个船长,但他的船因为经不起海上的风浪,有一次停靠在湄南河岸的时候撞上了暗礁。大家都知道我俩不合,他吸鸦片上瘾,每天至少花一块大洋买鸦片。他几乎无恶不作,从不听从其他中国人的劝阻;可他居然听说过强大的欧洲,知道欧洲瑰丽的艺术。他儿子是个傲慢粗鲁的年轻人,精通奸商之道,对金银财富无比贪婪……[13]船上的这群中国人成了“西方观察者”眼中的“活标本”,他们浑然不觉地接受“西方”的审视——他们没有高尚的生活目标,吸毒、偷盗、纳妾,没有家国意识,精神麻木,以满足生理欲望为目标,成为一群没有灵魂的“动物”,丧失了人的基本良知。接下来,最不堪入目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7月17日。在我们靠岸不久,我看到一大群小船包围了我们的商船,船头上都站着女人。我再次警告还留在商船上的船员,一定要压制自己的邪念。然而我的话根本不起作用,我前脚刚刚离开甲板,他们立马无所顾忌……[14]作为缩微版的“中华帝国”的这艘货船,其“船民”象征着中华帝国的“臣民”,船长就是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威”。作为报道者,郭士立的报道视点聚焦到船长身,这位船长是到了厦门后新换的。新船长是一位有文化的人,但生活教养极差,没有一点现代航海科学知识,在航海事务上却听不进去正确意见,容不得任何人对他指手画脚。这位“船长”固执己见,做事昏头昏脑,在他的引领下,船上“臣民”的道德状态丝毫没有改变。
船到天津,郭士立发现,在这里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大多抵抗不住欲望诱惑。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郭士立就试着用学过的医术,治疗那些上了鸦片瘾的中国人,很快就取得了疗效。几天后,一些中国人专程拜访他,有的还亮出他们尊贵的官职身份。[15]郭士立有意捕捉生活细节,以此考察中国人文化心理层面的共同特性。他发现,“天朝”文化意识也体现在普通人身上,他们常常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天朝”臣民的优越感。作者用略带反讽之笔写道:“中国船员都很穷,可尽管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买咸菜白米饭的钱都没有,他们整天依旧很快活,经常对我开玩笑,‘你终于离开了野蛮的原始部落,要到天朝上国去了!’”郭士立用事实揭示,中国人的自大和优越感,其实是因为对外部世界的无知造成的。譬如,中国的船员们问他,“西方蛮夷”们吃不吃大米?郭士立正在犹豫怎么回答时,一个船员们惊呼:“噢!西方世界真是荒凉!都种不出能吃的东西!真奇怪啊,你们的祖先居然没有饿死!” [16]郭士立的“现场报道”呈现出中国人充满矛盾的精神特质。首先,他认为中国人既对世界好奇又趋于封闭防守心理。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郭士立发现,西方国家在中国人的眼中是一幅渺茫而遥远的模糊图像。“观察者”所乘的船在山东刘公岛靠岸,据说1816年,英国大使阿美士德的舰船也曾停靠在这里。旧事重提,岛民好奇地向他询问外部世界的情况,似乎这艘船随时会向人们开炮。郭士立解释,西方人其实很友好,中国人却反驳,欧洲人身上都带着枪,到这儿来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17]郭士立发现,这里的居民认为,欧洲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住着一些商人,说着奇怪的话,靠与中国贸易为生。为了更正中国人的这种想法,郭士立告诉他们欧洲国家的名字,但发现中国人固有的信念过于强大,根本无法撼动。[18]其次,中国人既渴望财富又缺乏冒险精神。郭士立发现,中国人对金钱充满欲望,很想知道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欧元、美元是从哪里来的。当他告诉那些中国人更多有关欧洲的事情之后,他们对欧洲产生向往,希望到大洋对岸去,因为那里遍地都是金银。得知要经历漫长的航行才能到达,中国人感到恐惧了。郭士立所选择的这个事实蕴含着他的“观点”——中国人没有冒险性,不能拓展新世界。
再次,中国人既多神崇拜又缺乏信仰。报道中多处写到,中国沿海不同的地方风俗各异,或者拜关公,或者拜妈祖,或者拜天神,或者拜“天主”,但都是“有求必拜”。在厦门,“妈祖庙随处可见,修葺得并不十分华丽。基督教神职人员众多,且受到良好待遇,每天来拜访听教的人络绎不绝”。[19]但郭士立经过一番考察,发现中国人什么都不信,缺乏宗教情感,心灵深处没有信仰的根基。
郭士立的“现场报道”用不少篇幅描绘了中华帝国的没落图景,在他看来,帝国的没落首先表现于国民观念的滞后。他通过描绘天津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从而在人格行为取向层面,建构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没有政治意识、不关心国家的群体特性。当然,郭士立采取“用事实说话”的方式:天津人穿着漂亮得体,他们精心呵护自己的庭院,但对自己庭院之外的公共事务非常冷漠。作为靠近首都的商贸城市,天津竟然“没有一条专用的货运通道”。他在走访中发现,“中国人并不在乎帝国的统治者,只关心挣钱过上好日子”。[20]
三
郭士立的《中国沿海考察日志》连载完后,《广州记录报》和《中国丛报》有关中国人群体特性报道和评论,则倾向于在理性层面的探讨。1832年12月,《中国丛报》在“杂记”栏目里,刊发了《中国国民性》一文。“Character of the Chinese”作为关键词,在这篇文章中出现多次。自此,“中国国民性”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在此之前,《广东记录报》和《中国丛报》虽然注意中国人群体的某些特性,多是从现象层面进行认知性报道,没有使用“Character of the Chinese”一词。但正是之前两家外报鲜活而感性的有关报道,使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留下较深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Character of the Chinese”出现后,《中国丛报》和《广东记录报》所发表的一些研究中国的文章,开始频繁使用“Character of the Chinese”这个关键词,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中国国民性”。
1832年12月《中国丛报》发表的《中国国民性》这篇文章,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国民性”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到了清朝,强权垄断了一切,“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停滞不前”,中国人趋于保守,成为“古老传统的盲目追随者”,因此“不能认清自己的缺陷”。满族人建立了政权,需要与汉人合作,这就导致“两种国民性并存且互相影响”。满人高高在上的“做派”与汉人的诡谲多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现在的中国的国民性,一直保留到今天” [21]。作者指出,“瞒和骗”是中华帝国对外交往的手段,“如果中国在对其他国家的交往不满意,她会毫不犹豫更改事实”,把谎言说得冠冕堂皇。
1832年12月1日,《广州记录报》发表《中国研究》一文,作者指出“天朝”的臣民习惯于“崇拜偶像”“迷信权威”,这种共同的文化心理特质,使他们的观念“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几个世纪”。[22]对此,郭士立发表《中华帝国的宪章》一文,从文化与性格生成层面进行深度剖析。作者发现,中国人的“天朝”幻觉与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天朝”意识不仅建构了帝国的政治体制,也建构了“宗主-朝贡”外交秩序,并把这种不平等的外交秩序强加给西方,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文化疆界,认为“地球万国之王均应从这位政治教皇那里,得到授权,并尽速朝贡”。[23]郭士立的文章引发了西方侨民的关注,1834年12月9日,《广州记录报》发表一篇评论,探究“天朝”意识形态与中国国民性塑造这一问题。作者发现,从官方到民间,“天朝”文化优越感无处不在,形成高高在上的“臣民”心态。当面对西方的“蛮夷”时,其排外倾向就表现得特别突出。面对西方的发展,“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满足于官级和薪俸,认为自己优越于任何人”。[24]1833年12月,《中国丛报》发表《中国人的叩头与下跪》《骄傲与谦卑》,从礼教与国民性生成的角度,分析中国人的“奴性”问题。作者认为,中国人的奴性不是偶然生成的,是繁琐的儒家礼仪长期教化和皇权专制长期驯化的结果。“奴性”作为中国国民性的一个重要元素,产生的许多负面后果:钳制了人的外在行为方式,遮蔽了人的精神视野,扼杀了自由心灵,使人自觉认同被奴役的地位。这样,中国人精神不仅不可能开化,还会在“天朝”的幻象下产生自大和排外的倾向。
《广州记录报》和《中国丛报》往往把中国人性格的缺陷与沿海流行的野蛮风俗、宗教伦理连在一起,以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缺乏新知识作为良知丧失的根由。据不完全统计,1834年之前,两家媒体涉及报道中国南方沿海重男轻女、溺杀女婴,随意休妻、吸食鸦片、妇女赌博、拐卖儿童、迷信偶像、妇女缠足等问题的篇目就有40多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生存处境是两家媒体报道和评论的焦点。《广州记录报》仅在1828年就有多篇报道涉及这类问题。报道称,在广东东部一些地方,溺杀女婴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导致这里男女比例为10∶1。在那些贫困的家庭,两位兄弟会与一个女人结婚。[25]《中国丛报》的有关报道更多,根据前四卷统计,涉及这类报道内容的篇目就有20多篇。对于缠足这种陋俗,1835年4月,《中国丛报》发表《剖析中国妇女的小脚》一文。作者认为,缠足是一种政治计谋,目的是幽禁女人,中国女人以此为美,而实际上只是一种畸形。
针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问题,《中国丛报》的“时事报道”栏目,经常报道中国民间任意休妻、虐待女性、少女因害怕被虐待而自杀等现象。两家媒体所报道的“事实”,为在华媒体建构“中国国民性”之残忍、麻木的精神内涵提供了材料,同时,也为西方传教士欲用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提供了佐证。
四
“中国国民性”问题为什么一开始就成为在华外报关注的焦点?其背后的动因究竟来自什么?笔者认为,首先,中西关系的长期对峙格局是重要因素。以中英关系持续为例,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贸易关系持续将近两个世纪,但中英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关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获得在华利益,急于打开中国的门户。其次,他们发现,中国民间存在抵抗西方的强大力量。天朝华夏中心意识形态渗透在中国普通百姓观念中,在西方人面前处处表现出天朝优越意识。第三,西方人发现,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完全一致,在精神特质、价值观念、人格取向方面呈现共同特质。
上述问题,不得不让西方人深入反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认为,“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成功地与中国人接触,与他们交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对他们的性格茫然无知”。[26]他认为,要想解决西方面临的问题,必须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必须从了解“中国人的知识特性”入手。裨治文使用“Intellectu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一词,表明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思想与知识体系与中国国民性塑造的关系。人,是社会关系和文化塑造的产物;搞清了中国人的共性特质,也意味着把握了中国的文化。然后按照西方的意志,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观念形态,推进中国对外开放。这种逻辑,当然是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的一厢情愿。
西方在华媒体中的“中国国民性”毕竟是一面“西洋镜”,其背后对应着他们的现实需要,隐藏着西方对中国的欲望与期待。不可否认,无论是《广州记录报》,还是《中国丛报》,其建构的“中国国民性”其实是一种主观建构:一方面存在着某些“真实”;另一方面,由于受文化传统、现实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又不免存在某些夸大、扭曲事实。在此过程中,他们把中国当成确认西方价值的“他者”,确信西方是文明的、进步的,从而获得西方的文化优越感;与此同时,中国被重新定位:陶醉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半开化的国家。这样,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倘若不尽快唤醒她,我们如何阻止她的堕落”。[27]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顺从西方的意志,接受西方的“改造”。
结语
通过梳理早期在华外报的有关中国报道,我们试图寻找“中国国民性”话语生产的源头。《广州记录报》和《中国丛报》对中国人群体特性的报道,以及后来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讨论,开“中国国民性”建构之先河,引发了中国现代思想资源生产的“蝴蝶效应”。在华外报垄断中国对外传播80多年,“中国国民性”问题被持续关注,成为建构西方媒体建构“中国形象”的主导话语。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在华媒体生产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基本形成一套知识体系,“中国国民性”逐渐被定型化,其标志是1889-1890年,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以“中国人的气质”为专栏,持续推出美国传教士兼《字林西报》通讯员明恩溥“中国国民性”研究的系列文章。不久,这些文章汇集成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国家出版。1901年,这些文字又被译成日文出版,成为畅销日本的出版物(1903年,上海新作社又从日文本转译成中文译本《支那人的气质》)。梁启超、鲁迅等人也因阅读此书而产生思想震动。1903年,梁启超因此感慨,“支那人无爱国心——此东西人诋我之恒言也。吾闻愤之耻之,然反观自身,诚不能不谓然也”。[28]当然,西方在华外报所建构的“中国国民性”话语,本意是为西方提供知识资源,但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的文化自觉。通过反观在华外报建构的“中国国民性”这面“西洋镜”,中国重新自我定位,自我调整,自我变革。这样,西方在华外报生产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就转化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呼吁“新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精英倡导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中国借这面“西洋镜”,不断奋进,不断自我警醒,正如梁启超所说,“欲探求我国腐败之根源,而以他国之发达进步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自励策进”,[29]从而走向新生。■
①海外学者刘禾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他把中国国民性话语生产的源头,追溯到1889-1890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国人的气质》,并分析对梁启超、鲁迅等人的影响。而事实上,早在英美报刊在华出现初期,西方人就开始借助报刊媒体生产中国国民性话语,较典型的就是1827年11月创刊的《广州记录报》和1832年5月创刊的《中国丛报》。
②1827年11月8日,首家在华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出版;1831年7曰8日,第二家英文报刊《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出版;1832年5月,《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出版。
③张坤:《在华英商群体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英关系》第118-11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④⑤China,The Canton Register April 26th1828。
⑥BarbariansThe Canton Register May 17th1828。
⑦Epithets Applied to Foreigners,The Canton Register May 24th1828。
⑧Ethics of the ChineseThe Canton Register May 30th1830。
⑨[26][27]E. C. Bridgman,“Introduction”Chinese Repository,may, 1832.
⑩1831年,郭士立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沿海进行调查。1831年6月,他从曼谷登上一艘中国货船,经过东南亚泰国、越南等国家,到达中国海南、台湾海峡,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沿海,最后到达天津。此年10月再沿海路返回,12月到达澳门。郭士立把这次旅行的观察写成了一组旅行日志。
[11][12][13][14]Gutzlaff’s JournalChinese Repository,July1832.
[15][16][17][18][20]Gutzlaff’s JournalChinese Repository,September,1832.
[19]Gutzlaff’s JournalChinese Repository, August, 1832.
[21]Miscellanies,Chinese Repository,December,1833.
[22]The Study of ChineseThe Canton Register, December 1st1832.
[23]Constitution 0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 14th1834.
[24]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Weakness of Government; Not Able to Subdue the Mountaineers; Dangerous on the Borders,The Canton Register,December9th1834.
[25]China, The Canton Register, April 12th1828。
[28][29]梁启超:《新民议》,《梁启超文选》第3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谢庆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在华外报与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3BW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