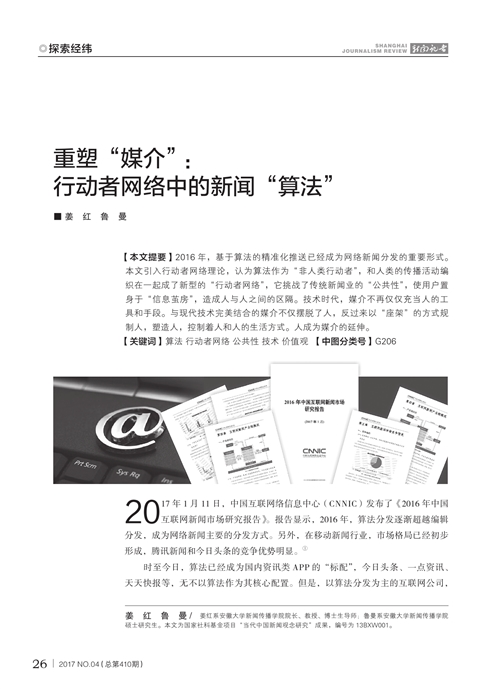重塑“媒介”:行动者网络中的新闻“算法”
■姜红 鲁曼
【本文提要】2016年,基于算法的精准化推送已经成为网络新闻分发的重要形式。本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算法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和人类的传播活动编织在一起成了新型的“行动者网络”,它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公共性”,使用户置身于“信息茧房”,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技术时代,媒介不再仅仅充当人的工具和手段。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的媒介不仅摆脱了人,反过来以“座架”的方式规制人,塑造人,控制着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人成为媒介的延伸。
【关键词】算法 行动者网络 公共性 技术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206
2017年1月1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算法分发逐渐超越编辑分发,成为网络新闻主要的分发方式。另外,在移动新闻行业,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腾讯新闻和今日头条的竞争优势明显。①
时至今日,算法已经成为国内资讯类APP的“标配”,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天天快报等,无不以算法作为其核心配置。但是,以算法分发为主的互联网公司,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媒体”,而更加强调其作为信息聚合平台的特征。今日头条CEO张一鸣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不断说明今日头条不是媒体,而是“平台”。但不可否认的是,今日头条具有强烈的媒体属性。作为一家“中国最大的媒体渠道,他们每个月为1.5亿用户提供服务,每天有近7000多万人花76分钟在今日头条上观看新闻、视频”。②无独有偶,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也一直否认Facebook是一家媒体公司,更否认Facebook在去年的美国大选中对民众舆论进行过干扰。
算法在网络新闻生产中的热度已经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关注。业界围绕算法讨论较多的是技术是否中立和有无价值观的争论。2016年12月14日,《财经》杂志刊发对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的专访,采访中提到了今日头条的技术算法、内容分发、价值观等问题。张一鸣表示今日头条是企业不是媒体,媒体需要有价值观,头条只关注提高分发效率,满足用户需求。③201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版发布了《算法盛行,更需“总编辑”》一文,文章提出“在算法主导的时代,更需要把关、主导与引领的‘总编辑’,更需要有态度、有理想、有担当的‘看门人’”。④当日,豌豆荚的联合创始人王俊煜在知乎上公开表达:“技术是有价值观的,取决于你做什么。” ⑤
目前国内关于算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数学以及互联网技术等领域,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开始于2016年下半年,只有寥寥数篇。在《数据与算法驱动下的欧美新闻生产变革》中,中国政法大学的王佳航主要探讨大数据时代数据与算法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她认为数据与算法正在重塑新闻业的整个生态系统,使得新闻生产模式从单向型新闻生产转化为闭环式新闻生产。数据与算法提升传统编辑室新闻效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行业难题。⑥清华大学的彭兰则更关注大数据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她认为机器与算法将是未来新闻生产的常态,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从那些简单重复的信息生产中解放出来,因此在机器时代,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变得更为重要。⑦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方师师则以“Facebook偏见门”事件为例,剖析了平台型媒体动态新闻推送的算法机制动态,她认为Facebook的算法是一种基于用户社交关系的协同过滤机制,目的在于过滤出对于用户“有意义”的信息;该机制有可能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算法审查、信息操控与平台偏向,从而影响受众态度。这样的推送机制也挑战了传统的新闻价值观。⑧上海大学的郝雨、李林霞认为,算法推送可以在海量的数据中帮助用户快速找到其可能需要的内容,有利于节省用户时间,但是完全依靠机械的数据和机器的计算进行推送,会导致人的扭曲和异化。⑨
国外学者关于算法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早于中国学者,早在2009年,英国的David Beer发现,以算法为基础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用户的生活中,这些算法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代理者身份出现,形成了新的复杂的数字鸿沟,也造成了技术性的无意识。⑩2014年,罗格斯大学的Philip M. Napoli 把算法看作是和媒介机构功能类似的“机构”,她认为以算法为核心的搜索引擎以及内容推荐机制已经深刻影响了媒介的内容生产和用户的消费行为。[11]来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Natali Helberger意识到算法介入分发系统,导致新闻媒体由公共信息的中介转向为个人信息服务,造成媒体与其用户之间的关系中新的不平衡。因此,她提出一种“公平媒体实践”(Fair Media Practices)的做法:即应该树立价值观和原则来引导媒体和用户之间的关系,规范算法向媒体内容呈现和推送给用户的方式。[12]加拿大学者Fenwick, McKelvey认为算法越来越多地控制媒体和信息系统的骨干。这种控制发生在不透明技术系统的深处。它也挑战了传统的公共理论,因为算法的技术操作不能提示形成公众所必需的反思和意识。[13]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是:在行动者网络的框架中,算法对传统专业化媒体的新闻生产有何种连接?对传统的新闻观念有何冲击?对人的生活方式有何种影响?进而思考,算法这种媒介技术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一、算法: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卡龙、劳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在分析“科学”和“知识”的形成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纲领即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该理论最初产生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之后发展成一种重新看待“社会”的认知方法,即“把社会看成是联结的科学”。[14]后来,ANT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和系统的方法,被应用到地理学、经济学、教育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领域。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是许多异质性事物之间联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其概念主要有三个核心:行动者(actor)、网络(network)、转译(translation)。“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 [15]行动者既可以指人类也可以指技术、观念等非人类的一切存在和力量。[16]网络在拉图尔这里是一系列的行动( a string of actions)。这种网络不是如互联网般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 ,所以应当是 worknet ,而不是 network。[17]行动者组成的网络是如何连接的?转译是网络连接的基本方法。转译是一种角色的界定是指行动者不断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所有行动者都处在这种转换和被转换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组合在一起建立起行动者网络。[18]“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 mediator) 而不是中介者( intermediary)任何信息、条件在行动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如果行动者不能造成任何差异他就一定不能被称为行动者。” [19]进行信息分发的聚合平台,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虽然同样是基于算法,但是由于算法设计方法不同,到达用户的内容就不同,内容在算法这里发生了转化。同时,算法本身处于动态变化中,随着用户在不同情境下各种数据的持续输入,仅靠一套算法系统并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因此算法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进以适应用户的变化。[20]因此,在信息传播的网络中,算法是一个“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
拉图尔认为行动者必须到行动的过程中去寻找。在互联网信息选择、传播与交流的网络中,行动者还包括为算法提供原始信息和内容的专业新闻机构,这些机构所进行的内容生产,往往遵循着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服务公共利益,到达用户的内容,是算法对这些专业新闻生产的内容二度选择的结果。此外,用户对接收的内容进行点击与否会作为数据被算法收集,所以接受算法推荐的用户也是行动者。而算法这样一种非人格的计算机信息计算的方式,已经具有比肩机构传播者的行动者特征。在行动者网络中,算法作为一种非人类的行动者,与个人、机构同时存在,他们在行动中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相互建构,共同编织着一张“传播之网”。
那么,在这张网中,算法与机构、用户之间,形成了何种关系?它如何改变媒介与人的传播关系,甚至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二、算法与“新闻机构”:“公共性”的失落
在强大的算法技术面前,传统的新闻媒体与算法推送平台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但又“相爱相杀”的。传统媒体既是算法的同行及竞争者,又是其内容生产者及信息源。离开了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和内容服务,再强大的算法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算法远高于人工的高效信息选择方式和推送方式,又对传统的新闻职业规范、生产方式、运行逻辑等构成了挑战。
算法与传统新闻业的博弈最早体现在版权上,今日头条曾经遭遇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的联合抵制。2014年6月3日,今日头条宣布完成C轮融资1亿美元。当日,《广州日报》起诉今日头条。两天后,《新京报》发表社论《“今日头条”,是谁的“头条”》,抨击其版权侵权。随后,搜狐起诉今日头条侵犯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腾讯宣布停止与今日头条合作。[21]传统纸媒也刻意回避对其的报道。但是,随着纸媒的衰落,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个人自媒体生产新闻方式的大量涌现,传统媒体已经越来越无力制衡算法。
算法与门户网站之间的关系体现在机器推送与人工推送的矛盾上。面对算法分发的快速崛起,从2015年开始,先后有腾讯推出天天快报弥补算法领域短板,新浪及网易升级客户端版本根据用户阅读偏好推荐新闻内容,算法开始进入门户网站,辅助人工分发。[22]然而时至今日,四大门户网站只有腾讯拥有和今日头条相匹敌的竞争优势,还离不开其特有的QQ、微信等社交渠道优势。门户网站算法推送的精准度不够高,无法实现真正的精准化内容推荐,或是其难以与今日头条竞争的重要原因。
目前看来,作为行动者的算法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算法解构了传统新闻业的“把关人”角色,将“把关”的权力交给机器。媒介的“议程设置”权力全然失效。以算法为核心的推荐系统,通过计算,得出符合用户定位的内容排序,这种优先序次决定受众关注哪些事实,决定受众讨论的顺序,把关的权力也由人(编辑)转移到了系统。
第二,算法解构了传统新闻选择的价值标准,仅仅突出一个要素——趣味性。这种价值观的突出体现是迎合兴趣,消失的是公共利益,培养的是“吃瓜群众”。算法的新闻选择标准是基于人“want”的东西而非人“need”的东西。客观上造成感官刺激、猎奇、标题党等的盛行。有人说,算法如同在人性面前放上钓饵,一步一步钓出人性中的“低俗”乃至“恶”。
第三,算法解构了“公共性”。其实,新闻业自诞生以来一直有着两种传统,精英和大众的传统。舒登森曾在《发掘新闻》一书中梳理美国报业史,提出两种新闻模式:“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他认为,“一般而言,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同信息取向相关联,而中间和工人阶层则与故事取向相关”。[23]大众和故事模式的代言者是《新闻报》,而代表精英及信息模式的则是《纽约时报》。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新闻观念中,新闻的“大众化”诉求是要让位于“化大众”之启蒙的,传统新闻业的价值基础是精英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正是精英立场的职业话语转换。新闻专业主义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为最高追求,孜孜以求的是对公共利益的守护,而公共性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土壤之上,建立在理性、独立、关心公共利益的“公共人”的前提之上。从卢梭到汉娜·阿伦特到哈贝马斯,这一传统深深植根于新闻业之中。与此相对,大众化的取向往往被诟病为“低俗”。今日头条的“算法没有价值观”之说恰恰掩藏着重视非精英群体诉求的“价值观”。
张一鸣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说:“历史上精英们一直在试图让大众拥有很高的精神追求,但社会整体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目标。以前的媒体精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特别希望导向的才是特别重要的。但多数人的强烈主张,从历史上看,多数都没有产生多大价值。少数精英追求效率,实现自我认知,他们活在现实中。但大部分人是需要围绕一个东西转的。不管这些东西是宗教、小说、爱情还是今日头条,用户是需要一些沉迷的,我不认为打德州、喝红酒和看八卦、视频有多大区别。” [24]以服务大多数人为目标,认为人“需要一些沉迷”刻意与“媒体精英”拉开距离,这也许是以算法名世的互联网公司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媒体”的重要原因。
三、算法与“用户”:过滤后的“信息茧房”
在行动者网络中,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算法与人类行动者的关系也是“互为主体”的,一方面,算法依据对每一个用户的阅读习惯和内容进行数据收集,“算出”用户的需求,对用户进行个性、精准的推送服务;另一方面,用户对接收内容的点击浏览等行为又在不断“修改”着算法的下一次推送。用户既具有主动性,又是被动的,用户和算法同时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中。
具体来说,算法根据用户的行为数据建立用户的兴趣标签推送匹配的内容,形成用户的媒介环境,用户获取内容后,点击、浏览、评论等行为都会作为数据反馈给算法,每一次搜索和点击行为都会不断更新算法对用户建立的信息模型,用户模型的每一次更新都会精准化推荐内容。由于用户的行为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为了保证推荐内容的精确性,算法自身也需不断更新,其所连接的网络也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用户行为的动态变化导致算法的改进,而算法的改进带来推送内容的变化改变了用户的行为。[25]算法与用户的实践呈现着结构二重性特征。
但是,这种高度重视用户需求的算法推荐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信息的闭环。由于每一次推荐系统的推荐都是建立在之前用户行为数据的基础上,搜索、点击、评论、点赞等行为算法都默认为读者的兴趣。换言之,用户点击什么,算法就会默认用户对该内容感兴趣,并给用户推荐相似内容,相似内容的大量推送导致用户点击量越多,点击量的增加造成推荐系统的持续推荐,形成一个顽固的循环。[26]即使用户的兴趣是多元化的,推荐系统能够做到覆盖用户感兴趣的内容,但是持续内容同质化的推送造成内容输出多样性的减少。每个人不同的头条,虽然传递了每个人想要的信息,却仅覆盖用户个人的兴趣点,没有与用户意见相左的信息,也没有可以使用户视野开阔的信息,算法成了一个“过滤气泡”,[27]为每个人量身定制过滤器,使每个人都成了一座信息孤岛,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区隔。
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他认为,公众的信息需求,并非是全方位的,往往是跟着兴趣走,“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根深蒂固”,[28]我们将不可能考虑周全,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算法通过单一化、同质化的信息推送不断在加固这种“信息茧房”,茧房可能是在“工作场所、学校、邻居之中”,[29]互联网扩大了它的范围,将人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隔绝了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和多元化的世界。这种所谓的“千人千面”实质上造成了“单向度的人”。
结语
早在二十年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在《数字化生存》中预言了一份可以高度定制化、个性化的“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尼葛洛庞帝充满遐想的写道:“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份报纸, 那就是把它看成一个新闻的界面……想想看, 未来的界面代理人可以阅读地球上每一种报纸、每一家通讯社的消息, 掌握所有广播电视的内容, 然后把资料组合成个人化的摘要。 这种报纸每天只制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这份报纸将综合了要闻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消息, 这些消息可能和你认识的人或你明天要见的人有关, 或是关于你即将要去和刚刚离开的地方,也可能报道你熟悉的公司。你可以称它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 [30]今天,“我的日报”已经成为现实,算法充当了所谓的“界面代理人”。如果技术逻辑也是一种“天命”的话,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在这二十多年中的发展正是循着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连接万物的路径奔腾向前。作为一个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算法,正在和人类的传播活动编织在一起成为新型的“行动者网络”。并且它正在悄悄改变人类的传播活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改变人本身。
罗马神话中有一尊名叫雅努斯的神,前后各有一副面孔,一张脸看向过去,一张脸注视着未来;一手拿着开门的钥匙,一手握着警卫的手杖。今天,与人类所相遇的现代技术,正如这尊两面神,有着截然不同的面孔。在传统的技术观念中,技术是人类的一种工具,本身并无价值观。正如米切姆所说:“关于技术的流传最广的老生常谈是: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它是中性的,其价值完全由使用它的人决定。” [31]但是,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并不只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造物、过程或科学理论,而是面对现代世界的整个意志态度”。“现代技术是一种实践的意志”。[32]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技术并非是对象化的“物”,在现代社会,“技术”已成为无冕之王,人生存的本源已不再是“存在”而是“技术”。技术将存在挤出世界,使自己成为这一世界的主宰。技术的本质是“Ge-Stell”(座架、框架):“座架摆置人,亦即挑动人把一切在场者都当作技术的持存物(Bestand)来订造(bestellen),就此而言,座架就是以大道的方式成其本质的,而且座架同时也伪造大道(verstellen)。因为一切订造看来都被引入计算性思维之中了,从而说着座架的语言。说受到挑动,去响应任何一个方面的在场者的可订造性。” [33]在这样一个技术时代,媒介不再仅仅充当人类器官的延伸、想象的延伸,或者充当人的工具和手段。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的媒介不仅摆脱了人,具有自主性,反过来以“座架”的方式规制人,塑造人,控制着人和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熟悉的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并没有道出技术时代媒介的本质,也许,这句话应该改写成——“人是媒介的延伸”。■
①[22]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第10页,2017年
②③[24]宋玮:《对话张一鸣:世界不是只有你和你的对手》,《财经》2016年12月14日
④人民日报评论部:《算法盛行,更需“总编辑”》,《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1/2016/1223/c78779-28971392.html
⑤王俊煜:《如何看待张一鸣的〈财经〉采访?》,知乎2016年12月22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658703/answer/136690009
⑥王佳航:《数据与算法驱动下的欧美新闻生产变革》,《新闻与写作》2016年12期
⑦彭兰:《机器与算法的流行时代,人该怎么办》,《新闻与写作》2016年12期
⑧方师师:《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围绕“Facebook偏见门”事件的研究》,《新闻记者》2016年第9期
⑨郝雨,李林霞:《算法推送:信息私人定制的“个性化”圈套》,《新闻记者》2017年第2期
⑩David Beer: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 Participatory web cultur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new media&society,2009Vol11(6):985–1002
[11][20][25][26]Philip M.NapoliAutomated Media: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Perspective on Algorithmic Media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Communication Theory,2014(24)
[12]Natali Helberger: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Algorithmic Profiling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readers and the Media,Javnost/The Public,2016(4),23(2):188-203.
[13]Fenwick,McKelvey:Algorithmic Media Need Democratic Methods: Why Publics Matter,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4
[14]成素梅,《拉图尔的科学哲学观——在巴黎对拉图尔的专访》《哲学动态》2006年第 9期
[15][17][19]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6]Couldry NActor-network theory and media:Do they connect and on what terms?.Hampton Press Inc2008
[18]王增鹏:《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科学与社会》2012年第4期
[21]《今日头条和他的“敌人们”》,《南方都市报》2014年7月7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D/html/2014-07/07/content_3273850.htm?div=-1)
[23][美]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E Pariser: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Penguin Group,201145(2)
[28][29]桑斯坦著,毕竞悦译:《信息乌托邦》第10、97页,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0]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第175-176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31][32]米切姆,《技术哲学》,选自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第30、34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3]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走向语言之途》,选自《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143-114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姜红 鲁曼/姜红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鲁曼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成果,编号为13BXW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