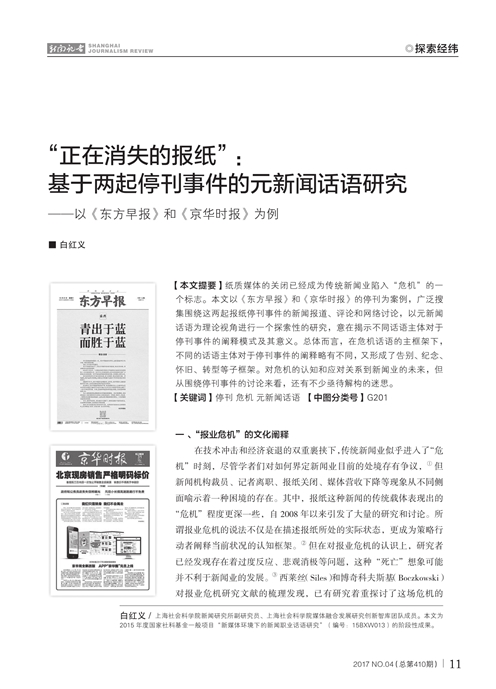“正在消失的报纸”: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
——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
■白红义
【本文提要】 纸质媒体的关闭已经成为传统新闻业陷入“危机”的一个标志。本文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的停刊为案例,广泛搜集围绕这两起报纸停刊事件的新闻报道、评论和网络讨论,以元新闻话语为理论视角进行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意在揭示不同话语主体对于停刊事件的阐释模式及其意义。总体而言,在危机话语的主框架下,不同的话语主体对于停刊事件的阐释略有不同,又形成了告别、纪念、怀旧、转型等子框架。对危机的认知和应对关系到新闻业的未来,但从围绕停刊事件的讨论来看,还有不少亟待解构的迷思。
【关键词】停刊 危机 元新闻话语
【中图分类号】G201
一 、“报业危机”的文化阐释
在技术冲击和经济衰退的双重裹挟下,传统新闻业似乎进入了“危机”时刻,尽管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新闻业目前的处境存有争议,①但新闻机构裁员、记者离职、报纸关闭、媒体营收下降等现象从不同侧面喻示着一种困境的存在。其中,报纸这种新闻的传统载体表现出的“危机”程度更深一些,自2008年以来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所谓报业危机的说法不仅是在描述报纸所处的实际状态,更成为策略行动者阐释当前状况的认知框架。②但在对报业危机的认识上,研究者已经发现存在着过度反应、悲观消极等问题,这种“死亡”想象可能并不利于新闻业的发展。③西莱丝(Siles)和博奇科夫斯基(Boczkowski)对报业危机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着重探讨了这场危机的根源、表现形式、社会影响以及解决之道。两位作者建议未来应引入过程、历史、比较和意涵等研究视角,这里所说的意涵是指加强对报纸衰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涵的理解。④亚历山大(Alexander)也批评了既有研究从技术和经济角度对危机的狭隘阐释,提出从文化的维度理解当前的新闻业危机。⑤与上述转向有所呼应,已有研究者从下列三种实际存在的新闻业现状着手,展开对报业危机的文化意涵的思考。
第一,从新闻记者离职的角度。新闻行业遭遇的结构性困境已然成为全球新闻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也导致大量新闻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新闻行业。厄舍(Usher)以美国离职新闻人发表的告别信、演讲、专栏和博客文章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离开新闻行业之时的最后思考。作者发现,这些离职的新闻人倾向于把当前新闻业的困境归咎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力量的侵蚀,而很少反思自己在变动的媒介环境中的职业观念和实践。⑥斯波尔丁(Spaulding)则主要考察了2009年被《巴尔的摩太阳报》解雇的员工们的“告别叙事”(goodbye narratives),这些个体化的叙事表达了作者们对他们工作与新闻专业的依恋之情,同时也反映了组织衰落产生的不利影响,怀旧在阐释共同体的告别话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⑦与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离职新闻人也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告别书。笔者对12位中国离职新闻人的告别文本进行研究后发现,离职新闻人总是会从自己为何进入新闻业开始追溯,怀旧充斥在对个人职业生命史的回顾中。在集体怀旧中,他们的告别话语有意将过去与当下的新闻环境进行对比,凸显新闻业所面临的困境。⑧陈敏和张晓纯对52位离职新闻人告别信的内容分析则发现,他们将离职原因归结为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四个方面,并在对个人职业经历的讲述中抒发着“黄金时代”不再的感慨。⑨
第二,从新闻室迁移的角度。美国很多报社进行了新闻室的搬迁工作,放弃原来作为城市地标存在的宏伟的总部大楼,选择更小、更便宜的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甚至有报社搬去了郊区。那些没有这样做的报纸也开始从他们的写字楼中腾出空间用于对外出租。哥伦比亚大学TOW数字新闻中心已经记录了35家报社的迁移,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中。⑩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室的搬迁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持反对态度,认为旧址代表着新闻业的传统,离开就相当于主动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另一种则持赞赏态度,认为新地址预示着新希望。不过对于报社是否可以搬去郊区,新闻工作者的态度较为一致,他们强调了留在市中心的必要性,不仅在象征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因为新闻网的设置,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如果因为远离新闻源导致新闻报道不能及时跟进,更无法维系报纸的权威性。厄舍认为,新闻室的迁移对记者和公众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记者不能适应,新闻室仍旧被怀旧的氛围笼罩,他们也许不能像以前一样提供重大而新鲜的新闻报道,也将失去其在城市新闻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也最终会影响公众能从传统新闻业那里获取的新闻类型。随着新闻机构的衰落,公众也许会对报纸失去兴趣,并忘记其在共同体中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11]第三,从报纸停刊的角度。卡尔森(Carlson)以“范式修补”(paradigm repair)为核心概念对两份因经营不善而关闭的失败报纸(failed newspapers)在最后一期所引发的新闻界的讨论进行了研究。作者发现,新闻共同体把两份报纸的关闭界定为一个危险信号,这不是两份报纸的个体失败,而是报业坚守的新闻范式正在遭到在线新闻的挑战,需要通过二级修补(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来保卫它的核心价值。[12]卢恩戈(Luengo)对一份停出纸质版而专注于新闻网站的美国报纸研究后认为,这种转变放弃了报纸对深度、准确和原创等价值的坚守,而是以煽情报道迎合增加流量的需要,对新奥尔良的记者共同体和市民共同体都构成了威胁。[13]吉莱维茨(Gilewicz)对四份失败报纸在最后一天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其中两家关闭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两家关闭于2009年。记者们运用集体记忆来勾连他们工作的意义,具体运用了两种技巧:一种是回顾式记忆(retrospective memory),“制造”他们报纸关闭在当下的意义;一种是前瞻式记忆(prospective memory),强调他们的工作为何及如何在未来仍然得到纪念。[14]尽管切入的角度上有所不同,但上述三类研究共同使用了一种文化阐释视角,通过强调新闻业的文化建构来“制造意义”。[15]如果说,新闻人的流动和新闻室的迁移只是间接地表明了报纸危机的存在,那么报纸的停刊则是一个直接的衰退信号。报纸杂志停止出版在国外已是司空见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失败的新闻媒体退出市场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商业行为。只不过,在新媒体技术的强烈冲击下,失败报纸的出现又有了新的文化意涵。而在中国,报纸停刊不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无论是停刊的原因、还是停刊的后果都有显著不同,为我们透视中国情境下的报业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报纸杂志的停刊在中国新闻界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2014年1月1日,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新闻晚报》成为两大报业集团合并后被关闭的第一家报纸,“媒体札记”称其为“纸媒的黄昏”。[16]此后三年报刊停刊消息不绝于耳,就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1月1日,又有北京的《京华时报》和上海的《东方早报》两份都市报正式停刊。虽然纸媒关停渐成行业常态,人们已经习惯了类似消息的发布,但《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的停刊还是令业界颇感震动,成为2016年度传媒行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7]尽管遭到关闭的报纸已不在少数,但却很少有研究关注这些报纸。
报纸的关闭首先是它自身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critical moment),无论是对作为组织的报社,还是作为职业共同体的新闻工作者都具有重大意义,对阅读这份报纸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其次,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背景来看,一南一北两份标志性报纸的停刊折射的是技术、商业、资本、专业乃至政治等不同价值的考量,成为新闻业转型过程中的最新案例。在许多针对停刊的评论中,都将两报的关闭视为报业危机继续深化的标志,一个最主要的理由与两报在报业市场的地位有关,两报分别立足于国内两大报业重镇北京和上海,无论在经济市场还是舆论市场都有着不俗的影响力。在两报正式关闭的日子前后,关于停刊的讨论则达到了一个最高点。两个阶段的讨论基调有所不同,前一阶段更多关心具体信息,如停刊原因、后续安排等;后一阶段则更多的是情感的表达,惋惜、怀念等情绪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流传。本文就以这两个阶段的报道、评论和讨论为经验材料,以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为理论视角对此次停刊做出分析。
元新闻话语是由美国学者卡尔森提出的一个旨在概述行动者如何协商记者作为新闻事件合法记录者的文化权威的分析概念。在他看来,新闻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嵌入在特定语境中的文化实践,在持续发布关于周遭世界变动情形的同时还在话语场域内建构新闻业及其社会位置的意义。“元新闻话语”就是对这个话语场域的描述,它可以被定义为对新闻文本、生产实践及接收条件的公共表达,在这里每个人可以公开地参与到建立定义、设定边界以及判定新闻业合法性的过程。[18]这个概念的核心是分析公众对新闻业的讨论所蕴含的文化意涵,研究者已经将其拿来分析过新闻越轨、[19]报纸的衰落、[20]新闻初创公司的创业宣言、[22]媒介批评、[23]媒介把关、[24]超链接 等具体的问题。
本文对停刊报纸的关注受到了卡尔森和吉莱维茨所做研究的启发,但两位作者在具体方法上有所不同:卡尔森主要以新闻界对报纸关闭的讨论为分析对象做话语分析,吉莱维茨则基本以四家报纸停刊前最后一天的内容为研究对象进行内容分析。本文则希望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既对停刊报纸最后一天的内容进行研究,也要分析新闻界对停刊这一关键事件的讨论,借此分析新闻界如何阐释报纸停刊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25]具体研究下列两个问题:其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新闻界如何报道、分析和讨论两份报纸的停刊?其二,这些报道、分析和评论对于我们理解变迁时刻的中国新闻业有何意义?
三、停刊事件的不同阐释
通过检索两张报纸停刊前后的新闻报道、评论以及相关的微博微信,本文根据叙事主体的不同,将告别叙事分为四种类型:报纸、员工、同行、读者。虽然说报纸停刊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的行为,但此前关闭的报纸却少有像《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这样在报业市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报纸。因此,两份报纸的停刊引起了新闻业界的热议,报纸自身、报社员工以及新闻界同行处在话语场域中的核心位置。在此之外,鉴于停刊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影响,[26]也使得读者对于停刊的反映必须被纳入进来。这些不同的叙事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对报纸关闭做出了叙事,这些叙事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意义。
1.报纸
报纸停刊前的最后一期具有十分重要的仪式意义,它正式宣告了报纸的“死亡”。报纸会在这一天制作特刊以表纪念,如重新刊登以往报纸的头版、回顾报纸刊发过的重要报道、集纳各界对报纸的纪念等。最后一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遇,讨论记者如何在停刊这一影响深远的时刻阐释和呈现他们工作的意义。[27]然而,中国的报纸在停刊时很少制作专门的告别特刊,大多数停刊的报纸只是在头版上以休刊词或致读者等形式发布停刊公告。与之类似,《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在停刊前最后一天(2016年12月31日)除了发表致读者外,版面内容并没有过多渲染“最后一天”的情绪。
除了在头版发布停刊启事外,两报的版面安排与内容并未做太多特别的安排。《东方早报》从2016年开始,双休日不再出版新闻版,只有提前制作好的周刊。[28]12月31日是星期六,虽是报纸出版的最后一天,但依然按照计划刊登了《身体》周刊。报纸在头版刊登“敬告读者”《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一文,宣布正式停刊:“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东方早报决定从明天,也就是2017年1月1日起,不再出版纸质版。” [29]剩余的15版均为《身体》周刊的内容。《京华时报》当日共有24版,头版、要闻、综合、北京时事、国际、文娱等正常版面均有体现,其内容与平日并无二致。与“东早”相同,该报在头版发布“致读者”《我们只是转身 我们不会离去》,文中称:“明天,《京华时报》将不再用白纸黑字为您记录昨天。但《京华时报》的白屏黑字,将继续与您为伴。” [30]在这篇致读者下方,还有一条消息:《京华网全新改版 APP“京华圈”元旦上线》,着重报道的是该报在新媒体业务方面的最新进展,“面貌一新的京华网已完成改版,全新APP‘京华圈’客户端1.0版正式上线。” [31]此外,该报在22版还有一条《休刊公告》,主要发布对纸质版订户的后续安排。在文字之外,还有两个广告版面也与停刊有关,一则主题为“蜕变”,发布官网和二维码。[32]另一则主题为“新征程 新出发”,图片下方为“泸州老窖向坚守新闻一线的京华时报人致敬”。[33]但实际上,这条广告也在其他报纸上出现过,刊登时图片上的小字也会相应改为相关报纸的名字,显然并不是为了停刊而专门设计的广告语。[34]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报的第二版“声音”版上还有一篇京华时评,题为《让我们留存时间的景深》。[35]按照微信公号“录音笔”的解读,这也是一篇向读者告别的评论,文中说“告别,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全文的基调则是对过往的怀念。[36]两报在最后一天的版面与内容安排方面与平日里没有太大的区别,对本研究比较有价值的只有两篇致读者。致读者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告知,两篇文章采用了近乎相同的告别叙事(goodbye narratives)策略:一方面,正式宣布纸质报纸的终结,如“东早”:“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东方早报决定从明天,也就是2017年1月1日起,不再出版纸质版。” [37]《京华时报》则写道:“明天,《京华时报》将不再用白纸黑字为您记录昨天。” [38]另一方面,还对报纸的未来有所交代,强调纸质版的停刊并不代表报纸的终结。“东方早报虽然休刊了,但东方早报原有的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功能,将全部转移到澎湃新闻网。” [39] “2017年元旦,《京华时报》纸质版将休刊。同时,京华网、京华圈、京华微博、微信以及系列公号组成的《京华时报》新媒体矩阵,将为您即时推送新闻、资讯,为您更快地链接昨天、今天和明天,和您一起更多地与亲友分享,与陌生人碰撞。” [40]在这短短的启事里,两报还回顾了当年创刊的事情:“2003年7月7日,东方早报正式出版发行。13年里,东方早报与上海这座城市相行相伴,忠实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和进步。” [41] “2001年5月28日,京城诞生了一家全新的综合类新闻都市报,命名为《京华时报》。一篇篇关注民生、担当道义、传播真相的新闻报道,连接了千家万户。” [42]这些表述带有对报纸创刊至今的历史做出自我评价的意味,重申着“记录”“道义”“真相”等传统的新闻观念。
除了在报纸上发布上述启事外,两家报纸还在各自的官方微博账号上予以转发和公布,不过选择发布的内容不太一样。《东方早报》的博文选取了该报“敬告读者”中的内容,以“今天,我们不说再见”作为叙事核心,既宣布了停出纸质版的决定,又交代了报纸的去向,“从油墨飘香的报纸,全面转型为网络传播”。意在表明这只是一种存在形态的转换,希望把读者对“东早”品牌的认可转移到澎湃新闻上。[43]《京华时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当日发布的帖子只是简单提及报纸将正式告别纸质版,更多是在预告旗下的京华时报APP“京华圈”将于元旦正式上线。或许是因为叙事策略的不同,《东方早报》的微博共计获得1182次转发、367条评论和749个点赞,网友留下了大量的怀念和祝福话语。而《京华时报》的微博只获得了44次转发、47个评论和20次点赞,留言的不少读者关心的是已经订阅的报纸该如何退款。
2.员工
已有研究将离职记者对其所属新闻组织以及新闻工作的阐释视为一种告别叙事,虽是告别当下,但厄舍的研究着眼于新闻业的未来,而斯波尔丁的研究则试图在理解当下的同时纪念记者个体和集体性的过去。[44] “告别”也是两家报纸的工作人员讨论停刊事件的主要框架,叙事主体既包括那些仍在报纸工作的在职人员,也包括在停刊之前就已离开报纸的离职人员。在针对报纸的告别叙事中,记者们在对个人、组织及行业不同层面的叙述中,将新闻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勾连起来。
微信公号“冬枣树”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的文章,共汇集了285位报社员工以一人一句话的形式所呈现的他们与《东方早报》的故事。[45]冬枣树是一个“东早员工内部交流平台”,原本就是呈现报纸运作的后台内容。在停刊这样一个重要时刻,这篇汇集了众多员工告别话语的帖子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内部的在线记忆空间。[46]由于篇幅较短,记者们的话语大多数以抒发情感为主,而下面三类情感成为主要的表达基调:第一是怀念。有人采用直抒胸臆式的表达,如:“我们曾经为了理想艰难前行,那些闪亮的日子,愿永远记着。” [47] “13岁的东早就坐在那里,深情望去,满满都是自己3岁时风华正茂的影子。属于东早的光辉时代不会随年华逝去,只会随澎湃的浪潮继续奔腾向前。” [48]还有人通过细节将怀念具体化:“14年前,7月6日深夜(准确说是7月7日凌晨),做完版走在839号一楼,遇到一位很有艺术气质的男子,他问我从哪里来,暂住哪里,便打了一辆车把我送到当时住的招待所。那会他并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那个时间段出现的人应该就是冬枣人,那会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却永远记住了那张很艺术的脸。那一夜,这一幕,温暖着我此后14年的冬枣岁月。” [49]第二是感恩。在众多叙述中,叙事者往往将“东早”塑造为个人生活与事业中的关键环节。如:“我2009年就来了东早,7年过去了,这7年来,东方早报见证了从我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妈妈,东方早报,谢谢你。” [50] “从2003年创刊就一直相随,7月7日的创刊号上有一篇我的稿子,然后就在这里买房买车生子,13年的光辉岁月和东早一起经过,感谢它给了我想要的事业和生活,冬枣树依然还在,让我们继续澎湃。” [51] “从22岁到35岁,整整13年的青春岁月都在839号度过。在这里,我们哭过,笑过,又陆续恋爱,结婚,生子,共同成长,一起品味酸甜苦辣。” [52] “感谢东早将我从象牙塔带入职业生涯,让我认识到新闻的生命。有限的生命里,期待与你一起澎湃。” [53]还有人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真的真的只想深情地说一句‘谢谢你,东早……’” [54]第三是祝福。这两家停刊的报纸并没有彻底的“死亡”,而是试图将原有的报纸品牌转移到新媒体平台上,延续原有的生命。“东早”由于比较早地创办了澎湃新闻,转移的阵痛已经被消弭到很低的程度,更被视为传统媒体转型的一条理想路径。如张军认为:“与其说东早即将别离,不如究其根本,衡之为完成了跃迁——和它创设的www.thepaper.cn一体融合于未来,既往5000个日夜“求达于真理”之理想,将在更广大的时空里剑及履及,而再开生面。” [55]韩雨亭也说:“虽然大家将无法领略《东方早报》纸媒油墨之美,但我想《东方早报》的价值观与精神在‘澎湃新闻’的平台上得到了继承与发扬,甚至可以说社会价值放大了数倍。面向未来,澎湃前行。” [56]还有记者说:“虽东早暂别,但我们仍在一起。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澎湃前行。”在告别纸质版之际,“澎湃前行”一类的表述蕴含着记者们对新媒体平台的深深期许。
除了“冬枣树”外,具有浓厚“东早”背景的“梨视频”发布视频《〈东方早报〉的漫长告别》成为另一个集中呈现离职员工纪念话语的平台。在这段长为9分54秒的视频中,共有9位曾供职于《东方早报》的前员工讲述与这份报纸的情缘。其中多位是创刊时即已加入报纸,并在新闻行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如吴晓波、徐俊、简光洲、叶檀等。所谓“漫长的告别”是指“在它2016年底停止出版前,转型早已发生,漫长的告别是从创办数字媒体澎湃新闻开始的”。[57]由于是9个人的访谈内容的剪辑,在不同的叙事者和不同的主题之间切换,不过总的叙述主轴依然有些类似,叙述者以个体视角回顾与“东早”的关系变迁。
不同于“冬枣树”和“梨视频”这两个集中呈现的机会,笔者没有搜集到《京华时报》员工对该报停刊进行集体叙述的材料,只是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号上搜集到一些间接的、零星的情绪表达。一个总体的感受是,《东方早报》的员工在纪念这份报纸时有不舍,却少见感伤。而从搜集到的间接信息来看,《京华时报》停刊引发的悲伤情绪似乎更为浓烈一些。据记者站报道,在停刊前一天,“京华一直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许多前京华人赶来,相聚一起,拍照留念,相拥而泣”。报道还引用了一位京华员工怀若谷在微信朋友圈写的话,“天涯各处,望各自安好”。[58]在未来网的报道中,一位80后记者颇为伤感地说:“京华时报当年是很牛的报纸,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稿件,然后没了,瞬间就没了。太难受了!”一位在2016年初刚离开报社的员工也表示:“京华时报走到今天,很心痛也很悲哀,作为一个媒体的品牌价值已经做到了最好,纸媒突然消失,大家都接受不了。” [59]微博上一位叫“胡二刀”的用户转载了三幅现场图片,配上了“一份报纸的最后一个夜班。报人的笑容依然灿烂”的文字。[60]网友“宛若蓝天”以《京华时报》员工家属的身份在微博上记录了她的家人在报纸最后一天的经历:“今天陪峰哥去报社收拾东西,十六年了,好长又好短,人生有几个十六年,何况是这样陪伴一份报纸由创刊到辉煌到休刊的十六年,俗话说旁观者清,可为什么我这个旁观者在今天——《京华时报》的最后一天泪湿眼眶了,我不关心《京华时报》飞得高不高远不远,我只关心陪它飞了这么久的峰哥,曾为它笑过、哭过的峰哥会因它的消失伤心多久。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只祈祷让我们一起把阴霾扔在身后,重新启航,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61]一位叫“周海滨”的网友则在微博上自称为“2016最后一天最悲伤的人”,这是因为:“我在21世纪初分别上过班的《东方早报》《京华时报》今天都休停刊了。所以朋友给我发的休刊各种链接一直无力打开。也许我是两个报社唯一的共同员工。” [62]产生两种不同情绪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两张报纸虽然都走向了停刊的同一命运,但是即将面临的处境却不尽相同。《东方早报》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媒体平台“澎湃新闻”,在停刊之前刚刚获得6.1亿元上海本地国资的注入。而《京华时报》的前途似乎不太明确,在最初公布的方案中,《京华时报》原本是要彻底停刊,主管单位变更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人员则并入《北京晨报》。到了11月底,才有了停出纸质版、全面转型新媒体的最终方案。方案的变更与11月发布《京华时报社员工转岗交流工作启动》的消息引发的争议不无关系,也就是说,经过抗争后才有了转战新媒体的安排,匆忙上马的新媒体项目前景如何尚未可知。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加深了《京华时报》员工们的伤感情绪。
3.同行
如果说报纸员工的告别叙事以抒发感情为主,那么,新闻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则着力于对所谓的新闻业危机的阐释。一般而言,新闻界对于报业危机的阐释以两种形式予以展现:一种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将报业危机本身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议题进行报道;另一种则是通过行业报刊、社交媒体等平台对相关的危机事件进行评论。笔者并未搜集到太多传统媒体对两报停刊的报道,反而是一些新兴的数字媒体如网站、微信公号对停刊进行了非传统意义上的报道。所谓非传统意义,除了指发布报道的主体不是传统媒体外,还指报道的形式也不再是规范的原创报道,而是编辑收集各方面信息进行的聚合报道(news aggregation)。在对停刊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中,对事件的诊断(diagnosis)和回应(response)成为两个最突出的面向。[63]诊断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界定报纸在当下所处的“危机”程度,其次是对导致陷入这种状态的原因进行分析。如一篇文章所说:“《京华时报》的关停足以成为反映纸媒处境和现状的标志性事件,也似乎预示着处于第一梯队的纸媒的未来。”而且,“《京华时报》的关停就像打开了某个口子,可以想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更多第一梯队的纸媒面临和《京华时报》一样的结局”。[64]在描述两报的困境时,一种常见的叙事策略是回顾报纸曾经的辉煌,进而凸显出停刊的无奈。比如《京华时报》在创办之初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人民日报办了《京华时报》,这等于中央机关报创办都市报,这就确立了都市报在全国、在党的正统观念里的地位。” [65] “在15年的时间里,其发行量曾经稳占北京早报市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北京地区名副其实的‘大报纸’。” [66]《东方早报》同样取得过不俗的口碑。“身为政经综合类报纸,《东方早报》以内容高端、有品位著称,是国内都市报中内容的佼佼者,也是上海都市报中名气最大、美誉度最高的报纸。”尤其不可不提它的一些经典报道,“2008年因为首报“三鹿奶粉”事件,该报揭开了“三鹿奶粉事件”的盖子,而“深度、独家”的报道也因此成为东早的特色。” [67] “尤其是“揭发三聚氰胺”一案,让全国感受到了这份“影响力至上”大报的强力,而其推出的各类文化副刊(《上海书评》《艺术评论》),也在多个文化层面上筑造了中国在北京之外的,另一个文化高地——上海的文化堡垒。” [68]这些评论从经济效益、发行量、报道影响力等多个层面证明了“在过往20年报业的‘小黄金时代’里,这两份报纸都算得上是‘一线都市报’品牌”。[69]因而它们的停刊是中国报业市场上的一件大事,接下来要分析的则是报纸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什么?《好奇心日报》以《16 年间,大报梦想的诞生与消逝》为题对东早创刊到停刊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报道,文章将简光洲、徐俊等人的个体变迁与“东早”这一份报纸的兴衰起落勾连起来,最重要的目的则是为这份原本号称要做“百年大报”的报纸的梦想消逝而寻找出原因,结论正如文章的提语所写:“技术革命、话语权的转移、越来越强势的管控,同时扼住了这个行业。” [70]微信公号“录音笔”则对《京华时报》的创办者朱德付进行了专访,以其个人视角解读《京华时报》停刊的必然性,“是体制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在他看来,报社作为个体是无法抵挡移动互联新闻的大势的。[71]最极客的分析列举了三点原因:广告营收困难、读者流失严重、纸媒内部抱残守缺。[72]一位做过记者的知乎用户提出,传播渠道的变迁、市场化报社的体制问题、人员问题等原因是造成整个行业出现困境的原因。[73]詹国枢则认为“京华关张,迟早的事”,他的分析指向了市场化的都市报存在的根本性难题:“倘若你信息不快,深度不深,批评很少,套话很多,真话稀缺,假话盛行,人家怎么还会自己掏钱,买这样一份没啥用处的报纸?” [74]这一观点实际上重申了报纸在现代社会立足的价值所在。
回应则涉及新闻业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标志性报纸的停刊以及如何为当前的报业危机提出解决方案。叙事者普遍认为,停刊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并将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步其后尘。“《京华时报》的关停,让这些处于第一梯队的都市报,终于能够看见自己的未来,不再死撑下去,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数年时间中,会有更多处于第一梯队的都市报停刊。” [75]对报纸和新闻人来说,这一代价极为惨痛。但是,“媒体的转型,一定是‘蜕皮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徐世平在东方网新年献辞中写道:“如果我们依然停留在停刊的悲怆回忆之中,怀旧‘共同的记忆,那才真的是我们媒体人的时代悲哀。” [76]因此,重要的是继续探索纸媒转型的路径,“一曲悲歌之后如何继续奋力前行,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77]两报的停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彻底关闭,而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更换了内容生产的平台和形式。区别在于,《东方早报》此前已经创立了澎湃新闻网,报纸关闭后全体人员将转向这个新媒体平台,而《京华时报》的新媒体业务仍在起步阶段。这种策略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评价,《东方早报》的转型被称为有先见之明,《京华时报》则被认为准备不足,“匆忙推出的APP体验很差,和上海澎湃相比中间隔的是生命”。[78]还有论者将两报的停刊放在中国报纸数字化的脉络下观察。窦丰昌概括了市场化报纸三种转型策略:一是“转业”,好听一点的说法是“转变行业”,难听一点就是“关闭报纸去干别的行当了”,如已经停刊的《今日早报》等报。二是“转型”,把原来以纸质媒体的报业形态转型为以新媒体为主的媒体形态,也就是所谓的“新型主流媒体”以及“新型主流媒体集团”。这是最优选择,但难度最大。三是“转场”,与“转业”不同,干的还是媒体的行当,只是把主阵地从纸质媒体转移到了新媒体上面,工作场地不同,但业务模式没有变。《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都属于第三种模式,属于最为务实的选择。[79]高渊在《纸媒不死,只是渐凋零》一文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议,而是讲述了三位资深媒体人的故事,提炼他们所具有的成功特质:根据曹景行的经历,作者认为:“媒体会生,媒体自然也会死。媒体人若想不死,或许有很多途径,但充满诚意地对待每一个字,投入地对待这个职业,始终是不二法门。”从胡锡进身上看到的则是:“如果说,什么样的纸媒是死不足惜的,或许就是远离公众关切和社会焦点的那一类。媒体人一旦‘失焦’,失去的将是基本的新闻价值判断,而这才是谋生之本。”张力奋的经历则表明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有效性。[80]这些体会对应的都是传统媒体时期所遵循、但在数字媒体环境下已经有所衰落的新闻范式,在危机关头,重新提起它们显然别有意味。类似的“规范性叙事的再确认”(narratives of normative reassurance)[81]话语在不少资深新闻人对报纸停刊事件的评论中屡屡看到。
4.读者
长期以来,报纸及其读者构成了一个所谓的“新闻业的共同体”(communities of journalism),[82]对地方性媒体来说尤为如此。以至于地方报纸关停的影响不仅停留在行业层面,甚至会深刻影响到当地的公共生活。[83]《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同为地方性的都市报,读者群以当地居民为主。但在新媒体时代,报纸内容的数字化传播已经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可以吸引全国范围内的用户阅读。报纸停刊原本是攸关新闻业生存与发展的行业议题,但在新媒体环境下,非新闻专业人士也能对此发表意义,将其变成公共议题。
每份报纸都面临着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个体因为教育、品味、兴趣等不同,对报纸停刊的认知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笔者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感性派,他们对报纸停刊表现出更加多元的情感表达,惋惜、留恋、失望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就在其个人公号撰文向《东方早报》致敬,只因为“这份定位影响力至上的报纸,编辑和记者们以10年如一日的努力,努力办一份对主流人群产生影响力的高品位日报,可以说她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仅仅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向她致敬”。章在文中通过描述三次接受《东方早报》采访的经历,展示了报纸如何“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构成我对自己个人生活史的记忆”。[84]与这篇文章中的温情不同,一位名叫“Summer160”的用户则对“东早”的停刊表达了强烈的失望之情,“2016年的最后一天,东方早报停刊了。失望,失望,失望。即便知道如今报纸业大势已去,但网络新闻稿与传统报纸文章的差异还是令我很难接受,不论标题、主旨还是配图,我都对前者整体上缺乏信任感。当初东方早报的犀利,澎湃以后还能延续吗?我看难。” [85]网友“何万蓬”在微博上写道:“东方早报@东方早报停刊,是文化之失,文化之憾,甚至文化之悲。纸媒之美,不是新媒体能全部替代的。” [86]也有网友提到,《东方早报》“是最早报道三聚氰胺的媒体”,但是“今后,还有谁给我们报道三聚氰胺”?[87]另一类观点可列为理性派,他们认为报纸停刊是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位叫王国华的深圳杂文家发表评论认为,报纸停刊就像饭店关门一样正常,“饭店可以倒闭,报纸倒闭了为什么要大惊小怪”?他也曾经把报纸尤其是都市报当成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记忆”。然而,“如果干脆把那些完全无用的报纸叫停,集中资源和人才办好一两家,像有些地方一样,一城一报,一城一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88]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也在其微博上发言:“以京华时报明年停刊为代表的不少纸媒陆续停印,好,纸媒总该让位互联网,尤其是图书和报纸太多的当下。许多时候,退出、减少和回归也是进步。” [89]这些观点都将报纸看作一种普通的产品,要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它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现象,很多网友坦承自己已经不看报了,“我以前订有三份地方报纸,现在一份也不订了,拿着手机,什么新闻都知道”。[90]一位网友说:“长时间没看报纸了,今天偶尔看了一下京华时报,确实没什么可看的。一份优秀的报纸办成了现在这样,那也是活该。” [91]尽管同为都市报,但是《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的风格存在很大差异。比较而言,《东方早报》以其颇具专业水准的报道成为具有“文化地标意义”的报纸。在知识阶层中很受欢迎,因此能看到不少学者、教授等知识分子在报纸停刊之际表达纪念之情。《京华时报》的办报思路则更贴近底层。对很多并不经常阅读两报的用户来说,提到前者往往是曾引发举国震动的三聚氰胺报道,后者则是与农夫山泉的那场“闹剧”。
四、停刊、报业危机及新闻业的未来
危机话语(crisis discourse)已经成为近年来讨论新闻业现状的主导框架。有研究者对美国新闻业危机话语的内容与文本分析发现,危机话语是一种使用了多种认知框架的符号表述。首先,调用认知框架将报业乃至新闻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状况指认为“危机”,然后在危机共识的主框架下,围绕危机的归因、表征、内涵与建议等特定主题形成子框架。[92]泽利泽(Zelizer)对美国新闻界的危机话语的批判性研究则指出,这样的框架为新闻从业者理解当前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认知框架,但是这样的话语可能将新闻业在新媒体兴起、公众参与、传统新闻业变迁的情境下所面临的挑战、条件、机遇、创新等遮蔽于同质化的表述之中。[93]尽管危机话语存在着这一风险,但不管其准确与否,它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危机话语’及其建构可以是一个认知的场所,通过对它的开掘,我们可以了解新闻界人士运用哪些话语资源来诊断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论述这些挑战的蕴涵、应对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他们所想象的新闻业的未来。” [94]报纸停刊作为报业困境的一个表征,对它的阐释也可列入新闻业危机话语的范畴。它渗透在不同叙事主体对于停刊事件的认知框架中,成为中国新闻界危机话语的一次集中呈现,并展现出下列三个特点:
第一,不同主体参与到有关新闻业的话语生产中来,尤其是非新闻行业行动者的介入丰富了事件的阐释。关于新闻业的话语生产一直是新闻从业者独享的权力,通过话语建构和使用,他们得以确立专业管辖权、厘清专业边界、塑造新闻权威。数字技术的发展则便利了新闻行业之外的新型行动者对以往封闭的新闻运作过程的介入,不仅能够影响到新闻媒体和记者对新闻事件的建构,也参与到新闻社群对新闻界内的行业、职业问题的讨论中来,成为元新闻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生产主体。就本文讨论的案例而言,不仅有与组织关系密切的在职员工和前员工,也包括其他媒体和同行,尤其是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以及阅读过两报不同形态报道的用户甚至只是单纯的网友。
第二,在危机话语的大框架下,不同的论述主体阐发的重点有所不同,又形成了各自的子框架。两份报纸在一个极具仪式意义的时刻,却并没有真正的仪式性的行为,比如以特刊的形式呈现自身的发展历程。因此报社自身对停刊的论述以事实宣告为主,可称之为告别话语。与记者们离职时发布的告别话语相比,这些以致读者形式出现的停刊词更少情感性的表达,而是单纯地陈述一个即将停刊的事实。报纸工作人员的论述以纪念为主,可称之为纪念话语。报纸的消亡也像那些著名新闻人的逝世[95]或退休[96]成为一次热点时刻,激发出大量的纪念话语。曾在两家报社工作的人员因为报纸在其职业生命史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投注了更为深厚的感情。就同行和读者而言,更多的站在相对中立的位置评判停刊事件的得失和意义,可命名为转型话语。当然,这种概括是一种理想型的分类,并不是说某类话语主体只能生产出特定类型的话语,而是不同类型的话语混杂在一起。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不仅是相关报社的工作人员以及离职员工在生产纪念话语,新闻界同行、读者也会成为纪念话语的生产者,但并不构成他们的主导话语。比如,在一些非个人的网站、微信公号上,作者通过重新发布两报过去的头版、重要报道等手段,运用这种对报纸的回顾式记忆建构一个告别的仪式。[97]第三,总体而言,对危机的阐释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情感表达多于理性分析。面对危机有两种叙事倾向:一是向后看,怀旧、纪念、告别等成为讨论的基调;另一是向前看,转型、改革、创新等词汇成为叙事的主轴。正是由于多元主体参与到危机的阐释中,两种叙事倾向在两报停刊事件的讨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浮现,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前者只是沉浸在对过往的怀念中,建构着“黄金时代”的神话,[98]将怀旧作为应对媒介变迁的方式。[99]后者则着力建构出一种“新媒体”神话,[100]似乎报纸只有转型为新媒体一条路,甚至将新媒体的转型方式单一化。这样的神话都无助于把握新闻业的未来,成为亟待解构的迷思。
泽利泽强调危机的本质是对不确定性的把握,它带来的不仅有挑战,也有机遇。[101]维斯伯德(Waisbord)则提醒人们,首先要厘清究竟什么是危机以及谁的危机。在他看来,与其说是新闻业的危机,不如说是报纸的危机更为准确,而且危机主要表现在传统新闻业的商业模式上,并未对新闻业的公共使命和社会角色形成颠覆性的挑战。[102]在西方新闻业,新闻初创公司的创业和传统媒体的创新成为两个突出的趋势。一方面是新闻初创公司作为新闻场域中的新来者,正在获得大投资商、风险资本和技术企业的青睐,将会在新闻产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103]另一方面则是创新不足的传统媒体难以适应新的新闻生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纸质媒体首当其冲,率先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新闻初创公司创立的初衷是因为深感传统的新闻范式在新媒体时代遭到了削弱,他们在新的数字平台重新以调查性新闻等优质内容为生存的根本。[104]在他们发布的创业宣言中,新闻的社会角色表达与旨在提升新闻的具体革新措施表述交织在一起。[105]与之相比,“商业主义构成了当下中国新闻业者在面对数字化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时所形构的话语的核心”,对创业、盈利模式等概念的广泛运用表现出单一的商业化维度,曾经作为一股解放力量的专业主义已黯然退场。[106]与此前彻底关闭的报纸不同,《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并没有完全地退出新闻市场,而是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东方早报》率先成立了新闻初创公司,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媒体平台“澎湃新闻”,抛弃纸质形态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而《京华时报》仓促上马,向新媒体转型的效果有待观察。至少从停刊两个月后,其主打新媒体产品“京华圈”的内容生产和下载数据来看难言满意。与此同时,[107]对《东方早报》的转型策略也要理性看待。尽管澎湃新闻被视作一次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在短时间内引发了一股模仿热潮,九派、封面、上游等传统媒体打造的新闻客户端纷纷出炉。但也有研究指出,澎湃新闻还是传统的“我出版你阅读”模式,在商业模式、新闻业务等方面的创新仍然有限。[108]新闻初创公司要想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不仅是生产平台的更新,还要在新闻业务、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等方面进行创新。当然,创新的路径也并非只有一条,有的力求新颖,有的则要回归传统。2017年2月13日,《广州日报》和《晶报》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改版。前者在改版宣言中提出:“要重新回到新闻本源,从基本做起、从专业做起,下苦工夫、笨工夫,花时间、花脑子,做好策划采访,编好稿件标题,去伪存真,删繁就简。” [109]后者则从《东方早报》彻底告别纸质版整体转入“澎湃新闻”并获得国资加持中获得启示:“其能走出转型新路,归根结底就四个字——坚守内容。” [110]
五、结语
本文以国内两份知名都市报的停刊事件为案例,通过对不同主体在这一仪式性时刻的阐释进行了分析。论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其一,是研究主题;其二,是研究路径。就研究主题而言,本文把两份报纸的停刊视为一个关键事件:在报纸层面,它是报纸发展历史中的一次巨大变故;在个人层面,它是报社员工职业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行业层面,它也是反映行业现状、影响行业发展的重要事件。就研究路径而言,本文借用了元新闻话语的理论概念。与笔者此前使用的新闻职业话语[111]以及其他研究者使用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112]聚焦于新闻记者对新闻、职业和工作的讨论不完全相同,元新闻话语的突出特征是强调了论述主体的多样性,既包括新闻行业内的传统行动者如新闻机构和记者,也将非新闻专业的行动者如泛新闻机构、读者或用户等纳入进来。可以预见到,类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阐释的案例将会频繁出现,这种方法也将会有更多的具体运用。但归根结底,无论是新闻职业话语还是元新闻话语,关切的问题是一致的: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脉络中,新闻业如何建构关于自身的话语,又是如何被其他社会实体进行建构的,以及这种建构将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①Zelizer,B.(2015).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888-908.
②Brüggemann, M.HumprechtE.NielsenR. K.KarppinenK.Cornia, A.& EsserF.(2016).Framing the Newspaper ‘Crisis’. How Debates on the State of the Press are Shaped in FinlandFrance, GermanyItaly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Studies17(5)533-551.
③ChyiH. I.LewisS. C.& ZhengN. (2012).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Examining How Newspapers Covered the Newspaper Crisis. Journalism Studies13(3)305-324.
④Siles,I.& Boczkowski,P.J.(2012).Making sense of the newspaper crisi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an agenda for future work.New Media & Society14(8)1375-1394.
⑤周红丰、吴晓平:《重思新闻业危机:文化的力量——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的文化社会学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⑥Usher,N.(2010).Goodbye to the news: How out-of-work journalists assess enduring news Values and the new media landscape.New Media & Society12(6)911-928.
⑦Spaulding,S.(2016).The poetics of goodbye:Change and nostalgia in goodbye narratives penned by ex-Baltimore Sun employees.Journalism17(2)208-226.
⑧白红义:《“下个路口见”:中国离职新闻人的告别话语研究》,强荧、焦雨虹主编:《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5)》第280-29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⑨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⑩Usher,N.(2014).Moving the Newsroom: Post-Industrial Spaces and Places. New York: ColumbiaJournalism School.
[11]Usher,N.(2015).Newsroom moves and the newspaper crisis evaluated: spaceplaceand cultural meaning. MediaCulture & Society37(7)1005–1021.
[12]Carlson,M.(2012).Where Once Stood Titans: 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 and the Vanishing U.S. Newspaper.Journalism13(3)267-283.
[13]LuengoM.(2014).Constructing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15(5)576-585.
[14]GilewiczN.(2015).To embody and to embalm: The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final editions of failed newspapers. Journalism,16(5)672-687.
[15]Berkowitz, D.A.& Zhengjia,Liu.(2014).The Social-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s: From Doing Work to Making Meanings.In R.S.Fortner & P.M.Fackler(Eds.)Th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pp.301-313).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16]徐达内:《媒体札记:纸媒的黄昏》,FT中文网2013年12月2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093?full=y。
[17]周志懿:《【盘点2016】中国报业十大标志性事件》,人民网2016年12月15日,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1215/c14677-28952437.html;朱学东:《再见,2016——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FT中文网2017年1月3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817?full=y。
[18]Carlson, M.(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19]Carlson, M.(2014). Gone, but not forgotten: Memories of journalistic deviance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Journalism Studies15(1)33-47.
[20]Carlson,M.(2012).Where Once Stood Titans: 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 and the Vanishing U.S. Newspaper.Journalism13(3)267-283.
[21]Carlson,M. & UsherN.(2016).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For-profit digital news startup manifestos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4(5)563-581.
[22]Carlson, M.(2009). Media criticism as competitive discourse: Defining reportage of the Abu Ghraib scand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33(3)258-277.
[23]Carlson, M.(2015). Keeping watch on the gates: Media criticism as advocatory pressure. In T. Vos & F. Heinderyckx (Eds.)Gatekeeping in transition (pp. 163-179). New York: Routledge.
[24]MaeyerJ.D.& Holton,A.E.(2016).Why linking matters: A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ism17(6)776-794.
[25]卡尔森对记录片Page One的研究使用的方法为本文提供了参考,他对这部反应危机中的《纽约时报》的纪录片的研究,既涉及到记录片本身的内容,又引入了新闻界对这部记录片的讨论。参见:Carlson, M.(2016).Telling the crisis story of journalism: Narratives of normative reassurance in Page One. In J. C. AlexanderE. Breese & M. Luengo (Eds.)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From technology to culture (pp. 135-1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Schulhofer-WohlS.& GarridoM.(2013).Do Newspapers Matter? Short-Run and Long-Run Evidence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Cincinnati Post.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26(2)60-81.
[27]GilewiczN.(2015).To embody and to embalm: The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final editions of failed newspapers. Journalism,16(5)672-687.
[28]大鸟:《告别〈东方早报〉,是媒体融合进程的关键一步》,微信公众号“新闻记者”2016年12月28日
[29]《东方早报》:《敬告读者》,2016年12月31日头版
[30]《京华时报》:《致读者》,2016年12月31日头版
[31]《京华时报》:《京华网全新改版 APP“京华圈”元旦上线》,2016年12月31日头版
[32]《京华时报》:广告,2016年12月31日第3版
[33]《京华时报》:广告,2016年12月31日第f01版
[34]编前会:《今天,不说再见》,微信公号“编前会”2016年12月31日
[35]《京华时报》:《让我们留存时间的景深》,2016年12月31日第2版
[36]《京华时报》:《让我们留存时间的景深》,2016年12月31日第2版
[37]《东方早报》:《敬告读者》,2016年12月31日头版
[38]《京华时报》:《致读者》,2016年12月31日头版
[39]《东方早报》:《敬告读者》,2016年12月31日头版
[40]《京华时报》:《致读者》,2016年12月31日头版
[41]《东方早报》:《敬告读者》,2016年12月31日头版
[42]《京华时报》:《致读者》,2016年12月31日头版
[43]东方早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名称在12月31日前已更改为“澎湃视频”。该报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于12月23日更名为“澎湃视频”。
[44]Spaulding,S.(2016).The poetics of goodbye:Change and nostalgia in goodbye narratives penned by ex-Baltimore Sun employees.Journalism17(2)208-226.
[45]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46]白红义:《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南都口述史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2期
[47]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48]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49]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50]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51]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52]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53]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54]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55]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56]冬枣树:《我们和我们爱的东早:不说再见,澎湃向前》,微信公号“冬枣树”2016年12月31日
[57]梨视频:《东方早报的漫长告别》,2017年1月27日,http://www.pearvideo.com/video_1029367。梨视频由前东方早报社长、澎湃新闻CEO邱兵领衔创办,其创始团队人员也多来自东早和澎湃。
[58]记者站:《京华时报休刊致读者:我们只是转身,我们不会离去》,2016年12月31日,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58604461275641
[59]杨佩颖:《京华时报今夜无眠:大家都在笑 最好的青春在这里》,未来网2016年12月31日,http://news.k618.cn/dj/201612/t20161231_9919005.html
[60]新浪微博“胡二刀”,2016年12月31日
[61]新浪微博“宛若蓝天”,2016年12月31日
[62]新浪微博“周海滨”,2016年12月31日
[63]Carlson,M.(2016).Telling the crisis story of journalism: Narratives of normative reassurance in Page One. In J.C.Alexander, E.Breese & M.Luengo (Eds.)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From technology to culture (pp. 135-1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4]最极客:《〈京华时报〉终成“烟云”,纸媒适应互联时代或能“向死而生”》,搜狐公众平台2016年12月30日,http://mt.sohu.com/20161230/n477399470.shtml
[65]刘洋:《〈京华时报〉创刊者朱德付:我知道会有这一天》,微信公众号“录音笔”2016年12月31日
[66]王弘:《京华时报停刊 纸媒还有机会吗?》,媒体训练营2016年11月8日,http://it.sohu.com/20161108/n472648562.shtml
[67]张耀升:《2017年1月1日起再也看不到的报纸:南东早北京华》,搜狐新闻2016年12月30日,https://m.sohu.com/n/477405408/
[68]令狐磊:《〈京华时报〉停刊了,还有什么在消失?》,微信公众号“令狐磊的杂志发现室”2017年1月2日
[69]窦桑:《东早与京华停刊,中国市场化纸媒的三条路:转业、转型与转场》,微信公众号“媒变”2016年12月31日
[70]徐婧艾:《16 年间,大报梦想的诞生与消逝》,《好奇心日报》2017年1月6日,http://www.qdaily.com/articles/36559.html
[71]刘洋:《〈京华时报〉创刊者朱德付:我知道会有这一天》,微信公众号“录音笔”2016年12月31日
[72]最极客:《〈京华时报〉终成“烟云”,纸媒适应互联时代或能“向死而生”》,搜狐公众平台2016年12月30日,http://mt.sohu.com/20161230/n477399470.shtml
[73]匿名用户:《如何看待〈京华时报〉将在2017年停刊?》,知乎2016年11月16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398433
[74]詹国枢:《别了,京华时报》,微信公众号“码字工匠老詹”2017年1月1日
[75]梅特卡兹:《如何看待〈京华时报〉将在2017年停刊?》,知乎2016年11月24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398433
[76]徐世平:《东方网新年献辞:循天下之公,争风气之先》,东方网2017年1月1日,http://pinglun.eastday.com/p/20161232/u1ai10212513.html
[77]大鸟:《告别〈东方早报〉,是媒体融合进程的关键一步》,微信公众号“新闻记者”2016年12月28日
[78]新浪微博“凯雷”,2016年12月31日
[79]窦桑:《东早与京华停刊,中国市场化纸媒的三条路:转业、转型与转场》,微信公众号“媒变”2016年12月31日
[80]水米糕:《纸媒不死,只是渐凋零》,微信公众号“水米糕饭局”2016年12月31日
[81]Carlson,M.(2016).Telling the crisis story of journalism: Narratives of normative reassurance in Page One. In J.C.Alexander, E.Breese & M.Luengo (Eds.)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From technology to culture (pp. 135-1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2]NordD.P.(2001).Communities of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Their Reader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83]ShakerL.(2014).Dead Newspapers and Citizens’ Civic Engagement.Political Communication31(1)131-148.
[84]章友德:《向一份即将停刊的报纸致敬》,微信公众号“章友德”2016年12月1日
[85]新浪微博“Summer160”,2016年12月31日
[86]新浪微博“何万篷”,2016年12月28日
[87]新浪微博“优道大帝”,2017年1月1日
[88]王国华:《报纸的停刊和饭店的倒闭》,《证券时报》2017年1月4日
[89]新浪微博“王旭明”,2016年12月15日
[90]新浪微博“张扬也扬”,2016年12月6日
[91]新浪微博“耿建华v”,2016年12月30日
[92]李赛可:《框架视角下的美国新闻业危机》,《新闻记者》2015年第11期
[93]Zelizer,B.(2015).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888-908.
[94]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95]陈楚洁:《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2期
[96]白红义:《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
[97]GilewiczN.(2015).To embody and to embalm: The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final editions of failed newspapers. Journalism,16(5)672-687.
[98]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5期
[99]Menke,M.(2017).Seeking Comfort in Past Media:Modeling Media Nostalgia as a Way of Coping With Media Chan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1626-646.
[100]丁方舟:《“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101]Zelizer,B.(2015).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5888-908.
[102]WaisbordS.(2017).Crisis? What crisis? In C. Peters & M. Broersma (Eds.)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pp. 205-215). London: Routledge.
[103]Usher,N.(2017).Venture-backed News Startups and the Field of Journalism.Digital Journalism, DOI: 10.1080/21670811.2016.1272064
[104]WagemansA.Witschge,T.& DeuzeM.(2016).Ideology as Resource in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10(2)160-177.
[105]Carlson, M. & UsherN.(2016).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For-profit digital news startup manifestos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 4(5)563-581.
[106]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107]熊少翀:《这家媒体发行量曾冠绝京城,休刊转型新媒体两月后,表现却是这样……》,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7年3月3日
[108]Peter,A.Mengshu Chen.& Carrasco,S.(2017).Power interplay and newspaper digit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Pengpai experiment. Global Media and ChinaDOI:10.1177/2059436416687313.
[109]《广州日报》:《我们永在身边》,2017年2月13日头版
[110]《晶报》:《坚定地重申内容为王》,2017年2月13日头版
[111]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和应用可参见笔者的三篇论文:《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南都口述史”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2期;《新闻范式的危机与调适:基于纪许光微博反腐事件的讨论》,《现代传播》2015年第6期;《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
[112]陈楚洁、袁梦倩:《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5期
白红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创新智库团队成员。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编号:15BXW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