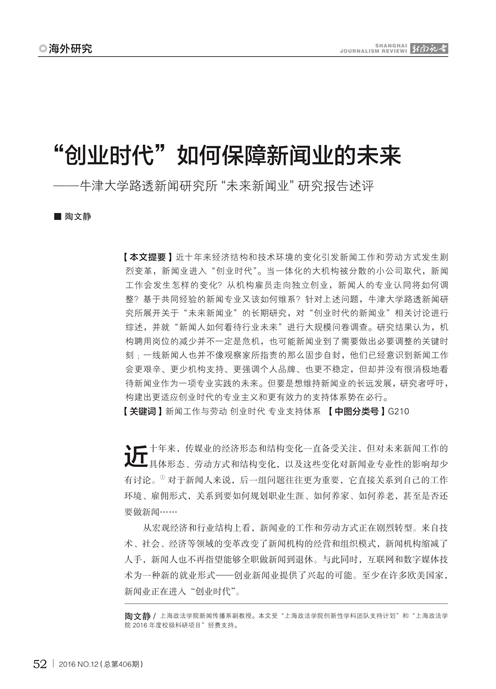“创业时代”如何保障新闻业的未来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未来新闻业”研究报告述评
■陶文静
【本文提要】近十年来经济结构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引发新闻工作和劳动方式发生剧烈变革,新闻业进入“创业时代”。当一体化的大机构被分散的小公司取代,新闻工作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机构雇员走向独立创业,新闻人的专业认同将如何调整?基于共同经验的新闻专业又该如何维系?针对上述问题,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展开关于“未来新闻业”的长期研究,对“创业时代的新闻业”相关讨论进行综述,并就“新闻人如何看待行业未来”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认为,机构聘用岗位的减少并不一定是危机,也可能新闻业到了需要做出必要调整的关键时刻;一线新闻人也并不像观察家所指责的那么固步自封,他们已经意识到新闻工作会更艰辛、更少机构支持、更强调个人品牌、也更不稳定,但却并没有很消极地看待新闻业作为一项专业实践的未来。但要是想维持新闻业的长远发展,研究者呼吁,构建出更适应创业时代的专业主义和更有效力的支持体系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闻工作与劳动 创业时代 专业支持体系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十年来,传媒业的经济形态和结构变化一直备受关注,但对未来新闻工作的具体形态、劳动方式和结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新闻业专业性的影响却少有讨论。①对于新闻人来说,后一组问题往往更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工作环境、雇佣形式,关系到要如何规划职业生涯、如何养家、如何养老,甚至是否还要做新闻……
从宏观经济和行业结构上看,新闻业的工作和劳动方式正在剧烈转型。来自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变革改变了新闻机构的经营和组织模式,新闻机构缩减了人手,新闻人也不再指望能够全职做新闻到退休。与此同时,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为一种新的就业形式——创业新闻业提供了兴起的可能。至少在许多欧美国家,新闻业正在进入“创业时代”。
当一体化的大机构被分散的小公司取代,新闻工作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机构雇员走向独立创业,新闻人的专业认同将如何调整?基于共同经验的新闻专业又该如何维系?行业结构剧烈调整之际,如何保障新闻业的长远未来?哪些人和机构需要参与其中?
针对上述问题,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the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RISJ)展开了关于“未来新闻业”的长期研究。已发布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创业时代的新闻业”的研究述评以及针对“新闻人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大型问卷调查。该研究认为,从总体的经济社会趋势上看,机构聘用岗位的减少并不一定是危机,也可能是新闻业需要做出必要调整的关键时刻,是促成更灵活劳动形式的契机。建立更具协作性的生产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就业规模。而实证调查的数据也显示,一线新闻人并不像观察家所指责的那么固步自封,他们已经意识到新闻工作会更艰辛、更少机构支持、更强调个人品牌、也更不稳定,但却并没有很消极地看待新闻业作为一项专业实践的未来;至于专业认同,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新闻的专业性是基于一套相对稳定的实践和技能的结合,并不依赖具体供职的媒体,也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威胁。但要维持新闻业的长远发展,研究者呼吁,构建出更适应创业时代的专业主义和更有效力的专业支持体系势在必行。
一、创业时代的新闻工作与劳动
为了充分解析新闻业经历的变化与面临的挑战,研究者首先将新闻专业中经常被混用的工作(work)和劳动(labor)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
1.工作与劳动的日益分化
后工业时代,生产劳动已经不仅仅是“产出特定产品”,还因“信息服务”等新兴产业的实际变化而更多被视为“一种关系性的、互动的学习进程”。②同时,工作与劳动的差别也更加明显。路透报告中,工作(work)被界定为“生产特定产品或者完成某项任务所进行的体力和智力投入”;而劳动(labor)则更多指“报酬劳动”,指个体为了获取报酬而出让其服务或产品。由此引申出,一个工人出售其劳动给雇佣方,而雇佣方购买了其劳动。大多数研究者将工作视为个体的特定行动,而劳动形式则较为多元,可以被进行货币化衡量,也可以在雇主和被雇佣者之间交易。也就是说,工作是任务的执行,而劳动是工作的出售。
由此可以发现,当下新闻业的工作内容和劳动形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二十世纪,大多数记者是新闻机构中挣薪水的雇员,新闻工作和新闻劳动的关系常常是紧密结合的。而在二十一世纪,“新闻工作的实施”(工作)和“新闻的雇佣方式”(劳动)已开始明显分化。
2.创业型新闻业的兴起及其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中大机构的聘任岗位呈总体下降态势,近十年来新闻业的裁员就不能只被当作孤立的个案。新闻业的变化其实是整个经济社会转型的一部分。③
但如果某个特定领域整个就业市场都受到了结构调整的冲击,从业者在同行业其他大企业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则相对有限。他们可能会失业、转行,或者采用类似“破坏性创新”(creative destruction)的策略④——建立新的小型企业、协作型的工作室等,走上自我雇佣或者创业之路——这在建筑、IT和新闻业都有显现。以美国为例,虽然总体就业市场中大公司仍然提供了更多的职位,但中小企业和创业职业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基本的经济规律是,创业职业者的数量受就业市场和GDP浮动的影响——当就业市场中的岗位增多,创业比例下降;但如果整体GDP涨势看好,创业者的热情也会提高。
3.协作型生产模式与行业未来
但是对于创业者自身,许多新的问题还是需要考虑。有调查显示创业者的担心主要有市场风险、工作家庭平衡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支持等。⑤经济学者建议,针对创业中的财政风险以及经济规模缩减等难题,可通过建立协作型的生产模式(cooperative production forms of labor)来应对,比如组建相应的区域联盟或行业联盟等。
当大机构的岗位减少,为维持就业,各种类型的小型新闻机构也开始创建。不同于“自由撰稿人”以项目的方式将自己的劳动出售给不同的新闻机构,新的创业形式更为独立和完整。新闻人通过创立自己的小型媒体(SMEs)来生产内容,通过网站或博客等建立自己的传播模式和渠道,并与其他公司结为辛迪加联合发布内容。在一些区域报道或者专业领域,已经有许多个人或者记者工作室采取了创业形式,积极从事内容的制作、营销与发布。研究者们认为,在21世纪,虽然大型新闻机构还会存在,但其他类型的生产组织形式也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⑥
同大企业相比,这些小公司更为灵活、勇于尝试,决策效率也更高。但如果从行业运行的角度,大公司聘任的减少也意味着支撑原有行业专业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流失——当企业规模减小,员工们的职责和工作范围都会增大。⑦如果创业者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行业生产模式的变化就足以引发各界对于新闻业专业性及其长远竞争力的担忧。
二、创业时代的新闻专业及其挑战
从全局的角度,新闻业的变化只是整个社会“新机械时代”⑧的一部分,许多行业也早有回应。例如美国的软件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工程师们就已经不再谋求在某家大公司聘用的稳定性,而是通过根据顾客和雇主的需求不断进行自我技能升级而积累的“可被雇佣的稳定性”(employability security)。甚至这一行业中的普通工人都被鼓励从“风险劳动”(venture labor)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而非一辈子拴在某个岗位上。⑨相比于这些行业,学者们普遍认为,新闻专业的调整有些落后于时代了。⑩
有学者甚至直接将问题指向新闻专业主义的滞后性,认为是新闻人自己不愿意去创新,不愿意分享知识和拥抱新技术。[11]部分是因为这会改变新闻劳动的程序和性质,[12]部分是因其干扰了新闻人的专业地位和自主性。[13]既然近几十年来数字化、全球化、多元文化交织已显著影响了新闻业,新闻意识形态就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1.工作与劳动变革引发专业问题
创业时代,无论是仍受雇于大型机构,还是已经走上创业之路,新闻人的工作内容和劳动方式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和分化,原有新闻专业的运行流程与环境的改变[14]威胁到“重视个人能力超过团队协作和知识共享”的职业文化以及“专业新闻人是公众知情把关人”这一基本“信条”,[15]新闻业的专业性受到重重挑战。
(1)工作变革带来专业实践分化
在新闻工作领域,有学者将“多媒体技能升级的要求、数字网络融合以及崭新的受众关系”列为近年最主要的几大挑战。[16]一方面,记者被要求掌握更多的新媒体平台的信息采集和发布技能,另一方面,更紧迫的截稿时间压力和更少的编辑部支持使背景调查、事实查证、多元信息来源以及一手资料独立调查等新闻业传统的专业技术和操作出现“技能退化”。
在一些领域,尤其是本地报道部分,许多新闻工作已不再包含多少真正的“新闻性”,而只是新闻通稿或者其他公关产品的翻版。另一些领域,对深度报道的需求也在增长。此外,虽然事实报道仍是记者工作的主要部分,但许多标榜“高端优质”的媒体也鼓励新闻人做更多的分析和解释工作。
技能升级方面,电脑相关技术是首要要求。除了加强对受众分析的重视,许多媒体还要求新闻人能够运用多种手段与读者或者用户直接交流,来推动自身的“新闻社交化”(Social Journalism)。社交新闻记者通常需要经营博客或推特等来打造个人品牌(有时也代表所在的媒体)与用户互动。更有甚者,受众有时会被从新闻的接收者直接转换到新闻来源的位置——新闻人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告示、状态或评论来收集信息。这种“社交化”的新闻提高了新闻信息输入和产出的数量和速度,但也因导致信息过剩而备受争议——新闻人过滤消息来源的难度将加大,也更不容易觉察其中的偏见。学者认为,“社交化新闻”正在重构新闻价值的标准,以及新闻人写作、呈现和进行跟踪报道等基本操作。此外,即时通讯的时代,不仅每时每刻都是“截稿时间”,还需要随时关注竞争媒体的报道和其他在线的信息来源。这些变化同样引发了对信息质量、公正性、自主性的影响以及超强工作压力的担忧。
(2)劳动变革带来专业边界模糊
除了转行之外,新闻创业者的数量日增,但其中许多是公司裁员和就业岗位减少的无奈之举。虽然新闻业一直有自由撰稿人的传统,但创业还是带来许多新的难题。首先是职业风险和创业风险的加剧(比如缺少顾客或者失去合伙人等),并要承担很多原来由雇主提供的开支(比如养老、管理、社会保险),也享受不到在原来做雇员时的税收优惠。虽然部分经济难题可以通过协作型生产模式来缓解,但还是会对新闻人个人的财务规划、生活节奏甚至还要不要继续做新闻产生影响。
最重要的是,许多创业者已不再只是新闻人了,许多其他工作,比如咨询、公关和宣传,都在支撑和补贴其新闻工作。此种联合大都处于收入上的需要,但却很可能引发客观性、故事选取以及偏见等方面的问题。新闻人能否坚持新闻的原则又兼顾市场需求?能在同一个领域中既做新闻又做咨询么?这引发了对新闻人工作路径的讨论,知道自己今天报道了一家公司,明天也许还会报道它(条线记者)是一回事;知道自己今天报道了一家公司,明天可能想为其工作,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即使仍是机构雇员,工作的稳定性也在下降,行业在萎缩,许多大型机构也可能关门。许多新闻机构要求其雇员掌握更多的新媒体技术,甚至鼓励“内部创业”来推动整个机构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劳动方式上的剧烈变动让人不禁对新闻业的未来产生忧虑: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人是主动的?做新闻是否已经只是某个职业阶段而非终生的事业?如果一个行业的收入持续低迷,这个行业的未来如何保证?
(3)创业时代的专业认同困境
工作和劳动方面的剧烈变化直接挑战了新闻专业实践和认同的稳定性与共享度。虽然新闻专业认同在各国多有差异,[17] “公众服务”“客观性”“自主性”“时效性”“符合职业操守”始终是其核心构成。[18]但在当下的多媒体格局中,上述信条受到了严重影响。自上而下的新闻与自下而上的新闻(比如使用更多的社交网络的内容)形成对照;专业新闻的客观性与覆盖性之间产生张力;强调自主判断的新闻人如今要更多与人协作才能发挥影响,并要从不间断24/7全时间在线发布的标准重新界定“时效性”。
与此同时,自营职业者的增加已经明显加剧了创业者同机构雇员之间,以及在那些将新闻活动与公关服务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同不这么做的新闻人之间的分疏。学者质疑,鉴于新闻工作的诸多变化,它是否还保有其公共服务、客观性、及时性、自主性等核心原则?在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双重压力下,这种基于共享的专业理念是否以及如何才能延续下去?新时代中,新闻人如何看待自身的职业认同?“从事新闻活动”与“身为新闻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不同代际、地位、类型的新闻人如何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专业认同的协商和重建中?
2.专业转型需要制度化支撑
除了内涵重建,相应的机构和制度体系的调整也是新闻业转型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关于原有的新闻专业认同能否在其机构和制度环境之外得以维持,已成为一个显在的议题。
曾经的专业性以从业者受雇的大机构为主要支撑。众所周知,受雇于大机构的普通员工对其工作和劳动过程的控制力相对较小,而专业雇员却能够运用其专业知识在选择做哪些工作和如何做好工作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当然他们并不能控制组织内部的资源分配和管理决策,并必须在雇佣方所限定的范围内行使其专业控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业者更能控制其工作,实际上,创业者很难保持持续的较高自由度和控制力,因为他们同样需要赚取收入,同样被市场需求驱使,因而远没有想象中的自由。[19]Carlin称这是“自由的幻象”。市场经济中,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商品,无论是卖给雇主还是直接卖给客户。很少有人的产品或劳动能稀缺到总是让买家来求着自己。他们需要维持收入、财政平衡,并受到总体的经济、社会需求,税收以及法律规制的制约。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创业者和受聘者在专业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于后者,支撑其专业地位的是其所受雇的大机构。而对于创业者、小公司的雇员等,则更多需要行业协会来为其提供市场风险和法律权益的庇护。
但在实际操作中,上述建议需要参照行业和一线新闻人的实际需要,并获得他们的参与和认同,由此引出的问题包括:为保障新闻业的未来,是否以及如何来保护一些特定的机构?谁应该来实施这种保护?如何能让记者的工作更具反思性、更有积极性地参与到对新闻专业性的重建中?新闻人认为谁应该参与到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中来?哪些制度安排能够更好地帮助大机构推动内部创业?这些设置中小型新闻机构负担得起吗?新闻专业培训方向该如何调整?新闻院校要教些什么才能适应未来15年的需要?尤其在这个教育成本攀升而回报不断下降的时代?
三、新闻人如何看待行业未来
为回答上述问题,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亟需进行。联合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力量,路透新闻研究所的问卷调查从一线新闻人的感受入手,将“新闻工作”操作化为“具体的行为和活动”,“新闻劳动”操作为“雇佣关系的性质”,而“职业认同”则主要集中于“什么是新闻业”,“谁才是新闻人”等核心问题。在美国专业记者协会的支持下,调查覆盖西方多国,共收回有效问卷五百多份。[20]1.工作内容更加繁重
新闻工作方面聚焦“新闻工作将要发生的变化”,涉及新闻工作的具体内容、工作强度与压力,以及这些对新闻人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生活平衡所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新闻工作将面临更大的产出压力,77%的人同意或者强烈同意将来要生产更多报道的工作压力会上升。78%的应试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将来的新闻人将不会有真正的“下班时间”,他们需要不停地处理报道、社交媒体推送,以及其他职业生活所要求的事情。无论如何,媒体机构所倡导的“社交化新闻”被纳入到新闻人对其“本职工作”的理解范畴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将来成功的新闻人需要做更多的个人品牌工作,并有更多的创业精神。其中86%的人同意或强烈同意新闻人需要进行更多的个人品牌经营,比如通过社交媒体、博客、公共活动等方式,以取得职业成功。
我觉得新闻人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建立个人品牌要比投身于某一家具体的媒体要来得实在。
—— 一位年轻的女电视记者
而对于未来新闻业的职业满意度以及记者的自主性、自由度等方面,新闻人的看法则出现明显分歧和不确定性。只有28%的新闻人认为未来新闻业的职业满意度会更高、报酬会提高。但也只有38%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人在将来会拥有更少的自由或者自主性。同时,新闻人意识到更多的职业困境。71%的新闻人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业将比一般的白领职业压力更大,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更加模糊。
雇主们要求新闻人在多媒体的平台上推销报道,虽然他们自己还没能够在这些平台上挣到钱。
—— 一位资深男性报纸编辑
2.劳动形式更不稳定
劳动形式部分聚焦“新闻业组织方式的变化”,主要涉及到新闻人是否会被全职雇佣,或者采取其他的劳动形式;新闻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新闻人的报酬和福利会受到哪些影响等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人把未来的新闻业仍看作一项职业,但他们也意识到传统的雇佣方式渐渐靠不住。60%的应试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大多数机构聘用的新闻人工资和福利将会减少。71%的应试者同意或强烈同意新闻业的雇佣关系将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86%的应试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将来的新闻人再也不能指望能在同一家机构里一直做到退休了,终身做新闻的行业稳定性也受到了挑战。
新闻就业形式将变得更多样,55%的应试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越来越多的新闻人将会独立创业或者成立自己的新闻公司。关于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非营利新闻机构,48%的受访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越来越多的新闻人将会为非营利新闻机构工作,但也有很多人不确定非营利新闻机构的未来。另外有48%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将来的新闻人许多都是兼职,他们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工作,来弥补收入上的不足。
新闻人也许不能再想当然地指望一直全职做新闻了。他们必须开始考虑在新闻业之外的赚钱能力。
—— 一位刚入行的女性自由撰稿人
3.职业认同分化重重
职业认同部分包括“什么是新闻业”“新闻人要做什么”“谁是新闻人”“如何成为新闻人”,以及“新闻专业标准和规范应如何建立”等问题。
这项职业正在失去其专业性,但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坚持那些传统的标准和信条。
—— 一位资深男性报纸记者
结果显示,受访者同意新闻业是一项专业。77%的受访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业是一套基本操作和技巧的集合,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媒体。同行间的合作仍被看重,84%的受访者同意或十分同意新闻人需要通过与人共事并经常合作,来建立和维系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标准。
但在界定“新闻人”身份时,调查结果显示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受访者发现成为行业组织的成员、为已被认可的新闻机构工作或者使用相应的新闻操作与技术都不足以划定谁是新闻人。61%的不同意或者强烈不同意只有为已知新闻机构工作的人才是新闻人;49%的受访者不同意或者强烈不同意记者必须参与某些代表新闻人或者新闻业权益的行业机构(行业协会、联合会等)。这一态度与学者希望通过加强行业协会的呼声存在一定分歧,至少说明目前的行业机构没有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界定“新闻人”这一问题上,之前基于 “认知”层面的“专业操作”等共识并没有延伸至“规范”和“价值”层面,因此也难以成为划定新闻业边界的标准。只有50%的受访者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那些拍下现场照片/视频,或者在社交媒体/博客描述“发生了什么”的人能算新闻人。但也只有47%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无论是谁,只要进行着新的专业实践和技能都应认为是新闻人,与其如何营生无关。
将来几乎没办法划定谁才是新闻人,有那么多混合的形式。
—— 一位中等资历的女记者
在如何成为一名新闻人的问题上,51%的应试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业是一门特殊的手艺或行当,需要一些训练和经验,但并不一定要采用专业教育的形式。也只有37%的应试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业建立在一整套只是体系和专业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并因此需要专门的大学专业。
4.专业支持体系调整势在必行
总体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新闻人普遍认为,新闻业的工作内容会变得更宽泛、更少有机构性的支持,但他们倒不一定觉得新闻工作满意度会下降或者更不自由。调查结果确实反映出一些担忧,比如认为新闻工作将会更艰巨,需要更多地去考虑个人品牌或者自主创业(Entrepreneurship),也不能再指望稳定的雇佣、全职的工作甚至是一辈子都可以做这行。但除了这些,受访者普遍认为新闻的专业性是基于一套相对稳定的实践和技能的结合,并不依赖具体供职的媒体,也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威胁。
研究者强调,调查结果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新闻人显然并没有否认媒介正在发生的那些基本性的变化给作为一项职业的新闻业带来的直接影响;第二,虽然承认新闻工作变得更高压,更需要单打独斗,也更不稳定,但他们并没有很消极地看待新闻业作为一项专业实践的未来;第三,调查结果在不同年龄、性别、从业资历组群中并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大多数新闻人都十分清楚他们的职业正在发生变化,并不像许多评论者所想象的那么固步自封。新闻人知道新闻业的就业结构会发生更多变化,并且新闻业所运行其中的环境和形式也将与20世纪不同。
四、评论:关注新闻专业的制度层面及其支持体系
新闻业的专业性及其未来走向是近年来渐热的话题。有学者通过“划界”机制研究变迁中的专业规范和行业边界;[21]也有学者倡导通过用其独特的民主功能而非聘用形式来界定新闻实践;[22]还有研究从对 “危机话语”的批判分析中,了解新闻人应对挑战的策略以及他们所想象的新闻业未来。[23]同时,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和运作方式也在不断调整。学者Usher对记者离职告白中对新媒体时代新闻业“最后的”沉思中发现,许多离职记者们认为“理想的新闻业不再存在了”,他们将此归咎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的贪婪”、对新闻品质不够重视。作者批评新闻人需要对变动的媒介环境更具反思性,并积极做出调整。但在另一方面,该研究也提醒人们关注新闻专业主义的制度层面。虽然新闻专业作为“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24]的特质已广为接受,但在实际运作中,影响新闻业的不只有“职业理想”,还有诸多的“职业困境”。
路透研究中心的“未来新闻业”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此,不仅以大规模实证调查的方法展现了当代欧美国家新闻专业认同和职业困境的现状,还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突破“划界”的“局内人”的视角,从经济社会总体转型的大趋势上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的制度、机构和相应的法律支持体系。当工作压力增大、技能要求多元、收入持续走低,除了不断供之以“情怀和理想”,还要提供哪些支持来维系新闻作为一个专业的未来?相似的问题也日渐引发国内学界、业界以及相应的管理部门的关注。
1.转型话语冲击下的大陆新闻专业话语
中国大陆的新闻专业主义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改革叙事的替代性话语,[25]一直处于模糊而零散的境地。近期的相关调查显示,新闻人将自身划分为“党报-都市报”“传统媒体-新媒体”“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群体类型,并在“专业理念及日常实践”“社会声望”“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26]虽然近年来一些关键公共事件发生的“热点时刻”渐成新闻人集体发声的积极场域,[27]但其随机性和反复性也显示出真正的专业共同体的内部协商机制还尚未形成。日益严峻的从业环境下,学界和业界一面批评专业的不成熟,同时也疾呼当代新闻人建构共同体的“当务之急”[28]——共享的专业主义不仅是新闻也是公共服务的基础,更是应对当下职业挑战和危机的策略资源。
与欧美相似,我国新闻业的专业性也受到新技术、新经济模式的冲击。学者李艳红指出,新闻业界和学界倾向于将当前新闻界的境遇“诊断”为一场商业危机与挑战,得到最多讨论的是新闻媒体机构的读者流失、盈利下滑、广告下滑以及新闻人的辞职等方面,但其是否造成新闻报道品质下降、将可能对公共领域造成何种侵蚀等问题则鲜有关注。[29]对商业危机的诊断首先是技术主义的,媒介机构和新闻人的技能升级成为主要的转型策略。以人民日报社为例,在其逐步搭建的“中央厨房”和“媒体方阵”中,内容生产、协作、分发的业务模式以数字化为导向进行重组;传统意义上的采编人员重新定义为:指挥员、信息员、采集员、加工员、推销员、技术员等岗位;报道形式和技术也不断“升级”,在2016年春运报道中,推出结合VR视频、文字、图片等各种元素的H5报道。[30]这些媒体平台和新闻操作中的“创新”固然带来了点击量和报道数量上的提升,但也使新闻人的岗位设置、工作内容和考核标准等发生了剧烈变动。加之各家媒体转型的具体部署不同,新闻业的日常操作已出现剧烈分化。
在商业动因的驱动下,新闻实践的评价标准也发生偏移。“商业模式、经营模式、产品、用户需求、用户兴趣和可持续利润”挤压“准确、客观、深入、丰富、监督、公众利益和社会公器”等成为新的关键词。记者的考核方式同欧美国家一样向“社交化”“咨询化”“服务化”偏转,原有的专业自主性在“点击量”“转载量”等指标的权衡下亟需进一步甄别和细化为更严格的操作规范。
2.转型新闻人的反思与困境
个体层面,国内新闻人也早已察觉到新环境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在媒介融合的要求下,记者对独家性、显著性、轰动性的新闻价值认可度仅次于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31]对近年来“记者节”叙述话语的研究显示,新闻人已经明显感受到机构、竞争和就业环境的变化,有人乐观地期待新媒体的冲击给传统媒体指明方向,使之在深度上和专业上作更多尝试;也有新闻人认为个体层面的职业转型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创业、转向新媒体或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部门等成为传统媒体人的几大去向。[32]另一方面,良好的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也确实让新媒体机构和自媒体创业者的数量呈现井喷态势。截至2015年底,微信平台上公众号数量超过1000万,微博平台上垂直领域专业作者超过230万,而在当年的“中国微信500强”中,有88%的公众号属于创业者,远超专业媒体,[33]学者将此现象称为“内容创业的春天”。
3.职业困境更影响行业未来
事实上,无论是留在传统媒体,还是转型去新媒体或者自主创业,危机之下国内新闻人对职业理想的认同反而有上升趋势,新媒体和自媒体创业者甚至更在乎“职业操守”带来的“尊严”。[34]导致传统新闻人最终选择职业变动的,更多的是对诸多“职业困境”的无奈。一份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的研究中显示,对于新闻这个专业本身,大多数记者仍旧存在高度的认同和依恋,而“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四个方面,则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35]而后者恰恰是与“理想”相对应的“现实”部分,其中既有自主性方面所受机构支撑减弱的愤懑,也有收入、工作压力、技能升级等职业困境方面的尴尬。
工作内容上,新闻业仍对其从业者有很大“黏性”,许多“转型”的新闻人只是转去新媒体或者自媒体创业,但仍旧以新闻为业。除了与国外同行相似的创业风险,许多大陆新媒体和自媒体创业者还遭遇“不被社会认可”、在遇到危险时缺少单位和同行的“强大靠山”、内部创业人员得不到相应制度性激励[36]等职业空间和职业保障方面的困扰,相应的税收和版权上的弱势也亟需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4.如何保障新闻业的未来?
在媒体支持力度下降,行业日常操作和评价标准日益多元,行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协商和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如何为新闻的专业性和整个行业的健康运转保驾护航?路透“未来新闻业”项目的研究者从文化、法律和社会管理三个层面给出了如下建议,其包容性和建制化考虑尤其值得国内学习:
(1)文化方面,在新的就业和工作环境中,公众、新闻机构和新闻人自己都需要参与到对新闻专业内涵的重新协商中。
(2)法律制度方面,针对各种新出现的新闻就业形式,要从法律角度制定出相应的合同细则来保障自由撰稿人、特约通讯员、外派记者以及协作型的新闻工作室等非雇佣身份的新闻人的合法权益,承认其作为新闻业的成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社会管理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作制度,让新闻机构、协作型机构和创业新闻人能够更方便、高效地合作。各种新闻专业协会则尤其需要思考如何为创业新闻人提供医疗和人身保险、养老津贴以及其他福利待遇,降低他们的职业风险,保障他们的权益,以便为这个处于激烈转型的行业提供更好的支持。■
①WitschgeT.and Nygren, G. 2009‘Journalistic Work: A Profession under Pressure?’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6/1: 37–59.
②Bandt, J. D. 1999‘The Concept of Labour and Competence Requirements in a Service Economy’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1: 1–17.
③NeffG. 2012Venture Labor: Work and the Burden of Risk in Innovative Industries, MIT Press.
④SchumpeterJ. 1942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Harper & Brothers.
⑤BayrasliE. 2011What Scares Entrepreneurs? Forbes.
⑥AndersonC.Bell, E.and Shirky, C. 2012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 Adapting to the Present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 .
⑦PadoanP. C.et al. 2010SME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OECD Studies on SMEs and Entrepreneurship, .
⑧BrynjolfssonE.and McAfee, A. 2014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W. W. Norton & Co. Carlin, J. E. 1962Lawyers on their Own: A Study of Individual Practitioners in Chicago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⑨NeffG. 2012Venture Labor: Work and the Burden of Risk in Innovative Industries, MIT Press.
⑩RossA. 2009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1]Stevens, J. 2002‘Backpack Journalism is Here to Stay’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2.SingerJ. B. 2004‘Strange Bedfellows? The Diffusion of Convergence in Four News Organizations’Journalism Studies5/1: 3–18.BoczkowskiP. J. 2005Digitizing the News: Innovation in Online Newspapers, MIT Press.
[12]GadeP.and RaviolaE. 2009‘Integration of News and News of Integration: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News Media Changes’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6/1: 87–111.
[13]WitschgeT.and Nygren, G. 2009‘Journalistic Work: A Profession under Pressure?’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6/1: 37–59.
[14]Russo, T. C. 1998‘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A Case of Newspaper Journalists’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2/1: 72–111.AldridgeM.and Evetts, J. 2003‘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sm: The Case of Journalism’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54/4: 547–64.Deuze, M. 2005‘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Journalism, 6/4: 442–64.
[15]FultonK. 1996‘A Tour of our Uncertain Future’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34/6: 19–26.SingerJ. B. 1998‘Online Journalists: Foundations for Research into their Changing Roles’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4/1DOI: 10.1111/j.1083-6101.1998.tb00088.x.
[16]Bardoel, J.and DeuzeM. 2001‘“Network Journalism”: Converging Competencies of Old and New Media Professionals’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23/2: 91–103.PavlikJ.Morgan, G.and HendersonB. 2001‘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2001 and Beyond, Report of the AEJMC Task Forc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New Millennium, .Yau, J. T. K.and Al-HawamdehS. 2001‘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Teaching and Practicing Journalism’Journal of Electronic Publishing, 7/1DOI: http://dx.doi.org/10.3998/3336451.0007.102.
[17]HallinD.and ManciniP.eds. 2012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 CommunicationSociet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Hanitzsch, T. 2011‘Populist DisseminatorsDetached WatchdogsCritical Change Agents and Opportunist Facilitators: Professional Milieusthe Journalistic Field and Autonomy in 18 Countrie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3/6: 394–477.
[18]Golding, P.and ElliottP. 1979Making the News, Longman London.Merritt, D. 1995‘Public Journalism: Defining a Democratic Art’Media Studies Journal9/3: 125–32.KovachB.and Rosenstiel, T. 2007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Random House.Deuze, M. 2005‘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Journalism, 6/4: 442–64.
[19]Bridenbaugh, C. 2012The Colonial Craftsman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Bridge, S.O’Neill, K.and Cromie, S. 1998Understanding Enterprise,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Macmillan.Duman, D. 1979‘The Creation and Diffusion of a Professional Ideology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Sociological Review, 27/1: 113–38.Heinz, J. P.and LaumannE. O. 1982Chicago Lawyer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Bar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受访者的男女比例分别为46.8%和53.2%,平均入行时间为18.5年。大多数应试者(329,64%)都出生于个人电脑时代(1980+),也因此可被看作是原生数字用户(native digital users)。地域分布上,79%(n=401)的应试者来自美国3%(n=14)来自加拿大,9%(n=45)来自欧洲,9%(n=45)来自其他国家。其中,专业记者协会的成员通过网站声明和群发邮件的方式招募,而其他北美和欧洲的记者则是通过记者网站和他们的社交媒体联络。调查时间为2014年10月至12月,共收回有效问卷509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招募方式,而不是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抽样,该报告的应试者有一定的自我选择性。
[21]2015年最新出版的论文集《新闻业的边界:专业主义、实践和参与》更是将主题聚焦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边界,12篇论文分为两大部分,其中7篇集中讨论专业主义、规范和边界的问题,剩余5篇则关注了NGO、UGC等新闻制作过程中的非传统主体。参见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22][美]艾佛·夏皮罗:《功能界定: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新趋势》,《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23]美国新闻学者Barbie Zelizer认为“危机话语”及其建构可以是一个认知的场所,通过对它的开掘,我们可以了解新闻界人士运用哪些话语资源来诊断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论述这些挑战的蕴涵、应对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他们所想象的新闻业的未来。
[24]Zelizer提出,可以将新闻人群体视为“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社群成员通过共享话语和集体阐释来建构有关自身及新闻工作的意义,与其他成员形成非正式的连接,从而构成一个话语及叙事基础上的新闻社群。
[25][29]李艳红:《关于当前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5日
[26]周睿鸣:《焦虑的自主:自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共同体与边界工作》,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302/c402788-28165929.html
[27]张志安、甘晨:《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期
[28]石扉客:《反暴力是构建媒体专业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南方传媒研究》第26辑
[30]何炜、张旸:《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中央厨房”运行流程》,《中国报业》2016年4月
[31]刘昶,张富鼎: 《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现状研究》,《现代传播》2016年第3 期
[32][34]丁方舟、韦路:《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人的职业困境——基于2010-2014年“记者节”新闻人微博职业话语变迁的考察》,《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33]新媒体排行榜:《2015 年内容创业白皮书》,2016 年 1 月 23日
[35]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36]谢奕:《报业转型再思考/事业化体制与专业化生产》,http://www.vccoo.com/v/bfe7a7
陶文静/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本文受“上海政法学院创新性学科团队支持计划”和“上海政法学院2016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