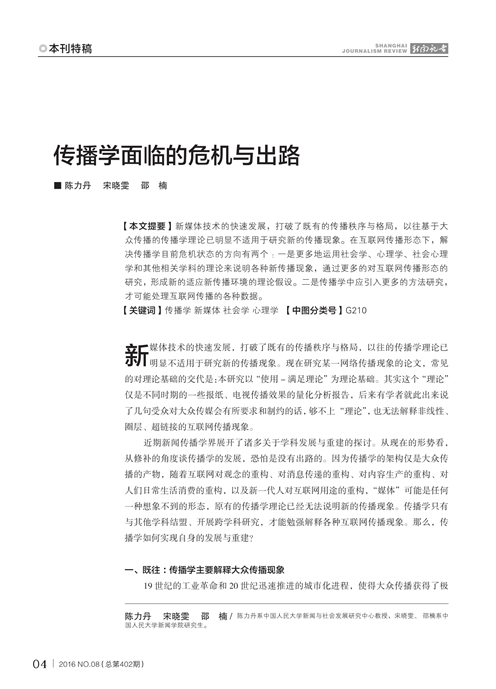传播学面临的危机与出路
■陈力丹 宋晓雯 邵楠
【本文提要】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既有的传播秩序与格局,以往基于大众传播的传播学理论已明显不适用于研究新的传播现象。在互联网传播形态下,解决传播学目前危机状态的方向有两个:一是更多地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来说明各种新传播现象,通过更多的对互联网传播形态的研究,形成新的适应新传播环境的理论假设。二是传播学中应引入更多的方法研究,才可能处理互联网传播的各种数据。
【关键词】传播学 新媒体 社会学 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G210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既有的传播秩序与格局,以往的传播学理论已明显不适用于研究新的传播现象。现在研究某一网络传播现象的论文,常见的对理论基础的交代是:本研究以“使用-满足理论”为理论基础。其实这个“理论”仅是不同时期的一些报纸、电视传播效果的量化分析报告,后来有学者就此出来说了几句受众对大众传媒会有所要求和制约的话,够不上“理论”,也无法解释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的互联网传播现象。
近期新闻传播学界展开了诸多关于学科发展与重建的探讨。从现在的形势看,从修补的角度谈传播学的发展,恐怕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传播学的架构仅是大众传播的产物,随着互联网对观念的重构、对消息传递的重构、对内容生产的重构、对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构,以及新一代人对互联网用途的重构,“媒体”可能是任何一种想象不到的形态,原有的传播学理论已经无法说明新的传播现象。传播学只有与其他学科结盟、开展跨学科研究,才能勉强解释各种互联网传播现象。那么,传播学如何实现自身的发展与重建?
一、既往:传播学主要解释大众传播现象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大众传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继报刊之后,广播、电视的诞生和普及,实现了传播手段和传播对象的社会性结合。大众传播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系统,并由此改变了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和方式,甚至影响了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创新模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战使大众传播的作用得以凸显,这一领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传播学应运而生。
来自社会学领域的约翰·杜威、罗伯特·帕克,来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乔治·米德、查尔斯·库利、赫伯特·布鲁默等,都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大众传播,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由此为传播学奠定了早期的学科基础。经验-功能学派的兴起,直接服务于对大众传播的掌控和发展,建立在经验和功利研究基础上的系列模式、理论一时统领了传播学的潮流。被视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另一位奠基人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皆立足于大众传播领域。后者的研究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着重考察广播这一新兴大众传播媒介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随后研究总统大选中媒体对选民的影响,出版《人民的选择》一书,提出“意见领袖”、“二级传播”等概念,都紧密联系着大众传播的传播效果。
有一派人在控制论基础上讨论各种传播技术,他们所讨论的传播技术,其主体是大众传播媒介。该学派关注媒介(机器)对人与社会的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所说的“媒介”是大众媒介,约书亚·梅洛维茨论证的“媒介本身成为一种环境”,也是来自对电视这一大众媒介的研究。
以批评经验-功能学派为己任的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因为研究对象的牵涉,也是以批判大众传播领域里的各种现象为起点,继而形成各种理论体系。这派的学者们专注于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背景,均基于大众传播现象。例如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以及后来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传媒“再封建化”,均以大众媒介为背景。英国文化学派则侧重解释大众传媒的利益、意识形态和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和相对的主动性。例如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书中分析的就是大众传播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的四个阶段。英国政治经济学派的纲领《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所有权及控制问题。皮埃尔·布尔迪厄“媒介场”的概念,分析的是电视的传播行为;梵·迪克的文本和语境分析,研究的是“新闻”这一大众传播的产物。
综上所述,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的产物。经验功能学派关注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技术控制论学派研究大众化传播技术的作用;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侧重批判大众传播行为与社会的关系。大众传播先入为主,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导地位。现在传播学内对其他人类传播现象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总体而言,以往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始终是大众传播,就像我国大多数高校的传播学课程内容,几乎等同于大众传播学一样,尽管理论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
二、危机:现有的传播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互联网传播现象
1.互联网影响下社会传播环境发生改变
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图罗(Joseph Turow)早在1992年就指出,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的架构被动摇。随着新媒体对社会影响的增强,大众传播中“大众”的说法应被“媒介”所替代①。2001年,史蒂芬·霞飞(Steven H. Chaffee)和米里亚姆·梅兹格(Miriam J. Metzger)提出了“大众传播终结”的命题,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与媒介传播(media communication)的差异做了归纳。②
这里的“媒介”不再是报刊、广播、电视等,而是互联网传播形态。这种“媒介”掌握了传输和检索规模庞大信息的能力,内容的生产和选择权被下放到用户手中,用户个体都有机会成为内容供应者,展现出其去中心化的趋势。由于网络带宽的提高和接收端的便携,用户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传播内容。这些传播的状况不断破坏着原有大众传播的根基,具体表现如下:
(1)信息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的所有层面和人的思维,包括虚拟世界。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空间条件变得不大重要了,交往速度越来越快,新媒体将身处不同物理空间的人整合进共同的虚拟场景,人们的交往处于即时在线的状态。
(2)传播渠道更加精细,用户自主性大大提高。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传播对象由模糊而统一的大众市场,向目标用户转变,传统意义的“被动、未分化”的受众已不存在,逐渐演变为主动选择媒体的理性用户,从前的“媒体对受众做什么”向“受众利用媒体做什么”转变。
(3)原来的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已经没有了区分的边界。霞飞和梅兹格认为,人们处在“分子社会”(molecular society)中,每个个体都被嵌入人际传播的网络里,而新技术的革新使得这种人际交往网络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大拓宽,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边界变得模糊。
(4)新媒体为网民提供了话语表达的空间,成为媒体内容生产者。以往对媒体内容同质化的担忧逐渐消散,人们开始重新建构小而分散的“趣味文化”(taste cultures)群。由于大量言论的涌入,许多草根得以形成虚拟群体。
(5)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的传播和连接方式,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的线性传播顺序。在新传播形态的传导和转译下,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图景被肢解,“强力浏览”和秒杀式阅读替代了逻辑化、有条理的信息接受。各种新信息中介商的经验策略,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在随时变动的传者和受者之间,加入了智能化的信息过滤系统,大大方便并控制了使用者。
2.原有的传播理论或不适用于新的传播环境或必须转换话题
新媒体的冲击,催生了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环境,旧的中心化的大众传播体系开始瓦解,那些在旧的传播体系土壤中培育出的传播理论、假设,需要重新审视。
例如议程设置论,它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受众从一定数量的有限渠道获取信息,某些信息最终在主流渠道上聚集成相对一致的媒介和公众共同议程。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形态已经不是原来关于“渠道”的认识了,呈现出多样化、多维度和立体交叉的状态,在信息分发方面目前社交媒体已占据垄断地位,报刊和广电分发渠道信息只占3%。这种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则是碎片化的、竞争性的、局部共享的议程。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1995年提出“Daily me”的设想,即利用编程手段将新闻自动选择出来,以满足不同的个性化需求,现在已变成了现实。互联网赋予普通网民设置自我议程的权利,原来议程设置的研究要点是“媒体告诉受众去想什么”,现在是“网民想要什么就会推送什么”了。例如现在的“今日头条”实现了个性化新闻推送。“今日头条”根据网民关注的内容进行分类推荐,通过阅读的文章模式包括阅读停留时间等一系列数据,使推送的信息最大程度地适合网民的需求。
再如培养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电视媒体构建了一个连贯的内容系统,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媒介有选择地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将话题限制在某一领域,可以培养出公众对某方面的兴趣。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传播内容更加多样、多维,网民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诸如培养理论的传播效果也随之减弱。但在用户自主选择某些特定话题的条件下,无形的培养效果甚至会更强,更偏向于选择与既有观点或偏见相似的信息,把自己置于一种自我强化观念框架内。
新的多样、多维的传播形态从形式上造成传播权力的下移,精英阶层的传播权似乎被瓦解,传播者和接受者身份可自由转换。分析这些新的传播现象,给予传播学批判理论新的讨论空间。例如,关于技术的发展逐渐被当权者控制的历史再度引发关注,因为互联网领域同样存在兼并问题,大公司会吞并小公司,58同城网和赶集网、美团网和大众点评网的合并便是如此。对于任何内容供应商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拥有资本、技术和经验的大公司在这一点上仍和以前一样占有绝对优势。一些批判学者还指出,虽然理论上,新媒体的产生带来了可能的网上民主,但现实远非如此。数字鸿沟的概念近来引起广泛关注,③精英阶层在获取新技术的能力上远远高于普通阶层。
三、前景:跨学科研究,构建大传播团队
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先驱都是其他学科的学者,在研究本学科的传播现象时无形中发展了传播学,因而传播学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相互交融的结果。在互联网传播形态下,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而需要与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相邻学科融合,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某些理论阐释各种互联网传播现象。
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从那时起,学术研究心理学化已成为传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人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离不开心理活动,特别是信息传播现象,总能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所以罗伯特·帕克将传播限定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④互联网时代,传播行为趋于个性化,从个人的心理活动出发解释个人的传播行为更重要也更有效。因此,传播学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融合是互联网时代传播学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
传播学与社会学具有天然的理论可通性,一方面,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社会学考察社会变迁深层原因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社会学本来也是传播学形成过程中的理论来源之一。现在的互联网传播,已经“重构”(re-imaging,玛丽·梅克尔语⑤)了几乎整个社会,例如重构了即时通信应用、内容和分发渠道、日常活动、数字钱币、垂直产业,还有观念的重构、消息传递的重构、内容生产的重构、新一代(12~24岁)对互联网用途的重构、人们日常生活中消费支出的重构等等,可以说,互联网已经全面颠覆人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消费方式、连接方式、商业模式等等。这些眼下正在发生的剧烈社会变迁,本身也是对社会学的冲击,迫使社会学的研究必须面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社会现象,诸如数字鸿沟、网络成瘾、信息无序和信息过载等。一些传播学无法有说服力诠释的新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可以进行社会化的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法。新的传播现象需要理论支撑,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融合,既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空间,也为社会学注入了新的内容。
面对互联网的一些新现象,传播学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将成为平常现象。例如经济学的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 effect)。2004年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用长尾理论来描述诸如亚马逊、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他认为,如果把足够多的非热门产品组合到一起,实际上就可以形成一个与热门市场相匹敌的大市场。非热门商品可以在网上被聚合起来,同样的道理,社会中不被重视的微小群体到了网上,也可以聚合起来做大,于是长尾理论给予网上小群体传播的研究以有力的理论支持。⑥长尾理论在互联网应用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奥巴马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成功,这除了离不开奥巴马个人素质和大财阀的支持外,也与其竞选团队对长尾理论的巧妙应用密切相关。两次竞选中奥巴马的团队都通过社交网站建立支持奥巴马的网络长尾,借助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尽可能增大“尾巴”的力量,成功获得了扩大传播的效果。
现在传播学的论文论证,越来越多地采用各个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就像传播学诞生之初涉猎各个学科知识那样如饥似渴。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篇硕士论文讨论“区域政府的舆情脆弱性评估”,选题很有现实意义。各级党政部门对所谓“舆情”的过度敏感,是人人都能够感觉到的互联网传播条件下的一种负面传播效应,运用什么理论才能充分阐释这个问题,给人以有说服力的结论呢?任何所谓“舆情”事件,它的产生和传播不可能摆脱发生地点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与调节。因此,“舆情”问题不能仅从信息扩散、传播能力、媒体受众等方面去研究(这是既往传播学研究的老套路),而要联系相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术理论来研究,从多个层面找寻答案。因为在传播学现有框架内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支持,作者注意到从自然科学(地理学、气象学、工程学等)发展到社会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再进一步发展到融合两大科学的流行病学、环境科学的各种“脆弱性理论”,进而提出“舆情脆弱性”的论证问题。作者运用风险与灾害(RH)模型、积累与释放(PAR)模型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根据这些模型得出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风险管理 HHM 框架”、“周期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脆弱性评估函数模型”、“脆弱性贫困干预过程”、“适应型灾害管理结构”等已有的论证,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评估指标和“开放应对网络”的结论。这篇论文的理论支撑,属于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但研究的是传播学话题。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原来较多地依据传播学的原理,现在也不得不多样化了,因为新闻传播的分发已经基本不在传统媒体的渠道内,而是社交媒体了。于是,2016年的硕士论文选题,诸如“新闻期待”、“新闻误读”的讨论背景,都转移到了“互联网传播形态下”,因而依据的学术理论,就必须到心理学、社会学理论中去找寻。
从目前情形看,传播学走出目前危机状态的方向有两个:一是更多地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来说明各种新传播现象,通过更多的对互联网传播形态的研究,形成新的适应新传播环境的理论假设。而在这种情形下,传播学不大可能再作为独立的学科创新理论假设,而需要与相邻学科合作,甚至融合,才可能取得较为公认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建构起适应各种互联网传播形态的理论假设和模式公理;二是传播学中应引入更多的方法研究,才可能处理互联网传播的各种数据。例如各种大数据新闻的得出,需要运用一定的计算模型来处理、鉴别大数据,为此,传播学研究者也必须拥有高等数学知识。对网络数据的统计,目前还没有有效的从样本推论整体的可靠研究方法,而创新互联网条件下的科学方法论,需要传播学与统计学的结盟才有可能。
四、回到本来意义的传播学,同样需要学科的融合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现象的学科,不是仅研究大众传播的学科,但由于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大众传播的发展紧密相关,因而关于其他人类传播现象的研究处于这个学科的边缘位置。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力丹、陈俊妮《传播学纲要》第二版,试图努力把传播学回归到对人类传播各方面的研究,依次讲述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文艺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传播控制、传播批判。虽然篇幅上把大众传播压缩到了十分之一,但传播控制、传播批判基本上还是在大众传播的圈内转,因为没有其他的材料,而自身传播,因为传播学本身没有雄厚的研究积淀,不得不从思维学借用了较多的理论。人际传播主要借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组织传播主要借助企业管理学的材料,文艺传播不得不借助各种文艺理论(包括绘画、音乐、视知觉思维等),跨文化传播借助的更多的是社会学、人类学、国际关系、文化学的研究成果。显然,传播学自身太缺乏对人类各种传播现象的系统研究了。
这种现状能通过传播学自身得到完善吗?各种传播现象的研究可以只凭不多的传播学专业内的人得出有体系的研究成果吗?显然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传播学的发展也得通过与相邻学科的融合,才可能有出路。
目前对互联网传播的研究是否需要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类别,就像当初对大众传播的研究那样?互联网的各种传播形态的变动不可能终止,描述一下某种传播形态的特征未尝不可,可以用于即时的政治、经济需要,但不宜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对象。传播学对互联网传播现象的研究需要较为宏观的研究视角,非线性、圈层、超链接、“智能一切”和未来光子计算机条件下的传播,人类在思维上对此的把握和得出某些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设,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合作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传播的未来,跨学科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①Turow, J. On reconceptualizing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1992(36)105–110.
②Chaffee, S. H& MetzgerM. J.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01(4)365–379.
③参见陈力丹、金灿:《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7期
④罗杰斯:《传播学史》第197页,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玛丽·梅克尔(Mary Meeker)2012、2013、2014、2015年连续4年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
⑥参见陈力丹、霍仟:《互联网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陈力丹 宋晓雯 邵楠/陈力丹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晓雯、 邵楠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