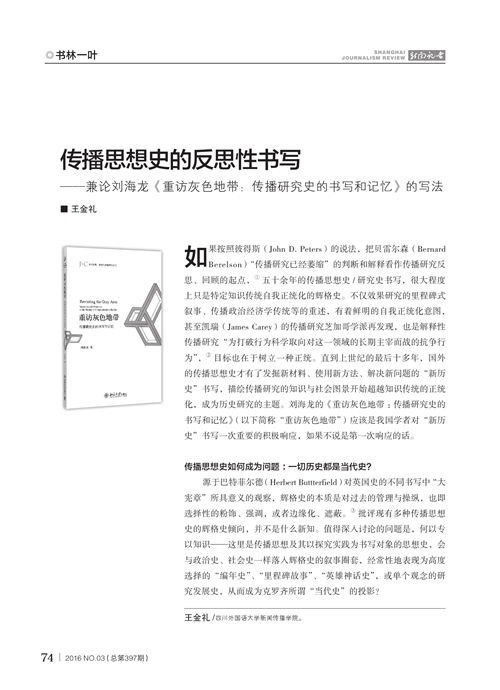传播思想史的反思性书写
——兼论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和记忆》的写法
■王金礼
如果按照彼得斯(John D. Peters)的说法,把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传播研究已经萎缩”的判断和解释看作传播研究反思、回顾的起点,①五十余年的传播思想史/研究史书写,很大程度上只是特定知识传统自我正统化的辉格史。不仅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式叙事、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等的重述,有着鲜明的自我正统化意图,甚至凯瑞(James Carey)的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再发现,也是解释性传播研究“为打破行为科学取向对这一领域的长期主宰而战的抗争行为”,②目标也在于树立一种正统。直到上世纪的最后十多年,国外的传播思想史才有了发掘新材料、使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新历史”书写,描绘传播研究的知识与社会图景开始超越知识传统的正统化,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刘海龙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和记忆》(以下简称“重访灰色地带”)应该是我国学者对“新历史”书写一次重要的积极响应,如果不说是第一次响应的话。
传播思想史如何成为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源于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terfield)对英国史的不同书写中“大宪章”所具意义的观察,辉格史的本质是对过去的管理与操纵,也即选择性的粉饰、强调,或者边缘化、遮蔽。③批评现有多种传播思想史的辉格史倾向,并不是什么新知。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是,何以专以知识——这里是传播思想及其以探究实践为书写对象的思想史,会与政治史、社会史一样落入辉格史的叙事圈套,经常性地表现为高度选择的“编年史”、“里程碑故事”、“英雄神话史”,或单个观念的研究发展史,从而成为克罗齐所谓“当代史”的投影?
传播思想史这种想象力的贫乏,刘海龙认为应该归因于传播学科自其诞生以来就十分急迫的“正当性赤字”:“为了填平这一亏缺,大量学术史话语被生产出来。” ④凯瑞则以“培植忠诚、化解争端、引导公共政策、迷惑反对者,并使建制正当化” ⑤给予了类似的解释。传播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正当性危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建制化之初,由于学科知识来源庞杂,问题与方法共识度低,核心理论的学理基础薄弱,学科之外更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科学等既有学科对传播议题不断涉入,传播研究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正当性并不明显。学科建制化的操作者因此不得不用“领域”、“十字路口”等模糊的描述性词语回避建制的身份问题,同时运用“奠基人”等起源神话构造其正当性。这一时期,辉格式传播研究史试图解决的,是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正当性竞争问题。当传播学终于在大学建制中据有了一席之地,传播学科内部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竞争便显露出来,不同研究取向开始了传播研究史正统化的争夺,不同的研究取向基于自己的正当性需求,把传播研究史的人物、事件、理论秩序井然地排列组合,从而形成了多种形态的辉格史。
不过,正当性需求仅仅解释了辉格式叙事逻辑的表层,更为紧要的,必须看到超越传播思想史编年体、纪传体、单一观念的思想发展史等具体形式、涌动于辉格史叙事底层的一种历史观、知识论的潜流,即,与辉格史强烈的选择性叙事极为矛盾的是,它所信奉的,其实是客观、科学,或者说是对历史真相的存在与对真相进行客观叙述的绝对信心。作为知识论,辉格史逻辑相信传播思想只是一种隐藏着的自然物,是某种可以在某个时间被某人以某种方式发掘、展示的东西,知识生产不过是知识与知识生产者之间宿命般的必然遇合,知识生产者因此不过是具名的匿名者;作为历史观,这一逻辑则认为记录、解释思想史可以充分依赖那些现实存在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承载着客观存在的思想史内容,自身即具有意义。因此,历史书写只是记录、整理这些意义并将其按时间顺序组织排列的自然过程。这一过程因而并未发生所谓选择、突显、粉饰、遮蔽、边缘化等主观行为。历史书写只是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传播思想史只是科学地记录了传播学知识持续性累积、深化,但也不排除其曲折性、迂回性的进步过程。
尽管这种科学化的历史观、知识论自20世纪中期以来即招致多方批评,令人奇怪的是,不仅相当数量的传播思想史书写者未能省察其历史书写的内在逻辑,截至目前,种种对辉格式思想史的批评也很少注意到科学化历史观、知识观的深刻影响。就历史书写者而言,限于其学术取向既定立场的视域限定,把传播思想史特定面相的局部事实当作正当性自洽的历史本身看待,并不难理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或岭或峰正是既定视角下看到的自然事实。然而,如果打算对传播思想史书写有所反思却又对其书写逻辑,也即其历史观知识论不加检讨,讨论辉格式选择性叙事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想当然的指控:虽然布雷尔森“传播(研究)已死”的说法凌空抛出了传播研究的正当性危机问题,⑥但正当性欲求毕竟只是思想史书写者隐而未显的主观意向,我们何以认定众多传播思想史书写隐藏着正当化的谋划?⑦
颇有些荒诞意味的是,服务于特定学术取向正当性需求的辉格史却使其自身陷入了正当性困境。从曼海姆的文化社会学到库恩的范式理论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知识生产并不是非中心化的,有着单一、唯一的问题关怀。知识生产实际上是多个知识人社群对具体设定的问题施用具体研究方法的过程,较之中心化,离散性是其更具经常性的特征。传播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以否定性思考而论,杜威的进步主义社会批评与法兰克福哲学社会学批判质的差别性远远大于其共同性,而在量化实证性研究的范围内,霍夫兰的态度改变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受众与效果研究也很难说有多大程度的共同旨趣。因此,辉格史叙事实际上体现了对非中心化的漠视与对差异性削足适履地整合这样的双重偏见。传播思想史的辉格史仅仅讲述了传播理论发展、传播思想演进的部分事实。
当然,正如萨默尔森(Franz Samelson)的研究所示,很多学科的早期历史书写都有过类似的辉格史阶段。⑧只有学科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历史研究才会被视为具有知识创造意义的学术领域,才会面对本学科研究的知识目标、问题设定、方法论思考、知识形态等,独立地提出问题,找寻答案。然而,问题不可能凭空产生,检讨辉格式叙事为传播思想史的问题的提出和解答设置了起点:如何超越辉格史的选择性叙事,建构具有知识创生意义的传播思想史?
唯其如此,传播思想史才有可能成为问题。寻找问题和答案,刘海龙提出了“重访灰色地带”的方案。
灰色抑或多色:传播思想史的反思性书写
作为描述性词语,“灰色地带”被刘海龙用来指称传播思想史辉格式叙事秩序井然的概念体系与因果关系之外的其他问题域与想象空间:所谓“‘灰’,指的是在宏大叙事中无法被归入非‘黑’即‘白’分类体系之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即那些令人尴尬、无法嵌入到某个连续事件流中的‘个案’与‘特例’”。⑨显然,灰色地带与主旋律预设以及基于主旋律而实施的对人物、事件、概念、理论等思想史材料的价值判定,有着内在的异质性。灰色地带拒绝对这些材料的客观描述与水平分类、线性排列,从而表现出一种拒绝体系化宏大叙事的否定性思维,问题而不是体系因此成为传播思想史书写的着眼点与落脚处。由于这种叙事逻辑,《重访灰色地带》实际上是一系列问题与解答的汇编。从拉斯韦尔、帕克等“四个奠基人”、芝加哥学派等起源神话中的“在场的缺席”到传播学登陆中国学术场的出场者与失踪者,作者努力避免线性时间的自然化叙事,而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为什么”的追问上。
以问题为导向,《重访灰色地带》表现出传播思想史新叙事鲜明的反思性特征。历史书写的反思性是指历史书写放弃对历史事件作客观描述的“不可能任务”,并在承认书写行为“嵌入”书写对象的方法论前提下,寻找历史的可理解性、可解释性。反思性使思想史书写具有了两副面孔,其一面向材料,其二则面向书写行为自身,也即传播思想史知识目标、方法论的自觉。承认历史观察很难免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一事实,反思性历史书写特别注重的,是“看”的行为。因此,从形态上看,反思性的历史书写中,“看”与“所见”相互缠绕,互为因果。把传播的正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研究史作为历史书写对象,刘海龙认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目标,是探究20世纪以来中西方传播研究何以如此的内在逻辑。对于这种逻辑,《重访灰色地带》特别提出了传播学术思想史“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的观点。作者发现,传统的思想史书写往往跳不出绝对与相对、连续与断裂的对立思维。或是强调绝对性,忽略内部的差异而把同一性视为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从而产生以今天为起点,沿着发展谱系回溯源头的“当代史”叙事模式;或是强调相对性,忽视累积和连续性,因而从学术思想的发展中更多看到的是断裂与一次次范式革命与转型。与这种片面强调“连续”或“断裂”不同的是,刘海龙认为,传播思想史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对于连续中的断裂与断裂中的连续的研究,突出的是思想史发展的特殊性。” ⑩这种“连续与断裂辩证法”构成了《重访灰色地带》探究中西传播研究史一系列被误读、被遗忘、被边缘化的人物与事件的方法论工具。
作为边缘化的案例,帕克的传播思想史境遇或许最具有典型性。将其作为问题对象,颇是显示了刘海龙突破传播思想史辉格式叙事模式、进行反思性历史书写的见识和匠心。几乎在所有传播研究史中,帕克都被认定为重要的传播研究者,或是“先驱之先驱”(施拉姆),或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切特罗姆、凯瑞),但这些传播研究史同时却几乎一致对帕克进行着极端化约的脸谱化描述,从而实质上将其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与帕克的贡献实际上极不相称。众所周知,帕克是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大学诸学者中在传播领域用力最勤的一位。帕克不仅在1922年就出版了美国最早的媒介社会学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甚至在更早的1910年代,他就曾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媒介社会学课程。[11]然而,作为传播研究史的书写对象,帕克却集中体现了刘海龙所谓“连续中的断裂”与“断裂中的连续”的辩证性:一方面帕克的对策式行政研究、功能主义效果论使其远离了凯瑞所称的传播研究芝加哥传统,另一方面,他的传播民主观和社群建构观点却正是杜威、米德、库利等人象征性互动理论的精髓。正是因为帕克的媒介研究、传播思想与任何一种辉格式叙事的扞格不入,难以归类,最终导致所有的辉格式叙事均对其进行了化约的模糊处理。
“连续与断裂辩证法”同样可以解释传播研究与中国原有知识体系的遇合事件。刘海龙用多个章节书写传播研究的中国旅行,综合了传播研究的连续与断裂和中国知识传统的连续与断裂这两种意义上的“连续与断裂辩证法”。深入调查中国的传播思想、传播研究接受史,刘海龙发现,以1980年代初期施拉姆访华为起点的中国传播学科发展史只不过是集体性遗忘之后的断片史,由杜威、帕克访华讲学、孙本文求学北美、戈公振撰写《中国报学史》等一系列思想史事件所构成的“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实际上远较施拉姆重新输入的对策式传播研究丰富多彩。但从中国与传播研究的知识遇合这一个特定角度看,“史前史”、“重新输入”这两个阶段一方面实现着中国与美国的空间连续性,孙本文、戈公振以及1980年代“社科院新闻所”编辑出版的《传播学(简介)》都延续着同一时间里美国的传播研究(或其一种),另一方面,两次连续所产生的知识落差,既是美国传播研究知识断裂的映射,更是中国既有知识传统断裂、改造、重生等多重知识行为的结果。两个辩证法帮助刘海龙形成了这样的判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传播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绝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简单的‘创新的扩散’的过程。中国的传播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先进学说’的接受者,还是积极主动的行动者。” [12]寻找传播研究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反思性地书写传播研究史所描述的知识世界,或许并不是刘海龙所称的灰色地带。相反,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力的律动,多彩,精彩。
内证与外证:传播思想史的解题方式
应该说,“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提供了认知、理解长时段里传播研究/传播理论形式流变内在逻辑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提供了传播思想史历史书写、历史解释的一种反思性思路。不过,这种理解、解释还只是一种知识形态学意义上的,传播思想史何时何处因何发生断裂、断裂中存在着怎样的延续等,需要更多的个案探讨。这些个案构成了传播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域,而这些问题也有着与“连续与断裂辩证法”的形态学思维颇为不同的其他方式的提法。
《重访灰色地带》对问题的提法和解法也有所省察,并将其概括为“外部观察”和“内部反思”两种路径。[13] “内部反思”主要着眼于理论、知识、思想本身,着眼于具体思想者/研究者个人或集体的知识传承、问题意识、知识承诺、概念与理论体系、表达方式、自我想象等材料。这一路径的方法论预设是,思想史/研究史是一个类似于生命体的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领域,思想、理论、知识的历史过程有其不受外部干扰了的内在逻辑,外在的因素——不管是政治动机、社会需要或其他原因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影响思想史的问题和解题方式,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摧毁它的内在规律。这种内在逻辑会将思想、知识、理论从一个阶段、一种状态,“逼出”下一个阶段与状态,思想史如何、为何的问题也可以依据内在逻辑获得解答。这种解题方式,余英时称之为“内证”。[14]余英时关于中国儒学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经学、从“德性之知”转向“闻见之知”的讨论,是从“内证”着手研究思想史的经典案例。余英时认为,不是清代学者个体或集体的主观偏好,也不是清初严酷的知识环境,而是理学发展自身的知识困境“不可避免地逼出”了考证之学。[15]在传播思想史领域,“内证”运用最为娴熟的,当数美国的约翰·彼得斯。通过细致审读杜威、李普曼、拉扎斯菲尔德、施拉姆、霍尔等人的传播研究著述,剖析传播研究者的社会观与政治关怀,彼得斯极具建设性地提出并解答了“传播研究思想贫困的体制根源”、“传播研究的知识系谱”等思想史命题。《重访灰色地带》从批判研究的政治化取向入手,破解中国引进传播学过程中的“批判研究失踪”谜题,同样依循着从知识、思想的内在品质产生问题的内证式研究逻辑。正是由于和传统新闻学学术话语的政治化倾向的同质性,批判研究尽管在英美等国已经获得了足以与施拉姆式传播研究分庭抗礼的影响力,但它在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必然会水土不服,举步维艰,因为当时的总体知识氛围恰恰是强调去政治化的“科学”、“事实”与“调查研究”。这些成功的内证案例可以看到,内证的历史想象力主要来自解读相对稳定、相对容易获得的正式文本材料。或许也是因为文本的稳定性、易得性,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尤其是辉格式叙事往往采取内证的路径,虽然内证并不必然地形成辉格史。
不过,作为解题方式的内证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文本的存在虽然是稳定的,但文本的意义却并不是唯一、确定的:一方面,文本与作者并不完全同一,文本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作者的思想表述。文本可以被作者工具性地运用,从而掩饰作者的真实意图;文本可以摆脱作者的控制,呈现出某些只能透过历史后视镜才可以读解的思想。作者不能对文本作出权威性解读的情况,并不罕见。另一方面,文本的接受受制于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前理解限定着文本的意义读取。如果承认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那就不得不同时承认,从文本中抽绎出的内在理路并不能排除其或然性。思想史叙事描述的思想,因此也只不过是历史叙事者建构的思想。正是因为对内证方法可靠性与充分性的疑虑,近年来的传播思想史研究开始强调知识生产的社会性特征,并把注意力投向了学术思想与知识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网络、知识生产机制、社会结构等的相关性研究,试图通过外在证据对思想史作出更为确切的解释。这种解题方式,即所谓“外证”。
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等宏大理论,外证逻辑的着重点是那些直接影响知识生产、理论建构的有形有质的具体关系、机制与思想史事件。就传播思想史而言,外证主要涉及知识生产者的社会交往活动与知识生产的资助体系,如观念的旅行轨迹、人物的迁移与人际交往、研究资金投放及其具体运用等可以确证的事实。理论、概念产生影响需要传播、接受等发生于实际空间、时间的社会活动,如师生间的知识传递、文本的阅读、学术会议的公开交流等。这些活动提供了思想流动的实质性线索。例如,普利(Jefferson Pooley)解释小群体概念何以成为“迪凯特研究”的解释资源时所依赖的,主要就是拉扎斯菲尔德、默顿与希尔斯(Edward Shils)的学术交往。[16]实际上,这些线索的捕捉能力构成了外证式思想史研究想像力的几个重要基础之一。另一个重要基础是研究资助体系。虽然几乎所有的资金提供者都声称不干涉资金的具体运用,不干涉研究的具体对象和结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资金框定了研究的基本问题域,甚至也框定了研究结果的大致区间。盖利(Brett Cary)、格兰德(Timothy Glander)、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等人对美国传播研究资金来源与研究结果的详尽调查,充分表明了传播研究者充当政府、利益集团智库专家的社会角色。[17]作为一种解题方法,外证很大程度上把思想史研究从想象引向了证实。
当然,外证与内证并非势同水火,两不相容。相反,反思性思想史书写需要的,恰恰是这两种提问与解题方式的配合与相互补充。探究传播思想史的可理解性、可解释性,基础性的工作首先是内证,也就是依据文本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论证方式、材料获取手段、致谢、引用及作者自述等可见信息,想象思想者、研究者的知识兴趣、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取向与思想史事件的历史意义,从而勾连出传播思想、传播理论的关系脉络。但是从内证中获得的结论,还需要外证研究的映证。众所周知的常识是,现代知识生产并不完全是知识生产者主观能动性的运作,社会的制度性架构、权力意识与学术地缘政治争斗等因素实际上更为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知识尤其是传播思想这一社会、时代特征极其鲜明的知识类型的生产过程。依据研究资助申请书、学术组织的章程、学术会议的备忘录、学科建设规划、学者私人文献(信件、日记等生活史材料。当然,信件、日记等某些内容也可以用于内证),外证可以将上述笼统判断清晰地勾画出来。但这种勾画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或然性,制度架构与权力关系对于传播思想的影响,可能如此,也可能如彼,从根本上说,它依然是整体性的、框架式的,主要也还是体现在经验性行政(administrative)研究上。如果说内证依据的材料直接呈现传播思想而可以称为传播思想史性研究的实质性材料的话,外证依据的材料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它更多的是在对行为主义传播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神话进行着否思性祛魅。或者说,内证提供想象,外证清除迷思。两者的兼顾,传播思想史的问题空间才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开掘。应该看到,《重访灰色地带》的一些研究已经有了内外证并用的意识,虽然其相对多的,还是采用了内证的方法。检讨该书的具体解题技术,此处不再赘述。■
王金礼/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①PetersJohn D“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31986p.536
②PooleyJefferson. “Daniel CzitromJames W. Careyand the Chicago School,”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4(5)2007p.470
③See ButterfieldHerbert. 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44p.28
④⑨⑩[12][13]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第7、11、13~14、135、35~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⑤Carey, James W.. “The Chicago School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Everette E. Dennis & Ellen Wartella(eds.)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emembered Histor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6pp. 21-22
⑥BerelsonBernard. “The Present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 221959pp. 1-6.
⑦当然,施拉姆的传播研究史书写的正当化谋划的证据,还是十分清晰的。这个证据,便是他的传播研究史叙事与贝雷尔森宣判之间的对应关系。施拉姆不仅在一系列著述中用“四个奠基人”沿袭着贝式起源神话,甚至其晚年检阅传播学领地时(“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31983pp.6-17)仍16次提及贝雷尔森,其喋喋不休既可以看到他的志得意满,同时也暴露出了内心深处的正当性焦虑。
⑧SamelsonFranz. “History, Origin Myth, and Ideology: ‘Discovery’ of Social Psychology”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Vol. 4(2)1974pp, 217-32
[11]“The Newspaper”see Winifred Raushenbush’s Robert E. Park: 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Duke University Press1979p.96
[14]余英时:《后世相知或有缘》,《余英时文集》第5卷第2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余英时:《后世相知或有缘》,《余英时文集》第2卷第2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PooleyJefferson. “Fifteen Pages that Shook the Field: Personal InfluenceEdward Shils And the Remembered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6082006
[17]CaryBrett. The Nervous Liberals: Propaganda Anxieties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Cold Wa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Glander. Timothy.2000.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Educationsal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cations;Simpson, Christopher.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945-196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et 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