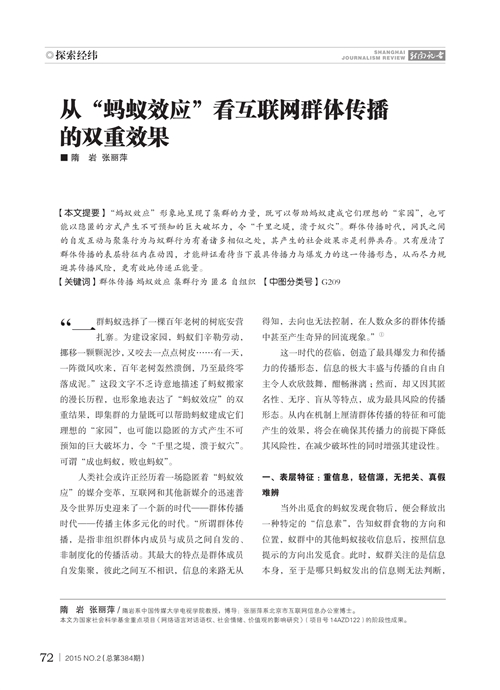从“蚂蚁效应”看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双重效果
■隋岩 张丽萍
【本文提要】 “蚂蚁效应”形象地呈现了集群的力量,既可以帮助蚂蚁建成它们理想的“家园”,也可能以隐匿的方式产生不可预知的巨大破坏力,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群体传播时代,网民之间的自发互动与聚集行为与蚁群行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其产生的社会效果亦是利弊共存。只有厘清了群体传播的表层特征内在动因,才能辩证看待当下最具传播力与爆发力的这一传播形态,从而尽力规避其传播风险,更有效地传递正能量。
【关键词】 群体传播 蚂蚁效应 集群行为 匿名 自组织
【中图分类号】 G209
“一群蚂蚁选择了一棵百年老树的树底安营扎寨。为建设家园,蚂蚁们辛勒劳动,挪移一颗颗泥沙,又咬去一点点树皮……有一天,一阵微风吹来,百年老树轰然溃倒,乃至最终零落成泥。”这段文字不乏诗意地描述了蚂蚁搬家的漫长历程,也形象地表达了“蚂蚁效应”的双重结果,即集群的力量既可以帮助蚂蚁建成它们理想的“家园”,也可能以隐匿的方式产生不可预知的巨大破坏力,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可谓“成也蚂蚁,败也蚂蚁”。
人类社会或许正经历着一场隐匿着“蚂蚁效应”的媒介变革,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介的迅速普及令世界历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群体传播时代——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所谓群体传播,是指非组织群体内成员与成员之间自发的、非制度化的传播活动。其最大的特点是群体成员自发集聚,彼此之间互不相识,信息的来路无从得知,去向也无法控制,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传播中甚至产生奇异的回流现象。” ①
这一时代的莅临,创造了最具爆发力和传播力的传播形态,信息的极大丰盛与传播的自由自主令人欢欣鼓舞,酣畅淋漓;然而,却又因其匿名性、无序、盲从等特点,成为最具风险的传播形态。从内在机制上厘清群体传播的特征和可能产生的效果,将会在确保其传播力的前提下降低其风险性,在减少破坏性的同时增强其建设性。
一、表层特征:重信息,轻信源,无把关、真假难辨
当外出觅食的蚂蚁发现食物后,便会释放出一种特定的“信息素”,告知蚁群食物的方向和位置,蚁群中的其他蚂蚁接收信息后,按照信息提示的方向出发觅食。此时,蚁群关注的是信息本身,至于是哪只蚂蚁发出的信息则无法判断,或许压根没想过要去核实这只发出信号的蚂蚁的身份。反观新媒介环境中的信息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大众尤其渴望获得相关信息,此时,一旦有与之相关的信息出现,受众往往会忽略发出信息的信源,注意力直指信息本身。而这种对信源的遗忘恰恰吻合了互联网传播的匿名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中传播主体的权威性,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为“人人都有麦克风”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每一个人都持有一部手机、或者更便捷的其它信息传输工具,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并能随时获得信息反馈时,信息传播者的身份随之变得更加多元,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相互转换着,以主动、自觉的热情积极投入到当下的传播大环境中。如此,群体传播的魅力彰显无疑,信源的扩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信息量,更成为表达言论自由,寻找真相,达成共识,展现自我,建构主体性,寻找身份归属感的社会利器。
信息的极度丰盛便意味着信息的产能过剩,这与后工业社会,或者称之为消费社会的显著文化特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也正是群体传播得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信息的丰盛固然满足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但伴随而来的却是信息的泛滥,无意义的信息和虚假信息耗费了人的注意力,由此引发的谣言更是打破了社会的平静,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群体传播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从贵州瓮安事件到西藏“3·14”事件,从四川“蛆橘事件”到山西“地震”事件,从恶意抹黑“张海迪”、“雷锋”事件到“被去世”的各种名人,以及“马航失联”事件,都因谣言滋生产生了诸多不良社会影响。究其原因,这与传播者身份的匿名性、信源的不确定性、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形态关系密切。“群体成员身份的匿名性带来信源的不确定性。集合行为中的群体,通常是联系松散、自发形成的偶然群体,群体成员彼此大多不认识,群体成员的身份被人群淹没,又不受任何主体和机构管理,处于不受社会约束的‘匿名’状态。” ②信息缺少了把关,意味着其真实性无从考证,然而“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群体成员往往会不假思索、不顾后果地将流传到自己这里的信息传播下去,甚至做出种种冲动举动。这样,信源与信宿都具有不确定性,也即信息是谁发布的,向哪里流传,会引发什么样的效果,都是不确定的。这就为谣言、流言的滋生提供了天然的温床”。③很多情况下,传播者本身无法判断信息的真实性,甚至在转发的时候也会发出提醒“难辨真假,先转,请留意”,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防御心理也加剧了群体传播的风险性。
二、结构机理:看似无序,但隐匿着稳定结构,这是互动行为的直接动因
蚂蚁的行为看似毫无章法,但生物学家们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蚁群具有严格的组织架构与身份属性,生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组织系统中,正是这种相依性让它们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遵循着一套独有的生存法则。曾有学者深入探讨过个体的简单行动是怎样组合成了群体的复杂行为,认为蚁群运作的要诀之一是:“没有哪只蚂蚁执掌大权。没有将军来指挥武士没有经理来使唤工人。它们靠的是个体之间的无数次互动,共同遵循着一套简单的经验法则——科学家称之为‘自组织系统’。” ④
群体传播亦是如此,网民个人的传播行为看似缺少了把关人和管理主体,但一旦参与到群体中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集合成一个群体后,却能在互动中确认自己的身份,随后按照这一身份自觉地去行动,主动遵循着群体内的一套隐性的秩序法则。这套隐匿的秩序,在无形中以价值观或某种权益为中心,为群体的行为设定了一个结构框架,以便信息在看似散漫的“无物之阵”中有迹可寻。以网民在微博、贴吧、论坛中的发言、互动为例,参与某个话题的讨论者,互不相识,发言也较为随意、自由。但关注这一话题、并转发、评论者,首先是对此话题感兴趣;在讨论者与传播者中,又可能会有支持者或反对者,这又会产生两个群体,两个群体在此进行博弈与互动,有可能分化为两个观点对立的群体,也有可能随着事件的进展最终达成舆论的共识,甚至还会产生舆论的逆转。无论最终产生何种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的交流与互动看似毫无章法,但总会以某种价值判断、观点态度为讨论中心,或者以争取某种权益为讨论焦点,在纷繁复杂的言论表象下面,掩盖着相对一致的态度、情绪或精神内核以及利益追求,吸引着参与者主动传播甚至生产信息。也即,参与群体传播的传播主体会主动判断这种传播行为是否符合自身价值观,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或者仅仅希望通过信息的传播完成自我身份的群体归属,抑或不被社会孤立,甚至仅仅是通过参与娱乐的狂欢获取某种谈资。
在传播个体通过互动建立起来的“自组织系统”中,个体的集结往往基于特定时空中相似的价值观,或是在某个事件中较为一致的立场和权益,暂时成为一个没有管理者的群体。此时,“地缘的社群被取代,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⑤这实际上为个体的发言、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平等、自由的机会,更能激发起个体参与传播的欲望,进而以此进行自我表达或争取某种权益。
在群体互动中,个体之间的情绪是最易相互影响的,而这种群体情绪的相互影响恰恰是助长信息变异的重要因素。“集合行为中信息传播的同时常常伴随着情绪的传播,而集合行为中的人们通常处于亢奋状态,行为之间容易相互模仿,情绪之间容易受其他人的暗示及整个氛围的感染”。⑥在此,参与个体的立场及价值取向决定着信息传播带来的是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是引发集结群体的狂欢,还是导致群体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传播带有某种盲从性,看似无序,甚至失控,以致信息变异为谣言,但却处于被某种特定价值观或权益支撑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结构中,正是这一结构的支撑,成为个体积极参与传播行为的动力,也为原本混沌的群体,搭建起了一条隐性的秩序链,成为看似无序,实则有据的传播形态。当结构支撑的价值观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时,群体传播将带来更多正能量,否则将引发更多的负面社会情绪,甚至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辩证认识:核裂变式的病毒传播产生的爆发力
微博的影响力往往体现在热点事件的传播中。热点事件发生后,微博会因其病毒式传播模式迅速引发集合行为,大量网民对同一主题的关注、参与,构成了“网络群体景观”,为舆论的达成提供了集结路径与物理空间。而能够令网民主动传播信息,促成核裂变式传播的内在动因正是群体成员秉承的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诉求。加之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介入,其传播力与影响力被迅速扩散,成为更强大的舆论合力。这种合力的结果,“要么建起自己的家园,要么毁掉一座城池”。
2014年9月28日,香港反对派和敌对势力突然宣布进行“占中”非法集会,并于9月29日晚宣布正式占领中环,试图以此扰乱香港秩序,破坏香港稳定。10月2日“占中”者与警方相互对峙,并提出了诸多无理要求。接下来非法“占中”者堵塞交通、阻碍政府人员正常办公、小规模暴力冲突等极端行为令事态进一步复杂化。相关消息在国内迅速发酵,成为国内主流媒体及网络媒体的追踪热点。截至12月中旬,“占中”行动已持续两个多月,其间涉及“占中”的新浪微博多达上百万条,微博舆论迅速形成并持续扩散,以交互式的传播形成逐级上升的舆论波。网民纷纷在微博中谴责“占中”者的破坏行径;继而支持市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呼吁理性爱国、爱港,提醒“占中”者不要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否则将成为“众矢之的”,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网民们的谴责声浪日益增高,维护香港秩序稳定、保护香港市民人身安全的诉求将群众凝聚起来,形成人数庞大的群体。同时,微信圈里谴责“占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分析“占中”行动的评论也被纷纷转发,至此,“占中”的非理性与破坏性已经显露无遗,敌对破坏分子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加之传统媒体的集中报道,与网络舆论的声音形成了共振,共同建构起了一个强有力的舆论场,这一舆论合力令“占中”者渐失舆论阵地。2014年12月11日香港警方对金钟地区的违法“占中”进行全面清场,持续了70多天的“占中”行动在舆论的一致谴责声中逐渐落下帷幕,极端分子搞乱香港的险恶企图随之被粉碎。这场反“占中”的舆论战,既保障了香港的稳定,也提升了国人的凝聚力,群体传播的爆发力与传播力彰显无疑。
再如,在“微博打拐”、“微博寻人”、“微博救助”“微博点赞”“微博益起来”以及各种微倡议等事件和话题中,微博以其“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有可能被关注”的传播理念为传播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传播平台,在传播者的联动之中,以及传统媒体、大V们的助力下,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传递了“人间有正义,人间有真情”的正能量。
在此,大众传播能将群体情绪、诉求或者价值理念,继续扩散给未参与到传播中的大众那里,两个舆论场的共振形成更强大的合力,共同影响社会舆论。此时,传统传播模式中以媒体为主导的上传下受的话语模式被逐渐弱化,“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已然来临。
然而,在群体传播助推社会舆论的同时,也有可能因其信源不确定而失真,因其集合行为而引发情绪感染,带来诸多负面社会影响。2011年3月11日,日本9.0级地震导致核泄漏事故,令人始料未及的却是此次事故居然在中国引发了一轮颇具声势的“抢盐风波”。经查,这轮风波源自于QQ群上的一条谣言。3月15日中午,浙江省杭州市某数码市场一位网名为“渔翁”的员工在QQ群上群发了一条消息:“据有价值信息,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并不断地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人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暂一年内不要吃海产品。”随后,这条消息通过QQ群、微博、论坛等途径被广泛转发。于是,号召“买盐”、“存盐”的消息开始铺天盖地地传播出来。与此同时,这条消息不仅通过网络传播,更因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迅速进入到人际传播渠道,以短信、电话、面对面口口相传的方式,传到了大街小巷,甚至是中国最偏僻的村落。于是,一夜之间,排队购盐成了市民们最紧迫的“任务”,多地商店、超市出现食盐脱销的局面。以四川省为例,仅3月17、18日两天,便销出2.9万吨,相当于2天之内卖出了近一个月的全省销量。武汉一郭姓市民甚至花高价购入1.3万斤食盐,被戏称为“抢盐帝”。随后,多个政府部门通过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渠道紧急辟谣,到3月19日,事件逐渐平息,各地抢盐潮告一段落,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然而,不少市民因屯盐过多,掀起了一小轮的“退盐潮”,但通过舆论及时引导,“退盐潮”很快平息。在这场抢盐风波中,一条本没有任何权威性、真假无从考证的匿名信息,只因内容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信息狂潮,促使信息接受者主动转变为信息传播者。这一传播过程无疑彰显了群体传播的巨大爆发力,但同时也折射出,滋生于群体传播的“谣言”的巨大威力,最终引爆了一场社会风波。除此之外,“蛆橘事件”令全国柑橘严重滞销、地震谣言令山西数百万人街头“避难”、“皮革奶粉”传闻重创国产乳制品行业……一系列产生于网络的谣言都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群体传播的威力足见一斑。
四、社会反思:“逐利诉求”、“群体极化”等现象令舆论生态面临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群体传播的这种爆发力也成为了某些不法分子借以牟利的筹码,甚至通过“造谣”、“传谣”进而形成了一条较为完善的黑色利益链。“部分谣言和有害信息因为契合微博用户的心理需求,从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巨大能量,产生高评论和高转发,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成为众所瞩目的社会舆论事件。” ⑦不法分子便借机乘虚而入,利用“情色”、“暴力”等博人眼球的话题迅速获得数量庞大的点击量,并通过抨击传统、夸大其辞、危言耸听等手段制造出迎合大众传播心理的话题,借助大众的二次转发产生社会轰动效应,以此实现牟利的企图。2013年8月,一则诋毁雷锋形象的信息在网上迅速传播,令“雷锋”原本的正面形象遭遇“滑铁卢”。随后有网民要求彻查诋毁雷锋形象的谣言制造者。经查,此谣言系以“秦火火”(原名秦志晖)、“立二拆四”(原名杨秀宇)为首,专门从事策划制造网络事件,蓄意制造网络谣言的网络推手公司所为。该公司为迅速提高知名度,蓄意编造了多起网络谣言:曾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在微博中故意编造、推送、散播中国政府花3000万欧元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该微博被迅速转发上万次,引发了网民对政府部门的不满情绪,致使原铁道部当夜进行澄清、辟谣;还曾利用“郭美美炫富事件”蓄意编造“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向红十字会捐款的谣言”,恶意中伤中国慈善事业。该公司凭借迅速崛起的知名度,成为了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微博等群体传播平台,以“删除帖文替人消灾、联系查询IP地址”等业务进行非法牟利。因秦志晖的行为社会影响恶劣,已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和互联网秩序,故被依法判处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⑧由是观之,群体传播的弱把关性、匿名性、门槛低、传者的自主性等特征同样令其颇具风险性,特别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令媒介伦理意识面临严峻考验。
同时,群体传播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也令社会舆论的客观性、真实性备受挑战。如前文所言,群体传播中的“情绪”往往会导致传播的偏向,成为非理性的众声喧哗。群体传播最终达成的“合意”,恰恰为带有主观色彩的个人情绪放大成为“社会化”的集体情绪提供了驱动力。同时,群体传播的匿名性、群体对“法不责众”的心理依赖,以及担心自己被多数人或某个团体孤立的心理诉求,令个体在网上的情绪更为激烈,态度更为极端,言论也更为大胆。于是情绪在传播过程中,最易引发“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所谓“群体极化”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⑨也即,如果群体成员的个体事先对某个事件或观点已经持有了某种态度,那么他会在讨论中通过情绪的不断宣泄来强化其立场和态度,最终团体的合意将有可能走向非理性“极端”,只有很个别的成员会改变自己的立场。正如凯斯·桑斯坦所言,“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意见。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⑩尽管并非所有的网络事件都会出现群体极化现象,但一旦触及到“民族主义”、“贫富差距”、“贪腐问题”、“伦理道德”、“政府失职”等话题,舆论往往会惊人地一致。而对网民的言论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多数发言是观点性的,评判性的,常常是某种特定心理情绪的释放,并非事实的客观陈述。显然多数个体在发言之前已持有了某种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通过群体合意的达成,强化了某种认知,也宣泄了某种情绪。基于此,网络群体的极化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社会问题的一种极端反映,“正确地看待和思考这些偏激言论,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利益调整、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也可能起到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出气筒’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毕竟是对民主的公共空间的破坏,无益于形成理性的舆论氛围,需要我们警惕和尽力规避”。[11]尤其是在某些有争议的社会议题的讨论中,群体的极化容易导致话题内容的“偏题”,最终成为毫无实质意义的情绪对立,甚至以激烈的“骂战”收场。除此之外,“网络暴力”现象也是群体极化的一种显著表现。从“虐猫”事件引发的对“人肉搜索”,到舆论一边倒的“道德审判”,原本线上的虚拟言论行为,已深刻影响了人的现实生活,“人言可畏”在群体传播时代更具破坏力和杀伤力。
正如开篇所言,“蚂蚁效应”爆发出的集群的力量既可以成就一个家园,也会毁掉一座大厦。“群体传播”亦如此,这一当下最具传播力的传播形态其建设性和风险性共生共存,“在推动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问题。对这种新现象、新特征、新趋势所预示的新时代,尤其是由此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既值得关注和欢呼,又需要警惕和理性”。[12]当社会信任感逐渐上升,信息公开制度逐渐完善,受众媒介素养逐步提高,媒体更加注重社会责任感时,谣言或将不会轻易肆虐,网络言论或将更趋于理性,互联网或将更有秩序,群体传播或将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隋岩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导;张丽萍系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博士。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语言对话语权、社会情绪、价值观的影响研究》(项目号14AZD1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③⑥隋岩、李燕:《从谣言、流言的扩散机制看传播的风险》,《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④彼得·米勒:《蚂蚁的群体智慧》,《青年科学》,2008年11月
⑤⑨⑩[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第37、47、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中国微博发展报告(2013-2014)》第277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⑧案例相关数据参考《新闻晨报》2013年8月21日报道《公安部严打网络谣言 网络红人“秦火火”被拘》,http://news.sina.com.cn/c/2013-08-21/074028006070.shtml;新华网2014年4月17日报道《网络红人“秦火火”一审获刑3年》,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04/17/c_1110283074.htm.
[11]戴笑慧、冷天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简析》,《新闻记者》2009年第7期
[12]隋岩、曹飞:《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49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