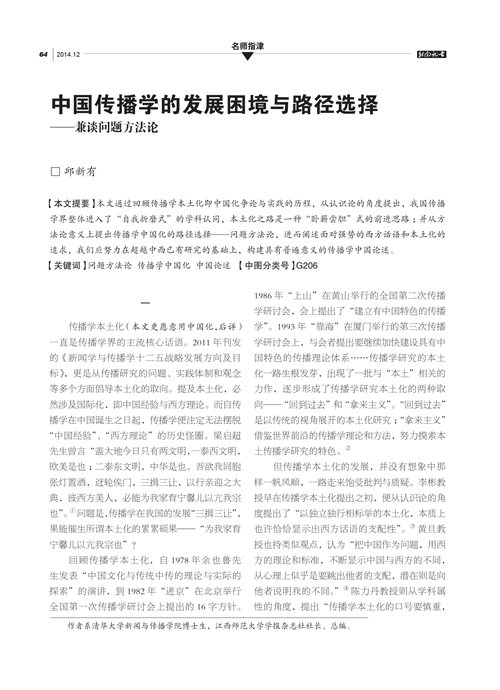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与路径选择
——兼谈问题方法论
□邱新有
【本文提要】 本文通过回顾传播学本土化即中国化争论与实践的历程,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我国传播学界整体进入了“自我折磨式”的学科认同,本土化之路是一种“卧薪尝胆”式的前进思路;并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传播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问题方法论,进而阐述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和本土化的追求,我们应努力在超越中西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学中国论述。
【关键词】 问题方法论 传播学中国化 中国论述
【中图分类号】 G206
一
传播学本土化(本文更愿意用中国化,后详)一直是传播学界的主流核心话语。2011年刊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十二五战略发展方向及目标》,更是从传播研究的问题、实践体制和观念等多个方面倡导本土化的取向。提及本土化,必然涉及国际化,即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而自传播学在中国诞生之日起,传播学便注定无法摆脱“中国经验”、“西方理论”的历史怪圈。梁启超先生曾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①问题是,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三揖三让”,果能催生所谓本土化的累累硕果——“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回顾传播学本土化,自1978年余也鲁先生发表“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到1982年“进京”在北京举行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16字方针。1986年“上山”在黄山举行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会上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1993年“靠海”在厦门举行的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一路生根发芽,出现了一批与“本土”相关的力作,逐步形成了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两种取向——“回到过去”和“拿来主义”。“回到过去”是以传统的视角展开的本土化研究;“拿来主义”借鉴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努力摸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②
但传播学本土化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一路走来饱受批判与质疑。李彬教授早在传播学本土化提出之初,便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③黄旦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把中国作为问题,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不断显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从心理上似乎是要跳出他者的支配,潜在则是向他者说明我的不同。” ④陈力丹教授则从学科属性的角度,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口号要慎重,某学就是某学,一定要某国的什么学,其实很难成学” 。⑤
如果说“要把传播理论本土化,作为意愿,我相信没有哪个华人传播学者会表示异议”。⑥上述学者论争的关键不在于本土化本身,而在于,“传播理论是否真的可以中国化或者华人社会化?这是一个永远的梦想,还是有现实基础的理想?我们如何理解传播理论本土化的问题?”⑦
本土化的论争,似乎并没有影响学者们对于本土化的实践探索。一方面思想争鸣,各有千秋。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各自耕耘。或把西方的经典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翻译、介绍、评论,如《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⑧《传播学原理与应用》;⑨或从传统的文化、史实中构建本土的传播学,如《华夏传播论》⑩《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1]或进行本土意义上的探索,用中国的经验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补充、检验、论证,如“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分析”、[12] “论中国乡村人际说服传播的三重情境”。[13]但上述研究,均自觉或不自觉陷入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
中国传播学研究对美国传播学著作有很大的依赖性,缺乏学术自主,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过于强调接轨、国际化, 移植或套用美国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而很少有新的构想和思路。正如贺雪峰指出,中国社会研究“存在过早学科化、技术化,缺少整体性反思,热衷于用中国经验与西方社会科学抽象对话等问题。……中国经验复杂而庞大,基本上所有的现象都是多因多果,而且这些多因多果多未经过充分的定性研究。在这种前提下,许多研究却贸然进入技术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因此,往往会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时,这些错误的结论又因为有数理模型和大量数据,貌似科学,实则更容易蒙蔽人”。[14]其实,对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传播学“何为本土化”、“如何本土化”等问题并没有一个结论性的清晰答案。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化的呼声虽不绝如缕,而本土化的进展却显得困难重重。究竟在哪些方面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在哪些方面又突破他们的桎梏,转而采用中国自身的理论和术语体系,到现在还是一个学术界激烈争论中的问题。吴文虎[15]、陈韬文[16]等学者都提出要从现代传播理论出发,先确定一个理论模式,然后使之作用于我国的传播实践活动,在其中寻找理论的“变异”,从而发现我们自己的传播个性,再对普遍适应的理论进行修订,这是所谓的“理论移植”;而陈力丹[17]则反对单纯把西方理论跟中国的传播实践简单对接,“将几个现成的模式或‘论’简单地用来说明和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不是学术”。孙旭培[18]则主张要先对中国的传播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强调要通过对大量素材共性进行提炼,升华出一批属于中国自己的传播学理论。
但由于在观念上没有彻底解决本土化研究理念上的根本症结,因此当前内地的传播学研究中,实际上仍明显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正如吴文虎所言:“谈传播理论的,有的仅止于以传播的实际事例作为佐证,很少进行深入的解剖;再加上行文越来越深奥难懂,给人以宁为‘阳春白雪’,不屑‘下里巴人’之感,而论及传播实务,有的又未能提高到理论的视角加以展开。” [19]中国传播学研究,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翻译到引进,再到借鉴,但是,由于中国传播学对美国的传播理论过于依赖,所以,即使进入“三十而立”的“成熟期”,却不见独创性研究成果。以前,我们一直在消化、吸收西方的现代传播理念和理论,学者们大量的工作是注解现代传播理论中的概念和定律,虽然有一些针对中国自身传播实践的研究活动(自然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都没有自己的理论支撑,要么仍是图解西方的观念,要么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成为单纯的实证考据。实际上,所谓社会研究和以新闻传播研究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可能不可能或必要不必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已有半世纪之久历史发展的活的传统。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今日仍具绝对宰制力和笼罩性影响力的大氛围下,这一土生土长的中国社会研究传统今后是否还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抑或像其他许多地区的本土化学术发展一样,最终仍逃脱不了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命运?所谓的中国经验到底是什么?
二
问题远未止于此。如果说本土化有论争,学界同仁亦有探索,这是传播学界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这并非自然界常见的日晒、风吹、雨淋,这是传播学本土化进程中特有的行为趋向,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种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话语。
所谓“本土”,是相对“异邦”而言,中国传播学本土化,是对“美国传播学的国际化”而言。其“本土化”构建的前提,本土即是对自我的否定,意即本土的研究是没有抑或还没有实现本土化。言外之意是非本土化是普遍意义上的学术知识体系,是学习、参考、借鉴、吸收的对象。这是传播学科成立之初,直至如今的现状。
传播的本土化,看似是学者基于学术的追求、民族的情感自觉的行为,更深层次意义上而言,是为了构建一种学科的认同。而构建一种认同,往往需要与他者的对比。而他者的存在,往往是受贬抑的存在。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的绪论中,阐述出了“西方”的确立,认为“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尽管近来在日本、韩国和印度支那的冒险活动到现在应该使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更清醒、更现实的东方意识”。[20]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我国的传播学引自国外,打一开始,面对西方的经典理论体系,便是“顶礼膜拜”,更遑论“批判”。而伴随着传播学科在我国发展至今,本土化的追求,意欲创建本土化的传播学。在与西方不断相碰撞的思想、知识、理论的交汇中,并没有出现坚强的“东方意识”,反是更清醒、更现实的“西方意识”。
我们殊难想象,在本土化的追求过程中,我们面对所有传播学的经典知识理论体系均是西方的,乃至于“民主”、“科学”这样人文社科的最基本的词汇。我们拿着西方的经典理论之矛,着意美化着本土化构建的盾。如果盾的本身的购置均来自本土,只是表面的美化来自“异邦”,倒也差强人意。关键是事实相反,材质来自西方,美化来自西方,只是在盾的边边角角做了些东方的修补。在一个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着力本土化的同时,从里及外均是西方化。因为还从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的原创性的传播理论。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其痛苦与绝决不言而喻。
我们回忆近代以来中西方的文化交往,“民主”与“专制”、“进步”与“落后”、“科学”与“迷信”……我们无一例外,把“丑陋”、“鄙夷”、“否定”留给了自己,把“先进”、“赞许”、“肯定”留给了西方。这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文化认同。自我否定并非抛弃中华文化,而是在“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之后,进行一种文化上的融合与创新。
从中西方的文化交往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传播学科的发展身影。整个传播学界在本土化的进程中,是否也已经进入了一种自我否定式抑或自我折磨式的学科认同。学科的发展过程,给了每个传播学者一个“本土未有穷期、创新永未止步”的痛苦与苦闷的定位。这是一种“卧薪尝胆”式的前进思路。通过自我的折磨与困境,激励自己,最终迈向成功。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人是否都能成为越王勾践?希望的未必能够在实践中像想象的那么成功!
三
如果说自我折磨式的学科认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阐发传播学本土化所带来的发展困境。那么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解决这样的困境,是亟需解决的新话题。1965年毛泽东在武汉数次谈及的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 [21]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和本土化的追求,我们应努力构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你打的有我的”研究取向,即在超越中西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传播学的中国论述。
自传播学传入我国至今,无论是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实证主义,还是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各种范式在我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或多或少在我国传播学发展的星空留下了精彩的一瞬。然而,时至今日,按照“海外学者对科学的狭义定义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并没有留下什么符合经典意义上或科学意义上的理论”。[22] “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 [23]方法论意义的本土化,是本土化论题最为直接的内涵。笔者认为,本土化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体现独立的本土问题意识,社会研究应该首先正确地提出反映本土立场的“真问题”,而不是过度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研究中流行的理论议题。而应该找准问题,从有价值的中国经验出发,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而不是仅仅把精力花在寻找中国经验的独特性然后将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就此而言,我们更愿用“中国化”而非“本土化”这样的概念与概括,就像美国的传播研究及其理论实际上是“美国化”而非“国际化”一样。
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看,只有确切地知道问题产生的过程,才能明白何为问题。所以,笔者首先将问题定义为社会事物所表现的各种现象与人们对该社会事物的预期之间的差距。[24]我们对传播现象进行观察时,传播现象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该事物的初始状态,而人们对此是有预期的。正是因为有预期,传播现象的初始状态与人们的预期状态之间往往会有差距,这种差距有时表现为常态生活逻辑的日常现象,即为正常问题,有时表现为焦点性的突发事件,即为非正常问题。差距越大,问题越严重。有价值,有意义,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为研究问题,没价值,没意义,不值得研究的问题为日常问题。现实中,当正常问题带有一定普遍性时,也会成为研究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即为问题的求解过程,求解过程就是问题从其初始状态向预期状态转化的过程。
如(图1 图1见本期第67页)所示,自初始状态I向目标状态T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有1、2、3、4甚或更多的状态出现,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多个问题P1、P2、P3、P4等,研究者必须有效准确判断选择何种问题进行研究、去除非研究问题,继而指向目标状态,达成差距缩短直至为零(即问题解决)。
为了使研究更加科学有效,笔者根据问题的表现特点从策略上将研究问题划分为正常问题和非正常问题,同时总结提出经验研究对问题处理的一般方法:通过将“正常”问题“非正常化”,将“非正常”问题“正常化”,建立案例研究的问题意识,将个案研究推向深入。
将“正常”问题“非正常化”就是将正常问题进行“问题化”处理,指的是对一般事物发展中表现为常态生活逻辑的问题,放在一种非常态的背景中。正常问题非正常化的技巧是:首先,将常态生活逻辑中的问题进行问题化处理。其次,进行关联考察。找出研究对象对正常问题思考的逻辑差别等问题。可以从两个维度着手。一是横向比较研究,将共时性的问题横向拓展,把相同时间内出现的同一问题进行关联性思考。二是纵向深入研究,将历时性的话题纵向深入,对研究对象的过去、现在、将来可能的表现做一历史考察。比如,目前乡村制度的表现形式,在古代、近代、现代是怎样演变而来,预测将来的可能发展趋势。
把非正常问题正常化, 即把非正常问题放在正常规则中思考,将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找出来。非正常问题,通常的表现是焦点性事件。非正常问题正常化的技巧,首先是要从常态生活逻辑中去理解问题,找到非正常问题发生的必然性。其次,从常态生活逻辑中找到了非正常问题发生必然性后,从中了解事件背后的社会基础。最后,当我们把个案的研究引向深入后,对非正常问题(焦点性事件)背后的原因进行透彻分析,使我们在非正常事件(焦点性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找到更具意义知识建构点,这样新的知识就发现了。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在研究方法论上,尝试了上述的经验研究的问题方法论(图2 图2见本期第68页),从问题出发,开始对社会事物现象进行考察,寻求现状与期望之间的差距,差距的判断可以有正常问题非正常化、非正常问题正常化等不同的具体解决策略,该差距的解决过程,即为问题求解之过程。从问题出发,在问题求解过程中,知识错位起到关键作用,知识错位点可能就是问题的切口,有利于发现问题,更由于知识结构的差异可以起到过滤问题的作用,留下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使得研究顺利进行。
基于上述问题方法论,笔者在研究成效上取得了一些原创性研究成果如科层政府组织传播过程中的“末梢现象”;[25]乡村人际说服传播过程中的“多重情境叠加”;[26]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的心理距离”;[27]村庄关系间的“摩擦系数”,[28]等等。
笔者认为,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与现实,回到学术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即问题的本土意识,逐步建构起超越中西的具有普遍意义中国论述,才是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取向的突围之路。“这是一次探索,希望能找寻到一个出发点。这是一项新的探究,盼望能找出一个研究的方向与范畴。在登堂入室之前,希望能找到入口”。[29]■
注释:
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
③李彬:《反思: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④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中国大陆传播本土化路径之批判》,“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传播学——海内外华人传播学者对话会议”与会论文,2010年10月,复旦大学
⑤[17]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⑥⑦陈韬文:《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载《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施拉姆著,余也鲁译:《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第2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
⑨[29]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⑩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2]张国良:《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6期
[13][26]邱新有:《论中国乡村人际说服传播的三重情境》,《现代传播》2011年第12期
[14]贺雪峰:《回归中国经验研究——论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的构建》,《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07年第1期
[15][19]吴文虎:《“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结合中国的传播实践》,载袁军、龙耘、韩运荣编:《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6]陈韬文:《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国传媒报告》2002年第2期
[18]孙旭培:《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载袁军、龙耘、韩运荣编:《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0][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1~2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第448~4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2]祝建华:《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载李彬等编:《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第7~8页,三联书店2012年版
[24]这是笔者应邀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所做的新闻传播学术前沿报告“问题方法论:经验研究的问题策略与处理技巧”时提出的问题概念。报告过程中,师生们提出了精彩问题和宝贵建议。关于此论题,在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课堂上也做过小型讨论,刘赣洪老师和同学们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25]邱新有、肖荣春、熊芳芳:《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缺失现象的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27]邱新有、金若晗:《传播距离与村民接受选举信息效果关系初探》,《求实》2010年第9期
[28]参看“村委会选举与乡村社会稳定”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报告。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社长、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