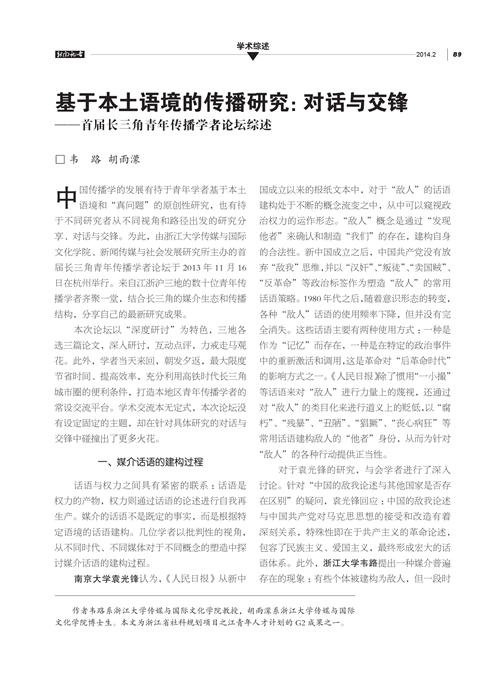基于本土语境的传播研究:对话与交锋
——首届长三角青年传播学者论坛综述
□韦路 胡雨濛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有待于青年学者基于本土语境和“真问题”的原创性研究,也有待于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和路径出发的研究分享、对话与交锋。为此,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主办的首届长三角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于2013年11月16日在杭州举行。来自江浙沪三地的数十位青年传播学者齐聚一堂,结合长三角的媒介生态和传播结构,分享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次论坛以“深度研讨”为特色,三地各选三篇论文,深入研讨,互动点评,力戒走马观花。此外,学者当天来回,朝发夕返,最大限度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充分利用高铁时代长三角城市圈的便利条件,打造本地区青年传播学者的常设交流平台。学术交流本无定式,本次论坛没有设定固定的主题,却在针对具体研究的对话与交锋中碰撞出了更多火花。
一、媒介话语的建构过程
话语与权力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话语是权力的产物,权力则通过话语的论述进行自我再生产。媒介的话语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根据特定语境的话语建构。几位学者以批判性的视角,从不同时代、不同媒体对于不同概念的塑造中探讨媒介话语的建构过程。
南京大学袁光锋认为,《人民日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报纸文本中,对于“敌人”的话语建构处于不断的概念流变之中,从中可以窥视政治权力的运作形态。“敌人”概念是通过“发现他者”来确认和制造“我们”的存在,建构自身的合法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敌我”思维,并以“汉奸”、“叛徒”、“卖国贼”、“反革命”等政治标签作为塑造“敌人”的常用话语策略。1980年代之后,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各种“敌人”话语的使用频率下降,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话语主要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作为“记忆”而存在,一种是在特定的政治事件中的重新激活和调用,这是革命对“后革命时代”的影响方式之一。《人民日报》除了惯用“一小撮”等话语来对“敌人”进行力量上的蔑视,还通过对“敌人”的类目化来进行道义上的贬低,以“腐朽”、“残暴”、“丑陋”、“猖獗”、“丧心病狂”等常用话语建构敌人的“他者”身份,从而为针对“敌人”的各种行动提供正当性。
对于袁光锋的研究,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针对“中国的敌我论述与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区别”的疑问,袁光锋回应:中国的敌我论述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和改造有着深刻关系,特殊性即在于共产主义的革命论述,包容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最终形成宏大的话语体系。此外,浙江大学韦路提出一种媒介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个体被建构为敌人,但一段时间后又被建构为朋友。浙江大学李红涛认为:这可能就是“实际的敌人”和“绝对的敌人”的区别。“绝对的敌人”是基于绝对的意识形态,“实际的敌人”则是基于工具性的需求。对于话语分析这一研究方法,南京大学胡翼青强调:单纯话语分析只是语言学层面的内容,但要进行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还原还需要田野调查、相关史料的搜集等研究方法。用话语分析更多的是讨论关于敌人的想象,但很难讨论话语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白红义以“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江苏启东排污工程”、“浙江宁波PX工厂”三起邻避冲突事件为例,对中国媒体的“抗争新闻范式”进行研究,探讨媒体对抗争者、政府官员和邻避事件本身的话语建构。研究发现:对抗议者,媒介采用了四种呈现策略:呈现其理性、审慎的一面;着重展示其弱势和无辜;苦难叙事;对其进行模糊身份的处理。另一方面,对抗议对象,媒体则多予以“缺席”与“模糊”的处理方式。通过以上文本和话语分析,研究者认为,抗争新闻范式的确存在,其形成是因为记者试图突破政府对事件的解释框架,展现出一套有别于官方媒体的专业操作规范、理念和文化。但在此之外,时刻在场的国家仍是决定抗争议题能否得以呈现的最大结构性因素,这就决定了媒体的抗争新闻范式只能在“有限的鸟笼内”施展。
对白红义的研究,与会学者主要从媒体建构的主观性方面进行了讨论。精英媒体与其他媒体之间,国家媒体和地方媒体之间的新闻报道范式的确存在区别。尤其是都市报媒体要与同行竞争,会绞尽脑汁选取角度来进行报道,以至于可能过分拔高事件意义。对此,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认为:每个人都会利用自己工作范围内的资源来提高声望,记者也是如此,记者采访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将社会事件变成一种景观,来获得“成名的想象”,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报道的文本和话语建构。
南京师范大学卞冬磊以晚清读书人刘大鹏的日记为史料,从报纸阅读中探寻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报纸话语建构了“国家”概念,使人超越“立足之地”,进入到一个由具体事务、“充满意义的真实体验”构成的国家空间。日记显示,报刊出现前,刘大鹏的空间认知和身份认同主要停留在“乡里空间”;“省”、“省外”的图景模糊;对“天下”亦只有想象式或道德化的认识。直到1902年,《晋报》创办并成为刘大鹏的主要阅读报纸,他的“符号空间”里终于浮现出“国家”概念。与过往的“道听途说”相比,报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建立在具体事务基础上的国家形象。此外,报纸建立的“帝国主义”威胁话语普遍流行,强化了人们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待的意识。“知有国家”是近代国家意识形成的基础。
对于“文本表演与实际运作是否存在分裂”的疑问,卞冬磊认为:阅读史的研究恰恰是为了弥补表达和实践之间的鸿沟。胡翼青补充认为:话语建构了想象力,建构了实在。研究可以基于所获得的经验资料来分析研究对象表述的内容是怎样建构了他们的行为、世界观和想象力的。
二、互联网与媒介参与
媒介参与是受众主动的媒介介入行为,受众超越简单“媒介使用者”的角色,更积极地利用媒介,对媒介内容施加影响。尤其是在新媒体语境中,受众的媒介参与行为更加广泛,参与内容包括提供新闻、表达观点、娱乐等;参与动机从爆料、个体维权到服务公益。在媒介使用和参与过程中,形成一系列值得研究的传播问题。
浙江大学刘于思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探究中国网民的媒介参与效果。互联网对个体的赋权为集体记忆带来了公民化书写的可能性,进而与“官方”生成的集体记忆产生竞争和对话。研究者采用网络调查方法,从历史事件本身的性质和网民的个人差异出发,探索能够影响中国网民的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程度及传播行为的一系列因素。研究发现,网民在媒介参与的过程保持了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传播,其中年龄、事件关联程度、信息环境发挥较大的影响。
对刘于思的观点,胡翼青提出疑问:个体记忆是怎样上升为集体意义的。李红涛也补充提问:互联网为基础的集体记忆除了表现在以网民作为研究对象上,是否还体现在其提供了一种民间记忆甚至反记忆的生成空间。对此,刘于思回应:新媒体的记忆状况的确很难通过一次调查去反映,之后的研究可能需要进行重复的测量,并用思辨的方法来弥补。
南京林业大学陈相雨通过解析网络空间中的符号生产过程,分析了网民在网络活动中面对精英霸权的“视觉抗争”。研究认为,虽然互联网的崛起将社会的符号生产带入“草根书写”时代,但精英的霸权仍然十分强大。草根民众为了博求集体围观,避免诉求议题的被淹没,往往采取非常规、有争议的方式,扩大符号生产的社会影响,即“视觉抗争”。但是,由于此方式存在畸变倾向,会产生民粹主义意义上的反动性,尽管它对社会秩序可以产生正面影响,但此影响是修正性的,不具有革命性。
复旦大学周葆华通过随机抽样,从经验层面上厘清互联网使用与中国公众的意见表达之间的关系,并从效果的同一化与差异化角度出发,探究这些关系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与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在全国范围内对公民参与有正向影响。研究不但证实了个体层面的政治兴趣对公民参与的独立影响,也证实了其对互联网影响公民参与效果大小的调节作用,提示了在中国整体意见表达和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背景下,网络使用会加大业已存在的“参与沟”。对该研究,与会学者从“政治兴趣是怎么形成”、“政治兴趣与新媒体使用谁因谁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三、网络社交与新的人际传播结构
特定群体的传播形态具有结构化特征,形成传播网络。在网络中每一个体扮演不同的传受角色,并呈现两级传播等传播模式。在新媒体视域下,“网络社交”行为又形成新的人际传播结构,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上海大学陶建杰通过探索性的个案研究,以整体网的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结构,获得群体内的六个人际传播网络:老乡关系网、工友关系网、衣食住行信息咨询网、医疗保健信息咨询网、维权社保信息咨询网、子女教育信息咨询网。研究发现:从微观结构看,农民工的人际信息传播网中存在一些“意见领袖”,性别、工作稳定性、居住方式是决定农民工能否成为“意见领袖”的主要因素;从中观结构看,农民工人际传播中的小团体结构稀疏,存在着众多相互重叠的“派系”;从宏观结构看,网络中普遍存在边缘-核心结构,并有一定程度的“小世界”特征。
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对于人际传播理论的特殊意义”问题,李红涛认为:首先,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传播是乡村社群型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而到了城市之后,人际传播受到了社会公共传播大环境的影响,这体现了传统中国人怎么向现代人转变,包含信息结构的变化;其次,该研究也可用于探讨农民工怎么融入社会的问题,因为传播的融入是在所有的制度和硬件的融入之前首先应该解决的。
南京大学付晓燕进行一项基于30位中国网民生命史的经验研究,探索童年经验对网民“网络社交”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家庭在现实生活中对个体社会资本创造的影响延伸到了个体的网络空间。开放与自主性的童年成长经验有助于青年更勇于承受网络交往的风险,更善于透过SNS来拓展虚拟社交关系。相对地,成长于不稳定与缺乏亲密联系的童年经验的群体多数难以在社交网络上扩展“弱关系”,无法有效利用“虚拟社交”的优势来提升个体的社会资本。互联网时代的“宅男宅女”现象并非因互联网技术而起,其真正的成因在网络空间之外,因为现实生活中缺乏稳定、亲密的情感支持网络,导致这些青年与现实社会疏离。
对于韦路“研究是否放大了家庭体验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因素”的疑问,付晓燕解释,在研究之前没有对儿童时代体验的重要性有所假设,也不会对研究对象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但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些个案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个体童年的创伤对其网络交往所带来的影响。
四、小结
经过激烈的对话与交锋,本次论坛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媒介话语不是史料,而是研究材料,是媒体表述的结果,对媒介话语的考察应结合符码的社会语境。话语分析不能拘泥于文本,还需要结合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需要进行从文本到行动者的研究。
第二,传播学者以各自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切入问题,虽存在分歧,但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的旨趣是一致的,在这一过程中完全可以相互补充和印证,这是产生对话和交锋的基础。
第三,以往传播学理论更多是与西方语境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大量值得研究的传播问题,为中国诞生基于本土语境的传播理论提供了契机。青年一代的传播学者要有创立原创传播理论的雄心。
最后,经过近十年本土传播学者的努力,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原创性的传播研究成果。现阶段可以将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和小结,通过出版的形式进行整合与推广,以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者韦路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胡雨濛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之江青年人才计划的G2成果之一。